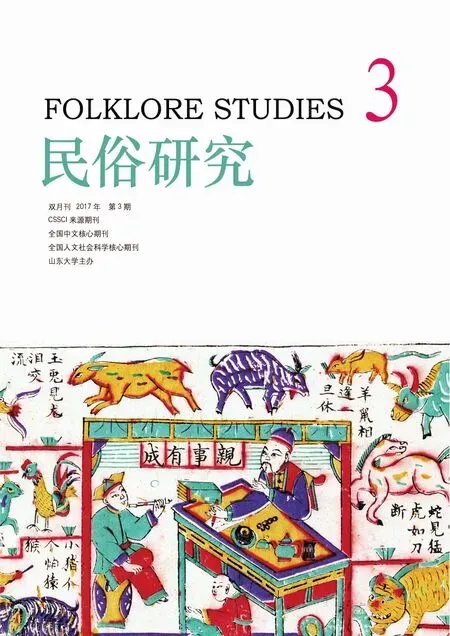族群认同传说流布的边界性
——以湘西土家族八部大王传说为例
金 晶
族群认同传说流布的边界性
——以湘西土家族八部大王传说为例
金 晶
八部大王又称八部大神,是居住在酉水沿岸的土家人公认的祖先神之一,其原型可以追溯至较早时期的部落英雄。有关传说在漫长的时光中被完善,且局限于湘西境内土家族的居住区域,并以龙山、保靖、永顺等县为核心区域。其传承的显耀程度,与土家人居住的密度成正比。在传承的核心地区,其神庙更是鼎盛一时,比比皆是。八部大王的传说不仅有单纯的民族性,而且还具有区域社会性,因为在此区域界线之外,即便是同一民族也无法将此传说内化成自我族群的历史记忆。而生活在传播区域内的人们,则出于日常知识与交往的需要,通过这一传说而强化了族群身份的认同意识。
族群认同;历史记忆;传说区域;传承方式;传播边界
八部大王,又叫八部大神,是由湘西地区土家族部落英雄演化而来的祖先神。传说中涉及湘西土家人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所属族群,因此具有族群认同的性质。据土家神职人员口口相传的“梯玛歌”记载,“涅壳赖”“热潮河舍”“里都”“苏都”“西梯佬”“西可佬”“拉乌米拢溪也所也冲”“背接也会也拉飞列也”八兄弟是八个部落的头领,其中老大名叫涅壳赖,是八部大王。而传说的异文中,八部大王是湘西土家三王“彭公爵主、向老倌人、田好汉”中的向老倌人(原名向宗彦),也是现居湘西的向氏土家人的祖先。
瞿州莲教授在《民间传说与区域历史构建》一文中,运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观点,在关注传说所记叙的历史时,重点了解其反映的现实社会关系如何形成。瞿教授将民间传说视为民众的历史记忆,以传说中的社会秩序关照真实历史时段中的区域历史,从而达到了重构区域历史的目的。①瞿州莲:《民间传说与区域历史建构》,《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传说的情节与历史时段的关照,可帮助我们了解一定区域内族群间的关系与互动。本文试图从民俗学的角度入手,通过传说传承的不同方式及其对区域历史的建构,对传说流布边界性的形成作进一步研究,并从传说传播区域边界的变化,看同一生存空间中族群之间的互动与身份认同。
一、传说的内容与流变
八部大王传说仅流传在聚居于湘西的土家人中间,是湘西土家人信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当地的文史资料以及相关研究叙述②黄柏权在其《土家族摆手活动中祭祀神祇的历史考察》(《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中,就提到了八部大王传说与信仰在龙山县域内的传播,文中着重提到的两个地点就是龙山县洗车河流域和长潭的着落湖地区。石应平在《湘西土家“八蛮”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一文中也提到,“在湘西北地区,民间历代流传其先民有称为‘八蛮’者,或叫做‘八部大神’和吴著冲。这里的土家人都敬奉他们,称其为迁入湘西的始祖”。另外,民间故事集成中的《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分卷》《保靖县资料本》等书中,关于八部大王传说采集对象和采集地的记录,都可看作传说流传区域划定的依据。,传说流布范围集中在土家人聚集的湘西北方四县,即龙山、保靖、永顺、古丈等县的酉水流域。与传说有关联的事物,也集中分布在这一区域内,且数量可观。根据现存关联事物的分布,我们可大致勾勒出传说在湘西流布的区域边界。
(一)具体分布区域
龙山与保靖两县内的酉水流域,是八部大王传说与信仰流布的核心区域。其中龙山县的流布范围是与保靖县交界的长潭乡,而保靖县的流布范围则集中在碗米坡镇的沙湾、马蹄、水坝洞等村。传说在保靖县的流布范围广、面积大,且关联事物多;碗米坡镇更是县内八部大王传说流传最为密集的区域,是八部大王庙遗址所在地。建在河岸边的八部大王庙,与镇中沙湾村隔河相望。
八部大王是八峒之首,八个部落推他为王。这里的水路上至四川酉阳,下至湖北来凤。过去(陆路)交通不发达,就靠酉水运送物资。(跑船的人们)经过这里,都要下船来祭八部大王,所以(八部大王庙)香脚比较宽。*被访谈人:魏品富,男,1965年生,沙湾村土家族人;访谈人:金晶;访谈时间:2013年1月12日;访谈地点:碗米坡镇沙湾村八部大王庙遗址。
八部大王在湘西土家祖先神谱系中排在首位,土家人对其祭祀十分看重。祭祀八部大王的时间在春节后,每年一小祭,三年一大祭。除此之外,遭遇变故时人们也会带上祭品,到八部大王庙进行祭祀以求保佑。这种日常的祭祀往往以香纸、活禽作为祭品,笔者在沙湾八部大王庙遗址调查时,就在不远处发现祭祀后遗留的带有鸡血的新鲜鸡毛。若是天气恶劣无法过河,沙湾村村民也会选择正对庙址的方向杀牲祝祷,以求仪式灵验。由此可见,八部大王庙虽只剩下遗址,但在当地仍具有影响力。
每年正月里,十五或社日,都有很多人自发的来祭拜……有钱的杀猪杀羊,用三牲祭祖;没有钱的用牛、狗、猪三个(牲口)脑壳供奉,代表三牲。还有(通过)唱戏、跳摆手舞、跳铜铃舞(这些方式)的,花样比较多。*被访谈人:魏品富;访谈人:金晶;访谈时间:2013年1月12日;访谈地点:碗米坡镇沙湾村八部大王庙遗址。
八部大王信仰具有年龄的局限性,因此传说的流布边界在空间上被缩小。年轻的土家人由于时代、受教育程度等因素,逐渐脱离了传统土家文化的影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原始农耕生活方式的取代以及日益进步的科技,也使人们对于原始崇拜和信仰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二)传说关联事物
传说的流传还表现在节日祭祀、表演活动、庙宇、神坛等建筑的分布上面。作为传说流传的核心地带,碗米坡镇内存在很多与传说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事物。如碗米坡镇的马蹄村,以及马蹄村附近的“杀鸡坡”(萨济坡),沙湾村附近的八部大王庙遗址等等;还有与传说相关,由传说衍生而来的一些祭祀仪式或艺术形式,如土家摆手舞、梯玛神歌以及八宝铜铃舞等等。
这些事物中有些真实可见,如只剩下遗址的神庙和现存博物馆的“八部大王”残缺石匾。有些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以口头形式世代相传,如“梯玛神歌”中对八部大王的记载、八部大王祭中涉及的祭祀仪式。它们有的或许随传说的流传杜撰产生,带有附会色彩,如保靖县碗米坡镇萨济坡、水坝洞等地名的由来,或多或少是传承者对传说人物、地名的附会。有的却真实存在,甚至仍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如土家人的摆手舞、八宝铜铃舞等,它们作为祭祀八部大王仪式的组成部分,其中涉及的场地——摆手堂以及祭祀用具等都与传说有着关联性。这些传说的关联物无疑从侧面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八部大王传说流传和影响的区域范围。这些与传说相关事物的具体名录、所在地以及类型详见表1:

表1 八部大王传说关联事物一览表
①保靖县征史修志领导小组:《保靖县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305页。
②转引自胡炳章:《土家族文化精神》,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06-107页。
③在保靖县马蹄村村民向魁益的叙述中,“萨济坡”和“马蹄枯”这些地名都与八部大王有着密切的关系。“萨济坡”,现在人都称之为“杀鸡坡”,认为坡太高了,人从坡下爬到坡顶的时间,杀个鸡都能煮熟了。但其实应该是“萨济坡”,“萨济”两个字,来源于八部大王父亲的名字。“马蹄枯”之所以在地名中有马蹄两个字,是因为八部大王在这里放马,因此地上到处是马蹄印。
(三)传说的流变
不同时代的政治对传说都发生影响并造成了传说的改变,从而构成了传说纵向传承的脉络,特别是反映出这一传说从部落神话向王朝历史传奇转变的印记。
据保靖县马蹄村村民向魁益的讲述,土家先人萨济和帕尼没有后代,四处求神拜佛后由神仙指点生下九个肉球。肉球被遗弃,并由龙母孕育出八兄弟和小妹妹。兄弟八人从龙母处学得本领,消灭了孽龙犬申、麻阳猖鬼和库其人熊三害,并收服各个部落当上部落之首。八兄弟威名在外,代皇帝出征打仗。得胜归来却遭到皇帝的猜忌,被算计毒害而死。最小的妹妹为了推翻皇帝的统治、给哥哥们报仇,当了新皇帝的皇后。新帝在小妹妹的辅佐下夺得江山,将哥哥们追封为“八部大王”。*被访谈人:向魁益,男,1941年生,马蹄村土家族人;访谈人:金晶;访谈时间:2013年1月12日;访谈地点:向魁益家中。传说主要包括四个叙事单元:第一,英雄弃子;第二,动物抚养;第三,抗敌立功;第四,遭受毒害。除此之外,还有分别以涅壳赖和向老倌人作为主角的传说异文,情节大体一致,这里不再复述。
传说中出现的一些场景,可以看作土家先民对某一时期生活经历的集体记忆,是对史实的关照。如流传在马蹄村的传说中,八兄弟铲除的孽龙“犬申”常做的坏事就是发动水灾。这种描述可看作原始时代洪水泛滥的历史记忆以及对这种历史记忆艺术化的重现和记载。而以涅壳赖和向老倌人为主角的传说,则被赋予更具体的历史时段。涅壳赖的传说开头点明,他是宋朝湘西土人的首领,参战对抗的敌人是辽兵。传说的铺排与宋朝的史实吻合,英雄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国家危难的任务。向老倌人的传说也是如此,不同的是,此版本的历史背景有宋、明两朝这两种说法,此处不一一赘述。
二、传说的传承方式
传说作为一种叙事,它的流传方式不仅仅局限于以口头语言作为载体的流传,还有以文字为载体的流传以及以现代传媒作为载体的流传方式。多样的流传方式为传说带来新的变化,也决定了传说影响范围的大小。新媒体的普及、年轻一代外出生活的需求以及旅游业的兴起,促使传说传播范围扩大。但由于缺乏边界和族群认同意识的支撑,传说虽然走出了以往的范围,其在更大范围内产生的影响却是微不足道。换言之,传说即使通过年轻一代将传播范围扩大到湘西外,但其受众也仅是更大生存空间内的一些湘西土家人。
(一)传统传承方式
八部大王传说的传承有口头和文字传承两种传统方式。口头传承中,讲述者为了提高受众的接受度,将地方特色、自己的喜好和习惯加入传说的讲述中。而文字传承虽然是对传说的集体记忆和叙事,但其由文人搜集、整理和记录,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整理者个人叙述习惯和风格的影响。
土家神职人员土老司——“梯玛”口口相传的“梯玛歌”和“摆手歌”里,都有有关祭祀和纪念八部大王的描述。“梯玛歌”是“梯玛”进行仪式时口中的念词,摆手歌是土家摆手舞的组成部分。土老司的主持与“摆手舞”的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八部大王传说与信仰在日常生活中被不断重复。节庆活动参与人数众多,相对于个人的讲述与传承,传说与崇拜借此产生的影响范围就要大得多。因此,传说对节庆活动参与者的影响是具有普遍性的,而参与者回到各自生活范围后对传说无意识地传播更使其影响范围具有了辐射性的效果。在这种情形下,传说的流传范围便被成倍地扩大。
而大多数八部大王传说的文字传承侧重于对文化的传播,只有少数地方文献和地方文人的创作,具有区域历史建构的价值。除开在地方文献资料中的记录,文字传承也包括八部大神庙及相关的碑刻和石雕。据记载,龙山县长潭乡着落湖的八部大王神坛就曾经有对联云:“守斯土抚斯土斯土黎民感恩戴德同歌摆手,封八蛮佑八蛮八蛮疆地风调雨顺共庆丰年。”*胡炳章:《土家族文化精神》,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06-107页。而保靖县沙湾的八部大王庙,大门两侧的条石上曾刻有“勋猷垂简篇驰封八部,灵爽式斯土血食千秋”的对联,大门上层嵌有一块神龙盘绕的石碑,中刻“八部大王”四个大字。如今,神庙遗址上仍可看到残缺不全的条石对联散落在地,字迹已经模糊难辨。刻有“八部大王”字迹的石碑被收藏在湘西自治州博物馆中。但不管何种传承方式和传承领域,八部大王传说的影响力依然只集中于湘西土家人的居住区域内。
(二)旅游现场传承
除了传统的传承方式以外,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兴起和民俗旅游在旅游市场的爆红,民族文化开始受人追捧,传说的传承也开始出现新的分支。旅游现场的传承不同于以往的传承方式,具有独特性。它既依赖于身体与物质的传承,如通过旅游项目中演艺节目的编排、表演,使传承者身体力行地去参与并进行传承。同时,它也融入了口头与文字的传承中,通过老一辈传承者的讲述、梳理,以及表演中对传说的改编、重构,完成了传说从老一辈向下一代的延续。这种传承方式不同于口头传承只面对族群内部,也不同于文字传承对历史的忠诚。旅游现场的传承,不仅要将传说的传承顺利地进行下去,也需要传承者在传承过程中顾及游客的感受,迎合他们的喜好。例如张家界地区的演艺节目《天门狐仙》,编排者不仅要考虑其对民间传说原型“刘海砍樵”的继承与传播,同时也希望通过声光电一体的现代舞台效果促进本地区旅游事业的发展。
湘西地区开展民俗旅游项目,必须紧扣湘西地区的两大民族土家族和苗族的民族文化。八部大王作为湘西土家人中广受敬仰与供奉的祖先神,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为逐渐势微的传说带来了新的传承与发展契机。八部大王崇拜是湘西土家族文化中具有代表性与独特性的组成部分,八部大王祭、“摆手歌”“梯玛歌”等与八部大王信仰有关的事象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随着“武陵山片区文化保护试验区”的成立,八部大王庙遗址将成为新兴的文化旅游热门景点,八部大王传说及其祭祀仪式也将逐渐让传说的受众将目光再次集中于这一古老的传说,并试图从中寻求民族记忆与祖先崇拜的痕迹。而在旅游业不断发展的同时,随着旅游从业人员的增加,职业需要促使他们必须掌握更多民族文化知识,这也从侧面促进了传说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承与传播。
作为一种历史记忆与日常知识,传说依然是一个区域社会的标志,有着边界限制。不管是哪一种传承方式,都可以看出其中对区域社会的建构。传承中,人们也会无意识地划分出族群的界线,传承的界线可说是族群社会内外的边界。
三、传说流布边界性的形成
八部大王传说的流变与传承,都发生在固定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界线的划分清晰明确。传说之所以在其传播区域内成为重要的传承内容,主要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族群构成有关。离开了特定区域和区域内族群间的交往与互动,对传说内在身份认同的强调便不再重要,传说的传播也不再具有作为日常知识的意义。
八部大王传说在区域内,是人们日常交往中作为日常知识的民俗文化。而游客或外乡人进入传说传播区域的行为是偶然的,他们了解到传说的内容也是一种偶然,即使因为某种原因进入传说的传播范围,并了解到传说的内容。作为他者,他们也无法将这个代表一个族群的传说内化成自身的历史记忆来传承。但是,他者通过这一传说对土家族的想象对于传说流布边界的形成,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促成作用。
(一)环境的影响
八部大王传说的流布区域有复杂的环境,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本地区十分复杂的自然环境。湘西地处云贵高原与鄂西山地的结合部,武陵山脉由东北向西南斜贯全境。湘西地貌形态的总体轮廓以山地为主,兼有丘陵和小平原,高山峻岭之间也多溪流河谷。重叠的山峦阻碍了此地与外界的交通,也使人们所能获得的生存资源大大缩减。因此,人们只能在靠近溪流河谷的山间平地上繁衍生息,通过渔猎或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存活。陆上交通欠缺的情况下,水路交通成为湘西沟通外界的主要方法。湘西的产出通过水路沿酉水、沅水运往常德,并通过洞庭湖进入长江运输线。与之相对的,外界的物资也从洞庭湖、常德等地,通过水运进入湘西。水路运输开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水路运输交通线附近的河岸、码头也成为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受到人们青睐,大河两岸自然形成众多人口聚集的生活聚落。这些聚落在功能与设施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相应地出现了信仰活动的场所——神庙。八部大王传说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八部大王庙大多临水而建,如永顺县老司城的八部大王庙建于灵溪河畔,灵溪河下游从芙蓉镇汇入酉水主干道;保靖县沙湾村就坐落在酉水河畔,沙湾八部大王庙则建在与村寨隔河相望的酉水一侧岸边。神庙的设立使信仰的传播范围随之产生了变化,据沙湾村民魏品富说,在水运发达的年代,八部大王的信仰与传说随水路传播到四川和湖北等地。只要是往来在酉水上的船只,必会在路过时拜庙求平安,因此那时的八部大王庙香火鼎盛。*被访谈人:魏品富;访谈人:金晶;访谈时间:2013年1月12日;访谈地点:碗米坡镇沙湾村八部大王庙遗址。
另一方面,湘西地区自古就是多族群聚集的地区。除了土家、苗、汉三个民族以外,还有回、瑶、侗、白等几十个人数较少的族群生活在湘西境内。由于族群间生存空间以及拥有的自然资源重合,在自然环境恶劣的情形之下,生存资源获取十分不易。共同的生存地域使得不同族群之间长期处于利益争斗的状态,并试图通过族群共同的力量保证生活资源的获取。人们在进行族群的划分和身份认同时,所依赖的根据就是有没有共同的习俗、传说及信仰。因此,传说的流传区域就具有与其他族群争夺生存地域范围的标界意义。
(二)日常交往的需要
在湘西地区,可以大致地将土家人与苗人聚居地作南北划分,其中土家人大多居住在北方,而苗人聚居在南方,当然土家人与苗人的村寨也常有嵌入到对方聚居区域中的情况。村寨之间山水相连、田地相接,因此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不免要发生接触。有了接触,便有了互动。在村寨间的互动中,有相互帮助、互通有无的例子,如修路搭桥时村寨之间的配合协作;也有产生纠纷和利益冲突的一面,如在耕种过程中对资源使用权的归属和相接田土的越界侵占等导致的矛盾纠纷。当村寨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时,人们对传说的边界性往往没有意识。而当村寨间产生互动时,人们便开始意识到传说的族群认同价值。互动只要一经产生,不管其性质好坏,人们都能从传说的角度给予合理的解释。如在古丈城郊的树栖科村,村里的孩子会取笑去赶集的茶坪村苗家姑娘:“茶坪阿娅下河来,绿布裤子套花鞋。”*儿童对来自不同村寨和族群的人们进行言语挑衅的行为,集中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后来土家与苗家两族间通婚的增多,很多村寨的民族组成不再单一。同时,受到适龄儿童进城入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村寨中居住的儿童数量大大减少,也使这种带有明确划分族群界限性质的行为不复存在。这种行为背后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孩子天性中的调皮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个村寨分别属于不同的族群、有不一样的身份认同体系,导致人们认为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理所当然的。
八部大王传说的流传也是如此,即传说中具有某一族群特有的族群性,同时也有作为一个区域认同知识的区域性。但在一定的地域社会中,只有当传说作为某一族群的内部知识时,它才有转化成日常知识的可能。
(三)日常知识的需要
传说在传承区域内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同一区域内还存在着别的族群,而族群之间的互动又频繁发生。湘西就是一个由土家、苗、汉等族群共同生存的区域,族群之间频繁的互动使它们的关系在缓和与紧张之间不断变化。在此背景下,族群之间对祖先传说就存在一种认同与非认同的区隔。但人们并不一味地排斥其他族群的传说,甚至会加入到传说叙事的交往活动中。这时传说便不再局限于某一族群祖先传说的定位,而是更多地带有地域传说的性质。
不同民族共同生活并形成族际关系的区域中,传说是地域内日常知识的体现。族群认同传说边界的区域性,往往是在多族群共同居住,日常生活中有大量实际交往关系的情形下产生的。这时族群认同传说的边界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区域内,而是会出现一种超越作为日常知识而流传的区域,而成为另一族群能够接受的外部知识。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流布范围事实上并不是整个藏区,而是相对地集中在汉藏两族互动频繁的牧区。正是由于牧区汉藏两个族群之间的利益纠葛,才使得这里的藏民将对“格萨尔王”这一战斗英雄的历史记忆转化成了日常知识。因此传说也会超出藏族的区域而被当地的汉人所了解。再以古丈县的跳马节为例,它的流传区域也与族际之间的交往密切相关。太坪村原名热溪,是跳马节流传的核心区。这个村寨是“改土归流”前苗疆通往田家峒长官司的必由之路,也是现在由南向北通往古丈县城的必经之路。不仅位于族群分布的交界处,也处在南北陆路交通线上。*如清光绪《古丈坪厅志》卷三《道路说》中提到:“由治城至镇筸巡道治营路,厅治古仗坪二里至新寨汎,四里至长潭,八里至热溪,五里至排口塘,五里至白岩,四里至虾公塘,三里至排达牛,七里至李家寨、吴家寨、尚家寨,共十三里至龙鼻嘴汎,十里至荡它,达乾州属之喜鹊营。”其中的热溪便是今天的太坪村,它恰好处在古丈坪厅与镇筸所在苗疆的巡道治营路上。因此,交流、冲突或是争斗都成为此地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时常发生的纠葛、战争的历史记忆,使得人们“创造”了跳马节这一以模拟战争场景为主要活动的节日。除了祭祀酬神之外,人们试图通过庆祝的方式,将祖先的骁勇善战从历史记忆转化成日常知识。
与“格萨尔王”传说和“跳马节”相似,八部大王的传说中也有很多对战争的描述。这些对战争的描述都以八部大王取胜告终,也可看作是人们试图在族群混居的生存环境中,彰显族群优势的一种方式。总之,族群间的互动是一切发生的基础,传说流传的区域一旦超过一定范围,没有了族群间日常的互动、相互之间利益纠纷的刺激之后,其作为重要口头文化资源的意义和普遍的接受性就不存在了。这正是传说流布区域存在界线的重要原因。
(四)区域社会以外的交流
区域社会以外的族群互动与交流,虽然不直接作用于族群认同的发生和完善,但也是区域社会得以建构的重要因素。这种交流的重要性体现在族群间的相互认识上。威·休·詹森在其《民俗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一文中,强调了集体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区别:
内部因素指一个集团对自己的看法,以及它推断的其他集团对自己的看法。外部因素则指一个集团对其他集团的看法,以及它所认为的其他集团的看法。*转引自[美]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67页。
我们也可以说,在一个族群内部,对自身的看法以及认为外界对自身的看法,属于内部知识。而在族群以外的社会中,人们对于特定族群的认识和他们认为这一族群对自己的认识是外部知识。两者有着巨大的差别。内部知识在区域内诞生,并被无意识地传承。而外部知识对于一个族群来说具有双重意义。在某些时候,族群内部不愿接受外部知识,这时他们便选择对其忽视,不承认。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族群在向外界解释或是描述自身的特点时,反而会借用或者是直接以外部知识为依据。此时,外部知识作为区域社会以外的交流方式,便成了人们界定族群、进行身份认同的主要工具。
对于外部知识将自身塑造成刁蛮凶悍的形象,不管湘西的哪一个族群,都不愿接受,并试图忽略。湘西以外的人们往往认为湘西民风彪悍,多出土匪,但湘西人只强调自己的勇敢和善战。相反,在自身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湘西人又会强调本地彪悍的民风,从而达到威慑他人、自我保护的作用。另外,传说等用于区别族群差异的因素被广泛接受,其在族群内部也被视作是族群身份认同的一个标尺。因此,人们在介绍自己的族群时,往往会强调它们从而达到完善和强化族群在他者眼中形象的目的。如湘西地区的苗族强调自己是蚩尤的后人,而土家人则强调八部大王的祖先身份。
结 语
区域社会中,族群间通过习俗、信仰方式的统一来完成身份的识别和认同,从侧面展示了同一地域内族群之间的关系、交往以及互动。人们所属族群的区别促使他们强调本族群的历史记忆,从而重视对传说的传承并产生固定的传说流传区域界线。同时,传说流传区域界线的划分,也使得界线内外的人们清晰地意识到族群间的差异,从而在交往与互动中产生更多的可能性。八部大王作为祖先神最主要的特质,就体现在传说流传区域的边界性上。
以往对传说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故事文本本身的探讨,并忽略传说中所蕴含的身份认同的利益,认为传说的传播是无条件的。但事实上,传说的传播具有一定的边界性。传说流传边界性的产生,与传说形成的文化认同功能及其作用息息相关。在多族群共同生活的区域社会中,传说的边界性尤为明显。对八部大王传说流布边界性的研究,也是对传说学以往并没有将传说作为身份认同的知识来理解所做的补充。
历史学家对民间传说的关注,更倾向于探讨传说中所包含的、与历史资料一致的信息点,以及这些信息点与国家历史写作所形成的互证关系。他们并没有看到传说在区域社会中作为人们的日常知识,对族际交往所产生的作用。民俗学在对历史进行关照时,目光更多地聚焦于自上而下形成的百姓的日常生活史。而从边界性分析传说的流布区域,就是希望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在解读历史与传说的关系时,不单单只从国家、政治的层面上理解,更要从传说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与人们实际交往的关系这一层面去理解。
[责任编辑 王加华]
金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