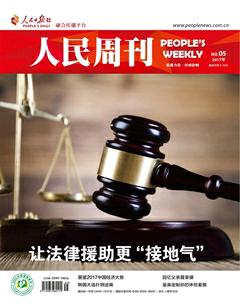香椿的味道
李红霞
鄉下老家,有许多野生的香椿树,一年一年滋生繁衍,零零散散地点缀满了乡村的各个角落。当然,最好能长在自家房前屋后,那样就可以整日看着香椿芽由小变大,然后近水楼台先摘先尝了。当春风温暖地让我彻底脱去冬衣的时候,那香椿也就该发芽了。我最爱吃香椿,总是一天三遍地看着房角那棵香椿树发呆,真想早日拿着钩子扒下嫩嫩的芽子吃个够。可我急,树不急,整日挺着干枯的枝桠在蓝天中显着它的沧桑与稳重,迟迟不吐芳香。
一个灿烂的午后,忽然在和风中嗅到了丝丝清香。迫不及待地跑到树下,踮着脚尖,寻找蓝天中闪出的那些暗红。找到了!一簇簇短短的芽子,不知何时已经在干瘪的枝尖绽开了笑脸,从高至低,错错落落地像是给这位老者扎上了灵动的蝴蝶结,将积蕴一冬的热情完美释放在这个春天里了。那嫩嫩的芽子,被阳光穿透成靓丽的紫红,闪着淡淡的油光,在湛蓝作为底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温情,一时间觉得香椿芽就是春天,春天就只有香椿芽。
春风催荣了万物。不出几日,香椿芽已经长成了小丫头的冲天小辫。竖在房角的长杆终于派上了用场。用铁丝弯成一个钩,绑在长杆上,就可以去扒那些垂涎已久的香椿了。站在房顶,长长地举起杆子,将那些可爱的芽子引入铁钩里,然后猛地一拧杆把儿,只听脆脆地“叭”一声,一簇香椿就应声飘落了下来。不一会儿,香椿已散落一地。
于是,便怀抱这些香椿,吵着让母亲给我炸“香椿鱼儿”吃。母亲先是把这些香椿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择好、码好,然后洗净,放在盆里用温水加盐腌一下。这时,母亲就可以腾出手来准备面糊了。在碗里打两个鸡蛋,放入适量的面粉和水,搅匀,直至能在筷子上拉出丝就可以了。烧开油,取出腌好的香椿在面糊里裹一下,迅速放入滚烫的油锅里,只听“吱啦”的一声,那个裹了面糊的香椿,顿时翻滚着膨胀起来,成了焦黄颜色。一直站在旁边的我,早已被锅里的香椿鱼儿惹得大咽口水了。一出锅,就用手抓起来吃,烫得我直跺脚摇手。母亲乐了,拿出碗盛好递给我。我便乖乖地坐在灶前,稀溜稀溜地吃到肚圆,抹一把嘴上的油,跑着玩去了。等回来,又会吃上一大碗。
一茬一茬的香椿吃下来,夏天已近,香椿已不能用来炸着吃了,我对香椿的热情也淡了下来。可母亲却去摘那些稍微嫩一些的叶子,切碎,晒在太阳底下,说是晒干后还可以吃。我不信,这怎么吃。炎炎夏日,母亲便取出那些干香椿,放在锅里用油炸一下,然后拌在黄瓜丝里,放上醋,浇在凉水浸过的面条上,一碗清凉喷香的凉面吃过,夏日的炎热一下子就在香椿的清香消失了。这种干香椿只要保存得好,可以吃一年,直到又吃上那暗红的嫩芽。
母亲知道我爱吃香椿,因此总是在春天里给我带来嫩香椿芽,有的嫩到可惜,可母亲却说这样的才好吃;过几天又会捎来一大包干香椿,于是我就一年都能吃到香椿了。生日长寿面里,浇上油炸香椿,那味道真是特别透了,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珍藏在香椿里的春天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