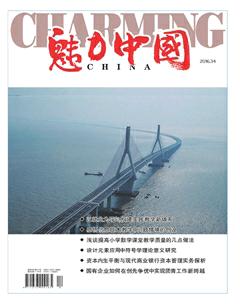论我国有限公司增资中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排除
韩卅
【摘要】我国对于我国有限公司增资中股东优先认购权排除的规定过于简单且存在较为严重的漏洞,本文以《公司法》第三十四條为切入点,首先探讨了股东优先认购权的含义和法理基础,其次列举了世界各国对于有限公司增资中股东优先认购权行使采用的三种模式:固有权模式、非固有权模式和相对固有模式,论述了在这三种模式下排除股东优先认购权的可能性,然后分析我国在有限公司增资中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排除制度的缺陷,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对我国有限公司增资中股东优先认购权和公司利益冲突时如何解决这一现实问题提供应对策略,也可以为进一步研究股东优先认购权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股东优先认购权 固有权 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排除制度
一、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概述
(一)股东优先认购权的含义
我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 这就是我国对于股东优先认购权的具体规定,而本文所研究的有限公司增资中股东优先认购权实际上是指在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的过程中,原有的股东基于自身的股东身份和地位,在其增资时,按原有的持股比例优先于一般人认购新增加的资本的权利。优先认购权之优先为认购顺位之优先,仅于能比他人优先认股之点上具有意义,与可否享受发行价格或其他方面之优惠条件,并无关系。[2]
股东的优先认购权是优先购买权的一种,与其他优先购买权有着诸多的共性,它们都是相对于法律关系外部的第三人所享有的“优先”利益,都具有附从性,服从于一定的法律关系。但是,股东的优先认购权又有其显著的特征,它具有弥补股东股权稀释利益损害的作用,新增资本会使得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下降,从而在公司事务的参与权利和公司盈利的分配权利上均遭受了损失,新增资本的优先认购权正是为了弥补这种损失,维护公平。
(二)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法理基础
关于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法理基础,学术界众说纷纭,笔者较为认可我国学者的观点,即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法理基础根据在于股东平等原则。股份平等原则中的第二层含义为比例的平等,投资者认购公司之股份、成为该公司之股东,则其依据股份平等原则所享有的此种比例上平等的待遇亦同时得以确定,这种比例上平等的待遇实质上体现了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在财产与管理诸方面的利益分配格局。此种利益分配格局一旦形成,则非经每个股东与公司间之合意或合于股东平等原则的一般标准,则不得擅予变更。每个股东依据此种利益分配格局所享受的利益实质上是一种契约性利益,此种利益非经该股东抛弃,则仍专属于该股东。[3]
这种观点是对德日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但亦有可商榷之处。首先,股东平等原则之比例平等指股东根据自己的持股比例平等地享有公司财产和管理方面的利益,是在既定格局之下的比例平等,不能从股东平等原则引导出股东在固守既定格局上的利益。其次,股东之比例地位乃指股东之持股在公司全部发行股份中所占之比重,股东与其他个体股东在持股上的比例衡量于股东地位而言意义不大,也无法控制,因为已发行股份具有流动性,现有股东之间在持股比例上可能发生变化,也可能有新的股东加入。最后,股东之比例平等并不体现股东与公司之间在财产和管理方面的利益分配,因为股东平等原则考察的对象是股东,衡量是否平等的参照系同样是股东,与公司没有关系。股东平等是公司行为的原则,公司并非股东平等原则的参与主体,除非公司本身是自己的股东,当然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二、有限公司增资中股东优先认购权行使的模式及其排除的可能性
(一)固有权模式
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的公司法一般都明确规定,公司进行增资发行新股时,公司现有股东有权优先于其他投资者认购公司新发行的股份,无论是公司章程还是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决议都不能做出与此相悖的规定,即优先认购权作为股东之法定权不得议定排除。例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183条(1985年12月4日第85-132l号法律)规定:“股份”包含有增资时的优先认购权。股东拥有优先认购与其股份数相应的、为实现增资而发行的货币股的权利,一切相反的条款均视为未作订立。在认购期间,如优先认购权与本身可转让的股票相脱离时,该权利可以转让;在相反的情况下,该权利可在与该股票相同的条件下让与。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67条第3款规定:公司发行新股时,除依前二项保留者外,应公告及通知原有股东,按照原有股份比例尽先分认,并声明逾期不认购者,丧失其权利;原有股东未认购者,得公开发行或洽由特定人认购。“此乃股东依法享有之权利,不得以章程或股东大会之决议剥夺或限制之,故属股东之固有权”。[4] 从具体的条文可以看出,在认定股东的优先认购权为股东的绝对股有权的模式下,有限公司增资时任何人都须尊重原有股东的优先认购权,除非本人自愿放弃,不然不得予以排除。
(二)非固有权模式
非固有权模式采取的态度与固有模式截然相反,其一般认为有限公司增资时股东并不享有优先认购权,除非在公司的章程中有相关规定,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优先认购权的排除。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是日本,原日本《商法典》第二百八十条之二第一项规定:“于公司成立后发行股份时,如章程未定下列事项,则由董事会决定。但是,本法另有规定或章程规定应由股东全会决定时,不在此限”。其中章程未定事项第5点为“给予股东以新股认购权事宜及认购权标的股份的额而无额面的区别、种类及数额”。[5] 2005年制定的日本新《公司法典》第202条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即发行新股时赋予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意旨及相关规定,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或董事会决议决定的,依章程办理;此外之情形依股东大会决议办理。
(三)相对固有权模式
这种模式亦可称为有条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首先的前提是和固有权模式一样肯定了有限公司的股东在增资时拥有优先认购权,但是其承认的优先认购权不是绝对之权利,一旦存在法定事由或实质性合理事由时,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可以排除股东的优先认购权的适用。例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186条(新股票认购权)规定:“(1)经要求,必须分配给每一位股东与他在原基本资本中所占份额相适宜的新股票。对新股票认购权的行使应规定一个至少为两周的期限。(3)在关于增加基本资本的决议中可以全部或部分排除新股票认购权。在这种情况下,决议除了要遵循法律或章程对增加资本所规定的要求外,还需要一个在做出决议时代表着基本资本的至少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章程可以规定一个更大的资本多数和提出其他要求。(4)排除新股票认购权已经明确地、符合规定(第124条第1款)地予以公布的,始得做出一项全部或部分排除新股票认购权的决议。董事会应向大会提交一份关于部分或全部排除新股票认购权理由的报告,在报告中应就建议发行的金额加以说明”。[6] 根据德国《股份公司法》的规定,抽象性优先认购权属于股东的法定权利,公司章程不得概括排除或限制,惟股东之具体性优先认购权得依股东大会以加重多数或更为严苛之要求通过之决议予以排除,但需以存在法定事由或其它实质性理由为限。
三、我国有限公司增资中股东优先认购权排除制度的缺陷
对于有限公司增资中的股东优先认购权,无论是固有权模式,还是非固有权模式,两者皆非最佳的选择。在固有权模式下,股东的利益虽然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司资本的灵活、及时和充分调度,限制了公司应对发展的需要和瞬息万变的市场灵活、迅速筹集资本的能力,至少是使公司筹集资本的效率有所减损;而非固有权模式的出现克服了固有权模式在筹集资本效率上的弱点,赋予了公司业务执行机关在筹集资本上的充足空间,但是其也导致了股东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董事会和大股东容易滥用新股的分配自由。固有权模式和非固有权模式的冲突提醒了立法者需要在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之间进行价值衡量和平衡,同时兼顾到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因此相对固有权模式才是最好的选择,股东优先认购权排除制度的设立也是必要的。
我国的《公司法》采用了相对固有模式,其三十四条规定:“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这表明了我国在前提上承认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这就为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排除制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诚然我国采用的是较为先进的相对固有模式,但规定本身存在严重的疏漏,根据法条的规定,在有限公司增资中,公司的全体股东可以通过章程的约定将股东的优先认购权加以任意的排除,而在公司利益和股东的优先认购权发生冲突时,由于该权利的排除必须经过全体股东的同意,那么主张优先认购权的股东必定是不会同意排除其优先认购权的行使的,这就导致了实践中无法操作,排除的制度形同虚设。我国实质上在有限公司增资中股东优先认购权上采用的相对固有模式和固有模式没有差别,这种缺陷在市场经济中是致命的,排除制度本身以平衡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为目的,如果不能达到平衡,这种排除制度就不再存在。上述的缺陷为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排除制度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
四、我国有限公司增资中股东优先认购权排除制度的完善
在有限公司增资中,股东优先认购权排除制度的设立是为了平衡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如果要排除股东的优先认购权,侵害股东的利益,那么这种行为就必须严格限制,但又不能实施不了。笔者认为只有满足更为完善的实质性要件和形式性要件,股东优先认购权才可以得以排除。
(一)实质性要件的规范化
首先,从股东优先认购权的设立的法理基础来看,其排除必须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非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利益,只有有限公司在增资时对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排除是基于公司的特许利益,为了实现整个公司利益而采取
的特殊举措,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法合理。其次,股东优先权的排除必须有必要性,也就是说,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如果不排除股东的优先认购权,公司利益将会受到损害,没有其他的办法予以避免。此时,排除股东的优先认购权已经成为拯救公司利益的一种必要手段,这种排除才是被允许的。最后,适当性是不可忽略的,排除股东的优先认购权是为了公司利益,但如果排除股东的优先认购权对股东造成的损失比挽回的公司利益要更大,这种排除就失去了价值。
(二)形式性要件的具体化
在符合上述的三个实质性要件的基础上,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排除也需要符合相应的形式性要件。第一,只有在有限公司决定增资时,在增资协议中排除股东的优先认购权,而不得以公司章程等形式在增資前将股东的优先认购权予以排除。第二,排除股东的优先认购权的决定须由股东大会做出,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的多数同意方得以施行。第三,规定相应的救济制度,如股东可以针对股东大会做出排除其优先认购权的决议向股东大会提起复议或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参考文献
[1]《公司法》三十四条
[2]柯芳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3页
[3]沈四宝:《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4]柯芳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5页
[5]王书江:《日本商法典》,殷建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6]贾红梅,郑冲译:《德国股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 -115页。
[7]沈四宝.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8]柯芳芝.公司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9]王书江. 殷建平译.日本商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10]王光东.论新股优先认购权及其排除[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9
[11]方伟南.有限责任公司新增资本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探究[J],法制与社会,2009,8
[12]刘雨萌.股东新股优先认购权制度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长沙:中南大学法学,2013
[13]崔江飞.有限责任公司新增资本与股东优先认购权的保护[D]: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