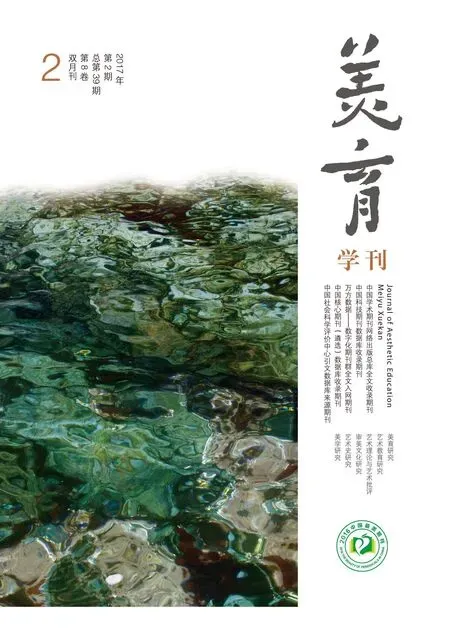“中性”:罗兰·巴尔特美学的辐辏
金松林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1)
“中性”:罗兰·巴尔特美学的辐辏
金松林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1)
罗兰·巴尔特从特鲁别茨柯伊、叶姆斯列夫和布隆达尔的结构语言学中挪用了“中性”这一概念,并且经过一系列创造性转换,将它确立自己的方法论。以此为手段,他对隐藏在语言结构和话语领域的意识形态进行了解构。但是由于巴尔特晚期将“中性”和古代怀疑论以及东方的禅道哲学结合起来,这一错误的理论嫁接不但削弱了其理论解构的锋芒,更重要的是使他本人陷入了寂静主义的泥沼,由此反映出巴尔特理论的限度。
罗兰·巴尔特;美学;中性
罗兰·巴尔特在传记中追问:“在一个作者的词汇表里,难道不总该有一个魔力般的词汇,这个词汇热烈、复杂且难以把握,它像是某种神圣的意指;通过它,人们将会产生可以答复所有问题的幻觉?”[1]129在他看来,“这个词汇既不是偏离中心的,也不是中心的;它相对稳定,却又有所负累;它不断漂移,总是居无定所(逃避任何主题);它既是剩余之物,又是替补之物;它是占据任何所指位置的能指。这个词汇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地出现;首先它被真实(故事的真实)的要求所掩盖,随后又被效用(系统和结构的有效性)的要求所掩盖;而今它振枝展叶,花团锦簇。”[1]129-130在福柯的词汇表里,这个“魔力般的词汇”是“权力”(pouvoir);在德里达的词汇表里,是“延异”(différance,有时也译为“异延”或者“差异”);在拉康的词汇表里,是“漂移”(dérive)……而在巴尔特本人的词汇表里,这个“魔力般的词汇”是什么呢?答案是“中性”(neuter)。在法兰西学院的研讨班上,他明确指出:“我曾带着‘中性’这个词汇旅行,它作为一种所指在我心里挥之不去(实际上,这种情感自《写作的零度》就有了),当我阅读某些著作的时候,它就一直缠绕着我。”[2]8若翻阅巴尔特的《全集》我们就会发现,他在《论纪德和他的日记》(1942)中就已经提到了“中性”概念,此后,这个术语又频频出现在《写作的零度》《符号学原理》《流行体系》《神话学》《S/Z》等著作之中。1978年春季学期,他更是花费了数个月的时间与学生一起讨论“中性”。巴尔特说:“思考中性,对于我而言,它作为一种方法——一种自由的方法——目的是为了在时代的竞争中展现我自己的风格。”[2]8由此可见,“中性”不仅仅是巴尔特著作中的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更是他整个美学的辐辏,他的所思所想都和“中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贝纳尔·科芒(Bernard Comment)也强调巴尔特的这一思想“是在很早就出现的,并且具有惊人的连续性,因为这种观念在巴尔特兴致不减的写作行程的不同‘阶段’中不曾有过任何收敛”[3]。既然它如此重要,那么究竟何谓“中性”?它从何而来?巴尔特为何要搬出这一概念?它具有哪些深刻的内涵?其作用又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本文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下我们将主要围绕《中性》(2002)展开。
一、概念的来源
这本书是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所开设的第二期研讨班上的讲稿。他遭遇车祸意外去世以后,胞弟米歇尔·萨尔泽多(Michel Salzedo)作为遗产继承人遵照他的遗愿将这期研讨班的讲稿以及其他讲稿一同存放在法国当代版本档案馆。后来,埃里克·马尔蒂(éric Marty)协同瑟伊出版社经过多年谈判才最终获得米歇尔的授权。从2002年开始,这些讲稿被命名为“书写的痕迹”丛书相继面世,《中性》就是其中之一。迄今为止,人们很少注意到该书的重要价值,有人甚至认为它在巴尔特的著作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实,这本书的出现不仅仅是巴尔特长期思考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本书中他首次明确了自己的方法论,并且运用这一方法对语言结构和话语乃至整个西方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先前他在一些著作中尽管已植入了“中性”的观念,却没有哪本著作能够真正像《中性》那样将这一观念谈得如此透彻。因此,它的出现既带有总结的性质,又意味着新的开端,即在《中性》面世之后我们必须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巴尔特。
该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一个相对简短的“开场白”,在它的名下又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权充题词;(二)论据;(三)准备和阐述的步骤;(四)中性之欲。在这些内容的前面,巴尔特还开列了一串长长的书单,其中既有哲学和文学类书籍,又有名人传记和回忆录,甚至还有美国著名音乐家约翰·凯奇(John Cage)的音乐作品集《为鸟而作》(1976)。在准备这门课程的过程中,巴尔特大致阅读了这些作品,所以它们和《中性》具有互文的性质。通过这些著作,巴尔特建构了他的《中性》;而通过《中性》,他又不断地影射这些文本。在随后的讨论中我们将会看到,其中有些对于《中性》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二部分是与“中性”相关的熟语以及一些必要的补充。按照原计划,巴尔特准备讲30个熟语,实际准备的只有27个,而系统讲完的只有24个。他采用一种随机数学的方式对这些熟语进行排列,目的是为了打乱它们的顺序,使它们丧失某种整体性*巴尔特认为“整体性”(totality)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主体意志和权力观念的生动体现,因此,在《罗兰· 巴尔特谈罗兰· 巴尔特》中,他斥之为“恶魔”。详情参见Roland Barthes. 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 trans. Richard Howard.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1977, pp.179-180。。这种安排使该书具有相册的性质,或者说《中性》所采用的就是他在《米什莱》《萨德、傅立叶、罗耀拉》《符号帝国》《罗兰·巴尔特谈罗兰·巴尔特》等著作中早已操演过的相册式写作,这种写作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片断缝合式”(rhapsodic)。巴尔特说:“我有这样的幻觉,即我相信在把我的话语打碎的时候,我便中断了有关我自身的想象性的话语,我就减弱了趋于超验性的风险。但是,由于片断(俳句、箴言、观念、报刊头条)终究是一种修辞文类,而修辞又可以将自己完美地显现给阐释的话语层面。通过假设,我打发了我自己,实际上我又乖乖地回到了想象物的床上。”[1]95这段话具有两层含义:第一,采用片断的方式写作,目的是为了去理论化,突破自我中心主义的幻觉;第二,片断终究还是一种修辞,而几乎所有的修辞都隐含着作者心中某种挥之不去的欲望,这种欲望渗透在每个片断之中,最终汇聚成某种类似于主题的东西。
就这本书而言,作者内心挥之不去的欲望就是对于“中性”的欲望。巴尔特在开场白中说得非常明确:“这门课名为‘中性’,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中性之欲’(the desire for neutral)。”[2]1根据拉康的理论,欲望之所以成其为欲望,就是因为它根本性的匮乏,如果欲望能够被轻松地满足的话,那么它就不成其为欲望而是浅层次的东西——需要或者需求。由此,“中性之欲”也就可以理解为“对于不可能性的事物的欲望”。“不可能性的事物”即在现实中永远都无法实现的东西,德国著名思想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将它定义为“乌托邦”:“‘乌托邦’这个术语的当代涵义,主要是一种原则上不可能实现的思想。”[4]明知这种思想无法实现却还要去欲望它,这里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家的情感固执,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美好事物的想象。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巴尔特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我们稍稍考虑一下人文科学中最可靠的一门即历史学的话,就必须承认它与幻想之间始终存在着关联。这就是米什莱所理解的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归根结底是有关典型的幻想领域,即人的身体的历史。正是从这种幻想出发,并通过使过去的身体重新复活,米什莱才能把历史变成一门了不起的人类学。因此,从幻想中也能够产生科学。”[5]477在巴尔特的观念中是否有加斯东·巴什拉的成分我们不去深究,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中性”观念背后所隐含的乌托邦的性质,只要他在言说“中性”,其实也就是在以乌托邦的形式说话。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中性”是他所欲望的对象,那么何谓“中性”呢?这一概念又是从何而来?在本期研讨班上,巴尔特尽管有所交代,却语焉不详。因此,要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将目光暂时转向结构语言学,特别是结构语言学中的音位学,因为巴尔特正是从这门学科中汲取了这一概念。
1873年5月24日,在巴黎语音学会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德热内特(A. D. Dereneite)率先提出了“音位”的概念。他建议用法语的“音位”(phonème)而不是“语音”(son de langue)来翻译德语的对等词Sprechlaut。表面上,这是一个跨语际沟通中术语的翻译问题,实则意味着理论视角的转换,即从对语音的外在研究转向对音位即语言结构的内在研究。受德热内特的影响,路易· 阿韦不久即在自己的语言学著作中直接使用了“音位”概念。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他对“音位”的理解仍然带有十分强烈的语音学的残余,认为“音位”就是指“任何一个发音清晰的音”[6]12。
后来,索绪尔在对语音研究的过程中继承了路易·阿韦的音位学观念,并且将它运用到自己的普通语言学讲座之中。他提醒学生不要将“语音学”和“音位学”混为一谈,因为“前者是语言科学的一个主要部分,而音位学——我们要重复说一遍——却只是一种辅助的学科,只属于言语的范围”[7]60。这一限定表明,索绪尔并没有真正走出路易·阿韦的阴影,他虽然强调学科的区分,但仍然是从语音学的层面来理解音位问题。在音位学的历史上,他之所以被人们记住,主要是因为他率先将音位看成是一个具有区分功能的语音系统。一个常识性的事实:人类的发音动作并不能构成语言,我们即使把产生语言的每个音响形象所必需的一切发音器官的动作都解释清楚,也无法阐明语言的问题。正是在这点上,索绪尔教导我们说,一个词的重要之处不是它的语音而是语音之间的差异,语音之间的差异能够使一个词和其他的词区别开来,并且拥有自身的价值。以国际象棋为例,每个棋子的价值并不是由它的物理属性所决定的,而是由它在棋盘上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我们如果把这个类比运用到语言上,便可以理解索绪尔所得出的重要结论:语言中只有差异,而没有任何正面的规定。这也就是说,通过语音形象所呈现的能指,其意义并不是预先规定的,而是在语音系统中通过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而获得的。如英语中的bed(“床”)和bad(“坏的”)、bud(“蓓蕾”)和bid(“投标”)、head(“头”)和lead(“领导”)、food(“食物”)和foot(“脚”),这些词汇之所以有着各自不同的含义,就是因为它们在语音上的彼此对立所造成的。所以我们说,是语音区分了词义。为了简便起见,索绪尔将语音之间的对立概括为:a/b。作为能指,a和b都不是简单的项,它们两者都产生于某种特殊的关系。在思维活动中,人的意识所达到的永远只会是a/b的差异,而不会是单纯的a或b。习惯上,我们将语音之间的这种对立称之为“聚合关系”或者“二项对立”。
作为他的后继者,雅柯布森也基本上是在二元论的框架下来思考音位的问题。在《音位的概念》一文中,他以土耳其元音系统为例。土耳其的元音系统共有8个音位:i、ü、、u、e、ö、a、o。按照数学的组合公式,这8个音位可以产生28种区别,即28种二项对立的关系。然而,数学的运算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有些音位在语言表达中并不能形成真正的对立。由此,雅柯布森将该元音系统的8个音位缩减为三种基本的对立:(一)低音位与高音位的对立;(二)非前音位与前音位的对立;(三)圆唇音位与非圆唇音位的对立。这三种对立形成了土耳其语的区分性特征。后来,他发现在其他语言中也存在类似现象,也就是说,每种语言的全部音位(元音和辅音)都可以分解成不能再分解的区别性特征。如法语中的开元音[ε] 和闭元音[e],它们之间的对立使dé(“骰子”)和dais(“华盖”)拥有各自的含义;捷克语中齿音[t]和前腭音[tˇ],它们之间的对立使sit(“播种”)和sit’(“网”)拥有各自的含义。
1927年冬,在向第一届国际语言学会提出的建议中,雅柯布森对音位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他说:“一个音位的相关关系是由共同的原则确定的一系列两分的对立组成的,它能够独立于每一对对立而起作用。”[6]73比如在英语中,爆破音:[p]和[b]、[t]和[d]、[k]和[g];摩擦音:[f]和[v]、[θ]和[e]、[s]和[z];破擦音:[t]和[d]、[tr]和[dr]、[ts]和[dz],等等。这些对立项总是以特殊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只要一者出现,另一者即便不出现,我们的大脑也会快速地联想到它,就像由白联想到黑,由美联想到丑,由高联想到低。在《语言的基本原理》中,罗曼·雅柯布森和他的合作者莫里斯·霍尔(Morris Halle)认为,二项对立不仅是语言结构中最自然、最经济的法则,而且也是儿童学习语言“最初的逻辑活动”[8]。
然而,流亡捷克的俄裔语言学家特鲁别茨柯伊(N.S.Trubetzkoy)在音位学研究中却发现了一种比较奇特的现象——音位中和(phonemic neutralization),即在不同的音位系统中,一些特殊音位上的对立会突然消失。在《音位学原理》(1938)中,他将音位相关的对立位置叫做相关位置,发生中和的位置叫做中和位置。前者无论如何,在所有的音位上都具有区别力;后者仅在某些音位上具有区别力,而在某些位置上就被中和了。例如,德语中,双唇音[d]和[t]在词末位置上发生中和;英语中,爆破音[p]和[b]、[k]和[g]在清辅音[s]之后发生中和;在保加利亚方言和现代希腊语中,[u]和[o]、[i]和[e]的对立在非重读音节中发生中和。中和现象的发现对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来说,可谓影响甚巨,它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二元论思维模式的怀疑。因为既然二项对立是音位区分的基本准则,并且被语言学家视为科学的思维方法,那么,它就应该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在《语音变化的机制》这本书中,法国著名语言学家马丁内(André Martinet)对这种二元论的音位学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他发现音位系统中绝大多数对立都是二元的,但也存在一些例外的情况。这就表明,索绪尔的二元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和布龙达尔(Viggo Brondal)是丹麦哥本哈根学派著名的语言学家。为了弥补他们的前驱——索绪尔和雅柯布森——在音位学理论上的缺陷,他们在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伊科学发现的基础上,对音位关系作了进一步概括,他们认为索绪尔的表达式应该调整为:a/b, a+b,既非a也非b。意思是:如果a和b是存在潜在的对立关系的两项,那么,a和b之间既可能完全对立(a/b),也可能产生中和以及更为复杂的操作。在《语言理论导论》中,叶姆斯列夫就举了这样的例子,丹麦语音节尾部的[p]和[b]产生中和,然而当它们处在音节首音位置时,交换关系立即中止。后来,布龙达尔还将这一音位模式类推到符号学领域,他将有标记的项用“正”(+)表示,而无标记的项用“负”(-)表示,按照以上调整之后的表达式,在这两个对立的项次之间还可以插入一个第三项,这个新增的项次既可以是“中性”,也可以是“复合”,由此就有了这样两种理论模型:(一)正vs 中性 vs 负;(二)正vs复合vs负。[9]这两种理论模型不但打破了索绪尔的二元论逻辑,更赋予了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理论家们新的灵感。
A.J.格雷马斯就直接将叶姆斯列夫和布龙达尔的理论挪用到自己的结构主义语义学之中,创建了符号学矩阵,并且将它运用于对叙事性作品的分析。在这方面,格雷马斯是否直接启发了巴尔特已无确切的资料可考,但是可以肯定,后者也正是从叶姆斯列夫和布龙达尔那里汲取了理论资源,他的“中性”概念就直接来自于这两位丹麦籍的语言学家。当然,特鲁别茨柯伊作为这一概念的制造者,他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觑,比如在《符号学原理》(1964)中,巴尔特就一再地提到他。正是在这些语言学家的影响之下,他获得了理论灵感,并且创造性地将“中性”发展为自己的方法论。
巴尔特为何要从语言学中挪用这一概念?这就涉及《中性》一书的主要目的。在第一部分的“开场白”中,巴尔特就说得非常明确:
对中性之欲进行专题的、详尽的、终极的描述并不属于我的工作。这是我的一个谜,也就是说,只有别人才能看到属于我的东西。我能够做的仅仅是发掘我内心深处的洞穴,中性在里面若隐若现。因此,我想说,中性之欲是这样一种欲望:
——首先,悬置(悬搁)各种命令、规则、胁迫、傲慢、恐怖主义、公开威胁、攫取意志(the will-to-possess);
——其次,更进一步,拒绝单纯的反对话语。悬置自恋:不再害怕形象(imago):消解某个人自己的形象(这种愿望接近于消极的神秘话语,禅宗或者道家)。[2]12
“各种命令、规则、胁迫、傲慢、恐怖主义、公开威胁、攫取意志”,这些都可以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或者说它们就是权力的生动体现。巴尔特曾仿照福柯的口吻揭示了权力的特征:“它无处不在,在领导关系中,在规模不一的组织之间,在压迫集团和被压迫集团之间,到处都有‘权威’的声音,它让人们用权力的话语——颐指气使的语气说话。于是,我们发现权力在社会交往的各个环节存在,不只是在国家、阶级、集团里,甚至出现在时装、公众舆论、娱乐、运动、新闻、家庭以及私人关系中,甚至还出现在反抗权力的解放冲动中。……它在这里被驱赶耗尽,在别的地方又会重新萌生,权力永远都不会消失。”[5]459-460既然如此,那么怎样才能摆脱权力的束缚?对于每个个体而言,这都是在世存在的重要问题,巴尔特将它看作一种生命引导计划或者生存的伦理学。以权力的方式来反抗权力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逻辑即以暴易暴,结果非但不能消解权力,反而会使它更加显露出自己狰狞的面孔,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抗权力断然无效。1978年9月,巴尔特在接受法国《改革》杂志的采访时说:“如果我们想将自己和暴力分开,就必须接受非权力的思想。从当前社会状况来看,也就是必须采取一种绝对边缘的思维。如果要反对暴力,就必须确立一种外在于权力的坚固的伦理,自己不要介入到任何权力的运作当中。”[10]
以非权力的方式来反抗权力,这是巴尔特整个思想的核心,自然也是《中性》这本书的核心。如何运用非权力的方式来反抗权力?如何在权力之外来确立一种坚固的伦理呢?答案均是“中性”(neuter),当然,前者是一种策略,而后者是一种立场。以上我们在追踪概念的来源时曾提到“中性”就是介于两个对立的项次之间的第三项,这个项次既不是对前两者的中和,也不是综合,而是一个纯粹的差异项。而在语义上,“中性”就是“既不,也不”“非此非彼”。落实到实践层面或者伦理层面,当我们采取“中性”的策略即不在任何矛盾中进行选择,由此我们也就远离了各种权力斗争。在这点上,巴尔特说得比较明确:“世界面临威胁:非得选择不可,被迫生产意义,卷入矛盾冲突,‘承担责任’,等等。→尝试悬置、破除和避开聚合关系,它的胁迫和傲慢→免除意义→这个避开聚合关系和矛盾冲突的多样性的领域=中性。”[2]7
二、结构与权力
如果说以上是从实践层面来思考问题的,那么在《中性》这本书里巴尔特还将思想的触角延伸到了语言结构的领域。一些语法学家们通常认为语言结构就是我们必须遵从的语言规范,就是语言得以形成的基本准则,一旦我们背离了这些准则和规范,就会造成语言沟通的障碍。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巴尔特就以自己的母语为例:“在法语中(我举这个明显的例子),我必须首先假定自己是主语,然后才能对行为加以陈述,行为从此时起不过是我的属性:我所做的仅仅是我之所是的结果和延续。同样,我必须永远在阴性和阳性之间进行选择,中性和复数对于我是禁用的。进而言之,我必须借助于tu(你)或vous(你们)来表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从社会和情感方面悬置了我自己。由此,语言结构通过其结构本身包含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异化关系。说话,或者说得更庄重一些,发出话语,并非像人们通过所说的那样是在沟通,而是使人屈服。整个语言结构就是一种被普遍化了的支配力量。”[5]460如果和雅柯布森的观点相比,我们就会发现巴尔特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多少新意,因为前者早就已经指出语言规则并不是依照它允许我们说什么而被定义,而是依照它迫使我们怎样说而被定义。
巴尔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对意义生成的机制展开分析的过程中有了惊人的发现。大家知道,意义产生于聚合关系,凡是有聚合关系的地方就会有意义,反之,凡是存在意义的地方必然有聚合关系。索绪尔在《手稿》中说得非常明确:“无论哪里都摆脱不了这根本的而且永远是两个词项的差异,差异永远都是以相反的方式存在,而不是取决于一个词项的特性。”[11]正是从这里巴尔特看到了意义生成机制之中隐藏着暴力——我们总是取此而舍彼,即在选择其中某项的同时总是以牺牲和它相对立的另一项为代价。比如,当我们说某个学生“很傻”“很笨”“很懦弱”的时候,其实也就排除了与它们相对的另外一些词汇:“很伶俐”“很聪明”“很勇敢”。更何况,某些词汇本身就具有多重含义。在《柏拉图的药》一文中德里达就举了这个例子:在希腊语中,“pharmakon”这个词汇既有“良药”的意思,又有“毒药”的意思。当我们认为它是“良药”的时候,也就否认了它是“毒药”;当我们认为它是“毒药”的时候,也就否认了它是“良药”。通过肯定(或者选择)某项而否定另一项,这就是隐藏在语言结构中的权力。假如要将这种意义生成的机制概括为某种普遍模式的话,巴尔特认为可以将它表述为:“是(+)/否(-)”,意思是:我们在肯定聚合关系中的某项时即在否定它的对立项。只要我们跟意义打交道,这一模式就会自然启动。若有人说:“我姐姐刚生了个男孩。”言下之意,他姐姐刚生的不是女孩。“男孩”(+)/“女孩”(-),这就是通过选择前项而排除后项。这样的例子在语言应用中比比皆是。
在《符号学原理》(1964)中,他把这样的机制称之为语言符号的“否定性对立”。在这种对立中,其中一项的能指以一种意指成分或标记的形式出现,而与之相对的另一项则没有这样的成分或标记。例如英语中的“impossible”(不可能)相对于“possible”而言就属于有标记的项,“im-”是否定性的前缀,是前者区分于后者的特殊标记。一些语言学家把无标记的项视为常项,而把有标记的项视为变项。而众所周知在语言系统中常项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变项。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变项不过是常项的派生物而已。比如在英语中,当我们给一些形容词加上这样的前缀(如“un-”“in-”“im-”“dis-”“a-”“de-”“mis-”“anti-”“no-”“non-”),或后缀(如“-less”“-able”“-free”“-proof”),它们就从常项变成了变项。在德语、法语、西班牙、俄语等语言中也同样如此。巴尔特把这种状况视为语言学的“丑闻”,因为“‘是’(断言)藏而不露地镌刻在整个语言之中,可是,言‘否’却无一例外地需要一个特殊的标记。换言之,这也是哲学中众所周知的老问题,语言生来就是断言性的”[2]42。当我们说某人是个“好人”时,即在宣示他作为一个好人的存在,而否定了他还有可能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妻子的坏丈夫,在她们眼里,他有可能是个十足的坏蛋。肯定某个词项即刻认为它存在,这种断言性的判断在语言中随处可见。当它蔓延到话语以及由话语所形成的文化领域,必然导致各种各样的掌控欲或攫取意志的出现。
实际上,巴尔特早就意识到了这种二元论的语言结构所存在的问题。在《罗兰·巴尔特谈罗兰·巴尔特》里,他举了这样的例子:大众看法/个人看法、多格扎(doxa)/反多格扎(paradox)、俗套/更新、疲惫/清醒、喜欢/厌恶。他认为这种二元论的辩证法实际上就是意义的辩证,是儿童所玩的弗洛伊德式的滚轴游戏(Fort/Da),而这些统统都属于价值的辩证法。[1]68-69不仅仅是传统哲学和符号学,甚至包括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在内,它们都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在两个相互对立的词项之间,高一级的词项通常隶属于逻各斯,所以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价值的体现,反之,低一级的词项则被视为堕落。[12]76如我们在西方哲学中经常遇见的:灵魂/肉体、理性/非理性、始基/杂多、意志/表象、直觉/表现,等等。
在接受让-路易·乌德宾和居伊·斯卡培塔的采访时,德里达说:“要公正地对待这个必要性,就要认识到古典哲学的对立中,我们所处理的不是面对面的和平共处,而是一个强暴的等级制。在两个术语中,一个支配着另一个(在价值论上、在逻辑上等等),或者有着高高在上的权威。要消解对立,首先必须在一定时机推翻等级制。”[13]48他所采取的方法是釜底抽薪,即通过“延异”的方式铲平意义的根基,使语言成为一种差异性的游戏。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早就说过:“语言中只有差别。……就拿所指或能指来说,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和声音,而只有由这个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7]167德里达批评索绪尔在《普通语音学教程》中只看到了语言之间的静态的差异,而忽略了这种差异也是在时间中形成的。因此,他根据法语词“différence”(差异)杜撰了“différance” 一词。这两个词尽管只有一字之差(e/a),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德里达说“différance”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作为名词,它表示空间上的差异;而作为动词,它表示时间上的延宕。当我们将这个词汇植入语言系统,更准切地说,当我们运用“延异”的策略来解构语言,其结果必然会使每一个概念的所指都处在无限的迟延之中。德里达还进一步强调在语言中没有任何先于延异的东西(各种形式的真理、价值、形而上学的观念)。借此,他动摇了意义以及形而上学的根基,瓦解了语言结构中的双边对立。

除了德里达和拉康以外,吉尔·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千高原》等著作中也对语言结构发动了攻击,目的同样是为了颠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命题。乔纳森·卡勒说:“解构主义不是一种界定意义以告诉你如何发现它的理论。作为诸理论赖以奠基的各种等级分明的二元对立之一批判消解剂,它阐发了任何从单一途径来界定意义(如看作作者意象所指、惯例所规定的、读者所经验的等)的理论所面临的难题。”[12]115为了解构隐藏在语言结构中的权力或者各种形式的攫取意志,巴尔特所采取的策略依然是“中性”。在第一部分的“开场白”中,他将“中性”定义为“破除聚合关系之物”[2]7,落实到操作层面即在两个对立的项次之间植入一个新增的项次,譬如在“he”(他)和“she”(她)之间植入“anyone”(某人),相对于前两项而言,这是一个中性项,它的出现显然消解——更准确地说,避开或逃逸——了原有的(性别)对立。在一个名为“多元,区别,冲突”的片断中,巴尔特把自己的这种哲学称之为“多元论”(pluralism)。[1]69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它可以取消传统的二元对立。日裔美籍学者塞缪尔·早川和艾伦·早川在他们的著作中早就说过:“二元价值观点只能产生争斗精神,而无法提升我们准确评价世界的能力。除非我们是以争斗为目的的,否则在这种看法的领导下,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总是会与原来的目的相反。”[16]第二,它能够瓦解各种形式的中心主义。通常而言,“中心是那样一个点,在那里内容、组成成分、术语的替换不再有可能。组成成分(此外也可以是结构所包含的结构)的对换或转换在中心是禁止的。至少这种对换一直都是被禁止的(我有意使用这个词)。因此人们总是以为本质上就是独一无二的中心,在结构中成了主宰结构同时又逃脱了结构性的那种东西。”[17]当结构被拆解以后,中心也就不再是中心了。第三,它动摇了本质主义的根基。本质主义是一种僵化的、封闭的、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方式。在本体论上,本质主义不是认为事物具有某种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超时空的永恒的本质,并且相信这种本质不会因外在条件而改变。在认识论上,本质主义建立在现象/本质二分的基础之上,坚信绝对的真理,并以此为核心排斥其他的理由或见解。多元论的出现突破了这种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它对所有的事物一视同仁。因此,对于传统的哲学来说,多元论显然是一种进步。
可问题在于,利用“中性”的策略来解构语言中的对立,抛开其操作层面的难度不说(这点在《写作的零度》中已有所体现),该策略的核心并不是“消化”“排解”矛盾,而是“避开”矛盾,在面对矛盾冲突时却逃之夭夭。所以,有人对此十分不满。比如德里达在批评巴尔特时说:“如果人们迅速进行中和活动,但在实践中却留下了先前未被触及的领域,没有抓住先前的对立,那么就会失去任何有效地干预该领域的手段。我们知道什么是直接跳过对立和用既非这个又非那个的简单形式进行抗争的实际结果(特别是政治结果)。”[13]48那就是“既置身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却又毫不介入其中”[18]的行为态度。巴尔特虽然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其一生却远离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甚至在革命来临的时候选择逃避,他之所以会这样,就是“中性”在转化为一种生存论后所造成的恶果。换言之,这也是“中性”的限度。接下来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
三、话语伦理学
在《中性》这本书中,解构语言并不是巴尔特的终极目的,其终极目的在“论据”中交代的非常明确:“我们的目标并不在学科方面,因为我们的探索跨越了语言、话语、姿态、行为、身体等等。但是,由于我们对于中性的探索涉及聚合关系、冲突、选择,我们思考的一般领域将是:‘从善而择’(不玩弄政治的游戏)、‘不选择’或‘另作选择’的话语伦理学。”[2]8在五六十年代,黑格尔、海德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四位思想家对法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影响就没有法国当代哲学的辉煌。然而,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巴尔特却认为他们没有关于伦理学的话语,“他们没有(或者是不想)提供给他们自己可以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或者毋宁说,伦理学在他们那里也许被压抑了”[2]8。这一评价是否准确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巴尔特是从什么角度作出这一评价的。答案自然是语言符号学。黑格尔、海德格尔、马克思是非常纯粹的哲学家,他们是从正统哲学的角度来建构他们的理论。和他们相比,弗洛伊德则显得非常随意,他的领域是精神分析。这些人在世时,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或方法论闻所未闻,只有到了巴尔特才由一种假想变成现实。
从符号学的角度,或者说以符号学作为方法来创建话语伦理学具体是如何展开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以上的讨论。上述中,我们曾提到语言结构的断言性,巴尔特将它视为语言学的丑闻,因为“是(+)/否(-)”这样的判断始终镌刻在语言结构之中。然而,众所周知,话语作为更高一级的形式是确立在语言结构之上的,既然语言结构是断言性的,那么话语必然也会是断言性的。“这个是”“那个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类似的说法在日常生活中层出不穷。古代的怀疑论者早就指出这种判断所存在的问题,即将自己的感知经验当成了事物的属性。在《论感觉》中,古希腊著名的怀疑论思想家蒂孟说:“我并不认为蜜是甜的,但我承认它显得是甜的。”[19]“某某东西是什么”和“某某东西显得是什么”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前者是独断论,而后者只是在描述某种事实。胡塞尔在他的现象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即我们的认识只是到经验为止,超出了经验的范畴我们的判断就不具有有效性。所以,当我们说“某事物是什么”的时候必须警惕,不能忘记它的重要前提即“我们认为”“在我们看来”“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感觉到”,等等。在现象学和怀疑论哲学的启发下,巴尔特对话语进行了全面的解构。
恩斯特·勒南(ErnestRenan)是法国著名的宗教史家、作家和语言学家,他在一次大会上声称:“女士们和先生们,法语从来就不是荒谬的语言,也从来不是反动的语言。我根本想象不出一种严肃的反抗会以法语作为发音手段。”[5]460勒南说这番话的目的是为了强调法语作为民族语言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理性的,它从来不会充当意识形态的工具,更不会受到权力的驱使。当时这种语言上的清洁主义在法国很有市场,特别是在那些追求“纯文学”的作家们(如魏尔伦、兰波、马拉美、瓦雷里)中间。然而,巴尔特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作为语言结构之运用的语言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进步的;它完全是法西斯主义的”[5]461。在这里,“作为语言结构之运用的语言”实际上也就是话语。话语一经说出,即便是从主体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它也会自然而然地为权力服务。巴尔特将这种话语称之为“支配性的话语”[20]143。它在形式上主要由这样几个要素构成:(一)话语支配的主体;(二)话语支配的对象;(三)话语支配的过程。在《夏吕斯的话语——一种话语的分析提纲》(1977)中,巴尔特引述了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里面的一个细节来说明这种话语的支配作用:小说的叙述者在结束盖尔芒特夫人举办的家庭晚宴之后匆忙赶赴与夏吕斯男爵的约会。他在门厅等候良久,终于得到夏吕斯的接见。他本来以为夏吕斯会热情地迎接他,不料却遭到了话语的奚落:
“您坐到那张路易十四式的椅子上去,”他以命令的口吻回答我,与其说在叫我坐下,不如说是强迫我离他远一些。我在离他不远的一张安乐椅上坐下。“哼!这叫路易十四式的椅子呀!亏您是一个有知识的年轻人。”他用嘲笑的口吻嚷道。 ……“您甚至不知道您坐的是什么椅子。我让您坐路易十四式安乐椅,您却一屁股坐到了督政府式样的烤火用的矮椅上。过两天,您也许会把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膝盖当马桶呢。谁知道您会在上面干什么。”[21]
凡是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知道,这番话从夏吕斯男爵的口中说出一点也不稀奇,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他就是一个充满控制欲的人,即巴尔特意义上的“话语支配的主体”。在这个场景中,夏吕斯显然运用了一系列策略素:首先是故作高深的文化编码(路易十四式的椅子/安乐椅);其次是断言性的言语行为(“这叫路易十四式的椅子呀!亏您是一个有知识的年轻人。”);最后是虚假的逻辑推理(“过两天,您也许会把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膝盖当马桶呢。”)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将小说的叙述者变成他话语支配的对象。“他的话语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策略(直接的算计),而是属于一种晦涩难解的,甚至主体自身都尚未意识到的策略(参考后面的‘表达’、‘爆发’)。不过,我确信:策略=获得或者控制叙述者。除此之外,还存在某种无策略的话语吗?任何话语:隐性地或者无意识地,都想把他者(其他人)作为目标,也就是说,想将他者视为可占有、可支配的对象。根本就不存在无意图的话语:只要说话,必定有所期待。如果没有策略=沉默,话语就失去了它的功能(精神分裂症的形式?自闭症的形式?)。”[20]164尽管这段引文并没有完全展开,可它的内涵却清晰可见,即在话语背后经常隐藏着意识形态的要素。
巴尔特的上述思想和福柯有很多的交集。在《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知识考古学》(1969)、《疯癫与文明》(1972)、《性史》(1976,1984)等著作中,福柯深入地探讨了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在他看来,话语就是规则、秩序、分类和控制手段,借助于科学、真理、禁律、仪规、信条等名义,话语总是在不断地滥施它的淫威,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被规训的个体”[22]。在巴黎学术界,有人认为巴尔特“总是带着福柯情结”[23]。言下之意,巴尔特在步福柯的后尘。其实,大凡熟悉原样派(TelQuel)的人都知道,不仅在其核心成员之间,即便是在其外围成员之间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帕特里夏·弗朗奇(PatrickFfrench)在回顾原样派历史时就说,这些人拥有“共同的分母”[24]。为了揭露和批判隐藏在话语中的权力,福柯求助于尼采的谱系学,而巴尔特则逆流而上回到了语言学。他天真地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语言本身的问题,特别是由于语言的断言性所造成的,而忽略了语言之外的其他因素如阶级、阶层、文化、制度、习俗等也加于其中。他曾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局限,却并未做出相应的改变,仍然执拗地从语言内部来思考问题。*1980年2月,即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巴尔特在接受《新观察家》记者菲利普·布鲁克斯(Philip Brooks)的采访时说:“我经常从语言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是我的局限所在。知识分子不能直接攻击权力当局,但是他们可以用论说的方式来改变事物。”参见Roland Barthes, The Grain of the Voice: Interviews 1962-198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p.362。这段话体现得非常明显:“因为话语是由生来就是断言性的语言构成的,断言性的制约也就从语言运动到了话语之中。这也就意味着,要想将话语从断言中抽离出来,使它能够表达细微的差异(取向否定、怀疑、疑问、悬置),我们就必须不断地跟语言的原材料及话语的‘规则’作斗争。”[2]43《中性》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开断言,确立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从而引导人们更好地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怎样才能避开断言呢?古代怀疑论者所采取的方法是悬置判断,不妄下断语,对所有可能成为问题的事情始终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所以他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这样做在生存论上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能够使人们摆脱各种纷扰,始终保持内心的宁静。从这里巴尔特深受启发,他在将“中性”定义为“破坏聚合关系之物”后不久又对它作了新的界定:“中性=主张沉默的权利——一种沉默的可能性。”[2]23换言之,“中性”就是在面对各种断言时保持沉默,因为“既不,也不”“非此非彼”原本就是这个词汇固有的含义。是/否/既是又否/既否又是,这些都是我们在面对某些事物时的态度,巴尔特认为不管采取哪种方式,或者选择什么样的立场,实际上都掉进了断言性的陷阱,只有不置可否才能避开它,这是“中性”的方式,同时也是恪守沉默的方式。
将“中性”与怀疑论结合起来,这是《中性》这本书最鲜明的特色。然而,大家知道,怀疑论在历史上口碑并不是很好。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就明确指出:“自古以来,直到如今,怀疑论都被认为是哲学的最可怕的敌人,并且被认为是不可克服的,因为怀疑论是这样的一种艺术,它把一切确定的东西都消解了,指出了确定的东西是虚妄无实的。因此几乎成了这样的局面,仿佛怀疑论本身就是不可克服的,仿佛分别只在于看个人究竟是决意信从怀疑论,还是决意信从一种积极的、独断的哲学。……我们有一种想法,认为一个人如果投入了怀疑论的怀抱,便无法与他接近了;而另一个人却只是安守着自己的哲学,因为他对怀疑论是不加理睬的,——真正说来,他应当这样做,因为真正说来,对怀疑论是无法反驳的。”[25]对于历史上那些怀疑论者,费希特也语带轻蔑地说:“在这些松懈、麻痹、善变、华而不实的人身上,有一大堆的相反的命题和矛盾,他们却能相安无事地比肩而立。在他心里,没有一个是清晰的或者独立的,所有的东西都混在一起,纠缠在一起。这种人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是对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错的。他们既不热爱什么,也不憎恨什么,无爱无恨是他们的基本状态。因为爱或恨,每一种情感的发生都需要积聚能量,而这点他们根本做不到,理由很简单,要想选择某种情感,他们就必须判断。”[2]70-71面对这些指责,巴尔特却毅然决然地将“中性”和怀疑论嫁接在一起。在他看来,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够避开各种矛盾冲突。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不仅从古希腊哲学中寻找理论资源,还将目光转向东方,因为无论是禅宗还是道家,它们都推崇“不言之教”。比如老子在《道德经》中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就不是常道;可以说出来的名,就不是常名。”[26]形而上学的“道”和“名”是无法言说的,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用来表述它们。通达它们的方式,只有老子所讲的“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或庄子所讲的“心斋”“坐忘”“涤除玄览”,自行切断与世俗世界的联系,剔除一切身心挂碍,当然也包括语言,才有可能达到这种形而上学的境界。所以,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中国历代禅师在参禅悟道的过程中也意识到若执著于语言文字,便只会泯灭自身心性,陷入各种机巧,从而难得佛法大意,正所谓“言语道断”。百丈怀海在教化僧众时指出参禅悟道的关键就在于必须“割断两头句”“透过三句语”,即割断两个矛盾对立的判断对人的束缚,透过“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的执障,直契大道,立地成佛。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巴尔特并不能深刻领会禅宗要义,而是用西方的怀疑论思维来简单图解禅宗的智慧。
在《中性》这本书中,他首先谈到了禅宗的心印活动。《祖庭事苑》卷八云:“心印者,达摩西来,不立文字,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黄檗禅师传心印法要》卷上云:“自如来付法迦叶以来,以心印心,心心不异。……若能契悟者,便至佛地矣。”在此,心印之心既是人心也是佛心,依照禅宗的思想,假若人心与佛心相契,便是开悟。巴尔特之所以援引佛祖传禅于摩诃迦叶的例子,因为在他看来这就是一种沉默的艺术,而这种沉默不是宗教的沉默,而是怀疑论的沉默,其目的就是要阻止语言以及由语言所产生的信息——各种断言、价值或者意义。在《符号帝国》(1970)一书中,他曾按照自己的思路详细阐释了这一活动:
……这是一个正在从事于心印活动(或正接受大师教导)的佛教徒所要做的事:不是去解决问题,好像它拥有某种意义,甚至不去怀想它的荒谬(这仍然是某种意义),而是认真领会,“直到牙齿脱落”。由此,整个禅宗(俳句仅仅是它的一个分支)便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实践,它注定要阻止语言,堵塞那不断向我们发送的内在电波,这种电波甚至出现在我们的睡眠之中(一些佛教徒有时不睡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抽空灵魂中不可压制的低语,使之呆如木鸡,使之欲语忘言。这大概就是禅宗的“悟”,我们西方人只能用一些语义含混的基督教术语(启迪、启示、直觉)来翻译。悟,不过是对语言的悬置,这种空白消除了符码对我们的统治,内心记忆的破灭建构了我们的人格。如果说这种非语言(a-language)的状态是一种解放,那是因为在佛教徒的实验中,第二级思考(对思考的思考)的增长,也可以称为所指的无限增补——能够形成一种循环。在这个循环中,语言自身则是仓储和范式——显示出一种阻塞作用:它反而取消了第二级思考,由此打破了语言的恶性循环。显然,在所有这些实验中,不是用玄奥的沉默来挤压语言的问题,而是对付它,将旋转着的语言陀螺——它沉溺于自己的旋转,即符号替换的强迫性游戏——加以阻塞的问题。简而言之,它是饱受攻击的语义操作的象征。[27]74-75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深究什么是“第一级思考”“第二级思考”,这仅仅是他的一种“障眼法”,其实巴尔特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确,即禅宗的心印活动就是要阻塞语言,从而达到“无言”(aphasia)的状态。“寂”(さび,Sabi)是日本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常与“物哀”“幽玄”相并列,主要指一种自由、洒脱、淡泊、宁静的生活状态,因此有时也被称为“风雅之寂”。巴尔特从日本学者冈仓天心的著作中借取了这个概念并且用它来描述禅宗所追求的无言状态。他认为“寂”可以定义为:“简洁自然,不落窠臼,优雅精致,无拘无束,超然淡定的亲切感,它用内在的超脱巧妙地遮蔽起了日常生活的庸碌。”[2]35很显然,巴尔特不但将禅宗的心印活动精致化了而且浪漫化了,使之变成了一种“优雅的原则”。随后,他又把“优雅”等同于“温和”,甚至将“温和”视为“优雅”的最后的代名词。如此复杂的语义转换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巴尔特要千方百计地将怀疑论植入自己的哲学,至于禅宗的本义是否如此早已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
在《中性》里,他还用了很多篇幅来讨论禅宗公案。铃木大拙在《禅论集》中曾记述了高峰和他师傅的故事。一日,高峰问:“师傅,是谁穿着你这身臭皮囊?”师傅听后操起棍子便打,高峰让他住手,并说道:“今日您不可打我。”师傅问:“缘何道理?”高峰没有回答,却抬脚走出门去。次日,师傅问:“万物归一,一归何处?”高峰说:“狗添锅里的沸水。”“你从哪里学来这等蠢话?”高峰回答:“您何不问问自己。”师傅听后十分满意。[2]113-114众所周知,禅宗是反智主义的,禅悟的最大敌人便是逻辑和理智。“当人们用逻辑来认识整个世界,以分别智来分别整个世界的时候,禅否定逻辑,否定理智,肯定直觉,肯定体验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意义,并认为唯有原初的直观体验,完全摆脱了分别智和逻辑污染的直观体验,才能把握本来的世界和生命的原初内涵。”[28]所以,禅宗十分推崇不落言荃、不涉理路的答非所问(有时也称之为“聋子乱打岔”),高峰和师傅的对话就体现出了这点。然而,对于禅宗的这一言语行为巴尔特有自己独到的解释:
答非所问=“聋子的对话”=一种经验,一种装聋作哑的策略。因为它可能是歇斯底里的(选择性的耳聋或听觉过敏)。有一种聋子的权力:通过一种神话学的否定,人们把耳聋和失聪混为一谈。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喧嚣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噪音(话语)“污染”。耳聋是一项权利——一项尚未获得认可的权利。[2]120
在巴尔特看来,任何问话都带有“恐怖主义”的特征,即无论你做什么,如何回答,都会像一只被套牢的老鼠,因为发问者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已经为你铺设了一个陷阱,你要么顺着他的陷阱往下跳,要么不回答。假如你真的不回答的话,那么不是被视为默认就是无知。总而言之,在几乎所有的问答逻辑背后都隐藏着意识形态素。所以,巴尔特感慨地说:“任何问话都可以被解读成一种提问、权力和宗教审判的场景(在政府和官僚机构中尤其如此)。”[2]107而禅宗的答非所问不仅能够让人跳出语言的窠臼,而且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
巴尔特说:“在思考东方的时候,能够表明的不是另一种符号,另一种形而上学,另一种智慧(尽管后者看起来让人迷恋),而是符号体系的规范中所产生的一种差异、一种变革和革命的可能性。”[27]3-4也就是通过东方——即便是已经被东方化了的东方——来反观西方,借他人的镜子照自己的面孔。在跨文化沟通中,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思路。然而,从这些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尔特在理论吸收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忽略了禅宗和道家哲学的形而上学因素,将它们“澄怀味道”“绝言绝虑”的方法直接当成了一种生活实践,用祈向神圣的超越之维直接取代了庸常的生存经验,结果只会是将人从日常生活中连根拔起,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然而,比这更为重要的,巴尔特只注意到了东方文化相对消极的一面,而忽略了它积极的一面,即儒家文化所体现的践行态度和入世精神。在讨论巴尔特的文学时,有学者认为“仁学的人本经验自然主义使其能够摆脱唯逻辑主义的框架和前提,并从个人的社会性实践(另一种‘独修共同体’形态)提供了一种历史伦理学指南。这样,作为西方文学‘本质’的价值虚无主义,将可从东方解释学的仁学传统中获得重要的另类启迪”[29],可遗憾的是,在巴尔特的著作中,我们根本找不到仁学的影子。晚期,由于巴尔特对怀疑论哲学以及东方哲学中这些消极因素的信从,使其理论解构的锋芒日趋黯淡,最后他直接躲进了自己编织的乌托邦里以逃避外面的世界。*详情参见拙作《晚期罗兰·巴尔特与怀疑论哲学》,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21-26页;《新华文摘》2016年第3期网络版全文转载,网址:http://www.xinhuawz.com/page/ArticleList.aspx。“这种彻底的沉默已经不再是缄口不言,而是万籁俱寂了。在大自然的沉寂中,人类四处飘散,他们仿佛(在控制论的意义上)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些杂音。”[2]29
[1] BARTHES R. 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M]. London: Macmillan Press,1977.
[2] BARTHES R.The Neutral[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3] 张智庭.罗兰·巴特的“中性”思想与中国[J].文艺研究,2016(3):39.
[4]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李书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196.
[5]BARTHES R. Inaugural Lecture, Collège de France[C].London: Jonathan Cape,1982.
[6] 克拉姆斯基.音位学概论[M].李振麟,谢家叶,胡伟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7]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 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5.
[9] 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M].蒋梓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30.
[10] BARTHES R. The Grain of the Voice:Interviews 1962—1980[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310.
[1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M].于秀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54.
[12] 卡勒.论解构[M].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3] 德里达.多重立场[M].佘碧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4] 张一兵.可能的存在之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23.
[15] 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433.
[16] 早川.语言学的邀请[M].柳之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09.
[17]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下册[M].盛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03.
[18]BARTHES R. Writing Degree Zero / Elements of Semiology[M].London:Jonathan Cape Ltd,1967:77.
[19] 拉尔修.名哲言行录:下[M].马永翔,赵玉兰,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2011:519.
[20] BARTHES R. How to Live Together[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21]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III[M].潘丽珍,许渊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536-537.
[22]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M].London: Penguin Books,1977:308.
[23] 阿尔加拉龙多.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M].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5.
[24] FFRENCH P. The Time of Theory: A History of Tel Quel(1960—1983)[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17.
[2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15.
[26]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9:58.
[27] BARTHES R.Empire of Signs[M].New York: Hill and Wang,1982:74-75.
[28] 华梵.空悟的心性[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8:106.
[29] 李幼蒸.解析罗兰·巴尔特的“实证虚无主义”美学[J].现代中文学刊,2009(1):104.
(责任编辑:紫 嫣)
"Neuter": the Nucleus of Roland Barthes′ Aesthetics
JIN Song-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01, China)
Roland Barthes borrowed the concept "neuter" from structural linguistics of N.S. Trubetzkoy, Louis Hjelmslev and Viggo Brondal, and incorporated it into his methodology with a series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s. In this way, he deconstructed these ideologies hidden in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and discourse. However, in his later years,Barthes combined the "neuter" with ancient skepticism and oriental Zen and Tao philosophy, a wrong grafting that not only weakened the strength of deconstruction, but also plunged him into a quietistic quagmire. Therein lie the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of Barthes.
Roland Barthes; aesthetics; neuter
2016-11-14
金松林(1978—),男,安徽宿松人,哲学博士,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现代美学研究。
B83-0
A
2095-0012(2017)01-008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