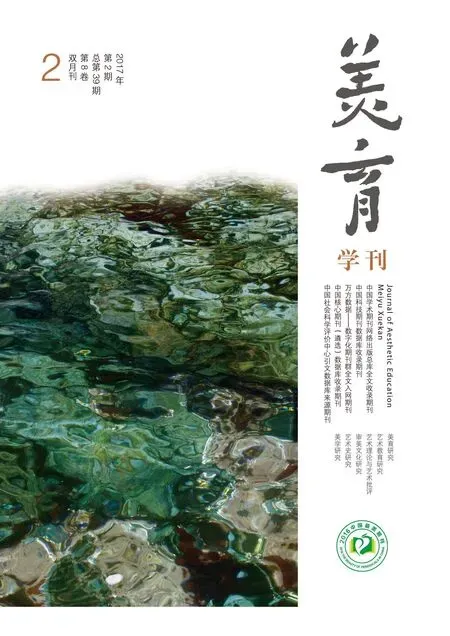鼎与新石器中期陶器的审美观念
张 法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鼎与新石器中期陶器的审美观念
张 法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鼎由炊器之釜加上三足升高而来,从裴李岗文化始有了体系性的结构,并向东西南北演进,成为饮食器中的核心。鼎的观念内容,不但从文献上黄帝之鼎和禹启之鼎的传说中,更主要从甲骨文鼎字的构成,以及从鼎字与其他如贞、旨、凡、匕字的关联上体现出来,形成一个鼎—贞—正的统一体,并使鼎在成为仪式核心之器的同时,成为美之器。
鼎;起源演进;结构定型;观念内容
公元前7000年后,现今中国的地域中进入新石器文化中期,涌现了约20个考古学文化,各文化在经历早中晚三段的互动中,呈现为三大地域文化,这些文化在陶器上的特征表现如表1:*此表据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1页)约改而成。

表1 三大地域文化在陶器上的特征表现
表1中可见,华北和东北延续新石器早期着罐的传统,而另两个地区已经从釜和罐中扩展为多样器形。从陶器体系上讲,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裴李岗文化的鼎和高庙文化的豆。如果说釜是炊煮器和盛食器的统一,罐是盛食器和贮食器的统一,那么,鼎则在此基础上有质的提升;如果说,盆以盛食为主,那么,豆则是在盆基础上质的提升。鼎和豆相对于釜—盆—罐进行提升的所谓“质”,从器形学上看,体现在高度上:鼎似乎在釜上加了三只脚,豆好像用高脚把盆进行了支高。这一器形升高,透出了远古中国在饮食器的器形演进和观念演进中的具有本质性的东西。本文且只对鼎进行论述。
一、从支脚到鼎
釜从炊煮的实用角度进行提高,最初的想法是对之加上支脚,严文明讲,支脚从新时期早期(从河北的磁山文化到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开始分布在河北、山东、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台湾、广东的广大区域。大体在燕山山脉以南、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以东的平原和丘陵地区。而且与鼎文化区基本重合。[1]因此,透出了由支脚到鼎的演进逻辑。支脚并不限于炊器之釜,也用盛器的盆盂和贮器的罐缸,因此类型甚多,严文明将之分为七型:倒靴型、猪嘴型、馒头型、角型、圆柱型、塔型、歪头柱型。吴伟进一步归纳为两个大类:直腹盆盂支脚系统和圆底釜罐支脚系统。前者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及黄河以北这一地区。后者可细分为六个支系。沂泰、胶东、长江中上游、杭州湾、珠海、台湾。并列出了支脚分布图(图1)如下:[2]

图1 中国古代陶支脚区域分布图
支脚虽然在釜、罐、盆、盂上普遍存在,但在器形上的成功升级却是最初产生鼎(然后是鬲等其他器形),而盆盂支脚的升级最初也以鼎的方式出现,后来才转向两类具有自身特质的器形,一是三角大变形的爵等酒器,二是看不出由之而来的豆等食器。器形的升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下面是陈文玲对釜、鼎、支脚在考古地理上的分布图(图2)[3]:

图2 陶鼎、陶釜、支脚的分布图
由此可见远古各族群在由陶器上附加支脚向新的器形上演进上的艰辛。最后鼎作为这一探索的成功升级出现。从严文明文章中举的磁山文化支脚实例(图3),可以直观地看到,只要达到技术条件,鼎一定会出现。

图3 磁山文化支脚实例
二、鼎的类型
在率先实现鼎的成功升级的裴李岗文化,呈现的是釜、盆、罐在鼎上的全面升级,王兴堂等把裴李岗的鼎分盆型鼎、罐型鼎、钵型鼎三种类型共18式。*A型盆型鼎有3亚型10式(Aa4式、Ab3式、Ac3式),B型罐型鼎有2亚型5式(Ba2式、Bb3式),C型钵型鼎有3式,三型共18式。见王兴堂、蒋晓春、黄秋鸯《裴李岗文化陶鼎的类型学分析——兼谈陶鼎的渊源》,载《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且举其分类的三型数式(图4、图5、图6)如下:

图4 盆型鼎

图5 罐型鼎

图6 钵型鼎

的复杂变化,牵连到炊器、盛器、贮器之间在转型和互动中的复杂关联。《尔雅·释器》把鼎归为五类:鼐、鼒、釴、鬲、鬵,就透出鼎的体系包含鼎、鬲、釴三种器形互动融合的结果。裴李岗的陶鼎体系,第一次突出了一种新器形的重要,里面内蕴着重要的观念体系。这观念应当是后来的鼎字内蕴的观念之核心。这一观念内容,虽然以后的三足器由之演变出鼎、鬲、鬶、斝的丰富展开,进而又有尊、彝、觥、盉的酒器加入进来,但鼎在与其他三足器的互动中最后保持了重要位置。从考古上看,裴李岗(前7600—前5900)、磁山(前7400—前7100)、北辛文化(前7400—前6400)、老官台(前7800—前7300)基本上同时出现鼎,其中裴李岗最强,磁山、北辛、老官台则逊色一些。极有意味的是,由老官台演进到半坡时,鼎在关东的半坡遗址(如苪城东庄村,永济金盛庄,万荣刘村,襄汾赵康村,陕县三里桥一期,王湾一期,偃师汤泉沟、浙川下集和下王岗早一期等)中继续着[7],却被关中的半坡类型拒绝了。大地湾例子最为经典,鼎在大地湾一期(属老官台文化)占有相当的地位,且看表2数据*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综合第32页两表与第63至66页内容而制。:

表2 大地湾一期陶器器类表
而且大地湾一期的鼎其由无底演进上升高的理路也较为明显,且看图7和图8:

图7 罐形鼎的演进

图8 钵形鼎的演进
但在大地湾二期(前6500—前5900,属仰韶文化早期),鼎就不见踪影,而彩绘和图案特别强烈,鱼纹、鸟纹、花纹产生出来,盆(盎)占有了主导地位。这一结果只应以观念来进行解释。当大地湾一期作为老官台文化与裴李岗、磁山的鼎趋势相向而行时,鼎产生了;当大地湾二期作为仰韶文化在关中的崛起,有自己具有地域性的文化方向时,鼎就被拒斥了。整个仰韶文化的兴起,从大地湾二期到姜寨到半坡,基本上没有鼎的作用。而当仰韶文化出现在豫北冀南以后岗(前6500—前6000)、钓鱼台、大司空出现时,鼎又突显出来。当半坡类型演变为庙底沟类型(前6000—前5300)进入河南的伊洛—郑州地区,鼎再一次继续大放光芒。韩建业在《早期中国》第47页用图呈现了鼎由前9000—前5000段的裴李岗—贾湖—双墩核心圈经过四个年段(前7000—前6200、前6200—前5500、前5500—前4500、前4500—前4000)向东西南北四面的扩展,该图仅是简约性标注,总而言之鼎在整个东南地区(从北辛到大汶口到山东龙山文化,青莲
岗到薛家岗到龙虬庄到崧泽文化,从河姆渡到马家滨到良渚文化,从大溪到屈家岭到石家河文化,乃至更南的昙石山、石峡、石脚山)全面鼎鼎有名,而仰韶文化也在进入中原成为庙底沟文化之后,把鼎庄严地纳入怀中,让鼎在大河村中大放光芒,本在整个东南都有优势的鼎也随之入主中心,且影响四方,连鼎味不大的西北(西到齐家,北到老虎山),也可见其光耀闪烁,如大地湾四期的红色瓦足鼎和甘肃火烧沟顶有三兽的方鼎,作为礼器性质甚为明显。
古代文献正是在庙底沟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期,产生黄帝之鼎的记载。《史记》的《五帝本纪》讲黄帝获宝鼎,《封禅书》讲黄帝“作宝鼎三,象征天地人”,总而言之,突出了鼎的重要。到夏之时,又有《左传宣公三年》讲禹铸九鼎和《墨子·耕柱篇》讲启铸九鼎的说法,九鼎作为朝廷拥有天下的象征,成为从夏商周到秦汉的重大主题。再从夏之九鼎、黄帝三鼎回到鼎的体系出现之初的裴李岗。裴李岗文化包括新郑裴李岗和唐户、舞阳贾湖、郏县水泉、沙窝李、密县莪沟北岗、长葛石固、巩义瓦窑嘴、孟津寨根,分布在河南大部分地区,在贾湖,不但有鼎的体系,还有内蕴七声音阶的成双骨龠,龟甲、绿松石饰器。韩建业说,裴李岗文化在强盛时的向外扩张和衰败时向东迁徏而产生与周边各文化的持续互动,产生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型。[8]
三、鼎的观念
鼎在裴李岗文化中体系地出现,有着怎样的观念内容呢?
鼎,《说文》曰:“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鼎的功能是“和五味”,可见鼎的核心来源的是釜。《吕氏春秋·本味》里伊尹讲调味,说的是“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关乎“四时之化,阴阳之数”。回到远古,这是以鼎为核心的仪式观念。鼎以釜的炊煮功能为主,加上盆的盛食功能和罐的贮食功能,从炊的角度讲鼎就是“镬”,鼎镬一词,重点在镬,强调的就是釜的功能,因此高诱注《淮南子·说山》曰:“无足曰镬。”偏重于鼎,就是从鼎的调好味之后盛食展示的功能讲,这时镬亦为有三足之鼎。但从有了鼎而釜转为镬来讲,又是要把釜—盆—罐体系中的罐的内在本质贯穿到鼎中去,镬字中的“萑”与罐字中的“雚”具有了内质上的同一。以鼎为核心的饮食器新体系得以建立。鼎之成为核心,不仅在通过镬鼎而进在思想上的统一,更在于与传统思想相通而又有新的提升,这就是后来鼎字中的“目”。这目可以说是对雚中的双目“吅”的提升。吅作为太阳鸟之目,具有一种普遍的天道性质,这是一个凝结了悠久历史和各方文化的共同点,从远古各地岩画到各地玉器,到各地彩陶,都或明或隐内蕴着这天道之目,邓淑萍将之称为“旋目祖神”,王仁湘从天地运转的角度讨论旋目,似可合称为旋目天神。*参见王仁湘《史前中的艺术浪潮》“旋纹:旋目之神”一节,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87-510页。把横着的“吅”竖起来就是“目”,横之吅与竖之目是旋的两种最基本的形态,后来太极图的两个小圆,也是旋目,是从阴阳互含和与阴阳合和的角度讲旋目。鼎字的目在器上,正是旋目与器之间的互动关联。当然这已经是篆文时代的定型了,在甲骨文,鼎上的旋目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的:







鼎,正因为内蕴了如此多的观念内容,在成为仪式核心之器的同时,成为美之器。
[1] 严文明.中国古代的陶支脚[J].考古,1982(6):622-629.
[2] 吴伟.史前支脚组合炊具的区域类型分布与兴衰[G]//贺云翱.长江文化论丛·第六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4-8.
[3] 陈文玲.中国史前的釜鼎文化[J].南方文物,1996(3):11-24.
[4] 余西云.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陶鼎研究[J].华夏考古,1994(2):61-71,108.
[5] 石兴邦.白家聚落文化的彩陶——并探讨中国彩陶的起源问题[J].文博,1995(4):3-19.
[6] 张忠培.关于老官台文化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81(2):224-231.
[7] 严文明.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J].考古与文物,1980(1):64-72.
[8] 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J].中原文物,2009(2):11-15,40.
[9] 李圃.古文字诂林:第3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0] 郑玄.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31.
(责任编辑:刘 晨)
Aesthetic Conception of the Tripod and Neolithic Pottery
ZHANG Fa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The tripod is composed of a cooking vessel and a supporting tripod. Starting from the Peiligang culture, it began to assume a systematic structure, spread from east to west and north to south and became a principal eating utensil. The aesthetic concept of the tripod is manifested not only from the legends in the literature about the tripods of Emperors Huang, Yu and Qi, but also more importantly, from the oracular characters engraved on the tripods and the connection of the word 鼎, which means a tripod, to words such as 贞、旨、凡、匕, Which mean respectively loyalty, royal edict, all and dagger. A unity can thus be traced among the tripod, loyalty and orthodox. Thereupon, the tripod became not only the central instrument in various rituals but also an instrument of beauty.
tripod; evolution of the origin; structural stereotypes; conceptual content
2017-02-05
张法(1954—),男,重庆市人,教育部“长江学者”,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与中国美学史研究。
K876.3
A
2095-0012(2017)02-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