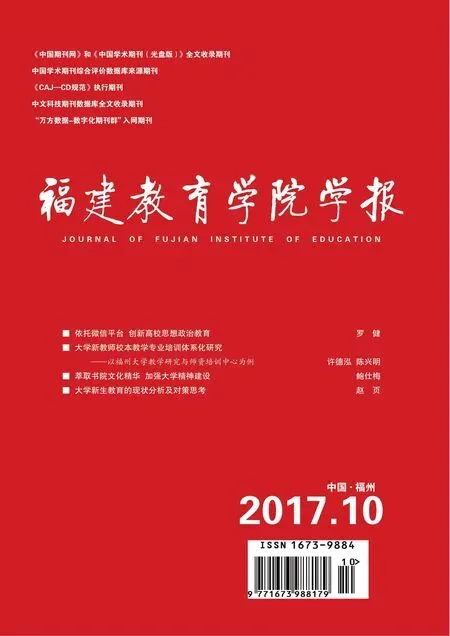白鹿原上扑火的飞蛾
——田小娥悲剧形象分析
黄伟群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白鹿原上扑火的飞蛾
——田小娥悲剧形象分析
黄伟群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最具悲剧性的一个女性形象。田小娥一生追求肉体的欢乐和精神上的自由,却在不同的男人之间不断撕裂自己的身心;由于时代动荡、封建宗法礼教压迫,更重要的是自身性格的弱点,田小娥在这个悲剧的社会中演绎了一场属于自己和中国妇女的悲剧。
《白鹿原》;悲剧命运;女性独立;个性自由
《白鹿原》是当代文学史上一部巅峰之作,“它继承了古今中外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中最优秀的东西,是整个人类文学史长期发展的智慧和结晶”。[1]陈忠实以厚重而又极具张力的语言和魔幻传奇令人记忆深刻的情节,“突破了顽固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一个时代一部文学’的观点,为我们文学创作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天地”。它“是史诗,重要不在写史,而写人的心灵、性格、命运,折射着历史文化的夺目光彩”。[2]陈忠实通过对历史中的人的描写,展示人的历史——心灵史和生命史,揭秘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蕴含着浑厚恢弘、苍凉深邃的史诗风韵和血泪交融、悲剧交叠的文化底蕴,塑造了田小娥、白灵等个性鲜明、命运迥异的女性形象,展现了一幅幅极具中国乡村特色的“悲剧女性人物画卷”。
在白鹿原众多女性形象中,“水性杨花”的田小娥无疑是《白鹿原》人物系列中最具悲剧性的一个。这个以“淫妇”“祸水”“女鬼”等标签被六棱砖塔镇压的女性形象,其悲剧命运所辐射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境丰富。在这个男人主宰的父权社会里,白鹿原上的女人饱受来自宗法社会的压迫和摧残,田小娥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出于本能地追求灵肉和谐的爱情和平平淡淡的幸福家庭生活,并为此不断挣扎、反抗。然而,弱小的她依然无法逃离身心俱灭的悲剧命运,由追求真情到走向堕落,由洁身自好到拖人下水,从肉体放纵死亡到灵魂被永世镇压。其短暂的一生充满苦难和血泪,令人怆然,发人警醒,震撼人心。
一、田小娥悲剧的一生:生命到灵魂的撕裂
《白鹿原》人物众多,事件繁杂,田小娥的故事是其中关键的枢纽。田小娥人生轨迹发展的每一步都关联着与之相对应的人物和命运。如果说娶过七房女人的白嘉轩是白鹿原上“正义”“秩序”的化身,田小娥就是闯进白鹿原破坏秩序的“恶之花”,与白鹿两姓家族的争斗都发生了密切联系:和鹿家黑娃私奔进入白鹿原,“风搅雪”的农民运动失败后,她转向鹿子霖的怀抱,又受鹿子霖的唆使与白孝文鬼混,后赤条条的在祠堂前和白孝文被白嘉轩毒打,最后被鹿三用梭镖杀死,死后化为瘟疫为祸乡里,被白嘉轩用六棱塔镇住。田小娥出身于一个穷秀才家,貌美如花,体态妖娆,却被不负责任的父亲嫁给了一个七老八十的武举人郭财东做妾。虽说是二房,实际上就是一个给郭财东养生的泡枣工具,一个月只有三天同房时间,“敦伦”的时候大房甚至还在旁边监视。剩下的日子就是每天泡三个枣,早晚端尿壶,给长工做一日三餐。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得不到身体和精神上的满足,面容跟她的人生一样黯淡无光。田小娥不甘心过这样的日子,天天用尿泡枣给郭举人吃,发泄怨恨;遇见黑娃之后,一次假摔、两声“哎吆”,把黑娃从井边带到炕上,将情窦初开的黑娃揽入怀中,勾搭成奸,夜夜厮混。
好景不长久,他们的奸情被郭财东发现,郭财东倒是大度,没有把他们浸猪笼或一棍子打死,只是辞了黑娃、休了田小娥把他们打发了。黑娃到田小娥娘家打探消息,从田秀才家长工口中得知,大丢面子、羞愤不已的田父准备将丢人现眼的田小娥扫地出门。黑娃趁机提出要娶田小娥,田秀才大喜过望,倒贴给他两摞子银元,并声称从此最好不要往来了。
两人回到了白鹿原。可是在以“仁义温情”著称的白鹿村,两人伤风败俗的爱情和婚姻不被祝福,公公鹿三不接纳,以白嘉轩为首的白鹿村民不准她进祠堂。黑娃只好带着小娥在村外的一破窑洞安家,虽然远离村社,却总算有了自己的窝。田小娥决定从此安心过好小日子:“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3]此时两人终于从两性吸引升华到两情相悦。这段破窑洞的蜗居日子,使田小娥达到了她人生的鼎峰——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满足。
然而,幸福平静的日子在动乱的年代是无法长久的,何况黑娃从来就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随着黑娃为了实现童年的“冰糖”梦想追随鹿兆鹏在白鹿原上撒起“风搅雪”,闹起了革命,小娥的幸福日子也到头了。革命运动失败了,黑娃出逃了,田小娥留在四面楚歌的白鹿原上,掀开了人生最为悲惨岁月的序幕。
失去了黑娃,意味着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六神无主的她四处奔走,哀求当权派鹿子霖挽救黑娃。鹿子霖垂涎于她的美色,诱骗田小娥以肉体相报。孤苦无依的田小娥病急乱投医,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只能出卖唯一的武器——青春的肉体,去寻求挽救丈夫苟活生存的些微希望,却不曾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对黑娃而言,是一次赤裸裸的背叛。
不久,村里的花痴光棍狗蛋儿意图染指田小娥,天天骚扰,还发现了鹿子霖与小娥的奸情。田小娥听从鹿子霖的挑唆诱惑狗蛋,并直接导致鹿子霖将乱伦之罪转嫁到狗蛋儿身上,结果搭上自己被白孝文抓到祠堂一同受刑,也使狗蛋儿接受了族规的严惩并因而丧失了性命。继出卖肉体之后,田小娥又出卖了灵魂。此时,鹿子霖和族长白嘉轩在争权夺势,于是指使田小娥色诱白孝文,达到“尿到族长脸上”[3]的卑鄙目的。田小娥出于被白孝文施于刺刷受辱的私愤,主动出击,手到擒来。性陷白孝文是她对白鹿原这个仁义村以牙还牙、以毒攻毒的报复,也是招致杀身之祸的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和白孝文一起在饥荒中吸食大烟、沉沦堕落,最终促使公公鹿三以祖传的梭镖结束了她的一生。她的肉体和灵魂一同毁灭,于是,一个屈死的冤魂,开始了申冤和复仇的行动。
随着一场罕见的大瘟疫在白鹿原上蔓延,田小娥婆婆鹿惠氏是第一个被瘟神吞噬的人。田小娥告诉婆婆鹿惠氏,公公鹿三是怎样拿梭镖杀了她;她附身在鹿三身上,借他的嘴来诉说自己的冤屈,为自己申辩,还和族长白嘉轩进行口头上正面交锋,放言要把白鹿村老老少少捏死。
白嘉轩根据朱先生的方案,叫白孝武建造六棱塔镇压田小娥鬼灵,意将田小娥身心彻底灭绝:“把她的尸骨从窑里挖出来,架起硬柴烧它三天三夜,烧成灰末儿……把她的灰末装到瓷缸里,就埋在她的窑里,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3]
田小娥骨殖被封在塔底,不屈的灵魂化作许许多多彩色的蝴蝶,飞舞在雪后枯干的蓬蒿草丛中。[3]
二、田小娥悲剧命运的推手
陈忠实说:“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这些特有文化心理结构使得“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4]
如果说,田小娥还是安于当她的泡枣二房,她的人生不会是后面那样不人不鬼的活法。她的不幸看起来是起始于对黑娃的勾引,但从根本上说是追求幸福的本能促使她红杏出墙,她所要的幸福很简单,无非是一个与自己相爱的男人、一个地道的家。但是,背叛丈夫的越轨行为不容于封建宗法礼教,即使在白鹿原上小娥慎小谨微,只想做个名正言顺的农家小媳妇,可这种微末希望依然被白嘉轩代表的宗法权力扼杀了。
(一)性格成长的悲剧
性格即命运。考察田小娥的成长背景,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不甘雌伏的女子。
田小娥的父亲是个连年不中的只会“啃书儿”的穷秀才,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穷秀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在此环境下成长的田小娥读书不多,没有一个大家闺秀的范儿,“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等传统伦理观念淡薄。她被父亲卖给行将就木的棺材瓢子——郭举人做小妾,这是她命运的转折点。作为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子,田父为什么要将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个糟老头做小老婆呢?书中没有交代,可以猜想一下,田父考不上举人,所以找个举人女婿补偿一下自己的遗憾,也可以提高自家的地位,却不曾想女儿在郭举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供其娱乐的性工具而已。田父不负责任地把田小娥推入火坑,埋下了日后田小娥为此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祸端。
面对在郭举人家的这种灭绝人性的生存状态,大多数女人选择顺从,选择隐忍,受不了了就发疯,田小娥却不甘心这样不如狗的地位,为争取做女人的正当权利,孤军奋战,与整个世界为敌。
历数田小娥生命里的七个男人,父亲生她养她,却毫不顾及她的婚姻幸福与否,田小娥勾引黑娃,内心不乏存着丢父亲面子的想法;郭举人是她衣食父母,也是摧残她身心的刽子手,田小娥先是用尿泡枣报复,后又背叛出轨,迈出了追求人生自由的第一步;黑娃,田小娥生命中第一个真正爱上的男人,先是肉体的吸引,后是相濡以沫的相亲相爱,最后变成生活的依靠;鹿子霖是田小娥生命中的撒旦,是其走向堕落的始作俑者;白狗蛋是她的报复的无辜牺牲品,标志着田小娥进一步的堕落;白孝文是她报复白嘉轩的媒介和工具,及至后来发展成为孤苦无依时的难友;白嘉轩是她精神世界的紧箍咒,从始至终的对立面;鹿三是她努力讨其欢喜而不得并终结她生命的人。田小娥的一生都活在男人的阴影中,她所作的每一步选择,实际上都是激情冲动、缺乏理性的,只是任由自己的本能行事。勾引黑娃的时候她已然不计后果,所谓伦理所谓面子统统毫不考虑,要不是郭举人还算仁慈,她和黑娃都有丧失生命之忧;白鹿原上不被家长族老接纳,就应该作出理性判断,说服黑娃远走他乡谋生路,反而由着黑娃闹革命,并最终导致黑娃出逃,把自己置于无可奈何的境地;接着又辨不清白鹿原上的形势,一头扎进鹿子霖的陷阱,出卖了肉体和灵魂,成为其争权夺利的工具和牺牲品,并在一次次害人又害己的过程中滑向深渊,最终招致公公鹿三的背后一镖,香销玉殒。
实际上,田小娥的反抗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反抗,面对人生的每一次重大选择,她总是不由自主地利用自己的身体去开展“外交”,以获取男人的关注和保护,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和地位。不管选择哪个男人做靠山,都是为了跳出连只狗都不如的火炕,能自由自在地活得像个真正的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田小娥和大多数被情欲冲昏了头脑的淫妇不同,她更懂得运用“性”武器,更懂得在“肉偿”男人的同时讨好自己。
(二)宗法高压的悲剧
从宗法制的角度来看,女人只是男人传宗接代的工具、性发泄的对象以及做事时的帮手而已。《白鹿原》中的女性,体现出强烈的“工具性”意味。白鹿原上公认的“好女子标准”:良好家教,做人得体,精通家务,传宗接代。书中所展示的女性“工具”价值还有泄欲工具、复仇工具及联姻固势等。[5]
田小娥嫁给黑娃到了白鹿原,不被白鹿原祠堂文化所容,蜗居村外,又跟随黑娃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站到了封建势力的对立面反抗这个不把她当“人”的社会。黑娃出逃后,小娥无奈充当鹿子霖泄欲和争斗的工具,诱骗狗蛋,性陷白孝文,气晕白嘉轩,疯狂地以性武器嘲笑封建礼教。她这一系列离经叛道疯狂的举动正是将她推向死亡的主要原因,与其说她惨死在自己公公的梭镖下,不如说封建宗法乡约不容于她。因为在白鹿原人眼中,田小娥就是个“祸水”妖女,具备妹喜、妲己、褒姒、杨玉环、陈圆圆等中国历史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的“红颜祸水”的基本特征:一是天生容易受到魔鬼撒旦的诱惑,走上邪路;二是散发魅惑气息,蛊惑无辜的男人步入歧途。
“万恶淫为首”,对儒家文化的道德纲纪来说,性本能不亚于洪水猛兽。在白鹿原人看来,田小娥漂亮得不像话的美色只会给男人带来不幸,“三从四德”一样不占;更是导致黑娃和白孝文的堕落的罪魁祸首。文中写道,鹿三在土壕里撞见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着的白孝文。老实善良的鹿三惊呆了,他眼睁睁地看着白孝文一天天长大的,一步步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礼貌的族长,“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6]又看着他卖地卖房拄着打狗棒上门乞讨,最终在饥荒之际呆坐在土壕里静等野狗分尸。白孝文这样一个从土豪到“土壕”败家子的败落史,又一次验证了他的生活信条:美色头上一把刀,温柔乡是英雄冢,黑娃和孝文堕落的不幸根源来自于同一个女人,田小娥给他和他尊敬的白嘉轩两个家庭带来的灾难无法容忍、不可原谅。于是鹿三义无反顾地杀了田小娥,以拯救被女色迷了魂的白孝文。
白嘉轩做过一个白鹿村家庭调查,结论是男人成不成才关键在于老婆好不好:白嘉轩就不要说了,前六房不是身体不好就是脑筋不灵,直到第七房吴仙草知书达理又能生养儿子,才使得他时来运转,走上人生顶峰;与小娥厮混,黑娃落草为寇一步步滑向深渊;与知书识礼的高玉风结合,他逐渐成为一个好青年。黑娃梦幻般的人生道路为白嘉轩的理论作了完美注脚。
被视为“祸水”的田小娥无疑是白嘉轩所憧憬的乡村牧歌中不和谐的噪音,是威胁祠堂戒律与道德准则的捣乱分子,因而处处在封建伦理道德的神圣名义下被凌辱被损害。[7]小娥最终在惨烈的绝望体验中爆发出刚烈而冷酷的一面,走向了复仇的疯狂,整个白鹿原都是她怒火迸发的对象——鬼魂上身逼疯鹿三,发起大规模瘟疫绝门倒户,吴仙草也染疫而亡。但是,她的鬼魂所作的一切最后招来终极镇压——白嘉轩建造六棱塔将其压在底下,永世不得翻身。六棱塔驱鬼镇邪,象征着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的胜利,而塔底的幽灵再也没有兴风作浪。田小娥曾经拥有的一切烟消云散,即使是她曾经最爱的黑娃,在升官发财再婚皈依封建儒学的日子里,想起田小娥,只是觉得年少荒唐。
(三)时代转型的悲剧
在以父权为主的社会,女性的地位不断下降,因为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自我生存的能力,依靠男人是她们赖以生存之路。“悲剧之产生主要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8],作为男人的附庸,幼时从父,嫁人从夫,老了从子,她们没有能力与男人抗争,除非不想活了。
鲁迅说,“出走后,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显然,田小娥背叛婚姻是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的,被休回家,父亲又不待见,这时黑娃来娶她无异于给了她第二生命。换言之,田小娥从郭举人这个火坑跳出来,实际上又上了黑娃这个炕,区别在于这次是心甘情愿的。然而在两人过了一段虽然远离乡亲却两情相悦的日子之后,动荡的时代和黑娃那颗不安分的心,给了田小娥的家庭梦想致命一击。
20世纪初叶,田小娥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最黑暗、最飘摇的时期之一,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经过两千多年风雨结束了使命,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思想理念、民主思潮和各种新文化;同时,在中国这个四分五裂的大地上,各种势力依然在残酷角逐,新旧思想在激烈交锋,特别在贫困落后的乡村,旧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发生在白鹿原上的争斗,正是乱世纷争的一个剪影。田小娥虽然有一些自由思想和新女性意识,但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属于传统女性,身无一技之长,又不愿意去独立奋斗生存;她跟着黑娃搞农民运动,只不过是夫唱妇随罢了,她没有那个思想觉悟和坚强意志去真正参加革命,她毕竟不是白灵。于是当这支由白鹿原人心中的“死皮烂娃”所组成的“队伍”被镇压的时候,虽然这场运动只是当时中国无数个农民运动浪潮中一朵很不起眼的浪花,但是对不幸的田小娥来说无异于狂风暴雨,使得她整个人生发生逆转。黑娃从此亡命江湖,依附于他的田小娥,从此崩盘。
田小娥,这位中国底层最普遍、最悲惨的妇女,为着拯救他人而走向堕落,为着反抗压迫而滑向深渊,为着幸福而毁灭生命,从受虐开始、由害人告终,在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受苦受难女性其中一份子罢了。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田小娥强烈的个性与封建伦理的反差造成了她的时代悲剧,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一样,这一形象对传统儒家文化规范提出强烈的挑战性质疑,在性欲的放纵中揭示更深层的文化意蕴,表现了20世纪中国女性意识在乡村朦胧觉醒的艰难与沉重。
陈忠实塑造的田小娥形象,无论是从传统伦理还是从现代意识观照,从田小娥勾引黑娃上床那刻起,田小娥就是个婚内出轨的“淫妇”,是个不规矩的女子。从文本来看,即使陈忠实在田小娥身上“集中表达”了他对女性生命脆弱、命运多舛的深切同情和对封建伦理压抑、摧残女性欲望的无声批判,[9]但田小娥身上放荡女人的烙印是作者盖棺定论的。陈忠实“撕开来写”,深入而又生动展现了封建礼教下不甘于循规蹈矩扮演贞洁女子的悲剧角色。田小娥是破窑中的“潘金莲”,不是寒窑中的“王宝钏”。然而淫乱下所掩藏的悲剧与圣洁下所掩藏的悲剧,却有异曲同工之处,这就是女性失去自我、依附男人的悲剧,无论是性压抑,还是性放纵,都不能使女人真正拥有那份属于“自然人”的幸福。
如果说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白鹿村人一直在仁义、道德的幌子下压抑个性和人性,那么田小娥就是这白鹿村上唯一一个坚守自己的人,她的命运给人以百味复杂的感慨,她追求爱情、追求个性,报复卫道者,“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人性与兽性、正义与邪恶在其身上纠结不清。[10]然而她的骨子里有一种反抗精神,一种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她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对自我人生的伤悲,是一种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力量,是一种明知前方最终是死亡仍然不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是一种即使堕落成鬼也要化作妖报复仇人的疯狂。
陈忠实通过塑造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女子,在揭示历史的痼疾与传统文化糟粕中,反思动荡不安的百年历史,反思临危思变的中华文化,思考民族命运和国家未来。这正是《白鹿原》的厚重思想和撼人心魄之所在。
[1]李星整理.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纪要[J].小说评论,1993(5):16-22.
[2]张建良.《白鹿原》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3]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4]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5]连思齐.陈忠实《白鹿原》女性书写新探[D].广州:广东技术师范学院,2014.
[6]孔尚任.桃花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刘洪雨.原型批评视角下的《白鹿原》解读[D].青岛:青岛大学,2013.
[8]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9]王利荣.历史转型时期的女性悲剧——论《白鹿原》中女性悲剧形象[D].西安:西北大学,2015.
[10]张颖.论《白鹿原》的悲剧意识[D].吉林:延边大学,2006.
I207.42
A
1673-9884(2017)10-0121-05
2017-08-21
黄伟群,女,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