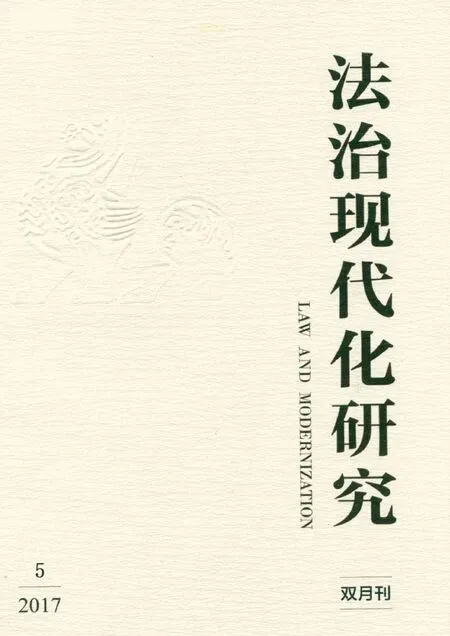司法政策变迁中的刑事司法
马荣春*
司法政策变迁中的刑事司法
马荣春*
* 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司法政策的样态决定刑事司法和刑事法治的样态。伴随着“严打”到“两个效果”再 到近期可欲的“社会公信”这一司法政策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中国刑事 司法政策的阶段性,而后者又决定了中国刑事司法与刑事法治的阶段性,并说明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 不可能一蹴而就,且无法偏离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双失”到实质法治对形式法治的“贬损”,再 到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渐趋结合”这样一个“三部曲式”的发展轨迹。迎合刑事司法和刑事法治 的公众认同,“社会公信”政策将从以往的效果型司法政策之中“涅槃”为引导中国未来刑事司法和 刑事法治的新政策,且将赋予刑事司法和刑事法治以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结构性黏合”,并将体 现为相关刑事司法制度的切实安排。
司法政策 刑事司法 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 社会公信
刑事法治是法治的重要构成部分,刑事司法又是刑事法治的重要构成部分,且刑事司法和刑事法 治都无法抽离司法政策这根敏感神经,故本文以司法政策的变迁为切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刑事 司法和刑事法治的发展轨迹。
一、“严打”政策主导下的刑事司法
(一)“严打”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文本评价与实践评价
改革开放之初的犯罪情势,“人心思稳”的主流社会心理,以及国家治理策略从“群众运动”向“依 法办事”的转型,这些因素促成了“严打”政策。在文本上,“严打”政策已经蕴含了后来的“两个效果”(法 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司法政策,这体现为“严打”政策强调“依法、从重、从快”。具言之,1979年11 月 22 日的《关于整顿城市社会治安的几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强调,为了能够及时地、 准确地依法处理重大刑事案件,应采取集中办公的方式办案,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切实弄清案情, 分头依法办理。《意见》还要求,要很好地运用法律武器与违法犯罪活动做斗争。1其中,“依法处理”“依法办理”直接亮明了“严打”的“节制”所在,而“运用法律武器”也有“严打”要“节制”的意思。彭真同志曾指出,党委领导也是领导正确执行法律;即便“从重、从快”,也要搞准和依法。2其中,“正确执行法律”即“依法”的“节制”意味更加明了不过。随着“严打”的推进,“从重、从快” 的“依法性”又得到了多次强调,如对杀人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和对国民经济危害严重的 大案要案,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即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从重、从快。这是“常识”。3“在法律 规定的幅度内”也明确强调“依法”。实际上,当《意见》强调要“打得稳”时,就有“严打”要“节制” 的意味。如今,在回顾和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正视和重视“严打”政策中 的“依法”二字。据此,“严打”甚至被认为是进行“法治建设”,4越是在“严打”期间,越应强调“依 法办事”,否则有可能背离依法治国的要求,甚至出现以政策代替法制而破坏法治的现象。5由此可见, “严打”政策至少在文本上已经兼顾了我们当下所说的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依法”所欲谋 求的是刑事司法的法律效果,且法律效果谋求在先;而“从重、从快”所欲谋求的是刑事司法的社会 效果。由于“依法”是“从重、从快”的前提,“从重、从快”是在“依法”的限制或框定下进行, 故在文本上,“严打”政策不仅已经兼顾了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而且还是在法律效果之内谋 求社会效果,即其似乎隐含着“法律效果决定论”。可以说,“严打”政策在文本上是坚持“法治”的, 这可为与“建设模式”相对应的“依法治国”策略所印证。
但是,“严打”政策的实际运行却与其文本相去甚远。概括各种现象,“严打”政策下的刑事司 法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外用法”与“曲法用法”;二是“从重、从快”变成了“加重、 加快”;三是超出范围,实施滥打;四是只“严”不“宽”,宽严失济;五是惩罚过头,改造不足。“严 打”政策推行中的这些问题集中说明:“严打”政策下的刑事司法相当程度地丢弃了我们后来所说的 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兼顾”。
“严打”政策下的刑事司法丢弃的是文本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兼顾”,而“收获”的是典 型的政治效果,正如“革命根本利益的需要”6所印证的那样。“严打”政策期间的刑事司法对犯罪 注重“惩罚”而非“治理”,实即对罪犯予以“敌人式的专政”;当时虽已提出“综合治理”,但其 只是针对刑事司法领域外的一个补充,而非在刑事司法领域内对犯罪予以“刑罚个别化”和“治理疏 导化”;当“严打”政策在运行中用“稳定压倒一切”来充斥或鼓胀刑事司法,刑事司法必然在“稳 定压倒一切”的任务之后亦步亦趋;法律工具主义的践行,不是尊重或信仰法律,而是将法律当作是 超出法律本性的、用于达到某种用途或目标的“刀把子”;“严打”政策下的刑事司法是一种“党领 导下”的“群众运动式”司法,正如中央号令一下,“严打”斗争风起云涌,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7而从1983年开始,大仗小仗持续不断,战绩巨大。8这里的“风起云涌”和“大仗小仗”便是“严打” 政策下刑事司法政治色彩的映现。简言之,“严打”政策下的刑事司法实践给我们的教训是:对犯罪 只能“治理”而非“惩罚”;坚守法治是谋求稳定的根本,法律工具主义是“法治”应谨防的极端。
之所以“严打”政策下的刑事司法丢弃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兼顾”,大致因为:一是,群众运动观念的时代残留和完成政治任务的心理迫切。在改革开放之初,“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群众运动”仍然扎根在人们的观念中,故当把“严打”上升到维护安定团结和保护国家建设的政治高度时, “斗争”和“运动”的观念又得到了“宣泄”,从而,“不守规则”便在“严打”中以“不守法律规范” 即“不依法”体现出来;又当“严打”逻辑地“吻合”着发展经济和维护稳定这一党的政治任务时, 势必容易造成法律与政治之间界限的模糊不清。9于是,在“严打”的推行中,对犯罪分子唯恐用刑 不重,甚至不加区别地一概“严打”,因为对司法人员而言,“打击不力”可能与“指导思想出了问题” 挂钩,如此,“打击不力”的责任会远远大于“不依法”的责任。二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整体专业素 质低下。在“严打”政策落实初期,与恢复高考同步,国家的法学教育才刚刚恢复,教育机构能够“产 出”的法学人才在数量上尚处在“产量”低下状态。而在这一时期,各种犯罪却一路飙升。此时,在 法学人才“生产”与犯罪“供应”之悬差之下,能够胜任司法工作的专业人才更显得极为匮乏。于是, 大量的非法学背景的人包括专业军人便“涌入”司法机关、各级政法委,进而使得刑事司法领域形成 “外行人办内行事”的局面。“外行人办内行事”必然造成不按“规矩”办事,或曰不遵守司法的“游 戏规则”。于是,“不依法”的状态便在料想之中。“严打”政策最终带来的是刑事司法的效果颠倒, 即该政策下的刑事司法视司法的政治效果应高于或优于司法的法律效果。而此效果颠倒是前述两项原 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即不受规则约束的“斗争”和“运动”观念本来就害怕规则约束,而司法工作人 员整体专业素质低下又恰好让不守规则约束的“斗争”和“运动”观念大行其道。
(二)“严打”政策下刑事司法的法治特质与状况
“严打”政策下的刑事司法效果当然牵扯刑事法治问题。“严打”政策下的刑事司法所带来的是 政治效果对法律效果的压倒性进逼,就是对刑事法治的压倒性进逼。“严打”虽然强调“依法、从重、 从快”,但其暴风骤雨式的运作方式可能会使法治的底线被突破,故“严打”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是 我们在反思“严打”刑事政策时应面对的一个问题。10实际上,“严打”政策下的刑事司法已经突破了“法 治的底线”。显然,在“政治效果主导”之下,刑事司法本身难有自主性和自洽性,而“法律工具主义” 与“政治效果主导”相互为用。于是,“严打”政策下的政治效果主导型刑事司法所司者乃是“安全刑法” 和“仇敌刑法”,从而该政策文本中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兼顾相当程度地蜕变为刑事司法中的政治效果, 因为该政策的运行变成了国家权力与“稳定压倒一切”政治任务的“交互为用”。
政治效果型刑事司法并非赤裸裸地呈现其政治效果,而是通常将社会效果作为衬托或边饰。在“严 打”期间,“依法、从重、从快”中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兼顾事实上被政治效果“绑架”,故造成 法治的束缚作用减少且带有政治工具性。11对于“湖北佘祥林案件”的死刑悲剧,有人认为,该起冤 案是司法机关屈从民愤的力量,忽视必要的司法证明活动,仓促定案而发生。12其实,地方党政机关 如果不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而介入司法程序,则该起冤案也不至于发生。对于该起冤案,我们与其说 是讲求社会效果导致的,毋宁说是以“稳定”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效果使然。
刑事法治问题是我们考察“严打”期间刑事司法“政治效果化”的落脚。在此,我们可看到“严打”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刑事政策主要以国家权力为中心展开,故其深受政治影响。当“严打”政策与政治挂钩,便意味着“严打”政策首先是政治的工具,这必然引起刑事政策与法律的冲突。而 在我国目前的权力框架下,如果“法治”不能获得同等和同步的推进,则“严打”政策的推行必然将 导致国家刑罚权与法治的紧张关系。13国家刑罚权与法治的紧张关系,实质就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 的紧张关系。而刑事司法的法治问题,其实质是包含人权在内的公平正义问题。但“严打”之下,刑 事司法的政治效果化所造成的是“稳定压倒一切”所表达的“绝对安全”价值完全排斥了包括权利或 自由在内的其他社会价值这一局面。但任何刑事政策的实施都必须立足于对人权的有效保障,否则激 发犯罪人的对抗心理,促使其采取更极端的方式对付社会。14在此,刑事政策只有真正置身于“综合 治理”或“最好的社会政策”之中,才不会走向极端,从而其所导引的刑事司法才有“法治化”可言。 导致“政治效果化”刑事司法的“严打”政策应属于国家极权型刑事政策,15而此种类型刑事政策下 的刑事司法的法治性能即“国家极权化法治”及其程度是可以想见的,即其在相当程度上是“反法治” 的,因为在政治效果化的刑事司法那里,实质问题即实质法治大于乃至代替了形式问题即形式法治, 而问题恰恰在于:没有形式问题或形式法治,则法治问题即法治本身是不存在的。
在政治效果的追求之下,刑事法治的状况正如在政治司法模式的影响下,对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 破坏致使司法在陷入“喜怒无常”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在遇到重大典型案件时,维稳压力抑或国际 影响会迫使司法机关牺牲个案公正以追求短期的政治效果,16从而法律舞台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论 坛”。17这里,我们或可获得对“政法”概念的一点认识:政治效果时常或容易破坏法治,毕竟“政” 在前而“法”在后,且“政”字吊诡地变成了“攻”字。“严打”政策本可通过“依法、从重、从快” 来导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兼顾,但其事实上却“造就”了一个政治效果型的刑事司法。政治效 果型的刑事法治凸显出实质法治有余而形式法治不足,而当形式法治不足到可有可无的地步时,刑事 法治本身都将荡然无存,因为法治包括刑事法治都永远必须是“形式”的。
政治效果型刑事司法的法治问题终究是人权问题。“严打”政策下刑事司法的实际运行逻辑是社 会稳定→政治任务→刑事镇压,正如公、检、法要对“敌人”实行专政,因为对犯罪的仁慈、手软就 是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的残忍。18可见,“专政”便是“严打”刑事政策及其所导引的刑事司 法的政治属性,而“敌人”和“人民”可视为其政治属性的话语转换。显然,在前述政治属性之中, 以牺牲个体正当权益为代价的社会稳定是一种“伪社会稳定”,正如“严打”使得死刑政策导向是一 种复仇模式,19在复仇模式下,刑事司法是很难守持人权保障的。
政治效果型刑事司法的提法,可视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刑事司法反思和总结的开端。不认真对待权利的政体也不会认真对待法律,20即不认真对待权利的政体也不会认真对待法治。若以此来观照“严打”时期的刑事司法,则社会效果和政治至上的意识形态共同谋害了中国的法治。21这里,“政治至上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演变成了绑架社会效果的政治效果思维。由于人权是法治问题的根本,故“严 打”政策下刑事司法所造成的人权状况可想而知。“严打”政策下的“政治任务型”刑事司法明显说明: 司法政策对应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主题,而与“政治任务型”刑事司法相对应的阶段性社会发 展主题则是“稳定压倒一切”。“严打”政策下的刑事司法给我们留下了司法政策的效果性问题思考, 进而是刑事司法的法治性问题思考。
二、“两个效果”政策主导下的刑事司法
(一)“两个效果”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渗透及其运行状况
2002年,“两个效果”政策首先在民事司法领域正式形成,两个效果即司法的法律效果和司法的 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实即严格适用法律本身;22而社会效果,实即法律适用结果的公众认同。23在 渐趋完善的过程中,“两个效果”政策便开始向刑事司法领域渗透,并形成“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 “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等影响性刑事个案便是“两个效果”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发挥作用的生动说明, 正如学者所言,“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可视为最高法院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项司法 政策的指导下作出的最终选择。24而“邓玉娇案”等个案处理也被认为是实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两个效果”是我国司法机关的“独创”,25或法官理案的“极致”或“最高境界”。26于是, “两个效果”政策向刑事司法领域的渗透似乎有着无可置疑的正确性,并点燃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所内含的“两个效果”的“火种”。“两个效果”政策如此容易地渗透到刑事司法领域,不仅因为该政 策具有“统一性”要求,更是因为刑事司法自身的特殊性,即刑事犯罪及其刑事惩罚对社会公众的理念 冲击力较大而容易引发公众对相关讨论的参与。27所谓“容易引发公众对相关讨论的参与”其实就是容 易引发“社会效果”。
“两个效果”的运行实际便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博弈。“两个效果”博弈在影响性刑事个案 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并形成两种博弈类型,即社会效果赢家型和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双赢型。
例如,在“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从一审的死刑判决到二审的死缓判决再到最高人民法院 的再审死刑判决,其所体现的是社会效果大于或压倒法律效果的博弈局面,因为对应着刑讯逼供的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效果最终还是被淹没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社会效果之中,正如学者所言,最高人民法院史无前例地对刘涌案在判决生效后提审改判不能不说是社会公众舆论作用的结果。28同样,就“许霆案”而言,从一审的无期徒刑到发回重审后的改判5年有期徒刑,其所体现的也是社会效果 大于或压倒法律效果的博弈局面,因为从法教义学的角度,行为人采取自以为他人不知的手段而恶意 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能够符合常识、常理、常情地被认知为“盗窃”,而从金融机构自动取款机盗窃 财物的行为也同样能够符合常识、常理、常情地被认知为“盗窃金融机构”,而案发时的刑法明文规 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可见,一审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完 全符合刑法教义学,且暂时收获了丰满的个案法律效果。但由本案掀起的舆论浪潮卷走了暂时的法律 效果,取而代之的是一审法院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假借“核准减刑”的程序而通过5年有期徒刑这一生 效判决,使“舆论怒潮”很快风平浪静。且不说现行刑法关于减轻处罚的第63条第2款中的“特殊情况” 赋予了审判机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即便是符合“核准减刑”的条件,本 案也应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刑度内减刑,而不应该“跳格减刑”。故“许霆案”的生效判决应 被视为司法的社会效果战胜了司法的法律效果,正如5年有期徒刑带来的随意性让我们看到了法律之 外的太多魅影。29其实,许霆案5年有期徒刑的最终结果是社会效果论所造成的“迫不得已”,而所 谓“魅影”即社会效果的魅影。而就“邓玉娇防卫过当案”而言,同情弱势的社会舆论或民意倾向并 未带给邓玉娇无罪的结果,而防卫过当依法“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故该案所体现的是社会效果 与法律效果的双赢局面,也可说是社会效果实现在法律效果之内的局面,正如学者所言,邓玉娇案件 正好给了民众一个期待正义的情绪突破口。30就“药家鑫故意杀人案”而言,同情弱势的社会舆论或 民意倾向只是使得法院在自首“可以”从宽的自由裁量之内形成了社会舆论或民意倾向所希望的死刑结 果,故该案所体现的也是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双赢局面。就“李昌奎故意杀人案”而言,同情弱势的 社会舆论或民意倾向所促成的最终判决仍然是在自首“可以”从宽的自由裁量之内,且通过“赛家鑫” 体现了早就提倡的司法裁判的地区平衡,故该案所体现的仍然是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双赢局面。
可见,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双赢型的“两个效果”政策运行中,刑事司法呈现出了形式法治与 实质法治被兼顾或相结合,从而刑事法治厚重、稳健的可喜局面;但在社会效果赢家型的“两个效果” 政策运行中,刑事司法呈现出了形式法治萎缩而实质法治过度膨胀的局面。因此,“两个效果”政策 至少是“有时”会危及法治包括刑事法治,而这“有时”已经足以让我们谨慎对待“两个效果”政策了, 因为其最终可能危及法治特别是刑事法治。刑事犯罪对社会公众的理念冲击力较大而容易引发公众对 相关讨论的参与,31公众对相关讨论的参与就是公众对法治特别是刑事法治的参与。
(二)“两个效果”政策下刑事司法的法治特质与状况
“两个效果”政策可能危及法治包括刑事法治,原因在于:“两个效果”政策错置了法律效果与 社会效果的应然关系。“两个效果”政策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置于并列关系上,抛出空洞的“统一 论(兼顾论)”,从而使得社会效果“借机”形成其对法律效果的“优先关系”甚至“决定关系”。但两者并不属于同一位阶,32如果不澄清两者的应然关系,则会给实践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33正是由于将两者置于同一位阶,才有所谓“两个效果统一(兼顾)论”乃至“社会效果优先论”甚或“社 会效果决定论”。然而,“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个分裂的命题,因为法律是社会关系中的 法律,本不存在法律效果之外的社会效果。34在本文看来,司法包括刑事司法的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之间的应然关系应表述为手段与目的、途径与目标或“源”与“流”的关系。“两个效果统一(兼 顾)论”的“分裂性”正是手段与目的的“分裂性”、途径与目标的“分裂性”或“源”与“流”的 “分裂性”。易言之,“两个效果统一(兼顾)论”的“分裂性”破坏或扰乱了刑事司法本身与刑事 司法效果的应然关系。而正是前述“分裂性”,才先造成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并列,进而生成了 社会效果对法律效果的“话语霸权”。进一步地,这里的“分裂性”便是对法治包括刑事法治的“分 裂性”,即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分裂性”。而“两个效果论”中社会效果对法律效果的“话语霸权” 就是实质法治对形式法治的“话语霸权”,其实质便是保护社会对保障人权的“话语霸权”。尤其是, 当把本属于法律效果的内容不当地划给了社会效果,以至于贬低法律效果,则最终导致司法者在追寻 社会效果中的方向迷失。35所谓方向迷失,就是法治包括刑事法治的方向迷失。
在本文看来,“两个效果”政策中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应是手段与目的或途径与目标或“源” 与“流”的关系。实际上,“效果”本指事物的对外功用性,司法包括刑事司法是不存在与社会效果 相并列的所谓法律效果问题的,即(刑事)司法的效果当然指的是(刑事)司法的对外效果,即其作 用于社会生活的效果。违背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即混淆或偷换“效果”这一概念的内涵而形成的“两个 效果论”以及作为其具体体现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兼顾)论”“社会效果优先论”“社会 效果决定论”,实际上都是破坏或扰乱了(刑事)司法本身与其所能产生的效果之间的手段与目的、 途径与目标、“源”与“流”的关系。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对立或冲突,其问题实质是手 段与目的、途径与目标、“源”与“流”的脱节,而此问题要么在根本上是由立法质量所决定,要么 是由(刑事)司法水平所决定,故此问题应从完善立法或提高司法水平两个方面来解决。而“两个效 果”政策在将两者并列的基础上制造了目的大于手段、目标大于途径、“流”大于“源”的局面,而 这里的手段、途径或“源”相当于形式法治,从而造成了形式法治憋屈甚至窒息于相当于目的、目标 或“流”的实质法治之中的局面,法治包括刑事法治本身便遭受折损甚至销蚀殆尽。由此,形式法治 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可视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问题所在。名为“两个效果统一(兼顾)论”而实为“社 会效果优先论”“社会效果决定论”的观念,对我国正处于发展中的法治建设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实 为“社会效果优先论”“社会效果决定论”的“两个效果论”明显将法治问题“倒果为因”,颠倒了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手段与目的、途径与目标、“源”与“流”的因果关系,并造成先有实质法治, 后有形式法治的倒置局面;倘若我们还没经过形式法治的熏陶就贸然转向实质法治,或许将出现法治 的异化,即完全背离形式法治而使法治本身成为泡影。
“两个效果”的论断实为“结果决定论”,其法哲学基础是实质主义法治理论,故其可能滑向法治的反面。36其对法治,包括刑事法治的危害,或许正如许霆案的最终结局那样,与其说是“两个效果论”使然,毋宁说是“社会效果论”使然。名为“两个效果”实为“社会效果”的司法政策思维对法治包括刑事法治的危害,体现为对法治的可预测性包括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从而使得法律包括刑法成为 “白条”,失信于民,因为社会效果是一个极为模糊和宽泛的概念,且其毕竟不是司法裁判的依据。37在刑事司法领域,社会效果导向应当受到限制甚至遏制,因为其将导致司法人员根据预想的裁判结果 来重新建构犯罪事实和刑法裁判规范。38显然,“重新建构犯罪事实”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重 新建构刑法裁判规范”不仅违背了“以法律为准绳”,而且导致事实上的“法制解构”,而这两者所 走向的必然是在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个层面都违背刑事法治。
“两个效果”政策对法治的危害,甚至体现为政治效果型司法政策“借尸还魂”。两个效果相统一 的早期表述中就包括所谓“政治效果”,亦即司法机关所要认真考虑或更为注重的“社会效果”经过政 治权力系统的理解、过滤和传达也就变成了“政治效果”。于是,法院所追求的最终就是法律效果与政 治效果的统一。39由此可见,法律效果可能为社会效果所绑架,而社会效果又更有可能为政治效果所绑架。 容易被政治效果绑架的“两个效果”政策对法治的危害更加“隐蔽”和“深刻”。在金字塔型全息式的 政治权力结构之中,法院要实现社会对整个国家权力系统的功能期待,必然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的统一。40实际上,法官这个职业群体可以或应该力求在“法律之内”或“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对整 个国家权力系统的功能期待,因为司法权本来就是整个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而如果在“法律之外”或“不 通过法律”,则等于是分裂了整个国家权力系统,又谈何实现社会对整个国家权力系统的功能期待呢? 而如果在国家权力系统之外又另立权力系统,则实现法治包括刑事法治的希望将更加渺茫。
“两个效果”下的刑事法治问题,其终究还是牵扯人权问题。当将“社会效果”镶嵌到司法政策 之中以影响刑事司法时,其应引起人权问题的警觉,因为社会效果论特别强调“主流价值观”和“长 远利益”。41“主流价值观”显然是对价值多元之下价值冲突的事实轻视乃至无视,进而形成“一者” 压制“他者”,即“多数人压制”乃至“多数人暴政”的局面;而“长远利益”也容易被假借为当下 政治功利的堂皇理由,且吊诡地呈现出“理性姿态”。于是,当社会效果的话语演变为主流价值观的 政治话语,其便构成了打压乃至“镇压”属于“少数人”的“他者”的话语工具。可见,“社会效果论” 难免有着违背乃至无视法治原则和践踏人权的危险倾向。
总之,“两个效果”政策下的刑事司法状况可作这样的大致描述:形式法治虽被强调,但实质法 治更被凸显,故最终是实质法治贬损形式法治。但相较于“严打”政策下的刑事司法,“两个效果” 政策下的刑事司法的法治性问题及其地位得到更加重视和抬高。与“两个效果”政策思维相对应的阶段性社会发展主题是“社会和谐”。
三、“社会公信”政策主导下的刑事司法
(一)“社会公信”司法政策的“涅槃”及其法治目标
司法包括刑事司法的效果问题不应是一个立于自身,而应是立于其外部的判断。如此,司法的社 会效果才是符合问题真相的,即所谓司法包括刑事司法的法律效果是一个脱离问题真相的“自体判断” 的概念。在官方语言和理论语言中,法律效果的本意是指成文的法律规范被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去,但 司法的效果应是指成文的法律规范被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去“之后”,通过具体案件这个“点”而对包 括当事人在内的社会这个“面”产生了怎样的符合我们整体利益需要的正面影响即社会效应。法律效 果是一个法社会学范畴。42立于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来界定法律效果是正确的,从而应在“法治之中” 而非在“法治之外”谈论社会效果,否则便有“社会效果论”贻害法治的危险。马克思曾指出,当法 律是自私自利的,则大公无私的判决将无意义。43“自私自利”和“大公无私”都表明马克思那里的“法 律效果”实际上指的就是法律的社会效果。可见,法律效果只能是一个表达法律与外界关系的概念, 即所谓法律效果实质上是指“法律的效果”“法律的社会效果”。我们一直在争论“恶法非法”和“恶 法亦法”问题,且“恶法非法”越来越深入人心,而“恶法非法”所强调的也是“法律的社会效果”问题。
实际上,所谓司法的法律效果,本意即法律适用本身的严格性。很明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 并列的提法,潜藏着违背“同一律”的形式逻辑错误。“效果”本来就是一个表达事物与外界关系的 概念,即效果本指事物的对外功用性,故法律效果或许只能是个社会学概念,与司法的社会效果相并 列的法律效果概念,是偷换了“效果”内涵的,从而违背形式逻辑同一律的伪概念。总之,法律效果 这一概念应联系社会来予以驳正,且驳正之后的表述应是“司法的社会效果”,而原本与社会效果相 并列的司法的法律效果应将表述变换为“规范自足”。
有人指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就是一种效果,故将社会效果当作背离法律效果使得对社会效果 的追求已脱离正当轨道。44“一种效果”的说法在否定“两个效果论”的同时,也否定了将法律规范 适用本身视为效果的“法律效果论”。有人指出,法律与社会的契合度越高,法律效果就越好。45这里,“与 社会的契合度”说明所谓司法的法律效果就是社会效果,即不存在与社会效果相并列的所谓司法的法 律效果。司法的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并列,被视为迎合在政治上消解法治所设计的“圈套”。46与社会效果并列使用的所谓司法的法律效果是个伪概念,也是个“危险概念”:一是,即便当法 律乃“良法”之时,强调和坚持严格规则论或决断规则论的“法律效果论”也会因其机械性或武断性 而使得司法包括刑事司法与现实生活有所脱节;二是,当法律乃“恶法”之时,强调和坚持严格规则论或决断规则论的“法律效果论”便会因其蛮横性而使得司法包括刑事司法背离或“反叛”现实生活, 而非仅仅是有所脱节。因此,如果非要使用法律效果这个概念,则其真实所指即法律的效果,而法律的效果即法律的社会效果。可见,以统一、确定的“效果”概念作为属概念而并列出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在形式逻辑上似乎没有问题,但在事物逻辑上确实存在明显问题,而形式逻辑必须与事物逻辑保持一致。易言之,应该被我们所抛弃的是与社会效果相并列意义上的那种所谓司法的法律效果, 因为那种所谓的司法的法律效果,指的仅仅是法律规范包括刑事法规范的适用本身,而问题恰好在于: 法律规范包括刑事法规范适用本身不是我们的司法目的所在,法规范适用对社会所产生的效果才是我 们所真正谋求的法律效果。
走出了“两个效果论”及其所包含的“法律效果论”的“圈套”,司法政策才可能实现一次“涅槃”。 但是,新的司法政策若要从“两个效果”政策中实现一次“涅槃”,还需要某种可欲的目标在前方召唤。 而本文所说的目标召唤即公众认同型刑事司法。
有人质疑理性交往理论,并指出当无法取得共识又不能达成妥协时,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会将人 们抛进黑暗的“沙漠”。47这似乎意味着刑事司法的共识谋求与认同达成不可欲。肯定刑事司法公众 认同之难,是基于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的社会现实。然而,正是由于这一社会现实,司法领域的共识 才有被谋求的可能,而公众认同才有被达成的可能。可以说,正是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才生产了司法 领域的共识达成与公众认同,当然也产生了共识达成和公众认同的难度。无论如何,司法的共识达成 与公众认同是可欲的。至于在解决社会冲突的过程中,有效的共识必定是在震慑机制失效后,社会文 明仍未放弃控制内部冲突的一种补充性方案,48论者所谓“补充性”强调共识的“有限性”,而“共 识的有限性”最终是靠“权力的有效性”予以弥补的。49显然,共识就被放在了无足轻重的位置,而 这是由权力的强大能量所对比出来的。于是,当把目光转向司法领域,我们便难以对司法共识和司法 公众认同抱有多大希望。然而,事态不应如此,一是因为权力机制并非能够有效解决任何纠纷;二是 因为“权力的强制”并非可以无限透支公共资源,其始终要面对“何以合法”的追问。50权力的不逮 之处,自然需要出现共识的身影,因为纠纷终究要解决;而“权力的强制”本身的“合法性追问”又 是事物情理的追问,从而最终又是共识的追问。由此可见,共识谋求的机会大小和公众认同达成的强 度如何,端赖权力的姿态,而当司法权力骄横跋扈之时,司法共识和公众认同是难见踪影的。相反, 我们所欲求的共识论基础已经呼之欲出,即我们只希望通过合理建构的论辩结构尽可能地推动公众能 够在最大范围内达成共识,而一个理想的司法论辩结构应该是“权力搭台,当事人唱戏”。这里,“权 力的强制”以排除当事人的家族势力等因素的强制而为平等博弈提供平台为唯一宗旨,故我们只是反 对导向性压制或专断性压制。同时,对裁判可接受性命题,我们将把关注视角由传统的“以合法律性 支撑合法性”转换为“以合意性支撑合法性”。51当合理的司法论辩结构摈弃了导向性压制或专断性 压制,即摒弃了司法权力的专断,则“以合意性支撑合法性”便意味着司法结果的可接受性和可认同 性,因为“合意性”表达着“共识性”和“认同性”。由此,司法包括刑事司法的社会共识与公众认同, 只要强化甚至突出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地位,则不仅是可欲的,也是较权力主导司法 模式更为容易谋求和达成的。而我们以往惯于将司法领域的社会共识和公众认同的谋求之难归责乃至“归罪”于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利益偏私性”,但要正视的是,纠纷当事人渴望纠纷的消解,而社会公众是最低限度的“价值共同体”。于是,在司法包括刑事司法领域,“权力搭台,当事人唱戏”宜转换为“权力搭台,共识唱戏,认同收场”。 公众认同型刑事司法所要求的司法政策是“社会公信”政策。而“社会公信”政策所对应的社会发展主题便是“社会公平”。
(二)“社会公信”司法政策下刑事司法的法治特质与制度安排
“社会公信”司法政策下的刑事司法是一种“理性交往”法治。政治领域中公民关心的不是对暴 力的顺从而是相互的交谈。52所谓“交谈”,意味着“理性交往”,而理性交往的直接后果便是公众认同。 于是,理性交往便与公众认同型刑事司法发生了关联。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纵深发展,以社会价值观的 多元化及其冲突的加剧化为根本表征,而社会转型期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便是以社会价值观的共 识化为问题根本。本来,法治就是被用来更好地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而社会转型及其纵深发展使得 法治的这一功能显得更加重要,亦即法治在社会转型期将具有更加重要的谋求社会价值观的共识化的 社会治理价值。于是,当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就是多元化和冲突加剧化的社会价值观在“理性交往” 中的冲突消解和共识达成,则法治应形成谋求共识,达致公众认同思维。由于刑法是法制体系中的“后 盾之法”和“保障之法”,其对应着社会纷争处置即公力救济的“最后手段性”,故刑事法治更应讲 求共识性和公众认同性。又由于刑事司法是作为文本的刑法条文的实践运作,且刑法规范的一般性与 抽象性和个案实践的特殊性与具体性之间永远无法克服的“距离性”,故共识性与公众认同性对于刑 事司法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交往理性对于刑事司法同样显得尤为重要。当中国司法需要民众的 积极与理性参与,且要求司法程序公开透明,53司法包括刑事司法公开透明的程序所保障的民众的参 与及其所促进的司法独立与公平正义,说明法治包括刑事法治离不开理性交往。而体现理性交往的法 治包括刑事法治必能赢得公众认同。
交往理性型刑事司法可视为公众认同型刑事司法的一种转述,即公众认同型刑事司法就是理性交 往型刑事司法,而理性交往型刑事司法又是追求“民本法治”的刑事司法。“社会公信”政策下的公 众认同型刑事司法由于谋求制度“镶嵌”生活的“原叙事”,并注重规范命题的生成与实践的“对话 合作”即理性交往,故其所承载的是一种“内生性民主”,即其能够从根本上克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 果博弈型刑事司法中的“民主虚妄性”及其“外来挟制性”,故其将更加契合罪刑法定等刑事法基本 原则的精神与价值。不同于效果型刑事司法,“社会公信”政策下认同型刑事司法中的“认同”具有 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可形成性与可验证性,而前者中的“效果”则是在刑事司法过程结束后才形成,且 具有模糊性和空泛性,而正是其模糊性和空泛性,容易滋生刑事司法的暴政性与专制性。于是,“社 会公信”司法政策下的公众认同型刑事司法将使得民主与法治实现牢固结合且相互促进和相得益彰。 “社会公信”下的刑事司法谋求的是一种“民本法治”。
由前文所论可见,司法政策的效果模式问题关涉中国法治建设。公众认同法治模式可以视为对以 往效果型模式的统合与扬弃,但此模式需要“社会公信”司法政策的肯定、引领和推动。弥合法律与社会的差距是法官的核心任务,54这里的“弥合差距”就是弥合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差距。在“社会公信”司法政策之下,刑事法治将被弥合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紧密结合体,即以实质法治充实形式法治,以形式法治框限实质法治,因为没有明确标准的刑事司法和没有实质正 当的刑事司法,都难以赢得“社会公信”,即“社会公信”对刑事司法所提出的是从形式到实质的双 重要求,从而刑事司法所对应的刑事法治也被赋予了形式公信与实质公信的双重要求。社会转型及其 纵深发展使得我们的法治实践包括刑事司法在陷入“眼花缭乱”甚至“无所适从”的同时,也时常陷 入“合法不合情理”的悖论,从而加剧了转型期的“法治危机”。“社会公信”政策下的公众认同型 刑事司法将助益于缓和与消解当下社会发展的“刑事法治危机”,从而助益于“刑事法治公信”。
“社会公信”司法政策使得我们追求刑事法治的制度安排能够或容易是自觉的而非自发的。而这 里所说的制度安排既包括外在的,又包括内在的。所谓外在的,是指在“社会公信”的目标之下,刑 事司法能够更加清楚地被视为一个动态的信息吐纳与转换系统。对于该系统而言,外有社情民意的簇 拥,从而需要运行一套较为科学合理的鉴别机制以进行信息输入与转换。如此,我们便能够形成对舆 情民意的正确态度。具言之,刑事司法不是在真空之中,故其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将舆情民意视为“愚 昧无知”或“洪水猛兽”,而应在“去伪存真”之中使得自身更具情、理、法的融合性,进而在对舆 情民意的“兼听则明”之中使得自身获致最大可能的公众认同即最大可能的社会可接受性,进而赢得 最大可能的刑事法治公信。那就是说,“社会公信”下的刑事司法将对舆情民意形成更加科学、理性 的取舍态度,并将促成舆情民意的吸纳与鉴别机制。有人指出,民粹主义在促进公民权、监督权的同时, 也不时演化为话语暴政。55“社会公信”下的刑事司法就是要排斥司法的民粹主义和话语暴政,因为 法治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对作为个体的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由于社会效果不等于民意,故不能决绝地 通过社会效果来论说民意与司法民主的关系。正如“邓玉娇防卫过当案”中,民众对强势主体犯罪或 被害的刑事个案的关注在相当程度上是表达其民主、平等的追求。56可见,完全否认民意,等于否认 司法的公众认同和法治的公众认同。因此,舆情民意的鉴别机制需要我们去作出切实可行的制度完善 或创新,正如日本判例是将公众舆论的影响作为法益侵害在违法性阶段进行判断,即将之还原成为犯 罪的社会影响。57至于所谓邓玉娇案等是司法对“社会问题司法化”的妥协,故民意最终将有损司法 独立和权威。58其实,“社会问题司法化”所说明的正是司法的独立而非相反。
所谓内在的,实指刑事司法这一信息系统还有其自身的信息转换规律,这更需要我们去作出切实 可行的制度完善或创新,而这里所说的需要完善或创新的制度包括刑事审判的陪审制度、定罪量刑听 证制度、裁判文书说理制度、法庭之友制度等。就刑事审判陪审制度而言,应立足于真正改变人民陪 审员“陪而不审”的“审判傀儡”局面,力求让人民陪审员把涉案所需的专业知识带到刑事审判及裁判 合议之中,同时把生活情理即常识、常理、常情带到其中;就定罪量刑听证制度而言,应改变以往注重 量刑听证的做法而转为也注重定罪听证,因为刑事个案引起公众争议首先是定罪;就裁判文书说理制度而言,应根本改变现在依然普遍存在的裁判文书对辩护意见只表态采纳与否而不清楚说明为何采纳与否的“暗箱状态”;就法庭之友制度而言,“法庭之友陈述”能够帮助法院作出公正的裁决。59“法庭之友”制度的建立,同样将使得专业知识和常识、常理、常情进入审判中,以帮助法官作出准确判断。法庭之 友制度可视为陪审制度的有益补充,陪审制度与法庭之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对应着对“法官精英化” 的恰当把握,即法官相对于普通人在法律专业知识上可被视为“精英”,然而司法的过程远远不仅是运 用法律本身的过程,国外的陪审团制度早已昭告法官的“有所不能”或“能力欠缺”。经由外在鉴别机 制和内在规律运行,公众认同的裁判结论便是“社会公信”下的刑事司法这一信息系统运转的“正品”。
前述制度安排对应着司法实践中法律世界观多样化的客观现实与法律世界观融通性的务实主张。这里 的“融通性”,即交往理性,它直接决定了司法机关及其人员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社会面前、以一种 什么样的话语方式展开对话。于是,压力型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阶段性特 质:司法机关缺乏足够的法律智慧,不能很好地驾驭司法风险。因此,司法机关唯有树立正确的法律价 值观和世界观,以建构回应型和融贯性司法。60前述制度安排将有助于增强刑事司法的“法律世界观的 融通性”,从而有助于增强刑事司法和刑事法治的公众认同,而此可视为是在“社会公信”政策的导引之下。
前述制度安排最终应放在司法独立的语境中以求证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司法独立不是机械地看司 法是否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是要看当司法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时司法系统自身的鉴别力和决断力 如何。易言之,司法独立并不排除司法机构依据自身的立场和判断去接受、吸纳或认同社会各方面的 建议和意见,而评价司法是否具有独立性的标准是司法有无排拒依据法律所应当排拒的因素的能力, 故在高度强调司法独立的美国历来把创造性地、及时地、恰当地回应各种社会要求视为重要的司法理 念,因为视法律制度为封闭系统的观点不过是学院中的纯粹理论教条。61易言之,拒绝民意在法律思 维上是封闭和不求上进的,是另一种“法条主义”。62因此,中国的司法特别是刑事司法应在其与舆 情民意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关系中保持独立性,而前述制度安排正是出于这样的宗旨。由此可见, 不像“社会效果”是有待事后实证的东西,“社会公信”是可在司法过程中予以制度化和程序化安排 和落实的东西,从而是可以“指数化”的东西。
按照韦伯的理论,刑事政策包括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和社会本位型。63公众认同型刑 事司法所要求的“社会公信”司法政策对应着刑事政策的社会本位型或社会本位型的刑事政策。
四、结 语
当置身于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刑事法治历史,我们对司法政策似可形成如下判断:当法制不健全 与人治思维根深蒂固交互作用时,则盛行的是以“稳定”一词为表达的政治效果话语;当法制接近健 全和人权思维越发深入人心交互作用时,则崛起的是法律效果话语。当分别走向两个极端的问题被有 所认识之后,便形成了“两个效果”话语。“两个效果论”不仅存在着无法统一或兼顾的问题,而且陷入了实为“社会效果论”甚或“政治效果论”。于是,在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冲突消解已成普遍社会诉求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公信”便构成新的主导型政策话语。从“严打”政策及其所对应的刑 事司法一路考察过来,刑事法治的整个发展概貌是:刑事法治从无到有,由弱变强,而正在形成的趋 势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这两个层面在此消彼长之中渐趋黏合。进一步地,司法政策包括刑事司法政 策终究是社会政策,而作为社会政策的司法政策包括刑事司法政策应仅仅盯住法治包括刑事法治这一 根本目标。中国自己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所勾画的当然是法治包括刑事法治建设的“中国轨迹”。 由此“中国轨迹”,中国刑事法治无可避免地需要经历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双失”到实质法治 对形式法治的“贬损”再到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渐趋黏合”。“社会公信”将成为引导中国未来 刑事司法和刑事法治的新政策,并促进刑事司法与刑事法治之中的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
刑法之真,是指刑法在符合事物的状况和规律中得以制定出台,后在自身的内外协调运行中反映 刑事个案的事实真相,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且行刑科学。其中,符合事物的状况和规律,指向“刑法 本真”;自身的内外协调运行,指向“刑法自真”;反映刑事个案的事实真相,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且行刑科学,指向“刑法用真”。64显然,“社会公信政策中的刑事司法”是将“刑法用真”作为自 己的精神与价值境界。
[学科编辑:王彦强 责任编辑:王 艳]
1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202-203 页。
2 前引1,彭真书,第213-214 页。
3 前引1,彭真书,第303 页。
4 宫志刚:《邓小平“严打”思想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5 期。
5 赵秉志:《对“严打”中几个法律关系的思考》,载《人民检察》2001 年第9 期。
6 前引1,彭真书,第212 页。
7 杜渐:《“严打”要常抓不懈》,载《社会》1996 年第9 期。
8 黄洪:《“严打”斗争中需要研究的十个问题》,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6 期。
9 参见[美]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7 页。
10 薛剑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司法实现》,南京师范大学2009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9 页。
简短的宣誓仪式后,我们沿路折返。抬头望去,太阳灿烂而耀眼,天空澄明而透亮,雪山纯净而巍峨,大地静默而厚实。这是真实的所在,我们不忍打破这静谧,沉默着步履匆匆地行进,却在心底涌动着爱的热流。离乡万里来援疆,我只是一位平凡的教师,是这天地中的一粒微尘,我愿在疏附二中的三尺讲台上,像那石头小屋般驻守,为我的学生们留一盏爱的心灯。
11 参见陈金钊:《被社会效果所异化的法律效果及其克服——对两个效果统一论的反思》,载《东方法学》2012 年第6 期。
12 参见陈卫东:《“佘祥林案”的程序法分析》,载《中外法学》2005 年第5 期。
13 参见曲新久:《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268-269 页。
14 于改之:《论“严打”的要素底线及刑罚效益》,载《法学》2001 年第12 期。
15 严励:《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载《社会科学》2003 年第9 期。
16 韩宏伟:《公众意愿与压力型司法——基于李昌奎案的延伸思考》,载《理论月刊》2015 年第3 期。
17 前引9,诺内特、塞尔兹尼克书,第107 页。
19 王勇:《超越复仇:公众舆论、法院与死刑的司法控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 年第4 期。
20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版,第270 页。
21 前引11,陈金钊文。
22 齐崇文:《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法理学分析》,载《人民司法》2011 年第11 期。
23 阴建峰:《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中心》,载《河南社会科学》2011 年第2 期。
24 吕芳:《穿行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载《法学论坛》2005 年第3 期。
25 刘岩:《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若干思考》,载《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 年第4 期。
26 张旭东、刘时杰:《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下司法公信力研究——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视角》,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2 期。
27 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载《中国法学》2008 年第4 期。
28 杨高峰:《从刘涌案看司法判决的社会公众认同》,载《学术研究》2004 年第10 期。
29 杜少光:《处境尴尬的法官——从许霆案说起》,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30 页。
30 黄懿斌:《“邓玉娇案”后问题的审视》,载《中国检察官》2009 年第9 期。
31 前引27,顾培东文。
32 孙万怀:《罪刑关系法定化困境与人道主义补足》,载《政法论坛》2012 年第1 期。
33 江必新:《司法视域中的法学研究课题》,载《法学研究》2011 年第6 期。
34 前引11,陈金钊文。
35 尤金亮:《刑罚裁量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比较与选择》,载《学术界》2013 年第3 期。
36 前引11,陈金钊文。
37 孙海波:《“后果考量”与“法条主义”的较量——穿行于法律方法的噩梦与美梦之间》,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
38 王强军:《论刑事裁判中的结果导向及其控制》,载《法学》2014 年第12 期。
39 张军:《审判工作既要讲法治也要讲政治法官既要做法律家也要做政治家》,载《人民法院报》2008 年9 月15 日。
40 宁杰:《制度结构视野中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以英美差异为参照》,载《福建法学》2009 年第2 期。
41 吕忠梅:《论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载《人民法院报》2008 年11 月4 日。
42 晁秀棠:《法律效果及其研究和测定方法》,载《法律科学》1992 年第5 期。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178 页。
44 孔祥俊:《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一项基本司法政策的法理分析》,载《法律适用》2005 年第1 期。
45 杨永:《法律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帕累托最优——基于婚龄的研究》,载《经济师》2010 年第10 期。
46 前引11,陈金钊文。
47 桑本谦:《法律论证:一个关于司法过程的理论神话——以王斌余案检验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 期。
48 陈洪杰:《共识难题:法律商谈的经验之维》,载《交大法学》2013 年第3 期。
49 前引48,陈洪杰文。
50 前引48,陈洪杰文。
51 前引48,陈洪杰文。
52 [美]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87 页。
53 罗智敏:《从邓玉娇案看民众“干预”司法的若干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09 年第6 期。
54 [以]巴拉克:《民主国家的法官》,毕洪海译,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253 页。
55 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第170-171 页。
56 徐光华:《从涉案主体的身份特征看影响性刑事诉讼中的司法与民意——以2005—2014年〈南方周末〉评选的55件影响 性刑事案件为例》,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3 期。
57 前引19,王勇文。
58 徐光华、艾诗羽:《从影响性刑事案件反映的社会问题看刑事司法与民意——以2005年至2013年的119个影响性刑事案 件为例》,载《法学杂志》2014 年第10 期。
59 参见陈桂明、吴如巧:《“法庭之友”制度及其借鉴》,载《河北法学》2009 年第2 期。
60 参见前引16,韩宏伟文。
61 [美]本杰明·内森·卡多佐:《法律的生长》,刘培峰、刘骁军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65 页。
62 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载《中外法学》2009 年第1 期。
63 前引15,严励文。
64 参见胡祥福、马荣春:《论刑法之真——刑法文化的第一个勾连》,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 2期。
The pattern of judicial policy determines the shape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rule of criminal law. The change of judicial policy from "severely cracking down on criminal activities" to achieving "two effects" (i.e. judicial and social effects) and to enhancing "social public credibility" shows tha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has determined its judicial policy, which requires the country to select the type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rule of criminal law in agreement with its actual conditions. All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le of criminal law is a long-term cause which can never be accomplished at one stroke. To be more specific, it will inevitably go along the three-step path from the zero- sum competition between formal legality and substantive legality; to the achievement of substantive legality at the expense of formal legality; and to the convergence of formal legality and substantive legalit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public acceptance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legality, the policy aiming at "social public credibility", evolving from the previous policy intended to achieve positive social and judicial effects, is to become the policy leading China's future criminal justice and rule of criminal law. With this policy, the criminal justice and rule of criminal law will witness a structural integration between formal legality and substantive legality and be realized as corresponding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justice.
judicial policy; criminal justice; judicial effects; social effects; public cred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