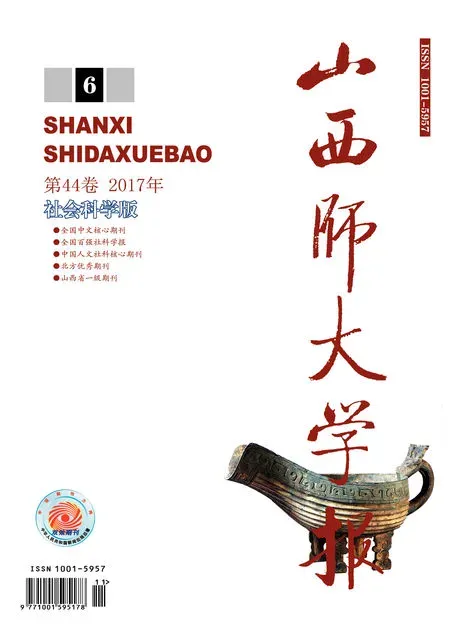沉沦与澄明
——多维存在的祁同伟
梁 晓 萍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改编自周梅森的同名小说,由原作者担任编剧,李路执导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被许多人指认或命名为一部颇有影响力的反腐力作,如豆瓣读书网以传统文学史的口吻简介该剧的内容曰:“本书讲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临危受命,调任地方检察院审查某贪腐案件,与腐败分子进行殊死较量的故事,艺术再现了新时代、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反腐征程的惊心动魄,深情讴歌了反腐斗士的坚定信仰和无畏勇气,并最终揭示出党的领导干部应如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一宏大的政治主题。”但我认为,《人民的名义》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此,它更应该被看做近年来在人性刻画方面具有出色表现的一部力作,尤其是祁同伟,以其充满张力的形象演绎,成为该剧中一个最具有隐喻性的存在学意义上的存在者。
一、存在意义的坚持
存在是一个亘古的话题,也是当代人格外关注的一个命题。尤其是在“人”这一独特的存在者被权力、金钱等各种欲望之洪流裹挟着越来越远离存在之基、越来越背离存在之真意的时候,《人民的名义》浴污泥而出染,有意针对时弊和人性之偏,并没有简单图解欲望,也没有粗暴处理人性,而是以对比的视角、追忆的方式以及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等,向观众郑重声明:祁同伟是生成的,而非现成的。祁同伟之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镜像,或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逐渐生成并敞开了的人格蜕变之“存在境域”。
祁同伟出身于农村,没有显赫的家庭与家族背景,没有得力的靠山,“一切只能靠自己”成为他奋力向上攀爬以改变自己生存处境的唯一信念和途径。凭着努力学习,他考入汉东大学政法系;凭着品、学、能兼优,他成为学生会主席;凭着执著与真诚,他吸引了官二代女朋友陈阳;同样地,他梦想着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出色表现而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以及与女友共处一个城市的资格。这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一种包含着对命运与现实安排否定的存在,其中有着一个强烈要求按自我意愿存在的“意识主体”,这个意识主体不安于“已是所是”的既定命运,不安于与其他事物毫无二致的“在那里”式的存在,而要求与这个世界发生自为的更理想的联系;相比于安于现状而沉默的大多数人,好不容易才走出农村的他不愿意追求“消失在人群中”式的安全感,更愿意在“他者”构成的壁垒中搏击、跳脱,走向一片自我设计、意志为王的开阔地带。
最初,祁同伟的这种勇于对抗现状,大胆探索人生且无害于他人的做法是“生存”着的人的一种自觉选择,应当受到称颂与鼓励,然而,现实的利害之网具有强大的阻拒力量,祁同伟遇到了来自“他者”的恶意控制。最直接的他者是梁璐,一个被异性欺骗导致无法生育的女子,以其掺杂着报复等混浊的功利色彩来控制异性的任性心理,追求着已经有女朋友的祁同伟。剧中的梁璐是西蒙娜5德5波伏娃笔下为父权制造的被“统治主体”观望的客体,她的显赫的出身并没有使其摆脱“次要的他者”身份,而是不可避免地成为满足男性欲望与欢愉的身体与肉体。要命的是她没有在反思中找回自我与主体,走向属于自己的自由境域,反而放弃自我沉思,放逐主体,试图凭借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征服祁同伟,以赌徒的心态充当一次黑格尔笔下的“奴隶主”。
主体被扭曲的梁璐让自己的父亲利用权力把祁同伟和陈阳分别分配到小山村和北京,让他们在彼此分离中“考验感情”。祁同伟明知自己如同棋子,遭人摆布,却不轻言放弃,他拥抱着自己清醒的意识主体上下求索,为了能够去北京与陈阳相聚,他主动选择加入缉毒队。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他一个人闯进毒贩窝点,被穷途末路的毒贩群追杀,身上连中三枪,几近致命。无处可逃的祁同伟被一个小孩子的歌声吸引,躲进一位乡村老人的家,才免于一死。只身深入虎穴的祁同伟如愿地成为了“英雄”——“缉毒英雄”,他想,凭着自己“英雄”的行为与功绩,自己一定可以离心爱的人近一些,再近一些,倘若运气不错,甚至可以从此改变处境,扭转时运。然而,祁同伟只是获得了英雄的称号,获得了一个小官,如其自己所言:“英雄在权力面前只是工具”,如此而已。“他者”梁璐再一次以“奴隶主”的身份控制了祁同伟的身体这一“物”,并且还开始控制祁同伟的主体意识。这一次,她让父亲以惜才为名“重点培养”他,胁迫他,不让他调离山村,甚至想让他和那个同样受打压而在山村一呆就是三十年的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生一样,在山村呆一辈子,除非祁同伟改变选择,放弃自为的努力,由否定的、超越的“自为的存在”变成一个没有否定的、僵死的“自在的存在”。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指出,当个体意识到它与对象的同一时,自我意识就产生了,两个作为欲望的自我意识在较量中便产生了“主奴关系”,这种“主奴关系”的确立建立在“奴隶”屈从于自身的生命也屈服于他人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坚持自身的生命力和意志力,无论遭受何种压力,也绝不放弃对于自由与尊严的追求时,他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意识主体而沦为“奴隶”的。在乡村一线工作的祁同伟尽管生存空间有限,生存条件艰苦,尽管他与世界的关联域还很局促,而且由于与心爱的人相距甚远,也会有精神上的折磨,但只要他不让另一个自我意识(奴隶)虚无化、主宰自己的自为存在,那么,他就是自己的主人,就是一个拥有自由、追求超越的存在者。
然而,祁同伟的意识主体被“校园一跪”击中了,其苦苦坚持着的存在的意义自此开始向着另一个向度奔跑,而这种奔跑,使其自身的存在离自由越来越远。
二、正向的存在意义被遗忘
当他者以光明的动机遮掩其卑鄙的行为时,祁同伟决定改变航向,将初恋的真爱永久封存,在自觉的自我否定中转变为一个积极归顺“奴隶主”的“奴隶”,转变为一个面目全非的自我。这也是一种自我选择:选择事业,放弃爱情;事业上选择借势发展,放弃自我努力。但这种选择是以让渡“自为存在”、牺牲真正的自由为代价的,它必然使自己陷入被无形的“大他者”牢牢控制、无法超越常人、无法实现本真自由的人格和人性困境,致正向的存在的意义被严重遮蔽、扭曲。结果其正向的存在意义在遭遇来自无形的他者的否定、绞杀或虚无化中被严重地遗忘。
祁同伟回到学校,在梁璐的命令下,他手捧鲜花,在操场下跪,“求”对方嫁给自己。从此,祁同伟像换了个人似的,在梁璐面前变成了一具“僵尸”。祁同伟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难道这一跪,真有那么大的致命性?当代社会,不是有不少青年男女精心策划属于自己独有的一场求爱场景吗?对于这一富有浪漫色彩的场景,多数女孩子会非常羡慕,多数男孩子则会因之敦促自己的勇气,在脑海中营构一个惊天之举。这一跪如何会改变祁同伟的心理与人生呢?
原来,这一跪之所以成为祁同伟人生的转折点,是因为其起因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在他者的逼迫中做出的一个表演性动作;这一跪,跪的不是充满自由感与幸福感的爱情,而是可以改变其命运的权力;这一跪,接受者表面看来是梁璐,实际上是剧中未曾亮相的梁璐的父亲;这一跪,表面的接受者内心充满了不屑,因此从一开始便以居高临下的不平等目光俯视着祁同伟,从而加速了祁同伟内心情感的基因突变;这一跪,地点选择在容易收集到众多见证目光的操场,然而滑稽的是,众人的见证并不能成为祁、梁二人爱情长跑的道德约束力,反而成为并非情愿下跪的祁同伟不堪回首的揪心一幕;这一跪,激发出的不是对于自由之世界的向往,而是对于捆绑式人生的厌恶与逃离……这一跪,彻底改变了祁同伟的生存轨迹。
一方面,祁同伟向着表面的自由进发,他借助政治婚姻成功升迁,进入省检察院,官至公安厅厅长,在仕途大厦中抵达了一个一般人尤其是一个没有引荐者与推动者难以抵达的高度,甚至很有可能向着更高一级“副省长”的高度进发。他掌握着极大的权力,为家乡的亲朋好友办成了许多棘手的、合理与不合理的事情,权力使其生存的空间不断被拓展,也使其“自由感”不断升腾,祁同伟的现实的、可以感知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都被打开了。
另一方面,祁同伟却朝着黑暗的深渊不断下坠。黑暗是世界的必然存在物,这里的黑暗不是指科学意义上所说的宇宙的初始阶段,也不是指自然界与白昼相对的那一段时光,而是指因利益、权力等被掠夺、瓜分而引起的邪恶冲突、血腥斗争等,以及因之而来的心灵的阴沉、残酷感与压抑感。黑暗的存在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仍有权利期待着某种启明”[1]3,这是存在主义思想家、哲学家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呼吁与倡导。阿伦特曾经因其犹太人身份而倍受身体与心灵上的打击与伤害,并且渡过两段充满艰辛的流亡生活,但她没有被黑暗吞没,也没有被黑暗带来的恐怖所击垮,被激发出来的反而是“世界之爱”,是对能够反映人的自由与完善的“公共领域”的热爱与重建“世界之爱”之决心。鲁迅也是如此,面对苦难、黑暗与虚无的世界,他没有成为黑屋子中“昏然入死灭”的“熟睡的人”,而是选择了直面体认与勇猛还击,并重新回到了年轻时对摩罗诗人们“反叛—抗世”型生存方式的肯定之中,重新做回“战士”,成为“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清醒者”,以此超越自我生命的虚无,积极创造自我的生命意义。[2]面对黑暗的侵袭与包裹,祁同伟却没能如阿伦特、鲁迅一般让追求自由之自我坚强屹立,有效反击,反而被其裹挟着向着欲望的深渊滑落,下坠,离“自由”渐行渐远。
“自由”是哲学家词典里的常客,在存在主义领域,“自由”既包含了康德缘于“自律”的“自由”,也有马克思建立在“人是社会关系总和”基础上的“自由”,既重视个体的意识与行动的自由,又不忽视社会“处境”的重要作用与责任承担的必要性,也即意味着,人的自由是一种关联四域的自由,是一种充满辩证转换可能的自由。在这种包含着“他者”关系的“自由”中,他者对一个人的自由既是限制又是依凭的条件,既是否定,又是否定之否定,即更高层次的肯定。过分强调他者限制及其否定自身自由的一面,人的自由不过是假想的、虚幻的、永远得不到实现的乌托邦式的自由;过分强调他人决定和肯定自身自由的一面,则又会因过分依赖他人而使人的自由被扭曲畸变,使人变成与椅子、石头等没有区别的自在的存在之物。祁同伟的确是在积极主动地适应不断向他展开着的存在之境域,想要通过自己的选择与行动,超越现实的处境,抵达自由的存在之境。然而可惜的是,他的选择与行动因客观上过分依赖梁璐及其父亲的权力,因而他获得的自由实际上存在着使其不断沦为“椅子、石头”的可能,这是一种自由的异化,祁同伟没有能够克服和抛弃这种异化。而且,他也仅把自身的自由当作目的,而没有把梁璐的自由当作目的,因此,在实现自身自由的同时,不仅不去实现梁璐这一同为弱者的他者的自由,反而阻碍梁璐自由的实现,如此,则梁璐这一不自由的他者则会变成他的地狱。
如果说汉东大学校园操场一跪,祁同伟丢失的是尊严的话,那么这一跪,也使其因情绪偏激、抛弃他者自由而失去了获得自身自由的机会。尊严的丢失可以用真诚与努力挽回,放弃他者却彻底斩断了祁同伟的身心自由之路,使其在这悖离自由的路上越走越远。成为公安厅厅长的祁同伟开始大肆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顾共同自由之“伙伴”的个别人利益:通过丁义珍,他为情人高小琴圈下名义是工业用地实则用来经商的山水度假村,成立了山水集团;通过山水集团,他帮助前任汉东第一把手的公子赵瑞龙侵吞汉东油气集团这一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7个亿;通过高小琴放临时贷款以及唆使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清泉派人恶意误判,置大风厂几百工人的利益于不顾,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属于大风厂工人的股权,并且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欲强行拆掉大风厂;当得知丁义珍被最高检察院盯上时,他第一时间指挥丁义珍成功外逃;当得知陈海将与检举者见面,他的暗箱操作将很可能浮出水面时,他作为幕后主使制造了车祸,使陈海的意识几近停滞……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是祁同伟作为一个意识主体的选择与行动的展开,有的事件,祁同伟也许并未直接露面,但他是一个隐藏的行动者,尤其是丁义珍出逃与陈海被害两件事。选择与行动可以使人自由,然而问题在于,祁同伟的选择与行动割裂了与他者的关系,他在为自己的自由实现开启了一扇门的时候,却为别人,更为一些生存处境极其艰难的弱势个体,如同法的门前的卫士一样,结结实实地筑起了一道门*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法的门前》:在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卫士。一个乡下人请求卫士放他进法律的门里去,卫士告知他有可能进去,但现在不允许他进去。法律的门始终打开着,乡下人得知不能进后始终未进去。临死前,乡下人问:"怎么在这许多年间,除了我以外就没见有任何人来要求进去呢?"卫士大声告知他这门就是专门为他而设的。卡夫卡著,谢莹莹等译《变形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至此,祁同伟确然难以实现其自身的自由了,其作为一个特殊存在者的存在意义也被其不负责任的选择与行动被绝大多数地遗失了。
三、一个矛盾的存在者
在《筑5居5思》中,海德格尔曾以桥作喻,强调存在者之存在的境域关联性特点:“大桥‘自如而有力地’横跨在河流上。它不只是把在那儿的两岸连接起来。”“桥让河流自行其是,同时又为必死者开出一条路,使他们能往来于两岸之间。”[3]141—142祁同伟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关联四方、关联众多他者的“桥”一般的存在者,以祁同伟为“桥”,高育良是他的老师兼上属,侯亮平、陈海是他的同学兼合作同事,他的上属还有沙瑞金、田国富、李达康,他的合作同事还有季昌明、赵东来、陈清泉、肖钢玉,他的下属有程度,他的生意合作伙伴有赵瑞龙、刘新建、丁义珍、高小琴,梁璐是他的妻子,高小琴是他的情人,其他或远或近的相关人物还有吴慧芬(高育良的妻子)、欧阳菁(李达康的妻子)、陈岩石、王馥真(陈岩石妻子)、蔡成功、郑西坡、王文革、钟小艾(侯亮平妻子)、易学习、王大路、家乡不知名的同乡亲戚等。关联多方关系的祁同伟成为一个多棱的存在,在高育良眼里,祁同伟是一个有能力又善于审时度势、工于算计的学生;在李达康眼里,祁同伟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为了权力能够很上心地哭别人的爹的官场小人;他是梁璐眼里善用权力、情商极低甚至冷酷阴险的男人;却又是高小琴眼里肯于吃苦、能力极强、又充满温情的可靠的男人;在侯亮平、陈海看来,祁同伟有心计,很莫测,有能力,有抱负,能吃苦,能忍受;在陈岩石老夫妇看来,祁同伟出身贫寒,本性善良,却因时因势而变得趋炎附势,过于钻营,贪婪自私,变本加厉。祁同伟是赵瑞龙们眼中有着与一般人没有多大区别的“软肋”的当权者,可以以美色诱惑之,也可以以金钱打动之;却又是同乡亲戚眼中凡事都可以迎刃而解,巧妙化之的大官、能人。
在以祁同伟为核心的关系图谱中,以其权力为着眼点,存在着以下两大类人:一类利用他和他的权力,或者实施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谋取巨额利润,是为赵瑞龙们,或者借其权力为自己办点私事,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困境,是为程度们与同乡们,或者利用其权力与地位的提升扩张自己一方的政治势力,是为高育良们;另一类则试图约束其权力,矫正其权力使用的方向,使其在一定的域限内发挥正向的作用,是为沙瑞金、李达康、侯亮平、陈海、陈岩石们。从情感是否真诚的角度来看,有的对其付出真情,譬如未露面的陈阳及其父母,以及同学侯亮平、陈海等,这些人看重的是他善良的人性、对生活的执着以及对理想的追求;有的则虚情以待,与其交往,看重的是他手中的权力、他可以为其谋利的能力。如此简单的分类当然难以揭示出祁同伟周围诸多变动不定的复杂关系,但联系上述两种分类大致可以看出,出发点的有无功利性基本决定了与其交往时情感的真诚与否,进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祁同伟实现其自身真正自由的进程与效果:利用其权力的相处者,谋利是其宗旨,故而虚情以待,为其制造各种生活的幻象,使其在短暂的安逸与满足中被套上无数私欲的绳索;无功利者则以真情相处,不慕名利,真挚交往,在云淡风轻般的自然而然中,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舒展身心的自由空间。
在祁同伟的交往关系图谱中,高小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她最初与祁同伟的交往完全是被安排的,即被赵瑞龙等当作行贿“工具”送与祁同伟这位公安厅厅长。然而二人一见如故,随着二人交往的深入,随着彼此由于际遇的相近而惺惺相惜,二人之间有了一种心灵上的默契,甚而成为了带着温情的彼此的知己。当祁同伟准备孤注一掷时,高小琴出于良知与真情会劝阻他放手,停下脚步,这种纠偏,尽管充满了自私的打算,而且也不会被祁同伟采纳,但毕竟因其存在着良知与真情,也会使在官场与人世间打拼得心渐坚硬的祁同伟为之一动。
祁同伟的人生关系图谱中,还有两位非常关键的人,即在其身中三枪而救其性命的那位乡村老人以及唱着儿歌的那位小男孩。此二人与祁同伟素不相识,却能在最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以最为纯洁的人性之光为祁同伟保存了生命中最为透亮的一片光明地带,正是他们的存在,使祁同伟内心深处的良知在关键时刻被唤醒,使其在坠入黑暗的深渊时突然被人性的光明照亮。故事的结局处,当祁同伟已经将自己的救命恩人安排到安全地带,他完全可以利用先进的武器与超凡的射击能力射杀侯亮平时,却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举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纵观祁同伟的所有选择与行动可以看出,他既心存善良又心狠手辣,既坦率真诚又善于伪装,既懂得收敛又贪财无厌,既乐助同乡又雇凶杀人;他在官场为官时是两副面孔,时而谦逊奉迎,时而霸道施令;他作为一个男人面对异性时也是两样态度,时而冷若冰霜,时而温柔体贴。一个词或一类词都不可以概括祁同伟复杂且富于变化的性格特征,正是这种丰富性、多义性、多维性使其成为《人民的名义》中极具魅力的一个形象。
祁同伟还是一个多维镜像的存在。以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当婴儿冲着镜子里的镜像微笑时,他第一次把镜像这一他者视作了自我,并开启了以想象建构自我与世界之关系的历程。之后,镜像阶段便成为人生恒久的一个过程与存在,它的隐喻性在于:在这个永久性的镜像过程中,人的自我通常借助于他人而诞生与生存,倘若没有他人,自我便无法独立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周围他人的眼光和评价以镜子般的作用要求于我,使“我”得以做出回应式的“美容”“补妆”,故“我”就是他者的依赖者或亦可说就是一个他人。祁同伟从他者的目光与评价中也看到了自我:从高育良指责其听到“沙李配”便在丁义珍出逃一事的会议现场支持达康书记的言辞中,他看到了在政治中“善于选择,调整航向”的自我;从李达康婉讽其“哭坟”的评价中,他听到了一个敢于为进阶而表演的自我;从梁璐的目光中,他看到了一个丢掉尊严的自我;从高小琴一句“我愿意”的真挚话语中,祁同伟又找到了一个充满善意且能够被托付的自我;与赵瑞龙结伴,他嗅到了自己身上强烈的贪欲;与侯亮平相处,他又试图寻找回充满正义感的自我……镜像中的祁同伟正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存在者,该剧正是通过祁同伟身上这种重叠着善恶、交替着美丑的矛盾性,制造了敞开性的“世界”(意义)与锁闭性的“大地”(形象)之间的“亲密争执”,使作品呈现出一个比较复杂而广阔的人性境域,赋予祁同伟这一形象的深邃、独特、复杂、歧义和难以言尽的神秘性。应该承认,这一形象的塑造是近年来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难得的突破,尤其是借用存在主义哲学来审视它,就更能窥见其独有的艺术价值。
四、走向孤鹰岭:从沉沦走向澄明的努力
当祁同伟收到高小琴发来的短信,得知自己已无路可走时,他背着狙击步枪选择上了孤鹰岭。孤鹰岭,一座孤傲、孤独的“孤岛”,一个全村都在贩毒、吸毒,只有一家人远离毒品、保持着洁净的小村庄,是祁同伟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他荣誉之光最为耀眼的地方,是他的身心能够得以安顿的地方,也是其可以诗意地栖居的地方。在这里,他听到过世上最清澈、最打动人心的歌曲:“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音色纯粹,歌词无邪,歌中的自己是一名百分百值得信任的警察叔叔,代表着正义与道德至高点,尊严被托举得很高,很高,人格被塑造得几近完美。在这里,祁同伟体验过生命之流几被截断时最为真实的自我,奄奄一息,浑身乏力,却依然可以冷静地应对无数倍于自己的敌手,依然可以机智地交给老人一个救命的电话,依然可以咬紧牙关等待同道之人胜利的讯息;在自己的人生被逼迫得只留下生命本身,如同冬天被狂风扫尽树叶的树枝时,依然可以剪掉繁华的功利之枝,只留下本真一个自我。孤鹰岭是祁同伟的心灵栖居之所,是其人格化的存在境域,在这里,祁同伟感受到的不仅是自然的深邃与静谧,宏大与无限,还有海德格尔笔下“山林小屋”般的意趣与灿烂。孤鹰岭、儿童的歌声、老人、小木屋,是祁同伟人生最富诗意的维度,他的精神在此得以饱满,他的气息在此得以顺畅,他的心情在此得以舒展,他的思绪在此得以伸向远方。在自然质朴的氛围中,他可以从外境的纷扰中澄净于内心的空灵之境,把日常生活中碎片化的自我整理成一个完整的自我。
在自己人生最为落魄、身处绝境而无处逃遁时,祁同伟选择来到了这里,在小屋里与自己的救命恩人聊天,在表面的静谧与安宁中整理自己的人生。他的选择表明了他的回归与心灵取向,他纯洁的人生底色依然存在,耳边讴歌着警察叔叔的歌声依然打动着自己的灵魂,他不屈的魂魄依然想将自己的荣耀之旗高高举起,但这次,在这座孤鹰岭,他遇到了最为强大的对手——自己,这个曾经不安于命运的安排,不服于权力的不公,以不屈的灵魂对抗强大的外力,却又丢掉尊严跪于权力,自此为挽救做人的尊严而贪婪,而滥用权力,甚而杀人灭口,为改变命运而奴颜奉迎,而巧取豪夺,而欺凌弱小的自我;这个曾经拥有真情,敢于为爱而拼命一搏,却又折服于权力,仗势欺凌尽管过于霸道却同样弱小的梁璐的自我;这个变得连自己也不太认识的陌生的自我……但无论如何,即使埋葬自我,祁同伟也要选择孤鹰岭,这个在他看来是一个让他的心灵可以被涤荡干净的地方,来存放一个尽可能干净的自我。
祁同伟是一个富有弹性的人物,或者说,他就是一个弹簧,操场一跪之前,他生命的弹性被极力压缩,他存在的张力也逐渐被蕴蓄得饱满,敢于自我选择与行动的他是一个自由的存在;操场一跪之后,他生命的弹簧陡然由压缩状态调至膨胀状态,他存在的域限被不断扩大,自主的权限却相应地被挤压。在他的生存历程中,有着令人可歌的坚强、勇气与抗争: “我们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并且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哪怕搭上我自己的性命,我也要胜天半子”;有着令人同情的不公与无奈:“我希望凭我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这样慢慢地做上来,但现实残酷”,“改变我命运的是权力不是知识”;也有着令人痛恨的阴险与凶狠:“为了抓住这个机会改变命运,我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当他放弃杀害侯亮平,放弃最后的报复,说出“陈海的命我会还,但这世上没人能审判我”,又以耸动的喉头、绝望的眼神、抽搐的表情、嘶心裂肺地喊出“去你妈的老天爷”时,依然可以听到人们的叹息!因为他罪至于死,却又似乎不至于立刻去死。我们无法抹去他手上的血迹,却也无法忽视其“胜天半子”般的决绝与找回尊严的努力。而之于祁同伟,却因其丢掉了一切包袱,看轻了一切束缚,抛弃了作为“工具”的自己,仪式性地把自我引向一片自由地带,而为观者留下了诸多未完待续的人生思考。
作为敢于自我选择的“存在者”,祁同伟又一次做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所不同的是向其正向存在、正向自由、正面人格的以“死亡为代价”的一种“方向性”挣扎、仪式性的回归。“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他已经回不去了。但这最终的“回不去而仍要象征性地回”,一种向善的主体意识、灵魂转向,虽不免完全为一种“形式的行为艺术”所俘获,但仍然力重千钧,义压全剧,因为它是对祁同伟另一种“存在”的指示,是一个罪无可赦的临死者,对人生正向选择、正向存在的终极性肯定。这一肯定,依佛教哲学来看,便可几近于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义了。很显然,这一笔也仿佛有海德格尔“去存在”之选择之义,它指向“能在”,指向可“无中生有”的“无”,开启的是接受者的不无积极意义的想象和思考……祁同伟虽饮弹而死,但却涅槃性地走进了“存在论”的另一界面……
祁同伟及《人民的名义》都可观之以“存在哲学”之眼,如此观取到的正是“沉沦/澄明”之“庐山式”多面镜像,而其无限风光之“仙人洞”正是祁同伟这个多维、多面的存在者。
[1] (美)汉娜5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M].王凌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2] 鲁迅.《呐喊》自序[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3]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诗学文集[M].成穷,余虹,作虹译,唐有伯校.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