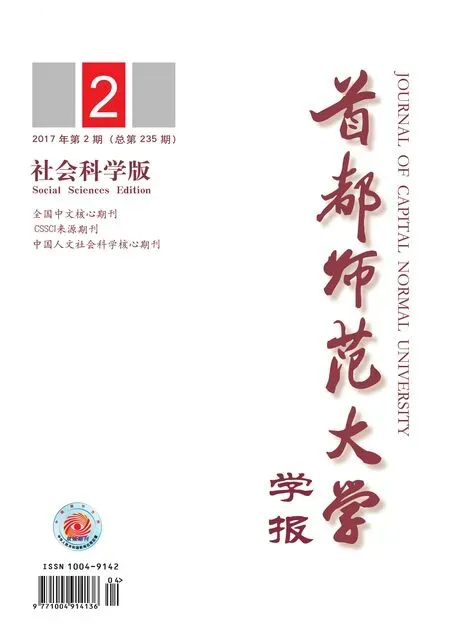评 “新清史”的概念、论点与视角——以《满洲之路》为例
沈培建
一、 新清史与对新清史的回应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些学者在研究清史时,运用族裔概念,强调内亚视角, 宣称其研究主要依靠满文史料。他们认为清朝满汉之间只有“涵化”,而不存在汉化,因此满人保留了满洲特殊的族群认同。[注]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刘风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6页;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125页。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新清史”。 欧立德《满洲之路:八旗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注]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新清史的代表作被称为“四书”。除《满洲之路》外,其它三部著作是:(1)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2)Pamela K.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3)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hina, 1861-1928,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是新清史的代表作之一。
新清史问世后,美国学界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不少评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米华健(James Millward)和濮德培(Peter Perdue)。他们认为,新清史提倡运用满文史料,从内亚角度重新解释清朝统治,开辟了清史研究的新途径。[注]James Millward, Review of the Manchu Wa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2 No.2 (Dec. 2002); Ruth Dunnell and James Millward, Introduction in James Millward (et al.) ed.,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RoutledgeCurzon, London 2004, pp. 1-11; Peter Perdue, Review of the Manchu Wa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33 No.2 (Autumn 2002)。其他一些美国学者的评论载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如盖博坚(Kent Guy):《谁是满洲人?——综合书评》(孙静译),第129-146页;司徒琳 (Lynn Struve):《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美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和问题》(范威译),第323-333页;宿迪塔·森(Sudipta Sen):《满族统治下中国的研究新进展和亚洲帝国的历史书写》(袁剑,董建中译),第334-353页;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新清史》(董建中译),第394-406页。但华裔学者黄培不同意新清史否定汉化,主张涵化的观点。他认为仍应以“sinicization” (中国化) 来解释满汉关系。[注]黄培:《满族文化的转向(1583-1795年)·导言》,董建中译,《清史研究》,2012年第3期。
最初,新清史并未获得国内学界的关注,只有定宜庄介绍并呼吁重视这一清史界的新动态。她和姚大力等学者颇为推崇该学派,认为新清史将新观念、新视角、新方法引入清史领域,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值得借鉴。[注]定宜庄:《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9期;《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满族研究》,2002年1期;《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1期;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史》,《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第125页。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年5月7日和 《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到什么》,《东方早报》2015年4月5日(转自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1902)。台湾的刘世珣、蔡伟杰在介绍《满洲之路》时,也对其学术价值予以肯定。[注]刘世珣:《评介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史耘》14期2010年6月;蔡伟杰:《书评Mark C. Elliott,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政大民族学报》第25卷,2006年12月。
另一些学者相对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小萌。他一定程度上肯定新清史在方法、角度和观点上的创新; 同时又对新清史否定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以汉满对立取代满汉融合,提出批评。他希望新清史和传统清史能相互取长补短,共同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注]刘小萌:《新清史中的八旗研究》,刘凤云等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165页; 《关于“新清史”的几点看法》 (载中国近代史所网,网址,http://book.ifeng.com/special/detail_2014_07/04/141600_0.shtml)。
然而更多国内学者对新清史持批判态度,如黄兴涛、郭成康、葛兆光、钟焓和李治亭等。他们根据史料与史实反驳新清史的观点,说明满人的汉化过程,中华民族和中国观的形成过程,从而证明清朝是中国王朝的延续。[注]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清朝的国家认同》,第267-293页;《清朝满人的 “中国认同”——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第16-34页;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朝的国家认同》,第212-244页; 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清朝的国家认同》第245-266页;钟焓: 《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 (上)—是多语种史料考辩证 的实证学术还是意识形态化的应时之学?》, 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七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213页和《“新清史”学派的着力点在于话语权构建》,《中国社会科学报》734期2015年5月6 日。台湾学者汪荣祖编的《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一书也包括了多篇批评新清史的文章。
新清史自出现至今,一直伴随着意见交锋。最初,新清史学者罗友枝批评何炳棣教授的汉化观,引起后者对前者的强力反驳。[注]罗友枝:《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清朝的国家认同》,第1-18页;何炳棣:《捍卫汉化——驳罗友枝之〈再观清代〉》,《清朝的国家认同》第19-52页。近来又出现了姚大力和汪荣祖关于新清史的争论。[注]姚大力:《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汪荣祖:《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5月17日(转自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1902)。迄今为止,无论是新清史著作还是对新清史的回应,多集中于讨论如何认识清朝历史和满汉关系,对所涉及的概念缺乏充分的论证和明确的认识。概念是学术研究的支点,如果概念不清,往往各执一词;观点和问题的探讨也显得颇为隔膜,无法深入。
本文通过对中美民族历史特点的比较和对北美族群社会的分析,以《满洲之路》为例,澄清书中引用的概念,如“族裔”(ethnicity)、“族群”(ethnic group)、“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涵化”(acculturation)、内亚视角等;进而指出新清史的概念、论点和视角看上去十分新颖,但它们不适用于满汉关系,也不能用来正确阐述清朝历史。
二、 “族裔”:被误用的概念
《满洲之路》以“族裔”为中心展开讨论,强调满洲“族群认同”;认为满洲作为一个群体并没有被同化进中国社会,八旗制度使满洲认同得以保持和强化。[注]Elliot, The Manchu Way, pp. xiv-xv, 12-13,34-35.欧立德将满洲对中国的统治比作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将满汉关系比作美国、德国和法国社会中的少数民族和白人的关系,[注]Elliot, The Manchu Way, pp.7,17,290.并未顾及这些民族关系在族裔和历史背景上有什么不同。
那么,就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民族形成及其族群社会的特点。
15世纪,欧洲早期移民到达美洲,揭开了美国族群形成史的序幕。欧洲人的到来,形成了白种人和红种人(土著印第安人)两大群体。几乎同时,欧洲殖民者从非洲掳来大量黑人作为奴隶,成为美国黑人族群的前辈。而从东方来的移民被称为“亚洲人”(黄种人);加上来自南美和太平洋岛屿的土著居民,形成了美国社会以不同种族(race)为特征的五大族群。至今美国政府的人口普查仍按这五个种族分类。[注]US Census Bureau, Overview of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and 2010 Census Briefs, https://www.census.gov/2010census/#/panel-2.
在美国,“族群”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以不同种族为基础形成的,带有某种文化特点的人群。这一族群本身固有的含义根植于美国历史,并非来源于学者的书斋。因为当社会学家瑞斯曼(David Riesman)在1953年首次使用“族裔”(ethnicity)一词时,[注]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Moynihan, Introduction in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Moynihan (ed.),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5, p.1.美国的五大族群早就形成了。
“Ethnicity”和形容词“ethnic”来源于古希腊文“ethnos”。在《韦伯斯特新百科辞典》中,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 “race, people, cultural group”(种族、人民、文化群体)。[注]Merriam-Webster, incorporated, Webster’s New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Federal Street Press, Springfield 2002.“Ethnicity”按《牛津英语辞典》的解释是族裔或族性(ethnic character)。[注]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英语中原先用“race”表示种族和民族。二战以后,反种族主义浪潮兴起,race一词过于敏感,所以人们渐以ethnicity取而代之。Ethnicity与race同义,但词义更宽泛;除了种族、民族之外,还包括文化。相应地,西方学界也随之出现了用文化因素来划分族群的倾向。
在语境中减弱种族敏感性是社会的进步,但ethnicity 的引入使得族群划分变得莫衷一是。例如,按语言可将人群分为英语和非英语族群;按宗教可分为新教徒族群、天主教族群和穆斯林族群;按来源地和国籍可分为英格兰人、法国人、德国人、犹太人、非洲人、中国人、日本人等。照此分法,一个法属非洲殖民地来的黑人天主教徒,既属于非英语族群,又属于天主教族群。而在他所属的非英语族群中,既有黑人、白人、亚洲人,又有天主教徒、东正教徒、穆斯林。这样,同一个或同一群人,可以分属几个族群;反过来,在一个族群内有又存在多个有不同文化特点的群体。
尽管文化划分的方法有利于从不同角度观察人群,以期他们不会因为自身的族群特点(语言、宗教、来源地和国籍等因素)遭受社会歧视或享有不当特权,但由于“文化”标准本身就很宽泛,通常只在学术领域内讨论,无法成为社会实践中划分族群的标准。
根据1964年美国《社会科学词典》的解释,族群就是“一个在更大社会文化系统中存在的社会群体。它宣称或被认为在复杂特质(族裔特质)方面表现出或被相信表现出具有一致性的特殊身份”[注]Glazer and Moynihan, Introduction in Ethnicity, p. 4.。简言之,族群就是一个具有“族裔特质”(ethnic traits) 的群体。
美国学界对族裔概念意见不一,但公认的是:种族将白人和黑人分为两个族群,族群研究只能以此为基础。[注]Nathan Glazer, Affirmative Discrimination: Ethnic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Basic Books, New York 1975, pp.172, 233 note 6;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4, p. 6.
此外,学界对“族群认同”的看法也不一致。有学者认为,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份认同,如职业、地区、宗教、社区均可以成为族群认同的标志。[注]Nathan Glazer, Affirmative Discrimination,p. 176.但是另一派意见显然更有说服力:即肤色和体征仍然是强有力的群体身份标志。[注]James Olson and Heather Olson Beal, The Ethnic Dimen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4th ed.), Wiley-Blackwell, West Sussex 2010, p. 3.他们认为:身体是个人或族群认同最明显的成份,是唯一没有争议的生物根据,而其他群体特征是可以改变的。一个人可以改换姓名,重写自己的历史,采用不同的国籍,学习不同的语言,信奉不同的宗教,但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体。身体特征是认同的标记,明显可见且无法改变,有力地影响着族群间关系。[注]Harold R. Isaacs, Basic Group Identity, in Glazer and Moynihan (ed.), Ethnicity, pp. 36-37, 39;Talcott Parsons,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on the Nature and Trends of Change of Ethnicity, in Glazer and Moynihan (ed.), Ethnicity, pp. 74-75.实际上,美国许多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否认以文化因素作为族群特征,他们宁愿采用更鲜明的种族认同来争取自己的群体权利和群体认可。[注]Michael Omi and Howard Winant, 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90s (2nd ed.), Routledge, New York 1994, pp. 10-11, 20; Linda Martin Alcoff, Philosophy and racial identity, in Martin Bulmer and John Solomos (ed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Today, Routledge, London 1999, p. 32.
2000年版《加拿大百科全书》的“族群认同”定义是:“族群身份认同描述的是一种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基于和这个群体共享的个人特质、共享的社会文化经验,或同时享有两者,群体成员相信,他或她有共同的祖先。”[注]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McClelland & Stewart, Toronto 1999.定义中虽未用种族一词,但群体成员有“共同的祖先”就是属于同一种族。
尽管西方学界众说纷纭,但官方在社会实践中运用“族裔”概念还是有法可依的。例如,加拿大的《人权法》包括下面一些禁止歧视的依据(ground):如种族(race)、肤色 (color)、来源地 (place of origin)、性别(gender)、年龄 (age)、残疾 (disability)、宗教 (religion)、婚姻状况 (marital status)、家庭状况(family status) 等等。其中种族和肤色是区分族裔的依据。不同族裔(种族)人之间发生歧视,首先考虑是否属于种族歧视。同种族人之间发生歧视,即便他们具有不同的民族或文化背景,一般不视为种族歧视,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族裔区别。
在社会生活中,北美有色人种是少数民族(minorities)。加拿大官方特别将他们称作“可见的少数民族”(visible minorities),就是强调“可见的”肤色和体征是族群间最基本最明显的标志。“可见的”种族标志,不仅用来划分白人和少数民族,也用来划分黑人、印第安人、亚洲人。然而,它却不适用于同种族群体,因为同种族内部没有“可见的”族裔区别。
以黑人群体为例,无论他们来自非洲大陆什么国家,操何种语言,他们之间不存在“可见的”种族差异,均被称为黑人(blacks or African-Americans)。他们原有的民族和文化差异不会被视为族裔区别,因而他们有着共同的族群认同——“African identity”。白人群体亦如此,无论他们来自欧洲什么国家和民族,也无论他们的母语和文化有多大差别,由于不存在“可见的”种族、肤色差异,他们之间不再做“族裔”区分,被统称为 “白人”(whites or Caucasians)。可见,在北美,族裔区别和族群认同,只存在于不同种族的人群之间。
综上,族裔、族群和族群认同等概念中的“族”字,其首要的、核心的含义是“种族”。这不仅载于辞典之中,而且根植于北美族群形成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尽管美国学界对这些概念仍然众说纷纭,但都公认族群研究中种族基础是不可忽视的。
因此,如果用“族裔”来分析美国历史是可以的,因为美国民族是在不同种族基础上形成的。即使美国的白人和黑人以及亚裔等少数民族形成了一个有共同文化的美利坚民族,他们之间以种族为特征的族群区别仍然是明显的、持久的,甚至带有互不兼容的特点。然而,欧氏将族裔概念套用在中国清代满汉关系上,说明他没有分清美国的族群关系与清朝满汉关系之间实质上的区别。满汉关系虽也是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关系,但两者同属一个种族,不存在种族差异这一区分族群的关键因素。从民族和文化上看,满洲在入关前,与汉族世代比邻,八旗中同时包括满蒙汉三个民族,彼此之间的差异与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原始差距,不可相提并论。实际上,欧氏本人也深知满洲祖先女真早已汉化了。[注]Elliot, The Manchu Way,pp. 9,276-277.
此外,美国黑人和清朝满人虽然均为少数民族,但黑人因其固有的种族特征, 他们的非裔身份(African identity)就是他们的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而满人和汉人之间没有种族差异,欧氏所说的满洲认同(Manchu identity),并不具有以种族为核心的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性质。换言之,“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种族身份认同,后者是民族身份认同。欧氏的错误就在于:他完全不懂我国少数民族对自身的认同是民族认同,与西方族裔概念中的族群认同根本不是一回事。费孝通先生早就说过:“ethnicity, nationality 都是英国的ideas, 不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没有这一套。”[注]费孝通:《文化随笔》,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还要指出:欧氏将满清入主中原比作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也是似是而非的。如果一定要比的话,倒有几分像英格兰吞并苏格兰。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
三、 汉化还是“涵化”?
欧氏坚称,满汉之间只有文化交融的“涵化”,不存在民族融合的汉化。他反对汉化,其理由是:
“汉化”……包含着一种大汉族主义的味道,因为好像它忽视汉人受满洲人影响的可能。……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就是有清一代的满洲人已经彻底变成了汉人……
“汉化”…… 容易造成某种误解,以为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现象,……其实,历史上所有的大帝国都有如此表现,无论罗马帝国,还是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沙俄帝国、乃至日本和美国,都或多或少地以为自己承担着一项神圣的“文明使命”,但最后的结果,却总是导致了不同程度上的文化交融,而不是单方面的“同化”。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注]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史》,《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第130-131页。
在分析上述论点之前,我们先要弄清什么是汉化,什么又是“涵化”。
汉化是指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同化与融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族和少数民族互相影响。汉族的影响是主要方面,但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截取该过程的任何一段,都会发现被汉化的少数民族在不同程度上仍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只是这种“持异”有着逐渐衰落的趋势。
被汉化的少数民族并不一定完全变成了汉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同情况:例1,五胡十六国时,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被彻底汉化,完全融入汉族。例2,元朝蒙古族人统治中国近百年,受到一定程度的汉化,然而退出中原时,整个民族仍然保持着不少基本的民族特点。例3,满人入关后,包括语言在内的基本民族特点逐步消失,与汉族已没有太大区别,但仍然保持满洲身份。
关于“涵化”(acculturation),美国社科研究委员会涵化组委的诠释较具权威性:涵化“就是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成的群体间发生持续直接接触,那样的现象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来的文化模式发生后续的变化”。西方学界通常认为“涵化”和“同化”的含义高度重叠,这两个概念往往被不加区别地用来表达同一个意思。只是社会学家多爱用“同化”,人类学家则喜欢用“涵化”。[注]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pp. 61-62.
厘清了汉化和涵化的认识之后,让我们回到欧氏前面的论点。
对第一段引言我们要指出的是:第一,采用汉化概念是因为它客观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以汉族影响为主、少数民族影响为辅的民族融合过程,与大汉族主义没有关系。第二,欧氏的“涵化”似乎要强调民族平等,但其缺陷是无法客观反映满汉间相互影响有主有次的实际情况。即便在美国,以盎格鲁-撒克逊为核心的白人文化对各少数民族的影响是主要的,少数民族文化对白人的影响是次要的。第三,没有谁会认为汉化就是满人已经彻底变成了汉人,因为满人作为一个民族至今仍然存在。
对第二段引言我们要指出的是:欧氏说西方殖民者征服异族时发生的只是文化交融(涵化),中国也不能例外。但是,他又忽视了其中关键的区别:西方殖民者征服的多是有色人种民族。如英国人统治印度,种族区别永远横亘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英国人整体上仍然生活在本国,并不与殖民地人民杂居,所以他们和被征服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表现为涵化。再如美国,黑人或其他少数民族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地接受了白人文化,即被涵化了,他们和白人之间的种族界线,不会因涵化而消失。中国则不然,各民族间没有种族区别。他们之间存在的主要是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即使通过涵化也会逐渐消失。更何况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融合(包括血缘融合)是全方位的,远远超出了涵化的范畴。
实际上,美国社会也并非像欧氏说的那样,似乎只有涵化,没有同化。美国二战前一直在推行被称之为“熔炉”(Melting Pot)的同化政策,其目的就是要非英语人群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从而失去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美国化在同种族的不同民族间进行得比较顺利。以白人各民族为例,1782年出版的《美国农民书信》这样回答“谁是美国人?”的问题:美国人“就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兰西人、荷兰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的混合”[注]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pp. 86-87,100,116,129.。所以在美国,同化也是普遍并存的。这恰恰证明:同化——民族融合——是同种族的各民族在共同生活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现象。
欧氏对汉化的批评,无论是“大汉族主义的味道”,还是说人们容易对汉化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都不是汉化概念本身的错。他将西方“政治正确”的潜规则用来评判汉化,完全不合时宜。我们认为,汉化包括涵化。不同的是:欧氏将汉化与涵化割裂并对立起来,他的涵化论仅仅承认文化融合,否认民族融合。而我们的汉化论不仅承认文化融合,而且承认民族融合,尽管不去规定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最终的结果。欧氏的涵化可以用来说明美国不同种族群体间的彼此影响,但无法全面解释中国同种族为基础的民族间相互融合。
此外,史学界还有一种看法,主张用“华化”取代汉化。[注]杨念群:《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第144页。汉化的英译也可以理解为“华化”(sinicization),英文的解释是:To make Chinese in character or to change or modify by Chinese influence(使之具有中国人特质或被中国的影响所改变)。然而两者不同的是:汉化主要指中华民族内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同化过程,无论其程度和结果如何,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华化在英文中有另一层含义:即中国人对非中国人的同化和影响。如果用它来取代汉化,就意味着少数民族在同化过程完成之前不是中华民族的成员或不是中国人。有些西方学者往往以此来曲解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把汉人完全等同于中国人,把非汉少数民族 (non-Han minorities) 等同于非中国人 (non-Chinese); 进而推论少数民族王朝不是中国王朝,少数民族地区自古就不是中国领土,严重扭曲我国国家和民族历史。欧氏就认为:辽金元统治是外国人 (alien people) 的统治,直到明朝中国才成为中国人的。满洲不是中国人,清朝统治是“非中国的”(un-Chinese)。[注]Elliot, The Manchu Way,pp. 5,22, 356,361.因此,是否使用“华化”,应当特别慎重。
四、何为 “满洲之路”?
欧氏将满洲分为 “文化群体” (cultural group) 和 “族裔群体” (ethnic group) 两个方面。他承认满汉间的文化融合,但仍坚持说:“满汉之间的文化距离逐步缩小,但满汉间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ies)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保持甚至强化。”[注]Elliot, The Manchu Way, pp. 17-18.欧氏认为,满洲之所以是满洲,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精于骑射、满语能力和尚俭精神。这些特点构成了满人区别于汉人的族群边界,而对这些风尚的实践就形成了 “满洲之路”。[注]Elliot, The Manchu Way,pp. xviii,8.
下面,我们就根据欧氏本人的论述,分析一下这条“满洲之路”。
据欧氏考察:第一,18世纪下半叶,满洲几乎不会骑射了。除了负责皇家狩猎的八旗兵外,满洲总体上已失去了精于骑射的民族特征。在这方面走上了皇太极担心的汉人之路。[注]Elliot, The Manchu Way,pp. 277-278,282.
第二,康雍时起,奢靡之风渐盛。在满洲聚集的京师,情况尤甚。[注]Elliot, The Manchu Way,pp. 284-290.随着入关日久,满洲尚俭的民族特点已丧失殆尽。
第三,满语能力的丧失。尽管清廷极力保持满文在官场上的使用,但无法阻挡使用汉语的潮流。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已经没有多少满人能流利地说满语了。不过欧氏又说,满人讲的是带有满语词汇和口音的汉语—北京方言。这是满人保持与汉人区别的方式。[注]Elliot, The Manchu Way,pp. 290-304.但谁都知道,无论满人的北京方言有多少满语词汇和口音,毕竟是汉语,恰恰体现了汉化中的“化”。
欧氏的考察基本符合史实,但他的论述却有问题。他将满洲分别看作“文化群体”和“族裔群体”,又将满洲“族裔”特征的消失,说成是“涵化”,即“文化群体”方面的融合。既然涵化可以使满洲“族裔”特点统统消失,而这些特点又是构成满汉族群边界的要素;那么,没有了区别彼此的族裔特点,如何能使满汉间“族群边界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保持甚至强化”?
尽管满汉民族差异在逐渐消失,欧氏又找到了一条满汉之间永久的族群界线。他认为八旗制度的改革保证了满人的地位和特权,使得满洲认同得以存续,形成了一条区别满汉的鸿沟。他将此称做“新满洲之路”。[注]Elliot, The Manchu Way,pp. 275-276,344.
据他考察,由于庞大的军事开支,八旗内部人口增长,腐败奢靡之风日盛,八旗制度出现了财政和制度危机。雍乾时期,清廷让许多“二等旗人”即八旗汉军出旗,减轻了负担,“挽救了八旗制度和满洲族群认同,因为留下来的旗人按标准是不折不扣的‘满洲人’”。[注]Elliot, The Manchu Way,pp. 305-306.
欧氏这条“新满洲之路”有诸多可商榷之处。
第一,八旗改革虽然保住了满洲的地位和特权,却没能恢复满洲的民族特点——骑射、满语和尚俭。于是,欧氏用八旗制度保障的满洲地位和特权来充当满人新的“族群”特点,构成新的满洲认同。[注]Elliot, The Manchu Way,pp. 275-276,344.西方族群概念中的文化因素虽然复杂,但包括的是族群本身具有的特点,如语言、宗教、来源地等等。族群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族群因自身特点而处于不当的社会地位或享有不当的社会权利。换言之,族群特点和社会因素(制度、地位、特权等)恰恰是必须分开的。将满洲的制度和特权作为族群特点塞进族裔概念,的确十分罕见。
第二,欧氏说八旗改革后留下来的旗人成为不折不扣的满人,将旗人和满人混为一谈,将“旗籍”等同于“满洲身份”。他无法自圆其说的是:其一,如果留在旗内的蒙古人、汉人都成了满洲,那么认为民族间只有涵化没有同化的他,就需要回答:旗内这些蒙古人和汉人如何仅仅通过涵化而不是同化就变成了满洲?其二,欧氏以旗籍来做满洲身份的基础。但清代有些旗人因犯罪刺字,逃亡不归,打工糊口,或自愿出旗,被销除旗档。其中也有满人。[注]许会娟:《简论清代旗人出旗》,《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9期。那么,失去旗籍的满人是否仍然拥有满洲身份?如果失去了旗籍就不再是满人,他们的民族身份为何?
第三,他将满洲身份认同的延续完全归功于八旗制度,也值得商榷。历史证明:清朝覆灭,八旗制度衰亡,但满人作为一个民族依然存在,其民族身份认同依然存在。所以,满洲认同的延续并未依托八旗制度。综观今天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在本民族历史上并未实行过八旗那样的制度,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身份。可见,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保持并不依赖八旗那样的制度。
五、扭曲的 “内亚”视角
《满洲之路》的主题之一,就是强调“内亚”和“非汉”因素,力图证明“清帝国的确是个满洲帝国而不是中华帝国”。欧氏的根据是:满洲是来自内亚的少数民族。清朝采取中亚民族的统治模式——“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 代表蒙回藏等内亚非汉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注]Elliot, The Manchu Way, pp. 4-5,355.清帝国包括了大部份内亚地区——满洲、蒙古、回疆、西藏。这一地区未曾长期被汉族王朝统治过,也未曾接受过任何儒家思想文化。清帝国是“中原”(即中国)和“塞外”(即满蒙疆藏地区)的联合体。其中,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部分, 而且不是核心部分。[注]定宜庄、欧立德:《21 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历史学评论》,第117-118页。这就是欧氏和其他新清史学者所标榜的“内亚”视角。
“内亚”视角听上去很新颖,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漏洞。
首先,欧氏认为满蒙回藏等内亚地区未曾长期被汉族王朝统治过,也未曾接受过任何儒家思想文化。他引用中国史例,似乎只举宋明之后,不涉汉唐以前。盛唐时期,疆域东起朝鲜半岛,南抵越南顺化一带,西达中亚咸海以及呼罗珊地区,北至贝加尔湖至叶尼塞河下流一带。内亚大部,尽收其中。元代蒙古族统治者视汉人、南人为一类,将宋金疆域中的女真、契丹和高丽均称为汉人。[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女真归汉人类,并非“非汉”类。这说明将北方各少数民族看作一个“非汉”整体,并无历史依据。欧氏自己也承认,皇太极常常担心满洲会像他们的祖先女真人那样被彻底汉化。[注]Elliot,The Manchu Way,pp.9,276-277.也就是说,他知道宋元时期的金国等内亚地区已经彻底汉化了。
其次,欧氏强调满洲是内亚民族,采取中亚民族的统治模式。由于满洲的“内亚”和“非汉”因素,清帝国的中心是内亚而不是中原。然而,清朝“统治模式”和欧氏本人的考证都恰恰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例如,清设理藩院管理蒙疆回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这个“藩”字恰恰是清廷在满洲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划的一条界线,明确了正统与非正统之间的关系。清朝和汉人王朝一样视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为“藩”,将自己与非汉少数民族区隔开来,以示正统。可见,作为统治者,清廷站在与汉人王朝相同的立场上,与“非汉”因素划清界线。
理藩院的“藩”字还明确了宗主与藩属、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蒙古贵族和西藏上层与清廷保持着朝贡关系。这种藩属与宗主的关系说明,他们虽然是清朝国内的同盟者,但还不像汉人那样已是体制内的僚属。清朝对内亚的管理并非是在皇帝和蒙藏贵族间直接进行,而是通过理藩院这样的国家机构。这就说明,内亚和中原是清朝国家机器统一管理下的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两个地区简单的联合。理藩院对蒙疆回藏地区的管理是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理藩院的“藩”字同时还确定了中原和内亚之间中心和边陲的地位,反映出清廷是站在中原立场上看内亚地区的,即中原是核心,蒙疆回藏地区是边护藩屏(新疆的“疆”字也有此意)。这一点可从欧氏对理藩院的称谓上得到反证。他将理藩院写成“the Court of Colonial Dependencies” (殖民属地院),其他新清史学者也是这样。[注]Elliot, The Manchu Way,p. 40;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p. 20; Rhoads, Manchus & Han,p. 20.将清朝对蒙疆回藏地区的统治视为殖民统治,当然是错误的。但他们自相矛盾的是,如果说内亚地区是清朝的殖民地,世界上哪有殖民地是国家中心的呢?
再次,清朝入关,迁都北京。其后近三百年,北京一直是清朝的统治中心。据欧氏统计,八旗大部份军队, 满洲大部份人口移驻以北京为中心的地区。西安、杭州这样的大城市也成了满人集中的地方。满人的生活方式已从农村生活方式变为几乎与汉人一样的城市生活方式。[注]Elliot, The Manchu Way,pp. 119-121, 131-132.
据欧氏考察,乾隆帝有旨:“北京是所有满人的归属之地。”[注]Elliot, The Manchu Way,p. 262.所以,清初各省任职的满洲官员退休都必须回北京。如过世,尸体也要运回北京安葬。后来由于转运困难等原因,清廷准许就地安葬,他们的家属也可以留在当地。于是,满洲八旗所在的各省就成了他们北京以外的“家外之家”,而“满洲只是理论上的‘家’”[注]Elliot, The Manchu Way,pp. 105,150,258-259,266-267.。从18世纪中到19世纪初,各地满洲内城和汉人外城的界限开始被打破,逐渐实现满汉杂居, 满人汉人成了朝夕相处的邻居。[注]Elliot, The Manchu Way,pp.116,225.在北京,满人汉人更是难以分辨。[注]Elliot, The Manchu Way,pp. 208.
早在顺治五年(1648),清廷准许满汉通婚。其后虽又有禁令,但终清之世,满汉两族从统治者到民间的双向通婚从未间断。满汉人民真正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戚。[注]滕绍箴:《清代的满汉通婚及有关政策》,《民族研究》 ,1991年第1期。长期的共同生活必然产生亲情和乡情,满洲认同也必然随之变化。[注]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清朝的国家认同》,第147-168页。可见,满洲入关后将中原而不是内亚当作他们的家乡,他们与各地汉人之间结成了亲属和乡亲的关系。这时的满洲已经不再是欧氏笔下的内亚民族,而是扎根于内地的中原民族了。犹如欧洲人移居到北美,生活了两三代(更不要说两三百年)之后,便完全成为北美人。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别人,都不会再说他们是欧洲人。欧氏执意将定居在中原近三百年的满洲说成是内亚民族,用“内亚”中心取代中原中心,目的就是要证明满洲是非中国人,将清朝非中国化。
六、欧氏的 “中国”观
欧氏一直在追问清朝的“‘中国’和‘中国人’究竟指的是什么”。据他观察,满洲不论用汉语还是满语,“有时候”将他们管辖的土地称为“中国”。这种“有时候”在1644-1911年的《大清历朝实录》中有1088处,其中三分之一指内地,三分之二指整个国土。所以他觉得这种用法是“模糊不清”的,“可能会让生活在单一民族国家的现代人混淆,在单一民族国家中,这些定义应该是一清二楚的”。他要中国学者对中国这样的概念 “谨慎使用”,“抱着怀疑的态度去做出判断”。[注]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第10、14-15页。
如果认为“中国”这个概念是模糊不清的话,世界上恐怕没有多少国家的概念是清楚的。仍以美国为例:美利坚合众国常被称为“美国”(America)。然而,“America”有时候也指美洲大陆,不仅包括美国,而且包括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南美各国。据网络辞典提供的信息,“America”在实际使用中,大约85% 指美国,15% 指美洲。[注]http://dict.cn/America这与欧氏所说《大清历朝实录》中“中国”出现的情况十分相似。但无论是单一民族还是多民族国家的现代人,只要有粗浅的文化知识,谁都不会认为“America”是模糊不清的,更不会将它当作学术问题来与新清史学者探讨,说“美国”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让美国学者在书写美国史的时候,要对“美国”概念抱着怀疑态度,谨慎使用。
尽管如此,欧氏仍然认为:
不仅仅是清朝,而是每个王朝都有它的独特性,也都是独立的政权,所以每个王朝都存在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中国”却与每个具体的朝代都不一样,它是一种超越历史的、比较笼统而容易改变的信念和概念……
“中国”的概念只是一种设想,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中国”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不会有任何纯粹的中国或纯粹的“中国性”。[注]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第135页。
寻求 “真正的中国”是徒劳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注]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第14页。
很明显,欧氏这种虚化中国的手法不过是照搬了战国时期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诡辩,将“中国”概念中的一般(中国)与个别(王朝)两方面割裂开来,利用概念中抽象与具体、内涵与外延之间的差异对概念本身提出质疑。 他认为自己发现了清史中的重大问题,“颠覆了中国百姓从小学到的,从来都以为是最自然不过的常识”。[注]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第142-143页。作为中国史专家,如果他读过两千多年前“白马非马”的典故,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尽管公孙龙试图利用诡辩术证明白马非马,但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他仍然无法“颠覆”人类的正常思维:即不仅白马是马,无论什么颜色的马都是马。欧氏将诡辩术引入历史研究,或许是“新清史”研究方法上的又一创“新”。
中国不是凭空的“设想”。它是一个有五千年之久的历史存在,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绵延至今的伟大文明。它的确在不断发展变化,但我们与欧氏不同:欧氏认为这种变化使“中国”变得“比较笼统而容易改变”,因而否定有“真正的中国”的存在。我们则将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变化相互联系,即每个汉族或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都是中国的传承;因而我们头脑里的中国随着时代的延续变得更加坚实、更加丰富。
还须指出的是:中国人对自己祖国(中国)和自己民族(中华民族)的认同是自我认同。欧氏应当清楚,自我认同是最基本的民主人权,谁都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更不应当假借学术探讨来质疑这种认同。欧氏认为自己可以挑战和颠覆“中国认同”,并要求中国人按美国学者的理解来改变自己对祖国和民族的认同,[注]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第142-143。这不仅超出了学术理论范畴,而且突破了民主人权底线。
在少数民族是不是中国人,少数民族王朝是不是中国王朝的问题上,新清史学者和中国多数学者之间永远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尽管中国学者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做过详细阐述,[注]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清朝的国家认同》,第245-266页。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清朝的国家认同》,第267-292页。黄兴涛:《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第16-34页。汪荣祖:《以公心评新清史》,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23-56页。但新清史学者往往充耳不闻。他们囿于单一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概念,将汉族——中国对应,认为只有汉族王朝统治的国家才是中国,少数民族统治的就不是中国。他们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之间的不同,不仅视而不见,而且常常削足适履,将丰富悠久的中国历史硬套入他们僵化的概念之中。 这归根结底是因为价值观不同,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可以解决的。
中国人的价值观以群体为中心,个体或小群体的属性和认同,由大群体的属性和认同决定。在民族认同上,我们坚持大群体——中华民族——的属性和认同。西方人则不然,他们的价值观以个体为中心,个体或小群体的属性和认同,先于大群体的属性和认同。所以他们强调个体和小群体——“族群”——的属性和认同。相应地,中国学者判断少数民族是否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不仅看他们的起源,更重视他们的归属,就如看一条条支流是否汇入同一条江河。汇入同一条江河的支流,尽管最初都分别有自己的发源地,以后也保持着自己的名称,但它们最根本的属性归于那条融入的江河。新清史学者则不然,他们看待中国少数民族,着眼于他们的起源,并习惯于将起源和归属分割开来,只注重支流的源头和汇入江河之前的部分,并以此来确定支流的属性。即便支流融入了江河,他们也会寻找这一支流的水与江河中其它水之间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他们却认为少数民族不是中国人的症结所在。
新清史学者对满汉关系的看法,或与他们的族群形成史有关。如果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其形成像一条包容许多支流的江河,浑然一体;而美利坚民族历史短浅,其形成就像一杯五彩的鸡尾酒,色泽分明。新清史学者头脑中“鸡尾酒”式的框框,可能很难理解浩瀚江河式的民族形成。正如庄子《逍遥游》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七、余论
和其它新清史著作一样,《满洲之路》的字里行间暗含着几重弦外之音:第一,以捍卫者的口气,强调“族群认同”,反对汉化;似乎汉化就是要剥夺满族同胞的民族认同。第二,利用强调少数民族对自身的认同,将满汉差异等同于西方社会的种族矛盾,凸显民族对立,否定民族融合;削弱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总体认同。第三,将清朝与世界上其它殖民帝国做简单类比,希望证明清朝也是个殖民帝国,[注]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清朝的国家认同》,第390页。蒙疆回藏地区就是殖民地;而现代中国建立在清朝版图之上,也就是部分地建立在殖民地之上。这种“研究成果”可能被用来质疑中国领土的合法性,甚至成为藏独疆独的理论依据。我们在客观理性地讨论新清史时,不应忽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