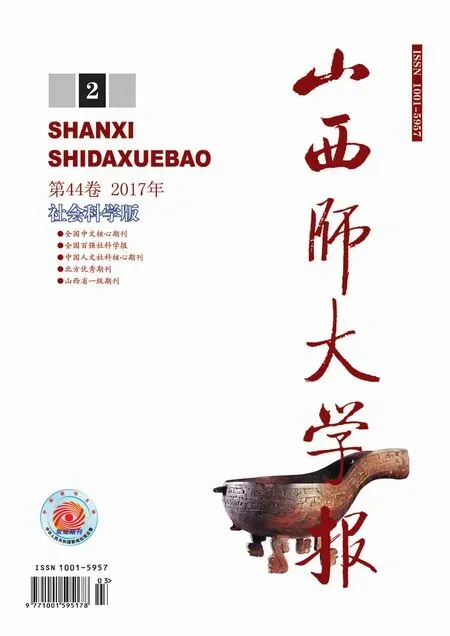百年来晋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郭 永 琴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太原 030006)
晋国是我国先秦时期一个重要的地方封国,从立国到灭亡,前后经历六百余年的时间。晋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元侯级诸侯国。当时,它是周人在汾河谷地的重要战略支点。西周末年,随着晋文侯勤王,晋国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了春秋时期,自晋文公始,晋国不仅成为中原霸主,霸业持续百年之久,而且也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诸侯国之一。
晋国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一朵奇葩。它最早打破西周宗法制的束缚,实施打击公族,任用军功的政治策略,从而促成了独特的六卿执政的政治格局;晋国多次制定法律并坚持贯彻法的思想,使之深入人心;晋国最早采取新的行政区划——县,并形成完整的县制,开创了中央集权的先河;晋国军事制度发达,并深入到职官设置上,形成了军政合一的职官体制;晋国还采取了博大包容的人才政策,“楚材晋用”不仅成为一时美谈,同时也促成了晋国的百年霸业;晋国制造的商品曾一度控制了春秋时期的中原市场;它创造的城邑建造模式和多种先进制度,制造的晋系青铜器,以及长期秉承的重贤任能,礼法并重的思想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独立的先秦史研究是在20世纪开始的。而独立的晋国史的研究则更晚,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晋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
20世纪初到1978年以前是晋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恰是中国史学界经历大变革的时期。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的传入和新材料的发现,中国学人将之与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相结合,采用新材料与旧文献相互发明的二重证据法,研究上古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在新思想的冲击下,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崛起,对旧的古史系统以及记载这些旧史的古文献提出了怀疑。他们提出了所谓“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这一古史观对当时中国的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传说时代及其人物的认识上。这一时期,学者们绝大多数都接受了进化史观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西周至战国历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相比之下,晋国史的研究成果则寥若晨星,仅有容庚的《晋侯平戎盘辨伪》、杨树达的《赵孟疥壶跋》和王玉哲的《晋文公重耳考》,其研究内容尚徘徊在传统的研究范围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晋国史研究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开始有学者专门研究晋国的问题。如常正光的《春秋时期宗法制度在晋国的开始解体与晋国称霸的关系》、应永深的《论春秋时代鲁国和晋国的社会特点兼及儒家和法家产生的历史背景》、张以仁的《晋文公年寿辨误》。
考古发现也给晋国史研究带来了契机。建国后,考古工作备受重视,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山西省考古所在山西境内开展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工作。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牛村古城附近发现并发掘了侯马盟书。盟书及其反映的历次盟誓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刚一发现便震惊了学界,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郭沫若在《文物》1966年第2期上率先发表《侯马盟书试探》,随后盟书发掘者张颔也发表《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此外还有陈梦家的《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将出土盟书与周代的盟誓制度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学者对侯马盟书研究的热情也未减弱。如陶正刚和王克林的《侯马东周盟誓遗址》、唐兰的《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朱德熙和裘锡圭的《关于侯马盟书的几点补释》、李裕民的《我对侯马盟书的看法》等。1975年,《文物》杂志在第五期上专门刊出一组四篇关于侯马盟书的研究文章。
总体来看,1978年之前受当时史学研究风气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晋国史研究虽然已经起步,但是成果还非常有限。
二、晋国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1978年到2000年是晋国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从事晋国史研究的学者大增,山西境内的高校和相关刊物也积极搭建平台促进晋国史研究的展开。同时伴随新的考古发现,晋国史研究在时空上也得到了拓展,开始从山西学者研究的重点发展为全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迎来了新生。在历史研究走向正轨的同时,大量考古发现的资料也为研究地方史提供了新机遇,在春秋时期与楚国长期争霸的晋国历史的研究也被山西学者日益重视起来。1979年,罗元贞先生率先在《山西大学学报》上发表《晋国的爰田与州兵》。1982年,张颔发文呼吁:“晋国地望在山西,作为山西省的史学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于晋国史和晋国文化的研究有着不可推却的责任,这不仅是山西社会科学的一件大事,就是对于全国史学界来说,也是不可漠视的重要课题。”[2]同时《晋阳学刊》开辟“晋国史研究”专栏,为晋国史研究搭建平台。山西学者也纷纷在《山西师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晋国史研究的文章。晋国史研究逐步引起山西史学界和全国学术界的重视,进而促进了我国国别史、区域文化研究的形成。与此同时,位于史籍记载的陶唐故地——临汾的山西师范大学率先建立了晋国史研究室,该研究室的常金仓和李孟存通力合作在1988年出版了《晋国史纲要》一书,该书结合古文献和考古资料,首次将晋国的历史展现在人们面前。全书共分十六章,二十余万字。该书在注重传统政治史的同时,也开始重视晋国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对晋国的经济发展分门别类,并对戎狄关系、思想文化等都设列了专章详细论述,颇有新意。尽管由于时间和资料的限制,本书在许多问题上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但《晋国史纲要》仍然是晋国史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成为此后晋国史研究者的必读著作。1999年,李孟存、李尚师又在《晋国史纲要》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增补,出版《晋国史》,第一次完整地展现了晋国的历史。
由于春秋时期是晋国发展的鼎盛时期,记载这一时期晋国历史的文献非常丰富,加之晋都新田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的佐证,为这一时期的晋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晋国史研究最初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春秋时期。学者们围绕这一时期晋国的各项制度、人物、史事、对外关系、思想特征、世族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注的焦点有晋“作爰田”、晋文公史事和思想、晋国的县制等方面。晋“作爰田”是学者们争论比较大的课题。1982年,林鹏发表《晋作爰田考略》,引起了学术界对“作爰田”的大讨论。不久,李孟存、常金仓随即发表《对〈晋作爰田考略〉的异议》。之后,双方以《晋阳学刊》为阵地,展开了交锋。林鹏发表《再论晋作爰田——答李孟存、常金仓二同志》、李孟存和常金仓回应以《爰田与井田——与林鹏同志再商榷》。此后,这一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文章有罗元贞的《论晋国的爰田与州兵》、李民立的《晋“作爰田”析兼及秦“制辕田”》、邹昌林《“作爰田”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兴起》、周苏平的《论春秋晋国土地关系的变动》、周自强的《晋国“作爰田”的内容和性质》、袁林的《“爰田(辕田)”新解》。
西周时期的晋国早期历史,由于史籍记载缺失,且无系统的考古资料佐证,因此研究相对有限。直到20世纪90年代,天马—曲村遗址发掘报告公布,西周时期的晋国史研究才有了突破。在这一遗址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晋侯墓地,从 1992到2000 年共发掘了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除车马坑和个别陪葬墓与祭祀坑外,基本上已揭露完毕。晋侯墓葬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玉器、漆器、原始瓷器等,许多青铜器的铭文还载有晋侯名号。天马—曲村晋国遗址的发现作为我国20世纪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和成果之一,其材料一经公布便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也掀起了晋国史研究的热潮。对晋侯墓地及其出土器物的研究成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晋国史研究的主流。2000年之前,学者们对晋侯墓地年代学、出土器物及其制度、墓地制度、晋国迁都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代表性著论有:邹衡的《论早期晋都》《晋始封地考略》,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考古队的《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及相关问题》,李学勤的《晋侯邦父与杨姞》《〈史记·晋世家〉与新出金文》《试论楚公逆编钟》《晋侯苏编钟的时、地、人》,王人聪的《杨姞壶铭释读与北赵 63 号墓主问题》、李伯谦的《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张长寿的《关于晋侯墓地的几个问题》等。
单件器物中晋侯稣钟、楚公逆钟、晋侯夨方鼎和杨姞壶是研究的重点。而晋侯稣钟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对其讨论的文章之多堪为诸器之首。晋侯稣钟完整地记载了周晚期某王三十三年,晋侯稣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除了这场史书无载的重要战争外,铭文还记录了“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方死霸”五个记时词语,对于研究西周历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全篇铭文用利器刻出,笔画流畅整严,为我们研究西周晚期文字提供了新的材料。鉴于晋侯稣钟的这些重要价值,从1996年开始,它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1997 年《文物》杂志专门组织多位著名专家对晋侯稣钟进行笔谈。
晋国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还带动了晋文化以及三晋文化研究的展开。1988年,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旨在挖掘和研究山西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其研究重点就是晋国和韩赵魏三晋历史文化。1997年,李元庆集多年研究成果而成的《三晋古文化源流》出版。他通过对山西地区历史与文化变迁的宏观研究,提出三晋古文化研究的“三个历史层面”和“三大理论层次”,并呼吁构建“晋学”研究。1998年,三晋文化研讨会召开,会议“围绕西周到战国,主要是春秋和战国时代的晋国文化和韩、赵、魏三晋文化这个中心议题展开了学术探讨”[3]2。在此次研讨会上,多位学者积极响应李元庆提出的构建“晋学”研究的建议。如张有智的《二十一世纪呼唤晋学——读〈三晋古文化源流〉》、高增德的《时代呼唤“晋学”或“晋文化学”——兼评〈三晋古文化源流〉》。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禁锢的解除和各地学术交流的加强,晋国史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而且它的发展一直是和山西区域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又是与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密切相关的。
三、晋国史研究的繁荣阶段
21世纪以来晋国史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旧有研究领域在继续深化的同时有所突破。在人物方面,由于地方文化研究的兴起和繁荣,促进了卿大夫一级人物的研究,使其和国君一样成为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对赵氏人物的研究最为集中,成果最多。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晁福林的《试论赵简子卒年与相关历史问题》、张润泽和孙继民的《赵简子平都故城考》、董林亭的《论赵盾》、白国红的《“赵氏孤儿”史实辨析》等。
与之相关的是世族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家族研究成为热点。晋国的公族和主要卿大夫家族基本都已被研究。其中卿大夫家族成为高校硕士学位论文的集中选题。截止2014年,相关硕士学位论文已经达到10篇之多,所涉家族包括韩氏、智氏、羊舌氏、魏氏、荀氏、郤氏、栾氏、中行氏、范氏等。此外出现了一批相关的学术论著,如聂淑华的《晋国的卿族政治》、白国红的《世族的崛起与春秋政治格局的演变——以晋国赵氏为个案》、曹丽芳的《晋国中行氏兴灭及世系考》和《晋国知氏兴灭及世系考》、张海瀛的《赵简子家族与早期晋阳文化》、杨秋梅的《春秋时期的晋国公族及其特点》、白国红的专著《春秋晋国赵氏研究》、王准的博士论文《春秋时期晋楚家族比较研究》、李沁芳的博士学位论文《晋国六卿研究》。其中《春秋晋国赵氏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该书上溯赵氏祖源,详细介绍赵氏家族由弱而至强胜,由中衰至复起,最终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并对多个复杂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为家族研究的一个范例。比较研究开始运用到家族研究当中,如王准的《春秋时期晋楚家族比较研究》。他引入文化比较的方法,将春秋时期晋楚两国的家族划分为公族、公室与卿大夫家族三个部分,解析三种家族形态与内部结构,进而分析其地位变化,总结其发展规律,还探讨了这些家族的地域特点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历史影响。
制度方面,县制、田制、军制、法制仍然是研究的重点。与世族政治相联系的家臣制度开始受到关注,如杨小召的《春秋中后期晋国卿大夫家臣身份的双重性》、谢乃和的《春秋时期晋国家臣制考述》等。
晋国有着悠久的史官文化,但此前却无人问津,这一时期开始有学者涉足这一问题。如,胡恤琳和韩晓霞的《从董氏家族看晋国史官的优良传统》、崔凡芝的《晋国史官及其职责》、畅海桦的《试探晋国史官地位嬗变之因》、樊酉佑的硕士论文《晋国史官研究》等。
历史地理方面,马保春的《晋国历史地理研究》和《晋国地名考》二书具有代表性。两书相辅相成,构成了晋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完整体系。前书在总结前人对晋国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晋国疆域内的地理单元进行了划分,并由此对都城变迁、疆域发展、县制、卿大夫领地、交通和军事地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后书则按历史聚落、乡邑、城邑地名,历史国族地名,历史政区地名,历史区域地名,山川地貌地名,关隘交通地名,宫室、田亩地名进行划分,一一考证,共收集了450个左右的晋国及与晋有关的地名。
在考古方面,伴随着晋侯墓地考古发掘简报全部公布,人们对其研究进入高潮。首先是上海博物馆于2002年4月出版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一书,并同山西省文物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织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展”,同年上海博物馆又出版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并召开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共有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76位正式代表参加,并有许多学者列席和旁听了会议。[4]学者们主要围绕晋侯墓地的性质、墓葬的排序和年代、墓主的身份、埋葬制度、器用制度、青铜器铭文和装饰艺术、随葬品反映的女性地位等议题展开讨论。此次研讨会是学术界对晋侯墓地的一次集中讨论,极大地推动了晋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晋国史研究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为晋国史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次是对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报告公布的M114出土的叔夨方鼎的研究。由于叔夨方鼎可能与晋国的始封君叔虞有关,因此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文物》2001年第8期在公布发掘简报的同时,刊发了李伯谦的《叔夨方鼎铭文考释》。同年《文物》第10期上又发表了李学勤的《谈叔虞方鼎及其他》。《文物》2002年第5期还刊登了多位学者关于叔夨方鼎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笔谈。2002年上海博物馆召开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有8位学者就叔夨与唐叔虞、燮父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其后随着羊舌晋侯墓地的发现,对叔夨方鼎的讨论基本结束。
在叔夨方鼎之外,晋侯稣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对象,虽然没有出现20世纪90年代末那样的高热现象,但是由于其独特的价值,仍然留有许多研究的空间。21世纪以来,晋侯稣钟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铭文、所涉地理问题、年代和历法、形制等方面。
除了个别青铜器研究高热之外,晋国青铜器的系统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代表研究成果有:蔡鸿江的博士论文《晋系青铜器研究》、李夏廷有关流散美国的晋式青铜器系列文章和专著《晋国青铜器艺术》;《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汪涛的《两周之际的青铜器艺术——以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例》、李朝远的《晋侯青铜鼎探识》、周亚的《关于晋侯苏鼎件数的探讨》、杨晓能的《从北赵晋侯墓地M113出土铜卣谈商周青铜礼器外底的动物图像》;李晓峰的硕士论文《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赵瑞民和韩炳华合著的《晋系青铜器研究——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等。
晋侯墓地的墓主排序问题、出土器物与制度、墓葬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也在深入当中。此外还有一些系统性的专著问世,如宋玲平的《晋系墓葬制度研究》和刘绪的《晋文化》等。
第二,新材料的出现为晋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进入21世纪,与晋国史研究有关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最著名的有羊舌晋国墓地、横水倗国墓地、大河口霸国墓地等。其中羊舌晋国墓地是继曲沃北赵晋侯墓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其墓葬等级很高,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相关成果有吉琨璋等《曲沃羊舌晋侯墓地1号墓墓主初论》和《再论羊舌晋侯墓地》、马冰的《也谈曲沃羊舌M1和北赵晋侯墓地M 93的墓主》、田建文的《也谈曲沃羊舍墓地1号墓墓主》、王恩田的《西周制度与晋侯墓地复原——兼论曲沃羊舍墓地族属》、李建生的《曲沃羊舍墓地几个问题的思考》、孙庆伟的《祭祀还是盟誓: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祭祀坑性质新论》等。
倗国西周墓地和大河口霸国墓地经发掘已知皆为狄人墓地,所发现的随葬品等级很高。目前,对于这两个墓地的研究还在深入当中,其与晋国之间的关系涉及周代的政治架构、族群关系等,对晋国史研究来说也是很重大的课题。
新见传世青铜器和竹简的发现也为晋国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如新见公簋和清华简《系年》。《考古》在2007年第3期刊发了朱凤翰先生的《 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一文, 公簋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该簋是一件香港收藏家的私人藏品,簋腹内底部有铭文四行共22字。内容是讲 公为他的妻子姚作此簋,恰值周王命唐伯为侯于晋的时候,时间在周王廿八祀。这一铭文与晋国名晋的由来, 公与晋国的关系,燮父被封侯于晋的年代问题紧密相关。而这些问题恰是晋国史研究的关键问题。此文刊出后,立刻引起学术界对该簋的关注。相关研究有孙庆伟的《 公簋、晋侯尊与叔虞居“鄂”、燮父都“向”》、彭裕商的《觉公簋年代管见》、李伯谦的《 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尹松鹏的《 公簋铭文“唯王廿又八祀”与西周年表》、张俊成的《 公簋与商周 族及其称谓问题》、张卉的《 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问题刍议》等。
清华简是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经碳14测定,年代为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以楚国为主。清华简中的《系年》简共138支。整理后,全篇分为23章。《系年》记载了西周初年到战国前期的诸多史事,其中关于晋国史事的记载颇多。相关的研究文章主要有:胡凯和陈民镇的《从清华简〈系年〉看晋国的邦交——以晋楚、晋秦关系为中心》、程薇的《清华简〈系年〉与晋伐中山》、李学勤的《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晁福林的《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马卫东的《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考》、张少筠和代生的《清华简〈系年〉与晋灵公被立史事研究》。
第三,伴随着新材料的出现、科技的进步、跨学科理论的引入和认识的更新,人们对晋国史研究的范围已经突破政治史、经济史等领域,开始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对晋国史研究进行新的尝试,从而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如性别研究、音乐学研究、人口研究、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等多个方面。其中性别研究比较深入。20世纪80年代,女性研究兴起,极大地促进了性别研究的开展。晋国女性在春秋时期的耀眼表现和西周墓葬中男女差异都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因此在性别研究方面不仅涉及到了对当时人物的考辨、王室女性形象、女性对国君的影响,而且分析了晋国墓葬中的性别差异。相关研究成果有:陈芳妹的《晋侯墓地青铜器所见性别研究的新线索》、赵剑莉的《晋国夫人考》、张丹绮的《春秋时期晋国王室女性形象分析》、张浏森的《论七位女性对晋文公重耳的影响》、林永昌的《西周时期晋国墓葬所见性别差异初探》、耿超的《晋侯墓地的性别考察》等。
跨学科方法的引入也较为明显。如李亚峰的《晋国人口知多少?》采用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文献材料估算出晋文公和晋平公时期以及晋国后期中心地区最高人口总量,并对晋国人口增长做了总体上的定性和定量分析。音乐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晋国史的音乐学研究得以开展。如:任宏的《西周时期七代晋侯金石用乐的组合与编列》、索美超的硕士论文《晋国乐舞考略》、任宏的硕士论文《晋侯墓地出土乐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晋侯墓地青铜器铸造工艺在材料公布伊始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但是限于技术问题,许多问题无法解决。进入21世纪,新的科技手段被应用到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研究中,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相关研究文章有杨颖亮的《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显微结构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胡东波和吕淑贤的《应用X射线成像对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铸造工艺的研究》。
2014年,李尚师的《晋国通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既是国别史中的通史,又兼具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两种体例,还吸收了志书的一些特点”[5]的新型史学专著。该书是在他和李孟存教授合著的《晋国史》、《晋国人物评传》及其独著的《先秦三晋两个辉煌时期暨治国思想》三本专著基础上,立足文献史料,又结合考古材料而写成的。全书共分33章,另有10个附表,分别介绍了晋国上自国君,下至三教九流的人物;晋国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和特点;晋国社会阶级结构和各阶级、阶层状况及其变化;晋国的制度、对外关系和政策;晋国地理、地名和疆域的演变;晋国最高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及由此形成的晋国政治特征;晋国的治国思想及文化成就等。
四、晋国史研究之展望
毫无疑问,晋国史研究从通史研究的附属,逐渐成为国别史研究的重头,进而得到不断的深化,不仅使人们认识到了晋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先秦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百年来晋国史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将近四十年的蓬勃发展,晋国史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面对未来,晋国史研究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积极吸收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建国后成为历史学界的指导思想,在其指引下新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作为中国史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吸收新的理论成果,拓展研究的领域,形成新的历史认识。如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理论,将历史时间区分为三种:“长时段”,也叫自然时间或结构,主要指历史上长期不变或变化极其缓慢的现象;“中时段”,也叫社会时间或局势,主要指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节奏的现象;“短时段”,也叫个体时间或事件,主要指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布罗代尔认为三种时段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历史,这三种时段彼此关联,长时段起长期决定性的作用,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制约中时段及其演变,中时段只能对历史进程起直接的重要作用,而短时段不过是长时段在历史表层的一种反映。只有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突破传统的通过宏大叙事建构起来的以政治演变为主导的通史性研究范式,更加重视那些在晋国六百余年的时间中所出现的诸如物种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和地质变化等对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被忽略的现象。如,晋国在六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是一个长期不变的因素和一种长期起决定性作用的结构,但是在六百余年的时间里,气候因素却在发生着变化,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水文的变化和动植物的更替,由之还会造成气候灾害的消长,这些都会影响到晋国的政治、外交、战争、社会、日常生活的发展。它又提醒我们,每个区域社会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互为发展条件,其间之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变化都是推动区域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晋国的发展不仅受到西周王朝的影响,而且在其独特的区域环境中与周边部族和国家的互动也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动力。
其次,积极引进多学科研究的方法,拓宽研究视角,积极开展比较研究。多学科研究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趋势。在晋国史研究方面,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研究相结合便是很好的范例。但是要想继续深入研究,这些就显得很不够。不过现在的已有成果显示,在青铜器研究上,已经出现采用先进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青铜器的工艺进行科学解释的成果。也有学者在人口研究方面,用人口计量学的方法,利用数理模式,进行科学统计和计算,得出相对精准的结果。但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使用在晋国史研究方面还很有限,急需加强。如,应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加强对晋国政治结构的研究;应用中心地理论、共同体理论和方法,重新认识晋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等。而现在科技的发展和其他学科研究的进步也为我们尝试应用多学科成果提供了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吸收也必将为晋国史研究的深入注入新的活力。
另外,比较研究还相当薄弱。有学者在评介《春秋晋国赵氏研究》时指出:“春秋时期家族兴起是一种普遍现象,‘政出家门’是各国皆有的问题,加强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赵氏家族的历史和当时社会的变化,比如齐国陈氏是可以与赵氏家族进行比较研究的绝佳资料。”[6]除此之外,晋国和楚国作为春秋时期长期的对手,其发展道路、霸业模式、社会特点、集体心理等各个方面都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其实,晋国和其他诸侯国之间也有很多比较研究的课题值得开展,在晋国内部各家族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有开展的必要。
第三,宏观和微观研究都有待进一步加强。近百年来的晋国史研究比较重视微观领域,对人物、事件、组织或制度等已做了较多的考证、叙述,其面貌已相对清晰。但是还有一些领域的研究没有开展,如聚落研究和日常生活研究。众所周知,聚落是文明的根系,它的存在推动了文明的互动,最终促成了文明的统一。聚落又分为城市聚落和乡村聚落,进行聚落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晋国基层的发展状况。与之相关的还有日常生活的研究。历史研究本质上是对人的研究,那么对人的日常生活的研究就是其内在之义。可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着力,现在考古学资料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已经为我们展开这项研究提供了可能,只要我们把眼光向下,这些研究不仅会为晋国史研究增添新的内容,而且必将成为晋国史研究新的热点。
宏观研究方面一直是晋国史研究的短板。近些年也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只有王万辉的《重新认识晋国在中国古代史的地位》、李尚师的《晋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几篇而已。晋国在先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不仅是周代重要的封国,而且是春秋时期的霸主。其霸主的地位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盟主地位,而且反映在政治体制先进、经济强盛、文化繁荣上,尤其是晋国尚武、尚法、尚能的发展道路以及具有变革精神、开放精神和包容精神的思想理念,不仅对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有学者提出,“从方国到帝国,晋是方国的终结者,又是帝国的前提和前夜。”[7]因此,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度去研究晋国史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此外,对晋国政治体制结构的研究也应该引起注意,封国政治体制研究是周代政治体制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春秋之后,晋国政治体制结构的变化又对此后中国中央集权体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晋国政治体制的结构及其变迁是今后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晋国史研究也应该走古为今用的道路,为现实服务也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晋国史在这一方面有着独到的优势。一个身居山林,拜戎不暇,立国环境如此险恶的地方封国能够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局面中不仅得到了成长,而且成为诸侯的霸主,其经验教训值得进行全面总结。尤其是晋国的变革路径、制度革新、经济政策、民族观和政策,以及价值理念、人才观等,都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地方文化建设和经济转型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另外,晋国又是法家思想的发源地,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播地,是名商巨贾的实践之所。研究他们的思想文化,有助于理解山西地区民众的集体心理和思想意识的渊源,有助于我们传承优良的文化传统。
最后,与其他国别史研究相比,晋国史研究的系统性著作屈指可数。诸如晋国的城市与建筑、经济、文化、思想、服饰、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专著基本没有,晋国史的专题性研究尚需加强。
总之,晋国史研究经过众多学者百年来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现在的晋国史研究正处于最佳的时期,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争取开创晋国史研究的新局面。
[1] 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J].历史研究,2000,(4).
[2] 张颔.重视对晋国历史及晋国文化的研究[J].晋阳学刊,1982,(1).
[3] 李玉明.序[A].李元庆.三晋学术研讨会论文专集[C].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4] 雯梅.群贤毕至——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J].上海文博,2002,(1).
[5] 李伯谦.喜读李尚师《晋国通史》[N].中国文物报,2015-1-30(4).
[6] 徐义华.评《春秋晋国赵氏研究》[N].中国文物报,2008-6-4(4).
[7] 王万辉.重新认识晋国在中国古代史的地位[J].文物世界,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