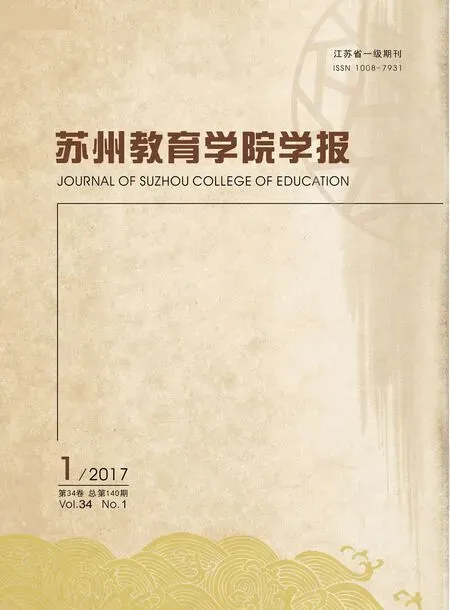《青城十九侠》:从小说到戏曲
鲍开恺,艾立中
(1.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2.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青城十九侠》:从小说到戏曲
鲍开恺1,艾立中2
(1.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2.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还珠楼主小说《青城十九侠》在连续出版的同时,就被他改编成京剧搬上舞台。这一主要是为“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表演量身打造的剧本,体现了一种“为专人编戏”的特色,是当时戏曲界“明星制”的产物。《青城十九侠》从小说到戏曲的改编,文本的主旨、情节、人物形象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是由改编者的思想观念、演员的演技、观众的欣赏习惯等因素决定的。
《青城十九侠》;小说;戏曲;改编
在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史上,还珠楼主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作品共有36部,其中《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最为知名,影响遍及大江南北,令无数读者为之倾倒。当时,还珠楼主这两部最著名的小说均被改编成京剧剧本,搬上舞台。从这个角度来看,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对于通俗小说与戏曲的互文关系具有研究参考价值。笔者这里所说的“互文”主要是指“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①本文所用“互文性”概念出自索莱尔斯,见蒂费纳萨莫瓦纳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一
还珠楼主②本文关于还珠楼主生平的介绍主要来自周清霖:《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年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40—50页。(1902—1961),本名李善基,后名李寿民,生于四川省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父母都是书礼世家,还珠楼主自小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7岁即随父亲初登峨眉、青城二山。峨眉山是西南佛教圣地,青城山是道教名山,皆景色壮丽,人文气息浓厚。还珠楼主后来屡登两山,对这两座名山充满了无限向往。10岁时,他曾向峨眉僧人学习气功武术。童年经历对还珠楼主日后创作《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产生了重要影响。成年以后,还珠楼主从事过秘书、编辑、幕僚和家庭教师等工作,生活阅历非常丰富,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沛的社会素材,锻炼了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能力。他的武侠小说大致可以分为“入世”和“出世”两类,《青城十九侠》和《蜀山剑侠传》被评论家称为“出世武侠”,或者是“超武侠”或“奇幻仙侠”。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青城十九侠》描写了较多民俗风情,是“入世”小说。相比较《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受关注程度不高,台湾学者黄汉立认为《青城十九侠》是《蜀山剑侠传》的别传,但又可以独立成书,《青城十九侠》的缺点是“不是流于夸大,便是失诸琐碎”[1]。但黄汉立肯定了《青城十九侠》的独特价值。
还珠楼主酷爱戏曲,1921年,他与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1900—1976)义结金兰,此后长期为尚小云编写剧本,陆续编写了《北国佳人》《卓文君》《林四娘》《青城十九侠》等剧目。还珠楼主与尚小云成为事业上的合作伙伴并非偶然。
首先,尚小云擅长武侠戏。他早年学武生,后来因扮相秀气,改演了青衣。还珠楼主少年时也学过武艺,他建议尚小云“文戏武唱”。经过摸索,尚小云把两者相结合,在刀马旦方面取得了突破,凭此在“四大名旦”中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地位。尚小云曾说:“中国的女子太软弱,太偏于依赖,本人所编的诸剧就是着眼在这一点的,虽不敢诩有转移风俗的力量,但是至少亦使女子多一种兴奋的助力。”[2]这一转型,使得尚小云能够胜任还珠楼主武侠小说中的侠女角色。
其次,还珠楼主充满奇幻色彩的武侠小说风靡海内,让尚小云产生了将还珠楼主的小说搬演于舞台的冲动,二人就此达成默契。还珠楼主又精通戏曲,遂帮尚小云编写剧本。当时,演出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四大名旦”都搬演过新编剧目,但梅兰芳、程砚秋和荀慧生的新编剧目的奇幻色彩均不如尚小云。尚小云是一位非常喜欢出新出奇的演员,爱演新戏,他曾说:“现在的年口,要想拿玩艺儿卖钱,不比先前容易了。倘使不拼命挣扎,向前迈进,真有不能生存的危险。”[2]当时剧评家曾批评他:
尚伶也要迎合上海滩上人们好奇心理起见,于是也学海派,便“新”了起来。所谓“新”的玩意,乃是于各戏上皆加一“新”字,如新《玉堂春》、新《三娘教子》、新《十三妹》、新《珍珠扇》、新《摩登伽女》,果然叫座极佳……我记得海上有班评剧家对于外江派的戏用“新”字相号召,曾作过严厉的批评,说戏上加“新”字,便是毫无意思的举动,外江派现已被指责得不再用了。而尚伶如今拾人唾余,拿来当真正“新鲜的玩意”,真是令人齿冷。[3]
民国时期,京剧表演界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京朝派”,一派是“海派”或“外江派”。“京朝派”偏于京剧传统,而“海派”喜欢出奇出新,讲究机关布景。正是尚小云这种酷爱出新的演员,才可能将《青城十九侠》这种奇幻小说形诸舞台。当时在坚守京剧传统的人眼中,尚小云是在破坏京剧传统。而今天我们在对历史的观照中发现:戏曲的发展既要坚守传统,也离不开创新,当然这种创新必须要遵循戏曲的艺术规律。
还珠楼主最著名的《蜀山剑侠传》也曾被改编为京剧连台本戏,但第二集开始才由还珠楼主改编。当时报纸曾这样描述其中经过:“上海荣记共舞台禹历春节所演《蜀山剑侠传》,因有若干新奇彩头,亦颇轰动。其头集《蜀山剑侠传》剧本系老牌编剧家尤金圭所打提纲所编,日前经名评剧家苏少卿拉拢,荣共总经理周剑量,特假座锦江,宴请小说原著作者还珠楼主,双方谈笑甚欢,彼此谈妥,自第二集起,编剧事宜由还珠楼主亲自动手,珠楼在北方,替尚小云编过《青城十九侠》,亦是老手也。”[4]
由于笔者尚未找到《蜀山剑侠传》的剧本,故无法探究全本戏的完整面目,也无法比较小说与戏曲之间的互文关系。幸运的是,《青城十九侠》的完整剧本目前尚存。
二
《青城十九侠》剧本(手抄本)藏于北京市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中,卷宗题名为《北平市华乐戏院万子和关于送审〈青城十九侠〉〈元夜观灯〉剧本的呈文、申请书及社会局的批示》①《北平市华乐戏院万子和关于送审〈青城十九侠〉〈元夜观灯〉剧本的呈文、申请书及社会局的批示》,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002-003-00531,1936年。,档案时间为1936年1月。北平市社会局是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成立的机构,其职责涵括土地、工商业和娱乐业、劳动行政、公益慈善等领域,任务为改造社会。1932年北平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给社会局发出公函,函文提到:“本市旧剧种类繁多,内容复杂,剧情取材极应注意,凡一切有违本党党义,消沉民族意志,及妨害良善风俗之歌词均应严予取缔,以免摇惑人心。”①《市政府、社会局等单位关于取缔妨害良善风俗之歌曲、成立戏曲审查委员会的指令、训令及审查委员会的常会记录》,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002-003-00048,1932年。1932年10月4日《北平市社会局戏曲审查委员会章程》(下简称《章程》)公布,《章程》第一条规定,“本会以审查北平市剧院所演戏剧及一切评书词曲、幻灯片等力谋改善社会风化及辅助教育为宗旨”;《章程》第五条规定:
(甲)应提倡者(一)富有民族意义者;(二)描写社会生活富有感化力者;(三)能增进民众常识者。
(乙)应取缔者(一)违反党义者;(二)有伤风化者;(三)违反事理人情者。[5]
《章程》所规定的检查标准主要是维护国民党的党义,巩固“三民主义”的统治地位,但有些条款界定的标准比较含糊,易导致戏曲审查委员会执法产生随意性。一些包含色情内容的剧目确实“有伤风化”,取缔是应该的,但表现男女自由恋爱的戏在当时也多被看作“有伤风化”,一概取缔,则显示出浓厚的封建保守性。戏曲审查委员会对每部剧本提出书面意见的同时,还要派遣专人赴戏院观摩,检查舞台演出是否符合原剧本,防止演员随意更改剧本,这种检查办法非常严格,对演出的自由度有一定的妨碍。
1936年,北平市社会局通过了《青城十九侠》的审查,审查意见如下:
查《青城十九侠》小说,系还珠楼主所编,载在《新北平报》之内。惟此本所演,并非该小说内一章或一段之事实。仅系就小说内,其剑侠叙述之寥寥数语,将其铺张扬厉,编为剧本。本内所演,系孝女报仇,淫贼伏法,妖道受诛,侠义成功。各情形提倡伦常,针砭社会,尚无不合之处,拟准予备案。②《北平市华乐戏院万子和关于送审〈青城十九侠〉〈元夜观灯〉剧本的呈文、申请书及社会局的批示》,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002-003-00531,1936年。
这里对《青城十九侠》从小说到戏曲的主题、情节改编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由于改编后的主题符合北平市社会局的戏曲审查章程,故得以通过。还珠楼主的另一部剧本《北国佳人》讲述了元代一位忠臣遭奸臣冤杀,忠臣之女侥幸逃出,后历经艰辛,为家族伸冤,最终大仇得报,奸臣伏诛,北平社会局对该剧的评语是“意在提倡伦常道德,并未触犯审查章程第五条乙项各标准,拟准予备案”③《尚小云关于送审〈北国佳人〉剧本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批示》,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002-003-00529,1936年。。《青城十九侠》于1935年5月在《新北平报》开始连载,并不断有单行本出版,一直到1947年第二十五集出版后中断。1936年12月,《青城十九侠》第四集初版发行,同年底被尚小云搬上京剧舞台。于是,形成了一种现象,即《青城十九侠》的小说一边在出版,戏曲一边在搬演,可见小说的轰动效应,而戏曲又扩大了这一效应。据现有资料统计,民国时期,尚小云五次搬演《青城十九侠》,分别为1936年、1937年、1938年、1940年和1948年。《青城十九侠》这个剧目后来之所以消失于大众视野中,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武侠类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不符合时代要求,遂销声匿迹。还有,当时戏曲剧本大多是以手抄本形式保留在主要演员身边,没有刊印出版,一旦因主客观原因保存不善,就无法完整流传。
三
从文化思想来说,《青城十九侠》很复杂,儒、佛、道思想都有,涉及经史子集、天文地理、民俗风情等。其剧本《前引》云:
西蜀本是一个神秘之国,因为民间传说和当地若干年前留下的种种仙灵遗迹,人民对于神仙剑侠、奇人异士本来就很崇拜;又值康、雍之间,满人入关未久,孑遗之民怀念旧君,目睹新廷暴虐,忍受压榨,敢怒而不敢言;庸懦一流,自然把一切都委之运数;具有国家种族思想、又富有聪明才智之士,既不愿委身异族,为仇敌的鹰犬,又不忍若千万亡国同胞俯首受人宰割,于是群趋剑侠一流,以诛奸杀恶为己任,冀略快意一时,虽然明知劫运难回,光复故业暂时无望,总想在除暴安良之中,种一点兴灭继绝的根子。风尚所归,奇人辈出,尤以峨眉、青城两派殊途同源,为个中巨擘。本书所记,便是这两派剑侠的轶闻奇迹。虽迹涉虚幻,难免铺陈;而笔人哀乐中年,浮沉人海,足迹流转,几半国内,蜀中故土,更是祖宗庐墓之乡,对于各种风土人情、衣服食饮、名山大川、珍禽异兽,大都有所本历,不同虚构。①《北平市华乐戏院万子和关于送审〈青城十九侠〉〈元夜观灯〉剧本的呈文、申请书及社会局的批示》,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002-003-00531,1936年。
在这里,作者谈到了故乡的神奇和人民崇拜神仙剑侠的原因,这也可以解读为巴蜀文化对还珠楼主的影响,他在《蜀山剑侠传》和《青城十九侠》中经常描写各种奇幻境界和奇禽怪兽。小说《青城十九侠》的背景是明末清初,具有反清复明的政治倾向,与民国初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有相通之处,在抗战期间也有一定的意义。《青城十九侠》描写了青城派的十九位侠客,分别是罗鹭、裘元、虞南绮、狄胜男、狄勿暴、纪异、吕灵姑、杨永、杨映雪、纪登、陶钧、杨翊、陈太真、呼延显、尤璜、方环、司明、涂雷、颜虎。
《青城十九侠》的小说没有描写剑侠与清廷的斗争,反映了“出世”的特点。小说通过对多位出世剑侠轶闻奇迹的描绘,展现了对自由、正义和生命的追求。同时,小说宣扬了“孝”,如女剑侠吕灵姑为父亲吕伟报仇,努力学习剑术,最后终于成功。但在戏曲《青城十九侠》中,那些神奇的意境和各种奇幻动物绝大部分都消失了,主要是宣扬了剑侠的孝义和官员的清正,正如北平市社会局批文中所提到的“孝女报仇,淫贼伏法,妖道受诛,侠义成功。各情形提倡伦常,针砭社会”,这种主题既符合了戏曲审查标准,也满足了当时市民的欣赏心理。此外,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小说中的很多奇幻的场面都无法表现出来。戏曲剧本第六场通过神僧轶凡之口宣扬了佛道的神奇:
昨日青城派剑仙朱梅到右飞剑传书,言说青城门下一十九个后辈剑侠内中有一转劫女弟子,名唤吕灵姑,现在莽苍山中隐居,事父。不久他父便被仇人杀害,只剩灵姑一人孤苦无依,请老僧前往渡化,接引到疯仙郑道友门下,不免到时前往便了。正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众生何苦自相煎。②同①。
这部分内容是从小说中移植过来的,把吕灵姑的身世遭遇都预测了,有一种宿命论在内。小说没有“冤冤相报何时了,众生何苦自相煎”之语,剧本改编后体现了佛教超脱世俗、忘却烦恼的人生追求。
从情节线索来看,小说《青城十九侠》目前共一百零六回③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出版的《青城十九侠》共一百零七回,其中七十九回和八十回重复。,还是未完本,结构比较松散,情节繁复冗长,一些地方描写奇禽怪兽的打斗场面雷同,这是通俗文学为了市场效益无法避免的弱点。戏曲剧本作了大幅精简,1936年1月1日提交给社会局审查的剧本共有二十三场。剧本第一场通过清初昆明知府陈敬之口介绍了故事背景:西川张鸿、吕伟当年为了搭救书生陈敬,与号称“七首真人”的江洋劫匪毛霸结仇,张鸿后来死于抗清斗争,吕伟携女儿灵姑躲进莽苍山避难。全剧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毛霸练就了五毒神砂,来莽苍山寻吕伟报仇雪耻,后将吕伟打死,吕灵姑受神僧轶凡的指点,投剑侠郑颠仙门下,苦练剑术,后下山寻毛霸,为父报仇。毛霸摆下都天阵挑战青城七侠,灵姑前往助战,斩毛霸,大仇得报,这一条是主线;另一条副线是毛霸的两个徒弟吴玉和王升到府衙“采花”,杀死知府陈敬女儿,吕灵姑、陈敬联手侦破陈敬之女被杀一案,为蒙冤的陈府更夫刘三平反,并擒获吴玉和王升两淫贼。剧本中的副线情节在原小说中是没有的,编剧增加这一情节后,使得剧本富有一定的悬疑性,可以更好地吸引观众。原著中陈敬的形象是借吕伟的视角展现的:
细看那少年,眉目清俊,神采秀逸,并不带一毫好邪之容,衣饰也朴实无华,不像是个坏人,只是文房用具。茶铛茗碗却甚是一精一美,颇有富贵人家气派。吕伟暗忖:“这人相貌不恶,如此年少,千里为官,却也不易。一旦死在恶道手中,岂不冤枉?”[6]667
……略一观察,便知是个清廉之官。那陈正年才十二三岁,不特相貌清俊,二目有光,不类常童,最难得是那般胆大心细,沉着勇敢,不由越看越爱。[6]674
此处流露出吕伟对清官父子的赞美,尽管是侠客的视角,但其实符合中国普通百姓对清官、好官的第一印象。这种以貌取人的方法不一定准确,但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小说中的陈敬有一儿子叫陈正,获救以后,陈敬与张鸿和吕伟结为兄弟,并让其子拜二位侠客为师,不免让人联想到“桃园结义”,反映了还珠楼主对于侠客与清官结盟的认可。在戏曲剧本中,陈敬生有一女叫陈凤娇,被毛霸徒弟吴玉所杀,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一个关目。
尽管三人结拜为兄弟,但小说中陈敬父子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体现了小说的“出世”倾向。而在戏曲剧本中,编剧特意设置了吕灵姑和陈敬合作擒贼之情节,吕灵姑和陈敬代表了正义的一方,毛霸师徒代表了邪恶一方,最后,正义终于战胜邪恶,案情大白,罪犯伏诛,冤情得到昭雪,符合民间最基本的信仰。这种官府和侠客合作的情节安排并非偶然,可以追溯到清代著名的公案小说《施公案》。《施公案》被看作是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的合流之作,施公就是康熙时期著名的清官施世纶。《施公案》后来在晚清时被改编成多部京剧,如《四霸天》《恶虎村》《莲花院》《盗金牌》《盗御马》《连环套》等,在晚清民国的剧坛上都比较盛行,这些剧目基本都是清官加侠客,主要宣扬“惩恶扬善”“扶危济困”“报效朝廷”等观念。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清官为民做主,在封建体制内为国为民谋利益,而侠客用武力为民解忧,则实现了封建体制外的一种补偿。尽管清官在古代并不多见,但侠客更显虚幻。然而,这类故事蕴含的主旨既满足了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又满足了民间百姓对虚幻的心理需求,上下同赞,还珠楼主可谓深谙各阶层的内心世界。
小说第六十二回描写毛霸找吕伟报仇,写得惊心动魄:
吕伟一掌挡去,见毛霸左掌收回,掌心向外,退向肋下,似在运用力气,右掌并未似前打到,忙往前一近身,待要一掌打去,猛瞥见毛霸身子往后略退,目闪凶光,满面俱是狞厉之容,指定自己大喝一声,心便一震。情知不妙,方欲纵避一旁给他喊破,忽然一阵头晕,毛霸右掌已然打到。这时吕伟人虽昏晕,知觉未失,真力尚在。自知中了邪法暗算,决意一拼,用足真力,横臂往上一挡。又听毛霸一声怪叫,手臂发酸,跟着眼睛一花,胸前中了敌人一掌,人便失去知觉,翻身跌倒。[6]1806
这段描写把两位武林高手交手时的心理和深厚的武功都展示了出来,双方都有受伤。在《青城十九侠》戏曲剧本第七场中精简了毛霸和吕伟对决过程的描写,着重于吕伟决斗前对女儿灵姑的嘱托:
生:既是我儿定要观战,此贼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少时为父如若受伤倒地,此贼念在当年放他逃走之情,必留为父全尸,那时我儿千万不可动手,须知为父尚且不胜,我儿焉有胜理?冒昧上前,如有差池,不但为父尸骨无人埋葬,日后报仇更是无人了。
旦哭介:喂呀呀!
生:我儿不必啼哭,日前胜败难分,快将宝剑取来,待为父迎敌此贼便了。
旦:是。
毛:吕伟,再不出战,你家祖师爷要打进来了。
生:毛贼,休得猖狂,老夫来也。(打介)
毛掌打生倒介。
(毛)不想你也有今日。
毛:日后报仇何惧之有,念在当年被舍,未曾杀害也,罢,饶你全尸与你女儿狗命,俺去也。①《北平市华乐戏院万子和关于送审〈青城十九侠〉〈元夜观灯〉剧本的呈文、申请书及社会局的批示》,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002-003-00531,1936年。
这段描写把毛霸重现江湖后那种骄横狂妄的神态突显了出来,同时着重刻画吕伟决斗之前对女儿的关爱以及女儿试图助父杀敌的孝心,让观众感受到吕伟参与决斗的凶险,为吕伟的悲剧命运担忧。与小说相比,《青城十九侠》的戏曲剧本描写吕、毛二人决斗的过程极为简略,吕伟被毛霸一掌打死,足见毛霸五毒神砂掌的威力。当然,剧本被搬演于舞台时,为了吸引观众,这种打斗场面可能会延长一段时间。至于设置毛霸放走灵姑的情节,一方面是为了表现毛霸的那点江湖义气,更主要是为了吕灵姑苦练剑术、为父报仇留下故事线索。这种情节设计都是为了表彰孝女。
在1936年10月30日《戏剧旬刊》上刊登的《名旦尚小云〈青城十九侠〉》显示,这个剧本后来改用了“幕”,一共是十四幕,每一幕还有题目,与北京档案馆所藏1936年1月的版本相比,1936年10月的版本主要是在第二幕“红裳侠女独门斗灵猿,七首真人飞行绝岭”中增加了灵姑斗灵猿的情节,大概是为了突出尚小云的功夫。当年的报纸曾有文章描述了演出斗灵猿戏的趣事:
尚小云演《青城十九侠》于新新,剧中有小猴一群,系借自荣春社,尚有提猴一幕,不料用手提猴尾,用力过猛,将猴尾揪掉,此小猴乃成一光屁股矣。台下为之莞然。[7]
今天这出斗灵猿的戏是《青城十九侠》目前留在舞台上唯一的一出。尚小云在当时出于演出市场的竞争需要,热衷于排新戏,但很多新戏包括《北国佳人》《摩登伽女》《绿衣女侠》《虎乳飞仙传》等缺少加工,艺术上不够精细,缺乏精彩的唱段和动作,如当时一位剧评家就写过《尚小云以武戏最为拿手》其中这样评价尚小云的表演:
查尚小云已四十余岁,其演戏年龄,当不止有三十年之过程。《摩登伽女》及《青城十九侠》等一类神怪不经之戏,皆为近年新排者,岂前此廿余年中,一百余出老戏内,无一为其拿手者欤?……但以愚外行人来观察,觉其诸老戏,如《探母》《雷峰塔》《御碑亭》《二进宫》等戏,不敢说独步一时,也可以说能垂范后昆,不以此等戏谓为拿手,而以时装异服、机关布景两出荒诞不伦之新戏,谓为绝活,其真不知尚小云也耶?[8]
从前面所引用的评论文字,加上这番评论,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当时的剧评家对尚小云的新编戏并不认同,而是认可他的传统戏。尽管这些新编戏在当时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但演完一阵后便搁置起来,因此没有全本戏甚至折子戏流传下来。这一事实说明,剧目的生存主要还是靠自身的艺术水准,只有艺术水准高,即便时代环境有变化,剧目也能流传。
四
在小说《青城十九侠》中,灵姑的形象描写非常多,但她并不是主角,因此显得比较零散。第七回通过旁人的眼光来描写灵姑的第一次出场,其形象非常奇特:
浑身尽是白毛,腰间还围着一片鹿皮,臂也不长。细看面貌,也和人相似,不类猿猴。胸前隆起,腰肢甚是窈窕。除了通体长着长毛外,竟有七八分像人,及至见她听了雷春那一番无心的话,便已避过一旁,大有害羞神态。走得虽快,上身笔直,也不似猿猴跳纵行路。……再看那小猿,头上乱发已经方母整理,身上穿了衣服,简直换了一个样儿,除那满脸长白毛外,侧背面看去,竟然与人无异。这时亭亭静立,垂手侍侧,听见众人谈笑问答,也不学嘴,只管凝神谛听,俯首沉思,若有所悟。[6]249
在小说中,灵姑是被猿仙所抚养,除了剑术以外,灵姑还有一件罕有匹敌的绝杀武器—飞刀,但其身世一直不清楚,直到第二十一回才知道其父叫吕伟,到第二十三回,吕伟回到家中看望妻儿,才遇见了灵姑。但是小说留下了一些疑点:吕伟为何遗弃了灵姑?既然幼年被遗弃,灵姑后来怎么知道她的家在何地,谁告诉她的?灵姑第一次见到吕伟,怎么知道吕伟就是她的父亲?灵姑的名字并非吕伟所取,吕伟又是怎么知道灵姑的?诸如这些疑点,使小说中灵姑的形象存在缺憾。
在戏曲剧本中,灵姑毫无疑问是全剧的核心人物,编剧着重表现了她的孝,删掉了小说中她和猿仙的戏。第十场中,灵姑冒着严寒为父亲挖坟下葬:“这北风吹得儿足僵手战,似这般天寒地冻怎得埋完?……似这般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锹锄难下。今日如不将坟作好,山中猛兽甚多,那还了得?”①《北平市华乐戏院万子和关于送审〈青城十九侠〉〈元夜观灯〉剧本的呈文、申请书及社会局的批示》,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002-003-00531,1936年。在为父报仇的过程中,灵姑经历了各种考验,如在第十场中,郑颠仙为了考验灵姑的诚心,便出言不逊,故意刺激灵姑,然而灵姑始终恭敬有加,没有埋怨:
我看这位婆婆虽是癫狂,颇有玄机。师父既称颠仙,必有颠象。莫非他便是我的师父试探于我,万一错过仙缘,悔之晚矣。我何不跪在他的面前苦苦哀求,看他如何。(颠)你背地嘀咕什么?(旦)师父不必相试,可怜弟子身带血海冤仇,望乞大发慈悲,收归门下了吧。(颠)起来,什么乱七八糟的,谁是你的师父呀?(旦)哎呀,师父呀,弟子已然看出行径,再不开恩收容,惟有一死而已呀!(颠)此女果然求道虔诚,也不枉我渡他一场,徒儿不必悲苦,为师收你就是。②同①。
灵姑的悟性和虔诚终于感动了颠仙。在小说中,灵姑和颠仙的见面比较顺利,没有剧本中的考验内容。
在小说中,陈敬被吕伟搭救后再没有出现,而戏曲剧本中通过对破案经过的描述来展现陈敬的形象。陈敬的形象具有明末清初很多文人的特点,正如剧中第一场陈敬自述:
原说弟兄三人同享福祸,谁知天下大乱,逆贼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夺了明室天下,大兄张鸿,为救福王,被吴三桂聘请能人刺死,二兄吕伟全家遇害,只剩他父女二人逃往莽苍山隐居避祸。明亡之后,本当辞官不仕,以全臣节,怎奈家贫,难以安度,只得投降新朝。③
这段独白反映了清初很多入仕文人的心态,显示了还珠楼主对历史的熟悉和尊重。陈敬虽为一名清官,但一开始对女儿被杀的血案缺乏清醒的判断,没有收集更多证据,也没有去刘三家了解情况,就直接断定更夫刘三有罪:“你手持钢刀满身血迹,还敢强辩,左右与我掌嘴。人证俱全也不怕你不招,左右将他钉镣收监,明日升堂,大刑审问。”④同①。后来却变得冷静:“不想近日连出无头命案,我想刘三乃本衙更夫,既是杀人,为何不逃?我女儿定被贼人所害,这等采花贼人乃是江洋大盗本领高强,恩兄吕伟已然身死,叫我怎生为女报仇?”⑤同①。既表现了他对案件的清醒认识,也流露出他对江洋大盗的恐惧和无奈,其实这一心理刻画讽刺的是官府的无能。这恰恰是为了突出灵姑在整个案件侦破中的主导作用:灵姑先是听到刘三之妻的申诉,抓到淫贼吴玉,后又抓到吴玉同伙王升,并保护了陈敬,剧本把灵姑这一锄奸扶弱、匡扶正义的光彩形象彰显了出来。
毛霸的形象在小说和戏曲中也有较大差别。小说对毛霸的形象作了深入的刻画,多处突出了他骄横霸道的一面。在灵姑复仇的情节中,小说又展现了他霸道与软弱并存的形象。第七十二回中,毛霸被赶来解围的灵姑击伤,此时他尚不知灵姑是吕伟之女,第七十三回毛霸在临死前流露出一丝悲情:
毛霸闻言,才知心计白用,生机已绝,敌人早有防备,自己不知还要受多少磨难,才得一死,不由心寒胆裂。那条断腿尚连着一点筋肉,不动已是痛楚非常,再就地一拖,直疼得通体冷汗交流,说不出的难熬。心想:“反正一死,还不如放痛快些,少受好些磨难。”忍不住颤声哀告道:“吕姑娘,我当初虽用重手法伤你父亲,也只一下倒地,并还留他全尸。你也是玄门中人,何苦如此狠毒?我已知道孽重,难逃一死,请你给我一个痛快吧。”[6]2106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侠客临终前的痛苦,这种痛苦与普通人无异。
与小说相比,剧本着重描写了毛霸的霸道,对他死亡前的言行没有展现。从创作宗旨来看,戏曲剧本主要是宣扬除暴安良,表彰灵姑的侠义和孝心,渲染毛霸的复杂心理必然会冲淡剧本的主旨,因此善恶对立十分明显;而小说则表现了多重文化主旨。在戏曲剧本中,毛霸的徒弟吴玉也很骄横,在第十九场堂审的时候,吴玉对陈敬说“俺乃英雄好汉,岂肯跪你”,还继续威胁道:
连日城厢内外采花杀人也是俺弟兄所为,今日闻听人言,我师在金狮岩设下都天七煞大阵,要提青城门下十九弟子,正要与俺师弟送信,便被这个贱婢拴住,好好将俺放了便罢,如若不然,被俺师父知道,叫尔等死无葬身之地。①《北平市华乐戏院万子和关于送审〈青城十九侠〉〈元夜观灯〉剧本的呈文、申请书及社会局的批示》,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002-003-00531,1936年。
吴玉这一骄横无礼的形象呈现出流氓恶势力的特征,揭示了封建时代法律欺善怕恶的本质,最后只能靠灵姑的高强功夫才能制服嚣张的恶徒。
总的来看,从小说《青城十九侠》到戏曲《青城十九侠》,故事的主要内容、情节线索和人物形象都做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戏曲剧本还加入了很多小说没有的人物和情节,这些情节、人物又受到晚清民国诸多小说和戏曲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戏曲和小说之间构成了互文的关系。然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明星制”的盛行,还珠楼主这种为“专人编戏”的现象在民国时期比较常见,“明星制”的根本问题在于“认角不认剧”,一切都为主角的唱腔和表演考虑,当感到小说中的“戏”不够的时候,就要从小说之外去加添情节,这导致了小说与戏剧 “互文关系”的弱化。时至今日,尽管有了导演,但很多小说的戏曲改编依然存在“认角不认人”的现象,应加以注意。
[1] 黄汉立.从《蜀山剑侠传》到《青城十九侠》[M]//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第1册.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151.
[2] 梅花馆主.奋发图强中之尚小云[J].半月戏剧,1937(1):17-18.
[3] 菊蕊.电影与戏剧:尚小云新的出奇[J].结晶,1934(3):14.
[4] 阙名.《蜀山剑侠传》编剧费三千[J].戏世界,1948(371):4.
[5] 北平市社会局.北平市社会局戏曲审查委员会章程[J].时代教育,1934,2(3):84-85.
[6] 李寿民.青城十九侠[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
[7] 阙名.趣事:尚小云演《青城十九侠》于新新[J].立言画刊,1940(86):26.
[8] 许穉良.尚小云以武戏最为拿手[J].十日戏剧,1939(22):1.
[9] 周清霖.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年表[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4(6):40-50.
[10] 韩云波.还珠楼主武侠小说序跋研究[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33(3):3-17.
[11]韩云波,滕巍.开千古未有之奇观:还珠楼主研究65年[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2,28(2):67-72.
(责任编辑:石 娟)
The Nineteen Swordsmen in Qingcheng: From Novel to Opera
BAO Kaikai1, AI Lizhong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During the process of publication, the novel ofThe Nineteen Swordsmen in Qingchengby Huanzhu Louzhu was adapted into Peking Opera and performed on stage. It was adapted particularly for Shang Xiaoyun, one of the “Top Four Peking Opera Performers of Female Heroines”, which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making a play for a particular person”, and was the result of the “celebrity system” in the opera circles. As the novel was adapted into an opera, the theme, plot and characters became noticeably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text, and playwrights’ ideas, actors’ skills and audiences’ habits contributed to such changes.
The Nineteen Swordsmen in Qingcheng; novel; opera; adaptation
I206.6
A
1008-7931(2017)01-0026-09
10.16217/j.cnki.szxbsk.2017.01.003
2016-10-08
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项目“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研究”;姑苏宣传文化人才重大项目“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
鲍开恺(1982—),女,江苏苏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戏曲史;艾立中(1976—),男,江西景德镇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戏曲史。
鲍开恺,艾立中.《青城十九侠》:从小说到戏曲[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34(1):2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