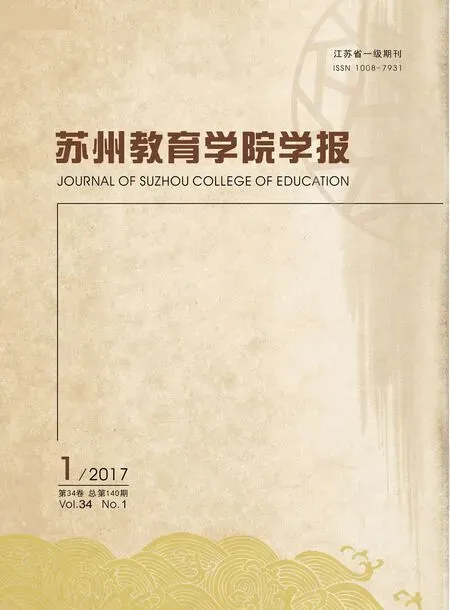通俗作家笔下的辛亥“武昌首义”—通俗文学映像社情百态“富矿论”系列之二
范伯群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通俗作家笔下的辛亥“武昌首义”—通俗文学映像社情百态“富矿论”系列之二
范伯群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清末民初,许多通俗作家是中国报业初兴时的第一、二代报人。在辛亥武昌首义时,他们能闻风而动,以时评杂感为革命鼓与呼,对革命发挥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又以小说与史话等多种文艺形式反映这场革命中各色人等对革命所持的不同态度;并尝试以文艺传记评价历史人物。
武昌首义;通俗文学;富矿论;时评杂感;长篇小说;史话传记
鸳鸯蝴蝶派的不少文人具有双重身份:1.作家和文艺刊物的主编;2.新闻工作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是清末中国报业初兴的第一、二代“报人”。作家与刊物主编的收入是无法固定的,个人办刊物还有亏本的可能,但从投资办报的老板手中获取固定的收入,往往是编辑的主要经济来源,此类收入并不比当年高工资的大学教授们低。但作为报人,他们编的即使是文艺性质的副刊,也都需要与报纸的整体内容相配合,因此他们都写过大量的时评、杂感,面对彼时的社会热点与国际国内政治的风云变幻,他们需要站在舆论阵地的最前沿。在当时,民间报纸如果不能承担“社会良知”和“市民喉舌”的角色,就难以生存,因为民间报纸需要广大市民自愿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订阅,一定要尽量追求读者面的最大覆盖率。所以,过去文艺界根深蒂固地认为鸳鸯蝴蝶派作家只是写些卿卿我我的言情小说或是他们的作品只发挥文艺的娱乐功能,这类观点是十分片面的①可参看拙作(与黄诚合作):《报人杂感—引领平头百姓的舆论导向—以严独鹤〈新闻报〉和周瘦鹃〈申报〉的杂感为中心》曾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8期上,论及通俗文学的报人作家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曹锟贿选、“五卅”、“三一八”惨案直到抗战和蒋介石政权崩溃过程中杂感随笔的主要内容,用白纸黑字论证他们用平头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引领平头百姓的政治舆论导向。。本文对通俗作家笔下的“武昌首义”进行盘点,从他们的时评、杂感谈起,因为他们用时评、杂感的武器最敏感地为“首义”鼓与呼!
一
武昌首义之后,通俗作家扮演了轻骑兵的角色,以多样的文艺形式讴歌革命首战的胜利,为“星星之火”造势,表现最为突出者,当属陈冷血与包天笑的时评。革命初起时,清廷妄图封锁起义的消息,电报局当即被官方控制,当地报纸也不准外运。《申报》在武汉的访员于10月12日通过当地租界的外国电报公司向上海《申报》馆发来电报,消息仅四个字:“武昌失守。”报馆心领神会,知道近期广州“黄花岗起义”虽惨遭屠戮,但革命的“星星之火”却在武昌开出了胜利之花。通过《申报》,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黄浦江之畔。10月13日,陈冷血与包天笑闻风而动,在任主笔的《时报》上特开个人“时评”专栏。陈冷血善写时评杂感,他的专栏定名为“时评(一)”;包天笑的专栏则定名为“时评(二)”,他还负责撰写有关辛亥革命的“逸话”与“佚史”。这些时评杂感都是“三言两语”。他们二人有时一天要连写数则,像“匕首”“投枪”一样击中清廷的心脏,为摇篮中的武昌首义保驾护航。10月12日得到消息,10月13日即“开栏”,到11月3日为止的20天内,陈冷血共发表时评六十则,平均每天三则;包天笑也有三十四篇,此外,还有“逸话”两则,“佚史”一篇。读这九十多篇时评杂感,就可知道这些“三言两语”的短文在当时能起何等作用。
10月13日,陈冷血的时评题目为《黄兴与荫昌—湖北革命记之一》:
武昌失守,汉阳又危。革命军既有兵队,又有军械,与政府俨然有对峙之势矣;而政府亦以对峙相待,命陆军大臣统近畿军队乘车而下,相见于江汉之间。是役也,南北战欤,人民与政府战欤,革命与专制战欤,其胜其败,势将大异。①陈冷血:《时评(一)》,载《时报》1911年10月13日。为节省篇幅,以下凡引用陈冷血和包天笑在10月13日与11月3日之间在《时报》上发表的“时评”,均在内容后附(×月×日),不再一一作注。
短文前半不仅写当时的大势,而且在文字的“背面”还指出,此役与广州黄花岗之役大不相同。黄花岗之役仅有数以百计的敢死队员,他们势单力薄,故而被清廷残酷镇压下去了;这次却是训练有素的新式军队,革命党手里“既有兵队,又有军械”,与政府是兵对兵、将对将的“对峙”。清廷不得不令陆军大臣亲自出马,可见形势之严峻。文章的后半是为这次起义“定性”,乃是“人民与政府战欤,革命与专制战欤”,认为这样的刀对刀、枪对枪的正规军之战是人民对腐败政府之战,是扑杀二百六十多年来的专制清廷之战,战将必胜。文章虽短,气势澎湃,立场坚定,实有千钧之力,宣告清廷的末日将临。这实际也是通过报刊的舆论,对全国人民的一次鼓舞。
包天笑也撰文为这次革命“定性”,文题是《共和与专制斗》:
二十世纪为专制政体将绝迹于地球之日也。革命军以提倡共和为宗旨,固以探得骊珠矣。以共和与专制斗,所以各国不敢以寻常内乱视革命军也。(1911年10月19日)
短文提出了“政体”这一个大问题,革命之所以必能成功,因“共和”乃20世纪大势之所趋。“骊珠”是一种珍贵之珠,“探骊得珠”在这里是指革命军所作所为已得到当时世界政体之精粹,这是必胜之源。武汉当时是长江中游之重镇,租界林立,帝国主义国家曾屡屡干涉中国内政,这次他们却只好宣告中立。
除了这一类为革命“定性”的时评外,这九十多篇短论尚可分若干类别。第二类就是一再强调“人心之所向”。人心向背是胜负之一大关键。因此,陈、包二人的时评中有多篇涉及“民心所向”的内容,进而谈及“军心之所向”。包天笑以设问的口气写道:“苟政府不失民心,则事尚可为耳,然而今之政府果不失民心也耶?”(1911年10月13日)老百姓心中当然只会有一种答案,清廷丧权辱国,腐朽颓败,已处于民心伤尽无可挽救的危局!正因为民心伤尽,军心也随之而起剧变。陈冷血在《湖北革命记之九》中谈及:“由汴梁、郑州派往武昌之防兵1500名,火车至汉口,将下车,兵问统带将何往,答曰往攻武昌,兵均不肯下车,统带官不得已折而北,电告政府,仍令往,兵不肯,乃暂驻刘家庙。”(1911年10月18日)另外还报道南昌调鄂之兵,也皆不肯行。当时的统带官们之所以不敢强令,是怕激起兵变,搞不好连自己的命也不保。武昌之革命,不也是起于有革命思想之军人之“兵变”吗?包天笑在文中写到革命军的宣传攻势也非常奏效,有时对敌军用“攻心为上”之策。在《革命军战胜于口舌》中讲到革命军“以三数人,激昂奋励演说一场,而五六百之军队倒戈投顺,此其气象为何如乎?”(1911年10月22日)这说明民心丧失之后,其必然后果是“军心之叛离”。“军”就是穿上军装的老百姓,但能使一再被灌输反动教育的“军人”—用于保卫清廷的老本—也“叛”了,说明这是最彻底的民心叛离。包天笑进而更具鼓动性地以《英雄用武之日至矣》为题鼓呼道:“今日者,正英雄用武之日也。吾有志之少年,尚武之志士,平日握拳奋臂,慷慨激厉,今日奈何不起耶!”(1911年10月20日)
第三类的杂感指出“政府之不可恃”。北军无斗志,官员惶惶不可终日,清廷已到穷途末路。1911年10月14日和15日,在陈冷血的“湖北革命记之二、三”中报道:“武昌新军起,不及日而长沙陷,保定陷,荆州、宜昌、重庆,四处凡有新军之处,无一不响应。南京已有不安之象,若广州、若安徽已有陈迹可寻者,今必更岌岌。呜呼,政府已无尺寸之柄矣!”(1911年10月14日)他在文中用“摧枯拉朽”四字形容当时的形势。冷血在杂感中又写道:“官吏惶恐自扰,各将家眷迁移至上海,是地方未乱,而官先乱之也,尚能付之以保卫地方之重任耶?”(1911年10月15日)天笑则以《逃死不遑之官眷》为题,报道官眷纷纷迁避至上海。他又另用“逸话”的形式写《旗人之狼狈》:“旗人妇女到上海后,要伪装成汉族,就雇人梳汉族妇女之发髻,被索价每次二元;又某旅馆之旗人极力为其小女儿缠足(满人是不缠足的—引者注),哭声震邻屋不能安睡矣。”(1911年10月21日)无论是“杂感”还是“逸话”,都告诉老百姓,清廷、官吏、眷属都方寸已乱,正纷纷作鸟兽散。与之对比的是包天笑在“时评”中报道的武昌民间的秩序:“武昌城内,商民照常贸易,米价亦平。惟每人每日仅许籴米两升,不许多购。每米店派有党人两名监示员,而人民亦恪守其律。或曰各省办平粜,有此整齐否?”(1911年10月18日)这表明民气正处于上升期,百姓以实际行动拥戴革命。包天笑一再在“时评”中强调革命阵营之有条不紊:“兵工厂加倍工作,而铁厂暂停工,然工匠仍留厂中,每日发铜元十五枚。现方各处运粮,以济民食。《论语》云,‘足食矣,民信之矣’,《论语》固一部政书也。”(1911年10月19日)
从“民以食为天”这一点出发,陈、包时评第四类特别关心民生。包天笑在《勿停各细民工食》中提及:“闻各处以金融恐慌,商业停顿,于是令工人停工。夫工人日以数百文以糊口,一旦断其生机,是促之使乱,力顾大局,当以维持之。”(1911年10月17日)而陈、包二人在“时评”中也一再写道:“国家有变,各处土匪往往乘机思逞,最为心腹之患。各处人民为自保计,急宜自组织团练队,绅商士民各有身家,时哉弗可失也矣。”(1911年10月17日)在关心民众时,他们也指出:勿乱杀满人。正因为彼时处于革命之初,有不分对象乱杀现象,所以引起了国际上的议论。
他们二人多次谈及革命军之上下皆勇武。就士兵而言,包天笑在《革命军武勇谈(二)》中歌颂了英勇牺牲之战士:“革命军中有一健儿,身受创伤数处,踣不能起。邻近民家舁之归,为之裹创,血透衣数重,不能脱。妇人均为之感泣,壮士怡然曰:‘我死奚足恤,特汝曹当知我之死,为同胞流血而死,并非于一己有所图。他日君辈享自由幸福之日,或能一回想我辈今日斯可耳。’言已遂瞑。”(1911年10月30日)这是对战士的歌颂。而对当时初任首义临时大都督的黎元洪也加以颂赞,则表示革命军上下一心,增进了民间对革命的信任感。这可算是他们时评的第五类内容。有关黎元洪的报道,基本上符合实际。陈冷血写道:“黎元洪蓄志已十余年,决定以武汉为根据地,故久不去,极力曲事张彪而利用之。张彪以其恭顺,也一切倚畀之,故所练新军,任其布置……久之而其党徒布满各地,一举即可以号召。”(1911年10月16日)张彪是彼时武汉军队的第一把手,黎元洪则屈居其下。首义时张逃窜到军舰上,继续效忠于清廷。黎之军事才能实远高于张。张彪当时有“丫姑爷”之称。武汉的最高长官张之洞曾将其最得意的丫环嫁张彪,因此背景很硬。而黎元洪不仅出身于北洋水师学堂,还三次到日本考察学习陆军等有关新知。当时武汉新军的训练教材都由他主编,还曾制定中国陆军改革的第一部法规《湖北练兵要义(十条)》。在清朝的两次全国性秋操中,在对抗实战训练时,南洋军在他的指挥下,三次打败了由段祺瑞指挥的北洋军,因此名声大振,南方各地不少军事长官也都到湖北军队中来交流见习,他在军中的人脉甚广,对这次革命也大有裨益。陈冷血还在《黎元洪逸事》中介绍:“平时喜读书,能知天下大势。性沉毅 ,寡言语,爱才能。凡湖北将士不见容于张彪者,黎氏悉延揽之,以故湖北军界无不爱戴黎氏者。”(1911年10月16日)其中还有一则云:“有人问黎元洪,何以不毁拆京汉铁路,以绝北军?黎答,吾自要用,故不损毁。又问,武胜关最为险要,何不派兵扼守?黎答,彼守者,即我之人,何必派兵?”(1911年10月19日)这说明革命首义都督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亦能服众。此类宣传,有利于民间对武昌革命军的上下产生信任敬佩之心。
这九十多篇短论,陈冷血将它归之于一个结论—《大局已定》:“凤山炸矣,荫昌退矣,庆王病矣,袁世凯不出矣;长沙失矣,宜昌失矣,九江失矣,广州变矣,西安变矣,云南、四川无信矣,南京、杭州汹汹矣;陆军败矣,水军降矣;财政竭矣,无人,无财,无兵,无器。呜呼!唯有哭而已矣。”(1911年10月26日)实际上,在这二十天中,已有湖南、陕西、九江、山西、云南、南昌等六地宣布独立。
上海报纸的影响力,在当时虽然对北方的渗透力十分有限,还不能辐射全国,但在长江以南,却是相当可观的。除《时报》外,《申报》《新闻报》也有若干大力支持首义的言论,但不及陈冷血与包天笑的那么及时、密集和锐利了。当然,时局形势也是多变的,他们的九十多篇时评杂感,也并非每言必中,因为他们不是预言家,而是革命大局的鼓舞者,读后令人对革命前途之信心倍增,也使我们可以改正过去一贯的偏执—通俗作家的所有作品,均是软性的卿卿我我、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
二
通俗作家用时评杂感打了“头阵”,接着他们又连篇累牍地以小说和回忆录等形式反映武昌首义的历史功绩。包天笑、李涵秋和蔡东藩等通俗文学的重量级作家皆从多个角度反映首义的实况,与正史的记载形成了互动,丰富了读者对首义的感性认识。
包天笑曾打算以小说的形式写一部80万到100万字的民国开国史。这当然要从辛亥革命前后写起。后来只出版了一部10万字的《留芳记》,计划没有全部兑现,却将辛亥革命史实用历史小说的形式加以呈现。当时,包天笑非常欣赏友人曾朴所写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因思历史小说者,不同于历史也,也不同于传记也,最好与政治军事无关的人,用以贯串之,始见轻松俊逸。”[1]1当然他是羡慕曾朴启用了赛金花其人其事,将清末的一段政界史实用旁敲侧击的“有趣的琐闻逸事”串连起来,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这部历史小说的兴趣,一口气就销了五万部,但包久久未得一人可以担此串连重任。后来有人向他建议用梅兰芳,理由是“这孺子一定成名,现在已经声誉满京华,士大夫争相接纳,用他来贯串,比了《孽海花》中的赛金花,显见薰莸的不同”[1]1。意为更显高格。这就是《留芳记》中的“芳”字所指认的人物了。可是包天笑没有算计到赛金花背靠的政治人物是当朝状元与后来的驻外大使洪钧,梅兰芳与许多政治人物的关系就淡漠得多,平时他只能在堂会上与这些人物见个面、寒暄几句,因此,这个建议导致写辛亥事件前后的故事与梅氏脱节;梅兰芳之后与政界的关系也并不密切,因此,《留芳记》自然不会像《孽海花》那样轰动。但是抛开梅氏,包天笑写的首义若干重要的情节,基本符合历史事件的真相。如在第三回“天怒人怨九州易帜”中,他写道:
我今且说共进会中,就有好多实行家。他们在实行家中,又分出两派来:一派是暗杀派,手枪、炸弹便是他们的利器;另一派是运动派,那运动派专以运动军队,输入革命知识。因为共进会中两湖地方人很多……所以这一派占有势力。加着近几年来,一班从东洋留学回来的学生,提倡革命的人,如怒潮狂飙地卷来。大家知道赤手空拳无济于事,非有实力不可,数年来大好青年被清廷杀戮的也不知多少。最近广东黄花岗一役,死了72名青年志士。可是东起西伏,断臑胸还是此仆彼继,因此共进会以运动军队入手,比较的似为有利。[2]132
的确,武昌首义之所以会取得胜利,革命党与新军的联手是一大成功的关键;或者说,由于革命知识的传播使部分新军成了革命党人,二者已融而为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在辛亥革命中也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在肯定包天笑能正确点出革命致胜的原因之余,也应该指出包天笑笔下也确实存在描写不实之处:
俗语说得好,蛇无头而不行。革命军原想是拥戴第八镇统领张彪的,只是大家说这个顽固老东西千万要不得,便想起这位创造中华民国、厚德载福的黎元宋黎协统来。这时大家拥到黎元宋房间里,黎元宋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吓得躲在床底下只是发抖。却被一位姓方的唤做方伟,眼快先瞧见了,便道:“请出来,请出来!我们大家商量大事要紧。”黎元宋只得出来,大家说明革命军要举他为都督、群情爱戴的话。黎元宋起初不肯答应,说:“元宋德薄能鲜,鄂省军界伟人很多,怎么推戴到鄙人?”这时党人中有位姓张的唤做张振武,性情最为暴烈,他便取出手枪来道:“今天我们大家一致推戴黎公,要是黎公不允我们,那就对不起你老人家了!这是我们大众的意思,你若推辞,就是违反了大众的意思,就是怀着二心,所以今天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公举你为首领,一条路就是送了你的命。”黎元宋沉吟了半晌,说:“既承诸君爱戴,一定要我出去,可是要听我的号令。”即便说了许多军法上应遵守的话,如不得抢劫、奸淫以及捣毁教堂等等。总算大事粗定,便发令一面袭取了汉阳,一面占住了汉口镇。[2]133-134
小说中的黎元宋即黎元洪,他在武昌首义时被拥立为革命军的“都督”。他从清廷的高级军官转变为革命军首领,在跨出这一大步时当然会有思想斗争。至于“床下都督”是证据不实的丑化他的“民间故事”。包天笑听了此类传说信以为真,而且觉得在小说中描写这种细节也能吸引读者。晚年在香港写《钏影楼回忆录续编》时,包天笑还用很多篇幅写过《辛亥风云(一)》至《辛亥风云(四)》四篇回忆文章。他写道:“《留芳记》里所写的人,都不是真姓名,而是影射的,……写小说不免有夸张的地方,也不免有隐讳的地方,有的出以故作惊人之笔,有的发为奇异莫测之文。但是我现在所记述的不是小说,只不过把从前在朋友处听来曾写在《留芳记》上的,加以修正,平铺直叙的再记录一下而已。”[1]13对黎元洪的“床下都督”一事,大概也属故作惊人之笔或奇异莫测之文?
包天笑是从“大”处谈武昌首义的,如指涉共进会从发动军队入手等。但在李涵秋的小说中是从“小”处着手去反映辛亥革命的,他以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在革命时的不同思绪与态度,用“以小见大”的另一视角,去反映当时的大势。应该说,李涵秋对辛亥革命是有一定实感的,因为他在1905至1910年生活在武汉。当辛亥革命爆发时,虽然他已离开了武汉,但通过报纸上的报道,再加上他熟悉武汉地域的情况,二者叠加,他可以在内心绘出较为具体的画面。他在《广陵潮》和《侠凤奇缘》等长篇小说的情节中都嵌入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巨变。在《侠凤奇缘》中,他虽然也正面描写了辛亥革命发生当晚的情节,但写得过于简单,无异于新闻简报,全书的重心放在“奇缘”之上,也即以辛亥革命为背景,促成“侠”与“凤”的“奇缘”,因此不及《广陵潮》所反映的内容更有特色。《广陵潮》的特色在于它的视角与其他小说不同,它没有正面描写革命的经过,而是通过富绅伍晋芳一家的各色人等在辛亥革命中的不同经历呈现:伍晋芳当时是清廷的武汉警官,革命发生的当晚,一家人正在为伍的爱子小美子大庆周岁生日,宾客盈门,炮声一响,宾客纷纷星散。小美子的生母朱二小姐原是伍家的家庭教师,因与伍晋芳发生了暧昧关系,就生米煮成了熟饭。为了争宠,她折磨死了伍晋芳的另一爱妾小翠,还阻止伍晋芳的发妻从扬州跟伍晋芳到武汉来,以使她可以独占丈夫。炮声一响,社会大乱,她在暗求菩萨保佑时,忏悔意识也有所冒头:她想到小翠比她现在经历乱世更幸运,小翠安安稳稳地躺在坟墓里了,而被她阻拦在扬州的发妻三姑娘也舒舒服服地生活在那里。朱二小姐想着自己如能活着,将来一定要善待三姑娘。伍晋芳知道做警官很危险,因为当时与首义的新军对峙的就是警察,街上躺着许多被打死的警察尸体,于是想弃官逃回扬州。革命军开放城门的一瞬间,他们随大批逃难的百姓一起涌出城门,却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件,朱二小姐不留神一脱手,玉雪可爱、刚满周岁的小美子已被踩成了肉酱。失去爱子的朱二小姐痛不欲生,往长江里一纵,幸被家人拖住,才留得一命。这一情节恐怕是根据报纸报道设计的。《申报》1911年10月15日在新闻中载:“是日武昌各城门皆未启,文昌门于二点后开一小时,难民出城者颇多,革军告以尔等即在城中亦必不加伤害……”同时报道百姓涌出城门时发生了踩踏死伤事件。但李涵秋并没有停留在一个妇女的忏悔和一个家庭失子的悲哀上,他通过这个家庭塑造了一位为辛亥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富玉鸾的形象。富玉鸾本是一个官二代,也是一个富二代,他父亲曾是清廷的高官,病故后遗下丰厚的财产给妻儿。他母亲为他定下了与伍晋芳的女儿淑仪这门亲事。淑仪原与《广陵潮》中的主人公云麟青梅竹马,大家本也以为她与云麟是天生的一对。但算命先生拆散了这对未来稳稳成婚的爱侣,说云麟是三妻之命。伍晋芳的后母、一家之主的卜氏将淑仪另配给富玉鸾。富玉鸾得知其中的原委后,一心要促成云麟与淑仪的婚事,竟然违背母亲的意愿,去佛庙出家了。他向云麟表示,一个青年人就应该要有“血性”,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夺人所爱。同时他还读了《民约论》等许多新书,与专权的母亲对抗,讲起平等来,活活将他母亲气死了。之后他散尽家财,东渡到日本留学,启程前还在扬州史公祠里演讲,以唤醒国人。留日期间,他成了一位革命志士。回国到武汉密谋起义,却被奸人告密,逃回扬州,匆匆和等了他多年的淑仪结了婚。婚后三天,他就在扬州组织起义,告密的奸人也跟踪到了扬州,富玉鸾被捕。在审判时,富痛斥审问他的制台:“你是旗人,不配问咱!你问咱多少同党,除了你们一班满奴醉生梦死,不识高低,其余大约都是咱的同党。”当受酷刑时,“富玉鸾此时已经置生死于度外,咬牙忍受,并不作声。只见那血花飞溅,顿时成了一个血人,眼直口闭,刚剩得奄奄一息!”[3]641这真是他平时所说的“血性”与革命意志的高扬。富玉鸾受刑之后,在死囚牢里静待行刑日期,他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那便是淑仪的终身:“早知咱今日如此结局得快,又何苦生生的玷污了她?况且他同云大哥自幼何等亲密,这婚姻是十拿九稳,偏生走出咱这一个人,硬拆散了他们这比翼鸳鸯,这都是咱母亲的糊涂主意。”[3]678于是他真真切切地写了一封长信给淑仪,力劝她万不能为自己守节,云大哥是他至好,须得依然成全了他们这一段良缘。当这封信托人传出去后,他觉得诸事均已布置妥帖,转而萧然长叹:未审将来这东方病夫国究竟怎生个挽救?全然一片拯救祖国与苍生的博大胸怀。当他在狱中听到武昌首义成功时,只恨这身子羁缚在这里,不能助他们一臂之力。他期望江苏的同志能使南京光复,“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咱干的事正多着呢!转未可以一死塞责”[3]679。应该说,李涵秋笔下革命志士的形象还是写得非常光辉的。朱二小姐想的只是小我一己之私念,而家庭的另一成员却是眼光远大,想的是自己牺牲后东方病夫国何日得以复兴重光。李涵秋写他死在张勋之手:“玉鸾临刑时候,固然毫无畏惧。旁边观看的人,莫不壮其有胆,说:‘他真是英雄!’”[3]681作者在小说中多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撼动了多种类型人物的灵魂,如他还写了一脑袋忠君思想的何其甫演出了一幕为清廷假“殉节”的丑剧。
通俗演义史巨子蔡东藩从1916年到1926年编著了《历朝通俗演义》,书中记载了上自秦始皇下讫民国共二千一百六十六年的中国历史,用演义体裁,共十一部六百五十一万言,使中国二十四史的高文典册,变成通俗的历史故事,飞入了寻常百姓人家。其中他所写的《民国通俗演义》共一百二十回。但这部演义中反映武昌首义的篇幅只有一回多书,未免过于简略。全书开首第一句就是:“鄂军起义,各省响应,号召无数兵民,造成一个中华民国。”[4]1写武昌首义得到民间的拥戴,则是以作者个人的观感为主:“小子每忆起辛亥年间,一声霹雳,发响武昌,全国人士,奔走呼应,仿佛是痴狂的样儿。此时小子正寓居沪上,日夕与社会相接,无论绅界、学界、商界、工界,没一个不喜形于色,听得民军大胜,人人拍手,个个腾欢,偶然民军小挫,便都疾首蹙额,无限忧愁。”[4]1又写道:“老天总算做人美,偏早生了一个孙中山,又生了一个黎黄陂,并且生了一个袁项城,趁这清祚将绝的时候,要他们三人出来作主,干一番掀天动地的事业,把二百六七十年的清室江山,一古脑儿夺还,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一古脑儿扫清。”[4]1-2这就是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提纲挈领的开端。黎黄陂即黎元洪,湖北黄陂人;袁项城即袁世凯,河南项城人。那时对著名人物,往往用他们的籍贯作为尊称。现在人们对于孙中山与袁世凯的生平都是耳熟能详的,而对黎元洪,普通人大概就较为生疏了。但要论及武昌首义的历史,是跳不过曾经被孙中山称为“民国第一伟人”①萧致治:《黎元洪:功过参半的“民国第一伟人” 》,载2011年7月7日《南方都市报》。文中谈及“直到孙中山辞掉大总统后,1912年4月初,黎元洪邀请孙来武汉访问,并热情接待了孙中山。孙中山、胡汉民都非常肯定黎元洪的功劳,称赞他为‘民国第一伟人’”。1912年4月15日,上海《民立报》《时报》也报道了孙中山出席黎元洪举办盛大欢迎会,并发表了《共和与自由之真谛》的演说之事。的黎元洪的。
三
最早写黎元洪大半生生平的是扬州通俗作家贡少芹的《黎黄陂轶事》,此书于1916年9月由上海国华新记书局出版,又于1917年10月再版,从黎氏的“军官时期”写起,直写至他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时所取的态度与立场为止。
要论及武昌首义,就必须对被革命党人举为首任革命都督的黎元洪—历史转捩点上的关键性人物之一—给予公允的评价,这也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通俗文学作家贡少芹的《黎黄陂轶事》既然是第一本较为全面地反映黎元洪大半生生平的著作,我们也应该对它作一鉴定与评价。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军人家庭出身。幼年家贫,曾读过几年私塾。1883年考入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当时水师学堂中除少数中国籍教师如严复、萨镇冰外,很多课程都由外籍教师担任,他们用外语授课,学生当然都要懂得外语,因此黎元洪在校中熟谙英语,后曾在军中任外国教练的翻译。他成为都督和任副总统、总统时,每当接待外国记者或开记者招待会,常用汉英两种语言。他从水师学堂毕业后,在北洋水师服役七年,以定远轮二管轮(驾驶)职务参加甲午海战。舰毁,他因有自购救生衣,与风浪搏斗近十小时,才得以游到大连。后在两江总督张之洞麾下服役。因在督造炮台时工作出色,在筹建的时间、质量和费用上都令张之洞十分满意,得其赏识,被委为管带,相当于现在的营长。1896年随张之洞到武汉,参与湖北新军的建立。当时天津小站有袁世凯训练的新军,人称北洋军;武汉则有张之洞训练的新军,人称南洋新军。张曾三次派黎元洪等人到日本学习考察军事,因此,黎既懂水师,也具陆军方面的知识。南洋新军的训练教材都由他牵头编写,编者都署他的名字。后晋升至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是湖北新军的第二号人物。湖北新军的第一号人物即“丫姑爷”—张彪,此人在军事上的知识远逊于黎,但黎只能屈居于张彪之下。黎在军中治军甚严,但又能体恤士兵,平日就住在军营中,并不回家歇宿,亲自参加操练,也没有官架子,很得士兵的拥戴。对一些被捕的革命党人,他也能以保外就医等名义将他们保释出狱;发现军中存在革命党人时,他只让他们离开部队了事,因此颇得革命党人的好感。革命党人在密谋起义时,曾有过如起义成功,欲推黎元洪为起义后的首任都督之议,但也只是一种议论,并未作出决议。革命当天,黎听到工程兵起义(这是张彪管辖的部队,与他无关),他“自扫门前雪”,将自己率领的部队集中,不表态,静观事变的进展,只求本部不出什么“乱子”。此前当有外面的士兵来报告起义的消息时,他亲手枪杀了这位来报信的革命党人,可见他是个“中规中矩”的清廷高级军官,并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但求自保。但他也深知清廷的极端腐败。此前当立宪派在四川保路运动中与清廷作斗争时,黎也以军人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湖北铁路协会”,得到立宪改良派的好感,因此说他的政见具有改良色彩比较恰当。当他看到起义的势头不可遏制时,就令部队解散,让各人去自找“出路”。黎不像湖北的最高长官满人瑞澂和“丫姑爷”张彪那样逃上军舰继续与革命为敌,只是躲在下级亲信的家中。当革命党人与咨议局立宪派人开联席会讨论由谁出任首义都督时,有人提议黎元洪,这个提议其实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一是当时著名的革命领袖如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宋教仁尚在香港和上海等地,而武昌起义革命军人的最高军阶也不过相当于连排长,缺乏号召力;二是武汉的新军也不全是革命党人,要使大多数的军人参加这场巩固与继续革命的战斗,一定要有一个他们信得过的人,黎元洪一直以重德行、颇清廉的汉官形象出现,平日既受士兵拥戴,就能产生一定的“向心力”;三是起义一定要有一个知名的人物出面,才能对外界产生震撼力,一般军人出面,外界只会以为是一场“兵变”,容易被清军或武汉租界上的帝国主义军队镇压下去,而黎元洪是知名的高级军官,在全国性秋操中,曾受到过清廷的表彰,在军界中颇有好评,南方多省的军队都派人到武汉南洋军中来参观见习,因此,他在部队中人脉很广;四是他与武汉各租界当局的关系也较好,因为懂外语可与他们直接交流,平时打交道就多,所以可使各租界当局不出面干预,有保持中立的可能,革命不会受外国势力的讨伐;五是他懂军事,可在以后对清廷的战斗中发挥所长。在贡少芹的小说中归纳起来大致是以上几点。
过去,革命党人不过是在起义前密商时,曾提及他或许能胜任这一职务;而咨议局立宪派又由于他能参与保路运动,对他抱有好感,于是一致赞成这一提议。当探得黎躲藏的处所后,大家派代表去请他“出山”,可是黎元洪非常惶恐,他借口事关重大,自己又不是革命党人,不能担此重任,请另选贤能。当时他是被挟持和拥戴到革命指挥部去的。在指挥部前革命军人还夹道鼓掌欢迎他,可是他仍不同意出任,于是被软禁在指挥部内,三天中食不下咽,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与后来盛传他是“床下都督”颇有关系,但称革命党人请他出任时黎躲在床下发抖,毕竟是无法证实的“民间故事”。当革命党人贴出第一张安民布告时就叫他签名,他一再说:“莫害我,莫害我。”还是旁人在布告上代签了一个“黎”字。但这张布告却在民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力:一是群众围观布告,不识字的急切地请旁人念给他听,大家都拍手叫好,民心得到了安定;外国人也啧啧称奇—“想不到黎也是革命党”[5]。在他具名的布告内有保护侨民生命财产的内容,于是他们也严守中立。而那位不吃不喝的黎元洪还在紧张地盘算:一是他也不愿为清廷“殉节”,如他不出任,革命党人也决不会放过他,已经有人建议,将他杀了祭旗;二是如革命失败,他也要被清廷视为管理部队不力而判罪,再加上布告由他署名,他有口难辩,保不定还有灭族之灾;而当时革命军很快占领了汉阳与汉口,局面有了进一步起色。另外,去年在秋操时他也领教过北军的实力。正如冷血在“时评”栏的《黎元洪逸事》中所记的:“去年北军秋操,元洪亦预其间,归对人言,极诋北军之不足恃,其轻之已久矣。”(1911年10月16日)种种考量,如出任都督也有利于保存自己和家族的一面;他也知道当时人心所向,革命成功的希望也很大。因此,在做了三天“懦夫”之后,他以剪辫为开端,干脆剃了一个光头,有人说他像一尊罗汉,他第一次露出笑容说像“弥勒佛”,表示决心要拥护革命。于是到楼下去进行演说,表示支持革命。革命党为了坚定他的决心,10月17日,在阅马场召开盛大的祭天誓师大会,黎元洪身穿军装,佩军剑,骑高头大马,俨然以首义都督、民国元勋的姿态出现。从此他由过去的消极转为积极地参与军事斗争。可以这样说,孙中山是英雄造时势,黎元洪却是时势造英雄。黎任都督后的又一大功劳是策反了清廷海军总司令萨镇冰。当时武昌前线海军的炮火最厉害,使革命军和百姓大受损失。萨原是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师,他对黎在学习期间的表现印象很好。于是黎以学生的身份写信诚恳地劝萨反正,取得了成功,海军主力退出战场,大大减轻了革命军的压力。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黎由消极转变为积极态度的过程是较艰难的,但贡少芹的《黎黄陂轶事》却简单化地忽略了他转变的艰难过程。书中写革命党人要黎出任都督时,“黎踌躇曰:‘公等此举,吾亦深表同情,吾不敢遽应命者,每恐蹈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之覆辙,徒多戕同志生命耳。’”[5]14他又怕自己不是革命党人,无法调动一切,但“众曰:‘惟都督之命是听,有不服从者,都督纵能恕彼,吾侪不之宥也。”[5]14于是“黎颌之”[5]14。将一个清廷的高级军官转变为首义都督的过程处理得如此简单化,实际上有美化黎元洪之嫌。
袁世凯出山后倡导南北协议成功,选孙中山为总统,各省代表又选黎为副总统,兼领湖北都督及海陆军大元帅。但黎一直误认为袁世凯有“治世之才”,也有治理中国之实力,袁世凯也积极笼络他。黎又于1912年8月借袁世凯之手屠杀了首义的革命党人、令他胆战心惊的张振武,这是黎氏生平的一大劣迹。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张振武,小学教师出身,武昌首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人称武汉“三武”,即孙武、蒋翊武与张振武。他思想激进,胸无城府,敢说敢做。在黎元洪思想苦斗的三天中,张早已不耐烦,曾建议干脆杀了黎元洪。黎元洪就职都督之后,张振武带了六十名卫士,累闯都督府,如入无人之境,又常常出黎的洋相,让黎元洪下不了台。后来张携巨款到沪去购军械,黎检查后认为其中次品甚多,又觉账目不清,就查问张振武,张当面打桌子敲板凳地回答道:“你是我们拉你出来做都督的,你现在竟这样对我们,你不要搞错啊!”[5]14当时再加上张当时有若干极左言论,开口闭口在演说中称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第一句话还说明张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派,他对辛亥革命后的现实是不满的;至于要流万万人的血不止,就说明张可能会无限制地扩大革命对象。中国当时也只有“四万万同胞”,哪经得起如此杀戮?而更让黎元洪胆战心惊的是,他觉得张有此类言论,下一个革命对象必然是他,因此欲除掉张振武。此事在武汉不能下手,黎就借袁世凯之手,以封张为蒙古巡边使为名,将其诱到北京,同时通电袁世凯:
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噬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欲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4]109
袁世凯正当笼络黎元洪之时,更有电报为黎主动杀张的铁证,自己可毫不负杀首义革命党人的罪责,于是立抓立杀,两小时就解决此事。当有人闻讯赶来营救时,也只能抚尸大恸了。此事件使黎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革命党人数次掀起倒黎运动,但都未成功。于是一度以“黎菩萨”为诨名的黎元洪也被改称为“黎屠户”了。
当时,除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南北势力外,黎俨然成为中国中部的第三势力。在孙中山内阁中,武汉首义的党人无一人入阁,引起武汉部分革命党人的不满,他们联合立宪党人,建成共和党,推黎为党魁。而在以武汉还是以南京为首都的建都之争中,首义之地又未能入选。再加上黎、袁合谋杀革命党人,这一时期,黎倒向了袁世凯一边。但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贡少芹的《黎黄陂轶事》却为黎氏开脱,并不实事求是。贡在文中说:“赣宁二次革命,黄陂恐湖北糜烂,不得不依附中央。”[5]33又说杀张振武非黄陂主动,而是袁世凯“托词将任张、方重要责任,惟不知其品性与心术,其任用与否悉取于黄陂一语”[5]33。黎素嫉张、方嚣张,“不得不历述二人在鄂专横之历史,其意盖使项城不必重用也”[5]33。此类辩白,徒使一本尚有一定价值的传记的真实性大大受损。
黎元洪虽向袁世凯一边倾侧,但袁对这位非北洋嫡系的第三势力还是放心不下,想诱其入京而加以控制。但黎在湖北苦心经营近二十年了,他就是不肯离开这老根据地。最后,袁世凯命手下悍将段祺瑞亲自出马,“敦请”黎北上商议国是。黎不得不乘火车赴京。在火车上他听到袁世凯宣布任命段祺瑞为湖北都督,如五雷轰顶,知道此去必然凶多吉少。这也使黎由原以为袁有“治世之才”发展到对他的为人失去信赖。袁世凯迎黎下榻瀛台,这是慈禧幽禁光绪的场所,于是“湖北王”一变而为“瀛台囚”了。先有段祺瑞,后有段芝贵将黎的军队改编或迁散,从此黎成了光杆司令,老本输个精光。“黎菩萨”成了“泥菩萨”。可以说,他以后只能俯首于袁世凯之下,即使袁死后他虽继任了总统,也非得看各派军阀的脸色度日不可,虽数度有总统与副总统之虚衔,却几乎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不过在以后的岁月里,黎还有一生中最大的两个亮点,使他在中国现代史上,除首义都督角色之外,还能看出他对共和信念的坚定不移:一是袁世凯称帝时先是杨度来做说客,贡少芹写黎当时的回应:“吾所处的地位,为共和国副总统,若关于民国事宜,既承下问,吾可妄参末议,若涉范围以外,吾不愿与闻,言已,挥袖入。杨度等惭赧而退。”[5]67袁世凯封他为“武义亲王”,武义即武昌首义之意,并将“武义亲王府第”的匾额强挂在他大门上,黎命人摘下弃之一边。袁世凯定武义亲王的俸禄每月三万,袁屡送黎屡退。袁以为孙武是黎的亲信,由他送去也许黎能够接受。贡少芹写道:“黄陂曰:‘我想辛亥起义诸先烈耳,若辈不惜生命,换取共和。君与吾亦起义时之一份子,所幸生存世界,当继其未竟之志,若曰改变初衷,异日何以见诸先烈于地下乎?’孙武惭而去。”[5]69当梁士琦再来黎宅说项时,黎指着厅中的一石柱说:“你们如再逼我,我就撞死在这里。”[5]69梁士琦怕惹出大祸,连忙退出。在袁欲称帝时,黎借机愤然早早从瀛台迁出,住东厂胡同。总之,在袁世凯称帝时,黎元洪的表现为生平之一亮点。
袁世凯逝世后,黎即为大总统。当时段祺瑞为内阁总理。段刚愎自用,视总统为他的盖印机器,他的命令非借总统府之名发出不可,他何时想盖印,总统府要立刻按他的旨意办,引起了严重的所谓“府院之争”,也即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不和。段等以武力挟持总统,而无一兵一卒的黎元洪奈何他不得。此时,张勋忽然愿以调停人的身份入京斡旋,黎正走投无路之际,病急乱投医,请张勋只身来京。谁知张勋带了六千辫子军,会同康有为演了一出复辟的丑剧:“武圣”与“文圣”扶持十一岁的幼主溥仪坐上龙座,封黎元洪为一等公,并要他“奉还大政”。黎答道:“此应由国民公决,吾不能私相授受。”[5]95对授予一等公的答复是:“洪宪时代,武义亲王,尚薄而不为,乌能此时而受是项乱命乎?盖余在位则为公仆,退位则为公民,举所谓亲王、公爵者,俱不足以荧惑我也。”[5]95这就是黎元洪继在袁氏称帝时持反对态度之外的又一亮点—对张勋复辟他再次表示了仍坚持民国共和制立场。贡少芹还写了一段“黄陂欲枪击张勋”:黎“谓其夫人曰,张逆叛国,余为共和国元首,誓必手刃此贼,俟其来而歼之,苟杀彼,余必无生全希望,否则余亦必为彼所杀。言已,匆匆出,其夫人牵衣挽之,绝裾而去,盖黄陂本挟一不怕死决心,将待张至,拼牺牲此生命,与之激斗也”[5]93。但张勋并没有亲自来见他。这一段,其他各书都未见,仅为孤证,只能存疑。
黎晚年悉心履行“实业救国”的宗旨,亦有所贡献。但这已是《黎黄陂轶事》之后的事了。
贡少芹的《黎黄陂轶事》出版于1916年,1917年再版时,才加上张勋复辟之经过。在“绪论”中贡少芹写道:“不佞居鄂最久,关于黄陂之微事细行,耳闻目睹者,不可偻指,兹特表章出之。”[5]2在这本轶事中,他的确讲了许多黎黄陂值得人们尊敬的言行,但它的致命缺点是处处为黄陂的劣迹辩护,凡此是有违历史真实的。
冯天瑜、张笃勤所著的《辛亥首义史》中,有一段对黎氏的“平议”:“概言之,来自旧营垒的黎氏出任都督,在湖北军政府时期所发挥的效力,可以喻为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军政府的稳定与发展,这种效用是由革命党人出任都督所难以企及的;另一方面,又在与革命派角力之际,曾借袁世凯以自重,打击党人,消弭革命力量……综观全体,步履蹒跚,充满矛盾性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及民国建设中的积极贡献和消极作用也不可小视,然置于历史天平,作一总的权衡,堪称一位应予基本肯定的人物。”[6]这是辛亥革命百年祭时历史学家对黎氏的评价。对历史人物,应该给予公允的评价,既不能“美化”与“拔高”,也不能“丑化”与“矮化”。
[1]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
[2] 包天笑.留芳记[M]//范伯群.包天笑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3] 李涵秋.广陵潮[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4] 蔡东藩.民国通俗演义[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 贡少芹.黎黄陂轶事[M].上海:上海国华新记书局,1917.
[6] 冯天瑜,张笃勤.辛亥首义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341-342.
(责任编辑:石 娟)
“The First Uprising of Wuchang”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in the Works of Popular Writers: Part II of the “Rich Ore Theory” on the Social Life Mirrored in Popular Literature
FAN Boqun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ny popular writers turned out to be the fi 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s of newspapermen when the newspaper business burgeoned in China. The writers responded immediately to the First Uprising of Wuchang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hailed and encouraged the revolution with reviews and essays, which protected and contributed to the revolution. The writers ref l ected with literary forms such as novels and historical stories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held by various people toward the revolution during the time. They also attempted to comment on historical fi gures with biographies.
The First Uprising of Wuchang; popular literature; rich ore theory; news reviews and essays; full-length novels; historical stories and biographies
I206.6
A
1008-7931(2017)01-0002-11
10.16217/j.cnki.szxbsk.2017.01.001
2016-10-0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120)
范伯群(1931—),男,浙江湖州人,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
范伯群.通俗作家笔下的辛亥“武昌首义”—通俗文学映像社情百态“富矿论”系列之二[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34(1):2-12.
——武汉市武昌首义中学校本课程文化建设的探索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