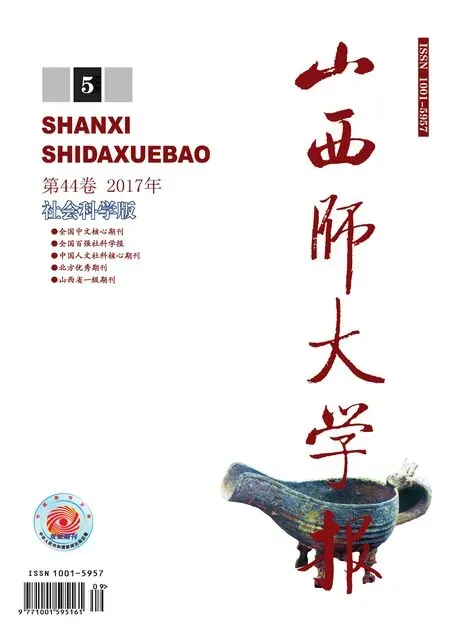张君劢政治哲学中的“民族国家本位”
欧 阳 询
(怀化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九一八事变”后,张君劢一直致力于构建一套完整的“建国方案”,它包括“修正的民主政治”“国家社会主义下之计划经济”与“文化政策”三个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套“建国方案”建基于“民族国家本位”的政治哲学之上。然而,张君劢所谓的“民族国家”具有多层涵义,且相互混杂,以致使得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面目模糊、聚讼不已。比如,台湾学者薛化元指出,“修正的民主政治”具有浓厚的极权主义倾向[1]154;大陆学者翁贺凯则认为,“修正的民主政治”并没有背离张君劢宪政民主的一贯立场[2]113。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厘清:一是对张君劢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三个概念进行语义学分析,从正面理解与诠释“民族国家本位”的真实意涵;二是对张君劢对中国传统“天下”观念和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批判进行反思性探究,从侧面考察和辨别“民族国家本位”的是非曲直。
一、“民族国家本位”的语义学分析
英文“nation”,既可译为“民族”,又可译为“国家”。同时,“民族”与“国家”还时常联缀成“民族国家”或“国家民族”,派生出更加丰富复杂的意涵。因之,当近代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作为舶来品输入到中国时,民族、国家等概念经常被混用。嗣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大力倡扬民族主义,他们不仅强调民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而且标举蕴含中华文化自信心的文化民族主义;但不可讳言的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高峰是在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受这一时代环境的影响,张君劢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精心构建了一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在内的建国方案,以作为“全国讨论政治出路的公共草案”。但惜乎张君劢与其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对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或国家民族)三个核心概念缺乏自觉的区分,比如他说:“民族之概念,是以种族为出发点,如条顿种、斯拉夫种、拉丁种,从其风俗语言上以定彼此之界限。”[3]19同时又说:“民族国家成立的要素有三:(一)言语;(二)风俗;(三)历史。”[4]在这里,“民族”与“民族国家”等同起来了。然则,张君劢笔下的“民族国家”又有着“民族建国”之义,“民族国家之成立,英法先头,而后德、意诸国继起”[4]即是明证。这无疑为判定张君劢是否属于文化决定论者,以及廓清其建国方案是否具有自由民族主义性质,笼罩了一层迷雾。
毋庸讳言,张君劢在20世纪30年代的所有著述中,有两处明确提及了民族与国家之别。《未完之国家哲学初稿》中写道:“国人或有解民族之义,视之与国家同,以为了解民族之意义,同时即了解国家之意义,而实误矣。民族者,同语言、同历史、同风俗之人种而已,学者名之曰自然概念,其地位与领土之为地理的因素等。国家云者,发号施令之主体,因其政策而能生死人民,故德人名之曰价值概念,意谓道德上善恶是非之标准存乎其中也。”[5]另外,《立国之道》第一编“国家民族本位”亦有着类似的意思表达。可见,民族属于观念文化范畴,国家因指涉主权与权益而属于政治范畴。但是,张君劢并未一直坚守这种立场、态度与观点,而常用文化层面上的民族概念指陈政治层面上的权益和利害。譬如,他说:“所谓民族就是同言语同历史、同风俗同利害的一部分人类,大家应当团结,对于外来侵略,应当防卫自己,保护自己。是所谓民族主义。”[6]“民族意识以全民族的利害为前提,拿全国的公法私法来维持他,有了公共的法制,公平适用于全国的人民,自然法治之观念重,对人之观念轻,其对外也,更有所谓举国一致之习惯。”[7]反之亦然,张君劢常用“国家”这一概念指陈或涵摄观念文化,“国家之特质在乎文化,是为精神方面之成绩,与衣食住之物质的利益大异”[8]。概言之,在张君劢那里,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混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张君劢把民族与国家两个词联缀成“民族国家”一词,必定使人产生晦暗不明、模棱两可之感。综合分析不同的语境,可以得出张君劢所谓的“民族国家”具有以下三种含义:其一,实指民族,如“民族国家成立的要素有三:(一)言语;(二)风俗;(三)历史”[4];其二,实指国家,如“十九世纪的一切制度建筑在人性善的基础上,共产党的一切制度建筑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关于共产党与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制度之同异,姑且无庸多说”[7];其三,指发轫于16世纪的民族建国运动,如“中世纪时代,欧洲人心目中所谓宇宙间之组织为天下而非国家,神圣罗马帝国与教皇统治全欧洲。至于民族国家观念则起于十六世纪之后,各国教会脱离教皇而独立,同时复有各国有本国语言、文学,各国有各国的政治与法律,民族间之争斗,因以开始”[9]。平心而论,在张君劢的20世纪30—40年代著述中,第三种含义占主导地位。
张君劢认为,西方的民族建国运动肇始于16世纪,并且在这一运动开始之前,早有一种新的政治运动,“如民约论、国民主权论、个人应该享有自由权利、政府应该得被治者之同意等议论,皆为此新运动之各种条目,求其在各个人自由独立之中能得一个完善的政治组织。”[3]20另外,民族建国运动的基本原则是“同语言、同风俗的一个民族,便应成立一个国家,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4]。为此,英、法、德等民族一方面务求文学、语言之独立,另一方面务求历史的共同利害和彰显历史荣光,以图形塑和确立各自的民族性。更有甚者,法、德等民族因世代相抗、常为劲敌,故“德人自知其为德人,并信日耳曼民族之优胜,法人自知其为法人,以为世界各民族,惟拉丁民族最强,民族思想所以充满国中者以此,而外人莫敢轻侮者以此”[10]。这就使得在民族建国运动中,民族语言、文学、历史被作为立国要素而得到推重。值得指出的是,英法两国与德国的做法截然有别:英法两国并未因推重民族性而视民族与国家为一物,从而把重心放在了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方面,走的是政治民族主义道路;德国却因民族建国异常艰难,“以民族精神为出发点,故其学者关于国家之定义,每以民族与国家联结为一”[11],如麦克司温德说:“国家者,由民族性之自觉的理性的动机中凝成之一体也。”[11]可见,德国走的是文化民族主义道路。
有学者指出,民族主义有两种范式:一是以英国、法国为代表,强调民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一是以德国为代表,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但说到底,“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互为表里,只是因各国情形不同,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12]如是,张君劢像调和英国与德国两种政治哲学一样,亦欲折衷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或者说折衷民族性与现代国家组织形式,诚如他所言:“种族(指民族精神——引者注)与政治上之基础(指国家机构——引者注),二者互为因果。有了种族的基础,政治机构易于成立;有了政治机构,种族的条件更能发展。因此二者相互之关系,于是演变而为民族国家。”[3]19从表面上看,张君劢似乎更强调现代国家组织形式,他在《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一文中阐述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八个特点,其中六个特点是关于现代政治、工商、军事等,另两个特点即“各国务求文学、语言之独立,于是各有其民族文学”与“科学哲学号为世界公器,而各国务求有贡献,故科学哲学方面,各民族亦各有其成绩”[4],则是关于民族性的。并且,他还明确指出:“今后民族建国,既然应该把重点放在国家二字上,……单单说民族建国,容易引人注意于民族二字,而忘却了国家行政改善之内容。”[3]21但实质上,他无论是阐发宪政,还是衡论军事,都更推重民族性和民族精神。
张君劢在《黑格尔之哲学系统及其国家哲学历史哲学》一文中说:宪法(宪政)作为一种外物,必待人民的自觉性先发达,而后乃能犹如有根之木,否则虽暂时种植在地面之上,不数日而葳萎而死。一言以蔽之,“宪法之保障,在于民族之总精神,即民族能自知自觉此宪法之必要者,则宪法乃能推行,宪法之为物,非若机器之可以一朝采办,实与民族之知识与道德,有不可离之关系矣。”[13]关于军事问题,张君劢指出,东北三省之沦亡,固然存在着军制、军器、军输等不如人的原因,但归根到底是由于民国政府不能团结一致,以及东北三省三千万民众丝毫不加抵抗,所以“与其说是外交上,军事上的失败,毋宁说是民族性的缺陷。在国家受重大压迫时,国民还是漠然无动,还是冥然罔觉,好像与自己毫无关系一样,这实在是国家观念未养成的缘故”[4]。由是观之,“民族性的缺陷”意指“国家观念未养成”,亦即是说,民族性主要是指国家观念。这无疑表明,中华民族在语言、文学、风俗、历史等方面并不缺乏民族性,但严重缺乏现代国家观念。现代国家观念,对内表现为“各份子立于平等之地位,且具有一体之自觉”[14],对外表现为“应停止内战,统一阵线,以临外敌”[14]。
如上所述,张君劢虽欲调和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民族性与现代国家组织形式,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更加推重民族性和民族精神。这似乎与他所强调的“民族建国”概念的重点相悖,如其所言:“谈到‘民族建国’四个字,我们应该将重点摆在国家二字上,知道国家的内容是什么?其基础又是什么?然后方可达到民族建国之目的。”[3]18为了有效地化解这一矛盾,张君劢把现代国家观念纳入民族性的内涵之中,并使现代国家观念成为“民族知识与道德”(国民性)的核心内容。这样一来,强调民族精神的文化民族主义与强调民约论的政治民族主义,便能和谐相处、融为一体。
二、对中国传统“天下”观念的批判
张君劢进一步指出,在促进中国国民养成国家观念的过程中,横亘着两大思想阻力。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其道德中,天下观念凌驾于国家观念之上,并抑制着国家观念的发展,诚如他所说:“最苦的就是我们旧道德中缺少国家观念,这问题为恢复旧道德的最大障碍,因为西方今日公民道德,皆与国家有不可离的关系。吾国既缺乏此点,故公民训练的学说,不能不借自外国,而非恢复固有。”[15]另一个制约中国国民养成国家观念的因素,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在《瑞金站在精神上防共第一线》一文中,他针对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严厉驳斥:“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必有多少相亲相爱的性情,然后能维持其生存,但有斗争而无亲爱,则父子不成父子,兄弟不成兄弟,夫妇不成夫妇,尚何民族国家之可言。”[6]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张君劢就开始展开了对“天下”观念的批判,这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等数篇文章中。仅从题旨来看就可见出:与天下观念相对的民族观念,亦即民族主义,是中华新民族性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立国与复兴的精神基础(心力)。而从内容上看,他对“天下”观念的批判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厘清“天下”观念与现代民族主义的本质差异。张君劢在《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一文中强调,中国一直不能成为近代国家,实误于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自表面言之,国人对于内外族之界限本已甚明,春秋之戎狄、晋末之五胡、辽金元清等,皆所谓外族而在排斥之列;但实质上,“春秋之所谓内外,其标准为文德非种族也……如是,华夷岂有定界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退为夷狄则夷狄之,此则姬姓汉族之晋所以变为夷狄,而南蛮之楚所以变而为中国也。”[8]这固然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但却不自知文德标准正是辨别本族与外族的大障碍。惟其如是,外族入主中夏时,常常利用此种心理,无不以服华服、习汉字、学诗书等手段,取得国人的同情,而国人甘为其顺民,拥戴其为天子。反之,若以“华夷之辨”中的文德标准衡诸现代欧洲,则欧洲各国的分疆而治全无意义,因为它们在正朔、衣冠、礼俗、文字四个方面无一不同;然而仍不免于此疆彼界,“可知除此四者外,别有其成为民族的国家之根据在,血统是也历史是也教育是也。”[8]举血统为例,犹太人入藉德国已逾数代,说德语,守德法,但德人却仍以外族视之;又如历史方面,英国人所推尊者为莎士比亚、克伦威尔,德国人所崇拜者为歌德、俾士麦,法国人所追忆者为伏尔泰、拿破仑,皆念念不忘其祖先的光荣历史,而非各成一国不可。一言以蔽之,“欧洲民族主义之本位,则血统而已历史而已。”[8]
其次,剖析“天下”观念的成因。张君劢指出,古代中国之所以产生“天下”观念并经久不衰,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客观的外在环境,二是儒、墨、道三家的大力倡扬。就客观的外在环境而言,古代中国的周边民族多属蛮夷,其文物制度粗陋落后,加之吾族对待邻封,又以宽大为怀,奉行“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文德标准;所以,数千年来,“养成民族意识之环境,缺然不备。吾国人民脑袋中充满者,乃‘天下’思想,而非民族思想。”[10]那么,儒、墨、道三家又是如何倡扬“天下”观念?张君劢认为,在春秋时期,明明有一百二十国的对立,而孔子心目中,却有牢不可破的正统观念——一个统一的天下。因此,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5季氏》)另外,《礼运》篇开宗明义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可见,这里面只有三个阶段:一是天下,二是家庭,三是个人,而唯独不提“国家”。至于墨家,其兼爱说虽与儒家的爱有差等说相对,然亦以“天下”为人类的最高理想,近于当今打破国家观念的世界主义,譬如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5兼爱中》)诚然,道家主张自然无为,有异于儒家、墨家的积极有为,但在“天下”观念方面,三家则是殊途同归。职是之故,我国古代“天下观念”极为发达,“我们可以说秦始皇统一的局面,未尝不是由于这种思想(指天下观念——引者注)深入人心,所以才能成功的。”[4]
最后,阐述“天下”观念的流毒。张君劢认为,“天下”观念的流毒既深且巨,不仅导致“吾族在历史中之演进,大异于欧洲之近代国家”,而且“此乃数十年改建新国之举,屡试而无成之总原因”。[8]具体而言,以“文德”为标准的“天下”观念,滋生了四个方面的危害:其一,唯以文德为标准,故国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表面上言之,似为吾族同化力强大,实则反令吾族受外族统治,而有亡于辽金元清之祸;其二,唯以文德为标准,外人供职于吾族者,直迎之而不拒,如金日石单仕于汉,马可波罗仕于元,戈登为常胜军司领,赫德为总税务司等;其三,唯以文德为标准,外族挟文化利器而至者,尤欢迎而不暇,文化主权遂而丧失,如利玛窦、南怀仁参与明朝改历,清朝钦天副监以用欧人为常例等;其四,唯以文德为标准,对于强悍之外族,只知服从不知抵抗,如吴三桂、洪承畴称臣于清,与当今民国官吏如郑孝胥、罗振玉之辈为伪满洲国、为日本奔走效劳。总之,“天下”观念对民族意识、民族自觉与民族建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三、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批判
如果说张君劢对中国传统“天下”观念的批判,主要是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对外关系方面;那么,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批判,便是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对内组织方面。从辩证法角度看,民族国家既要一致对外、武装抗敌,则其内部就必须齐心团结、犹如一人。为此,张君劢从军事方面告诫国人:“国家之对外作战也,必其全国之武力,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指挥统一,军纪严明,……虽然,此所云云者,惟统一之国家有之,岂所望于今日之中华民国哉?”[16]更有甚者,他基于“国家为一体之义”,做出了类似的比喻:“现代的国家,可以一个字来代表就是整个的,或说是有机的。有机的意义,就是说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政府是脑神经,人民是手足,二者须互相一贯,如是乃能成一国。”[15]需要指出的是,张君劢并不主张“独裁救国论”,相反,他在《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中还对这一论调进行过批判。他的根本旨趣是,在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基础上,让国家权力与民意同走一条路子,如其所言:“国家为一体之义,则欧洲各国不独公认,固已现之于事实,若法律上之人民主权说,若国会为民意之机关,若战时国民采对外一致之态度,非所谓‘一体’精神之至显者乎?国家之为性,其在对外之日,无所谓道德,然一国以内人民在法律前之平等,人人有生活之权利。”[5]
既然在张君劢看来,民族主义原则包括对外争取民族独立与对内建立现代民主政体、抗战与建国两个方面,并且它们互为前提、相辅相成;那么,他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展开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批判,就必将以这两个方面为标准。比如,关于阶级斗争对于中华民族一致对外所构成的严重威胁,他说道:“一部落、一国家专在内部从事于阶级斗争,则其精力只有消磨于内争之中,何有余力来图一部落一国家之生存。”[3]33又如,关于阶级斗争对于国内经济、政治建设所造成的重大危害,他指出:“持阶级说者,不以国家之立场,为革命第一目的,凡可以妨害生产,可以妨害治安,可以使政府不遑宁处者,无不尽力以为之。”[8]从表面上看,张君劢在批判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过程中,有时亦会用到阶级的“对立”“斗争”等词语;但仔细辨析后发现,他所谓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既不根源于社会生产方式或私有财产,也无法支配政治与意识形态两种上层建筑,更遑论像马克思一样主张“人类历史整个是一部斗争史”[3]33,故完全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那么,张君劢所谓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在《立国之道》中,他在驳斥恩格斯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观点时,明确说道:“纵令财产有废除之一日,但人与人间之争论不能因此而消灭,此吾人所敢断言。……然即令私有财产废除,而种种因财产问题而生之争端仍无法消灭。况财产问题之外,还有其他种种争端:如谋害、奸非、夫妇不睦、伪造文书、毁坏名誉、造谣生事、泄露机密、争夺政权等,此种种纠纷不全因财产而生,甚为明显。然此亦足使社会发生不安,非使用国家之强力不能解决。”[3]36由此观之,因财产问题而产生的争端,与私有财产废除与否无必然联系;另外,谋害、奸非、夫妇不睦等其他种种争端也“不全因财产而生”,所以张君劢毋宁称之为“因主观上、思想上之不同而起之争端”[3]36。不仅如此,他甚至把争夺政权的政治运动及其背后隐藏的经济利害,化约为主观思想的分歧。比如,一方面他主张,现代政党是从利害不同与意见不同中产生的,有的代表工商阶级,有的代表工人,这是利害的不同;有的主张根本改造,有的主张逐渐改良,这是意见的不同。[17]但另一方面,他却又说:“至于一种运动(指政治运动——引者注),当然遭遇反对,遭遇困难。人我之间,意见不同,必经过一种对立或仇视的状态,固然是意中之事。但所谓意见不同,我之所谓是,人家未必以为是;我之所谓恶,人家未必以为恶。这只是我所见到的地方,人家见不到,或者人家的思想不免于错误。”[18]正是因为张君劢把政党政治及其背后隐藏的经济利益化约为思想分歧、意见分歧,进而视同于谋害、奸非、夫妇不睦等日常生活争端,故此阶级分化与阶级对立在他那里并不具有根本性的、特殊性的意义。
在张君劢那里,包括经济、政治等在内的一切争端,既然被化约为主观思想问题,那么教育、教养便是解决一切争端的根本方式。同时,他像德国近代哲学家一样认“国家”为“真有”,反对马克思主义者认“阶级”为“真有”。因之,张君劢所谓的教育、教养,其根本旨趣与基本内容必以民族国家为本位。只有施行民族主义的教育、教养,才能对治经济、政治等争端问题,而不至演化为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阶级斗争。他如是说道:“民族复兴,先则须从教养入手,俾三万万九千万人民,咸认识其为中华民族之人民,乃当今根本问题。人民有教有养,民族情爱、民族知识乃能逐渐提高,其后乃由意志之统一,终则为行动之统一。如是则民族可以自存,国家可以独立矣。”[10]反过来说,在国家不履行其教养人民的责任下,人民不知道他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不具有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感,在他看来皆是情有可原的,一如其言:“管子说,‘仓廪足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人民有饭吃,自然知道要体面,自然不会为非作歹,他有饭吃,然后可以同他谈地方公益,谈爱国义务。”[19]显然易见,张君劢的先养后教思想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观念,但从根本上讲,它又是张君劢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题中之义。他曾指出,国家对于人民的教养,关乎社会公道,关乎人民自由平等发展,并且是阶级区别(基于知识技能)不至演化为阶级斗争的关键所在,“凡为一国之国民,除因其特别之知识技能而享有特别地位外,其谋生,其教育,务使其达于平等地位,则国中自无阶级斗争可言。此种民族主义,乃建立于社会公道之基础上。故吾人之国家社会主义,在一方面言之,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在他方面言之,以社会公道为基础的民族主义。”[14]简言之,张君劢的国家社会主义同时包含着两个方面,即个人的自由发展与整个国家结为一体。
四、结语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立场看,张君劢的“民族国家本位”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歧误:其一,他认为,始于16世纪的民族建国运动的根本动因是宗教革命,其他还有语言、政治等因素,举政治为例,“十六世纪以前,国王即位,一定要亲自到罗马去,受教皇的加冠,后来大家以为各有各的主权,为什么要到罗马去?为什么要受教皇的限制?这种局面,非打破不可。于是政治便脱离教皇而独立。”[4]然而,根据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可知宗教、语言与政治等因素最终决定于经济因素。列宁即曾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要求消灭生产资料、财产以及人口的分散状态,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诚如其所言:“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20]370其二,他认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是民族建国运动的大不幸,“即承认民族斗争,就是同一民族中,不论其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与贫无立锥之穷农,大家立于同等地位,来保护国家,如此一来,不啻将阶级斗争之说,完全取消。”[6]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族国家由于统治阶级的不同,而有着类型的差异:第一种类型是兴起于13世纪中叶至15世纪下半叶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第二种类型是兴起于17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第三种类型是无产阶级民族国家。无论哪一种类型,民族国家在实质上都有一个统治阶级,而在形式上则代表全民族。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后,虽会改变民族国家的阶级内容以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性质,但仍保留着它的形式。毛泽东在论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时,就曾强调:“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21]144
[1] 薛化元.民主宪政与民族主义的辩证发展[M].台北:稻乡出版社,1993.
[2] 翁贺凯.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3] 张君劢.政制与法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4] 张君劢.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J].再生,1934,(9).
[5] 张君劢.未完之国家哲学初稿[J].再生,1937,(5).
[6] 张君劢.瑞金站在精神上防共第一线[J].江西地方教育,1937,(67).
[7] 张君劢.亡国的小组主义[J].再生,1935,(3).
[8] 张君劢.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J].再生,1932,(4).
[9] 张君劢.中国新哲学之创造[J].宇宙(香港),1935,(8).
[10] 张君劢.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J].再生,1934,(6~7).
[11] 张君劢.未完之国家哲学初稿(四)——国家之性质[J].再生,1937,(8).
[12] 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J].历史研究,1995,(5).
[13] 张君劢.黑格尔之哲学系统及其国家哲学历史哲学[J].哲学评论,1933,(1).
[14] 张君劢.国家社会主义纲领[J].再生,1935,(1).
[15] 张君劢.民族复兴运动[J].再生,1933,(10).
[16] 张君劢.呜呼!不成国家[J].再生,1933,(9).
[17] 张君劢.论多党一党问题[J].再生(重庆),1940,(43).
[18] 张君劢.共产党变更方向与人类德性之觉悟[J].再生,1937,(9).
[19] 张君劢.如何提高大多数国民的人格[J].宇宙(香港),1935,(10).
[20]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