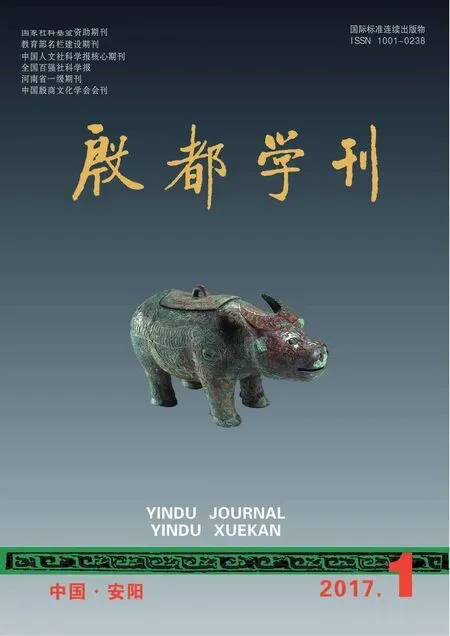殷墟大型族邑聚落墓地中墓葬陶器组合的比较研究
李贵昌,李 阳,孟小仲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 安阳 455000)
殷墟大型族邑聚落墓地中墓葬陶器组合的比较研究
李贵昌,李 阳,孟小仲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 安阳 455000)
目前殷墟遗址中大型族邑聚落墓地的资料是相当丰富的,有关这些墓地中随葬陶器组合资料的比较研究还是一个新的课题。本文就殷墟已公布的殷墟西区等5处大型族邑聚落墓地中随葬陶器组合资料进行了相对应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殷墟墓葬陶器组合中的主体器类和辅助器类中的主要器种在早晚期组合中的变化应是墓葬陶器组合变化的主线。觚、爵是殷墟墓葬陶器组合中的主体器类,豆、鬲、簋、盘、罐是殷墟墓葬陶器组合中辅助器类中的主要器种。各个族邑墓地中觚、爵始终是陶器组合的主体,而辅助器类中的主要器种在各墓地的不同期别的陶器组合中是有所不同和变化的,因而也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族邑组群特征。
殷墟;族邑聚落墓地;墓葬陶器组合
一、殷墟大型族邑聚落的发现概况
目前,殷墟发表的大型族邑墓地的资料已相当丰富。其中有1979年发表的殷墟西区(孝民屯村南、白家坟村西区域)大型族邑墓地的资料[1]、1998年发表的殷墟郭家庄村西南大型族邑墓地的资料[2]、2014年发表的殷墟大司空村村东南大型族邑墓地的资料[3]、2000年发掘的殷墟郭家湾新村大型族邑墓地的资料[4]、2015年发表的殷墟戚家庄村东南大型族邑墓地的资料[5]等等。这几处墓地资料反映出这些大型族邑墓地范围大、墓葬数量都在数百座以上,其中墓地中墓葬陶器组合的资料相当丰富,十分重要。
殷墟西区族邑墓地范围大,共发现殷代墓葬1003座、殷代车马坑5座。其中发掘殷代墓葬939座。西区报告的编写者将西区这一大型族邑墓地分为8个墓区。并认为“这八个不同墓区就是八个不同“族”的墓地”[6]。第一墓区位于西区墓地的东南部位,在白家坟村西南、梅园庄村正北约300米处,钻探面积21000平方米,发现殷代墓葬159座,发掘了144座。在这一墓区及其附近已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殷代夯土房基址、灰沟、灰坑等重要遗迹[7]。第二墓区位于西区墓地的东部,其东南和白家坟村邻近,在第一墓区正北约300米处,钻探面积1.7万平方米,发掘殷墓55座。其周围也是一处及居住、生产区、墓地于一处的族邑[8]。第三墓区位于西区墓地的东部偏北部位,具体在白家坟村西北、孝民屯村东南一带,正北距离洹水约200米,钻探面积11.25万平方米,发现殷代墓葬389座,发掘了369座,其中有四座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且M698墓道内有车马坑一个[9]。2000年春和2001年春在紧邻第三墓区的西北侧发现有大范围的殷代遗存。其中重要发现是殷代铸铜作坊遗址。铸铜作坊遗址紧靠洹河拐弯处。它是一处规模大、规格高、以生产礼器为主的铸铜作坊遗址[10]。第四墓区位于西区墓地的中北部位,第三墓区的西侧,孝民屯村东南一带。钻探面积3.5万平方米,发现殷代墓葬62座,发掘了60座。2003年4月至2004年5月,在第四墓区北侧发掘揭露了一批商代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址。同时发掘了商代晚期的铸铜遗址。这里是一处大型青铜器铸造场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推断该铸铜遗址以生产青铜礼器为主[11]。第五墓区位于孝民屯村东南一带,其西南和第四墓区毗邻。钻探面积2000平方米,发现殷代墓葬6座。第五墓区及其附近在后来2000年和2001年的发掘中发掘遗址面积达5000余平方米,其中发掘殷代灰坑55座、殷代墓葬241座(其中一座为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房基13座、车马坑2座和祭祀坑1座。还发掘了大面积的殷代铸铜作坊遗存[10]。第六墓区位于西区墓地的西北部位,在孝民屯村南,东侧和第四墓区相邻,钻探面积3.5万平方米,发现殷代墓葬151座,发掘了145座。该墓区北侧与铸铜遗址及工匠居住遗址相邻。第七墓区位于西区墓地中偏南部,白家坟村正西。该墓区分南北两区,相距约100米。钻探面积6.4万平方米,发现殷代墓葬124座,发掘了105座。第七墓区一带已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殷代夯土房基址、灰沟、灰坑、小墓、带墓道大墓和车马葬等。第八墓区位于西区墓地最西部,原北辛庄村东南一带。钻探面积1.16万平方米,发现殷代墓葬58座,发掘了55座。之前于1959年首次在北辛庄村南发现并发掘出殷代居住遗址和骨料坑,后又于2004年、2005年在这一带发掘制骨作坊遗址、殷代大墓3座及车马坑8座。以上资料说明殷墟西区这8个墓区及其周围一带在殷商时期就是集居住、手工业生产和丧葬于一体的8个大型的族邑聚落。
殷墟郭家庄村西南大型族邑墓地。这块墓地位于村西、南侧。这次钻探面积在5万平方米左右,发现并发掘殷代墓葬184座,其中1座是带墓道的墓;另外还发掘车马坑4座,马坑2座,羊坑1座。该墓地西侧和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遗址紧邻,其北侧和铁三路制骨作坊[12]相接。郭家庄村西、北一带应是一处集居住、生产和丧葬于一体的族邑聚落。
殷墟大司空村东南大型族邑墓地。这块墓地历经发掘10余次,至2004年初步统计:勘探面积约数10万平方米;发掘遗址面积23800平方米,其中发掘房址56座,发掘灰坑、窖穴、水井504个,发掘瓮棺葬100多座,发掘圆形祭祀坑1座,发现铸铜和制骨作坊各1处;共发掘殷代墓葬1525座,其中带墓道大墓4座;发掘车马坑5座。大司空村东南一带是殷墟遗址中在洹水北岸的一处集居住、手工业生产[13]和丧葬于一体的大型族邑聚落。
殷墟郭家湾新村大型族邑墓地。该墓地位于安阳机场南路路北地段,在大司空村墓地的东侧。2000年对该地段进行了文物普探,钻探面积6.455万平方米。这次发掘商代大型道路一条、房址10余座、灰坑窖穴65座、水井3眼;祭祀遗存3处。共发掘殷代墓葬379座,可以分期的墓中,一至四期都有,以四期墓葬居多。郭家湾新村一带是一处集居住生活和丧葬于一体的大型族邑聚落。
殷墟戚家庄村东南大型族邑墓地。该墓地位于殷墟范围的西南边缘区域。1981—1984年对该地点进行了文物普探,钻探面积约6.7万平方米。发掘探方136平方米,发现有商代的灰坑、窖穴、房址、柱洞等生活居住遗存(后于1999年在此处南侧还发掘1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殷代墓葬192座。戚家庄村东南一带是一处集居住生活和丧葬于一体的大型族邑聚落。
以上仅是殷墟遗址中到目前为止所报道的10余处相对比较完整的大型族邑聚落的资料(图1)。当然,殷墟遗址中的族邑聚落的资料远不止这几处。其他地点族邑聚落的相关资料,相对比较零散和不完整,这里对这些资料暂不进行讨论。
二、各处大型族邑墓地中墓葬陶器组合的要点
以上殷墟西区7个墓区的(西区第五墓区除外)墓葬陶器组合的资料和郭家庄村西南、大司空村东南、郭家湾新村、戚家庄村东南等11个墓区的墓葬陶器组合的资料是全面和完整的。殷墟西区发掘报告中,已将7个墓区中的墓葬陶器组合的特点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14](P114)。为有利于下文中各墓区墓葬陶器组合特点的相应比较,我们特将西区报告中的7个墓区墓葬陶器组合的简要情况择录如下:
第一墓区:有陶容器的墓105座。中间没有第一期的墓,二期的墓13座,三期的墓31座,四期的墓61座。前期有觚爵的墓的组合是觚爵豆鬲,觚爵豆簋或觚爵簋。无觚爵的墓的组合是单鬲,单簋或鬲豆簋。后期的组合是觚爵盘,觚爵盘罐或觚爵盘罐簋,无觚爵的墓是单盘,单簋或盘或簋与其它器物的组合。后期极少用鬲。

图1 殷墟西区等十二处族邑聚落墓地分布示意图
第二墓区:有陶容器的墓47座。中间没有第一期的墓,二期的墓13座,三期的墓16座,四期的墓16座。前期以觚爵簋为主。无觚爵的墓为单豆,单鬲或鬲豆簋。后期为觚爵盘簋或觚爵盘罐簋,不出觚爵的墓极少。
第三墓区:有陶容器的墓270座。中间没有第一期的墓,二期的墓36座,三期的墓78座,四期的墓147座。前期以觚爵、觚爵豆和觚爵簋为主。无觚爵的墓出单鬲,单豆,单簋;几乎不见有两件共出的。后期以觚爵盘,觚爵鬲和觚爵盘罐为主,无觚爵的墓出大量的单鬲和单盘,还有一部分是鬲或盘加罐或簋或豆等。这一墓区出鬲特别多,共有86件。
第四墓区:有陶容器的墓48座。中间没有第一期的墓,二期的墓3座,三期的墓5座,四期的墓40座。前期的墓极少。后期以觚爵盘鬲或觚爵盘簋鬲为主,无觚爵的墓以盘为主,再配以簋或鬲或罐。
第六墓区:有陶容器的墓106座。中间没有第一期的墓,二期的墓4座,三期的墓21座,四期的墓81座。前期多数墓的组合是觚爵豆,无觚爵的墓出单鬲或单豆,无两件共出的。后期为觚爵,觚爵盘或单觚,单爵与其它器物的组合,无觚爵的墓多数出单鬲,或鬲与其它器物的组合。
第七墓区:有陶容器的墓74座。中间没有第一期的墓,二期的墓4座,三期的墓30座,四期的墓40座。前期以觚爵豆为主,无觚爵的墓出单簋,单豆或簋豆组合。后期出觚爵盘或觚爵盘鬲,不出觚爵的墓以出单盘,单鬲或单簋为多。
第八墓区:有陶容器的墓51座。中间没有第一期的墓,二期的墓1座,三期的墓5座,四期的墓45座。前期墓较少,但都是出觚爵的墓。后期以觚爵盘,觚爵盘罐为主,Ⅸ式觚除一墓外,,都不与爵共出。无觚爵的墓为簋盘与其它器物的组合。这一墓地只出一件鬲。(以上西区7个墓区中的“前期”代表殷墟二、三期,“后期” 代表殷墟四期)[14](P113)。
殷墟郭家庄村西南族邑墓地。有陶容器的墓125座。这中间没有第一期的墓,第二期的墓10座,第三期的墓50座,第四期早段的墓35座,第四期晚段的墓30座。二期墓中陶器组合流行觚爵豆,觚爵簋和觚爵的组合。三期墓中陶器组合流行觚爵簋,觚爵豆,觚爵豆簋和觚爵盘的组合。组合中除觚爵外,簋的数量最大,豆、盘占较多的数量。这一期组合中盘的大量出现,是该期组合的突出特点。四期早段墓葬中陶器组合流行觚爵盘,觚爵盘簋和觚爵簋的组合。这一期含盘组合的墓葬数量猛增,含豆组合的墓葬仅有2座,觚爵盘配以小罐小壶小罍组合的墓出现5座。四期晚段墓中陶器组合流行觚爵盘,单盘和觚爵盘再辅以其它器类的组合。组合中含盘的墓19座,占该期段墓葬数量的63%还多。以觚爵盘小罐小壶小罍为组合的墓出现7座。
大司空村东南族邑墓地。有陶容器的墓187座。第一期的墓7座,第二期的墓41座,第三期的墓38座,第四期早段的墓42座,第四期晚段的墓59座。一期墓中陶器组合流行单鬲,单豆的形式。二期墓中陶器组合流行单豆,觚爵簋罐,觚爵,觚爵豆,单鬲的组合。该期组合中以单件器物形式出现的墓20座,占该期墓葬总数的近50%。其中有9座墓组合以单豆形式出现,有7座墓是豆、簋与其它器类的组合。罐、鬲在组合中占一定数量。3座墓葬陶器组合中出现瓿。三期墓葬中陶器组合流行单豆,觚爵,觚爵豆,单鬲的组合。觚爵簋再辅以其它器类组合的墓葬有10座。组合中含簋的墓葬有18座、含豆的墓葬有12座。3座墓葬陶器组合中出现尊。盘在4座墓葬陶器组合中出现。四期早段墓葬陶器组合中流行觚爵豆簋,簋罐,簋罍,单罍,单鬲的组合。觚爵簋再辅以其它器类组合的墓葬有8座。7座墓葬陶器组合中出现尊。5座墓葬陶器组合中出现盘。四期晚段墓葬中陶器组合流行觚爵盘簋罐,觚爵盘罐,觚爵簋尊,觚爵盘,单簋的组合。豆仅在1座墓葬陶器组合中出现。簋在37座墓葬陶器组合中出现。罐在32座墓葬陶器组合中出现。鬲仅在9座墓葬陶器组合中出现。盘在28座墓葬陶器组合中出现。6座墓葬陶器组合中出现尊。
殷墟郭家湾新村族邑墓地。有陶容器的墓201座。第一期的墓2座,第二期的墓55座,第三期的墓59座,第四期的墓85座。一期墓葬仅两座,陶器组合分别是单鬲,单豆。二期墓中陶器组合流行单豆,觚爵豆,觚爵,单鬲的组合。该期组合中以单件器物形式出现的墓26座,占该期墓葬总数的52%还多。其中有21座墓组合以单豆形式出现,另有3座墓是单鬲、2座墓是单簋的形式。觚爵豆与其它器类组合的墓有5座。簋与其它器类组合的墓有7座。该期组合的主要特点是有豆组合的墓达39座。三期墓中陶器组合流行单豆,觚爵豆的组合。其中有单豆组合的墓22座,觚爵豆组合的墓也有22座,有簋组合的墓7座。四期墓中陶器组合流行单鬲,觚爵盘,觚爵,单簋,觚爵鬲,觚爵簋,觚爵簋罐,簋鬲罐的组合。其中有单鬲组合的墓12座,觚爵盘组合的墓有10座,觚爵组合的墓8座,单簋组合的墓8座,觚爵鬲组合的墓葬6座。觚爵簋鬲辅以其它器类组合的墓7座。该期有豆组合的墓仅6座。
戚家庄村东南族邑墓地。其中有陶容器的墓134座。这中间没有第一期的墓,第二期的墓13座,第三期的墓28座,第四期早段的墓44座,第四期晚段的墓49座。这里二期墓中陶器组合流行觚爵豆,觚爵的组合。这一时期陶器组合中出现了两组带盘的组合。三期墓中陶器组合流行觚爵豆簋,觚爵盘簋,觚爵豆,觚爵的组合。这一期有10座墓葬陶器组合中出现了盘,占该期墓葬数量的32%。四期早段墓中陶器组合流行觚爵盘,觚爵盘簋,觚爵盘罐。另有觚爵,单盘组合的墓各有两座。觚爵盘组合是这一时段组合的突出特点,占该期段墓葬数量的52%还多。这一期段的墓葬数量总共44座,组合中有盘的就占40座。四期早段的墓葬组合中除大量使用觚、爵、盘外,罐的数量是其次(9座墓出罐),簋仅有7座墓出。四期晚段墓中陶器组合流行觚爵盘,觚爵盘罐,单盘。另有觚爵盘簋,觚爵组合的墓各有两座。觚爵盘组合仍是这一时段组合的突出特点,占该期段墓葬数量的57%还多。这一期段的墓葬数量总共49座,有盘的就占47座,而簋在墓葬组合中只有四座墓中出现。
三、 各区域族邑墓地中墓葬陶器组合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以上介绍的这11处族邑聚落的墓地情况,从地望上看,它们相对比较集中地分布在殷墟遗址的3个片区。即殷墟西区第一至第八墓区分布在殷墟西部区域,郭家庄村西南墓地及戚家庄村东南墓地则分布在殷墟南部区域的东南和西南部位,大司空村东南墓地和郭家塆新村墓地则处在殷虚洹水北岸的东北部位。下面就这三个区域墓地中墓葬陶器组合的特色及其相同点和不同点作一比较说明。
西区墓地中的7个墓区(第五墓区除外),我们分作三组较邻近的墓区进行相互比较。它们是第一和第七墓区,第二和第三墓区,第四、六、八墓区。
第一墓区和第七墓区:
第一墓区:二期流行觚爵豆鬲、觚爵豆鬲簋、觚爵簋的组合。无觚爵的组合是豆和簋罐鬲等炊食器种的组合。三期流行觚爵豆簋、觚爵簋的组合。无觚爵的组合是单簋、单鬲的组合。四期流行觚爵盘、觚爵盘罐的组合,觚爵盘簋配以小罐小壶的组合出现9组。无觚爵的组合是单爵、单簋、单盘的组合及簋和罐罍鬲豆等炊食器种的组合。该墓区四期中单爵组合的出现是一个特例。
第七墓区:二期流行觚爵豆的组合。三期仍流行觚爵豆的组合;无觚爵的组合是单簋、单豆、单鬲和豆簋的组合。四期主要流行觚爵盘的组合,觚爵豆盘、觚爵的组合也出现多组。
以上两个墓区墓葬陶器组合的相同点是:
1.二期组合中均以觚爵豆为其陶器组合中的突出点。2.三期组合中无觚爵的组合均多见单簋、单鬲的组合。3.四期组合中均流行觚爵盘的组合。
主要不同点是:1.第一墓区二期中无觚爵组合的墓较多,而第七墓区中则没有。2.第一墓区中四期觚爵盘罐的组合较突出,且觚爵盘簋配以小罐小壶的组合出现9组,单件器物组合尤其是单爵组合出现4组,这几点显然和第七墓区四期陶器组合的特点不同。以上两个墓区墓葬陶器组合存在着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但自身早晚陶器组合的变化还是连贯的和自成体系的。很明显第一墓区中,二期流行的觚爵豆鬲、觚爵豆鬲簋、觚爵簋的组合和三期流行的觚爵豆簋、觚爵簋的组合是基本相同连贯的,第四期陶器组合中流行的觚爵盘、觚爵盘罐的组合中盘罐取代了前期组合中豆簋的位置,这是晚期墓葬陶器组合的重要现象。第七墓区中,二期流行的觚爵豆的组合在三期中这一组合更加盛行。到了第四期陶器组合中觚爵盘组合是主流,很明显组合中盘取代了前期组合中豆的位置,豆在这一期组合中不见。这是晚期墓葬陶器组合的一个特点。
第二墓区和第三墓区:
第二墓区:二期主要流行单豆、单鬲的组合。三期以觚爵簋组合为主。无觚爵的墓为单豆,单鬲或鬲豆簋的组合。四期流行觚爵盘簋或觚爵盘罐簋的组合,组合中不出觚爵的墓极少。
第三墓区:二期主要流行觚爵豆和觚爵的组合,无觚爵的墓流行单鬲,单豆的组合;三期主要流行觚爵豆、觚爵、觚爵簋、觚爵鬲的组合,无觚爵的墓主要流行单豆,单鬲或单簋的组合。四期主要流行觚爵盘、觚爵鬲、觚爵盘罐、觚爵、觚爵盘罐鬲、觚爵盘鬲的组合,无觚爵的墓流行单鬲、单盘、单簋及盘和其它炊食器的组合,觚爵盘簋配以小罐小壶的组合出现8组。
以上两个墓区墓葬陶器组合的相同点是:
1.二期组合中两个墓区均流行无觚爵的单鬲、单豆的组合。2.第二墓区中三期组合中以觚爵簋为主,而第三墓区三期组合中的主流也有觚爵簋组合的成分;两墓区三期组合中均流行单豆,单鬲的组合。
主要不同点是:1.第二墓区二期有觚爵组合的墓葬仅有一座,而第三墓区二期有觚爵组合的墓葬却占该期墓葬总数的七成以上。2.第三墓区三期中主要流行觚爵豆、觚爵的组合,而第二墓区三期中却主要流行觚爵簋的组合。3.两墓区四期组合中,第二墓区有觚爵盘的组合中往往辅助以罐簋等器类,而第三墓区有觚爵盘的组合中往往辅助以罐鬲等器类。第二墓区四期组合中无觚爵组合的墓极少,而第三墓区四期组合中无觚爵组合的墓却占去一定数量。
以上两个墓区墓葬陶器组合存在着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但其自身早晚陶器组合的变化还是有连贯性的和自成体系的。很明显第二墓区中,二期流行的无觚爵的单豆、单鬲组合在三期仍然延续流行。而三期中流行的觚爵簋组合在第四期陶器组合中仍被沿用,只是组合中增加了盘罐等器种。第三墓区中的组合前后期的连贯也很明显。二期主要流行觚爵豆和觚爵的组合,无觚爵的墓流行单鬲,单豆的组合,在三期中这些主流组合全被沿用。到了第四期,盘、罐、鬲在组合中取代了豆,该期主流组合变成了以觚爵盘、觚爵鬲、觚爵盘罐、觚爵的组合。其中觚爵的组合仍被沿用。该期无觚爵的组合单鬲、单盘、单簋是主流。该期中单盘、单簋取代了前期的单豆。可以看出以上两个墓区中各自前后期陶器组合的变化是连贯和衔接的。
第四、第六和第八墓区:
第四墓区:二期流行觚爵豆的组合。三期流行觚爵豆鬲、觚爵鬲的组合;无觚爵的墓则为单豆、单鬲、单簋的组合。四期流行觚爵盘鬲、觚爵盘罐的组合,其它组合中几乎都有觚爵;无觚爵的墓是单盘、单鬲、单罐的组合;这一期出现两组单爵组合的墓葬,还出现一组与仿铜陶礼器组合的墓葬。
第六墓区:二期流行觚爵豆和单豆的组合。三期流行觚爵豆、觚爵的组合;无觚爵的墓则为单豆、单鬲的组合。四期流行觚爵盘罐、觚爵、觚爵盘的组合;另外单爵、觚盘、单鬲的组合在这一期组合中也比较突出。
第八墓区:二期仅一座墓即觚爵罐簋的组合。三期流行觚爵豆、觚爵豆罍的组合。四期主要流行觚爵盘罐的组合,另觚爵盘、觚爵盘罐簋的组合也比较突出;仿铜陶器配以其他器种的组合有两组,小陶罐小陶壶配以其他器种的组合有三组。
以上3个墓区墓葬陶器组合的相同点是:
1.第四、六墓区二期组合中均流行觚爵豆的组合。2.3个墓区中三期组合中均以觚爵豆组合为主,无觚爵的组合四、六墓区均流行单豆、单鬲的组合。3.三个墓区的四期组合中均以觚爵盘罐组合最为流行。三个墓区的四期组合中均出现多组仿铜陶器或小罐小壶配以其他器种的组合。4.第四、六墓区四期中出现单爵、觚盘、单觚的组合多组。尤其是第六墓区四期中的单爵组合达十余组、觚盘组合达七组。这和第八墓区中“Ⅸ式觚除一墓外,都不于爵同出”[14](P114)的现象相类似。即觚爵在组合中不同出。
主要不同点是:1.第六墓区二期流行单豆组合的形式,四、八两个墓区二期组合中却没有出现。2.第六墓区三期中单豆(5组)、单鬲(5组)、觚爵(4组)组合最为流行,而第八墓区三期中仅出现有觚爵组合的墓葬一座,第四墓区三期中仅出现有单豆、单鬲组合的墓葬各一座。
以上3个墓区墓葬陶器组合存在着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但各自早晚陶器组合的变化还是有连贯性的和自成体系的。比如第六墓区。该区中第三期流行的单豆和觚爵豆组合和第二期主流组合相同,明显是前后连续的,第四期组合主流中的觚爵组合和第三期组合主流中的觚爵组合是一脉相成的。而该期中最流行的觚爵盘罐组合和前期(三期)中觚爵豆组合相交接,只是后期组合中的盘罐取代了前期组合中的豆。当然,第六墓区四期中出现单爵单觚和第八墓区出现单觚的现象仅仅是一个特例。整体说,第六墓区前后期陶器组合的情况是连贯自成体系的。
郭家庄村西南族墓地和戚家庄村东南族墓地。
郭家庄村西南族墓地没有一期墓葬。豆、簋在二期陶器组合中份量很重。三期中除有觚、爵组合的墓葬外,有簋组合的墓葬数量最多,有豆组合的墓葬占一定数量,盘在组合中大量出现。四期早段主要流行觚爵盘簋、觚爵盘、觚爵簋的组合。除有觚爵组合的墓葬外,有簋组合的墓葬数量最多,有盘组合的墓葬占一定数量,有豆组合的墓葬已经很少,含小罐小壶小罍组合的墓开始出现。四期晚段盘在组合中占据主导地位,簋有少量出现,豆已经不见,含小罐小壶小罍组合的墓增多。
戚家庄村东南族邑墓地没有一期墓葬。二期墓葬中陶器组合流行觚爵豆、觚爵簋的组合,组合中出现了盘。三期组合中除觚爵外,含豆、含簋的组合最多,觚爵豆,觚爵簋的组合仍然流行。含盘组合的墓葬数量仅次于含豆含簋组合的墓葬数量。四期早段觚爵盘和觚爵盘辅以其它器种的墓葬组合数量占该期墓葬数量的90%以上。该期主要流行觚爵盘的组合。罐在组合中占一定数量,簋、豆在组合中数量骤减。四期晚段盘在组合中占据绝对地位,觚爵盘和觚爵盘辅以其它器类的组合仍是该期段组合的主流。仅有4座墓葬组合中有簋,豆在墓葬组合中消失。
郭家庄村西南族邑墓地和戚家庄村东南族邑墓地墓葬陶器组合的相同点是:
1.两处墓地均没有殷墟一期的墓葬,二期墓葬陶器组合中均流行觚爵豆、觚爵簋的组合。2.两处墓地三期组合中除觚爵外,含豆、含簋的组合最多,觚爵豆、觚爵簋的组合仍然流行。含盘墓葬组合的数量仅次于含豆、含簋墓葬组合的数量。3.两处墓地四期组合中带觚爵或带盘组合的墓葬数量均较大。郭家庄村西南族邑墓地中带觚爵组合的墓占比为72%,带盘组合的墓占比为51%;戚家庄村东南族邑墓地带觚爵组合的墓占比为90%,带盘组合的墓占比为94%。4.两处墓地四期组合中均出现了多组带小罐小壶小罍的组合。
不同点是:1.戚家庄村东南族邑墓地墓葬组合中二期就出现了带盘的组合。
以上可看出,郭家庄村西南族邑墓地和戚家庄村东南族邑墓地墓葬陶器组合除两处墓地二期中主流组合相同外,三、四期组合中的盘在两处墓地墓葬陶器组合中均占有大宗。这是两处墓地在墓地陶器组合上的一大相同点和突出点。
大司空村东南族邑墓地和郭家湾新村族邑墓地。
大司空村东南族邑墓地有一期墓葬7座,均为单鬲、单豆的组合。二期墓葬陶器组合中单件器物组合仍占主流,单豆、单鬲组合仍然流行。组合中含簋或含豆组合的墓葬远远多于含觚爵组合的墓葬,罐、鬲在组合中占一定数量。三期组合中单豆、单鬲组合仍然流行。有簋组合的墓葬数量最多,其中觚爵簋罐的组合份量较重,盘、尊在该期组合中开始出现。四期早段组合中含簋组合的墓葬仍然最多,含尊含盘组合的墓葬数量增多,含豆组合的墓葬少见,单鬲的组合仍然少量存在。四期晚段主要流行觚爵盘罐的组合形式。该期组合中簋、罐、盘数量最多,其中含簋组合的墓葬数量超过含觚爵组合的墓葬数量,尊在陶器组合中仍有一定数量。
郭家湾新村族邑墓地有一期墓葬2座,组合为单鬲、单豆。二期豆在组合中占主流,单豆和觚爵豆的组合最为流行。有豆组合的墓葬数量多于有觚爵组合的墓葬数量。含鬲或含簋陶器组合的墓葬数量极少。三期豆在组合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大,仍然盛行单豆和觚爵豆的组合。四期含簋组合的墓葬数量仅次于含觚爵组合的墓葬数量。含鬲组合的墓葬数额增大,其中单鬲组合比较盛行。含盘或含罐的墓葬组合各占该期墓葬总数的近四分之一。
大司空村东南族邑墓地和郭家湾新村族邑墓地墓葬陶器组合的相同点是:
1.两处墓地均有殷墟一期的墓葬,且该期墓葬陶器组合均为单豆、单鬲(其中大司空村东南族墓地一期7座墓葬,4座单鬲,3座单豆组合;郭家湾新村族墓地一期2座墓葬,1座单鬲、1座单豆组合)。2.两处墓地中二期墓葬陶器组合中单豆、单鬲等单件组合仍占主流。组合中含簋或含豆组合的墓葬远远多于含觚爵组合的墓葬(其中大司空村东南族墓地二期41座墓葬,包含以单件器物形式出现的墓葬20座,占该期墓葬总数的近50%,有9座单豆、4座单鬲、2座单簋、2座单罐、1座单瓮、1座单盆的组合;郭家湾新村族墓地二期56座墓葬,以单件器物形式出现的墓26座,占该期墓葬总数的46%还多。其中有21座墓组合以单豆形式出现,另有3座墓是单鬲、2座墓是单簋的形式。)。3.两处墓地中三期墓葬陶器组合中单豆等单件组合仍然流行(其中大司空村东南族墓地三期38座墓葬,包含以单件器物形式出现的墓葬10座,有5座单豆、3座单鬲、1座单簋、1座单盂的组合;郭家湾新村族墓地三期59座墓葬,以单件器物形式出现的墓24座,占该期墓葬总数的40%多。其中有22座墓组合以单豆形式出现,另有2座墓是单鬲的形式)。
不同点是:1.大司空村东南族墓地二期墓葬陶器组合中罐、鬲在组合中占一定数量;而郭家湾新村族墓地二期墓葬陶器组合中含鬲或含簋陶器组合的墓葬数量极少。2.大司空村东南族墓地三期组合中觚爵簋罐的组合份量较重,盘、尊在该期组合中开始出现;而郭家湾新村族墓地三期墓葬陶器组合中仍然盛行觚爵豆的组合。3.四期中两墓地中陶器组合关系均较复杂,差别较大。大司空村东南族墓地在这一期中觚爵盘簋罐的组合十分盛行。罍、尊、瓿等器种在多个组合中的出现,是这块族墓地中墓葬陶器组合的一又个特点。而郭家湾新村族墓地四期墓葬陶器组合中的单件组合仍然流行(其中有12座单鬲、8座单簋、2座单盘的组合)。觚爵盘、觚爵鬲、觚爵簋的组合仍占一定数量。
四、相关问题的提出
随着殷墟族邑聚落大片完整墓地资料的不断公布,有关族邑聚落墓地中墓葬陶器组合课题的研究势必会提到日程上来。早在1979年的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中,报告编写者就对西区墓地的8个墓区中的墓葬陶器组合的资料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分析,得出了8个墓区中前后期墓葬陶器组合的不同点及八个墓区相互间墓葬陶器组合的差别。并得出“这八个不同墓区就是八个不同“族”的墓地”[14](P114)。2014年出版的《安阳大司空》报告的编写者在报告中也对大司空村东南族邑墓地中墓葬陶器组合的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并提出了六点认识[15]。《安阳大司空》报告的编写者的几点认识,无疑切中了大司空村东南族邑墓地中墓葬陶器组合群体特点的要害,我们认为这几点认识可以简要精确到两点:
1.该墓区一、二期墓葬陶器组合的主流是以单件炊食器组合或以炊食器组合为一体的组合形式(一、二期有陶容器的墓葬48座,其中为单件炊食器组合或以炊食器组合为一体的组合就有35座)。可以说殷墟早期大司空村东南族邑墓地墓葬陶器组合是注重食器(炊器、盛食器)随葬。2.自殷墟三期开始,至殷墟四期晚段,酒器觚爵组合或觚爵加其它器物组合一直占这一时段该墓地陶器组合的主导地位(三、四期有陶容器的墓葬139座,其中为酒器觚爵组合或觚爵加其它器物组合为一体的组合就有78座)。也可以说殷墟后期墓葬更加注重酒器组合。
通过以上对殷墟西区等11处大型族邑墓地中墓葬陶器组合资料的基本统计与相应分析,我们认为如下有几个问题是值得肯定的,另有几个问题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
1.殷墟遗址中大型族邑聚落墓地墓葬陶器组合中普遍是以觚爵为核心的陶器组合形式。这种组合形式在殷墟墓地中是贯穿始终的。这一点值得肯定。
2.虽然殷墟墓地中以觚爵为核心的陶器组合形式占去墓葬陶器组合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但组合中没有觚爵的组合还有少量(或个别墓主人就没有随葬品),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呢?学界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殷墟某个区域的某个时段陶器组合是“重食器(炊器、盛食器)随葬”[15],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没有觚爵随葬的“这些墓的墓主人应属于贫民的下层,是较贫苦的族众[14](P118)”。就是说这些人生前在“氏族”中地位低贱,死后,在葬制上不能享用“礼”的待遇。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
3.我们知道觚爵同出的组合在殷墟族邑墓地中是一个普遍现象。殷墟西区墓葬第六墓区中有以单爵组合的墓葬7座,以单觚组合的墓葬两座、或以觚盘、觚罐、觚鬲组合的墓葬九座;在第八墓区有以觚盘罐小壶、觚罐盘、觚盘、觚盘盂、觚盘罐簋等组合的墓葬七座(这些墓葬都是没有被盗扰的墓葬)。这些组合的墓中或仅有觚或仅有爵,觚爵不同出。像这样觚爵不同出的墓葬陶器组合在西区第四墓区、戚家庄村东南族邑墓地、大司空村东南族邑墓地及郭家湾新村族邑墓地也有个例。这些觚爵不同出的组合现象,必定有它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西区报告的编写者指出第八墓区中“Ⅸ式觚除一墓外,都不于爵同出”[15](P114)。说明这些觚爵不同出的组合现象多是出现在殷墟晚期的。还有一个现象,西区第四、第六、第八墓区,这3处族邑墓地在地域上相互临近,且它们的四期墓葬中又都流行觚爵分出的陶器组合形式。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应该是相邻近族邑在葬俗上相互影响的结果。
4.到了殷墟文化四期的墓地中含小罐、小壶、小罍组合的墓、含仿铜陶礼器组合的墓的出现,是殷墟族邑墓地墓葬陶器组合中的一个新的现象。这一点也是肯定的。
5.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个族邑墓地中墓葬陶器组合早晚期组合的变化规律既有连贯性,又有各自的特征。组合的变化主要反映在器种和器物数量的变化上,觚、爵是殷墟墓葬陶器组合中的主体器类。组合中的辅助器类有十几种,辅助器类在早晚期墓葬组合中连贯性强,变化比较突出的有豆、簋、鬲、盘、罐等几种。这一点也值得肯定。
6.殷墟南区相邻的戚家庄村东南族邑墓地与郭家庄村西南族邑墓地墓葬中陶器组合的特征是基本一致的,早晚期段组合中都是以觚爵为主体,只是辅助器类中的盘、簋在四期早段组合中是有差异的。戚家庄村东南族邑墓地在四期早段组合中盘最多,而郭家庄村西南族邑墓地在四期早段组合中簋最多。洹水北岸大司空村东南族邑墓地与郭家湾新村族邑墓地在一、二、三期陶器组合中单件器物组合、含豆含簋的组合多于含觚爵组合的数量是这两处族邑墓地陶器组合的主要特征,第四期组合中的辅助器类都以簋为最多,盘在组合中数量较少。大司空村东南族邑墓地与郭家湾新村族邑墓地东西相临接。郭家湾新村族邑墓地应是大司空村东南族邑墓地向东的延伸部分[16]。这两处族邑墓地陶器组合的特征是基本相一致的。但这两处墓地陶器组合特征和相距较远的戚家庄村东南族邑墓地、郭家庄村西南族邑墓地陶器组合特征差别很大。这说明殷墟遗址中相邻近的族邑聚落的葬俗是相互有影响的。
殷墟族邑墓地中墓葬陶器组合资料的对比,看起来十分复杂,实际上从细节中可看出是有规律可循的。殷墟墓葬陶器组合中的主体器类和辅助器类中的主要器种在早晚期组合中的变化应是墓葬陶器组合变化的主线。觚、爵是殷墟墓葬陶器组合中的主体器类,豆、鬲、簋、盘、罐是殷墟墓葬陶器组合中辅助器类中的主要器种,这很显明。各个族邑墓地中觚、爵始终是陶器组合的主体,而辅助器类中的主要器种在各墓地的不同期别的陶器组合中是有所不同和变化的,因而也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组群特征。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9,(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郭家湾商代遗址[C].待发资料。
[5]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M].郑州:中州古藉出版社出版,2016.
[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C].考古学报, 1979,(1):114.
[7]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J].中原文物,1995,(3):90.
[8]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J].中原文物,1995,(3):90.
[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9,(1):60—61.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C].考古学报,2006,(3).
[11]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C].考古,2007,(1).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J].考古,2015,(8).
[13]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四.大司空村第二次发掘报告[C].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2008.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9,(1).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454.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郭家湾商代遗址[C].待发资料.
[责任编辑:郭昱]
2016-10-10
李贵昌(1963—),男,林州人,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殷墟考古工作与研究;李阳(1974—),男,安阳人,主要从事殷墟考古工作与研究;孟小仲(1982—),男,安阳人,主要从事殷墟考古及摄影工作。
K876.3
A
1001-0238(2017)01-00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