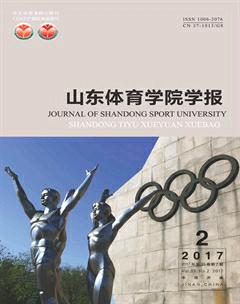依法治国背景下《体育法》修改理念的重塑
姜熙+龚正伟
摘 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开启了我国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在依法治国建设过程中,体育法治建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新时期体育治理的必然选择。《体育法》修改则成为中国体育法治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战略出发,结合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和国务院46号文件、2015年《中国足球总体改革方案》对新时期中国体育发展的战略布局,对《体育法》修改的基本理念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新时期《体育法》的修改应以“依宪治体”为最高准则,要以实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从“行政体育”转型升级为“法治体育”、 从“权力体育”转型为“权利体育”、从“法制体育” 转型为“法治体育”、 从“一元法治” 转型为“多元法治”、从体育治理的“有法之治” 转型为体育治理的“良法善治”为基本理念,以法治作为保障,实现新时期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新的飞跃。
关键词:体育;法治;体育法;修改;理念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7)02-0006-05
Abstract: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opened a new era of the rule of law since 2014. The rule of law has become the basic wa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course of exercising rule by law, the rule of law in sports has also become a basic choice for sports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ports modernization level of the rule of law for constructing a strong sport country. Under this background and combined with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layout proposed in the 46th document of the State Council as well as the Overall Scheme of China Soccer Reform in 2015,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c ideas on sport law amendment and explores the directions of rule of law of sport in China. It is concluded that rule of sport law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rule of Constitution and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basic ideological mechanism about "rule of law in sport", "sport rights", "multivariate7 rules by law" and take the rule of law as the safeguar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achievements of
2014年黨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是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将“依法治国”作为主要议题,将中国的法治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逢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战略进行全面部署的同时,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46号文件)。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虽然以上两个文件主要涉及体育产业和足球,但实际上是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意味着我国体育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而这个时代的来临与我国依法治国大战略下的体育法治建设息息相关,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都需要法治来保障。在此背景下,法治必将成为体育治理的基本方式和必然选择,也是体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中国体育法治建设而言,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完成《体育法》的修改工作,它既涉及到中国的体育法治建设,也关系到新时期体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本研究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出发点,结合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和国务院46号文件、《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为中国体育发展所带来的实践要求,对《体育法》修改的理念问题进行了探讨。
1 体育法治:当代体育治理的必由之路
进入当代社会后,法治成为世界各国基于理性而选择的现代治理之路,成为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基本方式,是各国在基于理性的价值基础上的选择。就体育法治而言,Andrew Pittman认为,体育法与体育的历史一样悠久[1]。在史料上留下记载的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法治可以追溯到西方体育的起源地——古希腊。相传,古代奥运会规则的创立要归功于赫拉克勒斯(Heracles),制定奥运会规则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所有参与竞赛者的平等机会,这些规则被视为 “Olympic Laws”(奥林匹克法)[2]。“奥林匹克法”除了包含“奥林匹克规则”(Olympic Regulations)还包含了每一届奥林匹克赛会组织和发展的管理规定[3-4]。 此外,古希腊时期的体育法治还包含了具有国际法性质的体育法规范,比如最为著名的就是古代奥运会期间的“Ekecheiria”,即“神圣休战”。
在国家层面,体育的法治已经兴起。20世纪上半叶是各国体育立法的一个重要时期[5]。据有关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全球有70多个国家已经颁布了专门的成文体育法,有许多国家还在宪法中有体育的相关条款[6]。
在国际层面,国际体育治理法治化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以“世界体育最高法庭”为发展目标的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已经迅速发展。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作为世界体育领域反兴奋剂的主要机构在反兴奋剂领域的立法和执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有一些国际体育组织也纷纷建立了内部的纠纷解决机构,与国际体育仲裁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等形成了国际体育法治的基本架构。在国际体育立法方面,《体育运动国际宪章》《奥林匹克宪章》《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等国际体育法律已经出现,这些都标志着法治已经成为全球体育治理的主流[10]。
2 《体育法》修改:中国体育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2.1 现行《体育法》立法理念的历史局限性
对于我国体育法治而言,1995年《体育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开启了体育法治时代。《体育法》的出台一方面填补了体育法律方面的空白,对于中国体育法治建设而言具有着重要的历史性意义,另一方面,《体育法》也有着其历史局限性。1983年,国家体委提出了制订《体育法》的问题。1988年,国家体委正式成立《体育法》起草领导小组。直到1995年《体育法》才正式颁布。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可见,《体育法》的立法准备和起草阶段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探索阶段,而直到1995年才正式确立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战略,《体育法》也正是在这一年颁布。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使得《体育法》的立法理念还是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因为体育领域一直以来采取的是“举国体制”,精英竞技体育在当时仍然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点。所以,在惯性思维之下,《体育法》立法理念没有及时、完全地跟上当时从市场经济转变的最新改革理念,且体育本身不是那一时期国家改革的重点领域,这就使得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而当时我国也还处于法制建设阶段,对于体育而言主要是是建立起相关体育法律制度,还没有真正上升到法治的层面。
2.2 新形势下对《体育法》修改理念重塑的必要性
从1995年《体育法》颁布至今年,已经整整20周年。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方面,整个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日益深入,党的十八大指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我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紧接着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以法治来保障各方面改革的顺利推进;另一方面,我國体育事业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精英竞技体育已经不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心,体育事业发展呈现出多元的价值目标。我国的体育事业在管理理念、体制机制等方面都面临着的深刻的变革。代表着国家对体育事业战略最新部署的国务院46号文件和《中国足球总体改革方案》则是意味着我国体育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来临。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提出,则意味着体育领域的全面改革需要法治的强有力保障。
在这种新的发展形势下,体育领域必将出现诸多新问题、新矛盾,而这些都无法由颁布于20年前的《体育法》来解决。因为当初制定《体育法》时所依赖的体育事业实践基础、调整的对象、规范的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体育法》中的一些法律原则、法律规范已不再适应当前新形势下国家对新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战略要求。那么,修改20年前颁布的《体育法》就成为体育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而在《体育法》修改进程中,我们首先就需要重塑《体育法》的立法理念。依据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大的战略部署,一方面要把握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和对体育领域的布局,使《体育法》的修改能为体育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另一方面,要把握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路向,使《体育法》的修改能够成为中国体育法治建设新的起点,以《体育法》为中心,建立起完善的体育法治体系,使体育法治体系成为整个中国法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体育法》修改理念的重塑
3.1 “依宪治体”—— 《体育法》修改的最高准则
法治,离不开宪法,宪法是依法治国的最高章程,体育法治更是离不开宪法的保障,要以宪法为最高权威。有学者研究发现,在世界上有74个具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在宪法中针对体育进行了具体的规定[7],宪法中都有针对体育的条款。有的是将体育和其他事项涵盖在一个或多个条款中,有的国家则是在宪法中有针对体育的单独条款[8]。《宪法》是我国最高层次的法律。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明确提出了“依宪治国”的新命题。就我国体育法治建设而言,首先就是要实现“依宪治体”。我国《宪法》一直对体育的发展有着明确的规定。1949年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在第四十八条明确提出“提倡国民体育”。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中的第九十四条提出“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发展”。1975年《宪法》在总纲中第十二条对体育进行了规定。1978年《宪法》第五十二条把体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加以了规定。1982年《宪法》第二十一条作出了“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规定,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次《宪法》修订中,这一内容一直得到保留。可见,我国在《宪法》上为体育的发展作出了规定,体育法治首先就是要做到“依宪治体”。 这就意味着《体育法》的修改工作要依据《宪法》来展开,以《宪法》为最高准则。要求《体育法》修改时不仅仅考虑《宪法》中的体育条款,还需要考虑到《宪法》中的其他一般性条款,最为重要的是《体育法》修改必须遵循《宪法》的基本精神,所有的条款都必须与《宪法》保持一致,要以《宪法》为最高标准。特别是在公民体育权利、体育纠纷解决、政府行政权责等诸多方面的规定都必须依据宪法精神。
3.2 《体育法》修改要把“行政体育”转型为“法治体育”
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就是通过法治限制公权,保障私权,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依法治国背景下,《体育法》修改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规范公权力,主要是对体育行政公权力的约束。就新时期体育事业的发展而言,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环境,我国体育的发展一直以来是采用的“举国体制”。在当前体育发展新的历史阶段,“举国体制”表现出了诸多的弊端。“举国体制”使得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权力主导着体育的发展方向和资源分配。在《体育法》修改过程中,必须力图将以往的“行政体育”转型升级为“法治体育”。
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体育法》中对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权责边界进行原则性规定,做到权责法定。过去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边界不清楚,也没有约束,这种权力边界的模糊性很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体育发展,很容易造成行政垄断,挤压社会和市场对体育发展的作用。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46号文件也明确提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行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加快推进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所以,在法治体育建设进程中,就必须在《体育法》中严格规定依法行政。体育领域的行政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应该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要求,依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列出体育行政的权力清单。在《体育法》中对体育行政权力边界的划定意味着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职能将进一步清晰,可以通过法定的形式为体育事业中社会和市场留下空间。在《体育法》中除了明确作为公权力的行政权,还必须保护私权,保护私权是法治的另外一个重要核心。在保护私权的过程中要区分体育发展中哪些是由社会或者说社会体育组织和团体来管,哪些则是交给市场。可以说,市场管的主要是私权。社会管的是什么?社会是自治团体,自治性就确定了它既有权力的一面,也有权利的一面,尤其是在社会关系中,确定哪些属于社会的权力,哪些属于社会的权利,把二者的界限明确划分。
3.3 《体育法》修改要把“体育权力”转型为“体育权利”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中,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包含了权利意识的唤醒。对于体育法治而言,公民体育权利的保障是最为核心的内容。一直以来,我国的公民体育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在相关法律规定中也没有加以明确。在依法治国背景下,要通过《体育法》的修改将中国体育法治以往以政府为本位的权力观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权利观,保障公民的体育权利。公民体育权利是从公民诸多权利中演化出来的一种权利,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与健康权、公民发展权、公民自由权等相关。早在1966年联合国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各国应承认和保障个人享有能达到最高体质和心理健康标准的权利”; 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体育运动国际宪章》第一条就规定“参加体育运动是所有人的一项基本人权”;1975年《欧洲体育运动宪章》和1992年《新欧洲体育运动宪章》都规定了“每个人都具有从事体育运动的权利”;1996年的《奥林匹克宪章》也增加了“从事体育运动是一项基本人权”规定。可见,从国际层面看,国际社会已经将体育权利作为公民基本人权的内容。在国家层面,很多国家在保障公民体育权利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有学者统计发现,全球有41个成文宪法国家在自己的宪法中明确了公民体育权利[9]。也有很多国家在体育法中明确了公民体育权利,比如2011年日本在新颁布的《体育基本法》中确认了“公民体育权利”。保障公民的体育权利已经成为国际体育发展的主流,也是各国体育法治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趋势。
就我国而言,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这意味着我国体育法治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确认和保障公民的体育权利。从我国《宪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看,我国体育事业的重点是群众体育的发展,国家发展体育的目的就是通过体育来增强人民的体质,是对公民体育权利的强调。这就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在《体育法》中对公民体育权利加以确认和保护,把我国体育法治理念从以往的“权力本位”转变为“权利本位”,真正做到体育的发展以人为本。整个《体育法》的修改工作和各条文的修改都始终要贯彻这一理念。
3.4 《体育法》修改要把“体育法制”转型为“体育法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号召就是要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法制”( Rule by Law)和“法治”(Rule of Law),一字之差却蕴含着不同的内涵。首先,我国一些法学家将二者区分为“刀制”和“水治”[10]。因为“法制”之“制”乃“刀”字旁,故称为“刀之制”,意为专政之工具, “法治” 之“治”是“水”字旁,故被称为“水之治”,寓意平之如水,是法治的精髓所在[11];其次,“法制” 是一个静态的概念,通常是指“法律制度”,而“法治”具有动态性,具有更深的内涵,“法治”要求在法制之中的法律是维护公平、正义、平等和权利等,通过法律实现科学有效的治理。可以说,只要有法律制度存在,就有“法制”,但却不一定就有“法治”。就体育治理而言,《體育法》颁布至今已经20年,以《体育法》为核心的许多体育政策和地方配套法规也出台了不少,但体育领域的治理问题还没有很好地与法律治理相结合,体育法治观念还比较淡薄,社会上对以《体育法》为核心的体育法律法规的了解也有限,《体育法》的许多原则和条款以及一些配套政策难以有效实施、执行力弱,或者效力不足,使得在体育领域有法不依,特别是有法难依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公民体育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法治保障滞后,运动员权利包括职业体育运动员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体育纠纷解决机制没有建立,政府、体育、社会、市场关系不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推进的法治在体育领域的贯彻就是要求在体育治理中全面贯彻法治精神,实行“依法治体”。这就要求通过《体育法》修改进一步完善体育法制制度,在法治之下,通过法律维护体育领域的公平正义,保障各体育参与主体的体育权利。同时,在《体育法》中要建立完善的体育执法和监督机制,加大对体育法律法规实施的监督和评估,扩大体育法律服务和体育纠纷的救济渠道,切实做到对体育领域各参与主体权利的维护,实现体育领域的公平正义。
3.5 《体育法》修改要把“一元法治” 转型为“多元法治”
我国体育领域以往一直是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在治理方面,举国体制所代表的行政主导模式造成了体育领域一元治理的局面。在体育法治领域,也存在一元现象,那就是仅仅只有体育领域这一个领域的法律即《体育法》来调整体育领域的各种关系,其他部门法很少介入到体育的法治之中。如我国的《著作权法》没有对体育领域至关重要的赛事转播权进行规定,而《体育法》也没有规定,造成了法律的空白。当然,在体育领域还存在诸多的法律真空地带。这就形成了体育法治领域的一元吊诡现象:即存在一部《体育法》,但《体育法》却无法解决体育领域的诸多问题,而其他部门法和司法部门则基本对体育没有进行较多的关注,《体育法》与其他部门法缺少互动。这样就形成体育领域只有《体育法》调整,但《体育法》却没有发挥作用的吊诡局面。这种“一元法治”局面最终沦为一种“形式法治”而没有“实质法治”。那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体育法治建设就必须突破以往体育领域仅仅只有《体育法》对其进行调整的“一元法治”局面,要建设《体育法》与其他部门法形成协同治理的科学的体育法治体系。那些体育领域可以以其他部门法解决的问题,都应该用各部门法来解决,因为体育领域不能与国家的其他法律隔绝开来,那就会使体育领域成为特权领域。同时,那些具有体育特殊性的领域和事项,如果各部门法无法对其进行调整,那么《体育法》就必须对其做出相关规定。这样一来,《体育法》与各部门法就可以共同形成一个完备的体育法治体系。此外,《体育法》修改还必须时刻关注整个国家法治体系的发展,如《立法法》修改、《民法典》的编撰等。这些国家重要的法律领域的新发展必将要影响到我国的体育法治建设,《体育法》的修改必须及时跟上这些发展形势,修改完成后的《体育法》才能与其他法律部门真正形成我国的体育法治体系。
3.6 《体育法》修改要把“有法之治”转型为“良法善治”
《体育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要实现我国体育的善治,而《体育法》的良法属性是体育法治和善治的前提,体育若要善治,须先使《体育法》成为真正的良法。目前,以《体育法》为核心,我国还出台了一些体育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还有众多的体育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各地方也有相关的配套法规政策,从数量来看已经不少,但事实上很多法律政策是否符合体育发展的实践要求,是否符合市场规律、社会需求都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通过《体育法》的修改,使我国的体育法律形成一个良法体系,从而实现我国体育法治从“有法之治”到“良法善治”的飞跃。需要利用《体育法》修改工作的契机,对我国的体育法规和政策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和立法评估。一方面,废除或取消那些阻碍体育发展的“恶法”;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体育立法的质量。从而实现从有“法”可依到有“良法”可依,从“数量法治”到“质量法治”的体育法治新局面。那么,体育良法标准是什么呢?总的来讲,体育良法要符合公平、自由、秩序、人权等价值标准,维护体育领域的公平正义,保障人们自由参与体育的权利,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建立良好的秩序;体育良法要保障民众需求;体育立法质量要高,要具有系统性、有效性、前瞻性、可操作性,改变以往很多体育法律法规难以施行或者实施效果不好、体育立法落后的局面;体育良法要符合体育发展的规律和社会现实,既要与中国体育发展实践相结合,也要与国际体育法治发展相对接;法律之间要协调,不仅仅是体育内部法律之间的协调,还要解决体育法律与上位法和其他法律之间不能出现法律冲突的问题。
4 结语
《体育法》修改工作既是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顺利推进体育事业发展与改革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和体育事业改革都要求我们思考中国体育法治的基本路向。法治是体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体育善治的前提。这就要求我们重塑《体育法》的修改理念,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将“依宪治体”视为《体育法》修改的最高准则,将为实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从“行政体育”转型升级为“法治体育”、 从行政权力主导的体育转型为保障体育权利的体育、从“法制体育” 转型为“法治体育”、 从“一元法治” 转型为“多元法治”、从体育治理的“有法之治” 转型为体育治理的“良法善治”作为我国《体育法》修改新的理念。
参考文献:
[1]Andrew Pittman.The Interaction of Sport and Law: Where Has it Been, Where is it Now, and Where is it Going?[J].Journal of Legal Aspects of Sport,1992:64.
[2]Alexandre Miguel Mestre. He Member States And The Olympic Movement: The Double Face Of Legal Subordination[J].Citius, Altius,Fortius,2010(3):101-131.
[3]孙葆丽.古代奥运会与妇女[J].体育文化导刊,2002(4):86-87.
[4]古代奥运会处罚规则.http://baike.baidu.com/view/1093009. [EB/OL].htm?fr=aladdin
[5]于善旭. 當代一些国家的体育法比较初探[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1990(1): 42-46.
[6]谭小勇,等.体育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7]陈华荣.体育的宪法保障研究 [D].苏州:苏州大学,2011:36-50.
[8]Janwillem Soek.Sport in National Sports Acts and Constitutions:Definition,Ratio Legis and Objectives [J].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Journal,2006(3/4):28-31.
[9]陈华荣,王家宏.寻找宪法中的体育权利——各国宪法公民权利章节体育条款比较分析[J].体育学刊,2012,19(3):24-29.
[10]何勤华.比较法学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01.
[11]宁杰. 跨越从刀制到水治[N].人民法院报,2007-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