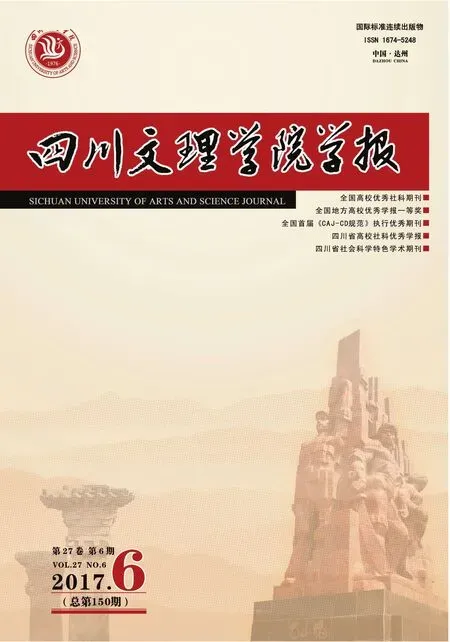纯粹的美与绝对的美
——中西审美思想探析
谭文旗
审美是人类情感世界的凝聚体现。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因为地理空间的分隔,审美呈现出不同样态。不同族群虽然在不断地交流、融合,但是在几千年的历史沉积下,还是分化构成了不同形态的审美思想。当前,现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资本世界超速扩张,时空压缩所带来的他者文化不断生成而又不断地彼此挤压,原有的审美思想文化不断地受到挑战而又不断地延异转变。该如何面对当前的审美文化?不同的审美文化思想该如何行进?本文主要选取中国古典审美思想和西方古典审美思想来言说审美的两种主要范式——纯粹的美和绝对的美,并对这两种审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展望,从而给予全球化语境中的个体生存以审美启示。
一、纯粹的美
从中国古典审美思想看来,审美不是认知世界,也不是意志世界,而是“我”与世界无目的、无功利但却有理趣的情感相通、呈现;审美视域中的世界既不是客体、物质性的对象存在,也不是主观、精神性的意志表达,而是“天人合一”的充满着人类原初情状的生存样态;审美世界的“世”作为时间、“界”作为空间不是指物理意义上的完全客观化、外在化的时间、空间,而是指与个体“我”紧密关联的人生在世的生存性时空;作为有“我”、有“你”,有“他”“它”的世界成为审美世界,就是不断去除外部事物对“我”的束缚、遮蔽、扭曲,不断自我化,又不断纯粹化的过程。这是一种纯粹的美。
纯粹的美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没有一种独立的、客体对象性的美
或者说,没有一种外在于人的、实体化的美。中国古人一般不推崇独立于“我”的客体对象,所谓“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认为这样的境地不高、韵味不足。所以,中国古典审美思想反对一味地对外在客体事物的摹写,认为对物体“形”的摹写最重要的是去显示“神”,艺术创作的“技”最主要的是要去通达“道”,如,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的这种“神”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先在的、绝对的、永恒的,独立于“我”的“理念”,而是“我”与天地万物息息相通,在相通中呈现出来的一种“韵”“味”“妙”“趣”,是一种通达天地万物的“觉”和“悟”。
(二)美是“我”“心”的敞开展现
中国古人的世界总是一种“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宋·陆九渊),“天下没有心外之理”、“天下没有心外之物”(明·王阳明)的状态。宇宙(时间与空间)的呈现与“我心”总是息息相关的。这类似于海德格尔的“我在世界中”。这种“在……中”不是书在抽屉中、桌椅在屋子中似的物理状态,而是主客无隔、“一气流通”的生存关联性,是一种共在相通状态。于此,美的世界呈现,总是以“我”为窗口绽放出来。“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唐·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中国文化思想一方面总是在消解实体性的、客观无我、绝对永恒的本体世界:“生生之谓易”(《易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另一方面又总是从“我”“心”的视角去言说“道”的通达、“仁”的实现、佛义的觉悟:庄子的“心游”“心斋”,孔子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他人欤”,禅宗的“即心即佛”“明心见性”。于此,审美总是关乎“我”的情意,“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艺术创作过程总是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然后才是“笔下之竹”。
(三)审美的过程,或者说美的世界呈现的过程是一个自我不断纯粹化的过程
“纯粹”就是去除经验、不杂经验。“我”,总是在世界中,总会被世俗生活、功利杂尘所缠绕,操心、操劳、烦神,所以,审美就需要“涤除玄鉴”“澄怀味象”。这是一种摆脱知识、意愿、欲念,自我不断“心斋”“坐忘”,“味无味,事无事,为无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自我不断地抛开个人偏狭的视角、自我固有的心理,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相看不厌”的境地,所以这种境地一方面是最自然本真的,另一方面又是新颖别样的。苏轼说的“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就是自我纯粹化的一种审美情态。
(四)纯粹化的审美过程最终通达的是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天地之境、宇宙之本
当把自我单一固有的视角消除,摆脱了世俗欲念的困扰纠缠时,在纯粹化世界中,“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这是一种天地万物在“我”心中,而“我”又在万物天地间的完全消融状态。“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当一切的喧嚣和躁动都荡去时,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本真、原初的世界,至静至深、地老天荒的宇宙本体。中国古典审美活动追寻的就是这样一个个体的“我”与天地共在状态下不断纯粹化从而自如其是、纯然同一、永恒自在的宇宙本体世界。
二、绝对的美
人人都能感受到美的存在,但是,什么是美?是什么使得人、物、山林、天空成其为美?或者说在那美的事物里面是否有一种美的本源?如果有,那是什么?这些问题促进了人们以“绝对”的方式来言说美的存在。
(一)作为本源性的绝对美
古希腊哲人认为,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有一个不变的本源,万事万物就是从这个本源而来。例如,泰勒斯的“水”,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火”,德谟克里特的“原子”。“美”也不例外。在柏拉图看来,美不是作为我们能够直接感知到的现象呈现,如漂亮的小姐、美的汤罐、美的竖琴,也不是恰当就是美,和谐就是美,而是漂亮的小姐、美的汤罐、美的竖琴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美之为美的“理念”。这种美的理念使“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泉源,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它也不是随人而异,对某些人美,对另一些人就丑”。[1]这种先在的、永恒的,不随人而异的“美”我们称之为“绝对的美”。西方审美艺术中的模仿说——现实世界是对本源的理念世界的模仿,而艺术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一直占主导,这和他们认为存在一种本源性的绝对美是紧密相关的。
(二)作为神性的绝对美
“古代‘希腊七贤’之一的哲学家泰利斯·封·米勒特曾经说过:‘神充斥一切!’他指出,古代的希腊人几乎都认为世界是神祇创造并由神祇统治的。”[2]其实,对大多数民族来说,没有神祇的世界是不可理喻的。神经常以神谕的方式启示凡人,而凡人从中获得觉解与力量。所以,作为超越凡人、永恒自在的“神”就是人类“绝对的美”,审美就是对这些绝对、永在的神的传达与表现。可以说古希腊艺术和神都有关联,除了直接的神话、神庙,其他的悲剧、史诗、雕刻都主要表现神的存在,乃至以后西方的许多艺术作品都是从这些“神”中得到灵感。在后来的西方世界中,源于古希伯来的宗教文化占据主导位置,世界的本源集中体现在宗教世界里,审美就是对宗教故事、人物所寓含的绝对、永恒、无限的追寻与表现。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艺术家与宗教关联密切,对他们来说,上帝、圣母、耶稣是一种绝对的存在,是美的源泉,是美本身。
(三)作为理性的绝对美
西方近现代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主体性粉墨登场,高歌猛进,人们开始摆脱宗教独断而展现出人的理性之光。笛卡尔的“我思”是一个绝对不可质疑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引发了西方哲学思维的转变——从先验的本体论转向以人为出发点的认识论,理性成为绝对的法则。康德的“哥白尼似的革命”进一步论证强调了主体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推断出人的理性所具有的一种先天综合判断能力;黑格尔通过严密的“精神现象学”演绎,展现出人类最后也是最高的阶段——绝对精神。缘于此,西方近现代文学艺术创作主要展现人的理性光辉。虽然,1750年鲍姆嘉通就建立感性学(Aesthetics,翻译为“美学”),以期与哲学的理性相区分,但是西方近现代主流的审美观念是黑格尔的“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四)不断“延异”的绝对美
西方现当代时期,哲学思想界一方面猛烈地反理性、反主体,反逻各斯,反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断提出更本源的“绝对”存在。尼采喊出了作为绝对的“上帝死了”,要“重估一切道德价值”,相应地又提出另一个绝对存在——“超人(The Super person)”。弗洛伊德一方面大力批判绝对理性,另一方面又揭示出非理性的“无意识”。海德格尔批判旧的形而上学,提出了作为世界敞开的窗口——“此在”,又提出了比此在更原本的“存在”。而各种审美思想总是关联于这些新的绝对者。20世纪下半叶在解构主义思潮下,西方思想文化界进一步对一切形而上学大加摧毁、消解,主体性、同一性、结构性衰落,他异性呈现。“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文化的关注,拉康对无意识话语的解读,福柯关于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论述,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论的解构,针对的都是他者和他性问题,都表现为对绝对他性的承认。”[3]列维纳斯更是直接以“绝对他者”作为世界呈现的原初方式。而审美思想就从这些他异性中寻找源泉根基。“物(Thing,或Das Ding),也称为不可能之物,是齐泽克哲学和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在物的概念烛照下,齐泽克思考了崇高美的本质、崇高化、崇高对象和崇高艺术等一系列问题,实际上已经建构了一个以不可能之物为核心的崇高美学理论。”[4]西方现当代在如此“延异”中展示出一种异质性的绝对美来。
三、在后现代状况下中国古典审美方式与西方古典审美方式的发展路向
(一)纯粹的美不同于绝对的美
虽然纯粹的美最后通达的也是一种万物之源、宇宙之本,但是这种源和本总是与“此在”息息相关、处处相连的,所谓“万古长空”总是关联于“一朝风月”。而绝对的美虽然总是在不断地演变,从柏拉图的“理念”到基督教的上帝,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到列维纳斯的“绝对他者”,等等,但是这种“绝对”总是先在、先验,与“此在”总有些区分。另外,绝对的美呈现出来的虽然是一个不断地从外在的物像走向内在的心灵,从绝对的神走向经验的自我,从对绝对理念的模仿走向一种“自我”表现的过程,这是一种摆脱外在物像不断探视、显示内宇宙的过程,但是我们要说,这种过程是一种对绝对美的追寻和期望过程,这是一种执着的美,与中国摆脱束缚、去除杂思的破执的美还是有实质区别的。
(二)中国古典审美思想对绝对的美——绝对的理念、绝对的神、绝对的物自体、绝对的他者等关注不够
中国古典审美对“绝对”的呈现不管怎么说都显得薄弱,因为,纯粹美总是与“我”关联在一起的,是以“我”的“澄怀”来“味象”,那种完全区别于“我”、完全绝对状态的美是不被认可的。中国审美思想一直讲究的是神、韵、意、趣,对完全以绝对他性的面貌呈现的事物以模仿,对某个事先就存在的理式进行展现,是贬斥的。这造成中国艺术过多地以简单的色彩、简化的线条去展现自我空灵的存在情形,而对纷繁的物象、思辨的时空缺少深入的探索、细致的表达。这种“大道至简”的“空无”观念使得中国古典艺术持续发展不够,表达方式不多。另外,在后现代时空压缩下,绝对他者的存在不可回避,自我的纯粹其实是无法摆脱他性的纠缠的。因此,中国现代审美不能以自我的纯粹来忽略乃至抹除他者之在,只有真正思考如何与他者的共存才能切实解决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建构中国的现代审美体系。
(三)从几千年西方审美思想的发展路向上看,虽然西方古典审美方式——对绝对美的不断探寻,实质上是一种向人、向心不断回归溯源的过程,但是这种内宇宙总是作为一种客体存在,总是与个体偶然的“我”有区别
对这种“绝对理念”浮士德式的审美追求有时会把我们弄得不知所措,比如当代的波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抽象艺术,以及艺术终结论等。对此,中国古典审美方式——自我的纯粹化,或许能够带来“他者”的启示。面对拉康的不可捉摸的实在界、福柯的异托邦空间、德里达不断延异而无最终所指的能指链,或许“道法自然”——天地自然而然地变易,万物如其所是地生长,是探寻绝对美的现代方式。“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自我内心的宁静与纯粹就在通达绝对的美,或者说,对绝对美的探寻须得注意回归到自我纯粹的一切如其所是的“道法自然”状态。
面对天地万物、人事纷繁,审美的人生一面是不断地自我纯粹化的过程,一面是不断地探寻绝对他者的过程。表面看起来这好像是矛盾对立的,实质却是一种“道者反之动”——不断行进的过程中转化、生成,提升、超越。这或许就是中西几千年的审美思想带给后现代时空压缩下的人们最简明的启示。
[1](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49.
[2](德)古斯塔夫·施瓦布.古希腊神话故事[M].赵燮生,艾 英,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1.
[3]杨大春.语言 身体 他者[M].北京:三联书店,2007:303.
[4]韩振江.论齐泽克“不可能物”与崇高美学[J].美学,2016(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