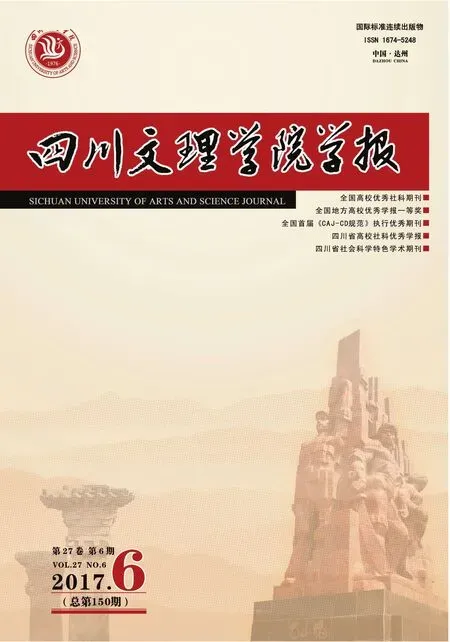将军赋采薇 勇士歌大风
——试论张爱萍的艺术人格及其美学启示
范潇兮
从达州市走出去的一代开国将军张爱萍同志,既是一位文韬武略的革命家,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艺术家。他创作的大量文艺作品体现出来的艺术人格,对文明今天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依然有着重要的美学启示。
“将军赋采薇”是毛泽东1942年为中国远征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殉国而写的《悼戴安澜将军》中的一句。这里面又暗含了《诗经·采薇》的典故,《采薇》中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本是一首老兵归家,物是人非而悲伤不已,表达了对战争的诅咒和和平的向往。“勇士唱大风”,引自刘邦《大风歌》中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以“大风”象征勇士征战沙场的雄风与豪情。
这两句诗与本文,即与我们要谈论的张爱萍将军的艺术人格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样的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诗歌,二者互为映证。本文旨在揭示张爱萍将军文艺创作的美学机制,他用艺术的方式不仅再现了波澜壮阔的20世纪,而且表现了“从战争中走来”的那一代职业革命者的雄才大略和理想信仰。今天,我们通过将军的文艺创作,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的艺术成就,而是正如张爱萍的次子张胜在《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的扉页,引用爱因斯坦悼居里夫人说的一句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1]是的,真正令我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张爱萍将军一生为何特别钟情诗词、书法、摄影,不如说是这些艺术之于他的学养积淀、精神风貌和人格结构的美学意义究竟是什么?
一、张爱萍将军艺术创作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风起云涌的20世纪在造就一代雄才大略的军事家的同时,也诞生了一群意气风发的军旅艺术家,首推毛泽东,其次还有朱德、陈毅、叶剑英、萧克、黄镇、肖华、魏传统等,更有集诗词、书法、摄影均有建树的开国上将张爱萍。这位从大巴山走出去的青年才俊,历经革命斗争的洗礼,成长为我军高级指挥员,不论是在戎马倥偬的征战岁月,还是厉兵秣马的和平年代,他都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摄影和书法等文艺作品,他采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独具匠心的笔墨、追光蹑影的镜头,直抒人民战士的胸臆,记录革命历程的内容和展示高风亮节的境界,更是得到了军队内外和文坛上下的一致好评。先后有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神剑之歌——张爱萍诗词、书法、摄影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神剑将军张爱萍》收录了他四十五首诗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长征诗词选萃》收录了他创作于长征路上的诗词若干。
据杨志鸿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神剑之歌——张爱萍诗词、书法、摄影选集》所收录的作品,诗歌的情况是,他从1925年创作《上征途》到1989年创作《浪淘沙》,半个多世纪,一共创作了或古典如律诗、词格、长调、小令,或现代如新诗、歌词等体裁不一的265首诗词。书法的情况是,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或苍劲浑厚、或婉约柔美、或古朴拙稚的50幅书法。摄影的情况是,从1940年到1989年,记录战斗场景、训练场面、军旅乐趣、国外见闻、亲情温馨、自然风光,以黑白为主、间以彩色的摄影,一共157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张爱萍将军艺术创作有两个独特之处。一是,他是一个既精湛于传统艺术,又擅长于现代艺术的全能艺术家;他是一名激情澎湃的诗人,还是一位纵情笔墨的书家,更是一个技巧娴熟的摄影家。集诗人与书法一身的有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陈毅、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魏传统、刘瑞龙等。既是军事家又是艺术家的,还有上将萧克,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上将肖华创作了红色经典《长征组歌》,还有曾担任过文化部长的黄镇将军,陈毅曾赋诗“黄镇有三绝,就是书画诗。若能常写作,定为天下知。”张爱萍将军和他们不一样的是,他不仅精通传统的诗书艺术,而且钟情现代的摄影艺术。二是,他的艺术具有史诗的意义,几乎贯穿了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的历程。从大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年代,几乎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走过的艰苦卓绝而英勇悲壮的革命战争岁月,所经历的波澜起伏而坎坷曲折的社会主义时代,几乎是20世纪中国民族要解放、国家要革命、人民要幸福的一个缩影。可以说,张爱萍将军的艺术创作,以史诗的气魄记录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展现了一代青年才俊最后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奋斗经历。
二、张爱萍将军为何对摄影情有独钟
张将军和那一个时代的职业革命家一样,既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指挥员,也是一名才情横溢的艺术家。他不仅精通传统的诗书艺术,而且钟情现代的摄影艺术。1940年在抗日战场上缴获了一架莱卡照相机,从此,照相机就伴随着他戎马征战和革命一生,先后拍摄了两千多福照片。他为何对摄影情有独钟,相比于诗词、书法、绘画而言,摄影这种现代艺术形式,在他的艺术人格建构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众所周知,摄影的最大魅力在于真实地再现人物和场景、对象和环境、时间和空间,因此,纪实性是摄影相对于其他如美术、雕塑等再现性艺术的显著特征。对于20世纪中华民族这场伟大的革命和变革,当抽象性的书法不能够书写将军的意气和意力,当写意性的诗词不足以抒发将军的豪情和豪迈,如何记录那些“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感人场景,如何留住那些“创业艰难百战多”的经典画面,如何呈现那些“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历史面孔,于戎马倥偬在征战中,在忙里偷闲的工作外,惟有“变瞬间为永恒”的摄影能做到。就这个意义而言,与其说摄影能为我们保留珍贵的历史记忆,不如说摄影能满足将军的历史情怀。让将军真正意义上成为这段历史全方位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记录人和留存人、创造者和欣赏者。东方鹤著的《张爱萍传》是这样记叙的:照相机这件特殊的武器,“之所以称之为特殊,是因为运用它可以进行鼓舞士气、振奋精神、陶冶情操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进行弘扬正气、鞭挞邪恶、瓦解敌军的战斗。”[2]从而使得张爱萍的艺术人格在结构中,增添了再现性的成分和现实主义的要素,使得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具有布尔乔亚情结的文艺青年,而且是一个有着英特纳雄奈尔的革命战士,不仅是一个洋溢着古典艺术气质的儒将,而且是一个彰显出现代艺术魅力的大师,这些在丰富他艺术种类的同时,也丰富了他的人格结构,具有了与这个风起云涌时代相匹配的历史厚重感。
三、张爱萍将军为何钟情艺术创作
关于将军与艺术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爱好就能解释得了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解答。从浅表层次看,这牵涉到的是一个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时代精神。我们都知道,那个年代的革命家大多出身于书香门第,接受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诗词歌赋的熏陶,他六岁时,就在私塾接受了蒙学教育,《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背得滚瓜烂熟。他青少年生活的地方,四川东部的达县,这是一块侵染着古老的巴国文化和巴人情怀的文化厚土,有关巴人性情剽悍、巴师骁勇善战的传说故事,如牧野之战、平定三秦、灭秦兴汉,还有清代发生在这里的白莲教起义,无不潜移默化地滋养着他的性格和情怀。再加上,20世纪中国革命的摧枯拉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天翻地覆,不论是在故乡参加学潮,还是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尤其是他成为一名军人后,所经历的枪林弹雨和九死一生,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经历,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正是这战乱频仍时代和追求真理、向往自由、渴求解放的时代精神,促使了他的诗情喷发,为他的艺术才华的施展提供了舞台。
张爱萍将军为何钟情艺术创作?还涉及到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的“潜意识”问题,借用著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荣格所谓的:“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艺术家和艺术品之间的关系,绝对不仅仅是“加工”和“产品”的直接对应,而是“原因”与“结果”的双向互动。即只有艺术创作,才能真正发挥他的潜质、满足他的愿望、实现他的理想。歌德用“浮士德”形象来替代性地满足了他不断进取、完善自我、追求永恒的内在渴望,这个浮士德形象更是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封建势力日趋奔溃,革命力量不断高涨的德国现实社会。今天看来,张爱萍将军的艺术创作和成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遗产”或“文化现象”,“文化沉淀为人格”。这背后一定与他的人格结构有关,也就是中国民间说的“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窥一斑而知全豹”。
结合本文所论述的对象看,他之所以成为“神剑将军”,原来他人格结构中,先天地具有艺术家的禀赋气质。一方面,他有着刚正不阿、崇尚个性的阳刚之气。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与坚定的革命者,张爱萍既是极富理想、敢做敢当的热血男儿,正因为他刚烈的性格与锋芒毕露、坚持己见的个性,从青年时代开始,即被视为是“共产党里的另类”。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而他本人的座右铭则是:“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真伪羞奴颜!”另一方面,他又有着侠骨柔情、缠绵悱恻的阴柔之美。他对家乡的恋恋不忘,对战友的拳拳深情,对妻子的儿女情长,对子女的呵护疼爱,在他的艺术作品中屡见不鲜。1972年,他在监禁中写下《步原韵和幼兰诗》:“战火纷飞同敌忾,红线相牵,优思六载,老来更难忘当年。”
这里革命家与艺术家、将军与诗人、热血男儿与多情才子,共同统一凝聚在了他呈现给我们的诗词、书法和摄影作品上。崇尚自由的理想,勇于创新的精神,特立独行的个性,侠骨柔肠的情怀,这些既是艺术家的重要品质,也是艺术的必备条件,这与其说是他艺术精神的体现,不如说是他艺术人格的写照,更是我们探寻他为何特别喜爱艺术的独特“秘钥”。
四、张爱萍将军艺术人格给我们什么样的美学启示
诗如其人,人如其诗,艺术家的作品与艺术家的人格应该是高度一致的,如此才能创作出隽永、厚重和深刻的艺术精品。借用古希腊的雅典执政官伯利克里的一句名言:“我们是爱美的人!”那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人,在率领人民开展救亡图存的悲壮征战,进行革故鼎新的伟大创举,从事前无古人的壮丽事业,不论是领袖还是百姓,将军还是战士,首先应该是一个人,就像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说的那样,“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也只有具有了“一个人”的一切时,才谈得上成为人民的先行者和领路人。那么,张爱萍将军艺术创作而凝聚成的艺术人格,在本质意义上,是一种伟大而高贵的审美人格。作为一代集诗人和文人于一体的“儒将”,享有“神剑诗人”、“将军书法家”和“马背摄影家”的张爱萍的艺术人格,给今天的我们,特别是从事一定管理职责的国家公务员和党的干部,有哪些美学上的启示呢?
首先,革命家应该有追求美的情趣。像张爱萍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深入虎穴出生入死,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可谓“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哪怕就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也是运筹帷幄旰食宵衣,检查指导夜以继日,似乎他们就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工作狂。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像张爱萍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哪一个不是“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不论对敌斗争多么艰难,地下工作多么危险,日常事务多么繁重,他们都应该有追求美的情趣,因为正如高尔基说的:“照天性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他无时不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否则的话,一个没有爱美情趣的革命家是多么的可怕啊!只能使人望而生畏,令人敬而远之。
其次,革命家应该有承载美的形式。如果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么创美之技并非人皆有之了。有了爱美的情趣而没有创造美的技艺,关键是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能够扬长避短地,而又恰到好处地承载的美的形式。唐代诗人柳宗元在《零陵三亭记》中说:“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所谓“游息之物”,就是交游和生息,即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要有高雅的情趣爱好,古人讲君子应该会诗词歌赋,懂琴棋书画,就是这个道理。张爱萍将军能够在那样繁忙的事务和繁重的任务之余,写诗填词、挥毫书写和摄影,将自己高尚的情操和高雅的情趣,寄予在艺术的创作中,真可谓如海德格尔所推崇的“诗意栖居”。
再次,革命家应该有创造美的造诣。艺术对于绝大多人而言,都是登堂容易入室难,看起容易做起难。而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已经到达一代宗师的境界人,凤毛麟角,微乎其微,更多的则为闲情逸致的“业余爱好”。而张爱萍将军的诗歌,笔者在几年前曾经总结道:叙事记物的再现与抒情言志的表现的融合,古典诗词的格律与现代新诗的体裁的结合,明白晓畅的语言与传神写照的意境的契合。当代书法艺术家胡秋萍也以《笔走龙蛇,卓尔不群》为题评价他的书法是“用笔含蓄,行笔快捷,粗细浓枯相间,章法分布自然,与诗歌内在的气韵相谐和谐,给人以铿锵跳跃或轻盈如水的音乐美感。”陈国恒和周文德主编的《神剑将军张爱萍》一书对他的摄影是这样评价的:“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著名摄影家袁毅平说:‘张老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而且有情有意又有艺术性,既有艺术审美价值,又有珍贵历史文献价值。’”[3]
将军赋采薇,勇士唱大风。是的,金戈铁马渐行渐远,战士豪情依然激荡;将军的征战足迹已经幻化成了一座永恒的雕像,而他的诗情画意正伴随着他返乡的步履,耸立起了一块巍峨的纪念碑。有着一生传奇经历和功勋卓著的张爱萍,能够创作并且喜爱诗词书法摄影,也许不足为奇。而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将军多才多艺所折射的艺术人格的深层奥秘和美学启示的现实意义是如此博大精深。敬仰之,只能高山仰止,研习之,只能浅尝辄止。是请听将军1989年1月26日《回春诗抄》的自言:
吟诵华章喜心头,墨痕几点纳千秋。
信手拈来无须琢,骚坛师表颂风流。
[1]张 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35.
[2]东方鹤.上将张爱萍传[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48.
[3]陈国衡,周文德.神剑将军张爱萍[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