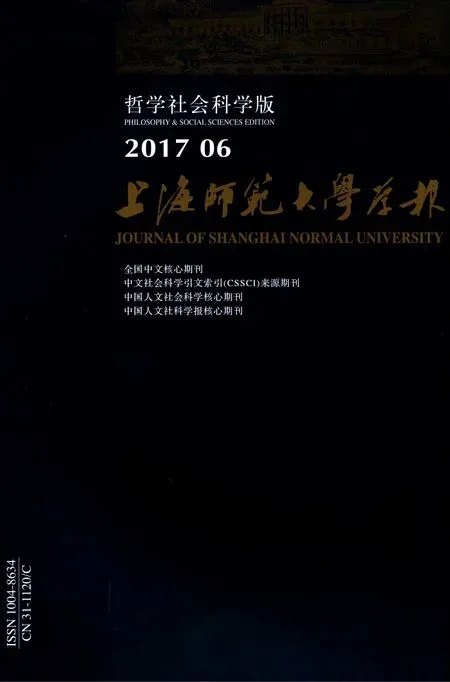近代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兼论文化的“综合创新”和“创造性转化”
张允熠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近代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兼论文化的“综合创新”和“创造性转化”
张允熠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大致与欧洲相仿,应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40年代,但被大大延阻了。“中西文明”之间实质性的直接接触、冲撞、互动和融合正是缘起于400多年前的16世纪末。如果说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之间的互动主要表现为“冲突”,那么,1840年之后则主要表现为“融合”。这种融合,不是无原则的混合,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创造性综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马中西”三派文化辩证地“综合于一”。“一”是什么?“一”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外文化经历数百年的互动、冲撞与融合,最终促成中华古老文化的新生,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复兴。
中西文明;综合创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近代”辨析
讲“近代中西文明”,首先要界定“近代”这个概念,因为中国与西方(泛指西欧)的近代分期是不同的。西方近代史起于17世纪,一般从1640年算起。因为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标志着欧洲走出了中世纪,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体系形成的时间还要晚些,晚到1789至1848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法工业革命,史称“双元革命”(dualrevolution)。“双元革命”是由英国学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这本书中提出的。欧洲从“双元革命”直到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个人或家庭(家族)形式为主,经济运行突出体现为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自由竞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产品的社会化之间的对立。
西方近代国家几乎都是18世纪双元革命的产物。这是因为:第一,工业革命奠定了工业化或称近代化的经济体制,它塑造了一种崇尚竞争与勤俭,看重效率与数量的文化;第二,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缔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进而成为一种政治制度模式被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并变通式仿效。因此,西方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欧资产阶级从发起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进而到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完善的历史。在中国,一般史书上把西方近代史断代为从1640年至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20世纪从1917年始进入了世界现代史,至今整整100周年了。
按照现在通行的说法,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比西方近代史整整迟了200年,即从1840年算起。因为这一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1842年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社会从此中断了传统的进程,被迫扭转了航向。换言之,从此中国被迫加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即加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历史”标志着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正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世界历史”使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农业民族服从于工业民族,东方服从于西方——“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①相对于西方近代文明,中国就是“半文明”“半开化”的国家,同时还是东方国家,又是农业民族,中国是带着浑身的创伤、满腹的屈辱和深深的痛苦开始了自己近代史的艰难苦旅。然而,中国人民最终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大无畏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斗,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结束和新历史纪元的开启。
相对西方来说,中国历史确实有其特殊性,如: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太长,没有经历像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光荣革命”“双元革命”那样剧烈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变革和社会革命。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平静得就像一条小溪,缓缓地流淌着,没有涟漪,更没大的波澜;又像一个沉睡的巨人,一梦不醒,如同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数千年前中国就是这个样子了,它就是一具亘古没有变化的“木乃伊”“僵尸”,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还不知何时醒来。
然而,人类的历史毕竟有其共同的发展规律。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内部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即使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迟早也要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笔者曾经把中国近代史的起始点放在17世纪,如果就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轨迹来看,晚明时期应是中国近代史真正启程的一页。这是因为:其一,早自15、16世纪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作坊和生产方式已经流行了;其二,由于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催生了城市市民阶层的形成;其三,与市民阶层的精神诉求相适应,思想界的民主主义和早期启蒙思潮也开始萌芽,要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呐喊平地而起,并且以文学和哲学形式反射到思想界;其四,基于上述原因,加之随同西欧天主教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西学”开始登陆中国,统治中国思想界的儒家官方哲学日趋僵化、腐朽和捉襟见肘,要求变革主流意识形态的呼声高涨,如,“王学”左派李贽就接过王阳明的话,高喊“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哲学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导——意识形态的变革是新纪元来临的曙光。
这种情形跟16、17世纪的欧洲社会大致相仿。16世纪末至17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与同时代的欧洲大体相当。如: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于16世纪最初发轫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商业城市,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欧洲市民阶层反宗教、反传统的思想启蒙已在酝酿。当然,中国的思想启蒙强度远没有欧洲那样剧烈,社会变革的脚步也远不如欧洲快速。但可以推断,如果没有1644年的清兵入关和随后建立起来的长达270余年的清朝政权,随着晚明时期中欧之间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的不断深入交流,中国社会必然会很早地就汇入到近代化的潮流,这一时间的节点也应该在17世纪40年代。正是清兵的入关,打断了中国社会自身的进程。生产方式落后、文明程度低下的满洲贵族的统治使中国资本主义的进程几乎戛然而止,近代化的进程被大大延阻了。
二、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的缘起
上文我们对“近代”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辨析,这有助于对于理解下文内容的理解,因为要谈近代中西文明的交往过程,就不能只从1840年说起。
所谓“中西文明”,就是指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此处的“西方”特指西欧。“中西文明”也可以称为“中西文化”。“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文化就是社会化,它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文明”只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譬如,有了人类共同体的群聚地或早期的城市,我们才可以称之为“文明的起源”。“文化”是个中性概念,例如,“中国文化”不一定都是精华,也有糟粕;“文明”则是个褒义词,我们凡提到某一文明,都是从它对人类历史的贡献角度来肯定它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并不刻意去区分“中西文明”与“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因为两个不同起源的异质民族的比较,没有必要刻意去区分其“文化”与“文明”的差异,完全可以将两者作为同义词看待。
“中西文明”之间实质性的直接接触、冲撞、互动和融合,实际上起源于400多年前的16世纪,即明代的中后期,也就是中国资本主义从萌芽到长足发展的历史时期。当时西方耶稣会士如利玛窦、罗明坚、艾儒略等人来华传教,他们不仅带来了基督教的圣经和教义(早在此前,基督教于唐代和元代曾两次传入中国,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带来了在当时欧洲流行的科技、数学、天文学,尤其是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逻辑学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这些来自西方的学问即“西学”,使中国知识界即士大夫阶层大开眼界,其所产生的影响不啻是在平静的中国思海中丢下一块沉重的石头,激起层层涟漪。从此,“中学”与“西学”之争、“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争声浪鹊起,中国思想界也开始分化出“开明派”与“保守派”。开明派在晚明有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保守派以清初的杨光先为代表。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由于欧氏几何学是用数学方式论证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从而填补了数千年来中国人思维方式和工具理性上的不足。
现代有人发现利玛窦介绍到中国来的都是两千多年前希腊人的创作,一方面认为这不是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人家两千多年前就有了这样的数学和科学成就,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确实落后于西方文化。实际上,这两种认识都有失偏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些知识在当时的西方并不是由他们祖宗传下来的,而是后来新发现和新流行的学问。众所周知,西方自从5世纪被蛮族统治之后,近千年的中世纪在文化上乏善可陈,欧洲的贵族普遍不识字,教会和教堂就是整个西欧社会的精神表征。正是由于11世纪开始的长达近两百年的“十字军远征”,欧洲人才偶然在西亚、北非遇到了自己的启蒙导师——阿拉伯人及其数学、天文学、逻辑学,以及阿拉伯人保留下来的希腊哲学文献。从此,欧洲人才算真正有了文化,才学会了办学校。现在英文中的“代数”(algebra)和“几何”(geometry)等单词,都不是来自拉丁文或西欧人的母语,而是来自阿拉伯文和希腊文。即使连欧洲人引以自傲的、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尽管在中世纪后期也有零星记载,但主要是在13世纪才进入欧洲思想界的视野,至15世纪他的名字才在欧洲思想文化界被熟知;欧几里得则要更晚一些。当利玛窦来中国时,欧氏几何学在欧洲是如日中天的显学,利玛窦在罗马的老师克里斯托佛·克拉乌(Christopher Klau/Clavius),就是研究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的专家。因此,有人责备利玛窦没有把17世纪先进的西学传到中国,而只是带来了欧洲古代希腊的“旧学”,这是不公道的。虽然古希腊在年代上泛指公元前东南欧接近亚洲地方的城邦国家,但欧氏几何学在欧洲的发现和流行却是距之一千多年以后的事,因此,它是日耳曼欧洲的“新学”而不是“旧学”。须知,利玛窦不仅是伽利略的前辈,当他来中国时,牛顿、莱布尼茨等人都还没有出生,他不可能把到他死后才在欧洲出现的“新学”带到中国来。由此可见,利玛窦传到中国的学问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等人的学说,实质上是在欧洲发现和流传时间不算长的新知识。如果当时中国能抓住时机,加强与西方的联系,虚心好学、奋起直追,中国决不至于到鸦片战争时期落后西方如此之远,失败得如此之惨。
徐光启早已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西方传教士想利用他们的学术优势达到“合儒、益儒、补儒、超儒”的目的,中国人完全可以因势利导,通过研习西学,最后达到超越西方的目的。所以他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令人扼腕长叹的是,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中断了这一进程。清朝统治者原为游牧民族,生产力落后,入主中原后并没有意识到农业文明高于游牧文明,摄政王多尔衮甚至想把整个华北大平原变成牧场,由此可以想见清初统治者是一种何等落伍的文化眼界和思维方式,他们根本不了解当时的西方已经跨入工业文明的门槛。倒是康熙皇帝喜好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当时主要指西方数学、科技、测量、天文、造炮等术,不包括神学、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由于康熙年间中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爆发了“礼仪之争”,最后导致清朝统治者于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下诏禁教,驱逐西方传教士,拆除各地教堂,遣散教民,使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次传播又以失败而告终。
中西之间表面上的“礼仪之争”反映了深层次上的文明冲突。除“礼仪之争”之外,中西之间在理念、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是十分尖锐的。明清之际,像徐光启那种要求“会通”中西的开明士大夫毕竟占少数,许多儒士和中国的精英人士对西洋人和西学始终抱有高度的戒备心理,有人指责利玛窦“儒服传教”是在“觊觎吾中华君师两大权”——“君权”即指政权,“师权”指的是意识形态权。更有甚者如清初的杨光先之流,公开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②从而对西学采取一种深闭固拒的态度。
由上而知,明清两朝中西文明的交往,以西士的“合儒”开始,以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和在中国的全面禁教结束,其基调是“冲突”。这些冲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思维方式的冲突。利玛窦在写往欧洲的书信中,屡屡提到中国人缺少逻辑思维,在孔子那里没有真正的哲学,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主要目的也是向中国传播欧洲的形式逻辑学。应该说,利、徐两人的初衷无可厚非,可惜这一工作没有持续下去,直至19世纪末严复翻译《穆勒名学》,三百年间形式逻辑学并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数学也乏善可陈。正是在这三百年间,西方人不仅完善、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学,而且还把从希腊、阿拉伯世界获得的逻辑学与数学发展到了极致。微积分、解析几何、二进制算术,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对推动西方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发挥了无与伦比的理性工具和工具理性作用。
第二,传统礼仪的冲突。中西“礼仪之争”的实质就是中国要坚持传统的忠君、敬祖、尊孔的礼仪,而罗马教皇则要求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必须放弃这种礼仪,只能遵行西方崇拜上帝的“一神教”传统。这种冲突是深层次的,在中国固有的道统、法统、政统中,是“尊夏攘夷”还是“以夷变夏”?这是中外文化冲突的根本性大问题,正是这种根本问题促使雍正朝下决心禁教。自1723年下诏在中国禁除基督教始,至1840年后基督教新教再次登陆止,100多年间基督教在中国大地上基本绝迹,不仅利玛窦“儒服传教”的事业毁于一旦,且“西学”在中国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与应用;而西方恰恰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完成了工业革命,西方社会以极大、极快的前进步伐把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第三,天文历法的冲突。天文历法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一个新兴的朝代无不是从“改正朔、易服色”作为其建制立规之始。清初康熙年间,发生了著名的“历案”。“历案”起因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与杨光先之间的争论。杨光先状告汤若望“谋反”,汤若望被判死刑。后来康熙亲自主持用西洋、回族、中国历法同时检测一次即将发生的日食,结果是比利时人南怀仁依据“西洋之法”的测算与日食发生的实际时间基本符合,而杨光先所推崇的中国“羲和之法”与实际日食发生时间差了数天之久。在这种铁的事实面前,杨光先不但不知反省,相反却提出“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极端保守排外言论,留载史册。后来南怀仁控告杨光先为鳌拜党羽,汤若望获昭雪,杨光先被判死刑,后被康熙赦免回乡,以死于途中终结了这场“历案”。“历案”是“夷夏之辩”的文化保守心态在科技侧面的投射。
第四,意识形态的冲突。康熙年间的“历案”不仅深刻地反映了中西之间在天文历法和科学理念方面的冲突,还反映了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明末崇祯年间,一批士大夫和儒生编撰了反对基督教的书籍,其中有费隐通容编《原道辟邪说》(1636)、徐昌治编《破邪集》(1639)和钟始声编《辟邪集》(1643)。其中尤以徐昌治编的《破邪集》(又名《圣朝破邪集》或《皇明圣朝破邪集》)最有名,该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初刻于浙江,共分八卷十万余言,汇集了群臣、诸儒、众僧揭批天主教的文章,是明末反天主教的主要著作。该书作者们主要从维护儒家正统的立场来反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他们指责利玛窦等人表面上“儒服传教”,骨子里却是在“觊觎吾中华君师两大权”,实为“邪教乱华”。这与清初杨光先的《不得已》同为意识形态的反基督教代表作,在今天读起来,仍带给我们许多启发和思考。
明末清初中西文明之间的关系虽然以冲突为主要表现特征,但暗中也不无融合。如徐光启等人对西方数学和科技知识的吸收,表现出了要求“汇通”中西文化的意向。以耶稣会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所传播的基督教并没有引起中国士大夫和知识阶层的真正兴趣,他们以传教为目的而带来的当时西方流行的科技知识如数学、测绘学、天文学等,却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积极的响应。然而,传教士的目的不是来向中国传播科技知识的,科技知识只是传教的工具,传播基督信仰和神学才是目的。所以,正如方以智所说,这些传教士,你向他们请教科技知识,他们“不肯详言”,相反,“问事天则喜”——你问他科技方面的知识,他们不肯多讲,而一旦问天主教的事宜,他们马上笑逐颜开。其实,中国学术思想史并不缺少理性精神,但中国的理性都是道德理性、实践理性,最缺少、也最需要的正是西方传来的这种理论理性、逻辑理性或工具理性。正因为耶稣会士传来的数学和科学知识在中国受到中国知识精英的如此欢迎,才在中国知识界埋下了“实学救世”即后来所谓“科学救国”的种子,这粒种子又终于长成了一棵“中西融合”的思想大树。如数学家梅文鼎就主张“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勿拘名相而取其精粹”。③他著26 种数学书,统名之曰《中西算学通》,实际上吸收了西方传来的数学和天文历算。再如有“清代第一学者”之称的戴震,其积毕生心血的校勘力作《水经注》,就吸收了当时已知的“西法”。概观之,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只局限于西方的数学、天文历算和其他科技知识方面,而对西方的哲学、神学,除像徐光启、李之藻等少数士大夫之外,基本上都采取排斥的态度。如明代《破邪集》的作者们和清初杨光先等人就认为西方的基督教是邪教;明代大哲学家方以智认为西人“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④就是说,西方人仅仅精于历算测量而已,至于他们的哲学,真的是不怎么样的。
出人意料的是,耶稣会士传到西欧的中国儒学(主要是朱熹“理学”),不仅在西欧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与西方思想相融合,促进了西欧的思想启蒙运动。如1998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丹尼尔·加伯(Danidl Carber)和英国剑桥大学的迈克尔·埃尔斯(Micheal Ayers)共同主编的《剑桥十七世纪哲学史》(TheCambridgeHistoryofSevententh-CenturyPhiosophy),是两位主编与数十位学者在历时16年(1982—1998)之后完成的计有1642页的两卷本哲学史巨著,该书在第一部分中就明确把中国哲学的西传以及西欧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回应作为欧洲近代哲学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和前提条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也写道:“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⑤这些英美学者都忠实地描绘了当时中学西传后中国思想文化被纳入欧洲的思维模式并融合于欧洲思想语境之中的真实情景。
三、近代中西文明融合的多元趋势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大转折,从此进入了教科书上所说的“近代史”阶段。从1840至1919年,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近8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西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如果说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之间的互动主要表现为“冲突”,那么这一时期则主要表现为“融合”。但“冲突”中有“融合”,“融合”中也有“冲突”,只不过有主有次而已。因为鸦片战争,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成为被羞辱的失败者,从此沦为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半殖民地国家,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劫难。同时,失败和屈辱也使这头沉睡的东方雄狮猛醒,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国已经落后,再夜郎自大下去只会亡国灭种。由此,中国踏上了向西方求索的征程,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也呈现出多元趋势。
魏源最早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其在序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⑥“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该书的写作目的,因为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相反,“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⑦1847—1848年,魏源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达500卷之多。这是一本能使国人真正“向洋看世界”的著述;对打破封闭、保守、僵化的思想视域,对加速近代化、追赶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具有启蒙意义的价值。然而,魏源的《海国图志》并没在国内受到重视,相反传入日本后,却促成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学者大谷敏夫说,明治维新前的“幕末”时期,“日本人的开明派,如饥似渴地读《海国图志》,他们从书中获得有关欧美列强的知识”;正是这些知识,成为“日本锁国时代的海外知识来源”,“《海国图志》起了决定日本前进道路的指南针作用”,“也成了体制改革的指南针”。⑧仅仅几十年后,日本就战胜了中国,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从16世纪的明末徐光启提出“会通中西”到19世纪的清末魏源提出“师夷”即“向西方学习”,三百年间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发生了巨大转变。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国势已经急剧衰落,头脑渐渐清醒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必须开放、必须变革,然后才能富强,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过,魏源的“师夷”也只是“师夷”之“长技”,即学习人家的造枪、造炮、造船的技术,而没有看到人家的“长技”是建立在强国的国体之上的,更没有看到思想、学术之“长”才是“长技”和强国的根本所在。
近代洋务派一方面沿袭了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另一方面主张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和国家政体上要坚守中国的伦理和纲常名教不变。如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冯桂芬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⑨早期的洋务派领导人薛福成也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⑩另一位维新派人士郑观应则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直至1895年,沈毓桂明确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早出处。1898年3月,张之洞出版了《劝学篇》,提出“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和“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在给光绪的奏折中明确写道:“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机,亦杜离经叛道之弊。”从19世纪的中后期直至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中西体用之辩”成为贯穿于中国思想界半个多世纪的一条主线,不仅洋务派讲“体用之辩”,像康有为、严复等维新派也大讲“中西体用之辩”,并汇成主导中国思想界的总体性的中西文化观。直至今天,“中体西用”的观念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但是,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与维新派的“中体西用”有着明显差异。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只在取西洋“坚船利炮”之方术,仅停留在“术”的层面,不愿触动封建政体;而维新派的“中体西用”不仅要取西方之“术”,还要取西方之“道”,主张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改革中国封建政治体制,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如康有为讲“以群为体,以变为用”,严复说“以民主为体,以自由为用”,皆是此意。
在这一时期,除“中体西用”论之外,还有“西学中源”说,即认为西洋的学问皆起源于中国。有人认为持这种说法的人都是保守派、顽固派人物,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一说法本来是开明派为对付保守派而提出的一项策略,目的在于淡化中、西学之间的界限,使两者亲和,至少也要同源。“西学中源”说贯穿于整个清代,清初的康熙皇帝就是这一说法的代表人物。清代中期的杰出学者、思想家戴震也是一位“西学中源”说的积极鼓吹者,而数学家梅文鼎与戴震观点基本相同。晚清坚持“西学中源”说的多半是维新人士,如陈炽、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主张“西学中源”说,康有为甚至把这一说法变成他推行变法的依据,如他说:“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孔子先发其端。”梁启超则把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描述成周代的“井田制”,说孟子早就提倡过。值得注意的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领导人物所说的源于中国的“西学”,已经从过去西方的科技知识一变而为西方的政治社会学说,这应该是对“西学”一次认识上的质的飞跃。为什么开明派、维新派人士都捡拾清初以来的陈词滥调,主张“西学中源”说呢?陈炽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他说:“知彼物本属于我,则毋庸显立异同;西法本乎中,则无俟概行拒绝。”——既然西方的制度、西方的学问本来就源自中国,是“吾固有之国粹”,那还有什么理由刻意地区分彼此或异同而加以拒绝呢?可见,“西学中源”说是对付顽固派的一件利刃,目的让西学能顺利地在中国传播。
无论是“师夷长技”,还是“中体西用”,乃至“西学中源”说,从本质上看,其旨都在于主张吸收西学、融会西学。然而,继鸦片战争失败之后,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进一步沉沦。日本作为一个两千年来一直吮吸中国文化乳汁长大的“蕞尔小国”,竟然打败了自己的师国——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大帝国,且使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极大地刺痛了中国人,同时也唤醒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自救意识。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写:“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后始也。”甲午战争的惨败也是康有为等人发起“公车上书”、开展维新变法运动的直接原因。中国人痛定思痛,于是穷究日本的富强之道——“明治维新”自然成为中国变法图强的样板。
作为儒家文化圈一员的日本,通过师法西方迅速成为东亚强国,一时“中西文化优劣论”遂进入学界比较研究的视野。部分维新派人士认为西方无论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并以西方标准剪裁中国、批判中国。如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写道:“则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严复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牛有牛之体用,马有马之体用,怎能以牛之体为马之用呢?严复坚持体用一源,反对体用二分,倡导“中西体用一致”,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严复大量翻译西方近代哲学、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种社会科学学说,引入“天赋人权论”“进化论”等近代西方思潮,提出“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其目的就在于推行变法维新,使中国无论在政体和政用上皆效法西方。因此,严复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代的自由主义者,是“五四”时期中国自由主义“西化”论者的思想先驱。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掀起了一个翻译、引介、学习西方的“西学东渐”的热潮。此时的“西学”已非特指一科一门之学,而是囊括各种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总汇。这一时期,“中西会通”和“中西融合”的呼声不绝于耳。如:王韬认为“天下之道”应“融会贯通而使之同”;章太炎提出要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王国维倡导中西二学“化合”之说;杨昌济主张“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冶之”。“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物,包括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主张中西学的会通与融合。如:蔡元培提出“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鲁迅提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李大钊说“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恽代英认为“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青年毛泽东主张,“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由此可见,该时期中西文化的主要基调是中西之间的会通与融合,但究其思想实质基本上是一种中庸之道。
近代思想界延宕已久的保守与激进的分化和对立,至“五四”时期走向极端。早期的保守派有“国粹派”,其代表人物是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他们以《国粹学报》等刊物为阵地,宣扬“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 国粹亡则其国亡”。值得注意的是,国粹主义者提倡国粹但并不排斥西方文化,而是认为:“国粹者,精神之学也;欧化者, 形质之学也;无形质则精神何以存?无精神则形质何以立?”可见,国粹派实质上是借中学以肯定西学,其目的是要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华,建构一个基于民族本位文化的新国学。继“国粹派”之后,“五四”后期又出现了“学衡派”。“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是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人,因他们在南京主办《学衡》杂志而得名;又因其主要成员大都有美国哈佛大学的留学背景而被称为“哈佛派”。“学衡派”的思想主张一方面在于复古,另一方面是反对新文化运动,但又主张“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立言宗旨颇似清末的国粹派。总之,20世纪初期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强调“昌明国粹”的前提下,都不反对融会、贯通中西方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保守主义的营垒中,“五四”时期还出现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以杜亚泉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他们都反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西化观点,推崇中国文化,甚至提出“复兴儒学”;但他们也都不拒斥西学,甚至主动去融会和结合某种西方哲学来支撑自己的哲学观点。因此,这一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前朝那些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即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具有性质上的不同;后者具有封建主义守旧派的性质,而前者则属于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民族主义派。
正值中国“五四”之时,欧洲刚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谓满目疮痍,萧条惨淡,于是国内出现了一种西方文明不如东方文明优越和“科学破产”的论调,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杜亚泉等。梁启超在1918年底至1920年初以巴黎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开始了对欧洲为时长达一年多的游历和考察,他亲睹了欧洲的战争破败和民不聊生,回来写了一部游记,名曰《欧游心影录》。他在书中认为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梦”,以民主、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中国应担当重建世界文明的重任,提出了中西文化的“化合”说。梁启超的说法遭到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的批驳。跟“西方文化破产”说恰恰相反,至20世纪30年代,一些激进的自由派人物抛出了“全盘西化”论,其代表人物就是胡适和陈序经,尤以陈序经为甚。陈序经鼓吹“全盘西化”达十多年之久,在他看来,中国无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都只能是全盘西化的道路,因为所有这些道路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所没有的东西,都是从西方传入的。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因其偏颇,支持者不多。胡适在被指责为是“全盘西化”论者时自我辩解道,他提倡的“全盘西化”并非全盘放弃中国文化而接受西方文化,所谓“全盘西化”就是“全盘现代化”。他说:“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风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中调和上去的。”胡适应是一位比较温和的“全盘西化”论者。
四、从“三流合一”到“创造性转化”
近代中西文化交往和互动的走向有一条脉络十分清楚,那就是:初以冲突为主,其中不乏会通的声音;继以融合为主,但不离民族文化本位主义,在精神上的反映就是“中体西用”论。“中体西用”论与“西学中源”说区别于那些固守纲常名教的文化保守主义,但却激起了另一派即西化派的应声而起,而“全盘西化”论就是西化派营垒中的一种极端声音。与“全盘西化”对立的极端派是“复兴儒学”派,这一派硕果仅存的只有当代新儒家了。从总体趋势来看,两极——即极端的顽固保守派和极端的全盘西化派——都不可取,而主张中西文化应走一条贯通、会通与融合道路的势力终将成为主流。
正值中西文化论战方兴未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具体来说,距今整整100年前——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思想文化的格局又一次发生了巨大改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尽管在十月革命前,甚至上溯至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有着零星的、陆续的传播,但马克思主义风靡全国却是直到“十月革命”和“五四”之后才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种显像,并且不久就在中国催生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中国思想文化界“中西”的二元模式被冲毁,李大钊指出的“第三新文明”即“马克思主义文明”迅速崛起,并后来居上。“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本来相对于中国的封建文化来说是一种新文化,自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它也变成一种旧文化了。”于是,“马中西”三足鼎立的定势取代了百年来的“中西”文化对立的二元格局。
随着中国主流思想文化领域的重新洗牌,如何处理“马中西”三派文化的关系便提上了日程,这实际上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哲学家张申府、张岱年兄弟两人便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提出了具有深谋远虑的主张。如,1932年以来,张申府一再提出要将“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三流合一”,“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受其兄的影响,张岱年于1936年最早阐述了“将唯物(马克思主义)、理想(儒家思想)、解析(西方哲学)综合于一”的思想,这就是著名的“文化的综合创新论”的滥觞。到了1987年文化讨论热的高潮时期,张岱年明确阐明了他的“综合创新论”。张岱年与其学生程宜山在1990年合著的一本书中对“综合创新论”有着经典的诠释:“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这种综合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辩证的。这种综合需要创造精神,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而这种综合又为新的创造奠定基础。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这段话与方克立1987年一篇文章的表述有较大的重合性,由此透视出从张岱年到方克立在文化心路上的高度一致性。
方克立表示,他本人非常赞同张岱年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并把“综合创新”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如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联系起来。他还以16个字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加以归纳,以此来代表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主张。方克立说,他后来发现这个概括也有缺陷,就是它只回答了古今中西问题,而没有对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论争的中心主题——中、西、马的关系问题给予回答,所以他又在2006年做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概括。这一概括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要按照“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的思路,把作为文化资源的中、西、马三“学”科学合理地整合与实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西方文化(外来文化)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起来,“坐集千古之智”,创造既具有博大气象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论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深化,其主要结论确实是从张岱年的有关思考和论述中引申出来的,按方克立的话说,是“接着张岱年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综合创新派”,从李大钊讲“第三新文明”、毛泽东讲“古今中外法”,到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提出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理论,都是主张充分发挥三种文化资源各自的优长,发挥其中的正能量,把它们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革命的创造的化合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在方法论上,他们强调“三流合一”不是折中主义的“平庸的调和”或无原则的混合,而是“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不是外在凑合的大杂烩,而是内在的“有机的化合”,“马魂中体西用”论正是这种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深化,“如果说,前者是分析命题,后者是综合命题,分析与综合都是必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张岱年、方克立的文化观实际上与习近平关于文化的系列讲话有着高度的共同点。如: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里的“继承”“创造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与“综合创新”的思想基本一致。方克立也认为,习近平文化观是党的文化方针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其与毛泽东的文化观是一脉相承的,而他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完全符合习近平的讲话精神。习近平虽然没有把“魂”“体”“用”三个范畴连起来使用,但其讲话中包含了这层含义。如在2016年的“5·17”讲话中,习近平特别强调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失去灵魂、迷失方向”。这里所说的“灵魂”,即“马魂”。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也表述了这种思想,比如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他这里强调的“根本”“根基”,实际上就是“中体”。至于“西用”,习近平讲得更明确,如他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为我所用”——其中就包含着“西用”。此外,习近平又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里,就包含着中(本来)、西(外来)和面向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文化。
由上而知,从“三流合一”到 “马魂中体西用”,从“综合创新”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近代100多年来中西文化的二元互动、冲突和融合,随着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崛起,便经历了“三元文化”的互动和冲撞,最后融合成主流,即“三流合一”。但是,这种融合不是无原则的混合,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创造性综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马中西”三派文化辩证地“综合于一”。“一”是什么?“一”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百川绵延汇大海,文化歧出终归一。换言之,近代中外文化经数百年的互动、冲撞与融合,最终促成中华古老文化的新生,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复兴。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②(清)杨光先:《不得已》(附二种),陈占山校注,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75页。
③(清)梅文鼎:《堑堵测量·郭太史本法》,见《梅氏丛书辑要》卷四十,第26页。
④(清)方以智:《物理小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自序第2页。
⑤[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亦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⑥(清)魏源:《海国图志》之《原叙》,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⑦(清)魏源:《海国图志》之《大洋洲》,第268页。
⑧[日]大谷敏夫:《海国图志对“幕府”日本的影响》,《福建论坛(文史哲)》1985年第6期。
⑨(清)冯桂芬:《采西学议》,见《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⑩(清)薛福成:《薛福成选集》,丁凤麟、王欣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页。
ConflictsandIntegrationofModernChineseandWesternCivilization——OntheComprehensiveInnovationandCreativeTransformationofCulture
ZHANG Yunyi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gan in 1840.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as roughly in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o 1640s, comparable with that in Europe, but it was greatly hindered. The substantive direct contact, collision,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were derived from 400 years ago,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mainly manifested as “conflict”, whil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during the modern period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integration” and diversity. This integration is not a mixture, but creative synthesi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Marxism,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re dialectically integrated into one new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undreds of years of interaction,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renaissance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ed the revival of the great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comprehensive-innovation,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creative development
K203
A
1004-8634(2017)06-0034-(10)
10.13852/J.CNKI.JSHNU.2017.06.00
2017-04-11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哲学的互动与主流研究”(13AZD022);上海市德育课程基地项目
张允熠,江苏沛县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西哲学互动与交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何云峰)
A文章编号1004-8634(2017)06-004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