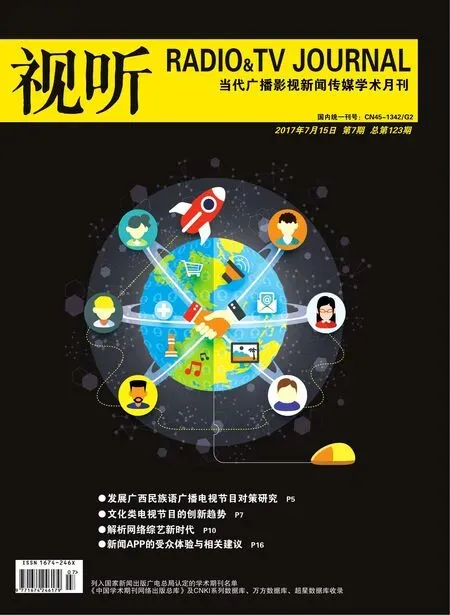从《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看大岛渚电影中的民族性反思与人性救赎
□潘梦洋
从《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看大岛渚电影中的民族性反思与人性救赎
□潘梦洋
大岛渚是日本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其电影的先锋意识和反传统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是其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作之一,该影片将同性之爱放置于残酷的战争背景中进行刻画,在剧烈的戏剧冲突之中表达了其对日本民族性的反思与对人性的关怀与救赎。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大岛渚;民族性反思;人性救赎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改编自英国小说家劳伦斯·包斯特的作品,主要讲述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东南亚爪哇岛上一个日军战俘收容所中发生的故事,战俘收容所由世野井和原上士主持事务。彼时收容所中同性之风盛行,无论怎样严酷处置也无法制止。然而讽刺的是世野井被崇尚自由的英国军队俘虏西拉所吸引,反复容忍其违反收容所规定的大胆行径……而后西拉因公开在战俘面前亲吻世野井而被处以活埋之刑,世野井也被调离了岗位。战后世野井被处死,而他在西拉死后割下西拉的一撮头发也被他托人带回家乡供奉。该片斩获当年《电影旬报》十佳奖第二名,被推荐为参加当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竞选作品,并被评为20世纪80年代日本最佳影片第七名。
影片将日本武士道精神影响下的日本军人与西方战俘放置于同一环境之下,中西文化对于生死、爱欲、人性、自由的思想在战争的残酷背景之下碰撞,通过这种碰撞反观日本民族性,对其进行反思。与此同时,整部影片围绕着战俘营中的同性之爱展开,有着禁忌色彩的爱欲在非常态的战争环境下凸显了作者对战争反人性的拷问,对人性自由的关怀与救赎。
一、对日本民族性的深刻反思
与其他讲述战争的电影不同,这部电影中并未出现任何残酷的战争场面,大岛渚从另一个角度将战争的背面呈现了出来。战俘营就是二战的一个缩影,在这里面同时出现了战争中敌对的双方。对此大岛渚是清醒的,在他看来,“日本电影史上的一些战争题材影片,往往只让战争的一方登场,见不到敌对一方的影子,这种描写手法苍白无力。”①因此,大岛渚以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不轻易剥夺任何一方在镜头中的话语权力,这令截然不同的东西方观念在电影中得以呈现。而导演借这种对比,对日本民族的性格根基以及战争中的军国主义精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揭发。
美国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提及日本民族文化中具有的一种“耻文化”。大岛渚在这部电影中也将这一民族精神表征展现了出来。电影中有几次提及羞耻,第一次是当朝鲜士兵爱上了战俘时,原上士认为其是肮脏与羞耻的,并命令他以剖腹这种原始而残酷的方式来自我惩罚。第二次是原上士与劳伦斯的谈话。“劳伦斯,你是怎么忍受耻辱的?如果你选择剖腹,我会羡慕你的。”日本军人近乎偏执地集中于罪恶与羞耻感,导致了他们在面对这些“耻辱”时,惩罚远远比事情的真相与对错更为重要。剖腹被视作洗去罪恶与耻辱的方式,甚至成为日本军人的狂热信仰,然而这种信仰已然取代了对生命应予的尊重,这其中的荒诞残酷是令人费解的。劳伦斯是西方人道主义的代表,从人道主义立场来说,他们追求的是宽恕与和解,因此哪怕被俘虏,劳伦斯仍然认为那是战争财富的一种而非日军眼中的“耻辱”。
这部电影中也透露出大岛渚对日本人的集体主义精神的一种审视。“‘和’的精神造就和固化了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在‘超越集体的价值决不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指导下,每个人时时事事都按等级秩序将自己归属于某集团。”②他们讲究规矩,个体意志在集体面前绝对不能彰显,包括求生的意志也应当服从于集体利益。当处在战争这种极端环境之中时,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往往会发展为一种愚忠。电影中日本法庭对西拉的审判正展现了东西方对于集体主义的分歧与对峙。西拉反复在法庭中问到自己因什么缘由被定罪。对于日军来说,西拉最大的罪行是供认不讳和主动投降。正如一名日本军官对西拉说,日本人被抓后不会透露真名,更不会主动投降,顺从地被抓。这违背了日本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对集体的极致忠诚在其看来是一种美德,是维护自身荣誉的体现,“他们虚拟出了一个‘崇高’的准则,并将这个准则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人自身却反而成了这个准则的牺牲者。”③同时这也是对人对于自由的渴求以及生存本能的一种扭曲。有人说,没有人比大岛渚更懂日本人。当他将日本民族放置在西方人本思维的面前,西方战俘们就像一面镜子,投射出这个民族的痛症与其民族性中对人性所扭曲的部分。
二、对战争反人性的拷问与人性救赎
大岛渚自然是反对战争的,这可以从影片的灰色调以及伤残的战俘群像中看出,但是比起直接地描绘战争所带来的肉体上的伤害,大岛渚选择了一个非主流的主题——同性之恋作为了其表现战争残酷且摧毁人性的切口。情感和欲望是人性的一个面向,而在战争中,因为情感欲望与战争所要求的人的刚烈和无情相背离,因此无论处在何种权力层级中的人,其人性都不同程度被战争所扭曲。而禁忌的爱欲与战争背景则达成了更巨大的冲突性。影片中,作为战俘营所长的世野井迷恋战俘西拉,但因为战争带来了二人立场、身份的对立,他只能痛苦压抑情感,直到西拉死后才割去一缕爱人的头发作为对自己情感的认证。这是对人情感层面的剥夺。而影片开头战俘营中负责包扎救援的朝鲜士兵因为爱上战俘而被下令切腹自杀,被他爱上的荷兰战俘在观看切腹仪式之后咬舌自尽。痛苦的惨叫和血腥的场面带来的不适感则展示了对人欲望的剥夺,也映射着被战争蹂躏得伤痕累累的人性。
然而电影中的人性也并非都是彻底失落的。正如那句“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问候,大岛渚也在电影中展现着他对于人性的悲悯情怀。被放置在战争中的人并没有被设定为好或是坏这样扁平的人格,他始终在伤痕累累的人性中去寻找着人性的温热和复苏。原上士粗俗残暴,恃强凌弱,却在圣诞节时借着醉意将自由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劳伦斯和西拉。当问及原因时,他对原野井说他认为这些被关押的战俘并不会伤害他们,人的善意在类似这样微小的举动中流淌。原野井在战后托人将西拉的头发带回故土,也是对自己被战争摧残的人性的宽恕,他接受了自己对于西拉的爱慕,接受了人性本能带来的一种可能性。正如原上士说的:“西拉在他(原野井)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而我们都分享了这颗种子的成长。”这颗种子,或许就是一个人性复苏的过程。
大岛渚始终带着一种救赎的心态来对待影片中的这些日军士兵,他不忍将人性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影片最后,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原上士再次见到劳伦斯,二人身份对换却似昔日好友般谈笑,原上士似乎已然能平静面对死亡,而曾经残暴的脸上竟然显出了一些天真,冗长的镜头定格在他的脸上,他眼睛泛红着对劳伦斯再次说出了“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这句话似乎是其内心深切的呼唤,呼唤平静,呼唤原谅,呼唤救赎。
三、结语
大岛渚的电影“多是对现实生活背后深藏的真实内容的关切”④,无论其叙述的是性、权力还是自由,他那些“离经叛道”的电影实则“指向社会或人类内心的隐秘之处”,且“批判立场与质疑态度始终如一”⑤。与此同时,他又带着对人的悲悯之心,他反对战争,关注战争中的日本民族,关注人的欲望与本能,而正是其自身的这种特质才造就了《战场上的快乐圣诞》这样一部有着巨大价值的电影。
注释:
①晏妮.浅谈大岛渚和他的若干作品[J].世界电影,1986(02).
②王豫秦.从日本人生活习惯透视日本民族性[J].新西部,2009(08).
③姜璐欣.武士与村夫[D].重庆大学,2013.
④范冰杰.论大岛渚电影的艺术特征 [D].重庆大学,2011.
⑤杨弋枢.大岛渚:法度世界的抵御者[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6(01).
(作者系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