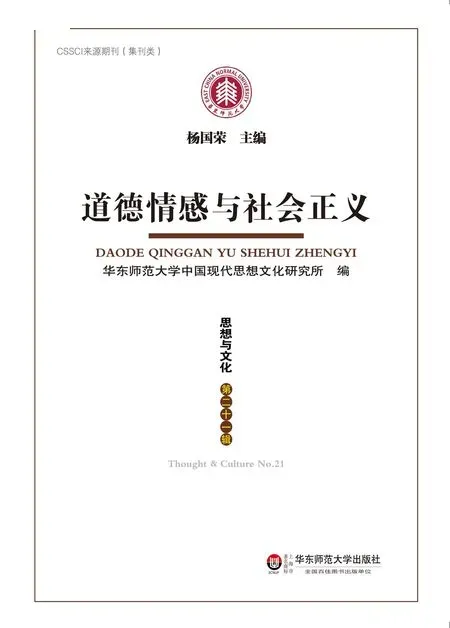郭店简《成之闻之》与孔子“性相近”说新研*
关于《论语·阳货》中“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后人有不少讨论。最晚在汉代,就产生了歧义。考察自汉代以来学者们的解释,可以发掘出其不同的偏向。这些解释大多有着其时代“知识型”的支撑,是以体现着一些理性的特征;不过也有难以解释,需要再治之处。而郭店简《成之闻之》篇的出土,为我们理解孔子的观点提供了新的更具有信服力的材料。由新材料入手,我们不仅要筛选过去学者的解释,更要探究这些解释及其产生原因。本文从《成之闻之》简出发,讨论孔子“性相近”的含义。
一、“性相近”研究回顾
对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句话的理解,学界已经有了很多意见,重点在于上句“性相近”的解释。李景林先生总结出两类:一是以孟子性善作解;一是宋儒以“气质之性”作解。而此二说皆有所偏。*李景林:《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页。如果再进行更细致的划分,我们可以总结出至少有四个偏向。除了上述李先生归纳的宋儒之说外,亦有偏向从性善恶说上剖析(对应孟子性善之说),亦有结合性三品说(即上、中、下三等)阐释,亦有从共性方面立说者。当然亦有综合几个向度之说,近来相关讨论亦多从上述向度进行考量。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出自《论语·阳货》,上章为阳货见孔子,孔子有“吾将仕矣”之语,与本章关系不大。下章则为“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似有一定的相通性。因此历来有许多学者曾用“上知(智)”、“下愚”来解释“性相近,习相远”。朱子甚至引或说,认为“上知”句前的“子曰”为衍文*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6页。,将两章合为一章。除了朱子以孔子之语作解,还有人征引《论语·雍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之语,《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之语,亦是以孔子之语来补充“性相近”的含义。根据这两段材料,性是有差别的,有了层次梯度的划分。后来董仲舒等人的“性三品”说就是由此而来的。
朱子之说是否可信,出土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可以提供一些证据。虽然“子曰:‘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一句已经残缺不存,然据竹简抄写之体例,此处确然当属两章。*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7、12、82页。从研究者所介绍的竹简体例判断,一支竹简字数写满一般为19—21字,但是“一枚简上部文字表现一个完整的意思后,下部为空白,而后面相连的内容另出一简”,如21简的“子曰:‘功乎异端,斯害也已’”,就只写了10字,下部即为空白。此处第504简在抄写完本章“子曰:‘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0字后,下部竹简就全部为空白,这明显证明简文当分为两章。当然,定州汉墓出土的《论语》只是汉代《论语》版本的一种。至于当时流行的其他版本,以及古人对此的理解,都还需要继续研究。
从目前的传世文献来看,从孟子开始就注意到了孔子关于性的讨论。《孟子·告子上》有“圣人与我同类者”,荀子也曾提出过“涂(途)之人可以为禹”的类似观点,似皆与孔子“性相近”有所联系。不过细较起来,孟、荀之学说与孔子之语也并非全然相同。下面我们从汉人的有关论述开始分析。
就目前材料,贾谊是汉代学者中最早直接讨论“性相近”问题的。贾谊在对文帝的献策中说: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48页。
此处贾谊之言不仅涉及了“性相近”,也涉及了“习相远”。其说夏、商、周三代君主与秦之“暴君”是“性相近”的;又引孔子之语证明后天之“习”的重要意义,由此得出“与正人居之”的结论。但这里的“性”没有等次之分,其主旨是正与不正,并非善恶。
不过,《新书·连语》中又曰:
抑臣又窃闻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尧、舜是也。夏禹、契、后稷与之为善则行;鲧、讙兜,欲引而为恶则诛。故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下主者,桀、纣是也。虽侈、恶来进与为恶则行,比干、龙逢欲引而为善则诛。故可与为恶,而不可与为善。所谓中主者,齐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则九合诸侯;任竖貂、子牙,则饿死胡宫,虫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贤人必合,而不肖人必离,国家必治,无可忧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贤正必远,坐而须亡耳,又不可胜忧矣。故其可忧者,唯中主耳,又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得善佐则存,不得善佐则亡,此其不可不忧者耳。《诗》云:“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趋也,故臣窃以为练左右急也。
本篇因谈及梁国之事,所以时间上应稍晚于上篇。本篇亦言及三代之政,并且将君主划分出了上、中、下三个梯度。不过从文意来看,这种划分实属于材(才)性之别。贾谊并未明确表达才性的善恶,只是说不同的才性对善恶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这其实已经显露出三品说、善恶说的迹象。贾谊言中主是“其可忧者”,是可以有变化的,有“又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的比喻。*《墨子·所染》所记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己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吕氏春秋·当染》略同)这可以看作就是墨者的人性论。此外,关于告子是否为墨子弟子,与《孟子》书中告子是否为一人,学界曾有争论,梁启超、钱穆二先生倾向于告子为墨子弟子,下及孟子。(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126—127页)今于人性论上或可添一证,《论衡·本性》记:“夫告子之言,亦有缘也。《诗》曰:‘彼姝之子,何以与之。’其《传》曰:‘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朱则赤。’夫决水使之东西,犹染丝令之青赤也。”此《传》今不见,墨者也传诗书,或可能为墨者所传习之《传》。而上主、下主则是“无可忧”、“不可忧”的,正与“上知与下愚不移”相联系。
从文献来看,汉代可能流行着与贾谊之说相类的说法。《汉书·文三王传》中载梁孝王八世孙“立”自言之语:“质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汉书·王莽传》有:“甄邯等白太后下诏曰:‘夫唐尧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圣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可见在时人认识中,“下愚者”之“性”是不可变移之物。结合孔子的“性相近”,很容易得出性有三品的结论:即性有上知(智)、中人、下愚三等,而通过“习”,中人之性可以移易。如《春秋繁露·实性》:“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
可以发现,前述贾谊之说已经有了将“性三品”与性之善恶联系起来的迹象。后来相关的说法就更多了。如《汉书·古今人表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传曰:‘譬如尧舜,禹、稷、禼与之为善则行,鲧、讙兜欲与为恶则诛。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桀纣,龙逢、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于莘、崇侯与之为恶则行。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因兹以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云。”即是在阐释孔子之语的基础上以善恶将人分为三等。《汉书·古今人表》中把人分为九等,其实就是从上、中、下三品每品再分出个上中下等,故而形成九等。
由于性与善恶联系起来的观点影响实在很大,是以之后刘敞提出“愚智非善恶”*刘敞:《公是先生七经小传》卷下,纳兰性德辑:《通志堂经解》,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本,第526页A。之说,就格外有见——虽然智愚和善恶有关,可是这其实是两个问题。阮元也认为智愚属于才性。*阮元:《性命古训》,《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24页。类似的还有戴震,戴震将孔子所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解释为“曰不移,不曰不可移”*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全集》第1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1页。,将性善之说和孔子之言作一融合,然而略显强辩。
汉儒以后,皇侃的《论语义疏》通过天地之气来解释“性”,并指出性无善恶,与贾谊的《陈政事疏》不乏相合之处。不过皇侃的解释着重从宇宙起源的层面进行说明*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81—1182、1187页。,体现出魏晋之风。但是程朱却另辟他径,由理气关系将“性”分出了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主要观点即“性即理”,本性(即义理之性)是无有不善的,而气质之性可分出美恶。如其解释“性相近”时就说:
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5—176页。
关于性、理的种种说法背后是宋儒的一套思想体系,已经超出了以《论语》解《论语》的范畴,是以后人有“绳孔”之批评。本文对此不作深究。
针对朱熹将“性相近”指向性之初的做法,徐复观先生指出:“就性的本身而言,总指的是生而即有的东西,无所谓‘初’或‘不初’。”*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78页。按:后人对朱子之语历有批评,朱子之说在于用自己的一套理论解孔子。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181、1183—1184页。不过现代新儒家对于宋儒并非完全反对,还是有一些赞成和支持的地方。如徐复观认为“性相近”的相近,仍吸收了朱子解《孟子》之语。徐复观先生所言朱熹之非,是因为其对《论语》中关于气质之性的内容也进行了考察,但并不能得出“相近”的结论,是以为非。*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第77—79页。展开来说,徐先生认为所谓的气质之性,“即是血气心知的性,也就是生理的性”。试举《论语》中以下诸段代表宋儒气质之性的话: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子罕》)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先进》)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季氏》)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阳货》)
以上诸例中,“狂”、“侗”、“悾悾”、“愚”、“鲁”、“辟”、“喭”、“中行”、“狂”、“狷”、“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狂”、“矜”、“愚”等等都属于性的范畴,故由此无法得到气质之性是“相近”的结论。*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第78—79页。按:所云《子罕》当为《泰伯》;所引《季氏》,未引“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徐先生继而在后文中补充说:“仅从血气心知处论性,便有狂狷等等之分,不能说‘性相近’;只有从血气心知之性的不同形态中,而发现其有共同之善的倾向……‘进取’、‘不为’、‘肆’、‘廉’、‘直’,都是在血气之偏中所显出的善,因此,他才能说出‘性相近’三个字。性相近的‘性’,只能是善,而不能是恶的;所以他说‘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雍也》)此处之‘人’,乃指普遍性的人而言。既以‘直’为一切人之常态,以罔为变态,即可证明孔子实际是在善的方面来说性相近。把性与天命连在一起,性自然是善的。”*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第79页。按:所引“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枉”当作“罔”,其下文即作“罔”。
不过徐先生虽然对朱熹有所批评,但是他最后的结论,还是体现出宋儒的思想传统,即将孔孟思想联系起来,以气质之性作解。当然,以上的分析仍有一些不妥之处。其所言的“狂”、“侗”、“悾悾”、“愚”、“鲁”、“辟”、“喭”、“中行”、“狂”、“狷”、“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狂”、“矜”、“愚”等“血气心知之性”,其实都是血气之一偏。而血气之一偏是无法体现性的全部内容的。《韩非子·说林下》引孔子之语“民性有恒——曲为曲,直为直”(详后文)。刘卲所作的《人物志》,开篇《九征》就言:“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着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人物志》以五行论性,即“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有“圣人”亦有“偏至之材”,还有“固而不端则愚”、“狷介之人”等。其所讨论的“愚”、“狷”等特性,与孔子之语有相同者,亦有不类者,然则其表明“偏至之材”虽彼此有所突出有所差别,但是其根本是相同的,都属于同一个阴阳五行系统。种种特性其有着相同的系统,只是功能有所偏至。就此而言,似可以言说“性相同”。
至于徐先生所说的“从血气心知之性的不同形态中,而发现其有共同之善的倾向”,这恐怕就更体现着新儒家的一些理念色彩。如徐先生所说,“‘进取’、‘不为’、‘肆’、‘廉’、‘直’,都是血气之偏中所显出的善”,可是孔子也说了“荡”、“忿戾”、“诈”等特性,这恐怕就与善无甚关系了。
那么说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前引孔子语中提到“狂而不直”,也说到“古之愚也直”,《论语·为政》篇还有“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颜渊》篇有“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相近,《公冶长》篇载“子曰:‘孰谓微生高直’”,《卫灵公》篇记“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季氏》篇孔子论“益者三友”有“友直,友谅,友多闻”,凡此诸例似乎说明孔子是推重“直”的。但是有“直”却未必能说是“性相近”。《泰伯》篇有“直而无礼则绞”,《阳货》亦有“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之语,可知“直”仅是一个基础,还需要其他的来进行引导,如果仅有“直”,就很可能变得“绞”,或者变成某种“讦以为直者”。并且,不同的语境下对于“直”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子路》篇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直”有着特定语境下的特殊含义。此外,《韩非子·说林下》中孔子说过“民性有恒——曲为曲,直为直”,表明人性并非只有一面,而是既有直的地方,也有曲的地方,单纯用善或恶的一种特质来指代性是说不通的。
另外,徐先生所说“把性与天命连在一起,性自然是善的”,也是难以讲通的。在早期的思想世界中,天命其实是不可测的,“天命”与“善”没有必然的关系。《尚书·召诰》载周公之语:“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可见“天命”不是只有“吉”的,也会作“凶”。天命为善的观念,主要是由后代尤其是宋人的思想萌发而来。孟子虽然认为人性善,但也不是从天命的角度来论证的。另外,《论衡·命义》还记有汉代很流行的“行善得恶”的“遭命”之说,亦可证“天命”不一定为善。
由《孟子》之说来解“性相近”的学者还有很多,如牟宗三先生也由上述《孟子》中“牛山之木”章,将“相近”解释为“发于良心之好恶与人相同”,并说“孔子恐亦即是此意。如是,孔子此句之‘性’当不能是‘自生而言性’之性,亦不必如伊川讲成是气质之性。”*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85页。其后蔡仁厚先生也从《孟子》此章出发,指出古人语辞使用并不严格,认同朱子“以‘相同’解释‘相近’”,从而认为“孔子所谓‘性相近’的相近,和孟子所说的相近,意思应该是一样的”,“性相近”之性“应该是人人皆同的义理之性”。*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第105页。
目前就出土的《性自命出》等材料来看,善恶与性相关,确实是当时孔子学派的一个观点。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好恶”是性,但“好恶与人相近”,却不仅可以说是性相近,甚至可以说相同(如上述牟宗三先生之观点)。因为我们谈“好恶”,讨论的实际上是抽象的有无的问题。但谈到“好恶与人相近”,就需要考虑“好恶”具体的细节。《性自命出》篇就既说“好恶,性也”,“善不善,性也”,也说“四海之内,其性一也”,这种“性一”就是从抽象共性处立说。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徐复观、牟宗三、蔡仁厚几位先生的结论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皆从赵歧之说,将“其好恶与人相近也几希”的“几希”解释为“不远”,继而得出结论。但这种解释不见于他书,恐怕不能信服,还是将“几希”解释为“甚微”更好。*参见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76页;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64页。《孟子·离娄下》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也宜解释为“甚微”。郭店简《性自命出》所谈到的“四海之内,其性一也”,此处之“性”也难以归结为宋儒、新儒家所说的“义理之性”,而应是《性自命出》篇“或动之,或逆之,或实之,或砺之,或出之,或养之,或长之”的性。
唐君毅先生指出:“其所谓相近亦当涵孟子所谓‘同类相似’、‘圣人与我同类’。”*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第39页。此说有可能得自于戴震。*参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全集》第1册,第176页。金景芳先生曾经指出:“‘相近’包括两层意思。第一,从人之性对犬之性、牛之性来看,人与人为同类,所以说‘相近’。‘相近’表明人有共性。第二,从人类自身看,人与人虽属同类,但智愚壮羸万有不同。所以应当说‘相近’,不应当说相同。这表明人又有个性。总之,二者都是指人的自然性而言。‘习’则不然。‘习’是指人的社会性。”*金景芳:《孔子的天道观与人性论》,吕文郁编:《金景芳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82页。其弟子李景林先生则进一步指出“性”与“习”相对而言,则性为先天、自然;“习”为后天,属社会性的修为。所以,此处言性之范围,以“生之为性”之说。孔子在这里实质上是从人之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上规定人性的内容。“相近”是从人之为“类”的共性角度来讲“性”;人可因“习”而相远,禽兽却不能“相远”,所以这里的“性”应指人之异于禽兽者,即人的本性道德性。*李景林:《教养的本原》,第60—62页。李先生之说,接近于孟子对人性的定义。
唐君毅、金景芳、李景林三位学者从共性说类相近,逻辑上是可通的。可是唐先生所引孟子之语,还需要进行讨论: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
人之感觉官能口、耳、目等相差不远,确实是相近的。不过这其实也应该属于才性的范畴。上文已经提到,戴震关于才性相近的意见并非不破之理。而且孟子指出“圣人与我同类”,并非只是简单的证明感觉官能的相近,而是为了推理出:“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这是一种常见的类比推理,但是此处的类比推理并不具有必然性。因为口、耳、目是感觉器官,和能够思考、判断的心,并不是同质。另外,孟子言“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其实正好可以说明在时人观念中,圣人与普通人是有差别的。故三人之说在哲学上是有成立可能性的,却未必是孔子本意。
二、《成之闻之》简中的“性”论
通过对以上种种说解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过去学者的意见仍存在着一些问题。现在郭店简中的《成之闻之》篇,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信息。
《成之闻之》篇,参考时贤意见,间以己意,可以写定为:
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分之;即于能也,则犹是也;虽其于善道也,亦非有译(怿)娄(足)以多也。及其溥长而厚大也,则圣人不可由与殚之,此以民皆有性而圣人不可慕也。
《成之闻之》篇说“民皆有性”,《性自命出》篇有“四海之内,其性一也”,也也是讲民皆有性;上博简《诗论》中则多次论“民性固然”。由此经抽象出类的属性之后,就是唐先生所说恶“同类相似”、金先生的“人与人为同类,所以说‘相近’”。但这种相近实际上就如同前文所讲的“好恶与人相近”一样,论证下去“性”甚至可以是相同的。但从抽象共性处立说的话,性的相近甚至相同,对于孔子性论研究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孟子还只是由口、耳、目等器官之相似来论证心性,到了程朱就由此得出义理之性相同的结论了。所以,对于“性相近”的解释,似不应从共性之说入手。
郭店简发表以来,已经有相当学者注意到了《成之闻之》与“性相近”解释上的联系。只是考订的文字可能有所不同,在此我们作一简单介绍。
郭沂先生认为:这种性不同的观点直承孔子,与孔子的人性论十分接近。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性只是相近而已,但不相同。孔子又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同上)这种思想反映在本章里,就是“民皆有性,圣人不可慕也。”民之性与圣人之性不但不同,且各有一定,不可习,不可移。另外,本章的“中人之性”之说亦来自孔子。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揣摩孔子之意,此处之“中人”乃就性而言也。*郭沂:《郭店楚简〈天降大常〉(〈成之闻之〉)篇疏证》,《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第65页。
李学勤先生指出:这一章,在用词上很容易看出是本于《论语》,在思想上也尽可能把孔子的话综合起来。章文云“民皆有性”,又说“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别之”,这是“性相近”,而且是性善论的雏型。说“及其博张而厚大也,则圣人不可由与效之”,“圣人不可慕也”,这是“习相远”,也合于“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章文只谈中人之性,没有说到中人以下,正合于“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李学勤:《试说郭店简〈成之闻之〉两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458页。
按:《成之闻之》简文,难点在“译娄以多”。“译”,今读为“怿”,《尔雅·释诂上》:“怿,乐也。”“娄”,疑读为“足”,二字古通。*参见张儒、刘毓庆:《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多者胜少者,故引申为胜之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316页A。
根据我们的考释,郭店简《成之闻之》篇的文意大致如下:圣人之性和中人之性,初生时没有什么分别,在能力方面也是一样;即使是对于善道而言,也不是特别喜好而胜于他人。当各自的性充分发展之后,中人和圣人就有了差别,中人想像圣人那样尽其性就办不到了。所以说民性皆有定数,圣人不是仿效而成的。
从《成之闻之》这一章的人性论来看,圣人与众人之性,不仅“生而未分”,在能力方面,还是如此;即使面对善道的态度,也难以区分。但是很明显这里讲的是生性而非性。性在尚未定型之时,圣人和中人是难以分别的。这时的性尚未充实、完成,好比一个待填充、发展的气囊,气囊的外形或大小不同,一旦充实之后,圣人与中人就判然有分。所以这里的“性”,主要讲的是人的天分层面。在《成之闻之》中,我们可以找到圣人、中人的讲法,性有划分品级的迹象。所以朱熹所说性是“以其初而言”,从本篇来看是有道理的。但是简文有“虽其于善道也,亦非有怿足以多也”之语,可知性并非定然与善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性与善是互相外在的。由此推断,“性相近”也不是性善论。
郭店简《成之闻之》一篇,是目前可见离孔子时代最近的材料。因此其中关于性的说法可以体现时人的认识,在对“性相近”的解释上要更为可靠。可以发现,《成之闻之》中关于性的论述涉及天赋、品级,与“性三品说”其实并不矛盾,但还未与行善、性恶之说联系起来。
总之,《成之闻之》一篇对“性”的论证,主要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性”是“生而未分”的,有品级之差别;二是“性”的这种差异,经过“溥长”、“厚大”之后,才会显现出来。所以“性相近,习相远”,是说人性初生时相近,经过习染之后,就表现出差别来了。显然,这种差别,不仅包括圣人和中人、下人的差别,也包括同为中人、下人者之间的差别,因为天所赋予每个人的性都不同。由此来看,过去很多学者的解释,恐怕过度诠释的地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