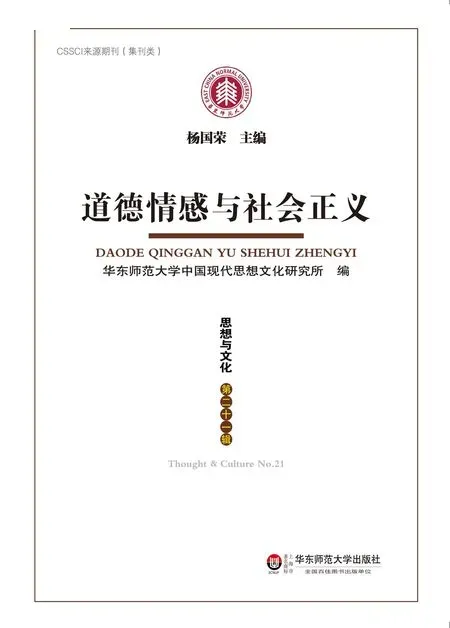何谓儒商?仁义、生生与企业家精神
一、引言:“儒商”概念之哲学反思
儒家精神如何在现代社会寻求新的体现?此问题已在当代儒学探讨中热议数十载。有鉴于商业机构与企业家们在现代社会所起的重大作用,不少学者开始聚焦于商业活动,进而审视其与儒家价值的关系。诚然,时至今日,企业家在其本业范围,藉由本身创意与产品,于改善人们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发展等层面,已经做出有目共睹的贡献。他们在创业与经营时所展现的眼光与决心,需克服的困难险阻,可以让人联想到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畏精神。此外,亦有企业家加入各种组织团体,以服务同行与大众。尤有甚者,进而慷慨解囊,捐助金钱物资以协助赈灾济贫;又或是注资推行文教工作,乃至出于忧国忧民之心而针对重大议题提出忠告建言,相关实例实已俯拾皆是。
就欲接通儒家与现代社会的儒学研究者而言,上述企业家种种成就,的确值得予以积极肯定与发扬,所以“儒商”一词乃应运而生。从历史沿革来看,儒商虽然是晚近才出现的名词,实则此种融合儒者与商人身份的思维,并非到现代才出现。据史家考察,明清之际以来,弃儒就贾早已逐渐形成一种风气。从商人士的社会贡献也日益受到肯定。如此看来,“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王阳明﹚,“士商异术而同心”﹙空同子﹚,“良贾何负鸿儒”﹙汪道昆﹚等说法会陆续出现,也就不足为怪。*关于这个主题,余英时先生曾作出详尽的探讨。参氏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第95—165页。
但要注意的是,以上这些新解固然可以帮助我们将儒与商这两种身份予以结合,作为提出“儒商”概念之佐证。不过在历史发展中,真正使商人地位提升乃因清末救亡图存之实际需要,而非来自以儒入商论调的影响。此外,上述说法在理论上也有待加强。因为在概念层面,尚须考虑儒商与儒家传统观念之一致性问题。就商业活动而言,获利动机是基本出发点,如何运用现有成本获取最大的利差,是商业活动的核心,也是从商的必要考虑。如此一来,若是我们想到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法,孟子不断强调的义利之辨,乃至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则从先秦儒下迄汉宋之儒对用心于“利”的保留,甚至否定,就与上述的获利动机有所抵触。此外,儒家的宗旨一向重在成圣成贤,或至少退而求其次:成为君子。所以修身成德才是本业要务。就算证明从商不会与圣贤之道产生冲突,但实在也不能提供什么助力。以上反省也可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在当今社会儒家思想并未广泛地在商界人士中产生影响。儒商一词也更多地是由学界倡导,而未在企业家中蔚为风潮。如此一来,儒商概念是否能成立呢?若可以,又如何将其与儒家观点予以调和、连结?这就是必须予以正视并作出理论疏导的问题,不宜轻轻地一语带过。
本文即基于以上理由,而尝试以孔孟论仁义,以及《易传》“生生”等儒家核心概念,进行儒学的现代诠释。并以此为框架,在理论上解释企业家精神如何在现代与儒家宗旨相互契合。首先,从何谓“义先于利”、“利以义制”、“以利行仁”的角度切入,对仁、义、利之间的关联提出相应的解释。另外,并藉由对“生生”的现代诠释,提出以“价值创造”取代纯粹道德修养的儒家实践观,使商业与修身成德同样取得在儒家架构下的合法性。这些尝试,一则赋予商业除了利益导向之外的更丰富内涵;二则欲使儒家淑世之核心价值,透过企业家善行之实例,在现代社会具有更多元而鲜活之展现。
二、结合儒与商的先声
自古以来,对儒者成就的关注实皆聚焦于道德之成圣、成贤工夫,对其他领域如商业与艺术等并未重视。特别是自古以来的重农抑商观念,对于商业活动的评价向来不高。真正以儒学大家身份而对商人作出积极肯定,则以王阳明肇其始,影响也最为重大。首先,他将治生与讲学视为一体之两面,而提出“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的说法:
先生曰:“但言学者治生上,尽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91页。
在此王阳明将治生亦视为讲学之一个环节,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否则会助长营利之心。重点是能不让治生之务妨碍学者从事致良知的工夫,那么就算是终日做买卖,也不害其为圣为贤。质言之,阳明勉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作买卖”既是百姓日用中之一事,自然也是良知所当致的领域。此种说法是合乎其致良知之教的。*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第94页。所以王阳明进一步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说法。*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五,第1036页。认为士农工商一样都在做尽心的工夫,只要所做之事有益于生人之道,则可谓是志同道合。余英时指出,王阳明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可见尽心二字分量之重,商贾若是尽心于其所业即同是为圣人之学,决不会比士为低,这是“满街都是圣人”之说的理论依据。墓表中明白指出当时士好利尤过商贾,只异其名而已,王阳明想要彻底打破世俗上“荣宦游而耻工贾”的虚伪的价值观念,其以儒学宗师的身份对商人的社会价值给予这样明确的肯定,不能不说是新儒家伦理史上的一件大事。*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第106页。
事实上,在王阳明的时代,这种平章儒与商,而主张能以儒家精神从事商业活动的“以儒入商”思维,可说日渐形成一种呼声。明人王献芝曾引用空同子的类似论调,而指出“士商异术而同志”,其言来自李梦阳《明故王文显墓志铭》。原文为:
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李梦阳:《空同集·明故王文显墓志铭》,收录于王云五主编:《四库全书珍本》八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4页。
之所以断定“士商异术而同心”,其理由在于“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此说与王阳明所谓“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如出一辙。都是在强化士与商同归而殊途的特质。只要能“利以义制”,士商之间就不再存有藩篱。有了这些说法为基础,无怪乎另一明人汪道昆得以呼应这种想法,而大胆断言“何负闳儒”:
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彰彰矣!*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五,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146页。
明代之后,这种连结儒与商的思路,也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清人沈垚在《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中所说的一段话,曾经一再地被学者征引,以作为论证明清时期士商之间界线已泯的主要线索。沈垚在文中说:
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收入吴兴丛书(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线装本),1918年,第12页。
“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的想法在明清以后虽已陆续出现,但要注意的是,以上对于士农工商四民的新诠,还尚不足以动摇传统的四民论和重农抑商政策。以上对商人地位与价值重新进行思考后所提出的四民新论,在雍正皇帝于1724年和1727年两度重申四民秩序和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后,实遭遇明显的挫败。就算明末清初的儒家欲以四民不分来改变国家的政策和社会的观念,雍正皇帝的两道谕旨,则是以官方的权威宣告了他们的失败。主张士、农、工、商平等的论调,即使在它最蓬勃的时候,都没有居于思想的主流,在雍正皇帝再度肯定传统的四民论后,更是流于沉潜,纵使未完全消失,但至少在光绪初年以前,它的声音始终是微弱的。*参见李达嘉:《从抑商到重商:思想与政策的考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2期,2013年12月。所以当我们在诉诸这些说法为“儒商”概念奠基时,必须同时意识到这些在思想层面上的发展与努力,仅为儒者与部分由儒入商者对儒与商二者关系的重新界定。这是一种新思潮的萌芽,既在理论上尚未发展成熟,也没有直接造就后来商人地位的提升,在清朝末期以前,重农抑商的意识形态实仍居于主流地位。
此外,据学者考察,真正使商人地位得到提升的,实乃出于清末救亡图存之迫切需求,而非以儒入商的思想启迪。清廷面对西方船坚炮利的威胁,最初以提升军事力量的自强运动为对应之策。然因与西方国家进行“兵战”屡遭挫败,同时出现严重的漏卮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开始受到强烈挑战。光绪初年,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首先提出“商战”重于“兵战”的主张,一些思想较新的知识分子,也相继阐扬重商议论。加上在甲午战争中国为日本所败,急迫的民族危机感,使得郑观应的“商战论”盛倡于一时。清廷在内外交逼之下,不得不改采重商政策,以挽救危局。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四民论至此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由工商致富的商人活跃于各个层面,也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李达嘉:《从抑商到重商:思想与政策的考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3页。以上史实也解释了为何从清末到现代,商人地位虽已大大提升,乃至后来居上,但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却并非普遍地存在于商界人士之中;“儒商”一词也更多的是被学界所倡言,而未在商人意识中生根。
三、义利之辨vs.获利动机
在上一部分,本文解释了明清时期以儒入商的思想沿革,并指出其为一种新思潮的萌芽,然而并未直接造就后来商人地位的提升。在历史发展中真正抬高商人价值的动力,乃清末救亡图存之实际需要,而非受到论者对四民的新解之影响。接下来将继而讨论,就思想层面而言,以上说法在理论上亦尚未发展成熟,如何将传统儒家思维与商人角色结合,还有理论问题尚待解决。
商业活动本质上是营生之手段,藉由劳务与货品交换过程中获取的利益以维持生活所需,并同时运用各种手段将获益极大化,如此则可继而累积财富。是以就商业活动而言,此种获利动机﹙profit motive﹚是其核心,此实适用于古今中外的一切商业运作模式,也是经济学中广为人知的基本概念。若从人际互动角度检视获利动机,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孔子在《论语·里仁》篇中有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分判,以及“放于利而行,多怨”之警语。可以说,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若以利益考虑为来往前提,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也有害于人际关系。这可视为儒家义利之辨立场的滥觞。此态度进一步为孟子所发展: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
舜与跖之分,关键即在于重利与重善之别。实与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路一脉相承。另外,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也讨论了重利而轻仁义所可能引发的流弊: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唯恐梁惠王为政上抱持孳孳为利的想法,于是当下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答复梁惠王是否“有以利吾国”的问题。并且指出,一国若从君王以下处事都抱持着如何对自己有利的想法,导致上下交征利,适会导致国危的结果。此外,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对江都王之问曰:“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名句,也为义利之辨提供了鲜明注脚。到了宋明理学时期,朱熹据此反驳陈亮“义利双行”的见解,王阳明亦在《答顾东桥书》中痛斥功利之毒*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五,第63页。。可以说,义利之辨由先秦开始,历经汉代,一直到宋明时期都是儒者行为的主导思想。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谨守义利之辨,是否即表示义利之间一定构成冲突呢?以董仲舒为例,他固然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严分义利之辨的立场,却也说过在义先于利的前提下,人也要义利并养:
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人必须身心俱养,是则义与利皆为维系生命之所需。他在《贤良对策》篇说明了强调义利之辨的理由,实为有鉴于周室之衰肇因于其卿大夫缓于谊(义)而急于利,乃力劝汉武帝:“尔好谊,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其用意在针对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劝告他“能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因为“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春秋繁露·玉英》)可见董仲舒并非抱持义利不兼容的态度,而是反对因求利而害义,因而主张义利要并养。
明代商人中亦有接续尝试将获利动机与义利之辨做出调和者。例如前文提到的李梦阳《明故王文显墓志铭》尝论“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因而有“利以义制”之说法。其意不外乎若能以义为前提,则求利也不是坏事,甚至可以与高明之行兼容。韩邦奇在《国子生西河赵子墓表》表达了类似意涵,并以本心作为义利合一之基础,提出“义利存乎心”的新解:
圣贤岂匏瓜哉!傅说之版筑,胶鬲之鱼盐,何其屑屑也。古之人惟求得其本心,初不拘于形迹。生民之业无问崇卑,无必清浊,介在义利之间耳。庠序之中,诵习之际,宁无义利之分耶?市廛之上,货殖之际,宁无义利之分耶?非法无言也,非法无行也,隐于干禄,藉以沽名,是诵习之际,利在其中矣。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人,是货殖之际,义在其中矣。利义之别,亦心而已矣。*韩邦奇:《苑落集》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47页。
以上这段话,处处看到陆王心学的痕迹,其独到之处在于:不以任何职业或身份,而以孟子所阐扬之本心作为衡量义利之标准。若求得本心,则不必拘于货殖或诵习之形迹。点出无论在诵习或货殖之际,皆有义利之分。因为即使在诵习之际,但若心系干禄,沽名钓誉,也是汲汲于利;反观从事商业之人,在行为处事之中,若能秉持在非其义、非其道的情况下“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人”的原则,则义亦在其中。韩氏虽非传统意义上之大儒,然此论实能紧抓孟子“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的成德要义而有以扩充之。
不论是李梦阳强调的“利以义制”,或是韩邦奇“义利存乎心”的新铨,都是力求融合义与利的尝试,强调义与利不见得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特别是韩邦奇对义在货殖之中的见解,点出求利或求义与职业身份无必然关系。各种事业或活动皆介于义利之间,汲汲于利或是义,端看个人之动机或心态为何,可谓能跳脱出传统思想的窠臼而另辟蹊径。
质言之,以上种种结合义利的论述,核心在于从正当求利与不当求利中做出区分,若是属于正当求利,则为“利以义致”、“义在其中”;相反地,若一味不当求利,就成为唯利是图的小人。但重点在于,裁决正当与不当求利的判准究竟为何?这些说法都只指出有此区别,却未能告诉我们做出此划分的明确标准为何。这样就难以界定何种商业行为乃高明之行而虽利而不污,也无从判断何种货殖是义在其中。因此,要界定何谓儒商,就必须提供这个对正当求利的定义,而且这定义必须能够与儒家的核心思想一致,才算是以儒入商。这就是本文以下要讨论的内容。
四、利、义、仁:“义先于利”、“利以义制”与“以利行仁”
依上述,明代商人结合义利的尝试,焦点在于对正当求利与不当求利做出区分,若能“利以义制”,则属于正当求利;若孳孳为利,则为不当。但对于何谓“利以义制”的问题,则并未提出说明。以下将从孔子、孟子乃至阳明的说法中寻找线索,探究对儒家而言,如何在“义先于利”的原则上“利以义制,并进而“以利行仁”。
质言之,孔子虽指责喻于利的小人,却并非一味反对追求利益。而是强调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亦即劝人自省:是否以适当的方式获得利益?他真正反对的是以不义的方式获取利益,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孔子抱持的是“义先于利”的观点。他并不排斥义与利并存的可能性,但反对由不义的方式取得利益。此思路亦为孟子所继承。孟子虽认为圣贤与小人之分,即在于为利与为善之别,也并未排除对利益之追求。相反地,从前述他与梁惠王“王何必曰利”的对话来看,他点出若“上下交征利”,结果将反而对大家都不利。若是大家以仁义为先,反而会在相互照料的基础上,产生“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的最佳结果。在此可以说孟子除了主张“义先于利”之外,也抱持着“义可生利”*有学者指出,孟子对义与利之间关系的看法,可以从四个层面进行考察,分别是“取代模式”的“以义斥利”、“条件模式”的“先义后利”、“化约模式”的“义即公利”,以及“因果模式”的“以义生利”等四种类型。并指出孟子存在有若干“先义后利”的成分,也确实有肯定公利而轻私利的倾向,但更正确地来说,他是在动机或存心上唯“义”是求,属于高浓度的“以义斥利”类型;而又乐于将“利”视为由“义”所衍生的必然结果,接近于“以义生利”的类型。参见叶仁昌:《孟子政治思想中义利之辨的分析:四种主要类型的探讨》,《政治科学论丛》第50期,2011年12月,第1—36页。就“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此命题而言,笔者赞同叶文之分析,肯定孟子思想中具有“以义生利”的思想成分。的看法。其中所谓利,可能涉及公利或私利,或甚至兼指二者而为言。*李明辉指出,单从“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段话来看,实难判断此中所谓利的性质为何。一方面可能意谓为人君、为人亲者之私利,另一方面也可能指的是整个社会秩序之和谐,因而涉及公利。参见氏著:《儒家与康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85页。笔者以为,非独此段,观《孟子》全书,其言利之论述模式,往往串连家、国、天下三者而为言,亦即公私二层面之利连带而言。在下面所引述关于孟子与宋牼之对话,也是相同的模式。职是之故,或许可以将孟子此处论述,视为同时涵盖公私两面之利而为言。孟子另一段话也透露出义可导出利的类似看法: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下》)
在这段话中,孟子固然仍维持义先于利的论述主轴,但也同时重复了《梁惠王》篇“义可生利”的论调,强调“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就孟子而言,虽然为人处事上须以“义先于利”为原则,但也不排斥追求利益。并为让人们更乐于行仁义,还指出“义可生利”的附带好处。
由此我们即可理解,何以追求富贵对孔子而言是合情合理的动机。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甚至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可见孔子认为富不是不可求,但要有原则,不能伤天害理。若不以其道得之,则富贵不可求,贫贱亦不可去。可以断定,对孔孟而言,“义先于利”并不蕴含“义利互斥”,他们会认同人们力求在义与利上两全其美的努力。将此原则应用在商业上,是要区分做人与维生两个层面。商业作为维生手段,虽以获利为目标,但不能凌驾做人层面的仁义底线。也就是说,做生意必须有获利考虑;但做人就不能只看利害,而是凭良心。以此来看商业活动,企业经营本就以获利为目标,而获利及累积财富,可使生活过得更好,只要能“以其道得之”,自是可以为之。不过,其中所谓“道”、所谓可求之富所指究竟为何呢?我们可以从孔子另一段话得到启发: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设若商业除了作为一种己立、己达的事业之外,同时又能具有立人、达人之功效,则就符合仁者精神。在此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又可分别从两个层面来作解释。首先,在产品方面,企业家推出好的产品,好的产品给自己带来获利,此为己利己达;但在同时,这些商品或服务也为消费者带来便利或快乐,这就具有一种社会功效,而为立人达人。在企业管理方面,企业家聘用员工,藉用员工的生产力创造获利,这是己利己达;在此同时,企业家也提供员工满意的薪资与福利,使其安居乐业,则为立人达人。以上所述互利互惠的状况,即可视之为“利以义制”,以正当的方式获利。此种互利互惠的精神,即可为空同子“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的说法奠定基础,不损人利己,而共同受惠,自然虽利而不污,才能算是“利以义制”。并能为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的主张提供补充:
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五,第1036—1037页。
王阳明之所以肯定四民异业而同道,是因为四者皆能做到孟子所谓尽心的要求。而尽心之关键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不论是利器通货,或是修治具养,若能有益于生人之道,就是尽心,既然都能尽心,士农工商四民虽然事业不同,却殊途同归,而为同道中人。依上述,秉持互利互惠的精神从事商业活动,即是藉由通货而进行有益于生人之道的活动,并使所谓“有益”之意涵在概念上更加明确。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还有另一层更深远的意涵。若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描述来看,这实与孟子“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见解相互呼应。在做到己达之后,不只局限在独善其身,而能进一步以博施济众的方式兼善天下。这样的行为,孔子给予的评价是“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直达圣人之境,可谓推崇备至。将其落实在企业家精神上,则可诠释为:在本身累积财富、提升生活质量到了一定程度后,同时运用所累积的财富去帮助别人,而泽加于民。这种“以利行仁”的仁民爱物之举,乃是比“利以义制”更上一层,从互利互惠升进至利他的境界,成为仁心更高一层的表现。从孔子的角度来看,能做到“利以义制”以及“以利行仁”,即可算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即可视为儒家本质在商业上的体现,而足可担当“儒商”之名。
五、由道德修养到价值创造:“生生”的现代诠释
即使在提出如上的新铨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对传统儒家而言,修身成德才是本务。商业就算可“利以义制”、“以利行仁”,目的终究不是成君子或成圣、成贤,如此一来,就算事业再大、做了再多慈善事业,终究仍非传统意义上的儒者。我们固然可以援引前述“以利行仁”的概念,指出其体现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精神,而这种表现孔子亦称许为仁。再补充阳明所谓“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的说法,以强化连结儒与商的合理性。论者仍可质疑,这些新解充其量只能证明:从商并不违背儒家信条,企业家慷慨解囊的善行符合孔子论仁的精神。只是更深入追究,儒家的工夫重点一向在追求内圣外王的境界:要经由不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工夫,达到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境界,或是孟子对“践形”﹙《孟子·尽心上》﹚的圣人要求,并实现其仁政理想于政治上。以此来看企业家,其本业是提供商品与服务,经营管理一家企业,其性质与专心致力于道德修养的儒家毕竟不同。王阳明告诉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致良知的工夫,而使一念之发动无有不善。不过对于任何人而言,要同时兼顾竞争激烈的商业活动,并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而无有不善,恐怕都是力不从心的苛求。那么,是否有可能在儒家的概念架构下,将商业纳入其工夫实践之一环呢?笔者以为,我们可以从《易传》的“生生”概念中汲取资源,对儒家的实践观提出新的诠释,以解决此问题。
质言之,儒家“生生”的要旨可以从存在与实践两个层面来看。就存在层面而言,《周易·系辞上》揭橥“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阐明生生涵盖成象之乾与效法之坤,乾坤并行实为“生生”之内涵。另外,也可从一阴一阳不断递嬗更迭以解《易》之“生生”,意指一生生不息、持续创生的过程。若从实践层面来看“生生”,则可将一阴一阳之道与君子之道衔接起来,勉励人须上体天道“生生”之德,努力不懈地进行人文化成的淑世事业。是以就“生生”的角度而言,人虽由天道所创生,但也可藉由道德行为体现天道。此种天人合一的关系,还可以从宋儒“理一分殊”的概念进一步予以说明。刘述先指出“生生”之天道作为理一,乃吾人之终极托付,以及不断发挥生命力与创造力的依据;“生生”落实在人道上,就成为分殊,乃吾人不断发挥生命力与创造力的过程。*刘述先:《两行之理与安身立命》,《理想与现实的纠结》,台北:学生书局,1993年,第231页。而且这种创造力的显现并非只局限于道德行为,实可以涵盖种种不同专业领域的创造活动:
理一而分殊,超越的生生的精神当然不必具现为现代社会的拼搏精神,但也不必排斥它在现代寻求新的具体的表现的方式。于是有人可以由学术来表现自己的生命,有人可以由文学艺术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当然也可以有人由企业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但我们应该了解到,这些仍然都只是生生的精神的有局限性的表现。一方面我们由分殊的角度肯定这些成就,当下即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像宋儒那样体悟到,由超越的角度看,尧舜事业也不过如一点浮云过太空。这才是两行之理的体现。*刘述先:《论儒家理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理想与现实的纠结》,第125—126页。
理一而分殊,超越的“生生”的精神要在现代寻求有别于传统的、全新的具体表现。“生生”之天道不一定只限于道德行为之显发,也可以表现在学术、文学艺术甚至是企业精神上。“生生”之仁是超越特定时空,历万古而常新的普遍性原则,即所谓理一;有限的个体所实现的则是分殊,受到自己的材质、时空条件的局限。这样我一方面要冲破自己材质的拘限以接通无限,另一方面又要把创造性实现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之内而具现一个特定的价值。这一价值不必一定是狭义的道德,也可以是科学、艺术、经济、技术,乃至百工之事。*刘述先:《方东美哲学与当代新儒家思想互动可能性之探究》,《现代新儒学之省察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第249页。如此一来,“生生”的实践观即可诠释为立足于理一,再分殊于人生各层面之多元价值实现,成为以有限之人接通无限天道的创造活动。
依笔者之见,若将创生万物的天道或天理定义为“理一”;人与天地万物等被创生的存在物,及其一切存在活动与现象则是“分殊”。就修身成德而言,道德行为固然可体现天道,成为一种具普遍性的模范或准则。但其他领域如科学、艺术、商业等皆为分殊,皆是“通于”而非“同于”天道或理一。这些不同领域的事物虽作用与特性不同,彼此价值定位实应对等,不必仅只以道德独尊,而矮化或忽略其他领域。那么我们在考虑“生生”的实践层面时,也就不必将焦点仅局限在修身成德一途。人类在其他领域的创造活动,也可以是儒家肯定的实践工夫,皆可由分殊通向理一。*以上对“生生”与“理一分殊”的诠释,乃依据笔者另一篇讨论“生生”现代诠释的专文而来。在该文中,笔者指出仅诉诸道德进路可能会出现的理论问题,而尝试将天人合一诠释为:分殊虽不直接“同于”作为天道之理一,但却“通于”理一。在此所谓“通于”,意指天或理一同时具备普遍性、绝对性与无限性。但分殊或人的创造活动,包括道德实践在内,则顶多只能达到普遍性,不能宣称有绝对性与无限性。依此主张将儒家的实践观予以扩展,在道德实践之外,纳入其他领域的人类创造活动如科学、艺术、商业等。参拙著:《论儒家生生的现代诠释》,收录于《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哲学探索:刘述先先生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2014年,第127—156页。
顺是,以上将“生生”意涵延伸至道德实践以外的其他技艺、专业之论点,可以发展为更细致的表述。其做法是:将“生生”在实践层面的诠释,从道德修养扩大为价值创造。顺是,前一个“生”字可视为动词,而有延续、创新、提升之意;后一“生”字则作为名词,指有价值的事物之存在。“生生”就可定义为各种正面价值的不断创造、创新与提升。如此一来,儒家价值理想的表现,将不必只限于成德的道德修养。举凡具有正面价值的人类活动,如在学术、科技、宗教、艺术、体育、环保乃至商业等领域持续精益求精,不断做出良好贡献,即可谓体现了生生的要旨;能持续在修身成德、专业技艺、社会影响等任一方面有所提升与帮助,也就是儒家精神的现代表征。*张子立:《论儒家生生的现代诠释》,见《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哲学探索:刘述先生八秩寿庆论文集》,第153—154页。这样的儒家特性表述,仍将保有适当的理想性,但其内涵实能兼容多元社会中不同专业相互分工、价值对等的现况。
此“生生”定义落实在商业活动中,商品与服务的不断发明、改良与提升正是一种正面价值的创造与提升工作,不但促进技术与技艺之进步,也使人类生活各层面同时获得改善、更加便利。尽管有别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道德修身工夫,却也是另一种“生生”精神的体现。商业也就同时可视为一种儒家式事业。在商品或服务的不断创造、创新与提升过程中,企业经营者必须持续因应所面对的问题或瓶颈,克服新的挑战。证诸当今的商业现状,所谓永远畅销的商品,一直获利的公司,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经营模式,可说已属天方夜谭。不败的企业既不可得,真正务实之态度乃永不言败之信念。能秉持上述“生生”的精神进行此任重而道远之工作,誉之为儒商则甚自然而顺适。
六、结语:儒商之后设思考
从明末至有清,一种调整商人在四民中定位的呼声开始浮现。举凡王阳明提出的“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以及“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四民新论;或是李梦阳“士商异术而同心”的看法;乃至汪道昆“良贾何负闳儒”,沈垚“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等论调,在近年来倡导儒商概念的表述中,经常被引述而视为先驱。但从历史发展上观之,这些观点虽形成了一种舆论,却未真能在商人地位与价值的提升上发挥实际效果。这样的发展乃在自强运动之后,商战之论蔚为风潮的推波助澜之下,才逐渐成形。
再从思想上理论融贯性的标准来看,以上说法要如何与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及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说法相容呢?于是本文检视了一些调和义利之尝试。诸如董仲舒主张义利须并养;李梦阳的义利新诠,将正当求利称为“利以义制”、“义在其中”,相反地,若是不当求利,才算唯利是图;韩邦奇另外点明“义利存乎心”:求利或求义,与职业、身份其实并无必然关系。各种事业或活动皆介于义利之间,汲汲于利或义,端看个人之动机或存心。不过综观以上论点,有个尚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裁决正当与不当求利的判准究竟为何?以上陈述都只指出有此区别,却未能告诉我们做出此划分的明确标准为何。这样就难以界定:何种商业行为乃高明之行而虽利而不污,也无从判断何种货殖是义在其中。因此,要界定何谓儒商,就必须提供这个对正当求利的定义,而这定义又必须合乎儒家的核心思想。
本文采取的进路是:借助孔孟对仁、义与利的阐释,以及《易传》中“生生”的概念,进行现代的诠释,以界定此“儒商”概念。首先,孔孟虽强调义利之辨,但也不认为两者无法兼容,亦即不主张“义利互斥”,而是“义先于利”。其意涵是在做人与维生之间做出区分。商业作为维生手段,必以获利为目标,但不能凌驾做人的仁义底线。获利及累积财富,可使生活过得更好,只要能“以其道得之”,是可以为之的。至于所谓“其道”,则藉由孔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原则,界定为互利互惠。企业家透过员工的生产力制成产品,而从中获利,此为己利己达;在此同时,企业家给予员工良好的薪资待遇,推出的商品也为消费者带来便利或快乐,则为立人达人。这种互利互惠的状态,可以用来解释何谓“利以义制”,以及王阳明所谓“有益于生人之道”。若能从互利互惠提升至利他的境界,则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更高层次表现:“以利行仁”。这指涉的是企业家运用所累积的财富去帮助别人,如赈灾济贫,此合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或是孟子表述的“达则兼善天下”。企业家若能做到互利互惠的“利以义制”,以及博施济众的“以利行仁”,则可谓之“儒商”。
有一种可能的质疑是:以上论点顶多只能说明从商与儒家精神并不抵触,企业家慷慨解囊的善行可视为仁的一种体现。但这毕竟不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道德境界,亦非内圣外王的大学之道,既然性质迥异,接通两者的理据仍不够充分。为了因应此问题,本文建请读者思考:身处当今多元价值平等互待、异彩纷呈之世,儒家实践观是否仍只容许修身成德的唯一选项?若把“生生”从仅限于道德行为而扩大至价值创造,并定义为各种正面价值的不断创造、创新与提升,是则儒家价值理想的表现,就不必只限于成圣成贤,举凡具有正面价值的人类活动,如在学术、科技、宗教、艺术、体育、商业等领域持续精益求精,不断做出良好贡献,即可谓体现了“生生”的要旨。就商业活动之运作而言,商品与服务的不断发明、改良与提升,即是一种正面价值的创造与提升工作,在此过程中,又必须持续解决遭遇到的问题或瓶颈,克服接踵而至的挑战。企业家若有此成就,实可谓“生生”精神之现代表现。综上所述,可知儒商乃力求商品与服务的不断改良、创新,同时做到“利以义制”及“以利行仁”的企业家。若以日常用语来说:不断创新、互利互惠、注资公益即是儒商定义。
众所皆知,儒家具有漫长的发展历史,累积了相当丰硕的言谈论述。其中不乏一些人生哲学的思想资源,通过适当的现代诠释,可为创业或企业经营提供助力。例如在吾人事业陷入危机乃至遭遇失败之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怨天尤人。此时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的表述,实为劝人保持冷静、反躬自省以努力再起的金玉良言。“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虽然描述的是孔子对推行儒家理想之坚持,但如果将这种坚持,类比于许多企业家草创事业时所曾面对的轻忽、质疑甚或冷嘲热讽,相信他们也能感到心有戚戚焉。如此我们就能明白,为何儒学研究者会从儒家学说汲取资源,尝试应用于当代的商业或企管领域,进而提出有关儒家式的管理哲学或商道智慧之理论。这些理论对于联系儒学与当代社会,促进商界与一般民众对儒家的了解及兴趣,可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或有论者会从后设层次提出疑问,指出仅凭儒学中有些概念或话语可以用来应用于商业层面这一点,难以使儒商、儒家管理哲学等词语成立。一则商业经营、管理毕竟与儒家事业有所不同,两者性质亦有看似冲突之处,如本文所谈到的义利之辨。二则非独儒家,很多哲学思想与宗教教义都蕴含了丰富的人生智慧,而可经由适当诠释应用于商业领域。如此一来,岂非也都可在商字之前冠以其名?从理论层面看,要在某个专业领域建立儒家式应用哲学,实不能仅满足于零散地摘取个别儒家命题或概念,继而运用于该领域中,更需论证儒家思想本质与此专业领域之特质有何合辙之处。本文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为此类应用儒学于商业、企管领域的工作进行后设证成的尝试,以回应类似疑问。厘清了义利之辨与获利动机并无矛盾,累积财富可藉以行仁,商业运作、企业经营、专业精进与道德修养同样可视为儒家价值创造的实践工作,即是在核心价值层面,点出儒家与企业家以及各种专业人士的相通之处。冀望在踏出这一步之后,吾人可更有备无患地谈论何谓儒家企业管理?何谓儒家商道?乃至进而试图从儒家经典中不断开发其中的人生哲学智慧,以与各种专业领域之中的创造、改良精神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