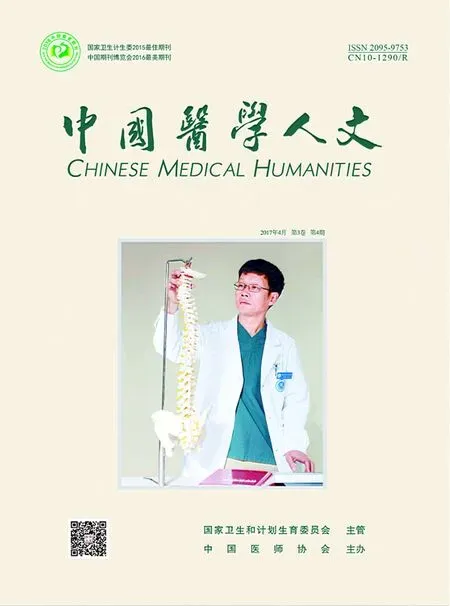衣食住行大于天
——美国华人医生西非之行手记(二)
文/徐 俊
衣食住行大于天
——美国华人医生西非之行手记(二)
文/徐 俊
衣
非洲酷热,摄氏40度以上是常有的事,我们基本上每天都经历45摄氏度。“不识高温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并不觉得太热。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儿子法厄同要求父亲同意他来驾驶父亲的太阳神车。这是一个由神驹拉的喷着烈火的车,连太阳神都感到炽热。父亲答应了,可想而知,法厄同根本经不住火烤……烧焦了。也烧焦了地上的草木,非洲的大片地方变为沙漠,居民的皮肤烧成了黑色……这个故事一直流传下来了。这里每年都要经历连续十个月旱季,很少下雨,天和地都干透了。常常是大汗淋漓,人却很舒畅,是那种干热,不像我原来在广州时的那种湿热,一到36、37摄氏度就受不了。我想这和我们去健身房,常常挥汗如雨,人却很透气是一个道理。身体的毒素,代谢物都随汗而出,伴之而来却是身心的欣快。同时,我去的地方是边远的山村,没有高楼大厦造成的热辐射,那种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感觉要少些。心理上,我们也很清楚这里不可能有空调,也就降低了期望值,一阵清风徐来,虽然没有水波不兴,却有一种遥望太湖,濒临仙境的愉悦心情。
衣服最好能长袖长裤,短袜球鞋,主要的目的是防止蚊虫叮咬。同时,每隔3-4个小时,就要喷一次强力驱蚊剂。不光是要喷在皮肤曝露之处,还要喷在衣服、袜子和头发上面,造成一个气㘯,让蚊虫小咬闻之色变,不敢前来。非洲的疟疾非常流行,我这次就看了很多疟疾病人。最大的问题是,许多病人体内的疟原虫在服药以后,并没有被杀死,只不过潜伏起来,过一段时间又发作。我的一些病人迁延不愈甚至长达2-3年。即使是现在所谓的旱季,也疟疾频发。我从美国带来了硫磺奎宁,疗效应该比较好,我给病人服用15天,也不知道是否能完全杀死疟原虫。我是一锤子买卖,看完病人就走,不知道疗效如何?
当地人都处于赤贫状态,缺医少药。尼尔森牧师告诉我,几内亚比绍全国没有一名像美国水准的医生,都是类似于中国早年的“赤脚医生”,培训了几个月到一年就上岗了。我去年在塞内加尔,他们地区卫生部门的主管接见我,非常盛气凌人,劈头就问我对于热带医学懂多少?说实话,我真不懂多少,但是他检查了我的美国西医执照和名片,美国的医疗执照上都写“Medicine and surgeon”,惊得他半开的嘴巴一直没有合上。他拿出他的名片,医学本科,四年毕业。他的办公室有一架发出巨响的窗式空调,我在他们省长和市长办公室,也没有见过空调。可见他们对医生的尊敬和医生资源的稀少。他立即批准了我可以在他管辖区行医。我想,如果我的同行能够在一生中有一次来到这些地方服务,将会是一生的福气,因为这里的人民真正需要我们。
美国有一种喷好了驱蚊剂的热带衣,它是用防蚊液浸透棉布纤维,透气凉爽,可以洗99次,只是价格太贵。我有几件,放在身边。
切记还要戴一个通风的帽子,非洲大陆阳光垂直从上面射下,我2014年忘记从美国带帽子去,一两天下来,我的脸没有晒黑,头皮却晒脱了,白白的头皮像柳絮一样缠在头发上,杜甫说过“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只是此地干旱,没有水流而已。

身穿防蚊衣的作者
食
在非洲吃什么?是一个大问题。对于我们这种娇生惯养的人来说,非洲所有的食物和水都污染了。他们气侯炎热,没有冰箱。刚杀好的牛羊,悬挂在热浪之中,几个小时以内,细茵就会以几何级数目成长。非洲没有污水处理系统。所有的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到仅有的江河湖海之中。因为缺水,东西也洗不干净,所以我们根本不敢在一般的市场和餐馆买东西吃,只在几家“指定特供”的地点购买和就餐。但是,许多人还是告诫我决不可吃色拉,因为他们的水不干净,洗过的色拉有各种病原体。同时他们本地不产蔬菜,色拉奇贵。我2013年在非洲15天,没吃过一次蔬菜。不吃蔬菜的直接后果就是便秘,我们的队员都被便秘苦恼。芒果只能吃青的,因为熟透的芒果,里面繁殖的细菌不计其数。我不信邪,不小心吃了一个熟透的芒果,结果拉了三天肚子。
我们在非洲主要吃三明治,我们在美国超市买好汉堡、牛肉、鸡肉和各种奶酪,用零下20度冰箱冻上一周。经过大约9小时飞行到达非洲,立即又放入零下20度冰冻。每次食用,拿出各式美味解冻,再加上非洲买的新鲜出炉的面包,倒也食欲大动。只是吃了几顿以后,就觉得难以下咽。非洲面包经过高温烘焙,里面的细菌都被杀死。我停留了15天,吃得我一见到三明治就想逃离。但是我带了儿子来,他和一帮年青孩子都吃得有滋有味,我怎么可以抱怨呢?
在非洲还经常吃不上饭,所以要准备一些蛋白棒和方便面,以备不时之需。
另一个忠告是,绝不能让任何生水沾入口中,即使是刷牙,也要用名牌的瓶装水。非洲店里只有一两个牌子的瓶装水可以购买,他们有一种塑料袋装的水,本地人饮用没有一点问题。我们一喝,绝对出问题。
在非洲还有一个大问题,上厕所。非洲人在地上挖一个坑,旁边用几块塑料布围住,里面的情形不敢想象。我们一般都在基地解决大号,到了村庄,我们控制饮水,让体内摄入的水份与汗腺挥发的体液数量保持均衡。我用这个办法,可以保持一天在外面都不用去小号。这是不得已的办法。

从美国带来的三明治,放在冰箱中
住
我们在塞内加尔住宿条件不错,尼尔森牧师和奥利弗牧师修建的基地有4个大房间,里面有卫生间。但是出了塞内加尔条件就差了。我的同事布鲁斯基医生去麻疯村,住在塞内加尔本地人的旅店,脏和乱不可言语。

从这个水桶里舀水洗澡。水压不足,无法淋浴

大树底下的饭店,我们还带了一箱方便面,蓝色的小桶是我们来不及煮开的水
在几内亚比绍,我们住在基地,但是条件比较差。十二、三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我与另外两人,其中之一是奥利弗牧师共住一个房间。其他人都是五六个人一个房间,没有空调,空气闷热,还有蚊子在空中奏乐。睡觉时一定要喷上驱蚊剂,等安鲁牧师的基地修建完毕,可能条件会好些。比绍号称是首都,只有一条路稍稍可用,其它的路都有着巨大的深坑,让人体验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觉。
我们租用了一辆大巴,每天250美元,大家集体行动,不至于为安全问题担忧。但是非洲的公路非常糟糕,政府从来不修缮公路。去年我们开车从塞内加尔到比绍,看到公路上巨大的深坑,有一些妇女儿童将道旁的石子和灰尘铲入大坑,以帮助过往的车辆行驶。车上的人们会给他们一瓶瓶装水,或者很少的钱,以示感谢。
医
出行前,我们自己要打所有CDC推荐的预防针。还要准备一些诸如清凉油、藿香正气水、黄连素、肤轻松软膏之类药物,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每次大约要带五万美元的药物去非洲,大部分由一个美国非盈利组织Americare捐献,他们主要供给美国常见抗高血压、高血脂等等的药物,抗菌素很少。我每次都需要自费购买许多抗菌素去非洲。由于我们是免费提供药物和治疗,病人蜂拥而至,我一个人每天大约看200到300个病人,许多病人并没有病,他们报告说有腹泻发热等等,主要目的是来要免费药物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这样的病人根本无法与真正的病人区分。
在非洲,疾病不单纯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环境和政治问题。例如非洲极度缺水,老百姓个人卫生极差,没人教他们饭前便后要洗手,也没人教他们吃饭要用勺子,分碗吃。他们用手从一个锅子里抓饭吃,由于食物缺乏,大家还得你争我夺,只要一个人有腹泻,往往就一家人都拉肚子。缺水不是老百姓的错,但是非洲国家政局非常不稳定,政客们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譬如说几内亚比绍,一个总统往往一两年就被推翻。我2013年来之前六个月,总统就被几个将军不经审问,直接从办公室拉到河边枪毙了,然后重新举行大选。我看到身体壮硕,荷枪实弹的士兵,乘坐装甲运兵车在市区巡逻,他们手扣扳机,随时准备击发,在那种情况下,任我胆大包天,也不敢给他们拍照。有鉴于此,任何一任总统当选,当务之急是巩固政权和全面捞钱,老百姓的福祉是没有人关心的,所以几内亚比绍名列全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人平均年收入300美元。作为医生,我们可以做的极为有限,但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非洲的病种繁多,我们必须自己带足各样药物,但是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药物都准备得面面俱到,每天出诊都取决于我们带去了什么药,没有药房,许多时候都是凑合着给药。有时我开好药方,给病人现金,让他们去药店买药或者去医院做手术,我们也送出了不少现金。我们也知道,大部分的现金,病人不是去买药,而是去买食品。我们只是尽人力听天命而已。
在非洲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病人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一天我看到我的翻译拿了我开的药物,只有原装的药盒,没有药袋。我非常生气,对着发药的同工咆哮:“你知道吗,这样会死人的。你们必须用药袋装好,写上服用剂量。”
这时牧师过来说:“他们不认识字,你写上有什么用?”这下我傻了眼,“那怎么办?”原来在比绍,他们有自已的特殊配药符号。譬如说,Cipro 500毫克,一天两次,药剂师就在原装的药盒上用颜色笔在一片药物上画上一种颜色,表示服用一片药物,如果是一天两片,则又有不同标示。尼尔森牧师知道这个困难,请来当地药剂师发药,再通过翻译认真解释,我真心希望不要出错。
在非洲行医,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系统工程来治疗病人,许多卫生条件和社会问题不是我们可以解决的。但是,当我面对潮水一样涌来的病人和他们渴望的双眼,我不用担心误诊误医,不用担心被人喊打喊杀,我只感觉到一种信任。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让我们更加满足呢?在非洲的每一天,我都哽咽不止,我啜饮着这涌流的生命泉水,感觉激情推着我向前走,烈火在我的心头燃烧,我暗暗发誓要把我以后的生命献给非洲人民,只有用生命才可以改变生命,这也是我每年都去非洲的最大动力。
/哥伦比亚大学附属斯坦福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