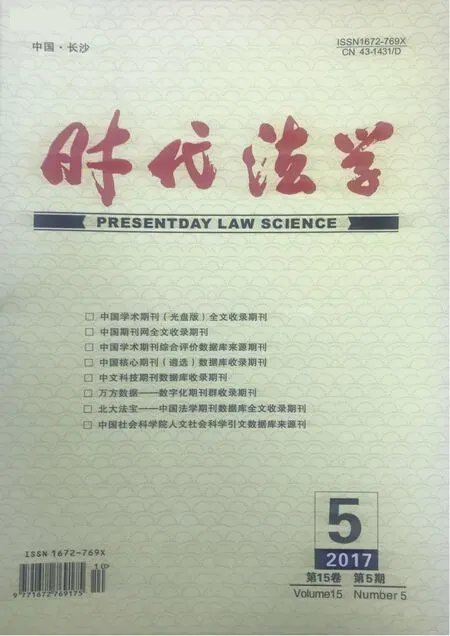中国古代两种反腐模式之评析
——以唐太宗与明太祖的吏治为切入点*
宋伟哲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042)
中国古代两种反腐模式之评析
——以唐太宗与明太祖的吏治为切入点*
宋伟哲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042)
唐太宗依靠法制反腐,明太祖选择人治反腐。唐太宗的法制反腐主要体现在完善法律体系、重视吏治立法、虚心纳谏、重视思想教育方面。他没有采用严刑峻法对待贪腐案件,而是依法治吏,将反腐常态化。明太祖的人治反腐主要体现在依靠严刑峻法、独断专行、特务反腐等方面,采用运动式的反腐方式。事实证明,唐太宗的法制反腐是帝制时代最佳的反腐模式,但依然不能摆脱人走茶凉的历史定律。中国古代的这两种反腐模式可以为今后的法治反腐提供历史借鉴,既要通过树立法治的权威、广开言路等方式调动全民的积极性来反腐,也要避免重走运动式反腐的老路。
反腐倡廉;法治反腐;唐太宗与明太祖;吏治
中国古代是一个人治社会,其反腐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人治社会下的法制反腐,一种是纯粹的人治反腐。唐太宗李世民与明太祖朱元璋就分别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两位君主堪称中国帝制时代的佼佼者,各自开创了一个大一统王朝,同时又都致力于肃清吏治。这两人所选择的反腐道路不同,其结果和对后世的影响也大不相同。这其中有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后人反思。本文通过对唐太宗与明太祖反腐之路的评析,为今后的反腐工作提供一些借鉴。
一、唐太宗与法制反腐
中国古代统治者强调“有治人无治法”,反腐在当时被称为“吏治”。尽管如此,并不意味这中国古代就不重视法制。“‘法制’强调的是法律制度,把法律文本作为主要表现形式,以静态为主要特征”*王立民.中国在依法治国中实现跨越的法治意义[J].学术月刊,2015,(9).。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中国是一个法制比较发达的地区。唐朝就是如此。唐太宗李世民曾亲眼目睹了隋朝吏治腐败、败坏法制而亡国的悲剧,对于反腐、法制等问题有着亲身体会。他在肃清吏治之时,并没有一味地采用强力杀戮、镇压的人治办法,而是能够充分发挥法制的重要性,依靠制度来肃清吏治,最终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政治基础,他的许多法制举措也为之后唐代法制的发展作了良好地铺垫。唐太宗反腐的举措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隋朝末年是中国古代法制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之一,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都被隋炀帝的暴政所打乱,史载当时“有司皆临时迫胁,苟求济事,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唐]房玄龄等.隋书·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717.。可以说,隋朝遗留给唐朝的法制基础很差。唐高祖李渊在位时期也有立法活动,但由于“于时诸事始定,边方尚梗,救时之弊,有所未暇,惟正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34.,因此这次立法并不完善。直到唐太宗李世民执政后,这种局面才得到了彻底地改善。唐太宗即位后,先后颁布了《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等法律。这次修律先后耗时十余年,由房玄龄、长孙无忌等精通法律的大臣领衔编纂,是唐朝最重要的一次立法活动。这些法律使唐朝的法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国家机器的运转有了稳定的制度作为保障,是防止吏治腐败的基石。
第二,重视吏治立法。“唐代吏治立法上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国家的主要法律种类都一致地重视吏治立法,让所有的法律形式协同配合起来,确立起吏治的整体机制。”*钱大群,郭成伟.唐律与唐代吏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7.唐代法律主要由律、令、格、式组成。其中,“一切政务都按照令、格、式的规范进行活动,凡违反令、格、式规范及作恶并后称犯罪的,则‘一断于律’。”*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隋唐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57.毫不夸张地说,令、格、式基本都是治吏的法律,它们的目录名称就清楚地反映出了这一点*比如《官品令》《选举令》《考课令》《公式令》《仪制令》《刑部格》《户部格》《兵部格》《职方格》《吏部式》《户部式》《度支式》《水部式》等等。。在唐代做官,一举一动必须严格遵守相关令、格、式,违反这些规定就要得到律的制裁。比如,唐朝禁止官员为百姓代送赋税,以免官员借此谋私利。《度支式》规定:“诸州庸调……有情愿输绵绢者听,不得官人、州县公廨典及富强家僦勾代输”。同时,唐律对于此类犯罪官员的处罚也作出明确规定:“诸监临主守之官,皆不得于所部僦运租税、课物,违者,计所利坐赃论。”*[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厩库》“监临官僦运租税”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3.293.诸如此类的配套规定在唐朝的法典中比比皆是。在唐律十二篇中,每一篇都有治吏的规定,甚至还专设《职制律》一篇来打击官吏犯罪。这些规定内容广泛具体、责任很严、刑罚很重*王立民.唐律新探[M].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8.。特别是在《职制律》中,直接打击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的条款至少有23条,约占该篇条款总数的40%。从中可以看出,唐代将严格治吏的思想切实地落实到了法律文本当中。
第三,虚心纳谏,依法治吏。良好的法律必须得到良好地执行才能发挥其最佳功效。唐太宗十分重视法律的实施情况,在处理官员腐败问题时,能够做到依法治吏。这里的依法治吏是指对于贪腐官吏的审判严格依照法律进行,不任意加减刑罚。唐代贞观年间这样依法判决的案例不胜枚举。然而,唐太宗毕竟是专制君主,他无法避免人治的色彩。但是唐太宗最可贵的地方在于能够虚心纳谏,使身边的大臣敢于在唐太宗破坏法制的时候及时制止他。比如,“弹乐蟠令叱奴骘盗官粮。太宗大怒,特令处斩。中书舍人张文瓘执据律不当死。太宗曰:‘仓粮事重,不斩恐犯者众。’魏征进曰:‘陛下设法,与天下共之。今若改张,人将法外畏罪。且复有重于此者,何以加之?’”*[唐]刘肃.大唐新语·持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4.55.唐太宗最终接受了大臣的意见,依法处理了此案。又如,唐太宗接受裴矩的建议,不通过“钓鱼执法”来治理贪腐问题。他还当众表扬“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五代]刘昫等.旧唐书·裴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09.贞观年间乃至此后唐代很长一段时间,君主意图破坏法制判决而遭到大臣依法劝谏的案例极多,这些案件基本都以君主向法律妥协而结束。这种妥协的本质,是法制对抗人治的胜利。在贞观时期乃至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律是约束君权的重要力量。唐代之所以能开创一代盛世,和崇尚法制密不可分,正是唐太宗以身作则开创了这种局面。正是唐太宗以身作则,崇尚法制,才开创唐代的一代盛世。
第四,思想教育。“廉政建设应该包括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钱大群.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32.唐太宗推崇依法治吏,又不一味地强调通过严刑峻法来遏制腐败。有些特殊情况的官吏腐败案件,唐太宗选择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来处理,通过这种方式强化自己与官员的廉政思想。比如,党仁弘为唐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官至广州都督。他卸任后因为贪赃枉法达百万之巨被判处死刑。当时党仁弘年事已高,又是有功之臣,唐太宗想赦免他的死罪。他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到宫殿中说道,“赏罚所以代天行法,今朕宽仁弘死,是自弄法以负天也。人臣有过,请罪于君,君有过,宜请罪于天。其令有司设藁席于南郊三日,朕将请罪”*[宋]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12.,最终将党仁弘减等流放钦州。其实,唐太宗完全可以直接根据唐律“八议”“老小废疾有犯”等条款对党仁弘予以减刑。但是唐太宗没有这么做。他通过向群臣请罪的方式来进行,既是对自己的一种警戒,也是对于朝臣的一种思想感化。又如,“右卫将军陈万福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家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令自负出以耻之。”*[唐]吴兢.贞观政要·论贪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378.这个小案件如果切实依照唐律判决,陈万福可以有多种合法的方式规避制裁。唐太宗用这种特殊的“羞辱”的方式对贪污官吏进行处罚,看似违法,却收效甚佳。除此之外,唐太宗还经常就廉政、反腐等问题与大臣进行讨论,教育大臣要洁身自爱,这些有关廉政的对话被大量保存在《贞观政要》等史书之中。事实证明,这种思想教育起到的警示效果不亚于于其他方式。
以上这些措施仅是唐太宗诸多反腐举措中比较突出之处。总观唐太宗的反腐,虽然无法摆脱帝制王朝君主专制的大背景,却能够将法制摆在崇高的位置上。在这一时期,法制甚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君主的人治,这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是莫大之幸。贞观时期的大法官戴胄敢于说出“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的言论,本身就是法制的一次重大胜利。这在此前和此后的各个朝代,这些言论和做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唐太宗的反腐工作平平淡淡,没有通过大案巨贪、严刑峻法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却取得了最理想的效果。他的这种崇尚法制的执政风格被此后的唐高宗、唐玄宗等唐朝几代统治者所沿用,这些继承者在完善法制体系、修订法律、依法治吏等方面继承了唐太宗时期的优良传统,“永徽之治”“开元盛世”等吏治清明的时代。
二、 明太祖与人治反腐
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一位极其重视吏治的君主,他出身低微,深知贪腐对于国家与百姓的危害。因此,从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投入了大量精力到反腐当中。与唐太宗依靠法制反腐不同,明太祖的反腐更多地是采用人治。值得注意的是,明太祖并不是不重视法制。仅从制定、修订、学习法律的投入和精力来看,他并不亚于唐太宗,有些地方还要超过唐太宗。他的反腐起点或许是从法制开始,然而随着反腐工作的深入,明太祖不自觉地一次次破坏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法制。他开始采用人治反腐,出重拳,下猛药。人治反腐如同是一剂“抗生素”,在一开始可能见效颇快,但是不久之后,“滥用抗生素”的副作用迭起,明太祖的反腐工作便陷入“奈何朝杀而暮犯”的怪圈之中。明太祖的反腐措施主要有以下这些:
第一,重视吏治立法。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立法的皇帝之一,《大明律》是他在立法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这部法律“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行天下。”*[清]张廷玉等.明史·刑法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84.也就是说,明太祖制定《大明律》先后耗时达三十年之久。从立法时间上讲,《大明律》是《贞观律》的三倍。明太祖在这部法律中,特别重视吏治方面的立法。《大明律》一共七篇,其中第二篇《吏律》用于专门打击官吏职务犯罪,一共三十三个条款,约占《大明律》条款总数的7%。明太祖特别重视官吏贪污、腐败等犯罪行为。他认为这类犯罪比一般的职务犯罪危害性更大,更需要加大打击。因此,他将打击这类犯罪的法律归纳到《大明律·刑律》中,专门列《受赃》一卷来打击这类犯罪,这与《唐律》只将这类犯罪列入《职制律》大为不同。《受赃》卷共十一个条款,比之唐、宋、元等朝代法律的类似条款,《大明律·刑律·受赃》用刑更重。除此之外,明太祖还颁布了《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数量繁多的特别法来惩治腐败犯罪。如果说立法是明太祖治国的重要手段,那么严厉打击官吏腐败犯罪则是明太祖立法的重中之重。
第二,重典惩贪。《明史·刑法志二》云:“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重绳赃吏之举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例如唐太宗也曾重绳赃吏,但基本都在国家法典的用刑范围内进行。明太祖则不然,主要表现在他设立了许多法外酷刑来对付贪腐官员。史载“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清]赵翼.《廿二史札记》“重惩贪吏”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84.不光如此,明太祖连续颁布《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峻法。他解释颁布这些法令的目的在于惩戒贪腐官吏,“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源而搜罪之。”*杨一凡点校.皇明制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5.在这些特别法令中,“总共罗列凌迟、枭令、夷族罪千余条,斩首弃市以下罪万余种。”*杨一凡.明初重典考[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31.这些刑罚大多是《大明律》中所无,量刑较之《大明律》却要残酷得多,许多在《大明律》中只需处以杖刑、徒刑的贪腐犯罪,在这些法令中都要被处以枭首、夷族等酷刑,甚至还规定百姓可以自行捆送贪官赴京。总之,明太祖通过“以刑去刑”的办法来消灭贪污犯罪。虽然他的这些措施是通过法令的方式来推行,看似属于广义上的法制范畴,实际上则是违背了法制的基本精神。以此为起点,明太祖的反腐彻底走向人治道路。
第三,特务反贪。推行特务政治是明太祖加强集权的重要手段,他专门设立锦衣卫来监视臣民的一举一动。这一特务手段很自然地被他运用到了惩治贪污腐败犯罪的过程中,特务反贪成为明太祖廉政建设的又一特点。锦衣卫并不是明朝的司法机关,却享有司法权。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享有侦查、缉捕、审理、行刑的特权。明太祖时期,经过锦衣卫处理的贪腐案件不胜枚举。不过,锦衣卫毕竟不是国家正式司法机关。他们不懂法理,凭借着直接受皇帝管辖的特权,在处理这些案件时,经常使用法外酷刑,杀戮极多,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们贪污受贿,欺上瞒下,名为反贪,实乃巨贪。史载“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19〕[清]张廷玉等.明史·刑法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35.锦衣卫对于明代法制之破坏是空前的,明太祖本人到后期也认识到了锦衣卫司法之弊端,于“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19〕尽管如此,锦衣卫之弊端已经酿成。况且明太祖本人也并未真正落实好这一法令,依然在使用锦衣卫抓人。到了其子孙时期,更是演化出东厂、西厂、内行厂等特务机关。这一弊政非但没有肃清明代的吏治,反而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祸根。
第四,独断专行。明太祖人治反腐的一个重要特征还在于独断专行。这本是帝制政治不可避免的,但是像明太祖这样将独断专行用至极致的皇帝也为历代所罕见。从明太祖反腐举措、言论可以看出他对于吏治腐败的担忧。他不信任各级司法官吏,而是亲自执掌司法大权,通过独断专行的方式来处理贪腐案件。明太祖本人文化程度不高,更不精通法律、法理,其性格又猜忌、暴戾,这就使他做出的司法判决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有时候完全凭借个人一时的喜怒哀乐来裁决。比如在空印案中,“帝疑北平二司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21〕〔22〕[清]张廷玉等.明史·刑法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18.2319.7185.更为可怕的是,明太祖不允许别人挑战他的司法权威。他不许别人议论他做出的判决,更不会听取别人的意见更改判决,提出异议的人往往会遭到重罚。比如上文提到的空印案,平民郑士利上书为这些蒙冤官吏辩护。明太祖览书大怒,将郑士利施以杖刑并流放〔21〕。这样就使得谁也不敢开口说话,反腐成了明太祖一个人的“独角戏”。
总观明太祖的反腐,蕴含着非常明显的人治色彩,而且将人治当中的独裁专制发挥到了极致。明太祖的反腐运动轰轰烈烈,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其间颁布的法令、杀戮的官员计之以万。史书虽然为其掩饰,认为“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22〕实际上,就连明太祖自己哀叹,“吾欲取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御制大诰》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惩贪力度最强的法律,用刑之惨、杀戮之广骇人听闻。可它颁行后不久,在《御制大诰续编》中又出现了大量的贪腐案件。“此辈皆系洪武十八年新诛奸恶贪婪之后,人人不畏其法,仍继踵而为非。”*杨一凡点校.皇明制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34.由此可见,明太祖人治反腐的效果并不理想,明一代也没有出现过比较理想的盛世局面,明朝更是以吏治腐败与严刑峻法而恶名于世。明太祖的许多反腐措施都成为了导致明朝的灭亡种子。
三、唐、明反腐模式之比较
唐太宗与明太祖都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专制帝王,都十分重视吏治,严厉打击官吏腐败犯罪。但是在具体的反腐策略上,唐太宗依靠法制反腐,整个过程平稳有序,奠定了一系列治世的基础;明太祖选择人治反腐,政策多变,整个过程波澜壮阔,却收效欠佳。仔细比较这两条不同的反腐道路,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正是这些不同点,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第一,对待法制的态度不同。法制反腐并不意味着制定出了反腐法律就叫法制反腐,人治反腐也不意味着只任人而不用法。法制反腐是君主专制时代反腐所能实现的最佳状态,它虽然不意味着法律完全可以遏制君主的人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限制君主的权力,防止其通过人治手段肆意破坏法制,作出违法的判决。也就是说在法制状态下,法律尚能够起到它自身维护公平、正义的作用,尽管这种维护远达不到今天“法治”的要求。唐太宗对待法制非常尊重,制定出了法律并不任意更改。当自己的决策违反法律时,基本上能够从善如流,重新依照法律裁决。因此在唐太宗时代,反腐并不是一种运动式执法,而是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并没有给唐朝官员带来恐慌,他们依然能够正常地进行日常工作。并且这时的法律非常稳定,不会随意大规模变更。明太祖则不然。他将法制视为自己施行人治的工具,法律、刑罚任意更改*比如,明太祖在《御制大诰序》中说“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又在几年之后颁布的《大明律》中又说“凡榜文禁例悉除之”,也就是废除了《大诰》中的许多规定。同样的贪腐案件依照《大明律》与《大诰》判决,其结果相差甚远,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很短的时间内这样大规模变更法律,充分体现了明太祖人治反腐的一面。。基本上他亲自裁决的每一例贪腐案件都是对明朝国家法典的一次破坏。他对待官员的严刑峻法造成了全国官员的极大恐慌,大家都不敢放开手干事情。这样导致明太祖对于官员的政绩又不满意,又会引新的杀戮。明太祖时期官吏少有任期满而平安卸任者,这使明太祖的反腐工作陷入了恶性循环。
第二,立法的内容不同。唐太宗与明太祖都十分重视立法,比如《贞观律》与《大明律》的制定都耗费了十年以上的时间。然而,唐太宗与明太祖的立法工作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唐太宗的立法全面、细致,不拘泥于刑法。他的立法律、令、格、式俱全,令、格、式的篇幅要远大于律的篇幅。各级官吏该做、不该做、怎样做的种种情况都清楚地规定在案。由于令、格、式基本不带有惩罚的性质,唐太宗又没有兴起过大的反腐运动,而是一直平稳地依照既定法律在治理国家,所以令、格、式在肃清吏治的过程中反而起到了比律更大的作用。毕竟绝大多数的官员能够依法行政,不会触及刑律受罚。明太祖则不然。他的立法工作重心在于刑法,而法外的严刑峻罚又是他反腐所依赖的最重要手段。明太祖虽然也颁布了《大明令》《洪武礼制》等少量不带有刑罚职能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在立法数量与质量上远不能与贞观时期的令、格、式相媲美,况且这些法律并没有在明太祖执政时期起到很大的作用。随着大规模反腐运动的兴起,这些法律更是被束之高阁。整个明太祖时期,刑罚甚至是法外酷刑一直扮演着反腐工作中的主要角色。
第三,纳谏方面的不同。唐太宗以知人善任、从善如流而著称于世,他虽然是个专制君主,其治国方式带有人治色彩,却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法制的重要性。在处理官吏贪腐问题上,唐太宗犹能做到如此。在目前留下的有关唐太宗从善如流的典故之中,听取大臣意见依法处理贪腐官吏的典故占了很大比例。唐太宗不但能够依法治吏,还会对向他提出不同意见的大臣给予物质和精神双重奖励,让他们继续监督自己的言行。唐太宗的这一做法,培养了一批直言敢谏的大臣,形成了贞观时期人人敢于言事的良好风气。更为关键的是,唐太宗的这一做法将法律的地位大大提高,树立了法制的权威。贞观时期没有大规模反腐运动,但是朝野上下都在依法办事,主动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来进行反腐,从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明太祖则在纳谏方面与唐太宗相反。在他推行严刑酷法反贪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曾对他的这种政策提出委婉地批评。明太祖对这些正确的意见非但不听从,反而对上书言事者予以重罚。这样一来,官吏都不敢对明太祖做出的判决提出异议,更不可能运用法律来约束明太祖的行为。反腐成为了明太祖一个人的任务,其余的官吏则丧失了积极性。纳谏在这里不仅是皇帝个人的行为,它直接关系到法制在这个王朝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关乎政治走向。
第四,留给继任者政治遗产不同。唐太宗反腐取得的效果不仅体现在贞观一朝,更体现在他的继任者唐高宗、唐玄宗等皇帝能够继承唐太宗的依法治国的优良传统,使唐朝的吏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清明接连出现一系列为后世公认的治世局面。唐太宗重视立法、修律,他的儿子唐高宗、曾孙唐玄宗更是将此继续发扬光大。唐高宗遵贞观故事,因时制宜,对于贞观时期的律、令、格、式都作了进一步修改。唐高宗永辉四年,《唐律疏议》三十卷的告成,更是将中国古代立法水平推向最巅峰,中华法系之法制即由此奠定。可以说,唐高宗将唐朝的法制水平又向前推进了一个台阶,其吏治也被后世认为“永徽之治有贞观之风”。唐玄宗也是如此,他在前几代君主的基础上又对律、令、格、式进一步修改,使之更适应时代需要。他还编纂了《唐六典》,这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行政法典。此外,唐高宗、唐玄宗等君主也都继承了唐太宗在惩贪方面从善如流、虚心纳谏、不任意破坏法制的传统,不少案例被记录在史册中流传至今。
明太祖则不然。他不但不允许大臣议论自己的立法、司法,甚至也不允许自己的子孙修改他制定的法律。他“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26〕[清]张廷玉等.明史·刑法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79.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法律因时而变的精神,给明代法制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而后乃滋弊者,由于人不知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于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26〕锦衣卫曾是明太祖进行反贪运动的主力军,他们虽然为明代肃清吏治作了一些贡献,但是其私刑滥杀、贪污受贿的劣性早在明太祖时已经臭名昭著。后来,明太祖虽然认识到了这种特务政治的弊端,禁止锦衣卫干预司法,但是却无法挽回这种局面。到了他的子孙执政时期,没有像唐代那样连续稳定地对法律进行修改、完善,仅有的一些修例举措也使明代的法制更为混乱,不像唐代那样有《唐律疏议》这样杰出的法典诞生。明太祖的后代将特务政治发挥到了极致。明太祖之后,其统治者更多的是留下了东厂、西厂、廷杖的恶名,而没有像唐代那样出现一系列治世局面。有明一代的吏治,也依然是一个腐败唱主旋律的舞台。
通过对唐太宗法制反腐与明太祖人治反腐的比较,基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君主专制时代,法制反腐是最理想的廉政建设方式。这时的法制虽然依然笼罩在君主人治的乌云下,但是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君主的人治,实现臣权与君权在某种程度上的妥协。这种妥协是以双方都认可国家法制为权威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当然,这需要君主主动做出权力的牺牲和让步。一旦出现昏聩、暴虐的君主,这种法制反腐就不可能实现。这也是君主专制时代不能进行最理想的反腐模式——“法治反腐”的重要原因。
四、 两种反腐模式之现代借鉴
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的两种反腐模式,可以为今后法治反腐提供历史的借鉴。近年来,反腐再次成为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焦点。随着一批批高官与小吏的纷纷落马,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反腐向何处去?明太祖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治反腐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唐太宗依靠法制反腐,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但是依然无法让吏治长期地保持清明。一旦到了君主晚年或者新的君主昏聩、暴虐,法制反腐便无法进行下去,法制便会退回到人治。因此,要想让未来的廉政建设长期有效地进行,法治将是必由之路。在民主共和时期,反腐需用法治。“法治反腐,是指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限制和规范公权力行使的范围、方式、手段、条件与程序,为公权力执掌者创设公开、透明和保障公正、公平的运作机制,以达成使公权力执掌者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从而逐步减少和消除腐败的目标。”*姜明安.论法治反腐[J].行政法学研究,2016,(2).法治反腐是一项大工程,唐太宗与明太祖的廉政建设中的一些经验值得今天法治反腐所鉴。
第一,完善廉政立法。明太祖进行廉政立法时,一味地强调惩罚,试图用严刑峻法来遏制腐败,结果以失败告终。而唐太宗的廉政立法则侧重于正面的积极引导,将官吏活动的所有内容全部容纳到令、格、式之中。我国应当考虑出台一些正面约束公务人员的法律,对其活动进行规范约束。这些法律应当简单、明确,告诉公务员该怎么做,并将其公之于众。此外,还应当弥补一些法律漏洞,使贪腐案件得到公正裁决。比如,我国目前的惩贪法律主要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其中刑法第383条是处理腐败案件的重要法律依据。随着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的公布,第383条的修改使得刑法条文中不再有犯罪金额的明确规定。然而,国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及时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不利于司法判决。类似这种漏洞应当及时封堵,以免造成判决不公。
第二,避免运动式反腐。明太祖的人治反腐特征在于运动式反腐,这种反腐运动的兴起源自于君主个人的强弱与喜怒,并没有完善的制度性保障。运动式反腐带来的最大问题在于造成司法不公,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这种反腐往往会带来整个官场的恐慌,人人自危,不能够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严重影响社会的发展。唐太宗的做法值得参考。将反腐工作常态化,以一套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将腐败案件正常按照法律处理,要做到公平、公正地对贪官进行审判,不能任意加重他们的刑罚。腐败问题要从根本制度上加以根治,而不在于采用多重的刑罚,判决多少贪官。
第三,广开言路。在法治反腐过程中,应当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反腐,反腐不只是最高领导阶层的任务。这一点,唐太宗的做法颇值得借鉴。他广开言路,虚心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还应奖励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者。最终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让崇尚法律的思想得以在政府中成为主流。未来的法治反腐也应当是这样。国家应当广开言论,允许所有的公民对国家反腐工作提出各种意见,奖励这些人,并且要将之制度化。绝对不能学习明太祖对于不同意见者施以重刑的做法。反腐是一件巨大的工程,紧靠国家机关的力量显得力不从心。唯有广开言路,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结语
历史的经验表明,法制反腐虽然能够在一时起到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同时局限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能力。当统治者开明时,法制反腐才有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当统治者暴虐专制时,前代法制反腐所留下的宝贵遗产会很快被扫荡殆尽。而运动式的人治反腐,则容易引发整个社会的恐慌。非但不能够在反腐上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还容易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唐太宗与明太祖的反腐故事从一个侧面证明,靠人治反腐与法制反腐都是行不通的,都无法避免人走茶凉的历史周期律。唯有法治反腐,它将法律作为最高权威,将所有人纳于法律的屋檐下。在这种反腐模式下,法律赋予了人们向腐败犯罪斗争的权利和保护,人们没有任何惧怕和恐惧。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反腐模式,才是未来廉政建设的正确道路。
ASurveyofTheTwoKindsofAnti-corruptionPatterninAncientChina—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Government by Li Shimin and Zhu Yuanzhang
SONG Wei-zhe
(LawSchoolofKaiyuanof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042,China)
Li Shimin combatted corruption by the means of law, while Zhu Yuanzhang combatted corruption by way of the rule of man. The anti-corruption of Li Shimin primarily reflected on improving legal system, emphasizing management legislation, receiving other’s suggestions and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education. He didn’t use stirct law to deal with cases of corruption instead of relying on law. The anti-corruption of Zhu Yuanzhang mainly reflected on using strict law, managing things arbitrarily and so on. Time telling the truth, though the way of Li Shimin had been more effective than Zhu Yuanzhang’s in the feudal age, the way couldn’t protect itself from being destroyed. It is time to apply the rule of law to combat corruption, in the meantime, we should not retrace the route of old ways of combatting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bid; anti-corruption by the rule of law; Li Shimin and Zhu Yuanzhang; management legislation
2017-03-08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17年9月21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宋伟哲,男,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法制史、法理学。
DF08
A
1672-769X(2017)05-007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