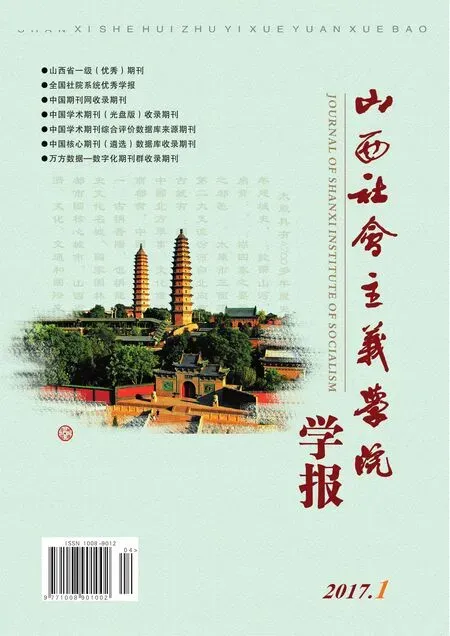于成龙与佛教
冯巧英
(太原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2)
三晋人文
于成龙与佛教
冯巧英
(太原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2)
于成龙能够参透人生、决绝物欲、恪守清廉,除易代给予他施展机会、地方人文钟秀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佛教思想内容,也是成就其为一代名臣的因素之一。
于成龙;易代;地域;佛教
一
本世纪初,山西电视台曾播映过《一代廉吏于成龙》,当时听到了各种议论。赞美的主调外,有些年轻人说:难以理解,这人傻呀,当那么大的官,把自己苦成这样。2016年底至2017年初,中央电视台又播出了电视剧《于成龙》,又有人议论不已。我曾拜读过《于清端公政书》,觉得真实的于成龙应该比影视作品、舞台剧中表现得更具历史真实性、更令人敬服。他的精神世界蕴含之丰富,值得今人深入探究。本文只想谈谈,明清时期深入中国民众心理的佛教思想在于成龙为政中的体现和深层缘由。先从一篇批件说起,原文照录如下:
批朱同知甘结
从重参处,此王法也,本部院岂肯轻轻放过。于天地鬼神何与?省心自问,发为誓词。孔夫子曰:“丘之祷久矣,如予所否者,天厌之!”非誓而何?誓虽为下等人说法,然君子戒慎恐惧工夫不外是也。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又何说欤?孟子云:“《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又云:“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又云:“人见其禽兽也。”又云:“禽兽相食,且人恶之。”又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又云:“桎梏死者非正命。”谆谆告诫,何尝不说到身家性命祸福上边。如今贪赃剥皮的提起笔害怕讲这话头,殊不知举头三尺有神明,如何瞒得过他去!立意要改恶,一刀两断,笔下就活现出一个阎罗天子来。重重地狱,如在目前,便时时打点一念一事,犹不敢肆意贪赃。如轻描淡写,姑且做个戏法儿玩一玩,殊不知湛湛青天不可欺,就有许多凶神恶鬼紧随。莫愁不参处,就有参处的日子,家破人亡,子孙讨饭吃。君子做事如青天白日,何讳之有?如今的人不知悔罪,都吃了讳的亏。知之。
这件批文是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批一位朱姓同知所具甘结的文字。“同知”,清代府、州一级或盐运使长官名下配置的副职,比知县品级略高。“甘结”是古代一种画押字据,一般是对官府所做的,大致相当于悔过书,写明保证绝不再犯,如果再犯情愿受罚等,字据最后作者亲笔签名,或者画某种记号,叫画押。没有查考这位朱同知名号籍贯、所犯何事,从于成龙批文看,大约是贪赃事发,悔过出具甘结。批文一开头于成龙堂堂正正表示要“从重参处”,遵的是“王法”。按于成龙为人行事的原则自然也不会“轻轻放过”。批文内容围绕两点:一是“誓”,赌咒发誓的“誓”,引经据典地说明按儒家大“道”也是重视誓的;二是“讳”,讳疾忌医的讳。讲“誓”,一开始强调的是应该“省心自问”,和天地鬼神不相干,那个时代认为本来“誓”是为下等人设的机巧方便,君子们应该是“戒慎”,警惕自己的言行,更要慎独。但任何事物发生总有征兆,所谓“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意为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况且圣人也是重视“誓”的。大量举《论语》、《孟子》语录说明之。有趣的是“戒慎”本属于主观内省的修身方法或者叫道德修养,于成龙一引再引圣贤言,却拐到“身家性命祸福”方面了。当然,“戒慎”讲道德修养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身家性命,避祸求福,于成龙不过说出了大实话。其下内容就直接了,大谈不可讳,因为“举头三尺有神明”,“阎罗天子,重重地狱,如在目前”,“湛湛青天不可欺”……口语化到意思不连贯,得意会。这样一篇短短的文字从文法看,前边是演绎法,后边是归纳法,粗看有点语无伦次、信笔写来,但细察之下,“誓”也罢,“讳”也罢,演绎推理出来的却是一个最普及于老百姓的道理:因果报应。因为作者是信笔所写,所以愈见其真实,是略无藻饰的真实思想。
粗略翻翻《于清端公政书》,其中鬼魅为祟、因果报应思想几乎随处可见,如在罗城时说:“罪孽未尽,死而不死……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治罗自纪并贻友人荆学涛》)在四川合州的《请复祀典详》中先是说明“一代之兴,首重祭祀之礼”,祭至圣先师,祭启圣公,祭山川、风云雷电、城隍土地,三月初一、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祭无祀孤魂……他重点解释“无祀孤魂,倍宜悯恤”,因为“蜀土遭劫屠戮,白骨遍地,磷火遍野”(按:明末清初蜀滇黔三省战火频仍,地方荒残,以至于“典籍轶失,仪文缺略”。于成龙到任时属新政权草创阶段),“往时民人寂寥,虽悲号夜月,无能为祟”。当“流民渐归,烟火渐生”,“无主孤魂当人间祭祀之期,必凄怆愈甚”。如果“恩祀不及”,则“怨气所激,或为灾眚,或为妖孽,必然之理”。可以看出于成龙对人死为鬼、鬼能作祟、无主孤魂非常可怜是深信不疑的。在武昌府任上他招抚了麻城县的一股“土寇”,单骑入山劝降了东山乱民,不厌其烦地在告示里劝“命由天定,祸自人出,思之慎之”。他委一位乡绅陈恢恢为“剿主”,专门出谕说:“如本府不以诚意待恢恢,天地鬼神速加诛殛。”平定东山之乱后,编立保甲,下文说明是为了“稽查匪类,劝勉为善”。最后强调如果“借端报复,仇害无辜”“犯神人之忌不浅矣”。康熙十六年在黄州剿灭了一股乱民后,于成龙明确宣告“其余胁从,概不追究”。事后有“不良人”“借端生事,遍地吓诈,民生不安”。于成龙认为是自己为善不终,以致“本府每夜泣祷”。过年的时候专发《严禁吓诈谕》文最后说“……不听本府之言,三日内必定有报应”。请注意,这是一篇知府签发的告示。现代人看了会惊诧,有的可能还会失笑。按现代人的理解至少明清时代,读书人习儒业,代圣贤立言,尊的是孔孟之道,怎么可以这样赌咒以鬼神报应为教呢?难道是为了警戒愚民采用的机巧方便吗?综观《于清端公政书》,可以看出这些都是他的真心话。甚至他做到两江总督,对专管科举考试的学政、江南儒学掌门发指示时还说:“谁无子孙,谁不愿子孙显达,而瞒心昧己,赃私累累,独不畏明有国法,幽有鬼神,现在发觉则有身家性命之忧,日后凋零更受男盗女娼之报乎!”于成龙是真心相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
身为朝廷命官、一方大员的于成龙在官方文告中屡屡以因果报应为说辞,是否就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呢?当然不是。于成龙生于明末,读书求仕进,崇祯十二年参加乡试,中过副榜贡生。当初朱元璋一建立大明王朝,就推崇理学,强调理学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朱元璋曾说:“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明史》卷三《太祖纪》)相反,对于他了解的佛教控制倒是相当严格的。他把佛教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各类僧人从事什么专业甚至服色都有规定,不许混淆。在经济上也对寺院有管制,防止“惑众滋事”。这种立国指导思想一直贯彻到明亡。掌权的和追随权力的儒们以道学(即理学)之名排佛,成为官方的声音,如明万历四十年(1612)修的《太原府志》卷二十四“寺观”项下劈头就说:“异端之禁,所从来矣……今虽未必毁旧,亦当禁其创新可矣。”清初,先是平定各地反叛,消灭南明,康熙初年三藩乱起,国家没有力量在思想文化领域做大动作,但自建都北京后就大力崇奉孔子,提倡理学,同时对儒生实行空前严格的思想控制。尊孔也成为清政府的基本国策。既然如此,那如何理解譬如在《批朱同知甘结》中所表现的先是大引孔孟之言,紧接着就引申到因果报应呢?很简单,作为口号的“尊孔”和实际施行的“奉儒”——依理学行政已不是一回事了。也就是说,到了明末清初,先秦儒家代表的孔子与明清儒学即理学已经有了很大差别。
先秦儒家代表——孔子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什么?近代以来众说纷纭,新世纪以来国学兴,到处讲《论语》,似乎《论语》即为国学代表,“圣之时者也”的孔子又大行于世,是耶,非耶,我不敢置喙,但有一点是不会错的,孔子关注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是‘人’的发现”(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孔子罕言“性与天道”注重人事。在宗法社会里如何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是先秦儒家着意探讨的。他们所说的“忠”也与后来的“忠君”概念不同。对于鬼神之事,很有名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句就很说明问题,老夫子没有亲身经历就不乱发议论。至于因果,孔子是讲的,但与佛教所说,到明清以后普及于中国人的因果观念不是一回事,这留待再说。孔子时代儒家是重人生重现实的。到汉代,武帝朝及其后的汉儒以董仲舒为代表极力强调“天”,他的名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由此演绎出伦理纲常“王者法天意”、君主“受命于天”、“王道三纲”,等等,成为后世儒家被封建时代历代帝王看中的重要原因。在理论上他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在行动方法上,行图书谶纬、星宿神灵、灾异祥瑞、方术神书,等等。汉儒已经变成了神学。宋明理学(包括清)还打着儒家的旗号,但它已经是融会了佛道二教某些思想内容和方法的“新儒学”。比如理学的理论核心“心性”学说就是隋唐“佛性”论的翻版。再如理学强调“修心养性”,几乎完全来自于唐宋禅宗的“明心见性”,以至于他们的用语都酷似禅门,如朱熹说,明心见性之后“豁然贯通”。陆象山说修行明本过程“多类扬眉瞬目之机”(禅宗机锋有扬眉瞬目的公案)。王阳明干脆说:“本体工夫,一悟尽透。”所以说,至清初,理学家以“主静”“居敬”“存天理,灭人欲”教人,理学已经是“阳儒阴释”“儒表佛里”(梁启超语),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和一定宗教功能的政治伦理哲学了。于成龙引述孔孟居然自自然然就转到因果报应说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代表了明清儒家——理学对孔孟的理解。
二
怎样理解于成龙总是以鬼神报应来说事呢?对佛教有些了解的人会大不以为然,认为于成龙对佛教的认识太低俗。其实不然,从于成龙的人品、作为和他的文牍表现来看,正是体现了中国汉传佛教的大乘菩萨行精神。
佛教大乘思想始于古印度,早期大乘经籍主要解决理论问题,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的理论嬗变,大乘信仰成为汉传佛教的核心教旨。佛教从根本上说不是理论性的,大乘佛教从早期“般若”类、“涅”类、“中观”等等,直到《六度集经》都包含了“行”的很大成分,这里说的“行”不完全是五蕴中的“行”识,是指实行、践行、行为等,就是说不要光谈理论,要“做”,要躬行实践。
审察于成龙的所作所为,他对自己省俭到苛刻的程度,对百姓却是倾囊随施;对有利于百姓的事不计个人得失安危,冒天下之大不韪向上司提建议;一心为公,离任之时还负责地留下意见(《升闽臬上抚台》);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为多数民众着想,如:他多次镇压、招抚作乱的臣民,对为首者毫不宽纵,但一再对协从者宽咎;他深信天命鬼神,却从不懈怠人事等等,这些事实已远远超越了儒家理学家的精神境界。宋代理学集大成的朱熹之学后来变得“固陋空疏”,明代理学的翘楚王守仁即王阳明先生创王学,其要领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此处不探讨这些学问的功过是非,只从字面看,这些高深学问与普通老百姓何干!明末清初于成龙生活的时代,佛教世俗化了(至今也还有一批理论家对佛教世俗化深不以为然),至少切切实实为老百姓带来一些精神抚慰。于成龙来自于中下层,他是“草根”派的念书人,曾在安国寺读书六年,与寺僧纯天上人多有切磋。如在他为数不多的诗词中有一首《梦餐优昙花作》前有小序,说“余读书山寺时,梦餐优钵罗花,即吟一句云:仙人赐我钵罗花。醒,语纯天上人,检藏,知钵罗花即优昙花也。因赋以志”。诗一般,略。从序可以见出两点,一是他对道佛两家等同看待,正是那个时代佛教世俗化影响于人们观念的表现;二是他为了了解优钵罗花是什么而“检藏”,从经藏中查找,可见他对经藏熟悉。在他人生蹉跎、蓄势待发的岁月里,和僧人(笔者未能查到醒天和尚资料,佛教修为如何,不得而知)有六年相伴,常常翻阅经藏,可见《于清端公政书》反映出的思想和行为,至少出于他的宗教感情以及对佛教精神的认同。
明末清初,一些雅士高人玩形而上学的学问夸夸其谈,造就了一批假道学(见《儒林外史》),失去人心。而佛教汲取儒道思想深入民俗,佛教的大乘菩萨道为中下层士人和广大民众所认同并尊奉,这种俗文化造就了于成龙。如果说他是要修佛道(此道非道教之道),那倒不是,但“公忠体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等大乘教义已成为他为人的圭臬,他坚定的信仰,表现为与一般人不同的苦乐观,才有了现代人难以理解的许多作为。他所呈现出的是佛教的积极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三
学习《于清端公政书》,我认为有几点值得今人思考。
首先,评价于成龙不应回避他的宗教感情。许多年来,人们对宗教成见很深,似乎一提宗教就等于迷信,“迷信”就是一根可以轻易加之于人的棍子。此处不辨析宗教和迷信的异同,只说宗教。为什么人们总是羞羞答答不敢表示对宗教的真实感情呢?且不谈“五四”以来在膜拜“德”“赛”二先生口号下对宗教的曲解,就只建国以来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称马克思说过“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中国人从1840年以来对鸦片深恶痛绝,既然宗教是鸦片,那么当然就毒害人民了。到20世纪80年代逐渐有了不同的声音,说那是翻译错了,修正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麻醉是中性词。有的人就说,马克思时代鸦片具有药的功能,至今镇静药里都有鸦片的成分,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是对受损心灵的抚慰补偿。有的说“麻醉”了人民就不好,它使人民消解了对剥削者统治者的反抗。一直到2007年还可以听到这种辩论。我认为以“鸦片论”观宗教,特别是谈佛教不仅偏颇,而且是类井底之蛙的见识。当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佛教是一种文化,已成为民俗内容,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考察近代以来高倡的“人间佛教”精神,有哪一点是危害社会和民生的?至于现今社会上各种问题、各种议论,能怪到佛教本身吗?怀璧其罪也。进一步说,佛教甚至宗教,是人类对社会和人本身认识的升华,毋论对错,是个复杂问题,在某些历史阶段和某些特定地区,不能没有宗教。因此对于成龙的佛教情结漠视甚至厚非,恐怕也是一种病——左派幼稚病。
其次,于成龙生于明末,29岁时江山易代,到45岁时出仕。23岁时(明崇祯十二年)乡试中副榜贡生就有机会出来做官,但他辞了。到清顺治八年他已45岁,却历经艰辛,远赴广西做了个处境危险的县官。此时清政权还不是十分稳固,到处有反清力量在活动,近在太原就有傅山等反清义士力倡复明,至少是与清廷不合作。两相对比,怎么看待于成龙的艰难入仕呢?我认为这是出于两者看事的角度不同。傅山、顾炎武等反清志士们着眼的是江山易主,更有“夷夏之辨”思想,难以接受落后的少数民族主宰江山、称帝称尊,这是由来已久的儒家读书人的观念。于成龙着眼的是百姓,最普通、最下层的百姓,怎么能让他们活得好一些少受些祸害苦楚。他深深懂得中国老百姓所求莫过“安居乐业”“平安是福”。明末政局已经根本无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了。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中就认为“利己残民”的君主可以抛弃。于成龙的选择主要是以民为重的,易代给了他机会。他个人为什么会甘愿如此受苦呢?最早在广西罗城给友人的信中坦承他也动摇过,“郁从中来,病不自持,一卧月余”苦恼而病倒,但他想到“吾如罪孽未尽,死而不死”,况且“乞归无路”,因而他没有逃避,没有沉沦,从此“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他亲民任事,抱定“奋不顾身、为民而死”的决心,果然罗城得以大治。很明白,他想的是赎罪业和济众生,这甚合佛教大乘精神。
再次,于成龙从始至终常怀感恩之心。在罗城他感谢了解他苦心的金抚台;在黄州、武昌感谢张抚台对他的赏识;至京畿、两江更因康熙帝对自己的优渥重用而肝脑涂地。中国佛教从东晋以来就大力倡导出家人要报四重恩(天下众生恩、国主恩、师尊恩、父母恩),严格讲,常将报恩付诸笔端、行为的人不是太多,但于成龙不但说了也真切做到了,能说这与佛教影响无关吗?
最后,如何看待于成龙镇压乱民的事。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一个“共识”,只要历史上的官吏镇压过啸众造反的,就一定是镇压了农民起义,这个人物历史就有了污点,比如岳飞等。于成龙《于清端公政书》中有多处记他大开杀戒的事,该怎么评说呢?我认为,古代造反作乱者不一定就当然值得肯定。古今同理,为了一己之私或小集团利益制造事端、引起至少一方社会动荡危及平民百姓安宁的,用严法也应属当然。是的,佛教五戒之首就是戒“杀”,但佛教不禁除魔。佛经中就有为了救更多良善甘冒自己下地狱的后果而杀却恶人的。于成龙杀怙恶不悛的倡乱者于世法佛法都能交代。
于成龙有着山西百姓那种认死理、认准了就一心走到黑的性格,他将“不为自己求安乐,但为众生得离苦”的菩萨道精神付诸实践,终生信守,最终成为一代名臣,垂范古今。
(责任编辑 王怡敏)
K82
A
1008-9012(2017)01-0066-05
2017-02-19
冯巧英(1940- ),女,河北清河人,原太原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于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