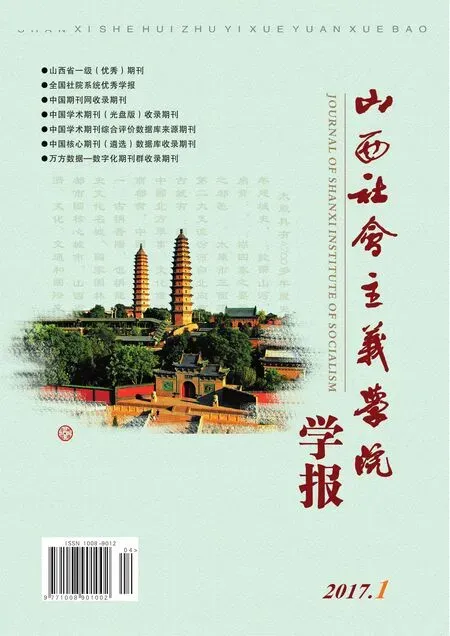试论我国企业治理的文化基础和理念
朱康有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新视阈
试论我国企业治理的文化基础和理念
朱康有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 北京 100091)
当代企业面临着由管理理念向治理理念的转变。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企业治理的文化基础和理念抉择应立足于由“道”的层次延伸至“术”的层次,修己立人、自正正人、身企共治。
企业文化;企业治理;传统智慧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出现了举步维艰甚至一些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的情形。作为现代经济组织“细胞”,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形势。和任何有机体一样,企业固然有其“生命”周期,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周期大约是三五十年,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周期则只有三五年。怎样使企业保持良性、长期运营呢?经济学家、政治家作了很多有益探索,处在一线的企业家更是殚精竭虑,有的可以说身心交瘁欲打拼出一条生路。基于此,本文欲就企业治理的文化基础和理念作一探讨。
一、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背景
企业作为由人和物组成的“生命体”,除了追求经济效益、满足人的生产生活物质需要外,其指导思想、规章制度、社会声誉等组成了企业的“精神”系统。最高管理者是企业的“大脑”,其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变化的思想和决策,在企业“神经系统”中占据“出令”的“中枢”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大中小企业纷纷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助推器。以西方近现代文化奠定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经营理念成了时髦的追求,企业家以拥有MBA、EMBA等文凭为荣耀。这些建立在“资本”“私营”理念基础上的现代经营文化,极大地迎合了改革开放年代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进一步“欲念”,一定程度上也确实促进了经济生活的极大繁荣。
让企业经营者为当前社会人心失范、道德滑坡等“颓废萎靡”精神现象负责,可能夸大了其“责任”,但我们不能不正视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比如,诚信丧失的恶果,增加了许多难以计算的“成本”。2008年以后的这次外来冲击,使企业蒙受了又一次巨大损伤。
不管是多么大的企业,其经营后果一定是影响这个社会的;每个企业多多少少都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在企业和企业家身上反映了社会的良心和状态。企业家的思想和理念、追求和欲望、胸怀和希冀、愿望和志向,在有形无形中往往引导着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的心理取向、价值目标之综合,组成了整个企业的精神面貌和无形财富,一定程度上包含在被社会大众所认同的企业“品牌”中。同样成本或质量相差不大的产品,品牌或贴牌者的价格能相差倍数。这即是企业有机体的精神文化层面的物化或价值化,其中有的是上百年历史的累积或者空间中数以亿计的口碑相传(不完全是广告的力量)。
企业最高层的功能一般被定义为“管理”,这一术语主要来自西方人的思想,其中蕴含着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管理中的“人”和“物”区分的“二分法”思维模式。在这一模式指导下,似乎管理者高高在上,被管理者处于执行层面;管理者外在于、超越于所制定的规章和制度,被管理者则只能照章行动,管理者的权益和被管理者的权益处于一种对立状态。如管理者被称为老板、总经理、董事长,与员工、职工等“职业”区分开来,“金字塔”式结构成为很多管理活动的模型。其优势就是自上而下的管理非常畅通,其劣势就是自下而上的渠道可能被“堵塞”。一定程度的“差异化”是企业乃至社会发展的动力,但过大的“差异化”则可能颠覆其发展前景。
最近几年,国际上出现了“全球治理”,国内出现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时髦说法,这与儒家经典《中庸》里说的“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的传统“治”相“暗合”。“治”,从字形上分析,与对水的疏导有关,强调治理者的以身作则、被治理者的自动“跟随”,治理者与被治理者是“一体”的,很难分清二者的界限。治理首先是“正己”,然后才是“正人”;首先是“出令者”先“身行”,而后才是“不令而行”,蕴含着从“有为”向高级“无为”治理模式的转化。中国古代“德治”的实质即在于此[1],没有自己身心之外的所谓“管理”。如果把自己置身于企业的管理之外,单靠所谓的规章制度,那么,在市场大潮中你就根本驾驭不了企业。
二、建立在“身企共治”基础上的治理学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指向一种对奠基在这种经济制度上的“企业运营”的根本性变革。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新一轮改革中,既把市场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手段,又将其限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向的实践创新和运用。实际生活中,一些企业的目标和理念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某方面的需求,而主要是为了使自己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甚至是为了企业经营者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比如,企业利润下降,企业管理者阶层的报酬却在节节攀升等“怪象”。企业社会责任感“消弱”带来的前景必然是企业生命循环能力的萎缩。
传统“治理”的智慧有利于抑制经营者对利益的过分冲动和渴望。中国历史上,凡是能够较好遵循这种治理模式的,休养生息,与民分利,便会出现“盛世”景象;凡是不能遵循这种治理模式的,与民争利,搜刮民脂民膏,皆走向败亡。因此,对利益的调整及其合理分配,是企业治理的关键。利润作为企业所得,如何使用决定着企业能否发展壮大、由弱向强。从企业内部来讲,如果利润的去向正好是按照与“管理金字塔”模式颠倒的形式进行分配,即那些愈居于高层的管理者所得愈多,愈往下愈少,就违背了儒家治理名言“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道理。企业内部失去凝聚力,分崩离析是早晚的事。企业经营之好坏,皆是老板的“事”,或者说是管理层的“事”,他们拿得多,自然负的责任大。一般员工则认为:我拿的仅仅是劳动辛苦所得,企业倒闭不倒闭与我无关——如果倒闭,换一家就是了——他们不会升起对本企业的责任感和责任心。企业管理层特别是最高层则不同,他们出资兴企,用尽心血,其命运和企业紧紧连在一起,但是有时候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它的衰亡而无可奈何。如果能让全体员工对这个企业负责,责任分摊,命运共担,那种“使命感”带来的尽职尽责和无限关注,就能使企业获得不竭的动力。奥秘就是“有饭同吃,有福同享”,把利润的内部额度拿出来“均分”,员工就会与企业同命运共患难。另一方面,从企业扩大再生产来说,除了正常上缴国家和地方税费外,其“节余”要按照一定比例、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做慈善事业等方式,回馈社会为好。这不仅能为企业赢得“名声”,更是在将利润“散”化于社会过程中,将企业的经营风险分摊于社会大众。这是符合“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则财恒足矣”(《大学》)的道理的。若从20世纪系统科学揭示的原理来看,企业的发展和成长,与社会方方面面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不只有资源、产品、资金的流动,还有各种心情、态度、情绪乃至思想、理念、文化层面的交换。“利”的背后是有无“义”的存在。“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大学》)应用到企业就是“企业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义”体现的就是企业的愿望和冲动、价值和理念。把“利”封闭聚敛的后果是丧失“义”。在“五行”学说中,财就如流动的“水”,只有在天地大自然之间、在国家和社会大众中周流不息,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按照这一理念,将利润按照一定的比例均分于社会、员工和管理层,而不在某个主体上“聚敛”和“凝固”,不但能极大地调动各方积极性,也能使企业实现一种“无为”自动运营的治理模式[2]。
挣钱是能力,如何花钱则是智慧。伟大的企业都从人性角度体现出价值观;企业的利润来自客户的感动、员工的满意;企业要具有使命感,缺乏使命感,只为赚钱,一定走不远。西方管理方式是八小时外不管,但西方人有团队精神、守规矩,中国人是八小时之外影响八小时之内的事情。比如,有人认为,一个企业家孝不孝顺,与企业无关,这是不正确的。中国治理学“身国共治、身企共治”就指出,修身齐家与治理企业紧密关联,从这种意义上讲,儒家经典《孝经》就是非常好的管理学。青岛亨达有限公司的成功就是“一部《孝经》成就亨达”的有力佐证。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将“圣贤教育”作为企业文化,把“家道”融入管理中,认为21世纪的企业不只要“管”理,还要“化”,通过教化、感化的方式,成就“幸福企业”之路。儒家之“孝”,非局限于对父母的感恩,可延伸至团体乃至国家的管理活动中。现实中一些经营管理者正从行动上不断验证着传统文化在企业治理方面的大智大慧。
古语道:“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是不知荣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为政忠告·修身第一》)做官做到将相,被世人公认是一种荣耀,但荣耀与耻辱往往并存;只有善于自我修养的人才能保持他的荣耀,不善于自我修养的人,荣耀只会招致耻辱。《列子》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楚庄王问隐士詹何治国之道,詹何回答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治国之道,只知道怎样修身而已;但是我听说,如果一个人身修好了,国家还没有得到治理,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列子·说符篇》)。换言之,一个企业,企业家真正把身修好了,这个企业要是治理不好,那也是从来不会有的事情。管理者真正修好身,能够为员工和下属做好榜样,团队的风气就会纯正。孟子认为,凭着强力让人屈服,人家并非内心真的佩服,只是自己力量不够,无可奈何;靠着道德让人信服,人家才是内心愿意并实实在在地佩服。管理活动中靠什么发挥影响力呢?一种是权力因素,一种是非权力因素。权力的影响主要是职务因素、资历因素,使人产生敬畏感和服从感。而非权力的影响,主要由道德品格、知识才能、意志情感等构成,使人产生敬重感、信赖感和激励感。由于非权力影响主要来自人的内在因素,通过潜移默化的自然过程体现出来,所以对他人的影响就非常巨大而且持久。只有恒久注重慎独修身者才能产生强大的“能量场”,其坚强的意志力、稳定的情感、高尚的人格就会时时刻刻“感染”周围的“环境”。
三、以传统文化的“大道”为理念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治国理政上要注意借鉴五千年文明史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教训。在企业治理上也要注重以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作为基础。很多经济学家不以为然,认为现代企业应借助于现代企业的制度文化。这里的“现代”具有歧义性,它是近代西方欧洲工业发展的“产物”,兴起于私有资本的冲动;它具有“普遍性”,但在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很难说是“普世”、“普适”的,从殖民时代血淋淋的原始积累到今天国际垄断集团另类的“攻城略地”,即证明了这一点。简言之,它不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到今天的“现代”,而是被近代粗暴“打断”文明进程后又粗暴进入的“现代”,是中国人“无根”的“现代”。今天不少学者简单地把“传统”贴上“落后”“封建”的标签,名之为“自然经济”“农业文明”而抛之一边,对其中“市场经济”(比如《周易·系辞下》关于“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观点,《管子》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孟子》关于“通功易事”的提法、中国文化中“经济学”的独特见解以及有关“义利观”的反复阐明、中华法系与中华法制传统的体系化,等等)的成分视而不见,而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当然,西方“现代”的成就,某种程度上也汲取了东方文明的营养,并有对“近代”辩证否定的部分,产生出很多“精华”供我们选择。只是“立足点”要选好——适应别人的,不一定能很好地适应自身。西方现代文明没有脱离其近代民族国家利益“惯性”带来的弊端和狭隘性。中国在21世纪的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发掘中华文化的“普适性”价值,比如被赋予新意的天下观、民族观、历史观、国家观,或许能为新世纪生活的人类带来光明前景。
企业家应选择“道”作为企业经营和长远发展的理念,而不是以“利”作为指导思想;观念一变天地宽,脱离了单纯“利欲”观导向的“陷阱”,很多企业就可能起死回生。用传统文化观念进行培训和感化,实践中确确实实“拯救”了许多企业家,“拯救”了许多企业。因为有道,有灵魂!引领了人生方向,也指引了企业的发展方向。我国企业的文化理念基础应当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以儒、佛、道三家思想为鼎立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含着“道”乃至“大道”。兵家有“兵道”,法家有“法道”……儒家之道,讲到极处,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乃“形而上者谓之道”;道家之道,玄之又玄,最高层面已经脱离语言的束缚;佛家之道,“离一切相”,无定无执,不拘泥于形迹……“道”贯通天、地、人,可以落实到一切形而下的操作层次,西方的“规律”术语近似之形下语义,同时形下之道最终又返归于“大道”。譬如艺术之“道”,得意忘言,得象忘意,从一般的“术”进至乎“道”的层次,遂有“空、灵”的意境出现。所以,中国思想文化中的“道”定位之高,它可以引领一个人乃至一个企业团体组织不断攀升,永远追寻向前而不停留。
台湾学者钮先钟先生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所有一切经贸活动都必须具有大格局、大气候……因为孙子所重视的是大战略而不是小战术……假使企业家能精通《孙子》,则他应能学会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如何迎接新的挑战”[3]。将“兵道”再进一步,其实更应以“大道”为理念。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道”,主要指企业的价值观,即确立卓越的价值观来教育和感召员工,其核心是要树立共同的价值观。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在总结自己创业60年成功经验时,把“首先确立经营理念”作为前提条件。美国IBM前董事长小托马森·沃森在总结其成功经验时,深有感触地讲道:我坚信任何一个企业为了生存并获得成功,必须拥有一套固定的信念,作为制定决策和采取行动的前提。比如,松下先生有一个250年梦想论:经营者的重大责任之一,就是让员工拥有梦想,并指出努力的目标。他把250年分成十个阶段,代代传下去,最后世间将不再有贫穷,而是一片繁荣富庶的乐土。他的目标何其远大!大大超越了自己的有生之年。长远的竞争之道应是兵家所言的“利国保民”。三星电子总裁李秉哲先生说,人类社会的最高美德就是奉献;对人类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了,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生活目标了;因此,人类经营企业的使命也应该是为国家、国民和人类作贡献。微软公司早期的经营理念是:每个桌子、每个家庭一台电脑,每天寻找提高和丰富人类生活的技术。后来改变为:使世界上的个人和企业实现其全部潜能。“视野”决定“事业”,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维特曾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发表“营销近视症”文章,指出企业营销者最大的危险是把企业的使命定得太狭窄。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儒学大会上的讲话中两次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价值在于其“经世致用”。“经世致用”的智慧蕴含着我们的“经济学”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经世济民”之道。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站在全人类解放的高度,从“平等”角度着眼,超越了狭隘意义上的所谓宏观、中观、微观“经济学”,与中国以“大道”为基础的“经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最大的功绩在于,它在同样逻辑严密体系背后有“公平”或“正义”的伸张。它远远超越了狭义经济学中的“分配调节”学说。从中国文化视野看,它饱含着道德经济伦理的思想内容。尽管侧重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秘密分析,但同样能够为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重要的启示。
中国古代经济学主张节俭,不刺激消费,否则必导致浪费;主张财富随取随用,不单纯累积财富,“多藏必厚亡”(《道德经》);和气生财,“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史记·越世家》),市场的真正动力在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不在于竞争;诚信为本,世代相传,精益求精;明码实价,适得其利,不取暴利,反而得“利”最大。生财的大道就是做人的大道,经济的学问就是做人的学问,是经世致用的“外王”事业与“内圣”的完美统一。“看不见的手”是自然道德伦理,或者叫因果定律。财富既然是善德的结果,那么经济风险的规避,就是一个弃恶扬善的伦理道德行为问题。中国本土经济学独有“德本财末”、德财相应的经济观念,衡量指标是福、禄、寿、喜、财“五福”。更高层级的经济学是救助和解决人类整体的物质和精神问题。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概念更广大,更人性,更以人为本,而不是简单的“商品”堆积。经济的本质是伦理德行的外化,遵守自然伦理就兴旺发达;悖逆自然伦理就动乱衰亡。《二十四史》记载表明,就国家经济整体观之,无非一条是因德而兴,另一条就是败德而亡,虽然“金玉满堂”,但“莫之能守”[4](《道德经》)。
“大道”路在何方?就在脚下。儒家反复强调“道不远人”。从“德行”、“德性”回归“道”是中国文化各家思想的共同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基础理念的许多现实中的企业,正是儒家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治理智慧的实践者、先行者。
把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企业的基础性理念,并不排斥外来的先进文化工具。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道器配合、道术兼备,其发展进程也不断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技术科学在我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遥遥领先于同期世界其他地区,与“中医”技术层面的“有机性”相似,大部分技术发明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很少应用于军事武器装备的改进而发挥其正面效应。这不能不说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规约力量之强大。正是“道”对“器”、对“术”的制约和限制,中华民族文化重视“以德服人”,蕴含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使文明延续至今。当然,对“器物”和“巧技”的轻视,亦使近代中国吃亏不少。科技的发展不能无限制地脱离人类的伦理恒常大道,“以善统真”在今后无疑具有相当重要性。
由于伦理道德向上直通“大道”的本性,我国传统文化对“智慧”和“知识”加以区分,认为根源于“大道”的“智慧”高于追求器、术的“知识”。两者之间,一为本,一为末。在企业文化设计上,需有暗含和对应于这两个基本层面的考虑,方能搭配适中。
当传统产业借助信息技术,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升级时,极少部分人占有了绝大部分人创造的财富,商业无法流通;在新技术刺激下,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会更短[5]。人类如果在利欲与道义之间的选择再次失衡的话,美妙的前景仍然可能成为不美妙的“陷阱”。任何国家、企业、个人都无法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置身事外。中国的企业家们,蒙中华文化之沐浴,不知能否为人类走出这一困境带来希望?
[1]彭新武,朱康有.中国管理智慧[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
[2]熊春锦.东方治理学——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3]钮先钟.孙子三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63.
[4]钟永圣.中国经典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
[5]水木然.工业4.0大革命[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王怡敏)
D616
A
1008-9012(2017)01-0061-05
2017-01-15
本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同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2015MZD044)子课题“意识形态建设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成果。
朱康有(1967- ),男,山西平陆人,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