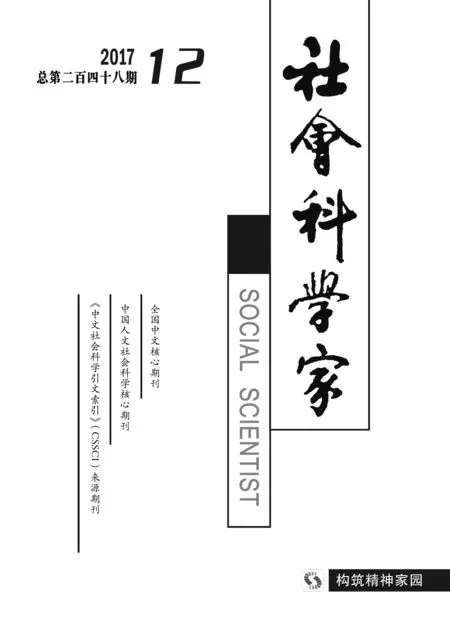16世纪西方对中国法的最初发现与表达
李 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一、引子
尽管中西文明之间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存在着广泛的交流,甚至那一时期西方很多史地类书籍中存在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载,[1]但是,这些记载很少会关注中国法。据考,最早对中国法有所记述的是公元2世纪左右叙利亚神学家巴德散内斯(Bardesanes,154-222年),他在对话体文章《论命运》(überdasFatum)用详尽的文字描述了“赛里斯人”的法律和社会:“在每一个国家,人们制定了不同的法律,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我将从世界肇端的地方(亦即远东)开始,谈谈我所知道的,以及我所记得的。在产丝之国(中国),法律禁止谋杀、卖淫、盗窃和偶像崇拜。在这幅员广大的整个国土上,看不到庙宇,也看不到妓女,也看不到淫乱的妇女;没有盗贼被带进法院,没有谋杀者,也没有被谋害的人。闪耀的火星在穿越子午圈时,无法强使人去杀人。金星和火星相遇时,也不能强使去和有夫之妇调情。每天晚上,在那里都能看到火星。在中国,不管白天或黑夜,没有一时没有婴儿出生。”[2]
然而,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亡,西方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西方对于中国的描述也相对减少起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蒙元时代”。13世纪中叶,天主教会担心蒙古人的征服会对整个欧洲造成巨大的灾难,于是派出教士与蒙古大汗进行试探性接触。1245年,圣方济各会(OrderofFranciscans)修士柏朗嘉宾(PlanoGarpini,1182-1252年)和劳伦斯奉教皇英诺森四世之命出使蒙古。①柏朗嘉宾1245年至1247年访问蒙古的报告是西方世界第一份关于远东地区的文字记载,只不过这份报告对于军事方面的考查内容,远远超过了其他。具体参见张国刚:《中西交流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3-95页。8年后,圣方济各会传教士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elmideRubruk,1220-1295年)于1253年奉法王路易九世之命造访蒙古,并撰写了38章的报告。他第一次向西方人证明契丹就是西方古代传说中的“丝国人”(赛里斯),②鲁布鲁克从丝的产地,推测到了所谓“赛里斯”和“契丹”是一个国家,他指出:“大契丹(Grand Cathay),我相信,那里的居民在古代常被称为塞雷斯人(Seres)。他们那里出产最好的绸料,这种绸料依照这个民族的名称被称为塞里克(Seric)。而这个民族是由于他们的一个城市的名称而获得塞雷斯这个名称的。”参见[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162页。西方一度中断的中国形象又被接续上了。接着,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年)在他那篇著名的游记中虽然对中国元代的法律有所描述,①[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48页。对于这一记载,史彤彪教授在《元史·刑法志》中找到了对应的条文,并做出这是欧洲书籍中第一次明确提到中国法律条文,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的论断。参见马小红、史彤彪主编:《输出与反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页。但其随着1340年代黑死病在欧洲蔓延以及蒙古王朝1368年的灭亡,马木鲁克王朝的兴起,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蒙元时代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又被阻断。因此,直至16世纪前,西方对于中国乃至中国法并没有太多的记录和信息。
1453年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伊比利亚半岛成为西方人逃脱奥斯曼帝国对地中海贸易控制的唯一出路。寻找到达东方的“海路”而不是“陆路”成为西方人新的选择。于是,“伊比利亚航海时代”来临,这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法律提供了新的契机。
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开辟了东方的新航路,二十年后的1517年,“葡萄牙国王”号就载着西方的使团取道爪哇前往中国,“这是中西方以国家的形式正式交往的开始,从此海洋将中国和西方连接在一起,同时也使西方的法律和中国的法律开始了接触与碰撞”[3]。
二、16世纪葡萄牙人对于中国法的描述
此后的几十年中,葡萄牙的探险家、商人、使节、传教士们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关于中国的报道,也相继出现在欧洲。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要对这一时期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进行区分,主要是因为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1493年以保教区为名义对当时两大海上霸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范围予以划定。西班牙人取得了向西半球的传教资格,而葡萄牙人的范围被划定在东方及远东地区。因此,从时间上来看,葡萄牙人对于中国法的描述早于西班牙人。
这些记述主要有:1515年前后葡萄牙人拖梅·皮雷斯(Tomépires)的《东方概要(手稿)》(Suma Oriental)、1516年葡萄牙人杜亚尔特·巴尔博扎(Duarte Barbosa)的《东方纪事(手稿)》(Livrodas Coisasdo Oriente)、葡萄牙人克里斯托旺·维埃拉(Cristóvo Vieira)于 1524年完成的《广州来信(手稿)》(Cartade Canto)、1549年葡萄牙人 D.热罗尼莫·奥索里奥(D.Jerónimo Osório)在科英布拉出版的《光荣之歌(手稿)》(Tratadoda Glória)、1553年葡萄牙人费尔南·洛佩斯·德·卡斯塔内达(Ferno Lopesde Castanheda)在科英布拉出版的《葡萄牙人发现和征服印度史》(Históriado Descobrimentoe Conquistadaíndia Pelos Portugueses:LivroⅣ)、葡萄牙王室贵族加里奥特·佩雷拉(Galiote Pereira)约写于1553年至1563年的《我所了解的中国》(Algumas Cousas Sabidasda China)、1563年若昂·德·巴罗斯(Joode Barros)在里斯本出版的《亚洲十年(第三卷)》(ásia:DécadaⅢ)和 1570年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da Cruz)在埃武拉出版的《中国概说》(Tratadodas Coisasda China)。
在这些记载中,葡萄牙人不约而同地对中国法进行了描述,并给予较高的评价。最早对中国法进行描述的是1517年葡使皮雷斯的随行人员维埃拉于1524年在中国被囚期间写给国内的信。在该信函中,维埃拉向西方首次介绍了中国的死刑。文载:
中国的死刑。最残酷的是钉十字架;在这里把人割成三千片而人仍然活着,然后把他剖开,去除内脏,让刽子手去吃,把全部切成碎片,扔给在那里为此准备的狗,交给狗吃,这是他们对强盗所施的极刑。其次是砍头,同时割掉私处,放进口内,把尸体分成七块。第三是,从后脑把头砍掉。第四是闷死。那些犯小罪不至于死的人,永远在中国充军,儿子、孙子[和]重孙都如此,例如,在广东的人,发配到很遥远的别的省份,永不返回他的家园;在那里充[当]军士。这就是中国的军人。那些由此上升为曼达林[7]士绅的人,我在上面说的那些人,一万名,有的终身被放逐,有的若干年。被流放到他省的人,为曼达林做家务,扫地和运水,劈柴,及其他这类的劳动,替国王的工程干活及服别的劳役。刑法是:有一种楦子(escospas),加大高筒靴(borzeguins),一个夹在脚趾中间,两个在外,用绳子紧勒足踝,并用槌子击打楦子;有时折断足踝,有时折断足胫骨,一两天就死去。同样类似的有用木块加在手指和足趾上;这使人十分疼痛,没有危险。还有鞭杖足、屁股和腿肚子,及脚底,并打足踝;许多无数的人死于这种鞭杖。所有人,大大小小,都挨刑法;有很严格的律条。百姓受到伤害,但没有控告曼达林作的恶行(meo)。鞭子是一支劈开的粗竹竿,干的,粗若指头,宽若一掌,放[在]水里浸泡,因为可以打得更凶。[4]
如果说在中国身陷囹圄的维埃拉对中国法还抱有成见,持批评态度的话,那么,之后其他人的描写则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态度。例如,亲身经历过中国的法庭审判、监禁、流放的佩雷拉对中国的司法审判和法官素质评价极高。他说道:
现在我要谈谈中国人在司法方面的措施,应知道的是,这些异教徒在这方面是多么超越基督教,比他们更讲公道和事实。[5]
在佩雷拉的著作中,他对中国法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佩氏首先对中国政制设置在总体上进行了介绍,他说道:
由于中国的皇帝总是待在大北京城里,而国家有很大,因此,它被分成很多省份,由巡抚和知府进行管理……
各省均有四个主要的老爷负责管理该省及其下属各市镇的事务。还有许多其他的老爷,管理司法事务,负责征收钱税,都为大老爷服务:他们巡视全城,预防坏事发生,对这些老爷来说,逮捕犯人,鞭打他们,并施以酷刑,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认为只是一种惩罚,并不觉的有失体面。[6]
接着,佩氏以比较法的视野对中国司法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总结出三个特点,并给予极高的赞誉。文载:
这些老爷似乎很公正,不管案子大小,提审犯人都是在各个老爷设有的公堂上公开进行的。我们每次受审都是这种情形。这样就不会出现假证,就像在我们国家里天天都会发生的那样,一个人的身家性命往往被掌握在一个居心不良的办案者手里。
……询问证人是公开进行的,公堂上很多人旁听证人的证词,因此办案者只能记录事实,无法伪造案情。而我们的国家里则有可能,因为证人的证据只有审讯者和法庭书记官知道。在这块土地上,除了在办案中有这样的制度,人们对皇帝十分惧怕和顺从,因此从不会用任何方式去打扰皇帝。这样一来,这些办案者就会了唯一的执法者,这一点比罗马人或者其他人都更甚。
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事必躬亲,因为他们只相信自己。
还有一点值得赞扬的是,在听证过程中,这些称得上是官位显赫的法官都表现得极有耐心。有很多次,我们这些外国人被带到法官面前,我们并不按他们的习惯表现得卑躬屈膝,而是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指责他们所记录的都是谎言,是假的。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忍耐令我们惊讶……而作为不信教的人,他们的司法制度在我看来相当优越,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外国囚犯,他们使用的是适用于我们的法律。[6]
最后,佩雷拉还对明代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监察御史在西方进行了首次介绍,并引发西方人对此制度的持久关注。是谓:
巡察院是皇帝的代表,每到年底,就被派到各省首府,重新审问已定罪的犯人,很多时候,巡察院会说哪个案子判错了,有些犯人就是这样得到解救。重新审理所有的案子之后,巡察院根据当时心情的好坏,选择七个或者八个罪行严重的犯人,把他们带到一个很大的场地,在那里,按惯例进行仪式之后,犯人就被砍头。[6]
实际上,对于中国司法的称赞,我们在巴罗斯和克鲁斯的著作里也能查到,巴罗斯在其著述中说道:
这个帝国的君王还有另一些治理政策:司法管理不得是本地人,而是外乡人,和葡萄牙国王任命的法官是从外地召来的一样,为的是司法对所有人公正,避免徇私情,但将官却是本地人,据说因乡土的情感,他们会尽力保卫它。[7]
克鲁斯在对中国的司法审讯、刑罚以及监狱进行详尽的描述后,[8]对中国的司法制度这样评价道:
这些信偶像的和野蛮的民族有他们自己的良好的司法手续和顺序,也表明上帝使得一位不认识真神的皇帝本性仁慈。他作出的极大努力,以及他对大案的慎重,看来是这个国家善治和德治的根源,以致尽管中国如我们所说是那样打,它却维持多年的和平而无叛乱。上帝保佑它,因为没有敌人入侵破坏,也因为它保持了繁荣和富强。这个国家的严厉司法是控制百姓易犯罪恶倾向和骚动的根本。[8]
沿着葡萄牙人佩雷拉所开创的传统,克鲁斯在其著作中也花了大量笔墨描述中国的监察制度。文载:
……
皇帝每三年派遣一次察院,他们通常都是干练的诚实人,不容易受贿。他们是皇帝信任的,可以办理有益于国家、皇帝和法制的事。这些人一般比其馀的官员更有权力……
察院参查完老爷们,便去访问监狱,接见囚犯,开释那些应当开释的,惩治那些应当惩治的……[8]
三、16世纪西班牙人对于中国法的描述
或许是对之前葡萄牙人对于中国报道过于零碎的不满,西班牙人艾斯加兰蒂(Bernardino de Escalante)于1577年在塞维利亚出版的《记葡萄牙人在东方诸国和省份的航行,以及他们获得有关中国大事的消息》①该书于1579年被英国商人约翰·弗朗布吞(John Frampton)翻译为英文在伦敦出版,题名《中华帝国概述》(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Discriso de la Navegacion que los Portugueses Hacen a los reinos y provincias de Orient,y de las noticias que se tienen de las grandezas del reino de la China)。②具体可参见澳门《文化杂志》编辑的《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和何高济教授编译的《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他在参考上述葡萄牙人克鲁斯、巴罗斯等人记述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以“章节体”介绍中国的著述方式。③实际上,这种“章节体”的记述形式在上述克鲁斯的《中国志》中就有所端倪,如他在该书中,将中国分为三十个章节进行介绍。具体篇目,参见[葡]克路士:《中国志》,载[英]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3-35页。《中华帝国概述》共分15章,其中作者在第12章和13章集中介绍了中国法。
作者开篇以赞誉的口吻向罗依埃斯主教表达了自己写作本书的目的,他说道:
在自然事情上以及在国家的治理上他们都天赋聪慧才能,看来没有别的民族(他们从未如此精明)超越他们,或者优于他们,也没有相似的各种技艺能力,这些是促使我撰写这个国家情况的原因(根据曾在该国的可靠人士的记述,以及得自被携至葡萄牙的中国人的消息),并将本书献给阁下。[9]
接着,艾斯加兰蒂介绍了地方政制的设计,提到了“总督”、“布政使”(Ponchasi)、“按察使”(Anchasi)、“海道”(Aitao)、“卢镗”(Luytisi)等官职,④可以看出,艾斯加兰蒂对于中国地方政制设置的描述与前述克鲁斯的著作基本一致。参见[葡]克路士:《中国志》,载[英]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6-108页。其中对涉及地方司法官职的“按察使”这样介绍道:
第三位官员是按察使(Anchasi),这是民政和刑事的首脑,他和他手下的书记和吏员审视和决定各种重大案件和事务,由该省普通官吏上诉到他的部门,还负责处理有关利于施政和司法的事体。[9]
在该书中,作者还详细地讲中国庭审的设置和程序进行了介绍,字里行间透露着对中国司法公正性的褒扬。文载:
而为此他们有一条法令,这些官员不得私下行事,必须当着所有吏员的面,同时公开执法,其方式如下:法官坐堂,在大堂门口,役吏站立,大声提出他的诉讼,或者用文字诉他的案子。一名书记收下并且大声宣布他的要求;在看过和读过后,他把它上呈法官去做。这种做法严格施行,他们无法接受贿赂,除非官员容许;因他们会被上司在他们的驻地免职和惩罚,所以他们害怕;这些人都严格执行命令,书记和军士及其余的人都如此。而如他们工作中犯错误,甚至当时就让他们手执小旗,拿着旗下跪,直到审讯中案子处理完毕。由此法官命令刑吏给予应有的鞭杖,这将在下面述及;以致这些官吏大多总带着膏药和伤痕,对他们说这是寻常的事,不以此为耻。……在所有民事和刑事诉讼中,法官们按诉讼顺序进行,执行法律,当着他们的吏员、役隶审问两名证人,为的是避免在审问证人口供,或者书面呈诉出现的谎报,或者欺诈。他们分别审讯每名证人,如果发现申诉和口供不一致,那就把证人分开,各自审问,直到他们之间出现不同之处,因为他们各自都说自己讲的是真话。当不能得到确实的口供时,他们就鞭杖证人,残酷施刑到他们各自吐露真情。在这些案件中他们对尊敬的人表示极大的关注,他们认为这些人不是会说谎的人。在重大案件中,涉及到要人,法官就不信任他的书记写的报告,而是亲手录下所有审询。[9]
最后,艾氏还对中国明代中央监察机构“都察院”给予了格外的关注,他写道:
这位君王十分关注他的法官和官员,以及总督首脑的公正治理,这是他们应做到的,除了每三年派出叫做察院(Chaenes)的官员考查外,还每六个月或每年秘密派出叫做御史(Leachis)的特殊法官,这是国王信任的,他们也忠于他,拥有极大权力访查各省,不用返回向他上报案情,可以惩处,不管多大的官,任意免除官员的职位。[9]
除了艾斯加兰蒂以外,整个16世纪,西方的中国法最具典型的文本应是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儒安·贡萨列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1583年开始编写的《大中华帝国志》。①《大中华帝国志》全称为《依据中国典籍以及造访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记述而写成的关于中华大帝国最负盛名的情事、礼仪、和习俗的历史》(Historia de las Cosasmas Notables,Ritos y Costa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Sabidas asi por los Libros de los Mismos Chinas,como por Relaciones de los Religiosos,yotro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该书共分 3卷 44章。第一卷是对中国的总体介绍,第二卷叙述菲律宾的西班牙教团三次前往中国传教的经历,第三卷则是关于中国的零散信息。这部书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由于该书是门多萨依据16世纪以来所有的使华报告、文件、信札、著述整理汇编而成的;②根据英国学者博克舍的研究,他认为门多萨的著作主要参考了佩雷拉、克鲁斯以及拉达的作品。参见[英]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8年版,导言,第2页。另一方面,作为这一时代的总结,该书自1585年在罗马出版,至16世纪末,已被翻译为7种语言,46种版本,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了西方。对此,哈德孙(G.F.Hudson)说道:“门多萨的书接触到古代中国的实质,它的出版可以被当作一个分界:从这个日子起欧洲学术界可以得到有关中国及其制度的充分知识。”[10]
门多萨在这部书中,记述并褒扬了古老中国尤其是明朝的军队制度、内阁制度、户籍制度、监察制度、科举制度和复杂的礼仪制度,而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对古老中国司法官员及其司法制度的评述。门氏首先对明代的公开审判进行了描述:
皇帝发给他们足够的薪俸。因为受贿或接受与案件有关的当事人的任何东西,都要受到严厉惩罚。法官同样受到严格的控制,内阁给他们的首要规定就是:不能在屋里接见任何诉讼人,只能在公堂宣布判决,所有官吏必须在场,并且,必须让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听得见。其做法如下:法官坐在审判席上,门卫站在大堂入门处,高声通报谁要打官司,有何要求。要打官司的人在距离法官较远的地方跪下,大声提出他们的冤情或申诉,或者以诉状上呈给法官。如果用诉状,则由一个文书或公证人宣读,官员听明之后,立即依法审理,他用朱笔在状上批示,并吩咐属下应如何去做……在办理任何案件时,不管民事的还是刑事的,法官只能书写,并当着其他官吏的面,公开判决犯人和审讯证人。[11]
其次,他还对中国古代司法官审慎地审讯证人,查找真相的重要性做出了说明,并给予了称赞:
因为无论是口头查问或书写记录,都不允许任何有违真实的东西存在,只能如实反映。老爷亲自审讯证人,如果说法不一,则把他们集中到一起,一个个当面加以盘问,直到通过努力知道更多的真相。如果这种办法不奏效时,就对他们施刑,逼他们招供。他们相信有经验和知识的人必须施刑才会讲真话。
如果案情重大,或牵扯到大人物,法官就不信任公证人或文书去做记录,而是亲自录下证人的口供,而且非常加以重视。这种细致负责,使得很少有人抱怨执法不公。这是值得注意的大优点,所有称职的法官均应效仿,这样就可以避免由于不采取这种办法而带来的诸多麻烦。[11]
最后,门氏还对中国古代法官兼理行政事务的做法,不但不认为这是缺点,反而觉着“值得称道”。他指出:
这些异教徒对待此事一丝不苟。法官除了执法公正之外,他们还采用一些值得称道的措施,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概莫能外。[11]
此外,门多萨还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对中国古代的死刑制度进行了描写,并赞扬中国对待死刑的审慎,文载:
对于死囚的处决,只有在他们称之为察院(Chenes)和御史(Leuchis)的巡访使或驻地法官,到监狱来巡查时才能执行。他们的出访是秘密进行的。他们察访囚犯,查阅所有被判死刑的犯人的名单及其原因。尽管有些判决已得到皇帝及其内阁的批准,他们仍然要当着审判该案的法官的面,或受理该案的官员不在时当着其大,代理人的面,再审查一次,弄清楚每个犯人所犯的罪行,以便了解判决是否公正妥当。充分审查之后,他们从中选出50名罪大恶极的犯人,命令狱吏准备处理事宜。这之后,他们又再重新检查一次,审查犯罪原因和所犯罪行,看是否能够尽量挽救他们。如果的确发现其中尚有一丁点儿的可以免死的线索,那就将他和其他人分开,同时立即鸣炮三响,那是通报把死囚提出监牢。接着,当死囚被押出来后,他们便再一次会商,看能否宽免某些人,如果不行,则命令再鸣炮三响,将死囚押赴刑场。不过在中断会商之前,他们会返过头去再次查看犯人的罪行,看有无可能通过什么办法挽救他们。如果发现有,或存在某些嫌疑,则把犯人从刑场带回,再关到监狱……当所有根据法律企图挽救的努力都无效时,他们再鸣炮三响,然后根据判决依法处置。[11]
即便之前有许多海外传回欧洲的书信都有对中国刑罚残忍的描写,如前述1517年皮雷斯使团随从维埃拉和葡萄牙商人瓦斯科·卡尔渥(Vasco Calvo)在《广州葡囚信》(Cartasdos Cativosde Canto)中的大量描述,①“1522年圣尼古劳日(S Nicolao)为他们插上了刑牌,以强盗罪处死并悬树暴民。判决书说他们是大强盗派来窥探中华大地的小强盗,故在树上吊死。据官员们讲,将此判决禀请国王核准,1523年9月23日国王降旨行刑。这23人被卸尸,头、腿、胳膊分家,肚肠从口中流出,从肚子处将尸体一刀两断,然后弃尸广州街头。还有些人被拉到城外的村庄主要街道上游街示众,然后处决,让广州城内外的人看看葡萄牙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叫人民不要再提起葡萄牙人。于是他们占领了那两条大船,趁两个船长还在酣睡之际,将全体人员捕获,就地正法。将首级割下,五脏六腑取出,让葡萄牙人背着去见广州官员。一路上,敲锣打鼓,招摇过市,然后弃之垃圾。从此不再允许葡萄牙人及任何外国人来此”。转引自田涛、李祝环:《接触与碰撞:16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亦可见[葡]克里斯托旺·维埃拉:《广州囚信书简》,载[葡]巴洛斯、[西]艾斯加兰蒂等著:《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9-100页。但门多萨也对此为中国进行了辩解,他说道:
如同他们的法律所体现的那样,中国的皇帝及其官吏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公共利益,惩恶扬善。为此,皇帝制订了严酷的刑罚,毫不留情;他们严加防范以免有人违法。[11]
总之,当时的中国法在门多萨眼中是优良的,是值得西方人学习的,甚至这些优良的法律构成了中国强大的原因。对此,门多萨总结道:
因此,将好处和为人所知的酬赏奖给治政良善者、严惩作恶者,使得这个强大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了解一个国家的统治、管理方法(在这本史书里已多次提到)并把它与我们悠久伟大的实践加以比较,你们将会同意我的观点。[11]
四、16世纪西方对于中国法描述的意义
如果说13世纪马可·波罗时代,西方对中国及其中国法还处于缥缈传奇,信息寥寥,其重心还在介绍中国经济繁荣,物产丰富的话,那么,以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为代表的16世纪,西方已经对中国及其法律形象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且重心已转移到称颂中国的典章文武制度。与之前马可·波罗时代的游记不同,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通过一个世纪航海家的实地记述,使之前“蒙元时代”马可·波罗笔下神话式的中国变成了现实。况且,他们的作品,如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是以“史志”的形式完成的,显然比之前的个人见闻性的各类“游记”更严肃,也更可靠。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为西方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中国法律形象。因为对于16世纪即将面临社会转型的西方而言,一个统一的、具有明确价值识别意义的中国形象,远要比混乱矛盾、毁誉参半的中国形象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此时的西方不仅可以在现实经验视野中了解中国法,而且进一步可以以中华帝国为尺度评判西方。例如,约瑟夫·斯卡利杰在读完《大中华帝国志》后激动地说道:
这一令人赞叹不已的帝国……它谴责我们的行为。从他们的天平上来衡量,我们这些法国人仅为一弹丸小王国,我们之间不能相互详解,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法国当时正被宗教战争搞得四分五裂);而在他们那里则生活的国泰民安,其法制如此有度以至于使基督教感到耻辱。[12]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于中国的赞美也影响了之后的耶稣会士时代,甚至是启蒙时代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对此,英国学者赫德逊说道:
这些记述极为生动而准确地描述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特征。这些特点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朽精华;另一些则是该世纪,即明朝盛极而衰的时期所特有的。门多萨的著作触及了古老中国生活的实质,它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从此关于中国及其制度的知识的一部适用的纲要就可以为欧洲的学术界所利用了。[13]
因此,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所主导、发现的中国,对于西方而言,其意义在于:一方面,中国形象的意义从器物才层面开始转移到制度层面;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西方开始的“中国风”(Chinoiserie),提供了一个知识与想象,评价与批判的起点。这其中中国的法律及其中国法律文化成为他们论述中重点。
[1]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十年来世界对中国认识史纲[M].学林出版社,2013.
[2]Eusebius.Praeparatio Evangelica,Ⅵ,10.(转引自李约瑟,翻译小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M].科学出版社,1975.338-339.)
[3]田涛、李祝环.接触与碰撞:16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
[4](葡)克里斯托旺·维埃拉.广州囚信书简[A].(葡)巴洛斯、(西)艾斯加兰蒂,何高济.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C].中华书局,2013.118-119.
[5]葡伯来拉.中国报道[A].(英)C.R.博克舍,何高济.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C].中华书局,1998.11.
[6](葡)加利奥特·佩雷拉,裘杨健.我所了解的中国[A].文化杂志.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C].大象出版社,2003.51-53;54-55;56.
[7](葡)若昂·德·巴洛斯.亚洲[A].(葡)巴洛斯,(西)艾斯加兰蒂,何高济.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C].中华书局,2013.30.
[8](葡)克路士.中国志[A].(英)C.R.博克舍,何高济.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C].中华书局,1998.120-128.
[9](西)艾斯加兰蒂.中华帝国概述[A].(葡)巴洛斯、(西)艾斯加兰蒂,何高济.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C].中华书局,2013.193.
[10](英)C.R.博克舍,何高济,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M].中华书局,1998.1.
[11](西)儒安·贡萨列斯·德·门多萨,梅子满,林菁.大中华帝国志[A].王寅生.西方的中国形象(上册)[C].团结出版社,2015.108-110.
[12](法)安田朴,谢和耐,耿昇.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M].巴蜀书社,1993.163.
[13](英)G.F.赫德逊,王遵仲,李申,张毅.欧洲与中国[M].中华书局,1995.219-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