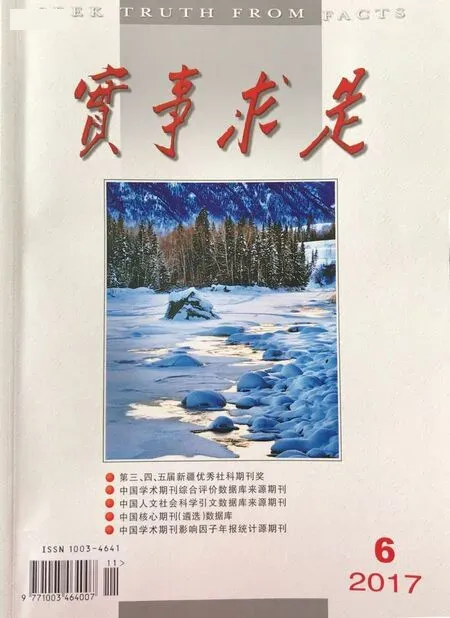《福乐智慧》中关于人生观的思想初探
孟璇璇
(新疆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福乐智慧》中关于人生观的思想初探
孟璇璇
(新疆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诞生于十一世纪的《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是喀喇汗王朝史上一颗不朽文化明珠。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以长篇的劝谕诗形式,全面呈现了当时维吾尔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国家政治结构、人才遴选机制以及思想状况。其中,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本人对于生命的感悟与沉思渗透于字里行间。其人生观思想,在今天读来依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质言之,贯穿全书的人生观思想,发挥着“源头活水”的奠基性作用。
《福乐智慧》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人生观
《福乐智慧》历来有“奇书”的美誉,这不仅在于它作为叙事长诗的艺术成就,更由于书中所涵括的丰富内容。正如魏良弢先生在《喀喇汗王朝史稿》中所言:“《福乐智慧》不仅是优秀的维吾尔文学著作和哲学——伦理学著作,而且是研究喀喇汗王朝的重要资料。它提供了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国家组织、行政管理、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非常珍贵的资料”。[1](PP1~2)可以说,《福乐智慧》堪称喀喇汗王朝时期社会风貌的一面镜子。
作为十一世纪维吾尔文化的里程碑性作品,《福乐智慧》体现了当时社会思想的发展高度,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本人即是此时期思想领域的杰出代表。深研此书不难发现,《福乐智慧》中立场鲜明的人物形象设计正生根于作者本人对人生的思索和拷问,甚至在面对现实与理想时的矛盾与挣扎。
一、《福乐智慧》人生观的形成背景
任何伟大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福乐智慧》的诞生既是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杰出才华的结晶,更离不开喀喇汗王朝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孕育。即《福乐智慧》的人生观思想绝非凭空产生,这与作者所处时代的时代背景存在深刻关联。
历史的卷轴尚须转回到公元840年。那时,雄踞漠北百年之久的回鹘汗国遭受到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直接导致大批回鹘人的西迁。其中一些部落翻越天山占领了吐鲁番盆地,与当地居民相融合而建立起历史上有名的高昌回鹘汗国(公元840~1210年)。另一支西迁的回鹘人主力则到达天山南麓喀什噶尔一带,建立起了以回鹘人为主体并包括众多突厥部族的喀喇汗王朝(公元840~1212年)。进入全新的生活空间后,这些人不仅面临着自然条件和社会制度的转变,也伴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
此时的喀喇汗王朝实行了一种类似于中原分封制的政治体制,初具规模的等级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福乐智慧》中提到的铁匠、靴匠、木匠、皮匠、弓箭匠、画师等工种,和直接表示各种工匠难以一一列举的现象来看,当时手工业的门类极多。农牧产品也较先前更为丰富,包括种植、园艺、水利技术等都有所发展。再加上喀拉汗王朝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商业在这一时期走向繁荣显得毫不意外。
与此同时,喀喇汗王朝已逐渐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频频通过增加赋税、巧取豪夺及宗教压迫等方式来强化统治。这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并引发底层民众的屡屡反抗。不止如此,统治阶级内部也充满了权力的征伐,整个社会处于高度的冲突与动荡之中。
这个经济繁荣而政治动荡的时期,社会思想却极其活跃。公元9世纪,东方文化的复兴借助贸易及宗教传播的力量很快波及中亚地区,本土思想亦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作为维吾尔文化史上另一高峰的《突厥语大辞典》与《福乐智慧》在此时期同时诞生。从二者的内容涵括与认知深度都可以看出,当时的维吾尔社会文化中已经吸纳了东方文化的因子。
动荡不安的政局酿出的,可不仅仅是思想领域的挣扎与反思,更是黎民百姓的颠沛流离和价值领域的纷乱支离。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长大,对黎民百姓的沉重生活深有体察:“有的人倍受欺凌压榨之苦;有的人拮据贫困、满怀愁绪;有的人无食,有的人无衣;有的人愁肠百结,呻吟痛哭”。[2](P682)所有作者亲历的社会不公现象,都在孵化他的精神世界:热情讴歌公平正义、崇奉智慧贤明,同时激烈抨击社会的阴暗事实。他在附篇的《论世风日下和人心不古》中写下:“信义充满了灾荒,不义充满了人世”、“我满怀忧伤,尽遇不义之徒。谁是信义之士,我愿为他奉献生命”等愤懑之言,若非陷于极度绝望的心境下,恐难有如此丧气之语。
遗憾的是,作者的生平资料业已无从考据,只有《福乐智慧》中的只言片语留下了些许线索。序言中说:“作者是出生于巴拉萨衮的一位虔诚信士”、“他在虎思斡耳朵诞生,出身名门,语言可做凭证”。[2](P10)可见,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应是出生于中亚巴拉萨衮的贵族家庭,而且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他还提到“人生度过了四十岁大关,意味着青春已别你而去。当五十岁伸手摸我的头顶,鸦翅似的黑发变成了白鸪羽翼。如今六十岁向我频频呼唤,如果大限未满,我定会向它走去”。[2](P51)据此,可以推测他写作此书时应该已年过五十。虽然直接的材料不够充分,但书中无处不藏有作者的影子,如他借月圆之口讲到的:“我具有万般美德,鹤立鸡群。我何必在此踽踽独行,不如去见国王,为他效忠。以我的才德为他效力,让他垂恩于我,使我摆脱苦辛”[2](P64)等等。
二、《福乐智慧》人生观的基本内容
一般认为,人生观是关于个人对人生目的、态度、价值、理想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即那些任何人的生活实践都离不开一套对人生的完整认识。具体来说,这包括对人生价值的定义、对人生轨迹的期待以及对死亡等人生之苦难的理解等方面。即便这种认识在部分人那里是“日用而不知”的隐晦存在,却渗透于每个人的点滴言行之中。
关于《福乐智慧》的人生观思想,书中虽然没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这部分内容却是研究此书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因为,无论是主要人物的形象设计、反复讴歌的诸多美德,还是主要人物之间立场鲜明的长篇辩论,都隐含着作者的人生观思想。
(一)普惠他人的人生目的
《福乐智慧》中除觉醒避世修行之外,另外三个主要人物包括日出王、大臣月圆和贤明的形象都突出惜时上进、建立事功的特点。作者在全文开篇的《论书名的含义和笔者的晚景》中已提出个人价值的倾向:“我首先要说的是日出国王,好人啊,请让我来讲讲他的含义。接着我要讲大臣月圆,因为他,吉祥的日子光彩熠熠。这日出象征着公正法度,这月圆代表了欢乐幸福。然后我又讲了大臣贤明,他代表了智慧,提高人的价值。最后我又讲到修道士觉醒,赋予他‘来世’的含义”。[2](P49)很明显,这里代表“此世”的人物均体现着某种社会价值,而唯一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觉醒被指向了“来世”。如果说这样的意指还不够明确,那么其后的内容则要直接的多:“置身于欢乐之中的俊杰,仔细聆听吧,莫要辜负我的心意。努力进取吧,莫要迷失正道,莫要荒废青春,要紧抓时机。珍惜青春吧,它会匆匆而过,生命难久留,它会匆匆逃逸”。[2])(P50)那么,这里所赞颂的“正道”是怎样的呢?书中用了大量篇幅宣扬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取向,将人生目的导引向发挥自身的卓越才能惠及他人。
对于第一位出场的日出王,书中是这样描绘的:“他英武威严,品行端正,美质使他的地位与日俱增。他依靠知识来充当国君,一言一行,庄重端正。他执掌国事果断有力,果断和宽厚相辅相成……谁若有智慧,被他召在身边;谁若有知识,被他奉为上宾……日出王时时体察民情,一切封闭的大门对他畅通。他一手扼制了无能之辈,一手使卑劣之徒扫地以尽。他时刻清醒地治理国事,威望越来越高”。[2](P56)寥寥数言,已经从外貌、品行、行事风格及性格特征勾勒出了一个勤政爱民的国王形象。同时,日出王的地位上升与他个人的“美质”关联甚大,即君王的品德在稳固权力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后文紧接着对“美质”的内容作了阐释:一方面是对于“知识”的尊崇,日出王自己依仗知识治理国家,同时召集有知识的人治国理政;另外,他重视体察民情,在处理国事时果敢与宽厚并用,以严明的态度对待民众中的“无能之辈”与“卑劣之徒”,以起到净化民风的作用。
如果单凭对上文的分析就判定日出王不断完善自身品质是为了惠及百姓还显牵强,那么,后文中他与月圆的谈话内容则要更加明确:“国君若善良,人民就正直,人民会习性善良,风气端正。国君若是亲近好人,坏人也尽力干好事情。若是坏人接近了国君,他们的手会伸到人民的头顶。坏人得了势,好人即会消失,好人执了政,坏人即会绝踪……王中之王制订了多好的法度,坏人会受到监牢的严惩”。[2](P121)很明显,日出王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统治者扮演的社会风气指针作用。他本身的品质及所推崇的特质都不仅仅与自己相关,更与治下的每一个百姓息息相关。他同时觉察到,正向的激励并不足够导引民风,还需要反面的约束,法度的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一个人所处的地位及相应的职权是其才能得以发挥的基础和保障,故而日出王凭借手中的权力极力完善国家治理、追求造福百姓,堪称惠及他人的典范。
如果日出王因地位过于特殊而不易效仿,大臣月圆则将普通人如何做到普惠他人发挥到了极致:“从此月圆在宫中供职,夙兴夜寐,毫不懈怠。他办事认真,毫无失误,夜间伴着逻卒,白天伴着门卫。他出入宫禁,常侍左右……国君器重臣仆,出于他的功劳,谁若建立功劳,低贱亦可变的尊贵”。[2](P84)这里描述了月圆在朝廷获得官职之后,不辞辛苦的充分发挥自身才华来为国效力。书中不但明确树立这样的人格典型,甚至大肆宣扬一种理念,“不幸的人因立功而获得高位,无能的人永远被拒之门外。为国君效力要忠贞不渝,建立了功劳会百事顺遂”,[2](P85)完全把积极入世、建立事功被看作一种值得讴歌的美德。
类似的观点十分丰富但散落于全书之中,不仅仅是日出王、月圆二人,包括贤明与觉醒的论辩中也有颇深刻的见解,这里不做一一摘列、分析。谨以日出王与月圆的一段谈话内容对本分论点略作总结,月圆进言:“请告诉我,我该如何为你效劳,你喜爱什么,让我把它找到……臣仆供职,若是不合君王心意,即使吃尽苦头也不得好报”,[2](P114)这里意在以月圆之口牵出日出王用人最看重的特质。日出王的回应不仅仅关乎他的个人喜恶,正如上文所析这也是全社会的价值风向标:“若问善德的秉性,它不顾自己,专利他人。他专为所有的人们行善,却从不居功要别人感恩。他不求利己,只为他人造福,造福于他人而不求回赠”,[2](P116)这里已经明确将普惠他人的主旨揭示出来,日出国王自己以之为人生追求的准绳,也以此作为选拔近臣的关键要素。
(二)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
明确了个人生命要追求的最终目的之后,就需进一步探讨个人应以何种态度面对无法逃避的诸多人生难题。在《福乐智慧》一书中,集中了大量笔墨进行探讨的人生难题落脚于面对死亡的问题。书中的第一条主线从月圆面见日出王自荐展开,但是很快就将话题引到“死亡”而告终结;第二条主线从贤明的出场展开。贤明一出场就接住了父亲关于“死亡”的探讨,提出了作为一个尚未长成的青年人对死亡的认识。在全书接近尾声的部分,觉醒也走向了生命的终结,为贤明留下了自己感悟人生的箴言。
需要明确的是,标题所指的“向死而生”并非重在突出对待死亡应当抱有乐观情绪,而在于提醒人们:当意识到人必有一死后,就需要珍惜时间、赋予自己的生命以价值。比起史铁生“死亡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优素甫这里对待死亡则要严肃、沉重得多,如月圆在弥留之际曾一再申明:“上升的事物终会降落,人有一生复有一死。有上必有下,有高必有低,有乐必有忧,有甜必有苦……头上的白霜是死亡的信息,使你懂得了生命的价值。你享尽天禄,尝尽生之乐趣,醒悟吧,死亡将要把你吞噬”,[2](P150)认为死亡既不是一种惩罚也不是解脱,优素甫着意强调死亡是一个人生命历程中必然会发生的事件,故而无须惶恐,应当平静对待。但死亡又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它从“头上的白霜”作为显现的标志,从“尝尽生之乐趣”中穿过,又是人人都不可逃避的结局。
这一思想在月圆临终前对儿子贤明的教诲里更为明确:“不管怎么生的总要死去,不管多么不愿死总会丧生,将死之人是时间的俘虏,时辰一到一步也再难迈进……世间万物都有定命,呼吸的次数都有一定。日月回环,生命也有来去,消逝的岁月把你送入坟茔”,[2](P165)在死亡面前一切条件都变得无足轻重,所有的努力也都不再生效,对于任何生命来讲那都是一个严格的界限。因而这里一再强调死亡的到来本身极其自然,同时又含有面对死亡时的无力感。
看清了死亡在人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后,作者又借贤明和觉醒之口进行了深化。作者安排贤明借着父亲月圆在临终前的忧愁悲泣来发声,意在揭开贤明作为智慧的化身对死亡所持的见解,他对弥留之际的父亲说:“你若为虚度的一生而悔恨,那你就哭泣吧,莫要擦干泪痕。流逝的白昼不再回还,等待着你的是黑夜沉沉。若是你为了我忧愁伤怀,别哭泣了应该欢欣。你既被创造就会消亡,被造者消亡,造物主永生。你是我父亲,仁慈又宽厚,造物主比起你来更为宏仁。他创造了你给了你幸福,相信吧,他也会给我福运”,[2](P168)贤明对死亡的认识使得向死而生的态度更为明晰。他既意识到了时间的不可逆转,认为一个人生命中被赋予的时间流逝就不可挽回,故若因死亡将来临而生命已虚度陷入无尽悔恨,则对于父亲的悲泣虽心痛却也在情理之中;同时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所有被创造者在造物主面前相对平等,会面对同样的出生、死亡以及被赋予福运,并以此劝慰父亲莫对自己的未来过分担忧。
在觉醒对贤明的遗言里,向死而生的态度再一次被深化:“兄弟啊,切不可昏昧不醒,更不可走邪途虚度了一生。要持身以正,莫失去正道,正道会使你如愿称心。对一切生灵都要关怀,要口心正直,对真主虔诚。少忧心忡忡,多做些祈祷,生气时要温顺,急躁时要冷静。莫忘了死亡,要做好准备,莫忘了自己,要认清根本。莫热衷于财富,玷污了自己,财富会留下,你会饮恨而终”。[2](P791)
这三次对于死亡的讨论颇有环环相扣的意味。首先,在月圆的遗言里强调死亡是一件必然会降临的事情;紧接着,在尚未成年的贤明口中提出时间的不可逆转与一视同仁,而在觉醒这里则是明白揭示出死亡对于人生的意义。正因生命要面对死亡,就被强加了界限,也才能在有限的时间段里凸显出个人自觉的价值。人的自主选择包括:坚守正道、关怀众生、为人正直且表里如一、温和沉稳、清心寡欲及对真主虔诚等等。牢记自己终将面对生命的终结,每一个选择都不得不谨慎;清醒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时间有限,懒惰势必被克服并积极追求进步。综览全书,恐怕这也正是作者想借两大主角之死想要传达的人生态度,即人的生命应当是向死而生的旅程。
(三)追求完美的人生理想
在设定了自己的终极人生目的,又理清了面对人生需持有的根本态度之后,接下来的关键则在于,要选择怎样的路径具体实现自己设定的人生目的,也即人生理想和蓝图的勾勒。《福乐智慧》的读者都会发现该书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即全书无一反面形象,书中的四大人物设定均高度理想化。从其人生图景来看,无论是日出王的勤政爱民,还是大臣月圆及其儿子贤明的位极人臣,包括觉醒避居世外的知足安宁,都呈现为完全出于个人自愿的选择并甘心投入其中的人生状态,几乎彻底抹去了现实生活干扰下的杂音。
作者从“月圆”的命名开始,就奠定了他的人生基调,“是一位哲士为我取名,这名字正符合我的秉性。幸运来临时声名卓著,好似新月日盈,光照寰宇”,[2](P401)还借国王之口对他的整体形象做了描绘,“国王对月圆考察了许久,认识到他是个完美之人”。[2](P104)而月圆的仕途更是令人羡煞的一帆风顺:“国王对月圆日益器重,赞不绝口,多有赏赐。赐予他大臣头衔,还有黄金印绶,赐予他旗帜、铠甲还有令鼓。月圆的权力遍及于全国,敌人闻风丧胆,销声匿迹。月圆执掌了全部国事,他趁此时机多行善举,从此天下大治,百姓富裕,人人为国君祈祷祝福。黎民摆脱了忧愁劳苦,羔羊和野狼一起游憩。国家兴旺,法度健全,国王的福运有增无减。国运昌盛,持续多年,普天下黎庶走上了正路”。[2](P141)虽则有明显的理想化痕迹,但这怎么看都是所有选择入仕为官者的终极向往:得到最高掌权者的信赖和器重,获得与能力相匹配的职位及权力,且有足够的空间和时机发挥才干,能够最终造福百姓而有所建树。这些要素作为仕途通达的条件,得其一者即为幸事,全得之者则甚为罕见。
但作者并不止于此,还在月圆辞世之后添了一笔,以日出王对他的回忆为月圆的完美人生画上了句点:“国王想起了月圆的美德,悲叹道:可惜了,人间英杰!他本是宫廷的美饰,我的良友,他执掌政务,人民获益良多”。[2](P211)如此一来,月圆的形象正如他的名字那样光辉、圆满而难得,借助于王权也把他的光辉洒向了普天之下,表现为一个形质兼美且事功卓越的完人。
不止月圆,子承父业的贤明比他的父亲更早踏上了完美人生的轨迹。国王先从考验他开始,“国王对他进行了考验,证明他办事公正不偏。国王有时器重他,将他抬举,有时厌弃他,使他卑贱。得宠时他没有仗势欺人,失宠时他没有少做贡献”。[2](P230)由此可见,贤明已然具备了极高的个人修养,尚未成年就养成沉稳持重且公正不偏的美德。关于他的办事才能,文中也有描绘:“贤明办事正直不阿,国王让他常侍身边。处理事务他条理分明,清点登记了国库的财产。管理财务他清廉自首,身居国库一尘不染”,[2](P231)个人美德与行事才干表里相彰,再加上国王的青睐自然会把他推向成功之路。
“贤明的权力遍及全国,权力所及,有令必行。给他赐予了头衔、印信、骏马、锦衣,使他福如东海,位极人臣。国王还以美妙的言词,颁令嘉奖他,让他做亲信。供职于汗宫的大小人等,都向他纳礼,愿为他献身。僚属们都向他谒见,为他祝福,奉献上礼品”,[2](P236)少年得意,何等风光!一人之下的权力、举世认可的赞誉、荣获世俗的财物、君王的高度信赖、僚属的尊崇等,几乎任何投身仕途者所期待和憧憬的内容,他都轻而易举地集于一身。比起父亲的大器晚成,贤明的人生实现了彻底的一帆风顺。及至全书结束,贤明依然深受国王倚重:“外界的事情你多留意,愿你耳聪目明时刻清醒。请尽力去做,莫依赖于我,力所不及之事,让我来做后盾……从此贤明勤勉效力,在宫中操劳,把政务料理。百姓安乐,天下大治,国君安逸,欢悦无比。国人为贤明日夜祝福,贤明的美名永留人世”,[2](P768)他不但少年得志、一生平坦还以权倾朝野的一贯身份得到了善始善终,这样的人生履历堪称完美人生的典范。
日出王不但个人品质极高还善于治国理政,并先后得到两位完美的大臣辅弼使得国家大治,自然称得上完美君王;觉醒对人生有着透彻的认识,一生为真主而活纤尘不染,更是公认的完人。就全书来看,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因过度理想而不乏溢美之词,但有一点可以十分明确:所有人都被勾勒出了一条完美的人生路径。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福乐智慧》的作者本人定是一位极度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他所期望的人生正如书中四大主人公的形象,拥有完美的人品、卓越的才能、极高的社会地位、广阔的施展空间以及造福普天下黎庶的政绩。正因为彻底抹去了世俗社会的底色,这样的人生理想美则美矣,却终究如水中月而可望不可即。
三、《福乐智慧》人生观的当代审视
作为优素甫在十一世纪的思考成果,虽然《福乐智慧》由以产生的社会土壤不复存在,但书中探讨的许多问题始终为人们关注,人生观思想即在其中。就人生观思想而言,并不存在绝对正确的历史标准。因而,我们要想从《福乐智慧》人生观的思想中有所借鉴,就需要对其人生观思想的内容作出妥当评价。
《福乐智慧》被誉为喀拉汗王朝时代的经典,但难以脱离历史的局限以及个人思想的片面性。以当代的视角来看,书中这种局限则更加明显,以下分述之。首先,价值根源上打着实用利己思想的烙印,并未提升到超越的价值层面。在全书中,这样的痕迹比较多,这里仅摘取部分以作说明。在诗句“即使我给你留下了黄金白银,也不能与我的教诲相等。黄金和白银总有用完的时候,照我的话去做,定能找到金银”[2](P28)中,为了强调自己教诲内容的重要性,他提出遵循该教诲的意义在于“找到金银”。如此,施以教诲的目的和遵循教诲行事的动力就达成了一致,都落到了对实际金银财物的追求上。
而在诗句“青春易逝,生命匆匆流失,尘世如梦,你岂能长久驻足。你应以生命为本钱,善行为利润,来世你将得到华服美食”[2](P34)中,既能看到对今生之短暂的强调,同时也有对善行的倡导,但是最终的落脚点则放在了来世可以获得“华服美食”的期待上。在实用主义思想主导下,生命本身也不过是赚取来世享乐资格的“本钱”。类似的诗句数量不少,还有“语言的好处巨大无比,语言得体,奴隶会得到抬举”,[2](P136)可见不仅仅是善行,包括优美的语言也只是受人抬举的工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文所述普惠他人的人生目的与此处的实用利己思想并不矛盾。因为,普惠他人作为书中大力倡导的一种人生追求,其价值根源依旧在于实用利己性。
其次,反复强调对时光流逝的悔恨,缺乏对“有意义人生”的正面建构。书中反复为生命易逝而哀叹、为虚度光阴而悔恨,却始终没有提出建设性的观点,即怎样度过一生才能免于悲叹?无限慨叹自然可以为读者留下广阔的发挥余地,这或许可以实现艺术上的成功,却难免陷于思想梳理中的矛盾。如诗句“月圆的心愿充分实现,财富空留世上,寿命将尽”[2](P143)“月圆的病情日益加剧,对生命已失去最后希望。他懊悔地说:可惜啊,生命,可惜我虚度了美好时光!昏昏然送走了匆匆一年,茫茫然抛掷了青春华年”,[2](P152)这里明确表示“月圆的心愿充分实现”而前文也曾对他建立的事功大肆歌颂,却紧接着感叹“虚度了美好时光”,若非作者曲笔另表他意,则难免互相矛盾的嫌疑。
另有“生命好似梦幻,去无踪影,无论你是奴隶抑或是帝王。往昔的岁月是一场春梦,剩余的时光将在懊悔中流淌”[2](P188)等多处,在时光之易逝与时间之公平的意味之外,似乎始终没有对“懊悔”作出解释,也就缺乏一个“充实”或者“完满”人生的标准。
或许,这里触及了对人生本虚无的意识,亦即任何形式的追求在死亡面前都会丧失意义。如书中有这样一番哀叹,“我曾倾心于尘世,陶然而乐,它却无情无义,将我厌弃。尘世曾召唤我,将我迷惑,我奉上了赤心它却逃逸。尘世以怨报德,幸运老却,要听我的话,莫让它骗你。该干的许多事被弃置一旁,我却追逐欲念干了蠢事。这生命好似清风,倏忽即逝,使我徒然自伤,呻吟悲泣”,[2](P160)有想要揭示“尘世”之虚幻本质的意向。但作者似乎并未深入觉察,故而止于反复感慨生命的易逝,不但使得整体上缺乏一种豁达和剔透,也始终没有呈现自己的最终思考结果。当然,这里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怎样的人生值得一过”,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原因——《福乐智慧》中勾勒的人生轨迹过分脱离现实以至于无法从思想建构上完成自洽。
最后,对完美人生的勾勒过分理想化,以致不符常规而难以自洽。书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几乎在每一个具体的讨论中都留有痕迹,但是最明显的,当属书中主要人物形象及其人生历程的塑造。身为统治者的日出王礼贤下士,全部精力放到了安邦治国上,而且天公作美,他几乎毫不费力地就得到了两个忠心耿耿又智力超群的辅弼大臣。在处理王权与相权的关系时,他能够以巨大的包容力和耐心应对,并且对握有重权的大臣全然信赖。甚至面对觉醒这样的普通百姓,他可以屡次三番写信、派使邀请,言辞温婉、态度谦逊。自荐入宫还身居宰相的月圆,集出众的外貌、高超的智慧、非凡的品质和宏大的抱负于一身,虽然大器晚成却能同时拥有生前的功名和死后的美誉。贤明的人生起点很高,子承父业同时也继承了父亲的几乎所有美德,有着比父亲更多的时间来驾驭愈加平稳辉煌的人生。还有贤明的宗亲觉醒,以才德无匹的世外高人形象出现,不但身居高位的亲属贤明对他十分恭敬,连日出王对他也是极为谦逊、渴慕。
当然,这里不是说人物形象的塑造过于理想化,而在于,一个人的人生要想辉煌到书中所描绘的程度,单纯依靠个人才华、品性和抱负是远远不够的。任何样态的人生轨迹都是多方面具体原因在综合作用下的成果,而在阶级社会要想达到这样的民主和开放程度是不可思议的。至于人际关系的处理方面,这里显然是把它简单化了,无论是日出王与月圆、贤明之间,还是日出王、贤明与觉醒之间,阶级的差别被抹去,他们相互之间的辩论似乎演变成了高度纯粹化的学术交流。
作者在附篇二《论世风日下和人心不古》中失望地哀叹:“信义发生了灾荒,不义充满了人世。谁若有信义,让他分我一份。如果我能找到一位仁义的豪士,我将把他扛到肩头、举到头顶”。[2](P853)对此,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倾向理解为作者基于糟糕的社会现实才构想出了这样一套理想图景。如此义愤之辞难免陷入偏颇,理想需要高于现实,而这里则颇有过了度的嫌疑。
人生观思想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它的存在从来不能罔顾所处时代的历史环境及个人成长环境。但是,自古以来也从来没有人生观上的高低之分,虽然精英主义者喜欢操持这样的理论。从本质上来看,人在面对自己人生的时候都将因无法借助于他力而沦为彻底的无助者,但同时又是潜藏无限创造力和可能性的超人。因而,在人生观思想的“陈列室”里,时空的界限比起观点的差异要模糊得多,也就形成了每一种人生观思想都可以并立存在的形态。而在人类的发展图景上,人生观思想则表现为同一块土地上高低迥异又各个独立的山峰。
《福乐智慧》的人生观思想与其他经典相比,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对人生图景的高度理想化。这使得它变成了人生观大花园里的一朵奇葩,在今天依然可以为大家提供一种向往,即便存在上述所分析的不足。那么,在需要无限想象力的未来面前,对《福乐智慧》中所构想的人生模式持乐观心态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1]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2]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M].郝关中,张宏超,刘兵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I207.22
A
10.3969/j.issn.1003-4641.2017.06.14
李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