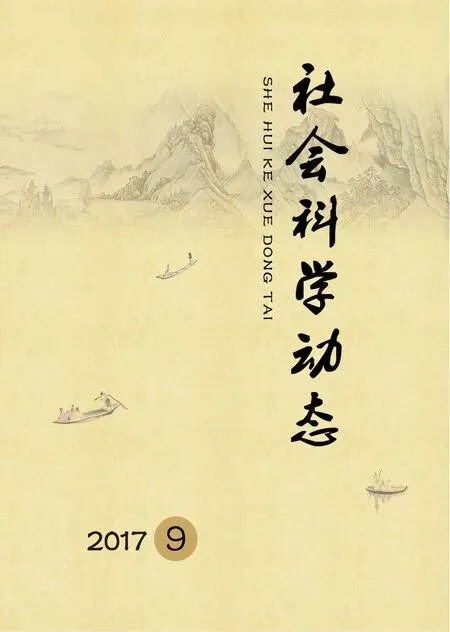谈谈关于董仲舒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桂钿
谈谈关于董仲舒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桂钿
哲学研究方法很多,首先要不迷信权威,不随众;其次,要全面掌握资料,对资料要作精当解读。要了解古人用语习惯,避免用西方观念误解和现代观念曲解古文;复次,要了解人物之间和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认识人物和事件的发展变化。总之,为了做到实事求是,需要运用唯物的和辩证的方法。
董仲舒;《春秋繁露》;独尊儒术;方法论
在多年对董仲舒的研究和阅读研究董仲舒的著作和文章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值得探讨的方法论问题。
一、事实求是地对待史料
《史记·儒林列传》的最后是董仲舒传,没有记载董仲舒生卒之年,需要研究者探讨。清代学者苏舆著有《春秋繁露义证》,有较高水平。因此,苏舆就被学界视为董仲舒研究权威。其书前有董子年表,将董子生年系于汉文帝元年,卒年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董子寿至75。这个权威结论在上个世纪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中广泛引用,许多论文也以此为定论。但是,班固说他“亲见四世”,从汉文帝到汉武帝只有三世(文、景、武),四世应上推至惠帝。这是简单的错误,因为收集资料不全,以致以讹传讹,错误流传多年,得不到纠正。
桓谭说董仲舒“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这句话对于确定董仲舒生年是极其重要的资料。“不窥园”发生在特殊时期,即董仲舒对策之前的准备阶段。按桓谭说法,“年至六十余”,约为61岁,3年埋头研究,对策时约为64岁。而对策时间,按班固《汉书》的说法在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上推64年,即公元前198年,高祖九年,那么,董仲舒在汉惠帝元年时才3岁,能不能说他也“见”了刘邦这一世呢?
董仲舒将《春秋》十二世分为三个阶段:“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孔子“见三世”是哀公、定公、昭公,从昭公元年到春秋结束,一共61年,孔子寿至73岁,有12年生活在昭公之前的襄公时代,为什么不能算又见了一世?大概汉人的习惯,小孩不知世事,不算见了世面。孔子12岁之前不算见了世面,董仲舒3岁之前也不能算见世面。桓谭说的“六十余”,即使从61扩大到65,也不会达到见世面的年龄。有的学者不愿意引用桓谭的说法,也不对“三年不窥园”的特殊时期作出探讨,甚至还将董子生于公元前179年这种低级错误当作一回事。而有的学者则断章取义以桓谭之说确定董仲舒“寿至六十多岁”。这都不是做学问的严谨态度。实事求是,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为了求真,要搜集全面的资料,进行联系、分析,作出有根据的合理的解释。不肯下苦功夫,只凭小聪明,是找不到真理的。
二、正确理解古文本意
这里就讲一个关于数字的用法。例如三字,有时就有多数的意思,如“再三”就不一定只有三次。董子说孔子“见三世”就是三世。但孔子说自己15岁开始知道学习,以后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为什么他都在整数的年龄才有一变化呢?怎么会那么凑巧呢?值得怀疑。古代还有“二十曰弱冠”,“七十悬车致仕”的说法,即20岁举行冠礼,70岁退休。从古代许多记载来看,不是一到70岁就退休的,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公孙弘一直到80岁才死于丞相任上。关于“二十曰弱冠”,班固对自己23岁、27岁,都称为“弱冠”,如说“弱冠而孤”,其父死时,他23岁成为孤儿。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说,从20至29通称弱冠。大概唐代就有人以为20就是整20,所以他才会给予明确纠正。
三、对古代范畴要具体分析
董仲舒讲天有十端,包括天、地、阴、阳、金、木、水、火、土、人。前一个天,代表整个宇宙,后一个天,只是与地对应的天,包含日月星辰。在一句话中的两个“天”,内涵与外延均不相同。汉代有“天有五号”说,也是从不同意义上讲天。汉代还有科学研究的物质的天,比如盖天说的如车盖的天,浑天说的如鸡蛋壳的天。董仲舒讲天基本上没有涉及这类天。
董仲舒讲天人感应,从来没说天有什么具体形象。天也不说话,只是会赏善罚恶,会用自然现象来表达意愿,表明好恶。自然灾害,就是天对当政者行为不当的谴告。当政者施行德治,就出现表明吉祥的瑞物,这是天的高兴的表达。有的人说,董仲舒讲天人感应是为了欺骗老百姓,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服务。而事实上董仲舒在对策中首先提出天人感应,是由于汉武帝在策问中问到这个问题。董仲舒借此提出上天赏善罚恶,意思是只要坚持行善,就不必担心,主动权在于自己。这是从政治上考虑,让汉武帝有敬畏之心,不像秦王那样无法无天,无所畏惧,折腾人民,导致国破家亡。汉武帝明确表示,对策只有自己一个人看,“朕将亲览焉”,其他官员都看不到,百姓更无从知晓。如果说欺骗,那只骗汉武帝一人。欺骗人民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四、如何理解和评价形而上学?
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天这个概念很复杂,其中有一意义是指整个宇宙。道也是复杂概念,有一意义相当于现代所谓规律。宇宙是不变的,规律也是不变的。如果这样理解,这句话并无不妥。
关于形而上学。形而下是具体事物,如一块石头、一棵树,都是变化着的。形而上即抽象的东西,如好与坏、善与恶、一加二等于三,两条平行线不相交等。这些都是不变的,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正确的。天与道如果在抽象的意义上说,认为是不变的,也是无可厚非的。西汉时代,董仲舒的辩证法思想是很丰富的,相当杰出的,因为说一句天不变的话就定为形而上学,并且将形而上学列入错误范畴,实在不妥。
五、何谓先进文化代表?
多年来,经常讲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但许多人并不了解其中真谛,只是当作口号、口头禅加以引用。一种社会制度适合当时当地的社会实际,又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先进制度,创立这种制度的阶级,就是先进阶级,即先进生产力代表。为这种制度,为这个阶级服务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代表。
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地主阶级创造了封建制度,与奴隶制度相比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在封建制度下,农民与地主是被统治与统治的矛盾关系,这个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封建社会初期、前期,统一大于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的成分更多一些。在地主阶级衰落以后,统一性逐渐减少,对立性逐渐增加。农民起来要推翻地主政权时,农民视地主为敌对阶级。共产党革命之初,也表达了这种感情,认为与地主的对立、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之后在理论上讲到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时,连相对的统一也不讲了,而且将地主阶级归入从来就是本质上坏透了的一群人。这种说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几乎成了社会共识。于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封建地主就是反动阶级。西汉当政者就是这种阶级,董仲舒学说就是为这种阶级服务的,因此就成了反动思想家。但是,如果按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西汉时代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制度,当时整个欧洲还都处在奴隶制社会。董学为这样的制度服务,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没有历史观念,一切以现代为标准,对历史都作出否定的评价,这就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发展而来的。中国悠久历史没有中断过,积累了丰富的人生智慧,特别是政治智慧。中国这么大,人口众多,民族复杂,能维持统一大国的局面,这正是政治智慧的体现。而欧洲只有五亿人口,却分成几十个国家,统一不起来。欧洲的封建社会只维持了几百年就崩溃了,中国则维持了数千年,这也是中国政治智慧的高明之处。这一切都有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家的贡献。董仲舒就是其中杰出者。他提出大一统论、天人感应说、独尊儒术、调均思想都对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六、关于独尊儒术
董仲舒没有说过“独尊儒术”这句话,但在《举贤良对策》的最后确实讲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即除了孔子之术都要罢黜,勿使并进。这里当然包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思,因此后代学者称董子有此建议,并非没有根据。但是,这个问题最为复杂,需要较大篇幅进行讨论。
20世纪,有些学者对此提出各种不同见解。有的说这种理论太偏激,只要儒家,消灭其他各家。实际上,这种理解不合原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独尊”并非仅存,“罢黜”亦非消灭。“独尊儒术”之前,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列六家有名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儒家和道家。各家都有合理成分,也都有不足之处,只有道家综合各家长处,又能应变,所以没有不足之处。说明汉初“独尊”道家。经过一百多年“独尊儒术”以后,到班固撰写《汉书·艺文志》时,“罢黜”了一百多年的名家、墨家、阴阳家、法家、道家都存在,一个不少,还增加许多家,如纵横家、农家、兵家、医方家、杂家、小说家、天文、方技等等。所以可以肯定的是,独尊儒术并不消灭其他学派。事实上,儒术独尊了两千多年,这许多家都存在,而且有很大的发展。任继愈先生曾告诉我:“独尊实在太高明了!”我完全同意他的评价。独尊儒术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各派学说各有优劣,但不是平等的,有高低之分,有尊卑之别。水平虽低,只要有合理性,就不会被消灭,因为社会需要它。例如在用人上,汉武帝不是只用儒家,也用一两个道家、纵横家。虽然多为儒家就是独尊的表现但将“独尊”作绝对化理解是不适当的。
又有学者根据汉宣帝一句话,即汉成立以来,一直实行“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认为汉从刘邦以来,当然包括汉武帝时代都既有儒家的王道,也有法家的霸道,说明并非“独尊儒术”。然而事实上所谓儒法对立,是文革中讲儒法斗争的遗迹。在春秋战国时代,百家殊方,儒法当然也有争鸣,但他们并非势不两立、绝对互斥的。管仲、子产都是著名的法家。《论语》记载了孔子对管仲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左传》中记载子产,孔子说别人再说子产不好,我都不相信。子产认为治国理政要从严,孔子也从中得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的体会,还称子产是“古之遗爱”。儒家还认为“圣人不能无法以治国”。孟子明确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只有善良意志做政治是不够的;只有法,它不能自己去施行,必须有人去施行。这人道德不好,就会贪赃枉法。这说明法律与道德都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因此,董仲舒认为德教为主,刑罚为辅才是最合适的。荀子认为,治国最高是王道,其次是霸道。说明霸道不是法家的专利,儒家在一些情况下,做不到王道,可以求其次,行霸道。
《史记》分纪、世家、传三级,天子上本纪,诸侯属世家,其它官员入列传。孔子不是诸侯,却有《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入《列传》,孔子后学还有一个专门的《儒林列传》,只有儒家有此特殊情况,老子没有入世家,墨子弟子没有列传,也没《道林列传》 《墨林列传》。如果不是独尊儒术,司马迁就不会这样处理了。
七、关于董仲舒的历史地位
董仲舒在西汉有特殊地位。班固说他“为群儒首”,“为儒者宗”。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汉武帝经过董仲舒墓前,下马步行,那里后世称为“下马陵”。可见汉武帝对于董仲舒的尊崇。
有人根据董仲舒对策以后,汉武帝留公孙弘在身边,直至80岁死于任上,而没有留董仲舒在身边,反使其远离京师,任江都相,后又任胶西相,认为董子没有像公孙弘那样得到汉武帝的亲近。但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先是遭主父偃陷害,董子入狱得到汉武帝赦免;退休后汉武帝又派人请教祭祀的事;最后,又有下马陵之传说。相比之下,公孙弘当时很红,成为士人楷模,死以后影响却不及董子。这是什么原因呢?值得探讨。
公孙弘在朝廷上很适应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当皇帝遇到难题,召集群臣议论时,公孙弘总是会想出几种对策,又能详细分析各种方案的利与弊,由皇帝权衡选择。汉武帝对这样的大臣很感兴趣,留在身边,好相处。公孙弘也因此得到宠幸,受到封侯,成为士大夫的楷模。董仲舒则不同,发表的言论,都是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不照办就违反儒道,让皇帝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董仲舒在身边,皇帝有不自由、不自在的感觉,因而还是“敬而远之”好些。两人作风不同,而有生前荣耀和死后流芳的差别。
还有人提出,董仲舒没有参加对策,理由是《史记》没有记载,《汉书》中所记,都是班固编的。如果对策不存在,当然,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和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也就成为子虚乌有了。有人就将“独尊儒术”的时间往后推迟几十年。于是,文、景、武时代的盛世就与儒学无关。汉元帝才开始“独尊儒术”,而西汉开始走向衰败。这样一来,儒学在盛世无功,衰世有罪的结论就可以成立了,批孔批儒就可以理直气壮了。
沙滩虽然可以建起高塔,但不稳固。历史问题即使有严密的推论,作为根据的史料如果不确实,就不可能有稳固的结论。关于董仲舒的资料,在《史记》中只有《儒林列传》的最后,记了数百字。而在《汉书》中则单独立传,纠正了董仲舒弟子名字的错误,抄录了正确的内容,最大差别是全文录入了汉武帝三个策问与董仲舒的三个对策,使董仲舒传从数百字扩大为数千字。如果董仲舒对策是班固编的,那么,汉武帝的策问也是编的。但班固曾因私撰史书差点杀头,他怎么敢胡编汉武帝的策问?中国写史,特别重视真实性,尤其有关皇帝的史实,怎敢乱写?司马迁对董仲舒思想的认识受到时代的局限,只知道他对《春秋》的解读最高明。而经过一百多年的考验,董学的影响巨大。因此,班固将三策全文录入《汉书》。当时也存在厚古薄今的问题,对司马迁来说,董子为同时代的今人,对班固来说,董子已是一百多年前的古人。在其弟子、后学的努力下,董子影响日增。在《盐铁论》中,在许慎《说文解字》中,在谶纬中都出现董仲舒的名字,都能说明问题。“为群儒首”、“为儒者宗”正确反映了他的社会影响。
八、关于董仲舒著作的真伪
在疑古盛行的时代,似乎怀疑一本古籍的真实性就是重大学术成果。至今还盛行的伪古文尚书,伪《列子》就是显例。疑古风也刮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理由很简单,汉代并没有《春秋繁露》这本书名。在《汉书·艺文志》中只有《董仲舒书》。同样情况,汉代没有司马迁《史记》这本书名,(有一《史记》是鲁国史书,是孔子写《春秋》的底本,也叫未改《春秋》。) 只有《太史公书》。如果不能否定《史记》是司马迁的著作,当然也不好否定《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著作。
《史记》称董仲舒重点研究《春秋》,《汉书》列董仲舒著作的篇名有《蕃露》 《玉杯》 《闻举》《清明》 《竹林》等。可能有这种情况:全书解说《春秋》之得失,因以《春秋》为篇名,第一篇为《蕃露》,后人以为书名为《春秋蕃露》,这样第一篇有内容无篇名,就取篇首“楚庄王”为篇名。这只是假设,未成定论,不敢径改。
有人提出《春秋繁露》中有九篇题“五行”的篇目,后七篇与前二篇思想不一致,因此认为后七篇是后人伪造的。前二篇与后七篇为什么不联在一起,可能由于写作的时间有前后不同,而且相隔较久。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因为相隔时间长,思想有了变化,文字不那么一致,就是很自然的事。以前有一些学者对一些古籍发现不一致现象,就以为有假,结果多有误判。如胡适读《论衡》就有这类误判。古代许多人一辈子只写一本书,几十年中思想会有许多变化,各种说法可能与当时语境还有关系,怎么能完全一致?
我以为,对于古籍要特别尊重,没有充分的根据,轻易不能改动,对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我认为都是可信的研究资料,采取怀疑、改动,都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责任编辑 胡 静)
B234.5
A
1003-854X(2017)09-0021-04
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