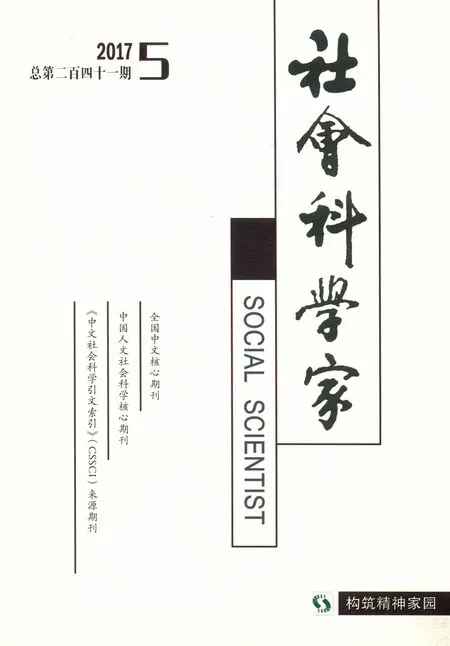春秋时期的本末认知与话语
李晓东,陈廷湘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春秋时期的本末认知与话语
李晓东,陈廷湘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论者假定华夏族的“本末”认知观念源于自然植物界的客观存在物“树木”;“本末”认知作为一种人与植物的类比认识,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即周时的“本枝”论;春秋时期“本末”成为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公共话语,这些话语得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模仿、回应及传承;可以从“本末”的语义,“本末”话语的表述方式,“本末”话语的作用三个层面去理解春秋时期的本末认知;“本末”认知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春秋;本末;认知;话语;表达
关于“本末”,现代汉语中有两种常见或习惯性的表达方式:一种谓某人、某人的行为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另一种谓某种措施、某种方法是“治标不治本”,而应“标本兼治”。这两种方式都代表说话者的某种看法或判断,并力求使之具有说服力。众所周知,这些成语不是在今天才开始使用的,而是自古代汉语传承和沿袭下来的。如果要考察这类成语、说法及其背后的思维模式,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时代。
一、“本末”认知述源
1.由“木”而“本”的逻辑认知
作为宇宙、自然的产物,人类为了生存及延续,是离不开植物界的。树木即是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而不可或缺的植物品类,尤其在农业尚难称发达的古代时期,更是如此。树木为古人的衣、食、住、行、娱等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同样也为古人的群体组织和群体行为提供物质保障,例如农业、手工业的木制工具,战争行为的兵器等。在考古学或线性史观中,常见“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发展分期,但似乎对“木器”和“木器时代”的关注就少得多。
对树木的广泛应用,同样也会映射到人类的认知当中。就华夏族而言,远在商周时期,知识阶层就已认识到树木和人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如箕子的“五行”说,将“木”列为“五行”中的第三位: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木曰曲直……曲直作酸……①《尚书·周书·洪范》,屈万里著:《尚书今注今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页。
合理的推测是,华夏族“本末”的认知观念源于自然植物界的客观存在物——“树木”。这种认知是通过将树木解构细分为树根、树干、树梢、树枝和树叶等组成部分并且应用于日常生活中而实现的,然后继续向社会生活领域延伸,进入精神和观念的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本末”的辨析中还包含或体现论者所认同或看重的价值观。
2“.本末”认知的先声:《诗经》中的“本枝”论
“本末”认知很早就在先秦的文献中表现出来,这就是《诗经》中的“本枝”论:“文王孙子,本支百世。”①《诗·大雅·文王》,王秀梅译注:《诗经》,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77页。
作为树木的一部分,“本支”和周王朝的宗族、国家认知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先秦社会中的一种“人与植物的类比认识”②(日)高木智见著,何晓毅译:《先秦社会与思想——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4页。。这里“本”指代周王室的嫡系亲族,“支”同“枝”,指代周王室的旁系亲族,“本枝”一起构成周王朝的统治支柱。为使周王室能够长久存续,就要注意避免重蹈商朝灭亡的覆辙:“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③《诗经》,第672页。
王室家族是“本枝”在国家层面上的意义,“本枝”后来也可以指宗法社会中个人及其所依附的家族背景。例如,孔子即认为人“身”是属于“亲”(宗族)的分“枝”,是应当礼“敬”的。如果不“敬”,就意味着对宗族的伤害,即是伤害到“本”了,而伤害“本”的直接后果,就是作为“身”的“枝”转而无所依托,亦随之而亡。④《礼记·哀公问》,《十三经注疏》,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847-848页。
“本支百世”简称则为“世本”,著录黄帝至春秋各统治者家族世系的古书亦名《世本》。周时的“本枝”及“世本”认知,作为象征上层精英统治者的观念,也被后世所沿用及传承。在春秋战国时代,只要成为国家的最高主宰者“国君”,就可以称为“本”;秦、汉以后,这种观念同样也被史籍所采用,如《史记》中记载帝王一系的体例为“本纪”,而次一级的公侯则为“世家”。
二、春秋时期的“本末”公共话语:各本其所本的话语现象
春秋时期的知识阶层及精英阶层普遍使用“本末”话语,这一时期的主要文献《左传》、《国语》之中,关于“本末”的言说即比比皆是。可以说,“谈本论末”是春秋时代的一种论说风气,也是当时思想世界的一个特点。这种风气也直接影响了战国时代的“本末”表达。
“本”、“末”本身的语义简单明了,它总是和论者的某种观点或看法密不可分,核心的功能是论者用以组织和阐释论点或论题的一种形式逻辑。对当时的论者来说,他们通过“本末”这种表述方式去凸显所坚持的观念,旨在强调其重要性。下面即以《左传》、《国语》、《老子》以及早期儒家为中心,来考察这一时代的“本末”话语。
(一)《左传》、《国语》中的本末话语及其回响
《左传》、《国语》中,与“本末”结合到一起的论题或主旨主要是“国之本末”、“周礼为本”、“治乱之本”、“忠信为本”、“义利之本”、“孝本与务本”、“不背本”。这些相同主题的“本末”话语在战国时代继续受到知识阶层及精英阶层的模仿及回应,从而使这种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得以传承和延续。
1.国之本末
《左传》的“国之本末”论,作为一种国家观念,沿袭自周朝的“本枝”论。对春秋时代的各个诸侯国而言,“本”、“末”自有其专属含义:前者指各诸侯国的国君,后者则指国君的同姓亲族(“枝”)或者异姓地方实力大族,双方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状态。
桓公二年载晋国公族的势力已凌驾于公室之上,其关键在于晋国公族未能把握“本大末小”的原则:“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⑤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3-95页。在桓公十六年记述卫国国君继承权政争之后,著者从“本”、“枝”、“末”三者的关系出发,又总结道: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后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谋;知本之不枝,弗强。诗云:“本枝百世。”⑥《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68-169页。
在《左传》的著者看来,国家的权力格局固然要注意“本大末小”,但更重要的在于“本末”或“本枝”内部之间的合作,所谓“本有保则必固”⑦左丘明撰,韦昭注:《国语·周语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文公七年的记载,以“枝叶”对“本根”的“庇荫”喻义再次强调公族对公室本具有的辅助作用:宋昭公想去“群公子”,乐豫建言“不可”,因为他认为“公族”是“公室之枝叶”,如果除去,公室就缺少了强大的政治支持力量,“本根无所庇荫矣”。
《左传》极大关注国之“本末”问题,目的就是提供历史经验,借鉴历史教训,传播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期待各诸侯国防止“本小末大”及“末大折本”,稳定政局。这一立场可从昭公十一年的一段记载清楚地显示出来:(楚)王曰:“国有大城,何如?”申无宇对曰:“……若由是观之,则害於国。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然而春秋诸侯国的政治发展趋势却是“本末”的对抗渐渐超过“本枝”的联合。到了战国晚期,政治学者韩非子则彻底抛弃了“本枝”辅助论,而提倡“披枝”论,认为国君要将家族血缘关系与政治权力相分离,强化国君的中央集权:“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不胜春风,枝将害心。公子既众,宗室忧唫。止之之道,数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数披,党与乃离。掘其根本,木乃不神。”①《韩非子·扬权》,张觉撰:《韩非子校疏析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740页。
2.周礼为本
春秋时期东周虽为各诸侯国名义上的共主,但列国间仍具有“周礼为本”的共识。闵公元年仲孙湫就是否兼并鲁国向齐桓公提出建议,显示了这种意识形态强大的惯性力量:“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②《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257页。
“周礼”既是规范共主与各诸侯国的亲疏与等级制度,又代表中原文化上的认同,也是区分夷、夏的标准。尽管周礼仍然在春秋列国间维持其基本的文化习俗与惯例的认同地位,但是周礼繁复的“仪式感”已逐渐衰落,而其在治理国政、凝聚民心上的实际效用则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就是鲁昭公时晋国的女叔齐所强调的“礼仪本末”的实用观念。从鲁闵公迄鲁昭公,已历经五代,对“礼”的认知由“周礼为本”变迁到了“礼之本末”,这也是诸侯国追求民多地广的国家实力使然。对“礼”“尚质”而不再“尚文”,这一点在早期儒家那里也得到了共鸣。他们探讨了“礼”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同样也不看重“礼”的形式:林放向孔子请教“礼之本”,孔子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③《论语·八佾》,(梁)皇侃撰:《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1-52页。而“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④《礼记·乐记》,第679-680页。
至春秋晚期,长江流域新的强权吴国崛起,黄河流域“周礼为本”的意识形态遭到了“弃天背本”的空前挑战。哀公七年载吴国致力于扩张,争夺中原霸权,在强索宋国后,再度向鲁国要求“百牢”。鲁国的大夫子服景伯认为吴国的举动多行不义“将亡”,因为“弃周礼”是“弃天背本”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礼”的正义性。春秋时的儒家也秉持同样的认知,如孔子认为“礼”的正义性是“本于天”,即源于天的:“是故夫礼必本于天”⑤《礼记·礼运》,第404、429页。。孔子不止一次,反复申说“礼从天出”(孔颖达正义),把“礼”看作是天赋的。“天”或“太一”是“礼”的本原或根本,因而就具有了某种不容置疑的正当性。这是儒家对“礼”的起源及合法性的最高或终极的解释。
战国时的荀子同样重“礼”。他认为“礼”有“天地、先祖、君师”三个本原,其中“天地”是生命的本原,“先祖”是人类的本原,“君师”是治理国家和人民的本原。“天地先祖君师”的“起始”意义是荀子所珍视的,他推崇“礼”的意义在于要凭借它来“别贵始”,于是“礼本”论便发展为“贵始”的“德本”论:“贵始,得(德)之本也”。⑥《荀子·礼论》,(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40页。那么“礼”还有哪些政治上的功能呢?荀子认为“礼”是“强国”的根本。基于此,相对地,他认为战争是不重要的“末事”。⑦《荀子·议兵》,第265、275页。将战争看作“末事”的认知,荀子很可能是受到春秋晚期越国大夫范蠡的启发:“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⑧《国语·越语下》,第423页。就战争和军事本身而言,战国的兵家也探讨了“兵之本”,其观点像是范蠡和荀子的反论:“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⑨《吕氏春秋·决胜》,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陈涛注译:《吕氏春秋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页。
3.治乱之本
春秋时期诸侯政权的更迭、国家的兴亡,引起了《左传》、《国语》的强烈关注,并试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境下探究其原因,这就是“乱本”、“祸本”和“亡本”论。
《左传》、《国语》从四个层面来关注春秋时代的治乱之本:
(1)国君或主政者的执政得失
桓公十八年:初,子仪(王子克)有宠于桓王,桓王属诸周公。辛伯谏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在政治上,妻妾、嫡庶、正副、都城应各安本位,各守本分,否则内乱必生。其中的“匹嫡”即指违反周以来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普遍为当时的精英阶层所反对:晏子曰:“不可。夫以贱匹贵,国之害也。置大立少,乱之本也……少长无等,宗孽无别,是设贼树奸之本也……”①张纯一撰:《晏子春秋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8-29页。
《国语·晋语一》史苏从国君夫人干政的角度来探讨“乱之本”:史苏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乱本生矣!……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灭祸不自其基,必复乱。……”骊姬果作难,杀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难本矣。”
(2)君臣之间严格的等级制度攸关治乱
《国语·齐语》中管仲认为“为君不君,为臣不臣”,是“乱之本也。”②《国语·齐语》,第161页。尽管由于政治实力的对比,周天子与诸侯盟主之间的等级制度已有所动摇,但维护严格的君臣等级制仍是列国间的共识。如果君臣等级关系破裂,必将引起严重的政治内乱。成公十六年晋与楚、郑鄢陵之战后,卻至居功自傲,单襄公认为卻至的行为会招来政敌或国君的怨恨,而“怨之所聚,乱之本也。”③《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894-895页。“卻氏家族,有三位卿、五位大夫”,号为“八卻”,“族大”逼君的权势,使晋厉公深感威胁,第二年“三卻”等即被晋厉公所杀。
战国时《韩非子》引述了《左传》襄公七年的一段史事,作为君臣之义的负面典型:穆叔曰:“孙子必亡。为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管子·明法解》也说:“故上下无分,君臣共道,乱之本也。”
(3)晋、楚竞争诸侯盟主的结果
晋与楚、郑鄢陵之战前,晋卿范文子的政治、军事意志都不强烈,本不愿意进行这场战争,这显示了晋国霸权的逐渐衰落:“若以吾意,诸侯皆叛,则晋可为也。唯有诸侯,故扰扰焉。凡诸侯,难之本也。”④《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952-953页。范文子认为晋、楚长期对立,反复争夺中、小国的附属是战乱的一大主因。
(4)民间社会舆论与祸乱
《左传》襄公十七年的一段叙述,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的统治阶层对民间社会舆论的看法。宋国的皇国父为大宰,为宋平公筑台,因为征用民役,妨碍了农收。子罕为民请命,向宋平公建议等“农功”完毕之后再去筑台,但平公不许,于是筑者舆论峰起,责皇国父而誉子罕。但这种议论引起了子罕的担忧,他亲自执罚鞭打筑台者,于是议论就停止了。有人问子罕这么做的原因,子罕认为小小的宋国,如果“有诅有祝”,实乃“祸之本也”。⑤《管子·明法解》,颜昌峣著:《管子校释》,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18页。联系到子产不毁乡校,这时的民间社会舆论处于“他者”的地位,都在精英阶层的话语支配与定义之下。
战国晚期的韩非子十分注重探究春秋时期的治乱经验,他从文官制度的角度提出见解:“赏繁,乱之本也”;“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⑥《韩非子·心度》,第1196页。等等。《庄子》书中从历史思辨的角度,针对儒家学说理想目标与现实人性相违背的缺陷,提出另一种深具洞察力的“大乱之本”的观点:“吾语汝: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⑦《韩非子·有度》,第72页。
反过来说,有“乱之本”则亦应有“治之本”。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商君书·错法》说“臣闻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举事而材自练,赏行而兵强。此三者,治之本也。”⑧《庄子·庚桑楚》,刘文典撰:《庄子补正》下,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28页。《管子·立政》认为“治国有三本……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劳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⑨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3页。等等。
4.忠信为本
“忠信为本”既是对国君人格上的要求,也是对国君所代表的国家的要求,认为各诸侯国在交往时,需要讲求“忠信”这种道义,而不是一味迷信武力。
《国语·晋语二》载宫之奇认为“忠信”是国家建立和巩固的条件之一,如果违背,则“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这种理念又为叔向所继承,认为诸侯国的盟主,无论晋国还是楚国,都应遵循这样的准则:“忠自中,而信自身,其为德也深矣,其为本也固矣”。这种“固本”的认知为墨子所吸收,具体所指则为农业:“固本而用财,则财足。”①《国语·晋语二》,第308页。
然而在春秋各国致力于兼并的政治现实下,“忠信为本”的道德约束毕竟难以发挥太大的作用;随着战争兼并的加剧,道德约束与国家行为就越来越相分离。
5.义利之本
中国传统上“义利之辨”的话语源于春秋时期晋国的里克:“夫义者,利之足也;贪者,怨之本。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②《墨子·七患》,王焕镳撰:《墨子集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僖公二十七年晋国准备与楚国进行城濮之战,三军主帅的人选上,讲求德、义的卻縠得到认可:“卻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③《国语·晋语二》,第199页。晏子则注意到“利”是人的本性,“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所以“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认为应以正义作为规范利益的前提,防止争利失序。《逸周书》也说“故必以德为本,以义为术”。
然而在儒家一些人看来,“德”、“利”是对立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④黄怀信:《逸周校补注释·柔武解》,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131页。荀子同样不太重视“利”,而推崇“义”与“忠信”,视其为“大本”:“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⑤《礼记·大学》,第993页。
战国晚期同样倡“义本”之说,但认为“义”是一种极高的要求及标准:“故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⑥《荀子·强国》,第298-299页。
6.孝本与务本
如不先入为主地考虑儒家的“孝”观念,就会发现春秋时期“孝”与宗教“神”是紧密相关的。晋周在周与单襄公共事,只要谈到“孝”一定就会提及“神”,于是单襄公认为应:“必善晋周,将得晋国。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孝,文之本也;……昭神能孝……”⑦《国语·周语下》,第61页。在单襄公看来,“孝”是一种虔诚的从事宗教活动的行为和心理状态,“文”代表某种人格精神力量,这种意义上的“孝”才能成为“文”的前提或基础⑧韦昭注引《孝经》云“言人始于事亲”,以“孝”后来的意义误解“孝”的早先意义。。孔子以后,经过儒家对“孝”的重新解释或定义,“孝”宗教上的话语意义逐渐淡化,最后仅仅意味着对父母和君王的绝对的“孝忠”。
《孝经》中孔子认为“孝”是“德”的前提,是“教”产生的基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⑨《孝经·开宗明义章》,《十三经注疏》,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2页。孔子弟子曾参对“孝”异乎寻常地狂热,他力图将“孝”的观念绝对化、普世化:“众之本教曰孝”,“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诗》云:‘自西向东,自南向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⑩《礼记·祭义》,第818-819页。曾子认为“孝”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成为一种永恒的宇宙精神。更进一步“,孝”有没有自身的“本”呢?他认为是“忠”“:忠者,其孝之本与!”11《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大戴礼记》,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147页。
孔子弟子有子在探讨“孝本”的基础上提出了“务本”观:有子认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2《论语义疏》,第5-6页。秦国编写的《吕氏春秋·孝行》篇中,从儒家“孝”的角度出发,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务本后末”观:“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
7.不背本
《左传》和《国语》都推崇“不背本”,这种观念显然是由华夏族的“祖先崇拜”而来,成为一种普遍受到赞誉的宗族道德精神。例如《左传》中的“楚囚”①《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845页。,《国语》中的晋周②《国语·周语下》,第62页。,都因为“不背本”的行为而获得当时精英阶层主流价值观的肯定。
这里“本”有两层意义,一层代表其家族先人,一层代表其母国,体现了一种双重认同:个人的宗族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两层意义和认同时常是混合在一起的。“不背本”在儒家那里,也称为“不忘本”:“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③《礼记·檀弓上》,第115页。《礼记·乐记》也说“礼,反其所自始”。可见“礼”本身就蕴含着“不忘本”的意义,即“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也”。④《礼记·礼器》,第455页。如果将“不忘本”替换成肯定句式,就是前述荀子所推崇的“贵始”。然而“不忘本”既非天生,又非人所共有,这就需要采取某种方法来培养或引导,如“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⑤《礼记·乡饮酒义》,第1014页。在“不忘本”基础上,还应进一步采取体现“报本反始”的祭祀行为:“社,所以神地之道也……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示本也……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而“大报本反始”则是国家最高的祭祀行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⑥《礼记·郊特牲》,第479、488页。这些不同层次、等级分明的祭祀的意义在于:“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⑦《礼记·祭义》,第812页。
(二)《老子》的“根”、“本”观及其回响
《左传》、《国语》中“本根”常常并称连用,如《左传》隐公六年周任建言及《国语·晋语八》阳毕建议平公灭栾氏,意指“本根”的连带喻义(连本带根),而非区分二者的差别。那么在《老子》中,“本”、“根”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呢?
《老子》中关于“本”的讨论极为罕见,仅有唯一的一条:“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榖,此非以贱为本耶,非乎?”⑧《老子》第三十九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8页。《老子》中的“根”论要远比“本”论多得多。老子所言的“根”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根源意义,如“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一种是根基意义,如“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相较于春秋时代的论者留心于“本”,老子则更为关注“根”。老子所着重的是“根”、“本”原始意义上的区别,即根源(本原)与基本的区别。战国时韩非子精细地探讨了老子所说的“根”的本意:“树本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
继承了老子哲学思想的庄子,对“本”、“根”的意义同样是明确区分的:《应帝王》中有一寓言式的人物名为“天根”;《大宗师》云“夫道……自本自根”。庄子和老子一样,也将“道”看作世界的本原或本体,认为“道”产生了宇宙和自然的一切。但庄子的问题意识在于,“道”本身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老子对这个问题存而不论,并没有提出清楚的说明。庄子则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道”是“自本自根”的母体:它自己产生了自己(自根),同时还要维持自身的存在(自本)。
春秋以来各家各派的论者都提出了本末论,并且从未怀疑过各自本末观的绝对真理性;而战国的庄子一方面除了继续使用这种本末话语,另一方面却对本末话语本身的绝对性产生了怀疑,从而把思考的角度转向了本末认知本身。《庄子》外篇《知北游》说:“彼为本末非本末”。在他看来,各家各派各本其所本,只是表达了不同的立场,在其自身所属的传承系统内或许不会受到质疑或挑战,然而一旦超出各家各派的论域,那么就没有任何一家比另一家更有本末话语上的特权,即己方的本末论是唯一正确的。
三、结语
以上对春秋时代整个“本末论”的面貌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审视,那么本末话语的意义何在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诠释春秋时代的“本末”话语。①此节部分解释参考了笔者硕士毕业论文《春秋战国的本末论研究》(2007年)。
1.“本末”的语义。“本”本来是“树根”的意思②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卷三,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3页。,但后来“本”、“根”的意义就各自分开了,至少在《诗经》里面,“本”就已指“树干”了。《说文解字》以“木”作为区分本、末、根的参照:“木下曰本”③(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437页。,“木上曰末”④《说文解字注》,第438页。;而“柢”、“根”、“株”的意义完全一样,都是“木根也”。“标”与“末”同义:“木杪末也。从木,票声。”段注:杪末,谓末之细者也。古谓木末曰本标,如《素问》有《标本病传论》是也。亦作“本剽”,如《庄子》云“有长而无本剽者”是也……《逸周书》中已有“标本”论:非本非标,非微非辉。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呜呼,敬之哉!倍本者槁。
2.“本末”话语的表述形式。春秋时的“本末”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仅仅表述“本”的,另一种是同时表述“本”与“末”的,这两种表述各有其特点。
在仅仅表述“本”的情况下,其语境意义大致有四种:
(1)某种决定性或基础性的力量。例如《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⑤《逸周书校补注译·文儆解》,第118-119页。;再如体现春秋“民本”观念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⑥《礼记·中庸》,第878页。。“本”与“源”、“基”在这个意义上是相通的,如前引史苏论骊姬乱晋。
(2)充当某种前提条件或先决条件。例如“昏礼者,礼之本也。”⑦《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第118页。
(3)事物产生的根源,或者事物的本质、本原,即哲学上的“本体”论。例如老庄以“道”作为世界的本原;曾子认为“神灵者,品物之本也”。⑧《礼记·昏义》,第1004页。
(4)历史事实变动的因果律。如前述的“治乱之本”。
在同时表述“本”与“末”的时候,其语境意义有两种:一种显示相互对立的意味儿,一种显示相互统合的意味儿。前者重在区分价值上的重要与不重要,判定和分析是否存在“舍本逐末”或者“本末倒置”的情形,提倡“知本”或“务本”,从而明确达到“正本清源”的方法或途径。后者则将重要与不重要都视为整体的构成要素,强调的是一体化。当“本末”与《诗经》中的“终始”⑨《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第150页。观念结合,就形成了“本末终始”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⑩见《诗·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王阳明的解释即着眼其统合意义“:夫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谓之本末。”11《礼记·大学》,第987页。
3“.本末”话语的作用。如果综观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史,就会发现其中一个极其鲜明的“本末”特质:春秋时期的“礼本”思想、“德本”思想“、义本”思想“、民本”思想等,战国时期的“农本工商末”思想“、法本”思想等,以及古医学上的“标本兼治”论,都是通过紧密结合“本末”形式来表达的。如果缺少了这种“本末”特质的承载,春秋战国的思想史无疑就将大为逊色。12《大学问》,《王阳明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360页。
春秋时代的论者,借助于“本末”的比喻、隐喻、转喻、讽喻,用来说明事理,参与论辩,表达立场,影响他人,从而形成了层出不穷、各“本其所本”的话语现象。这种现象引起了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注意而竞相模仿,塑造了诸子百家的“本末”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式最终成为中国人的一种认知方式。
[1](汉)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
[2]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学林出版社,1984.
[3]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杨宽.战国史(增订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许倬云.历史分光镜[M].中华书局,2015.
[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8]马伯煌.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9](英)葛汉瑞.论道者[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美)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校:阳玉平]
G05
A
1002-3240(2017)05-0140-07
2016-12-11
李晓东(1975-),四川乐山夹江县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陈廷湘(1948-),四川彭州市人,四川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的思想与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