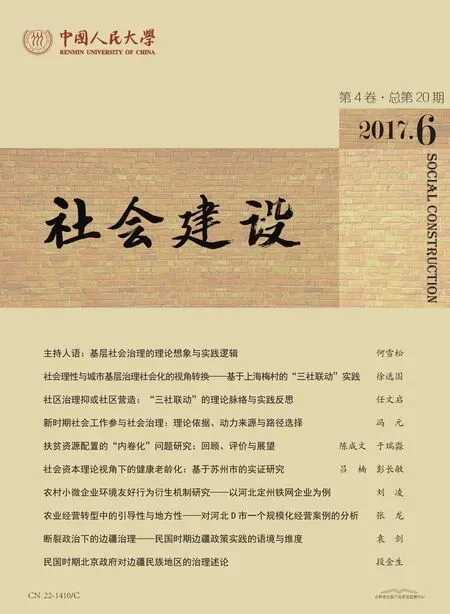断裂政治下的边疆治理①
——民国时期边疆政策实践的语境与维度
袁 剑
断裂政治下的边疆治理①
——民国时期边疆政策实践的语境与维度
袁 剑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地缘政治环境的分析,对影响民国边疆治理的几大重要因素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分析和梳理,认为民国时期的断裂政治、内外部几大力量的周期性影响以及战后五大国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民国边疆治理的执行力度。
断裂政治;边疆治理;民国时期;语境
一、时代感与中国语境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是世界格局深刻变动与调整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经历近代波折与动荡时代。在这一时期,一度看似无比稳固的欧洲大国权力均衡局面,随着德国的统一和崛起而逐渐走向崩解,而各大国在海外的殖民地扩张,也开始受到来自东方的日本以及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的制约;19世纪后期英俄在中亚的政治军事博弈最终奠定了当地后一个世纪的地缘政治生态,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则改变了东北亚的权力格局,从而在西部和东部两个方向塑造了当时中国的边疆格局。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原有的欧洲大国格局最终瓦解,奥匈帝国彻底崩溃,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相继在俄国爆发,曾经一度崛起的德意志帝国遭受重创,只有英、法两国苦苦维持局面,但其整体的殖民地格局已经岌岌可危。苏联的重新崛起以及日、美对一战后世界格局的深入介入开启了欧亚大陆尤其是东亚的新变局。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以英、俄、法为核心的围绕中国边疆而形成的殖民秩序,逐渐转变为以苏、日、英—法—美为主轴的新的中国边疆外部力量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并冲垮了世界殖民体系,经此一役,中国得以摆脱半殖民地地位,边疆危机基本消除,曾经长期承受的“国难”压力逐渐转变为战后大国体系下的定位与发展问题,原有的影响国家存亡的边疆危机也随之逐渐转型为与周边国家的不再具有全局性影响的边疆争议,其所蕴含的时代主题也从国家存亡问题转向区域发展问题。
民国政治也正是在这一世界性的转变格局中呈现出其自身的特征。在这个时期,在内外因素的交织影响下,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王朝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的转变,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在继承清朝疆域版图的基础上进入当时的世界舞台及其竞争格局当中,并力图在新的国家体制基础上进行国内建设与治理,正如陈旭麓先生在比较晚清民国的兴替时所指出的:“‘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民主革命的胜利,民国取代了帝国,使王朝的‘国歌’很快变成了王朝的挽歌。‘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压倒了‘帝国苍穹保’,显示了此时新声胜旧声。在这两种旋律的背后,是王朝时代的逝去和民主共和时代的到来。”①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312页。
这种“旧邦新造”的使命感,在两个方面形塑了民国在边疆认识与实践层面的总体语境,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民国处理和认知当时所面临的边疆危机以及更大的外部威胁时所凭依的基本理念。其一,“旧邦新造”所展现出的试图体现国家转型与政治重塑的道义感,在当时面对的以实力为主要原则的世界丛林秩序下,这种在国体转变中所凝聚的共同认同成为当时中国国家建设及其边疆治理层面的重要基础,也成为后来面对日本侵略而激发起全民族抗战热情以及推进边疆开发热潮的思想基础。其二,尽管限于当时的行政治理水平以及内部纷争,民国时期对于边疆地区的控制较为薄弱,但从大一统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从根本上塑造了一个新的共同体认知,那就是一个不再与“大清”相纠缠的“中国”认知,而这种认知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既继承了之前包括清朝在内的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与历史话语,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仰赖20世纪的行政与技术资源,进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认同与中国边疆认同的底色。在国家控制技术层面上,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作为‘政府’权力的监控的集中化过程,很大程度上仍只是(如果不全是的话)一种现代国家现象。只有现代国家,才能准确地使其行政管辖范围同具有明确边界的领土对应起来。凡是国家就都有地域范围的一面。然而,在民族—国家产生以前,国家机构的行政力量很少能与业已划定的疆界保持一致。而在民族—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年代,这种情况现实上已变得极为普遍。”②[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59页。从时间轴来看,可以说,清代从整体上奠定了当代中国的疆域版图基础,而民国则勾勒和塑造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属性与认同。
总体而言,随着近代中国在“边疆”概念与意识方面所出现的巨大转变,并与思想意识空间的扩展形成某种共鸣,进而在几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我们对于中国自身范畴的认识更加具体化了,开始清晰地意识到中国这一政治地理范畴是由实实在在的边疆所限定的,而不再是无边的“天下”。其次,对“边疆”的重新体认逐渐超越了纯粹的政治与地理意义,而开始以更为多元、多维的视角加以认知,并整体性地放弃了传统王朝朝贡体系的对外关系理念,而确立起更为现实的对外关系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于边疆区域及其治理的决策基础。③袁剑:《时局与话语:对近代以来国内关于“边疆”概念研究的分析与解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因此,以民族国家的新身份继承原有的疆域版图,并在此基础上意识到国家的有限性与边疆的局部性,这是我们在20世纪的地缘背景下全面理解民国边疆治理的关键所在。
二、民国边疆治理的整体特征
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它具有国家治理的一般性特征,而与此同时,由于边疆区域在国家结构内部所具有的特殊性,因此边疆治理本身在具体操作方面也具有自身的特色,与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治理有所差异。正如马大正、刘逖先生所指出的:“中国边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其不但有着较明显的自然特征,更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特点。”①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28页。历史、民族、区域以及政策的多层维度形塑了中国各个时期的边疆样态,到了近代,又进一步融入了外部帝国主义势力、地缘影响以及现实政治的诸多因素,从而呈现出民国边疆与边疆社会的独特样态。
不管是与之前的清朝,还是与之后的当代中国相比,民国的总体政治控制力偏弱,再加之周边地缘环境复杂,期间还面临日本入侵,因此,其国家治理本身出现阶段性和破碎化的特征,即便是所谓的“黄金十年”,也无法掩盖国家治理无法有效实施的困境,进而也无法在此基础上全面提升国家实力。国家治理本身的疲弱,反映到边疆区域的具体治理层面,往往就更多地带有权宜性和地方性色彩,即便是确立了相关的边疆政策,也由于内部地方实力派的制约,始终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整体性铺开。可以说,民国时期内部统合能力的薄弱直接影响到其政策执行的强度、广度与力度,进而弱化了其边疆治理层面的效能。
此外,我们也要注意到,民国时期的学术话语与当代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整个民国阶段,不管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南京政府时期,边疆议题并不是政府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内容,资源配置也没有专门向边疆倾斜,而这种状况反映到当时的国家治理话语与结构中,就表现为民国时期的边疆话语及其在政治层面体现的边疆政策都属于民国政治系统与决策体系的末端,除了国民政府内迁时期之外,在整个民国的政治动员与物资资源获取方面始终处在边缘性地位,这也直接影响到边疆地区在央—地关系下、以资源获取为基础的结构性调整与改革的具体成效。
当然,还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与清朝康雍乾时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建立制度性的、行之有效的帝国边疆治理秩序不同,民国从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巨大的内外部压力,各类战争频仍,尤其是外部帝国主义威胁侵略与内部地方军阀势力坐大,直接导致民国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长时段甚至中时段对继承自清朝的边疆区域进行有效治理,边疆区域往往处于地方势力的控制之下,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国家治理政策与边疆治理政策之间的断裂性危机。
三、理解民国边疆治理的几个维度
(一)一个国家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随着清帝的退位,“总期人民安堵,海宇 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②《清帝退位授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谕》(俗称《清帝退位诏书》),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辛亥革命》,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217页。清朝的疆域版图被后续的中华民国所继承。这种继承不仅标志着传统的王朝政权结构向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结构转变,同时也意味传统的王朝边地治理逐步向民族国家的边疆治理转变,当然,由于这种转型前所未有,又受到当时国内外政治军事因素制约,因此其间也多有顿挫。但对于“中华民国”的连续性与统一性认知,在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既成为当时国内各界的基本共识,也成为我们认识和面对这一时期边疆危机和边疆治理过程时所确立的基本时空定位。
清末的边疆领土沦丧,令民国初年的学者心痛不已,他们力图对遗留的边疆遗产加以保全:“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①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绪论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3页。原书出版于1938年。这种意识的塑造,标志着作为民国当时国家认同的共同基础已经确立,并力图以此号召国人奋发努力以振国威。
当然,在塑造保全边疆领土的意识过程中,学界也对清末之前的历代边疆状况有所认知,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应的建设性意见:“中国历代对于边疆地方,大抵均采恩威兼施办法。秦皇汉武勤远略,举凡南越北胡,无不臣服;然而武力往往只能用于一时,不能收一劳永逸之效。汉代大患为匈奴,唐代大患为回纥,宋有西夏、辽金之乱,明有鞑靼、满清之祸,历史转变,均以外患为起因,及至清代康乾年间,对于边疆地方,亦曾立显著功绩,颇有海内一统气象……吾人不敏,敢以今后边疆政策之原则数点,贡献于后,聊作本文之结论:一,确立民族平等政策,对边疆民族应力谋其教育之普及,民生之发展,政治之稳定;二,过去之怀柔政策应即抛弃,嗣后宜采取民族协和联合政策;三,各民族之青年优秀分子,宜尽量吸收,毋使若辈屈服在封建势力之下,而无从发展,更宜循循善诱,毋使走入反民族协和联合之路线;四,边境外交统一,由外交当局从速办理,以谋问题之根本解决。”②著者不明:《舆论选辑:确立边疆政策》,载《开发西北》,1934,第2卷,第1期,第79~80页。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这些建议确实有其针对性,也有相当的可行性。而其论述的前提,则依然紧紧围绕民国本身这一共同认同基础展开。
到了20世纪30~40年代,随着日本侵略日甚,当时的中国学人更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边疆史进行了反思,并将中国历代王朝的边地治理与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与开发实践放到同一条时间线中加以叙述,从而凸显出民国在保卫边疆方面理应负担的责任。例如,顾颉刚先生就曾指出:“我们的边疆是我国土地的一部分,我们的边疆民众是我国人民的一部分,一切统一,本来无所谓边疆问题。不幸帝国主义者压迫我国是先从边疆下手的,在这一二百年之内,他们使尽了威胁利诱的手段以求达到土崩瓦解的目的,实已形成极度严重的局势。当这魔手初伸进时,一般知识分子目睹危机,奔走骇告,想促起国人的注意。所以清代道光咸丰年间,虽值汉学极盛之后,士大夫的中心学问是研经考史,和实际社会脱了节,然而究有一班汉学家跳出了传统的学风,在古学之外更注意到当前的边疆情况,像张穆著《蒙古游牧记》、祁韵士著《藩部要略》、何秋涛著《朔方备乘》、魏源著《圣武记》、龚自珍著《蒙古图志》和《西域置行省议》,这就证明了他们感觉的敏捷和对于时代的正视。当时有了这一点研究基础,论理早该激发朝野的同情加以开发和防范,把我们的边疆问题扫除净尽。无如我国积习太深,这少数的知识分子的呼喊,总惊不醒多数人民的浓睡,到了光绪年间外患更酤烈的时候,研究边疆的空气,反而沉寂下来了。一望近数十年来帝国主义者的调查工作和出版物,好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真使得我们又痛恨又惭愧,痛恨的是这般反客为主,其结果必然是盗憎主人,惭愧的是我国太没有人,只有静待着他们的欺侮而已。……在本会成立宣言中,指明我们的工作共有五项:一是促进民族的团结,二是考察边疆的情形,三是研究建设的方案,再有两件是关于出版的,第一项是编纂边疆丛书,第二项是发行边疆期刊。……我们要使已未赐稿的同志都乘着这个宗旨而奋斗,我们要从边疆的学术文化里造起广博的建国基础来。我们绝不愿使道咸间的先进专美于前,也必不肯让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怀着恶意在我们的旁边越分包办,我们要挺起脊梁,鼓起勇气,用了自己的一点一滴的血汗来尽瘁于这方面的工作,为后来人辟出一条大道。我们知道,学术工作不动则已,只要动了总是会前进的,后人是一定胜过前人的,我们鹄望后起的人们把他们的精神感召而把现在号为荒塞的边疆建设得美丽辉煌。但我们处在这时代也不该妄自菲薄,我们要尽力抓住了这时代的公同的新向而完成一个启蒙运动,不辜负这时代,把我们工作的成就贡献国人,作他们认识边疆和建设边疆的必要的初步参考资料。”①顾颉刚:《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国边疆》,1943,第2卷,第1~3期,第2~4页。
总体而言,民国边疆问题的凸显本身,不管其内外部环境如何,依然紧紧围绕着民国这一国家基本结构展开,如果不承认这一国家结构及其现实,则无法全面理解当时的中国边疆及其边疆问题。这是我们探究民国边疆及其治理问题的基本前提。
(二)两个政权体系
民国政治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时段性,那就是按照中央政府的存续时间顺序,先后存在着位于北京的北洋政府与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这两个政权体系,基于各自不同的定位与地缘环境,在边疆治理思维方面,既存在着相同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
在北洋政府时期,所秉持的是以在事实上延续清朝边疆结构及秩序为主导的边疆治理思维。这种边疆治理思维的形成与维系,既跟北洋政府的执政者自身政治背景有关,同时也必须跟从清末一直延续到当时的对于地方主义(联邦主义)的争论有关。如杜赞奇所言:“20世纪最初的10年,随着被改造为现代化的‘他者’,‘封建’一词基本失去意义。但至少到1927年促成国民党人上台执政的(国民)革命为止,联邦主义势力一直都可以找到历来支持封建制对中央集权的批评的政治文化空间。在帝制后期,此种空间就是乡土、地方,它包括了从故乡到省籍之间的范围。联邦主义者的话语围绕着所继承的以强化地方来建国的主题展开,试图即使不把省确立为主权政府,至少也要确立为自治政府,并以此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联邦政体的国家的基础。”②[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170页。在这种背景下,北洋政府在国家治理层面上实际上就面临着地方治理与边疆治理两方面的挑战,而为了控御当时内地各省的地方主义势力,也不得不在边疆治理方面更多地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在事实上延续了清末以来边疆区域的内部政治与社会结构态势。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通过以北伐为核心的军事活动,并借由权力政治的运作,使国民党所秉持的中央集权话语替代了北洋时期笼罩在内地各省的联邦主义话语。这种替代与转化,从话语的层面消除了北洋政府在国家治理层面所面临的地方性危机,在地方治理层面已经没有有力的挑战性话语,使其有可能确立起以重建民族国家新秩序为主导的边疆治理思维,但同时,由于国民党内部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南京国民政府在地方治理层面的推进依然步履维艰,而这也附带影响到其边疆治理能力及其力度。这在东北、新疆、云贵等地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三年即1929年,国民党三大召开,在其三大政治决议案中,曾有这样的表述:“本党致力于国民革命,既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唯一目的,则吾人对于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舍实行三民主义实无第二要求。虽此数地人民之方言习俗与他省不同,在国家行政上稍呈特殊之形式,然在历史上、地理上及国民经济上,则固同为中华民族之一部。”③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646页。这一表述,实际上就体现了由国民党所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基本主张:以三民主义作为国家治理的最高理念,并在此指导下推进边疆治理,而这种边疆治理,除了在国家行政结构上有一定的特殊性之外,在历史、地理和国民经济层面,都强调了在整个民国治理框架下的同一性。
值得注意的是,与北洋政府时期在地方主义压力下不得不侧重于“内政”措施不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了关注边疆地区相关议题的“边政学”。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只有边政的策论文章,而无研究边政的专门学问。1942年吴文藻先生在《边政公论》第1卷中发表《边政学发凡》一文,构筑了边政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顾颉刚先生撰写《亟应废弃的几个名词》一文中,认为有必要在研究和叙述中废弃几个名称,其中就包括“中国本部”,并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华中”、“华南”、“华北”和“华西”的区域界限问题。他在文中认为“我们必须废弃了这些习用的名词始能保卫我们的边疆,保卫了我们的边疆始能保卫我们的心脏;我们也必须废弃了这些习用的名词始能开发我们的边疆,开发了我们的边疆始能达到全国的统一。”①顾颉刚:《亟应废弃的几个名词》,《战时中学生》,1939,第1卷,第2期,第52页。其中既包含着对于中国内部区域认知的期许,同时也展现出在南京国民政府理念指导下,开发边疆进而实现全国实质性统一的期待。
(三)三大外部力量/内部力量
民国不是现实政治的绝缘体。对于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探讨,还有必要考虑当时的内外部因素问题。在民国时期,如果从阶段和影响力而言,主要受到三大外部力量影响:俄苏、日本、英美。与此同时,北洋派系、国民党、共产党则构成了民国时期影响边疆治理全局的三大内部力量。以下分而论之:
在三大外部力量中,俄苏对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实践具有直接影响,并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其中,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日本则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在占领区(如东北三省和台湾等地)推进其自身主导下的边疆治理政策;英美则没有直接在当时的中国推进自身的边疆治理政策,其影响主要是通过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及理念的引入及其在边疆地区的学术实践而形成的。
在三大内部力量中,除了上一部分所提到的北洋派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所秉持的以延续清朝既有秩序为主导的边疆治理思维,以及国民党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民族国家重建新秩序为主导的边疆治理思维,关于这一点,如美国著名学者史华慈所言:“1927年以后的国民政府根据民族—国家的理论体系行事。无论蒋介石的观念中有多少传统的因素,他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确实没有明确表示要回归到传统的世界秩序观。他关于国家主权的必要条件的论述似乎源于法国思想家让·布丹的传统而非孔子的传统。”②[美]史华慈:《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过去与现在》,参见[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302页。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步形成关于民族平等和团结的话语,并在不同时期逐步在苏区、边区和解放区逐渐转入实践,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边疆民族治理理念在民国时期最为成功的实践,同时也为新中国的边疆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事实上,当我们回顾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时,如果按照上述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一讨论本身正是在上述内外力量的合力下展开的。当然,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不再展开。
(四)四个边疆区域
“从19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北部边疆危机是19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中华民族危机的一部分。这场危机覆盖的范围很广,西北自帕米尔,东北至库页岛,在这样一片广袤的边疆地带,仅中俄就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界约24个。这场危机以领土为中心,兼及通商、贸易、传教、驿传、领事裁判权等,对边疆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①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85页。民国在继承清朝疆域版图的同时,也同时继承了来自俄国和日本的侵略压力,并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承受来自日本更大的压力,并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接面对日本的大规模军事入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时结合中国古代历史时期草原游牧与中原农耕力量之间的周期性互动,以及各区域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在民国初年的学术话语中,逐渐形成了对于民国四大边疆区域的认知与分类,并以此形成针对性的边疆话语。
在上述的总体语境之下,民国的边疆治理主要在四个边疆区域展开,而由于时局的变化,这四个边疆区域的重点有所变动。在20世纪10~20年代,四大边疆区域为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当时作为海疆重要区域的宝岛台湾已在日本侵占之下;到了20世纪30~40年代,随着日本的侵略,东北沦陷,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因此其所在的西南地区逐渐成为政学两界关注的重要区域,四大边疆区域转变为西南、蒙古、新疆和西藏,当然,到了抗战后期,又开始逐步重视和经营海疆,并逐步形成中国海疆界线。②即传统上所称的“十一段线”,后来演变成“九段线”。该线最初在1947年由内政部方域司发布的《南海诸岛位置图》中加以标注。在1932年时人的记述中,曾这样写道:东北沦陷,“彼时唇亡齿寒……使举国国民,一致注意到西南国防这个问题上来……西藏滇边是吾中华民国的领土,吾西南民众,就是中华民国一部分的国民,保存西藏滇边的领土,就是以中国民国国民的资格,保存中华民国的领土。”③宋人杰:《西南国防论》,上海:中华书局,1932,第19~34页。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当时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开始着力于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1939年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其中更是直接指出:“吾国幅员广大,西南西北各省产业、文化亟须致力建设,今长江南北各省既多数沦为战区,则今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不懈,必有赖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开发,以为支持抗战之后方。西部各省资源丰富,人力无穷,建设之首要,一面固为先谋交通运输之发展,一面更应于各省人力、物力、财力有合理之统制,以应抗战之需要。惟统制之要旨在于发展生产,以利抗战,增进民生,故开发建设西部各省者,以巩固抗战之后方,实与普通奖掖国民经济之发展,同其重要也。”④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556页。最终在政治层面意识到西南边疆对于稳定民国统治秩序及其抗战事业的重要性。⑤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
当然,随着抗战的结束,东北和台湾复归民国版图,在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西南边疆地区的地位有所弱化,到了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国民党战场形势的岌岌可危,使其一度试图重新利用西南边疆地区为基地来扭转战局,但政治军事形势的迅速变化,使这一想法最终未能实现,最后则改由通过海疆(以台湾为中心)的经营,形成后来的两岸对峙局面。总之,民国时期的政局变迁,与其对内部边疆区域的关注重心变迁是同步而行的。
(五)五大国格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仅使中国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赢得了民族独立,而在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首次经由战胜国地位而获得有机制保障的大国地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这种结构之下,中华民国作为民族国家,一方面获得了新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则开始受到机制性“国际关系”(在当时为雅尔塔体系)的影响,并形成彼此相互扭结的关系。
在这种语境下,“现代国家的主权发展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国家间关系的反思性监控。无论是国家主权的巩固,还是民族—国家的普遍性,都是通过扩展了的监控操作才得以成立的,监控操作保证了‘国际关系’能够展开。‘国际关系’不是前民族—国家之间建立的关系(没有它们这些国家也能维护其主权),它们只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国际组织的萌芽生长(包括国际联盟与联合国),并没有超乎民族-国家智商。正是在这个时期,民族—国家无所不在地建立起来了。欧洲国家体系是通过战争与外交的混合并用而建立起来的。但是,在军事工业化的背景下,随便哪里的战争都有整体的特征,并以世界大战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影响到所有的国家。世界体系日益整合的结果,使外交再也不能只在国家集团之间进行,而要在某些基本方面囊括所有国家。”①[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313~314页;第315页。抗战胜利之后的民国,一方面受益于战胜国地位,彻底解决了因日本侵略所造成的边疆危机乃至国家危亡局面,在这之后,在中国版图上,近代意义上的、对于国家与民族发展存亡关系重大的边疆危机已经不再出现;而在另一方面,基于新的国家关系格局的建立以及民族国家单独行动的受限性,因此之后就出现了如何有效处理当时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国控制下的英属印度、法属印度支那等与民国相邻接的殖民区域,以及这些区域内部国家实现独立之后的边境争议,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五大国格局下遗留给当代中国的重大而棘手的问题。
此外,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的意义在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公开接受了‘势力范围’的想法,虽然它们同时也强化了国家主权的普遍性。其他大国充分承认苏联的主权自主性,就后果而言,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苏联对民族—国家之普遍性的认可。”③[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313~314页;第315页。在这种态势下,作为对获取机制性大国地位的回报,苏联实际上放弃了其超民族国家的苏维埃世界革命的理念,转而接受了自身作为民族国家的外部定位,这种定位也影响到苏联与民国双边关系的调整。
在学术研究层面,在二战后的五大国(美苏英法中)格局下,民国之前所面临的国家救亡运动已经结束,这种背景使得曾经一时火热的“边政学”与边政研究逐渐弱化,新的地缘格局逐渐转向五大国内部的协调问题。在此转变过程中,民国的边疆治理逐步从救亡式开发转向具体的政策执行,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逐渐向民族研究方向转变,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也逐渐转变为民族区域管理,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四、结语
如果说“恩威并施”和“因俗而治”是清朝控御边疆的基本方针的话②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56页。,那么,民国的边疆治理主要特征则是“断裂政治”与“有限效度”。由于民国时代所处的复杂内外环境,尽管国家认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逐步深化,但中央政府始终权威不足,使得这一时期的国家治理缺乏足够的时空保障,也缺少足够的资金支撑,而且其相关政策往往在内外部纷争中走样变形,效能大打折扣。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国家治理一部分的民国边疆治理,自然受到的关注和支持就更小,也缺乏必要的资源和人员来推进具体的边疆治理,被动因循成例者多,主动调整改革者少。当然,抗战期间民国中央政府对于边疆尤其是西南边疆大为重视,主要还是地缘环境所迫,一旦抗战结束,国内对于边政和边疆开发的讨论也随即消歇。总之,在断裂政治的不安环境下,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缺乏有效的指导原则,在具体操作层面也缺乏推进力度,这种局面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根本性的改观。
Frontier Governance under the Broken politics—The Context and Dimension of Frontier Policy Practic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Yuan Jian
Through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geopolitical background in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is paper made some corresponding analysis of som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af f ect the borderland governance in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nd concluded that the cyclical impact of the broken politics, the cyclical impact of the outer and inner great powers, the fi ve great nation-states’ structure after World War II, had to some extent af f ected and decided the executive ability of the borderland governance in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broken politics; the borderland governa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background
中央民族大学校级自主科研项目《近代以来中国“边疆”概念的范型与流变》(2015MDQN03)。本文的主要内容笔者于2017年5月11日曾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的专题讲座“断裂政治下的边疆治理:民国时期关于边政的讨论及其外部背景”以及5月27日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生态、边疆和文明工作坊”上宣读,得到诸位师友诸多建设性意见,特此致谢。
袁剑,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边疆、中亚问题研究。(北京,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