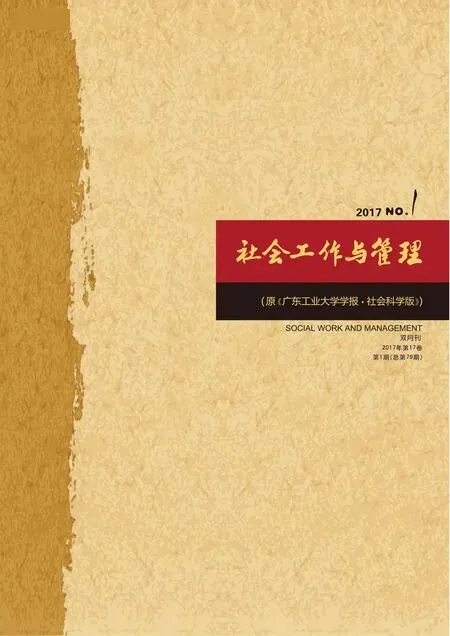从“协调冲突”到“源头治理”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治理与社会工作介入
陈立周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3;2. 湖南商学院社会工作系,湖南 长沙,410205)
从“协调冲突”到“源头治理”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治理与社会工作介入
陈立周1,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3;2. 湖南商学院社会工作系,湖南 长沙,410205)
社区冲突源于社区利益的分化,而社区信任关系的断裂使社区冲突失去了调和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要策略是进行“源头治理”,通过转变基层政府执政理念、改变社区居委会的角色错位、培养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等,使社区由“冲突”走向“合作”。
社区冲突;社区治理;社会工作介入
社区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实践平台。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参与社区治理发挥“服务型治理”[1]的功能。社区治理是指以社区为基础,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 它体现为社区范围内的不同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2]在存在利益分化的情况下,社区各主体间的互动更可能以“冲突”而非“合作”的形式体现出来,使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面临很大挑战。本文拟以一项社区服务项目为例,对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冲突的根源、社会工作介入的制约因素及其策略做初步分析。
一、由“公共建设”引发的社区冲突
2013年6月下旬,湖南地方媒体“新湘晨报”以“绿地上画个圈,清塘社区要盖办公楼”为题发表了一篇报道,使一个普通城市社区的名字很快被市民熟知。[3]该报道直陈事实:“清塘社区组织上百人,在无任何合法手续的前提下竟然强行围挡,声称要占地新建两栋社区办公大楼”,“清塘社区在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不但没有主动拆围,反而强行破土施工。”一位亲历整个事件的社区居民描述了当天的情景:
上午十点钟左右,大家正在小区门口休息扯白话呢。突然间,来了很多穿制服的人,城管啊,社区干部啊,警察啊,挖掘机推土机也开进来了。警车打着警光灯停在路边,有人用喇叭不停地喊话,割得耳朵发麻……(这些人)立马拉上警戒线,建起围挡……不准任何人靠近……
据居民回忆,当时一名业主不顾阻拦上前拆除围挡,被执法人员阻止,并拉上警车带到派出所讯问。一名试图拍摄的居民,手机在双方的拉扯争夺中摔坏;另一名居民在冲突中脚踝受伤。正如近些年部分地方政府常以公共建设的名誉强拆强建而引起人们极度反感一样,该报道被一些网站转载,多家地方电视台跟踪报道,引发市民的热议。很多网友用“无法无天”“管理部门不作为”“背后隐藏巨大利益”等语句来指责清塘社区居委会的这一行为。
社区居委会为何突然在此大兴土木建办公楼?居民又为何群起反抗?随着了解的深入,事件轮廓逐渐清晰。近年来,在举国推进的和谐社会建设浪潮下,“和谐社区建设”成为当地政府的重要行政目标。2013年1月,C市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到‘十二五’期末实现50%以上城市社区达到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标准”“争创首批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市”等目标。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文件还制定了具体办法:“新建社区办公服务用房面积,老城区应不少于500平方米,新城区应保证800平方米以上。现有社区办公服务用房未达到标准的,由各区县(市)政府牵头,街道(乡镇)负责,规划、国土、住建、城管执法等部门配合,通过整合、购买、新建、改建、共建或置换等形式加快建设,力争‘十二五’期末全面达标,所需资金由各区(县)政府统筹解决。”①三个月后,政府再次发布《有关社区办公服务用房建设达标工作的实施方案》,其中明确规定:“用三年时间完成全市69个未达标社区办公服务用房建设达标工作任务。”②
清塘社区正是全市69个未达标的社区之一。其总面积为1.5平方公里,辖15个居民小区,3个专业市场及多家企事业单位,有近2万人常住人口,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商铺2 200多个,是一个面积大、人口众多、商铺林立的大型社区。清塘社区工作人员达15名,但办公面积仅150平方米。为了落实上级政府的达标要求,在街道办的部署下,清塘社区居委会选定了清塘东路的一处“闲置用地”,欲在此建成办公楼。2013年5月28日,清塘社区在区发改局办理了立项手续,并报请区规划、国土和住建等部门签字同意。由于完成达标任务有时间期限,且没有其他可利用的土地,社区仅用了三天时间完成了施工部署。在大部分居民尚不清楚事情始末的情况下,项目于2013年6月19日匆匆上马。于是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③当追问为何不事先征得居民同意再施工时,社区干部无奈地答复:“周边居民思想工作做不通,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来。”④正是这一“硬着头皮来”的行为,给居委会惹来巨大麻烦,引发社区居民的激烈对抗。
然而,居委会没有就此放弃办公楼建设。一方面,在前期施工过程中已经支付了相当成本,若工程半途而废,前期的投入相当于“打了水漂”;另一方面,又无法完成市政府关于社区办公场所达标建设的任务,行政上面临巨大压力。在强行施工未果的情况下,社区居委会修改了前期的工程规划,将社区办公楼改建为“社区公园”,请专业机构重新设计了社区公园建设效果图和规划图,意欲获得居民的支持,以使工程顺利推进。在呈交给上级部门的汇报材料中,居委会特意做出如下说明:“现有的社区办公楼楼层太高且较拥挤,不方便居民办事,在向上级相关部门申请的基础上,选定清塘东路南侧的一块空闲用地作为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的建设场地,但遭到邻近小区少数住户和门店业主的阻拦,未能顺利施工。相关职能部门、街道办及社区居委会经过数次协调,均未收到明显效果,居民反对意见如故。后经重新规划,拟改建为社区公园。”⑦表面看来,居委会已经做出重大让步,工程性质亦做出了根本调整。
但从2013年11月至今,社区居民始终拒绝跟社区居委会“对话”。至此,工程已全面瘫痪,居民与居委会处于对立状态。在与居委会数次斗争的过程中,居民已能娴熟运用“弱者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不甘就此罢手的居委会,则以政府政策为依据,坚持认为这块公共用地不属于小区居民所有,而是一片闲置的“无主之地”,政府有权用于服务民生的公共工程建设。为此,居委会一方面对冲突中受伤的民众进行慰问,对居民的损失进行赔偿,另一方面刻意维持“围挡”现状,若发现谁强行拆除,便以破坏公共建设的名义追究责任。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街道办官员求助于社工机构(笔者在机构里担任专业督导),希望通过专业社工的介入推进社区公园建设。在正式介入之前,机构组建了项目团队,制定了工作计划,确立了服务目标:即将对立的双方拉倒谈判桌上,促成社区公园建设。
二、利益分化与社工介入的限制
“空地”犹如一个引力巨大的磁场,将居民、街道办及居委会强力吸纳进来,双方为之展开激烈争夺:街道办和居委会在市政府建设“和谐社区”的要求下,希望开发这一闲置的“无主之地”,建成社区办公楼,以完成上级部门规定的达标任务;在居民看来,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围绕这块闲置的公共用地形成许多“分利集团”⑧,他们绕开居民,从中谋取私利。⑨居民用尽一切办法,坚决反对居委会在空地上建社区办公楼,并获初步成功。据此看来,正是利益的分化造成了社区冲突,那么,社会工作介入的关键,就是弄清利益涉及各方的真实意图,协助它们形成“共容利益”⑩,使社区由冲突走向合作。
由于遭到居民的激烈反对,并受到上级部门的责问,街道办和居委会重新设计了工程规划图,对居民做出了一定让步,仅保留适当面积作为社区办公楼用地;此外,亦承诺对拥有临街商铺的居民给予标准不低的补偿。根据项目组的评估,社区现有办公用房狭小,地理位置偏僻,难以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是既存的客观现实。而且根据新的设计图,在社区公园建设中除了按照达标要求建设的社区服务中心外,并无其他建筑,不存在居民所说建成大批商铺用于出租的可能。总体上看,社区公园建设是有利于社区公共服务及社区环境改善的。如果社区冲突的根源是利益分化,那么“社区公园”是双方消除分歧、达成“共容利益”的重要契机。正是基于这一点,机构项目组在项目协议中将工作目标定为:“通过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协调居民与居委会的矛盾,消除误会,增进理解,建立互助合作的社区关系。”在介入初期,项目组成员不停地“穿梭”于街道办、社区居委会和居民之间,试图通过耐心的沟通,让居民在社区公园建设方面跟居委会达成共识。
在介入的第一阶段,项目组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沟通协调,但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居民开始对频繁来访感到厌烦,甚至认为社工就是居委会的“说客”,最后郑重通告项目组:“你们懒得跑,我们也懒得答复。请转告居委会,建社区公园可以,起房子不行。”⑪这一结果让项目组始料不及,而且也不清楚造成这一结果的真正原因。或许所谓的“共容利益”只是社工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并不存在?但据项目组的了解,社区治安不良、卫生环境糟糕、居民关系高度原子化等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项目组进行的社区需求调查亦证明大部分居民有提升社区服务水平、扩大公共活动空间的强烈愿望。那么,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共容利益”的假设都是成立的。
当试图以“建设社区公园利大于弊”为由说服居民时,居民坚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建设社区公园“隐藏有巨大阴谋”“官商勾结谋求巨额利润”,等等。有居民指出,居委会自称没有办公场地,实际上有许多房子用于出租。⑫另有居民直截了当地说:“居委会想用‘狸猫换太子’的伎俩强行施工,先斩后奏,房子一旦建完就等于‘生米煮成了熟饭’,他们想拿来干嘛就干嘛。他们现在说建活动中心,以后还会拆了建其他的。”⑬当项目组试图劝服居民“顾全大局”,居民愤怒地回应:
如,2017年3月,云南省科技厅引入4600万元科技金融政府风险补偿基金增信,运用“政府增信+N”的担保机制,对接农行“科创贷”产品。截至9月末,农行云南省分行“科创贷”余额1.97亿元,其中,科技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51.8%,科技型小微企业户数占87.5%。云南农信社、民生银行昆明分行与省工商局合作,实施企业注册登记全程电子化,提升工商注册效率,并及时获取企业信息,为银行发掘潜在客户。
我们支持社区建设,但任何人须依法办事。社区作为党和政府与居民沟通的一个纽带,乱来会影响政府的形象,违背群众路线……居委会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
直到此时,项目组才真正认识到,信任关系的断裂才是社区冲突难以调和的真正原因。在基层社会,利益冲突是普遍存在的,但仍存在通过利益协调取得“共容利益”的可能性。然而,在一个信任关系断裂的社区,已经失去构建“共容利益”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者企图因袭传统的“沟通协调”方法化解社区冲突,只能事与愿违。因此,社会工作有效介入社区治理的前提,是对社区信任关系断裂的根源有客观的判断。
无疑,正是居委会的“角色错位”,导致它失去居民的信任。当然这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后总体性社会”[5]出现,城市管理逐渐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20世纪90年代,民政部在全国推行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社区功能不断扩张,居委会作用逐渐凸显。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对居委会的性质做出了法律上的规定:“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6]但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对社会组织采用“分类控制”[7]的策略,将社区居委会塑造成“准政府组织”,使它们高度依附于政府机关,几乎没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重心在于执行政府的行政意图,而非作为居民的代表履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职能,导致“角色的错位”。清塘社区居委会面对的正是这种状况。由于对街道办及上级管理部门的行政依附,清塘社区居委会在处理社区事务时,通常代表“政府”而非“居民”,当涉及利益纠纷时,成为基层政府“与民争利”的“排头兵”,最终失去居民信任。
所以,只有将居委会放在整个行政体系里考察,方能弄清其“角色错位”的根源。清塘社区的案例表明,居委会只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街道办”才是真正的决策者,后者执政理念的偏差才是问题的关键。在中国当代的行政管理构架中,街道办名义上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事实上却是一级地方政府。[8]作为最基层的地方政府,它具有双重角色:一方面充当“代理人”,执行上级政府的行政意图,并受到上级部门的监督和约束;另一方面,又是“决策者”,承担着因地制宜维护当地经济发展、民众生计、社会治安的一系列任务。[9]后一种角色使街道办在发展地方经济过程中拥有极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这就能解释,为何在面临居民激烈反对、上级政府亦出面制止的情况下,街道办还要迎难而上,想尽办法推动社区办公服务用房建设,因为这些行为体现了中国行政系统特殊的运作逻辑。建国后,发展经济是政府的重要目标,上级政府部门通常以政治任务的形式下达各项任务,地方政府之间在压力型体制下纷纷展开“政治锦标赛”[10],以期在比赛中胜出。市场化改革并未根本改变这种运作逻辑,不过以更加技术化的方式推行而已。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上级政府往往以“指标”等形式下达指令,基层政府则可以灵活处理上级部门的“指示”,通过“逆向软预算约束”[9]行为,向辖区内的组织和个人谋取更多的资源,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指标。完不成上级政府下达的指标,地方官员的职务晋升就会落空,使得这一发展经济的过程亦变成一场残酷的“政治淘汰赛”。[11]为了不被淘汰出局,地方官员产生强烈的政绩冲动,通过“资源密集型政绩工程”[9]获取短期政绩。这里头涉及复杂的文化背景和制度因素,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但对探究街道办在社区办公楼建设中不遗余力的行为,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正是为了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达标,而这些指标又关乎基层官员的政治前途,街道办官员才会穷尽一切办法推进社区公园建设。当社区办公用房建设遭到居民坚决抵制、社区冲突加剧之时,街道办仍然坚持将社区办公用房作为建社区公园的前提。
一旦涉及利益纠纷,信任关系的断裂很可能使社区出现“不可治理”的状态。在介入的第一阶段,项目组以为抓住了“共容利益”这个关键因素,社区冲突就可迎刃而解。实际上,在一个信任关系断裂的社区,涉及核心利益时,社区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换句话说,如果利益冲突是造成社区冲突的主要原因,那么,社区信任关系的断裂则是社区冲突无法调和的根源。有了这些认识,项目组及时调整介入策略,将介入目标确定为“重建社区信任关系”。
重建社区信任关系,需要各方基于社区居民的基本需要展开合作。在介入的第二阶段,项目组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制定了新的服务计划。项目组通过居民需求调查发现,儿童和老年人是社区居民中服务需求最大的群体。项目组以满足这两个群体需求逐步开展社区服务活动,例如针对儿童在放学后或周末无处可去,而父母因工作繁忙无法照顾孩子的状况,社会工作者开展了“四点半课堂”服务模式,不仅帮助儿童学习文化知识,还培养他们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团队协作、社区实践、志愿服务等能力,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从最有需求的居民入手,以点带面,为社区居民提供全面的专业服务。
当然,社区信任关系的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服务还处于探索阶段,有许多现实困难还有待去克服;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它符合社会工作通过“服务型治理”参与社区治理的理念。依据这一理念,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要策略,是从“协调冲突”迈向“源头治理”。
三、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主要策略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通过服务来进行社会治理的理念是社会工作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贡献,可以从源头上减少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在冲突、矛盾出现之后也可以通过服务予以缓解和化解。[12]项目组“重建社区信任关系”的介入实践,本质上就是一种“源头治理”,目的是使社区各主体由“冲突”走向“合作”。至于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基于清塘社区的实践,项目组认为社会工作应该坚持以下介入策略。
首先,协助社区居委会的角色由“政府代理者”向“居民代言人”回归。正如前文的分析,由于行政管理体制的限制,居委会角色错位不仅无法履行群众自治组织的功能,反而成为政府执政偏差的“替罪羊”。例如,当社区办公楼建设遭到居民反抗,居委会希望得到上级政府支持时,上级政府又将“皮球”踢回社区,答复说:“建设社区办公楼须以征得居民同意为前提;若居民同意,可以边建边补办手续。”⑭这让居委会上下失据,左右为难。当然,居委会角色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但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先发挥社区居委会的传统优势,比如跟居民比较熟悉,了解社区的历史及社区文化等,在为居民服务的过程中逐步改变与居民的关系,获得居民的信任。在社会工作介入过程中,机构协助社区居委会,组织社区干部、居民及社工一起,提供居家服务和环境卫生服务等,这些社区服务项目的开展正是为了改变居委会在居民眼中的负面形象。总之,在涉及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和合法要求时,居委会应该勇于发挥居民代言人的作用,站在居民的立场,维护居民的利益,这样才能真正取得“社会合法性”[13],获得居民的认可。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出发,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14]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具有发展成为最具有活力的社区组织的潜力。如果一味服从于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这种活力的培养便无从谈起。
当然,若基层政府追求“短期政绩”的行为不改变,居委会的角色错位问题就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改变。⑮因此,社会工作发挥“源头治理”的第二个策略,是促进政府的执政理念转变。在当前“国强民弱”的现实下,政府仍然是社区治理的主导力量。发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需要政府行政理念从“管理”向“治理”转变。也就是说,政府除了促进经济建设的职责外,也要承担对社会公平的保护和对公共事务的管理。[11]目前,“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已经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强调,但是在基层社会真正得到践行还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发挥“政策影响人”的作用,提升基层政府的执政水平。⑯在政策层面上,社会工作通过服务发现问题,进而提出改善政策的建议。社会工作以自己的专业理念,社会良知、正义感和由具体服务深入接触底层群体而获得的真实资料为基础,倡导社会政策的完善和改变。[1]在清塘社区矛盾调停中,围绕围栏的拆除与否,社会工作者与街道办曾有多次讨论。在社区居民与居委会因社区办公楼建设陷入僵持之时,街道办及社区居委会均将“围挡”视为政府权力的象征。在他们看来,主动拆除围挡,意味着对居民妥协与让步,使自身的权威受到削弱。这是一种传统的“控制”思想。在沟通协调的过程中,项目组耐心地分析利弊,解释围挡的存在会造成居民的误会,甚至会引起社区的进一步分裂。事实上,围挡已经对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诸多不变,也增加了居民对居委会的误解与怨恨。在项目组的说服下,街道办与居委会主动拆除了围挡,将广场恢复了原貌。这一处理办法,使居民与居委会的对立情绪有了明显的缓和。
社区居民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在社区治理中,要真正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关键是培养居民的社区意识。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发展,城市居民的主体性逐渐加强,人们从原来某种程度上的“臣民”或“刁民”意识逐渐转变成为拥有责任意识、权利意识与平等对话观念的公民。这些公民面对社会议题不是坐而等待“青天”,也不是简单地对抗,而是积极行动,力求通过温和理性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增进社会福利,甚至影响政府政策的改变。[15]在实践中发现,虽然居民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但社区意识却相对缺乏。例如,在社区公园建设问题上,居民态度其实分为三类:其一,坚决反对,坚持“建公园可以,只要‘起房子’,就免谈”。调查发现,这部分居民都是那些有临街铺面的业主,对他们来说,保持原貌是最好的,这样商铺前面的宽阔空地就成为一个天然的免费停车场,方便做生意;若建成社区办公楼,生意势必受到影响,商铺的价值必定下降,这会威胁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其二,可以建社区公园,但要按照程序,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社区居民代表的监督下施工,居委会不能“把手伸太长”,违背承诺侵害居民利益。这部分居民没有临街商铺,他们更希望拥有一个健康的安居环境;其三,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对他们来说,社区公园、社区办公楼都是跟自己无关的事情,这部分居民主要是外来的租户,他们不关心社区建设,不愿意给自己惹麻烦。
而那些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居民,在社区冲突之中容易走到一起,成为跟居委会对抗的中坚力量。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与居委会抗争。但他们的行为主要是基于自己的利益。绝大部分居民则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既不在乎他人利益的损失,也不关心社区公共建设,这很不利于社区公共事务的发展。总体上看,现代城市社区具有明显的利益高度分化、社区生活高度原子化的特征。对于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区来说,培养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是最为关键的工作,对此,项目组设计了“美丽家园,从我做起”社区行动,通过维护环境卫生行动,培养居民的社区意识。很多居民认为,这样的社区行动很有意义,也愿意参与,但苦于没有人组织。这正是社会工作介入的空间之一。
四、结论
本文发现,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利益分化往往会导致社区冲突,而社区信任关系则是处理社区冲突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一个存在利益分化的社区,由于社区信任关系的断裂,社区冲突往往难以调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要策略,不是单纯的以中立者的身份“协调矛盾”,而是以“促进者”的身份进行“源头治理”,将“重建社区信任关系”作为核心任务,具体包括转变基层政府执政理念、改变社区居委会的角色错位、培养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等。也就是说,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不是单纯的提供“修补性”的服务,还应发挥“预防性”的功能,从消极介入转变为积极介入。作为一种具有“强价值介入”[16]特征的助人专业,面对切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服务对象,仅仅保持一种“协调者”的角色是不够的,如此社会工作无法真正融入社区;相反,应该将公平正义作为基本服务理念,在政策层面推动社区治理。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为作者调研访谈资料。
⑧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社会集团为其成员谋取利益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尽量在社会总体收益中为其成员争取更多的份额,而不顾社会总体利益的增加或者减少。奥尔森将这些团体称为“分利集团”(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分利集团只代表自己成员的利益,不会为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不会关心自身的分利活动对社会的影响。那些建立了组织的社会群体会利用自身的集团优势,采取各种手段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来谋取自身的特殊利益,导致其他群体特别是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体的利益受损。参见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曼瑟·奥尔森的《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
⑨在访谈中,一位居民愤怒地说:“社区以上级政府对社区工作要求为由,不择手段,骗取上级主管部门和有关执法部门的支持;同时,这次要在小区前坪的绿化带上建房3 000多平米,据称是个建筑老板出资,社区负责用地,利益五五分……”。
⑩奥尔森认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通常很重视“共容利益”,即他们对被统治者并不总是强取豪夺,往往通过减少税收、投资公共事业等,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以增加社会产出,使自己能在社会收益里获得更大的份额。奥尔森认为,虽然“共容利益”出自统治者的自利而非善心,但体现了统治者对于权力的“建设性使用”,具有积极的一面。本文借用这一概念,是要说明基层政府推进的社区建设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共容利益”的特征。参见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曼瑟·奥尔森的《权力与繁荣》。
⑪为作者调研访谈所得资料。
⑫清塘社区居委会为了扩大生存的空间,将原来的办公楼四楼以下出租给了一家私立幼儿园,此外还出租了一些商铺。当居民了解情况后,对居委会便产生一种本能的怀疑,认为居委会手上拥有大量的房源,还要不断扩大地盘,与民争利。在递交给上级政府的上访材料中,居民附上了这些铺面的照片,作为居委会不仅不代表居民利益,还侵害居民利益的“铁证”。
⑬⑭为作者调研访谈所得资料。
⑮居委会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居委会主任曾无奈地对笔者抱怨,干脆不要建社区公园,搞得我们左右为难。如果一开始就专心为居民办事,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种地步。
⑯这并非我们单方面的想法。我们在社区服务实践过程中,常常因为服务理念与政府执政理念的分歧而苦恼。一位民政局的官员明确希望我们坚持自己的理念,发挥影响和改变政府执政理念的作用。
[1]王思斌. 社会治理结构的进化与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J]. 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30-37.
[2]康宇.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历程及现实困境[J]. 贵州社会科学,2007(2):65-68.
[3]绿地上画个圈,清塘社区要盖办公楼[N]. 新湘晨报,2013-06-19.
[4]詹姆斯·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26.
[5]孙立平.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1.
[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EB/OL]. [2016-06-15].http://www.people.com.cn/item/ flfgk/nuf/1989/111201198908.htm.
[7]康晓光,韩恒. 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5(6):73-89.
[8]朱健刚. 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J]. 战略与管理,1997(4):42-53.
[9]周雪光. “逆向软预算约束”: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5(2):132-143.
[10]周飞舟. 锦标赛体制[J]. 社会学研究,2009(3):54-77.
[11]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9(6):104-127.
[12]王思斌. 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种基础—服务型社会治理[J]. 社会工作,2014(1):3-10.
[13]陈立周. 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行动逻辑[J]. 学习与实践. 2009 (8):120-127.
[14]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EB/OL]. (2013-11-14). 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 tj/2013-11-14/c_118121513.htm.
[15]朱健刚. 论基层治理中政社分离的趋势、挑战与方向[J]. 中国行政管理,2010(4):39-42.
[16]阮邦新. 迈向崭新的社会知识观[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2.
(文字编辑:邹红 责任校对:王香丽)
From “Coordination” to “Source Control”: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HEN Lizhou1,2
(1.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Hunan, 410205, China)
Community conflict comes from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mmunity interests, but the fracture of community relationship makes it difficult to reconcile. In this case, the main strategy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source control”, which includes changing the governing philosophy of local governments, changing the dislocated role of community neighborhood committee, cultivating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so on, in order to transform the community from conflict to cooperation.
community conflict; community governance;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C916
A
1671-623X(2017)01-0045-07
2016-06-21
■ 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居住空间调整与城乡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研究”(14BSH109);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三社联动’的城市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创新研究”(16YBA238);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本科院校社会工作专业‘整合型’实践教学模式研究”(湘教通〔2016〕400号);湖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三社联动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创新研究”(16C0880)。
陈立周(1975— ),男,汉族,讲师,博士后,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陈立周. 从“协调冲突”到“源头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治理与社会工作介入[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7,17(1):4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