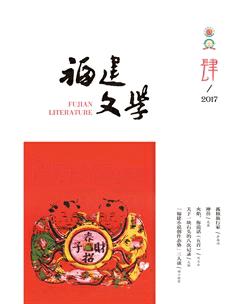放开一只被锁的狗(外一篇)
赵雨
一
第四次辞职后,他决定不玩了,不再工作,工作个啥!他的最近三次辞职相隔不到一个月,最后一次索性直接和车间主任拍了桌子:“老子不干了!”车间主任说:“你这种人懒惰成性,留你一个月算是给足面子了。”他磨拳霍霍,差点和主任动起手来,被工友拉开,才愤愤离去,为此,连当天的工资都没拿到,“老子不稀罕。”他说。
他职高毕业,从小不爱学习,读不好书,进了职高,学编程设计,三年下来,啥叫编程都没搞清楚。他确实有那么点懒惰,低学历注定他只能干一线工的活,该岗位讲究勤劳肯干、吃苦耐劳,奋斗在公司最肮脏、最不堪的地方。他心目中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可不是这样的,他应该坐办公室,干轻松的活,活得有尊严、受人尊敬。但手头没有学历这块敲门砖,没有单位鸟他,他只能往下、一直往下。一线工基本都是计件的,多劳多得,凭力气吃饭,他没这份心,找到偷懒的机会就逮着不放,这回和车间主任拍桌子的原因正是被发现躲在机器后玩手机。
频繁地跳槽,每次跳槽都不欢而散,让他养成了暴脾气,看什么都不顺眼,仿佛所有人都在针对他,身为员工,领导说他不得,一说就要引爆。他体内窝着一团火,针对一切,时刻准备烧掉一切,让这混蛋世界滚蛋。他经历了四次失业、再就业,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没有工作容得下他,所有工作都不适合他,他的归宿是远离人群,回到与世隔绝的地方,最好的去处就是:家。
他失业了,从此过起隐居生活。二十好几的人,没工作,他不在乎,父母健在,讨口饭吃总不至于不得。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对这样的儿子,始则劝解,磨破嘴皮子,一车话就像洒进泥浆,泡都没冒一个,终则放弃,就当他还是孩子,由父母供养,责任无可推卸。
他在家只干一件事:玩游戏。玩各种网络游戏,在虚拟世界中,他才得着心灵的宁静,拉帮结派攻城陷地,打怪兽、爆装备,技艺日渐精进,手下有了小弟,小弟唤他大哥,他找到了存在的价值。他从早玩到晚,早饭由父母备下,中饭不吃,晚饭还让父母端进屋,连迈出房的时间都不肯浪费。他认识了不少网友,其中有一个是同城,女,后来成了他女朋友。
他这样的人竟能找着女朋友,且不多久就住了进来,他父母不敢相信,原以为儿子堕落至此,工作无着落,侈谈感情归宿。眼下一个水灵灵的姑娘肯来寒舍下榻(她来的那天只背着个包,没有一件行李,见到他爸叫了声爸,见到他妈叫了声妈,叫得二老骨软筋酥),无异于天上掉馅饼,将她捧为座上宾,饭菜好好伺候着,他妈每天给她洗内衣裤,家务一概不让动手,绝无二话。她倒是工作的,只是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什么上进心。有人问她:“你怎么会看上这么一个不工作的人?”她说:“我觉得他身上有种别人没有的魄力。”“什么魅力?”“让你完全歇在家,你做得到吗?”“但那是不对的呀。”“不管对不对,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这就是魄力。”
他的生活有了点变化,笑得比以前多了,当然这只有她能看到。他们两人待在屋子里,他觉得这就是一整个世界,四面墙壁围起的空间将外界所有因素隔绝在外,以前他一个人,游戏玩得再激奋人心,深夜独睡,总不免感到内心空虚,他相信人是孤独的这句话,但既然孤独是他的选择,为何会感到痛苦?若不选择孤独,跑到围墙外面去,大千世界任闯荡,他又不适应。那么,人就是两难的,左右不是。现在,两个人了,空虚时跟她讲讲话,就在不足五十平方米的空间,得到的满足比五百平方米、五千平方米都大,他觉得寻到了生活最理想、最浪漫的状态,即便将他置身监狱,有她陪伴,他不会孤独。
但她的状况发生了细微的转变,一开始倒也觉得这样不错,和爱的人厮守一起,亲密无间,为之前所未曾经历过,她愿意出去挣钱,养活他俩。久而久之,工作的压力来了,一天上班结束,单位里遭遇的苦楚、不满,无法对他诉说,他对这些没有丝毫兴趣甚至本能排斥。他只愿意贡献漫无边际、没有实质内容的谈资,比如生活的意义、人生的苦楚……这东西听久了,会腻味。他在具体的现实事务上缺乏激情,内心犹如一潭死水,像一個八十岁的老人,不,老人或许也比他活跃。她强忍这种糟糕的感受,终于在半年后,达到了底线。
那天她对他说:“我出去住一段日子吧。”他乍听之下有些懵:“为什么出去住?”“我闷得慌。”“跟我在一起闷吗?”“我不知道。”“你具体说说看。”“你从不陪我逛街、看电影。”“逛街、看电影?你喜欢干这种事?这是最无聊透顶的事。”“我这样年纪的人都喜欢干这种事。”“你从来没说过。”“不说不代表我不喜欢。”“明天我陪你去一回。”
“你不工作。”“什么?”“我说你从来不工作。”“你一开始就知道我不工作的,你说我敢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魄力。”“现在我不这么觉得了,人活着还是要工作,你没赚过一分钱,把经济压力都丢给我一个女人,你和吃软饭的有什么差别?”“你这是要跟我闹分手吗?”“既然说到这分上,分手就分手吧。”
她起身出门,他强压着怒火,越想越不对,自己这是被蹬了!那隐蔽了大半年的暗火,来了个总爆发,任何东西都压不住。他从床边扯起她来的那天背的双肩包,冲出门,来到阳台,顺手把包给甩下去,她正走出大门,砸到她头上。“给老子滚!”他吼道。“你这神经病。”她揉着脑袋,哭着说,捡起包,头也不回。
他即刻把消息告诉父母,父母愣住了,两袋烟工夫,他爸拿出第三根烟续上,揉了把脸,他妈一拍桌子说:“不能让她这么走了。”他爸说:“你想怎样?”他妈说:“钱得算回来。”他爸问:“什么钱?”他妈跑进厨房,找出一个本子,摊到他和他爸面前,上头用铅笔写着一笔笔明细,某月某日,买菜多少钱,某月某日,买一双鞋……“这些都是这半年用在她身上的开销,幸亏都记了账,她当咱家媳妇就算了,这一走,都得算回来,我早料到会有这一天。”他爸傻了眼,他看了十秒,体内那团火再次窜出来,怒向胆边生、怒不可遏、怒可吞象。
“滚!都给老子滚!”他说。
二
他上了四年班,时间到了,该离开了。
他跟父母说:“爸、妈,从明天开始我就不上班了。”
“你要去干什么?”
“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你怎么能这样?”
“对不起,让你们操心了。”
他知道会伤父母的心,为此他准备了四年、牺牲了四年,现在,他该行动了。
他用工作的积蓄之一部分买了架单反相机,再一部分买了把木吉他,剩下的都当作旅资。他想成为一名摄影师,拍下沿途的风景。
他从老家出发,坐四个小时的大巴取道上海,开始全国之旅。
他拍下外滩欧式建筑圆润柔软的轮廓线;拍下黄浦江上悠然来往的客轮;拍下城隍庙人流如梭的九曲桥;拍下步行街迥然各异的晨昏之变。拍下中山陵白墙蓝瓦的国父祭堂;拍下夫子庙神色各异的吃客面容;拍下秦淮河桨声欸乃的波光浮影。拍下长安街如梦如幻的灯光;拍下天安门肃穆威仪的升旗;拍下长城内外苍茫浮沉的大地;拍下紫禁城百年浮沉的皇家宫殿。拍下布达拉宫的落日;拍下八廓街的晨曦;拍下河西走廊的尘土;拍下莫高窟的壁画。拍下三亚的海、青海的湖、昆明的雨、长春的雪。
他住便宜的青年旅舍,吃粗粝的食物,穿地摊甩卖的衣服,饶是如此,积蓄还是慢慢用光了。那把木吉他派上了用场,他坐在城市马路边,弹起了琴。他的面前摆着吉他盒,不时有行人往里面丢一元五元的钱,但更多的人选择匆匆经过,回头一瞥,将他当作一名流浪汉。他不觉得脸红,他不是在乞讨,而是在卖艺,正如曾待过的单位,靠劳动吃饭。那家单位离他很远了,远得像前世的一个梦,各种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两面三刀、溜须拍马,都变成已逝的一番游戏,入戏时他和别人一样认真,出戏时不过拍拍衣袖,转身离去。他倒是会想念一二同事,工作之余聊聊天,离开后失去联系他也不觉得惋惜,一个人安静地行走,他更喜欢。一天下来,他认真地清点吉他盒里的钱,硬币归一堆,纸币从上到下按照面值大小叠好,摞平整,夹进皮包,拿起吉他盒子,面朝下抖一抖,里面会有一些碎石子,将吉他放进去,合上盖,背上肩,去吃饭。
他凭借弹吉他所得之资,又走了许多城市,后来来到了杭州,正是大冬天,杭州下雪了。他突然很想拍一拍西湖的断桥残雪,那天起了个大早,背上相机,徒步往西湖景区走去。路边行人寥寥,到了白堤,真可谓山水一色,上下皆白,远方保俶塔成一枚芥子。堤上如铺了一层白毯,湖水浩浩渺渺,偶有舟子一二,若隐若现。雪悠悠忽忽飘大了,落在头上、肩上,天地间仿佛只他一人在这纯白的世界缓步而行。他靠近断桥,方才明白所谓的残雪只是文人墨客臆想出来的景致,雪未融、桥未断,寒气袭人。他架好相机,从取景框中看去,孤零零的一座桥,未免单调。他等着,等着什么走进视线,十多分钟后,雪更大了,飞飞扬扬,终于两个人影走进了取景框,是一对老夫妻,步履蹒跚,年龄总有七八十岁。挽着手、带着伞,穿着厚厚的棉衣,从他身后走来,将一对相互依偎的背影呈现在他眼前。当他们走到桥心时,他按下快门,与此同时,心头热乎起来,他想起自己的父母,眼泪渗出眼眶。这次流泪像一道决堤的湖口,将这些日子积蓄心中的意气一股脑发泄殆尽,他意识到是时候该回去了。他想象自己走进家门时对父母喊一声:“爸妈,我回来了。”父母脸上那种久不见的笑容,溢满他心头。
三
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玩伴,后来每年都会抽空聚一次,地点是在“新桥饭店”,这一年,他们又相聚了。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的应对之词,两瓶烧酒,一人一瓶,自斟自饮,话题自然离不开新近的状况。
他问:你还在家打游戏吗?
他说:是的。你已经回家了,不准备往外跑了吗?
他说:是的。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他说:还待在家,除了你,我根本不想见别的人。
他说:长期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
他说:走一步算一步吧,生活真是个狗屁!
他说:是个狗屁!
谈兴渐浓,他们到后来把别的什么也慢慢谈到了。窗外下着雪,他们都喝高了。时间向晚,当他们歪歪斜斜走出酒店大门时,路灯明晃晃地在长夜中点亮多时,街上有匆匆赶路的行人,有披着雨衣骑着脚踏车低头猛踩踏板的人,有汽车、摩托车、電瓶车,共同装点了这个旧历年的尾声。
他们步伐不稳,互相搭着肩,在雪夜长街上走。抵达一个十字路口,他们不经意间看到一家狗肉店。如此光明正大贩卖狗肉的店铺在本镇少有,时间接近午夜,生意还是很兴隆,白炽灯下,一桌桌狗肉爱好者一边喝着酒一边饕餮着。油烟气从开着一道缝的玻璃门内透出来,店门前漾着一条黑乎乎的油水,流向不远处的排水沟。
在隔离带的街树下,他们看到一只狗被一条链子拴在树身上,全身毛发皆白。它竖着两只狼一般的耳朵,四腿站立,双眼散发出诡异的光。雪落在狗身上看不出痕迹,它没有在严寒下瑟瑟发抖,脖子虽被锁链圈住,却仍傲然地面对幽暗的长街。
他们向它走去,他们觉得一条白狗不应该出现在一家狗肉店门前,二者的搭配让他们愤懑。走到白狗跟前,白狗没有叫唤,用眼睛盯着他们,似乎明白来者的意图。他们一人用身子遮着店铺玻璃门的方向,一人用最快的速度解开白狗脖子上的锁链。束缚被卸除后,白狗没有立刻逃走,凑到他们跟前,闻了闻裤子,这才转身,跑向黑夜。
他们也跑了起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好远,停下来,大口喘着气,仿佛做完了一件天大的事,心头充满强劲的力量。
出 走 之 前
我收拾东西,准备出门写一部小说,桌上放着弹簧刀、方便面、指甲钳、巧克力、刮胡刀……这些都是在出门时用得着的。在挑选背包时,一个本子从杂物箱里掉出来,翻开一看,是以前的日记。翻到的一页,记着一件事,文末赫然几个黑色大字,后面是蚂蟥般的感叹号:我要出走!!!
我的思绪一下飞回童年,十岁左右,大年三十晚,外婆家吃团圆饭。为了即将开席的丰盛的菜,我们兴奋不已。我是孩子中最疯的一个,满屋子跑,妈妈叫我,我不予理睬,拉着表弟蹦到椅子上,突然一个趔趄,朝桌子摔下去,只听“哐当”一声,整桌菜,一半掉到了地上。我揉揉屁股站起来,还未定神,脸上落了一记巴掌。妈妈怒气冲冲,揪住我的耳朵骂道:“你就不能安分点!”亲戚们围拢过来,把我拉到一边,我朝妈妈站的地方望了一眼,她也正在看我,又是一句:“你给我滚出去!”那一刻,不知哪来的勇气,我跑出了家门。
我朝晒场的方向跑,心头满是委屈,觉得世上最坏的人就是妈妈,她从来没有关心过我,动不动就打我。我甚至怀疑自己不是她亲生的——我要离开这个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永远不回来,让她后悔曾这么对待我。
这样一想,我就在烟花肆虐的夜空下,大步走去,然而走到村西那片乱葬岗,停了下来,杂草丛生的坟包让我心头涌起一阵战栗,迈不动脚了。我想外面那么大,能去哪里呢?外面没有温暖的床、没有好吃的、没有……这时,迎面走来一个人,是出门打工回来的小叔。他问我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我红着脸答不上来,他拍拍我的头,牵着我的手回家了。回到家,打翻的桌椅已重新归位,屋内一派喜气融融的场景,我发现一个严酷的事实:大人们根本没在意我跑出家的事,更不会想到刚才我内心的那番挣扎——一个孩子的挣扎,他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他们只是聊着天,满面笑容,将方才的事完全淡忘。妈妈看到我,过来拉住我的手说:“快洗洗手,吃饭了。”她似乎也忘了刚才对我的打骂,大人的记忆原来就是这么短暂。就这样,我的第一次“出走”轻描淡写落下了帷幕,很多年后回想起来,不觉惭愧,我想,当时为什么不能走远一点呢?
出走是一种状态,需要勇气和坚决,和我的失败经历相比,那些常年漂泊在外的人是让我羡慕的。我从小就喜欢收集背包客们拍的风景照,小时候有个很要好的朋友,长得清癯瘦小,像女孩子,和我相比,他的经历就“壮烈”多了,高中没毕业,就背上一个包,出走去了。
他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处,就给我寄来明信片。有灯光朦胧的长安街、青天蓝瓦的中山陵、藏羚羊点缀的西藏、大雪纷飞的兴安岭……在我眼里都那么迷人。我不理解他是怎么适应外界复杂多变的环境的,又是哪来的钱?他对我也不理解,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怎么可以忍受长年累月待在一个地方不厌倦!”
这问题后来我想了很久,它的关键不在于厌不厌倦,而是厌倦之后怎么办?那朋友是孤儿,生活只是他一个人的,想去哪里都行。我不行,受牵绊的东西太多,那时唯一的任务只有读书,家有双亲,古时还说双亲在不远游呢。但因那朋友的种种事迹耳濡目染日久,一颗心免不了蠢蠢欲动,总想找个机会,一个人真正去趟远方。
第一次去远方的机会是在高中毕业那年,暑假,休息在家。
高中毕业的暑假真漫长,憋了一整年的高考压力来了个总释放,把所有书都称斤卖掉,和同学们昏天暗地疯了两星期,今天去他家,明天去你家。两星期后,许是压力释放太快,玩得过了头,原本紧绷的发条松弛过度,一天早晨,从睡眠中醒来,盯着天花板,心头突然出现一片很大的空虚,似乎哪里出了问题,事情不该是这样子的,房子犹如一个大铁笼,使我窒息。于是我决定来一场远游,来填补不可抑制的空虚和漫无边际的时间,上网查询一番,最终定下行程,背起背包,踏上长途汽车。
我去的地方是乌镇,车子带我离开熟悉的县城,抵达目的地时夜已深。走进乌镇的牌门,一弯浅水,桨声欸乃,屋檐下一盏盏红灯笼,发出幽幽的光,如棉絮般轻柔。我沿着石板道走,两旁明清时期的建筑在夜色下苍老又清婉。那一刻,我心静如水。
我在那里待了三天,什么都不做,就是逛,晚上靠在木窗旁,望沿街的河水,听舟子的歌唱。三天后又辗转去了西塘,同样是轻柔似梦,多了绵延的烟雨长廊,廊下行人来往如织,摊铺点缀其间。
这次水乡之行,算是我第一次成功的出走,回来后打电话告诉那朋友,他听完却大笑,说:“你那哪叫出走,你只是出门旅游了一趟。”我问他在哪里,他说正在尼泊尔和中国交界处的一个沙漠,和漫天黄沙、陷阱、蝎子作斗争。
这又使我默然,想到“出走”和“旅游”的区别,而那次旅游也原原本本记载在日记本里,上面写着这样的话:“这次出走让我收获颇多,事后想想,这其实不是我心目中真正意义的出走,什么是出走呢?”如果不是收拾行李,我早已忘了还有这本日记的存在,它保存了那么长一段时光,反刍起来,别有一番滋味。我继续翻阅着,想从中找到更多有关“出走”的内容,十几页后,果然又有新发现,是距离“水乡之行”七年之后,时间是一个夏季午后,我大学毕业不久。
毕业后的我,原本想留在讀书的那个城市,它离家乡有四百多公里的车程,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但四处投简历,投石问路,却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万般无奈下还是回了家,漂泊无着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则由于父母的催促,他们不希望我离家太远,儿子总要待在父母身边的。回来后,靠着亲戚的关系,进了一家物流公司,成为经营部的一员。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安排发货计划,没过几星期就感觉枯燥乏味,周身犹如被一条无形的锁链捆住,连大脑都没闲暇的空间,唯一松懈的机会是趁着领导不注意躲进厕所,蹲在便池上,抽一根烟,看着烟圈袅袅上升。一天,我发错一笔货,客户反馈过来,给公司的信誉和销售额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横眉直竖,一拍桌子说:“一个大学生做事还不如中学生认真,有什么用!”
我憋了一肚子气,当天下午,给那朋友打了电话,这次,他在江南某个小山村“休养生息”,听我唠叨一通后,说:“你等着,我来找你。”原以为只是随口说说,不料当晚,他真来了,穿着件褐色T恤,几年不见,一进门,就来了个大拥抱。
然后我们找了个地方喝酒,酒瓶越摞越多,他看着我说:“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不出去。”我说:“我放不下父母,我对他们有责任。”他说:“屁责任,为了责任,你瞧你把自己逼成了什么样子!”我醉醺醺的,在饭店正对着桌子的一面镜子里照了照,一个双目无神、形容枯槁的男人。
“明天你就辞职,跟我走。”他说。
“去哪里?”
“随便哪里。”
我猛灌下一口酒,心底升腾出一股抑制不住的勇气,“行,”我说,“走就走。”
第二天,我瞒着父母辞了职,试用期不用办离职手续,走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我觉得浑身轻松,然后跟着他来到车站,上了一辆开往外省的车,大约三小时后,到了目的地。
是个海岛,一眼望去,岛面全为绿色草丛覆盖,像一条柔顺的毛毯,经风一吹,毛绒轻轻摇动,波浪一般。羊肠小道逶迤如线,我们走到岛的最高点,极目远眺,远处大海一望无际,滚圆的太阳将金光洒在海面,波光点点,海鸥、海船,自由来去。四周是一种巨大的风车,三片梭形长叶,微风下悠悠转动。
当天晚上,我们就地搭了帐篷,海风徐徐,天低云阔,耳邊十里蛙鸣声。我望着月亮,思绪漫游无边,觉得自己仿佛和自然融为了一体,所有烦心事都抛到了脑后。但好景不长,只过了一晚,第二天,母亲就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怎么不说一声就辞职了。我把经过告诉了她,她倒没怎么责备(这使我意外),还劝慰我说:“做得不开心就不做了,工作不怕找不到,但不该这样不说一声就走掉,爸妈要担心的,赶快回来吧。”我说:“再过几天……”声音明显没了底气,她又劝说:“这就回来吧,有什么话,回来再说。”到了这一步,我的心就软了,挂下电话没半小时就收拾行李,跟那朋友说我要回去了。朋友没阻拦,他说他还想玩几天,我一个人能走吗?我说能。分别前,他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玩。”
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像他那样心无旁骛地出走,出走除了勇气外,更多的是一种信念,我的包袱太多,做不到他那么洒脱。幸而那次海岛之行让我的心情平缓了些,这或许是远行带给我的最大作用。回来后,在家休息了一段日子,又去找工作,这次没让父母托人,自己投简历,最终被本地一家旅游杂志社录用了。这工作,虽也枯燥,但比较自由,只上半天班就够,还有一个月的年假,能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打算重整旗鼓、从头再来,为了自己的理想果断向前。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像今天这样,有了灵感和构思,便利用年假外出写一部小说。为实现它,我开始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训练,每天规定写足多少字,日复一日绝不间断。只有在写作中,思绪才能飞驰无界,才能从现实的条框中脱身而出。但技巧可以训练,灵感却时而要枯竭,每当想写而写不出东西时是最痛苦的。一次,我又遇到了这种瓶颈期,兀自坐在屋里抽烟,突然灵机一动,为何不写写那位朋友呢?他的经历我了然于胸,而他的做派最适合成为小说人物,内容自然是和“出走”有关——这些都是现在翻到日记本的后半部才想起来的(我已将原定出门的时间忘在脑后,桌上放着的弹簧刀、方便面、指甲钳、巧克力、刮胡刀……还没全部放进背包。我在窗外透进的阳光下,手捧日记本,看得入了神)。当即我就写了起来,日记本上原原本本记录着小说的全貌(当年我怎么会在日记本上写小说呢)。不止一篇,一气写了两篇。
第一篇,我用大篇幅介绍了他的身世背景后,将重点落在了一场虚构的远行上。那趟远行他孤身一人挺进一座海拔高耸的山脉,在险恶的环境中考验自己的生存能力。那里荒无人烟,山路崎岖难行,一年四季覆盖着茫茫白雪。他背着旅行袋,拄着登山杖,吃光所有配备的食粮后,渴了将积雪捧在手中当水喝,饿了去采摘雪山道旁的野果。后来他遇到一道险峻的山峰,除了攀爬再无生路,他卸去行囊,一步步攀岩而上,爬到半途,一脚踩空,摔下来,死了。尸体被雪花覆盖,从未被人找到。
第二篇,他摇身一变,不再孤身一人,每次出行都有一大帮驴友相伴,大家喝酒畅谈,去的是一些景色如画的地方。一次,他在旅途中认识了一个女孩,因前往共同的目的地而相识,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旅程结束后,他对女孩展开了追求,她让他第一次有了想成家的欲望。半年后,他们在一起,现实问题摆在眼前,他要努力工作,以后买房子,和她结婚。渐渐地,他很少再去远行了,远行需要时间和费用,他变成了一名普通的上班族,过起了普通的生活。
这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文本让我惊异,实际上它们有着本质的相似,就是一个热爱远行、喜欢跋涉的人,最终停止了远行,其一是生命的终结,其一是现实的阻挠。不管怎样,我就这样在两个文本中殊途同归地终止了他的步伐。
想到这里,我突然有些担心,从那次海岛之行后我们就没再联系,算算已有五六年了,他在干什么?我拿出手机,他的号码还存着,想打过去问候一声,还是放弃了。我有一种隐忧,生怕他当真遇到两个小说中描写的情况,现在的我更愿意想象他仍保持当年的模样,背着背包,拄着登山杖,如一名孤胆英雄,行走在充满未知的旅途上,永不停下他的步伐,这样的画面让我感动。
而我自己如今不也习惯了前往远方吗?我放下日记,将它锁进抽屉,所需的东西都装进背包。出门前我看了一眼那个上锁的抽屉,想起那位远方的朋友,我想我们终归还是会见面的,或许在极北严寒之地,或许在某个江南氤氲的小镇。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