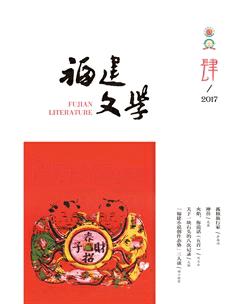雪下了一夜
黄杰,男,1993年出生,福建莆田人,现在上海某高校任职,曾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青年冰心文学金奖、烟台文学新锐一等奖等奖项。在《山东文学》等杂志发表小说若干。
加栋趴在下楼的地方往下看时,母亲歪坐在椅子上,盯着前方,头发凌乱,眼睛无神。
这样的情形已经有四天。在这四天之前,每天母亲都会用廉价的化妆品把自己打扮好,然后出去。加栋原本不知道母亲为何这样,大概是女人天性作祟,便也从不问起。加栋的父亲在外打工,每年才回来一次。加栋对于父亲相知甚少。
加栋又回到自己的小桌前写日记。他有着记日记的习惯。加栋记得以前也有一段时间母亲整日地待在家里。楼底下时常传来叹息声,不久后就变成了母亲整天整天地不在家,家里空荡荡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他能明显感受到家庭的经济状况比以前好了。母亲有次高兴时竟带他去买衣服。他疑问地问母亲:“妈,家里哪来的闲钱给我买衣服?”母亲的脸色忽然一变,尖声道:“咋了,給你买衣服你还不乐意了!”想到这,加栋站起身来,把头探到窗外,呼吸着窗外新鲜的空气。他看见了窗台上躺着一只死去的蟑螂。蟑螂一半的身体悬在窗台外,腹部向上敞开,发瘪的躯体轻若羽毛,黑褐色的翅膀在光下折现一圈光晕,周围的事情都因为它死去而失去了联系。加栋感到感动,他盯着死去的蟑螂看了一会儿,转身从桌子上的本子撕一张纸,把蟑螂的尸体包好,一扬手,消失在了黑夜中。
加栋收进了身子,关上了窗,顺手把墙壁上的灯都关了。他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无言地看着窗外。母亲在楼下抬起头看着早早就熄了灯的屋子,嘴巴很利地骂了句,不知死活。黑暗中的加栋是听见这句话的。
父亲明天应该就会回来。他揉了揉脸上的瘀青,摇了摇头,便蜷缩在自己的小床上。
月光透过小小的窗户洒进一些光芒。
父亲是第二天中午到家的。那时候他还在睡梦中。梦里他年纪还小,父亲牵着他的手去买冰糖葫芦,他把自己黏乎乎的小手往父亲的身上擦,两人都笑了。一晃眼,他长大了,父亲去给他开家长会,然后回来笑着夸奖他,因为他的成绩一直都是很令家长骄傲的。当他被楼下吵醒时,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他辨认出那男的声音是属于父亲的,因为父亲的声音是极为粗犷而又大声的。他没有马上下去,而是听着他们的吵闹声。父亲骂着母亲,母亲先是低声地争辩着,后来也开始尖声吵闹着,母亲的声音很尖利,就像是一把刀。他不用听就知道他们争吵的是什么。
他蒙上头捂住耳朵,被子里只有他的气息声。他忽然想起那个梦。真实的情况是:他的家长会是没有人去参加的,更没人回来夸他。在他很小的时候,也没有人带他去吃冰糖葫芦。在记忆里,很少有父亲的影子,这个男的并没有过多地参与自己的生活。这样想着的时候,他的被子就被人掀开了。
他惊恐地睁开了眼睛,父亲站在了他面前。
眼前的男人没有刮胡子,眼睛红红的,头发乱糟糟的一团,下巴青色一片。他看上去是那么憔悴。“爸爸。”他低声地叫了句。
父亲瞪着他,眼珠子仿佛随时都要掉了下来。
他知道他做的事就像是一把大大的枷锁把父母牢牢地锁住了一样。他就那么看着父亲,本以为他会发作,可是没有。父亲瞪着他,然后眼睛一红,便懊恼地捶了下自己的脑袋就转身下去了。在快下楼梯的时候又狠狠地跺了下地板,发出的那一记闷响吓了加栋一跳。加栋很想问他疼不疼。他是心疼父亲的,可是他不敢。
母亲站在父亲的后面。她看着地板上的碘酒,又尖声道:“怎么,给药还不擦是吧?”
加栋看着地板上的药,这才想起自己的脸上还有瘀青。他摸了摸,说了声:“不用。”
“还想省这个小钱不成。”母亲恶狠狠地说,话语里满是戾气和心疼,他听得出来,“快抹上。”
加栋愣在那里,看着眼前这个已被生活折磨得越来越佝偻的女人。他没想到她每次化好妆出门竟是为了那样的事!他的心里对她是怀有满满的怨恨和责备的。
加栋前一段时间和国煌两人去街上遛玩时,竟看到母亲站在一家旅馆前拉客。母亲站在风中,风簌簌地吹响着。母亲和其他女孩明显不一样,她的年纪大了,这样看起来竟显得有点悲哀。加栋赶紧拉着国煌离开。一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在分道口的时候,他告诉国煌,一定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别人。国煌拍了拍自己胸脯打包票。这是属于年轻人的承诺。
母亲走了过去,拿起地上的红花油,倒在自己的手心里搓着,然后轻轻地揉着加栋脸上的瘀青。他看着母亲,皮肤松弛地耷在脸上,皱纹已是很明显了,眼袋都快垂下去一般,眼睛也是通红通红的,明显哭过。揉着揉着,母亲的眼睛就又红了,眼眶一下子就湿了。她赶紧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嘴里骂了句“孽债呀”,眼泪就掉了下来。加栋伸手抹去了母亲的眼泪,母亲的表情忽然窘迫了起来。
加栋忽然想起,几年前他和母亲一起去菜市场买菜,途中遇见一个阿姨,那是母亲的同学。母亲牵着他的那只手汗津津的,另一只手拉扯着衣角,试图想要把那掉色发皱的衣角扯平一些。母亲窘迫的表情和躲躲闪闪的样子加栋都看在眼里。临走时,那个阿姨说:“你这身衣服也该扔了吧。”母亲一下子愣住了,然后赔笑着说,还能再穿穿,再穿穿。
她也真不容易,他想。
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在楼下叫加栋。加栋原本是在上面看书的,看着看着他就在想自己要怎么样才能赔偿那笔巨款。那笔钱对于其他人家来说可能并不是很多,可是对于加栋家里来说就是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都能把这个家压垮。加栋的父亲跑去外地打工,就因为那儿包吃包住,家里可以省下一笔饭钱。母亲身体不行,只好去站街。每次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安静得都可以听见空气流动的声音。他告诉自己要好好学习才可以对得起父母,因此他的成绩总是很好的。
加栋下楼的时候,父亲母亲都围坐在一个小型的四方折叠桌前。桌上有两道菜和一小碟的肉。菜应该还是买处理的,他知道每次临到收摊的时候,菜价都会特别便宜。那一小碟肉反倒让加栋有点吃惊,特别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加栋有些木然地坐在桌子前端起碗来吃饭。许是许久没有吃到母亲煮的饭了,他觉得今晚的饭特别香。以前每次回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自己煮饭炒菜,然后自己一个人吃。自从出事以来,这些事倒都回到原来主人的手中了。
饭桌上,一家人没有说话,低着头吃饭。加栋忽然觉得发生了这件事也好,起码能够让一家人在一起吃个饭,自己也能够吃上母亲煮的饭。但是这样的想法又显得极为滑稽,因为这平静下隐藏着多大的危机,没人知道。想着想着,加栋忽然就笑出了声。这一个小小的笑声显得极为怪异,就像一个人在苍茫的秋季割麦,满目的金黄在风中发出声音,割麦人在麦海中边挥舞镰刀边捂着嘴笑,笑声转瞬融在地里,融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中。
父亲抬起头来看着加栋,眼睛瞪大得像个圆球,脸上因生气而变得骤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父亲呵道。加栋不言语,自知这笑声是不合时宜的,于是就加快了吃饭的速度好快点回到自己的小屋子里。“到底怎么回事?”父亲把碗放在了桌子上,声音大了起来。加栋知道指的哪一回事,于是就更加低下了头,压低自己吃饭的声音。
母亲看了一眼儿子,看着父亲说:“到底让不让人吃饭了?好好地吃顿饭不行呀?”
“吃,吃,吃,他要吃死我们了,你知道吗?”父亲的声音又大了起来。
加栋刚吃完饭把碗放在桌子上,父亲就把筷子狠狠地扔向加栋的脸,加栋着实疼得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声音。他不哭不闹不言语,只是低下腰捡起掉在地上的筷子,放在洗手池里,然后又重新拿了一双新筷子放在父亲的桌子上,说了声:“爸,我上去了。”就猫着身子爬上了小屋子。
刚上阁楼的时候,他就听见了碗被恶狠狠地摔在水泥地板上的声音,伴随着母亲的咒骂:“要死了这家。”然后就是母亲低低的呜咽声,压低了声的,可是他依旧能够听见。
他坐在自己的桌子前。天黑了,远处的路灯一个个孤独地站着,它们被固定在那里,永远都是有距离的。他忽然觉得,这路灯多么像人呀,无论如何掏心掏肺,总是有着距离的,心里都是隔阂着的,即使这样路灯也尽量让自己发亮,这一点又是和人多么契合。
加栋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他起身对着墙上的镜子照了照,脸上两道红红的筷子痕。他突然觉得委屈,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可他并不怪父亲,真的,不怪他。他趴在楼梯处,看着父亲和母亲呆坐在桌子前,就和吃饭前一样,饭菜满地都是,母亲也不去收拾,一动不动。他皱了一下眉,然后便关上了窗户,拉了电灯,蜷缩在自己的床上。黑色的夜里,他睁着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废柴一样。不是像,就是。
不知过了多久,楼梯处响起了一阵声响,随即他的门就被打开了,他赶紧闭上了眼睛佯装熟睡。父亲轻轻地坐在他的床边。他感觉到父亲还在看他。有很久没有和父亲挨这么近了。父亲的手抚着那两道被筷子打的伤痕。父亲的手粗糙,起茧的指头像一块块树皮从加栋脸上划过,就是这种划过的感觉钻进加栋的心里,他的胸腔忍不住起伏得厉害。忽然,他听见父亲小声地吸了一下鼻涕,喘息声越来越重。他心一惊,他知道是怎么回事。过来好一会儿,他听见父亲叹了一口气,然后转身出去。他摸了摸自己的脸,父亲的温度还在。就在那一刻,他像是看见上方有一只蟑螂盯着,黑色油亮的眼睛滴溜转动,纤细敏感的触角直直地伸向他,这一切他在黑暗中看得清清楚楚。
他猛地下床,他的脚下有一小摊湿迹。他忘记了蟑螂,趴在地板上,手在地上摸索着,有几滴水。加栋将自己的脸贴在水滴上,湿迹越变越大。
学校来电话让加栋去学校收拾自己的东西。加栋的班主任很喜欢他,因为他总是能够争来各种各样的荣誉,而且他还听话,有梦想,这是班主任写在学生手册里面的评语。办公室的老师们每每说起学生的时候,都要说到吴秋梅班的加栋。吴秋梅对加栋的疼爱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她时不时地送给加栋一些课外书。加栋喜欢文学,两人经常会就一些文学问题争得面红耳赤。那件事后,吴秋梅也是多次请求校长不要开除加栋,可是事情很严重,非开除不行。
这是加栋这么多天来第一次出门。弄堂里混合着下水道的味道,街道两旁满是垃圾,苍蝇纷纷往上面扑。
加栋再次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事情发生的第五天了,这五天里他都没有出门,除了睡觉、发呆就是看书。在事发的前一天,加栋还就“零度叙述者”和“叙述者参与写作”哪个更好的问题和吴秋梅讨论了许久,两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吴秋梅对班上学生的解释是模棱两可,可是一和加栋一起讨论就有了更加鲜明的观点。放学的时候,加栋回到教室,那节数学课他们分发试卷。国煌是数学课的科代表,他和加栋两人打赌看谁会考得更好。结果试卷发下来,先是发了国煌的卷子,加栋看了一眼国煌的卷子,他说:“考得真不错。”国煌也笑了笑说,还好。加栋拿到自己的卷子时,只看了一眼便收了起来。国煌凑了过来,笑嘻嘻地问考了多少。加栋说:“还好。”国煌听着就管加栋要,加栋把课本装进书包里,国煌看见他夹在课本里面的卷子,便去抢,等看到分数时,国煌就傻了眼,自己整整少了加栋六分。
加栋看着国煌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便伸手把卷子拿了回来。“下次再继续努力吧。”他说。这话本是鼓励他的,可是在这个两人做赌约的条件下反倒觉得奇怪了,有点儿讽刺。国煌脸一红一白的,加栋也觉得不对劲,只好堆着笑脸把手搭在国煌的肩膀上说:“这次我走运罢了。”这样的解释反而越来越乱。国煌一手打开了加栋的手,骂了句狗娘养的。伸手不打笑脸人,骂人不骂父母。加栋的火一下子就升了起来,也反唇相讥着。国煌骂着骂着就把加栋母亲站街的事给抖了出来,两人接着就打了起来。局势一会儿就分了出来,国煌被加栋按在地板上,加栋站了起来。一切万恶的根源就在这里,在加栋转身走时,国煌在地上抓住加栋的脚往后一拉。加栋一个踉跄,手往后一挥,这时在加栋旁边的课桌一下子就倒了下去,砸在了国煌的头上。血忽然像水一样从国煌的脑袋里涌了出来。
这样想着,加栋已经到了教室。他走进教室的时候已是下课。他的座位被人从第一排搬到了最后一排。他在后面收拾着书具,全班的同学没有一个理他的。收拾完出教室的时候他竟还闻到了空气里飘来的血腥味。他原地站了会儿,缓了缓神。快下楼梯的时候,忽然想起,该去给吴秋梅老师告个别。于是折身回办公室。他看见老师还在安静地伏在桌前写教案,也不去打扰,就站在门口。旁边有老师发现他,就提醒她。吴秋梅一見他就愣住了。
她面对着这个学生,是心疼的,可是她又帮不了他。她站了起来,快步向他走去。吴秋梅一下子抱住了他。师生两人也不言语,只是拥着。忽然吴秋梅趴在加栋的耳朵说了句“对不起”。加栋愣了一下,然后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老师,我还是不喜欢零度叙述者,因为那样子人物都是被操控的,对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一点儿感情都没有。”说罢就走了。
吴秋梅老师木然地站在办公室门口好一会儿,一动不动。
加栋在校门口的时候被人堵住了。
一群人把加栋拖到了一个胡同里,一阵暴打。有人踢他的小腹,有人踹他的腿,也有人使劲地踩踏着他的手,他就像是一只流浪狗让人随意蹂躏着,觉得疼极了却没有一丁点儿的反抗。他看见墙角处有一只蟑螂停住脚步看着他,他牵着自己的嘴角笑。他感觉到自己的嘴巴里的血腥味,一恍惚又看到了那个血腥的下午。他想,国煌当时会不会也那么疼?加栋蜷缩着身子,像躺在自家的床上,慢慢地向有墙的那个地方移去,因为他觉得靠着墙会让他的疼痛减轻一些。
在那群人离开的时候,加栋翻了下身子。他抬起头看向天空,天空灰蒙蒙的一片,像一块布一样盖住了人间。忽然间就下起了雨来了。加栋觉得有一团气体就要在他身体里面爆炸开来,他在雨中哭了起来,他哭喊着,接着又变为了号叫,声音在大雨中仿若静音。这么多天来,这是他第一次痛哭,他告诉自己不要哭,要坚强,可是他再也忍不住了。他总感觉有一股气体堵在他的胸口,让他喘不过气来。他任着雨水打在他的身上,他的眼睛空洞洞地看着天空,雨水落进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生疼生疼的,开出了一朵朵水花。他挣扎着把散了一地的课本都捡了起来,然后沿着墙走到垃圾桶旁,全扔了进去。
雨停了,他的额头处还在不停地流着血,暖乎乎的。他的心里忽然有了个想法,“咔嚓”一声,仿佛有两个世界在那一瞬接轨了。
他在雨中笑了起来,越笑越大声。血水从他的脸上滴在他的衣服上,浑身湿漉漉的。一路上频频有人向他回头,却无人上前。
他不管不顾地回家,他只想快点儿回家,他冷极了。给他开门的是母亲。母亲一见他这样就尖叫了起来,父亲紧跟着过来,然后父亲赶紧把加栋的手搭在自己的肩上想扶着他进屋。父亲突如其来的关心让他一惊,他随即甩开了父亲的手,一点点的温暖都足以使他留恋。父亲一愣。
“你不是很有能力嘛,怎么不打回去呀?这个时候就变成龟儿子了呀!”
父亲的声音在背后响起,加栋觉得父亲真是搞笑,骂他是龟儿子那不也等于是骂自己吗?但他听得出里面的偏爱。他依旧不管不顾地上楼,母亲也要跟着上楼,却被父亲拉住,父亲朝她吼了句:“死不了。”
死不了的,他也知道。只是那一笔赔款可以让全家人死。
他脱了衣服后,便直接倒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他太累了。
梦里,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蟑螂,国煌全身血淋淋地走向他,额头上凹进去了一个大大的洞,还在不停淌着血。黑夜仿若黑水涌了过来,他的梦里黑色一片。他站在角落里,黑水无论如何也冲不到他这儿来。忽然,一匹和水一样的黑马冲进了他的梦里,国煌的头不断地被马蹄践踏着,他只能用自己的触角去顶那匹马。水马上将他淹没,他尖叫着醒来,窗外已是白天了。
他挣扎着起来。站在镜子前,他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眼睛旁边有一道长长的口子,眼圈全黑了,脸上满是瘀青。他又躺在了床上,看着窗外。
从那天起加栋的心就开始变得宁静了下来。有时他还会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笑出声来。他坐在桌子前又开始写日记了。忽然他想起来什么似的,他拿起自己的日记。他的日记是散页的,没有装订在一起。他把自己的日记本放在楼梯口处的一块木板上。他觉得那样子很好,因为那里有着他的梦想,他的未来。他把它们放在那里,让它们悬空着,像是有意为之,又像是无意为之。他将那天他看见母亲站街写的那张纸抽了出来,然后点燃它。
火迅速地席卷那张纸,金黄色的火像是一条条蛇,泛着蔚蓝色的光,纸慢慢地蜷缩了起来,猩红色的光块逐渐变得灰暗,然后聚集、变小、掉落在地,碎成一块块小的灰烬。加栋闻着空气里烧纸的味道,他越凑越近,灼热感扑向他的脸面,太过力了,那些烟竟然把他呛出了泪来。等他扔下最后一小块纸的时候,手烫了个泡。纸在空中打了两圈,坠落在地。
那晚,加栋下楼吃晚饭的时候,忽然手肘碰到了日记本,日记本竟像是下雨一样下了起来,他着急地下去赶紧把纸片都捡了起来。父亲见他这样,也捡起了一张来看,上面写着:
“我不想要住在这里。这里太吵了,我都看不进书。我想要住进一座大房子里,里面有着很多的书,安静极了。我每天都可以看书,不用被人吵……”
那是出事前几天。
加栋走到父亲的前面,等着父亲把那张纸还给他。父亲看着眼前这个整天跟个没事人一样的人,不由得来气,他把那张纸撕了,撕得碎碎的,砸在他的脸上,“还想要大房子,你杀了你老子吧!”
你杀了你老子吧!你杀了你老子吧!父亲的声音在安静的空间里一直不停地回响着。
加栋的眼神像小鹿一样慌张。他突然觉得自己这个梦想听起来是那么的让人臊。他连忙伸手去抓那些还在空中飘舞的纸片,想要把它们紧紧地抓住。父亲大声厉喝,唾沫星子溅到了他的脸上。他弯下腰去捡,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小块一小块的都捡了起来,夹进了本子里。
全都乱了,他心里想,然后像兔子一样抱着他的日记本回到了楼上。等下楼吃饭的时候,母亲已经把饭盛了出来,父亲正坐在桌子前揪着头发捶打着脑袋。他怅然若失地坐着。
“你这又是怎么了?”母亲问。
“有点儿困。”他说。
“整天都在睡觉,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还在睡觉。”母亲开始咒骂道。
他低头扒着饭。
饭桌上,母亲和父亲说她没有借到钱,大家都不肯借她钱。父亲也摇了摇头,抽着烟。加栋这时发现已经戒了烟的父亲又开始抽起了烟。街坊邻居看见我就躲开,大家一到这个时候就都有难处了。母親红着眼圈说。
“别借了,我有办法。”加栋忽然抬起头说了这么一句话。
母亲警惕地一下子抬起头问:“你有什么办法?”
加栋看着母亲这个样子忽然觉得很是心疼。她已经很辛苦了,可是每天都还得拉下脸面出去,明明大家都不是很想理她,可是她还得堆满笑容去讨好每一个人,那笑容就像是贴在脸上一样,贴久了看起来都皱了。他的心紧了一下。
“哦,没。”然后又低下头吃饭。加栋觉得这个情况自己闭嘴会好一点。
父亲和母亲一下子就都愣了。“哼,你刚才不是有办法吗,怎么又没了?”父亲说。
“你没办法你说什么呀!你要谁去解决这天大的窟窿呀!你这是要作死我们呀,我们这是做了什么孽呀!我们从不和人吵架,也不骗人,不干伤天害理的事,老天这是不长眼呀!”母亲又开始哭诉道。父亲只是看着。透过浓浓的烟雾,加栋看着就在对面的父亲,竟那么模糊,好像又回到了从前一样,爸爸不在家,妈妈不在家,就他一个人在病恹恹的灯光下吃饭。
在出事的第七天,已经飘起了小小的雪花,白茸茸轻飘飘地在路灯下飞舞,像是某种祭祀仪式。歌声从遥远的天边传来,雪花跟着伴舞,黑夜变成了黑水涌来,雪花都被染黑了,黄色的灯光也都变黑了。加栋的父亲和母亲病恹恹地坐在昏黄的病恹恹的灯光下。加栋在自己的阁楼上写日记。他看着窗外,然后笑出声来。父亲和母亲听见笑声,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看了一眼楼上,又都低下头,彼此无言地坐着。这时加栋母亲把手伸了过去,放在加栋父亲的脸上说,一切都会过去的。
加栋想,可以提前几天实行了。这么想着,他舒了一口气,好像看到了曙光一样。这次他无声地咧开了嘴笑,这么多天来,他第一次觉得这么轻松。
他打开了窗户,看着细细的雪花漫天飘开,等过几天雪大了该就会像樱花花瓣一样,白净而且轻柔。这样一想,加栋就觉得自己就站在樱花树下,抬起头,樱花在空中飘飞,像在跳着曼妙的舞姿一般,落在肩膀上,香味渗入了皮肤里,一丝一丝沁入心脾。他把手伸出窗外接些雪,又咧开了嘴。
吴秋梅到加栋家的时候,加栋还在睡觉。母亲在楼下叫加栋下来,加栋揉着自己的眼睛下来,看见老师笑着站在楼下。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衣服,就驚得一下子又跑到了楼上去。他是穿着睡衣下来的,怪不好意思的。母亲和老师这时“扑哧”一声笑了,加栋刚刚的行为太可爱了。这个家好久没有这样的笑了,这些天来就像是一潭死水,死气沉沉的,没有新生儿的喜悦,也没有搅动的新鲜。
加栋再下来的时候,他听见母亲在和老师商量着看学校可不可以给一点钱补助他们。加栋默不作声的过去,在旁边听着。加栋看着老师在旁边尴尬了,他知道老师也难做,便把老师拉到门口去。在门口处,老师从包里拿出了一本书给加栋。“加栋在家里也要看书,这样子才可以充实自己。”说完,笑了笑。
加栋看着老师笑,也跟着笑了笑。他站在门口和老师说了一会儿话。老师捋了捋加栋额前的头发说:“委屈你了,加栋。”
加栋笑了笑。“老师,我妈妈和你说的事你听听就算了,别在意。”
“可是……”
“老师,会好的。相信我。”加栋握着老师的手。
“那你有需要的时候要和老师说,老师会尽力帮你。”
末了,老师和加栋拥抱了好一会儿。吴秋梅要走的时候,加栋说:“老师,谢谢你!”吴秋梅也心疼这孩子,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连忙转身离去。加栋在后面大喊了声,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这句话吴秋梅是听见的,可是她没有应答。
加栋拆开老师送给他的书。吴秋梅在书的扉页上写着“永怀希望”四个字。
他笑出了声。再过几天就会下大雪了吧,加栋抬起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
晚上吃饭的时候,父亲骂了句娘了个天气,又降温了,冻死我算了。父亲刚在家里坐下不久,家门口就站了一大堆男人,他们像是有预谋似的都站在门口。加栋母亲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父亲随即就挡在了母亲的前面。最后一个进门的是国煌的母亲。
国煌的母亲一进门就说:“钱呢?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一分钱,你们到底赔不赔钱!”
加栋的母亲弓着身子赔笑说:“姐,我们真没钱了,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几天,过几天,我一定把钱凑齐了。”
国煌的母亲轻笑了声:“过几天?我儿子还躺在医院里需要钱呢。”她轻挥了下手,一群人就围了进来。
加栋的母亲向他们喊道:“你们要干吗?我要报警了呀。”那些人还没等她说完就开始把他们家的东西全都砸了。父亲冲上去阻止,他们粗野地乱扔家里的东西。每个房间里都是一片狼藉,不成样子,而且门口处还陆陆续续地有人进进出出。
“你们这是犯法的。”母亲向他们吼道。他们置之不理,继续干着他们的事。加栋站在旁边看着眼前的一切。母亲走到电话旁,要打110。这时国煌的母亲说:“你打呀,我儿子现在还躺在医院里,看看警察会抓谁?”她的话刚说完,一个男人就抄起手中的棍棒猛地向电话砸去,电话机“哐”的一声全碎了。
母亲冲上去拍打那个男人,那男的刮了母亲一个耳光,还往母亲的腰腹踹了一脚,男人劲儿大,她往后退了几步,就跌在了地板上,嘴角流出了血。加栋看着,他觉得自己的世界都快爆炸一般。他冲上去冲着那男人就是一拳。
忽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母亲一见到他就变了脸色。“原来是你这个臭婊子呀,倒是挺有能耐生出那样的龟儿子呀!”那男的话语愈加难听,“床上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这般能耐……”这时母亲竟像疯了一样尖声厉叫。加栋自是听出了这话的意思了,他不能让任何人在这最后的时刻再往他的家里放一根稻草,他想永远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他猛地朝那个男的扑了过去,那男的一脚踹在加栋的小腹上,加栋一下子就摔在地板上,疼得直打滚。
“你们这是要干吗,非得把我们逼死啊!”母亲伏在地板上拍打着地板哭喊。
一听到母亲的话,加栋笑出了声来,有那么一刻他看见了成群结队的蟑螂像洪水朝他涌来。他想要护住父母,于是张开双臂。一群男人围着加栋,母亲竟也一下子扑在加栋的身上。男人的脚落在母亲的身上,她痛苦呻吟。父亲听见母亲的声音,他也一下子扑倒在母亲的身上。他们都护住了彼此。一群人围着他们三个人。母亲趴在加栋的身上,父亲趴在母亲的身上。
加栋心里的绝望一下子膨胀到了极点。瓷砖冰凉的气息钻进他的胸膛里。
忽然,一双坚硬的皮鞋踢中加栋的太阳穴,加栋觉得脑袋里一片空白,嗡嗡地,好像下一秒会死了一样。他的头脑昏沉沉的。
“你们这是要我们死呀,要我们死呀。”这是加栋最后听见的声音。
等到加栋醒来的时候,家里一片狼藉。母亲头发凌乱地披散着,双眼无神地怀抱着他,父亲满身血迹,倚在另一边,独自一人。加栋的双眼扫视着四周,他觉得时候到了。
他伸手碰了碰母亲的脸,对着母亲一笑。母亲哆嗦了一下,然后紧紧地抱住他。
父亲也哭着过来,搂住了他们俩。他们三个人都哭了,像是受伤的野兽,舔舐着流血的伤口。
他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那一刻,加栋却觉得异常平静,仿佛身体里的液体都已流盡,宛如那只干瘪的蟑螂,所有的痛苦和不幸都跟着切断不再联系。一切都到了尽头。
夜深了。外边气温直降。
老师,你说要永怀希望,可是希望是什么?我再怀着希望,这个家也要没了。
加栋坐在自己的窗前。他看着窗外竟下起了大雨。黑色的水涌了过来,像是要把什么都淹没了一般。紧接着,又下起了雪,雪都变黑了。他看见一切都变黑了,水的声音一声又一声地响着,涌了过来。他似乎看见了一条路,那么长,那么黑,一直沿向远方。
这一天晚上,谁也没有注意到,加栋的楼上格外冷。
第二天,加栋的母亲叫加栋吃饭的时候,加栋没有回应。刚上楼梯,母亲忽然撕心裂肺地尖叫了起来,手肘一甩就碰倒了加栋放在楼梯处的日记本。纸纷纷扬扬地飘了起来。
父亲拾起了日记的封皮,上面写着:
“……这个家已经为我付出了太多了,我不能再拖累这个家。等我死了,爸爸妈妈就不会再那么累了,就不会再有人上家里来胡闹了,这笔债务就可以停止了。爸爸也可以和妈妈在一起了,如果我还能看见他们的话,我也要偷偷地和他们在一起……”
父亲的身子猛地一颤。
等他冲上楼的时候,加栋已经死了。加栋自己割的手腕,嘴巴用一条毛巾堵住,他的手放在水里,让血慢慢地流,反倒没有了知觉,就像是生活。脸盆里的水因为冷,结了冰,猩红色的一片。
窗外,地上积满了一层凋落的厚厚的白色花瓣。
昨夜,下了一夜的雪,天空灰蒙蒙的一片。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