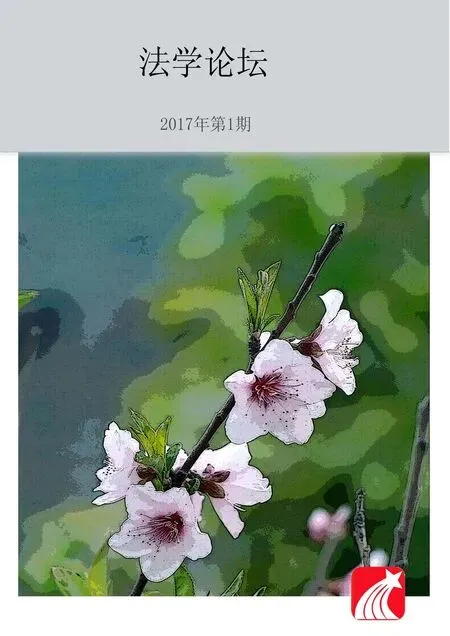我国应诉管辖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张 宇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我国应诉管辖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张 宇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应诉管辖制度在我国民诉法和司法解释中规定较为具体,但从制度配套的角度来讲,与“伪立案登记制”和移送管辖制度在法理和逻辑上存在较大冲突。这会引发限制应诉管辖适用及诱使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冲击正常诉讼秩序。解决之道是废除“伪立案登记制度”,并改“职权移送管辖”为“当事人申请管辖”。对于“法院告知义务”这一适用要件,保持不增设之立场。保留现有应诉管辖规定位置,同时针对应诉管辖具体适用过程中的问题一一予以明确。这种重构保证应诉管辖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良好运行。
应诉管辖;“伪立案登记制”;移送管辖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127条正式确定应诉管辖制度,《〈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223条提供了应诉管辖的适用标准。然而应诉管辖制度在实施后除引发众多理论争议外,*应诉管辖规定后所引发的理论争议主要有应诉管辖是否为默示协议管辖、与明示协议管辖制度关系如何。针对协议管辖是否能够包容应诉管辖的争议,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以王福华教授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协议管辖应包含着应诉管辖统一规定,参见王福华:《协议管辖制度的进步与局限》,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另一种以刘学在教授为代表的观点应区分规定应诉管辖和协议管辖,参见刘学在、孙曦晖:《合意管辖与应诉管辖之再探讨》,载《时代法学》2013年第6期。实践中也存在适用标准不统一现象。应诉管辖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因配套制度的冲突而致该制度名存实亡,分析该制度被架空原因以解决问题是应诉管辖广泛实践适用的必然前提。
一、应诉管辖真的存在吗?
民诉法第127条第1款按文义解释,被告一方当事人本因受诉法院没有普通地域管辖权而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纠正一般地域管辖错误,进而保护自己管辖利益。因此,应诉管辖以存在一般地域管辖错误为前提,这点并不存在争议。但是在我国民事诉讼采职权进行主义的模式下,一般地域管辖错误在立案受理阶段和审前准备阶段通过职权纠错的方式往往直接被消除。*这里管辖错误一般包括专属管辖错误、级别管辖错误、专门管辖错误及一般地域管辖错误。其分类依据是各种管辖制度所确立的依据及意义不一。在立案受理阶段直接排除一般地域管辖错误,是我国立案制度将管辖正确作为案件受理条件的组成部分。若是存在管辖错误,法院直接以不符合起诉条件裁定驳回起诉。在审理准备阶段,若是发现存在管辖错误的情况,法院会通过职权移送管辖制度纠正这种一般地域管辖错误。针对前者,特别是新民诉法司法解释及最新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立案规定”)确立了我国已经属立案登记制度。*该制度是应《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要求,在新民诉法司法解释与《立案制度规定》中的具体落实。然而针对其具体条文进行分析和对比之后,我国所谓的立案登记制度并不符合大陆法系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构成理论的要求,笔者将其称之为“伪立案登记制度”。*早在新民诉法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张卫平教授就曾指出了行政诉讼法在落实立案登记制度这一《决议》,并针对民事诉讼立法规定方面落实《决议》的这一要求的担忧,参见张卫平:《民事案件受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下面采用法规范分析方法分析我国现有立案受理的相关规定,以验证“伪立案登记制度”与应诉管辖制度适用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民诉法解释第208条是民诉法第119条和124条共同确定登记立案的条件性要求,即起诉条件,而立案规定第4条具体为民事起诉状的记载内容要求。根据上述规定,我国的起诉条件还是与2012年民诉法未修改前的情况一样而包含四个基本条件,其中就包含案件必须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民诉法第124条第4款和民诉法解释第211条规定,法院在受理当事人诉求时,必须审查其是否满足起诉条件。管辖作为其中一个起诉条件,法院若发现存在错误则会产生一个告知义务。该义务的存在使得法院针对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进行实质审查,并且要在案件受理或相应时间段内完成。*针对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的规定,与下文将要探讨的移送管辖实为同一制度,这里不再赘述。法院的审查和告知义务属于公法义务,也是法院必须履行的职责。假设法院在这两种职责行使中做到尽职尽责,完全不存在管辖错误而受理的案件*这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实践中很难实现。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上述提到的应诉管辖规定被架空的情形,其适用前提也就不复存在。换言之,将有管辖权作为法院立案审查的一个条件,与应诉管辖这一弥补不存在管辖权的一般地域管辖错误的作用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不可调和冲突。
大多数学者认为解决该矛盾的途径是改现有的立案审查制为真正的立案登记制。*参见王福华:《协议管辖制度的进步与局限》,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但从现行立案受理规定看,我国离真正立案登记制还有差距。那么,通过真正立案登记制度消除其与应诉管辖制度的冲突并不可行。此时,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径只有两个:一个是放任应诉管辖基于“伪立案登记制度”而被“架空”的后果;另外一个是改革现行立案制度,消除应诉管辖被架空的“原因”。孰好孰坏,需要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立法价值整体取向及民事司法实践需求而定。下文将具体比较两种思路的优劣之后再行选择。
若法院在案件受理后发现存在管辖错误情形,法院应该通过职权移送管辖制度予以纠正。职权移送管辖适用前提与应诉管辖有交叉之处,即存在一般地域管辖错误的情形。除此之外,专门管辖错误、专属管辖错误及级别管辖错误也是职权移送管辖的适用前提。在职权移送管辖适用中,法院具有管辖错误审查和纠正义务。那么,在一般地域管辖错误的情况中,法院就可能存在适用移送管辖和应诉管辖制度两难的境地。为纠正该逻辑上的两难境地,学者纷纷提出自己观点:一种观点是废除职权移送管辖,改为以“初步心证公开”为前提的依职权指出一般地域管辖错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另一种观点是根据两种管辖制度适用的时间段不同进行技术化处理,合理协调两者逻辑冲突。两种观点孰优孰劣尚无定论,第二种协调方法是否能真正消除移送管辖制度与应诉管辖制度的逻辑冲突还不得而知,有待进一步分析。
应诉管辖与立案受理制度以及职权移送管辖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中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即便民诉法确定了应诉管辖制度,但基于该种冲突导致应诉管辖规定适用中必然被“架空”。加之民诉法规定该制度的位置所引发关于应诉管辖制度具体适用的各种争议,使得应诉管辖规定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何去何从变得扑朔迷离。为避免这种后果出现,学者纷纷进言献策。大部分观点都主张需要针对现有的应诉管辖制度配套的立案受理制度和移送管辖制度进行改革,但对具体改革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又都莫衷一是。笔者以为,在众多建议之中做出一个符合立法和实践需求的选择应该慎之又慎。为此,我们可参考与我国同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例。其次,笔者以为应该明确应诉管辖制度本身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把这个价值目标作为处理应诉管辖与相关联制度关系、应诉管辖具体实施措施等问题的原则性规定。
二、应诉管辖的域外实践——基于立案登记和移送管辖制度背景
影响我国应诉管辖制度司法适用的事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应诉管辖与相关配套制度之间的关系决定应诉管辖具体的适用空间;第二个是应诉管辖的适用条件决定应诉管辖具体司法适用。这两个层面问题是应诉管辖司法适用主要决定因素。因此,笔者从这两个层面具体考察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应诉管辖制度。具体以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应诉管辖与立案受理制度、移送管辖制度关系和应诉管辖的适用条件两个方面进行比较法的考察,以求得可供我国应诉管辖制度参考的比较法资料。
(一)德国法上的应诉管辖制度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9条*第39条内容是“在第一审法院里,被告不主张管辖错误而进行本案的言词辩论时,也可以发生管辖权。但未依第504条的规定而告知时,不能适用本条的规定。”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丁启明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规定了“由于不责问而生的管辖”,即是应诉管辖制度。若清楚考察德国应诉管辖的具体适用还需要详细考察德国所采用的立案制度和移送管辖制度,因需探究德国的立案制度和移送管辖制度中是否具有消除管辖错误这一程序瑕疵的功能。
首先,要考察德国的立案制度。《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1条第一款*第261条第1款内容是“诉讼案件于起诉后即发生诉讼系属。”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丁启明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0页。之规定其实就是德国的立案制度全部,即源于德国的诉讼系属制度。德国的诉讼系属是诉状满足形式要件要求便可达到案件由法院接受,诉讼程序便因之而启动的一种程序状态后果。在诉讼系属过程中,德国法院并不对诉状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而针对其记载内容是否符合形式要求进行审查。从德国的起诉条件来看,其并不包含诉讼要件,而为单纯的起诉形式要件。按照我国民诉法理论话语体系,德国的立案制度是真正的立案登记制度。从这个角度讲,德国的立案制度与德国的应诉管辖制度并没有关联,因为德国的立案制度并不具有消除案件管辖错误的功能。
其次,需要考察德国的移送管辖制度。在德国民诉法理论和实务中均将法院的管辖作为诉讼要件对待,该诉讼要件属于法院审查诉之合法的事实。法院将诉讼要件作为职权调查事项对待,不论当事人态度如何,诉讼系属法院均会对案件有无管辖权进行审查。这一职权审查原则在一审之中绝对适用,二审只针对一审不当拒绝管辖进行纠正,所有的管辖权审查必须在最后一次事实审理之前结束。*参见[德]罗森贝克:《德国民事诉讼法》,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239页。管辖权的审查后果无非两种,一种是法院无管辖权,另一种是法院有管辖权。后者当然无疑问,然而无管辖权则处理的相对比较麻烦,其中就涉及到了德国的移送管辖制度及应诉管辖制度的配合。依据审查结果,德国法院应该将无管辖权的事实告知原告和被告,然后依据原被告的诉讼行为具体处理。此时被告可以进行无责问的应诉答辩,使得法院取得管辖权。而原告也可以主动申请法院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原告的这种申请其实就是德国的移送管辖制度。德国的移送管辖并没有主动依据职权启动,而是依据原告方的申请启动移送管辖程序。需要明确的是,德国法上并没有明确应诉管辖和移送管辖制度适用的次序问题,笔者以为这并不是立法者的漏洞,而是根据一般立法意,原告起诉肯定具有选择管辖利益的优先性。因此,在无管辖权时,原告申请移送管辖和被告应诉管辖并存时,移送管辖当然优先适用。
最后,需要考察德国的应诉管辖制度具体适用条件如何。根据德国法相关规定,应诉管辖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要件,即法院主动告知管辖错误的要件、被告不责问而参加实际诉讼辩论的要件及应诉管辖只适用于财产性案件。这三个要件决定了德国应诉管辖制度的具体司法适用,而上文分析的德国立案制度及移送管辖制度决定了德国应诉管辖制度的适用范围。*德国法上针对存在的专属管辖错误需要在法院审查发现时主动移送,而级别管辖错误却和一般地域管辖处理一样处理,即适用移送管辖或应诉管辖制度来消除级别管辖错误。
(二)日本法上的应诉管辖制度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2条*第12条内容是“被告在第一审法院中不提出违反管辖的抗辩而对本案进行辩论或者在辩论准备程序中不提出违反管辖而进行陈述时,该法院则拥有管辖权。” 参见陈刚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2006年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规定了应诉管辖制度。然而清楚考察日本应诉管辖的具体适用,还需要具体考察日本所采用的立案制度及相应的移送管辖制度如何适用后才能确定。首先,针对日本立案制度考察需明晰日本的起诉条件。日本的起诉条件具体包括诉状中必须写明必要记载事项、按照规定缴纳手续费及诉状送达于被告。这三个要件是法院审查当事人起诉是否合法的依据,并未包含关于管辖的事项。日本民诉法将法院享有管辖权作为法律方面诉讼要件进行的要求。若法院不具管辖权这一诉讼要件,则该诉将以不合法而被驳回。然而这一管辖权事项的审查确实在诉讼系属之后由审判机构进行,而没有单独的立案机构进行审查。所以,日本法也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立案制度。起诉行为引起的起诉条件的形式审查就是我国民诉法理论话语体系中的立案登记制度。其次,在诉讼要件管辖权事项的审查之中,法院若发现存在管辖错误,应依职权或者申请进行移送。职权移送时应听取原告的意愿,特别是存在多个管辖权法院时,应该尊重原告的意见。若案件在未被移送时构成应诉管辖,此时就会形成职权移送管辖与应诉管辖制度的冲突。因为日本法并没有明确哪些范围的管辖错误属于职权移送,哪些范围属于当事人申请移送,而将职权移送和当事人申请移送混用。但从日本的移送管辖制度多是征求原告意见而为之的角度解释,或许可以借鉴德国处理方法,以原告意见为主的申请移送管辖则较具有正当性。日本法院在发现管辖错误时,除了属于专属管辖错误的职权移送外,法院并不具有管辖错误告知的义务。因此,日本的应诉管辖制度也并没有法院告知管辖错误存在为前提要件,同时,其适用范围也没有类似德国限制为财产案件。*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7页。
(三)我国台湾地区法上的应诉管辖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的应诉管辖又称为“拟制的合意管辖”,规定在《台湾民事诉讼法》第25条*第25条内容是“被告不抗辩法院无管辖权,而为本案之言词辩论者,以其法院为有管辖权之法院。” 参见http://www.doc88.com/p-3902945635115.html,2016年7月21日访问。。关于应诉管辖制度与立案制度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台湾地区和德国、日本之规定一样,即都采用真正立案登记制度作为诉讼的开始,此过程并没有管辖错误消除的功能。管辖事项的审查都在审前阶段进行,若法院发现无管辖权,则依据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裁定移送于其他管辖法院。从此处看,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与日本规定基本类似,同样存在应诉管辖和职权移送管辖适用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而我国台湾地区的应诉管辖适用条件和日本法基本一致,不包含法院职权告知管辖错误这一前提要件,这里不再赘述。
(四)“德国模式”与“日台模式”比较
通过上述比较法资料介绍可以知道,德国的应诉管辖及配套之间关系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迥然相异,大致表现为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德国法上多处法院需要针对案件有无管辖权的审查后果告知当事人,包括告知被告作为应诉管辖适用条件;第二个是相对于日台模式,德国法上没有职权移送管辖制度。这两点区分主要说明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德国法更为注重当事人程序利益的保护,特别是在管辖裁量权的行使之中;二是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除关注法院职权决定因素外,更注重的是职权移送管辖制度与其民诉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虽然三个国家或地区的民诉法关于应诉管辖及配套制度规定中存在些许差异,但以起诉条件作为立案的唯一程序性标准的真正的立案登记制度应作为应诉管辖配套,属于基本共识。这点对于我国民诉法及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的“伪立案登记制度”和应诉管辖制度的配合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在学界广泛探讨立案登记制度的同时,也有学者已经意识到将管辖审查作为案件受理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已经影响到应诉管辖制度的适用。*参见郑涛:《应诉管辖适用之探讨》,载《时代法学》2015年第6期。
三、制度不配套引发我国应诉管辖的实践难题
通过比较法分析可明确,我国的应诉管辖及配套制度要比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制度复杂一些。但制度的复杂性并未随之带来优越性,相反许多制度的设计本身之间相互矛盾导致制度应用中漏洞百出,制度弊端非常明显。
首先,立案阶段因无管辖权而不予受理的裁定制作随意,当事人程序参与不足。相较于大陆法系国家中的管辖事项审查机构都仅限于审判机构的情况,我国的管辖事项的审查机构除了有审判部门外,还有立案部门。实践中,立案部门存在着饱受诟病的“立审不分”问题,而且其享有的管辖事项审查权、管辖错误消除权等职权,其自身正当性也令人质疑。纵观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通例,关于管辖权之调查都是依职权进行,调查之时都先依照原告之主张事实。若被告提出管辖权之疑问,原告还需就其主张之事实进行举证。虽最终确定管辖是以原告起诉事实为准,但此种调查程序中当事人参与程度保障了程序结果的正当性。反观我国的立案阶段审查管辖事项的程序,不仅缺乏最基本的调查程序,而且当事人全程无任何程序性的参与。这种程序状态下制作的裁定不予受理的程序结果不得不令人质疑其程序正当性何在。
其次,移送管辖中法院职权过大,缺乏相应约束,容易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等多种不利后果。比较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移送管辖制度,明显可看出我国只存在职权移送管辖,并且不会征求原告的意见。同时,我国并没有规定类似于德国法上无管辖权的法院告知义务,法院发现存在管辖错误后是否进行职权移送全然凭自己的主观决断。若法院觉得案件审理较为麻烦,审理案件还不如移送案件,大都会依职权移送案件到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若法院发现该案件涉及到本地区的地方利益,并不想主动移送,此时若是被告也没有发现管辖错误的存在,且主动进行应诉答辩的,造成法院本该进行职权移送管辖的无管辖权案件也因被告的应诉管辖而取得管辖权。这就从制度上为地方保护主义设置了生存空间,不得不引起我们警惕。
再次,当事人的管辖利益在移送管辖程序中得不到保障。我国的职权移送管辖制度并不包含征求当事人的意见,特别是原告的意见。法院根据自己审判工作的需要或者出于其他目的进行职权移送与否的安排,此过程中原告的意见并未得到征求和尊重,原告的管辖利益并未得到相应保障。同时鉴于我国没有类似于德国法院的管辖错误告知义务,*参见曹志勋:《民事地域管辖制度释疑》,载《法学家》2015年第6期。被告若在管辖错误不知情的状况下进行了应诉行为却构成了应诉管辖,被告的管辖利益也无从保障。
还有,职权移送管辖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造成程序不安定及管辖恒定原则的突破。程序安定原则是指程序进行必须按照法定的过程进行,除过程不可逆之外,要确保结果的稳定性。广义上将法定程序原则、管辖恒定原则、应诉管辖原则、当事人恒定原则、诉讼标的恒定主义及既判力制度均列为程序安定原则本质性内容。管辖恒定原则和应诉管辖制度就是确定管辖程序进行结果所须遵循的制度,而广泛自由裁量视角下的职权移送管辖模式基于法官的个人好恶,决定是否改变一般地区管辖错误,是针对管辖恒定原则的直接突破。所以有学者直接指出职权移送管辖破坏了程序安定原则。*参见郑涛:《应诉管辖适用之探讨》,载《时代法学》2015年第6期。
最后,现有应诉管辖制度及配套措施明显违背应诉管辖制度初衷,使得应诉管辖沦为一个“附庸性”制度。纵观大陆法系国家之立法,应诉管辖本是被告在管辖错误消除过程中主动作用的重要体现。而反观我国应诉管辖之规定,在未进行立案制度和职权移送管辖制度变革前,应诉管辖的规定存在被架空的危险。此时应诉管辖发挥作用的空间仅仅局限于当存在管辖错误时,法院并未进行职权移送管辖,被告也不知情的应诉答辩。此种应诉答辩构成应诉管辖,消除案件存在的管辖错误的程序瑕疵,成了应诉管辖制度唯一正常发挥作用的地方。
四、我国应诉管辖制度适用规范的重构
通过分析我国现有应诉管辖规定的弊端可明确,我国现有的立案制度和职权移送管辖制度严重限制了应诉管辖制度作用的发挥,加之现有应诉管辖规定在民诉法中的方位引起的争议,导致应诉管辖的未来并不明朗。下文首先从立案制度及移送管辖制度的视角探讨应诉管辖的完善,然后从具体应诉管辖适用条件的角度探讨应诉管辖的未来走向问题。
(一)将立案登记制度去“伪”存真
通过分析我国现有立案规定发现,我国民诉法将审查案件管辖正确作为法定的起诉条件。若法院立案机构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则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本文将这种立案制度称为“伪立案登记制度”。倘若该立案制度完全正确适用,应诉管辖的相关规定基本上等于被架空而无适用的空间。若从比较法及正确适用应诉管辖规定角度来说,废除“伪立案登记制度”势在必行。但也有人会提出疑问,废除该种立案制度,在地域广大的中国会不会造成法定管辖制度的混乱呢?笔者以为这种担忧稍显谨慎,原因在于:我国的法定管辖制度之所以“原告就被告”为原则,其主要目的在于不鼓励诉讼,让纠纷主体自行解决矛盾。但这种原则真的能够阻挡当事人进行公力救济的意愿吗?其实不然,原告在自己的居住地起诉也并不必然就会增加通过公力救济解决纠纷的意愿。这种意愿的大小衡量主要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纠纷的矛盾激化发展程度、对抗程度等多方面的因素,而当事人选择何地起诉在其中所起到作用基本可以忽略。也许会有人提出,取消立案制度中管辖条件的要求会不会造成大量当事人在无任何连接点的法院诉讼,从而不方便法院进行诉讼。其实不然,因为法院在不方便诉讼的情况下,当事人其实也会考量自己在这个“不方便”地方法院起诉所付出的额外成本。理性的经济人不会促使这种现象大量发生,除非在该种地方进行诉讼有其他利益的考量。
废除“伪立案登记制度”,提出起诉条件中原本属于诉讼要件的内容,将起诉条件形式化,便于法院形式审查是世界各国通行的立案制度。将管辖正确作为起诉要件,造成因管辖不正确而裁定不予受理的非正当性,因此应该将管辖要素剔除出起诉条件中。取消立案机构的管辖审查权及管辖错误纠正权是世界通例,将上述两种权力从立案庭返还给审判部门势在必行。
(二)改“职权移送管辖”制度*这里取消的是一般地域管辖错误的职权移送,而级别管辖错误和专属管辖错误的职权移送管辖并不能取消。同时由于我国已经取消“管辖错误”这一再审事由,因此,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错误作为二审重要的程序错误事项不能够再行消除。否则,管辖制度法定性和严肃性无法保障。为“原告申请移送管辖”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我国的移送管辖制度相对于大陆法系各国的移送管辖制度,职权因素较为浓烈。案件在职权移送过程中,当事人的意见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当事人的管辖利益得不到保障。又由于相应的职权移送管辖错误时,当事人没有责问的空间。法院在移送管辖中的权力没有任何约束,极易导致法院基于各种诱惑出现权力滥用的局面,从实践和理论中容易引发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基于法院这种无约束的移送管辖权,应诉管辖也逃脱不了被搁置的命运。但由于职权移送管辖没有约束,即使出现该移送的案件没有移送,法院也可在被告当事人未发现且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况下,利用应诉管辖制度成为法院取得管辖权而治愈本身所存程序瑕疵的一个辅助性制度。而我国有学者也从肯定该种现象的角度论述了应该建立这种“无异议管辖制度”,*参见许尚豪:《无异议管辖制度研究》,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1期。从而帮助消除法院和当事人基于疏忽而没有发现的程序性瑕疵。本文以为该学者的出发点并没有错。但是在职权移送管辖之中,若法院早就发现了该种无管辖权的事实却基于法院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进行移送管辖,此时这种“无异议管辖制度”反而成为法院达成这种不正当目的的制度帮凶。因此,不论是从保障应诉管辖制度适用,还是保护当事人管辖利益,甚至是约束法院在移送管辖中的权力的角度,废除职权移送管辖制度,变为由原告申请移送管辖都变得非常紧迫。*周翠教授主张的通过时间段的方式协调职权移送管辖及应诉管辖制度之间的矛盾并不具有可行性,因为只要保留了职权移送管辖就无法消除其所带来上述几大弊端。参见周翠:《协议管辖问题研究》,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而有学者以学理解释论的角度限缩性解释以法官职权主动纠正一般地域管辖错误而缩小法官在移送管辖中的权力,以此为基调论述不需要废除职权移送管辖制度。*参见曹志勋:《民事地域管辖制度释疑》,载《法学家》2015年第6期。此种改良措施建立在法官发现一般地域管辖错误时,以纠正管辖错误的心态去改变已经确定的地域管辖的基础之上。然而法官在实践中真能做到不受其他因素影响而单纯的抱有此种纠错的心态?答案未置可否。更有学者提出在职权移送中可以征询当事人的意见来决定是否移送及如何移送,并且将该意见征询过程设计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参见郑涛:《应诉管辖适用之探讨》,载《时代法学》2015年第6期。对比这两种改革模式,无疑后者更能防止法院职权滥用及保护当事人管辖利益。但后一种改革模式中再行独立设计一个程序不如直接将职权移送管辖直接废除,而采用当事人申请移送管辖来的更加彻底和公正,因为程序选择权视野下的程序设计更加具备程序正当性。
废除“伪立案登记制度”和“职权移送管辖”,建立“原告申请移送管辖”制度,将管辖事项的审查权统一由审判机构进行审查,法院在审查之中应该注重当事人程序参与及管辖利益的保障。在改革具体应诉管辖适用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扩大应诉管辖的适用,保持案件管辖的稳定性。然而如何改善应诉管辖的适用条件才能扩大应诉管辖的适用范围,下文再行探讨。
(三)不增设“法院告知义务”这一适用要件
有学者在探讨完善我国的应诉管辖制度时都主张借鉴德国的相关规定,即应增加法院发现管辖错误,并针对当事人进行告知,以此作为法院适用应诉管辖制度的条件。*参见周翠:《协议管辖问题研究》,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上述学者主张引进该种要件的理由也非常简单,即保护当事人的知情权及管辖利益。在笔者看来,增设这一要件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需要。通过上文比较法研讨可以发现,“日台模式”并没有这一要件作为应诉管辖的适用条件,原因为何,通过直观的比较法资料介绍或许无法说明。
然而,笔者发现日台控诉之中都有关于管辖错误不废弃原判决的规定,而相较之下德国却无此类似规定。据此,本文认为在德国管辖利益作为重要诉讼要件的事项,其当然属于重大程序性事项。当事人在其中所享有的利益必须得到足够的程序保障,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却恰好相反。对比我国废除“管辖错误”这一再审事由的趋势,笔者认为在我国增设法院告知义务并不合适。另外,德国的此种立法模式存在一定缺陷。在德国诉讼中,若法院没有审查出该种管辖错误的存在,同时也没有针对当事人进行管辖错误的告知,那么诉讼程序管辖错误的程序瑕疵始终存在。而纵观德国的再审之规定并没有管辖错误这种事由,说明当诉讼程序进行到再审之时,德国民诉法规定这种程序就不存在瑕疵。而这种管辖错误的程序瑕疵不治而愈,与德国程序法传统上与当事人利益直接相关的责问权的消失而自愈不同,这种程序瑕疵自我愈合并没有理论及判例作为支撑,难以站得住脚,不得不说其是一种立法上的不周延表现。因此,本文主张在我国不引进德国法上的作法,即不“增设法院告知义务要件”。
(四)不变动现有应诉管辖规定位置
本文一开始就指出我国民诉法关于应诉管辖规定的位置所引发的争议,该争议直接决定着应诉管辖制度适用是否包括“方便法院管辖原则”及“与诉讼事项具有实际联系原则”两个条件。本文认为王福华教授的观点*参见王福华:《协议管辖制度的进步与局限》,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有失偏颇,同时也不赞成刘学在教授所主张的应诉管辖并不是默示协议管辖*参见刘学在、孙曦晖:《合意管辖与应诉管辖之再探讨》,载《时代法学》2013年第6期。的观点。首先,应诉管辖制度是默示协议管辖这点并不存在争议。因为纵观实体法上关于默示行为的标准都是在没有任何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法律直接强制性认定某种行为是某种意思的代替。以接受继承的相关规定为例,在特定期间内未进行意思表示便是接受法定继承的意思,该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立法方法上属于法律拟制,具有不可反驳的特征。恰恰是这种法律拟制,在民法学上称之为默示的意思表示。*关于法律拟制,及应诉管辖作为默示协议管辖之典型,参见林洋:《论民事法律推定的反驳方式》,西南政法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0-47页。从此角度讲,大陆法系通行的诉讼法理论将应诉管辖称之为默示协议关系并没有问题。而我国民诉法却将应诉管辖规定于审前程序一章,而区分开管辖部分的规定。本文认为这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并不是一种立法局限性。其立法目的恰恰是为了避免协议管辖的限制性要素对于应诉管辖的适用。
(五)应诉管辖制度规范用语的一般性释义
关于应诉管辖的适用中还有关于应诉方式、应诉时间段、缺席审判时适用、应诉答辩及管辖权异议共存时如何适用等方面的问题。
首先关于应诉管辖的应诉方式问题,本文认为不应仅限于出庭的方式。若被告以书面材料的方式答辩而代替出庭,只要是针对案件的实体内容进行的应诉或者反驳,法院就可认定其为应诉答辩。这里就牵涉到缺席审判*虽然我国民诉法在缺席审判中采用了一造辩论主义的模式,但是跟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缺席审判的规定还有所差异。体现在我国的缺席审判仅仅适用于被告或者具有被告地位的当事人没有到庭,而不适用于上述当事人到庭而没有积极进行诉讼行为的情形。因此,本文所指的缺席审判类似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模式,其不仅包括被告或者被告地位的当事人没有到庭,还包括前述当事人到庭而没有积极进行诉讼行为的情况。此种情况作为缺席审判一种形态,也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对于当事人要求的具体体现,即积极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关于缺席审判制度的详细内容参见刘秀明:《民事缺席审判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时是否适用应诉管辖制度,因为我国现在采用“一造辩论主义”的裁判方式,只要被告提出的材料在诉讼中达到相应标准就应该予以认定。因此,只要被告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民诉法直接可以拟制为被告应诉管辖。*这种提法与许尚豪博士提出的无异议管辖制度有异曲同工的作用,目的都是维护管辖安定,尽快解决纠纷。参见许尚豪:《无异议管辖制度研究》,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1期。通过这种方式的立法能够增强诉讼效率及当事人的出庭率,并且保持诉讼程序的稳定。
其次,关于当事人同时应诉答辩及提出管辖权异议应如何处理的问题,笔者认为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比较可行。因为当事人一旦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则应诉管辖制度并不具有适用的前提条件,此时便不会出现所谓的到底如何认定当事人内心真实意思的情况。
最后,关于应诉管辖具体适用程序种类的问题有许多争议,有学者认为应该仅限于协议管辖所适用的范围,*参见王福华:《协议管辖制度的进步与局限》,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有学者认为应该适用于所有案件类型,*参见刘学在、孙曦晖:《合意管辖与应诉管辖之再探讨》,载《时代法学》2013年第6期。还有学者认为应该仅仅适用于非人身纠纷。*参见郑涛:《应诉管辖适用之探讨》,载《时代法学》2015年第6期。众说纷纭的观点中涉及到应诉管辖在地域管辖确定中与协议管辖的关系以及地域管辖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各种内容。本文认为应诉管辖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协议管辖,因为应诉管辖中的“未提出管辖异议”直接视为“当事人同意协议管辖”属于一种拟制。拟制是一种强制性认证,因此,应诉管辖的适用范围并不受协议管辖适用范围的约束。同时在人身案件中应诉管辖并不会影响当事人享有的实体人身利益,应诉管辖可以适用于所有的诉讼案件类型。
结语
本文在法规范分析语境下探讨应诉管辖的民诉法以及民诉法解释的规定,得出应诉管辖在现有制度下很难落地生根。通过比较法资料分析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应诉管辖制度与立案制度、移送管辖制度的关系,得出德国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立法例。总体结合我国的理论和现实状况,本文指出废除“伪立案登记制度”和职权移送管辖制度势在必行。同时明确表明应诉管辖在制度的重新设计中应该选择的方向。
[责任编辑:王德福]
Subject:Subject: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spondent Jurisdication
Author &unit:ZHANG Yu
(School of Law,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The respondent jurisdication has already setted in the civil litigation law in it’s 2012 year’s modification.Then,this institution may not function well in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present civil procedural law,because the adjacent instuation which includes the filling system and the jurisdication transfering system ,have essential confliction with the respondent jurisdication.The confliction leads to many maligent consequence,therefore,some necessary reformity of the respondent jurisdication must be taken.These include amendment of the existing registration system,correcting transfer jurisdiction according to authority to application,without adding requirements of telling obligation,retaining the position of respondent Jurisdication,making clear specific application problems.
the respondent jurisdication;the filling system;the jurisdication transfering system
2016-10-29
本文受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科研项目资助,系中国法学会2015年青年调研项目《司法拍卖实施状况》CLS(2015)Y08和西南政法大学2015年度校级科研项目(2015XZZD-1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张宇(1985-),男,河南光山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民事诉讼法学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学。
D915.2
A
1009-8003(2017)01-01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