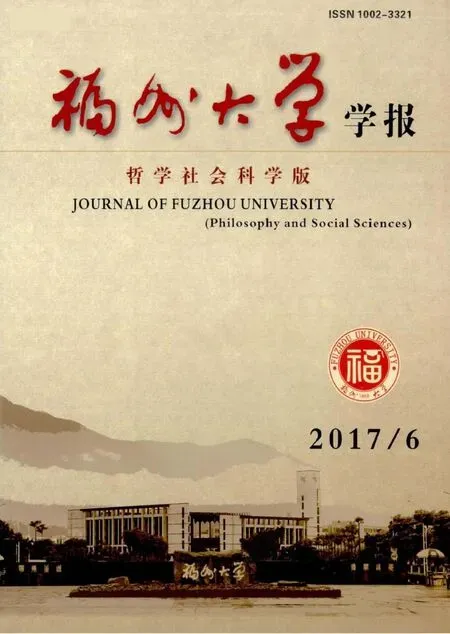陆游《钗头凤》词本事接受特征析微
袁 茹
(1.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2.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 江苏苏州 215009)
陆游《钗头凤》词本事接受特征析微
袁 茹1, 2
(1.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2.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 江苏苏州 215009)
由宋至今,有关陆游《钗头凤》词本事的接受呈现鲜明的特征,即多采信“陆游与前妻唐氏沈园相见,唐氏遣致酒馔,陆游题壁《钗头凤》一词,后唐氏和词”之本事,以致该本事成为学界接受陆游《钗头凤》的文学性事实,选择性忽略“陆游与唐氏于沈园宴席上相见,唯‘目成而已’,无作词相和等事”。究其原因,历代受众在通过艺术作品来接受经典作家时,更倾向于从文学性欣赏的角度来重塑读者心目中的人格范型,更注重激烈的“戏剧性”情节冲突,以期在审美效果上加深其悲剧性的强度,成就了《钗头凤》的文学经典地位。若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剖析,虽然会使陆游唐氏的婚姻悲剧与《钗头凤》相脱离,但陆游作为经典作家的人格范型塑造更合乎时代特征,历史事实的悲剧性更深远。因此,探究《钗头凤》词本事,不管是文学性接受还是回到历史真实,都有其积极意义。
陆游; 《钗头凤》; 沈园; 接受; 戏剧性
中国古典诗词以抒情擅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顶礼“实学”方法,“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1]的本事批评观念,探寻诗词本事自然而然地成为理解赏析诗词的常用模式。唐宋诗词的本事多散见于一些笔记之中,记载不一,又因笔记多源于传闻,真假难辨,使受众在接受某些诗词本事时众说纷纭,陆游的《钗头凤》之本事的接受现象即是如此。由宋至今,诸多接受者各执一端,且有理有据,论证推理均不易推翻。“一首诗文只要传诵得普遍了,对于作者和本事的传说一定失了真相。”[2]在目前没有发现更切实、更新的文献史料的前提下,如何分析这一接受现象?笔者提出这一问题,本意不在于加入《钗头凤》本事的孰是孰非的论争考辩,而更在于分析这一接受现象的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及意义,以期还原一个更切合历史真实的青年诗人陆游的形象,进一步理解其与唐氏的婚姻悲剧。
一、南宋至今《钗头凤》本事接受特征概述
福柯认为,历史的言说积累得越是重重叠叠,缺失的东西也就越多,“历史的每一次诉说都伴随着缺失的发生”[3]。对于陆游《钗头凤》本事的接受,近千年来亦足够纷繁,但具有鲜明的接受特征,呈现“一边倒”的现象,即接受者更愿意采信“陆游与前妻唐氏于沈园相见,唐氏遣致酒馔,陆游题壁《钗头凤》一词,后唐氏和词”,而选择性忽略“唐氏改嫁后与陆游相见于沈园之宴会上,除却‘坐间目成而已’,再也没有任何交集”,因此《钗头凤》是不是写于沈园,是否为唐氏所作,都成为争论的焦点。
历代读者多采信的观点首见于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十“陆放翁陆子逸词”:
余弱冠客会稽,游许氏园,见壁间有陆放翁题词云:“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裛鲛鮹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笔势飘逸,书于沈氏园。辛未(1151)三月题。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妇之情实不忍离,后适南班士名某,家有园馆之胜,务观一日至园中,去妇闻之,遣遗黄封酒,果馔,通殷勤。公感其情,为赋此词,其妇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惜不得其全阕。未几怏怏而卒,闻者为之怆然,此园后更许氏。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之,今不复有矣。[4]
稍后周密《齐东野语》卷一“放翁钟情前室”有相似记载:
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絜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唐后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云:(略)。实绍兴乙亥(1155)岁也。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尝赋二绝云:“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又云:“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盖庆元己未岁也。未久,唐氏死。至绍熙壬子岁,复有诗,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赋小阙壁间;偶复一到,而小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云:“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首蒲龛一炷香。”又至开禧乙丑岁暮,夜梦游沈氏园,又两绝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水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沈园后属许氏,又为汪之道宅云。
比较以上两处记载,周密记载比陈鹄记载少了“唐氏奉和词”一节。陈鹄所记唐氏和词只有两句,而清康熙年间沈辰垣等人编录的《御选历代诗余》卷一一八引夸娥斋主人语云,出现唐氏和词全阙:
陆放翁娶妇,琴瑟甚和,而不当母夫人意,遂至解离。然犹馈赠股勤,尝贮酒赠陆,陆谢以词,有“东风恶,欢情薄”之句,盖寄声《钗头凤》也。妇亦答词云:“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间,咽泪妆欢。瞒!瞒!瞒!”未几,以怨愁死。
以上观点广为学界采信,不仅确定《钗头凤》是陆游为前妻唐氏而作,尤其是“陆游题壁《钗头凤》”这一情节更是深入人心。如清代沈雄《古今词话》词辨卷下、丁传靖辑《宋人逸事汇编》之《香东漫笔》、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二十一,以及欧小牧《陆游年谱》、胡云翼《宋词选》、游国恩《陆游诗选》等均与周密说法相近,但多不提陈鹄《耆旧续闻》中记载的唐氏和词一事,甚至直接反对,如朱东润《陆游传》认为唐氏和词一首可能是后人的附会[5],于北山《陆游年谱》也认为唐氏和《钗头凤》词不足信。
稍晚于陈鹄、早于周密的南宋诗人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的记载一直没有成为接受的主流,最明显的区别是少了陈鹄、周密记载中的“小说家言”的传奇色彩:
放翁少时,二亲教督甚严。初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于学也,数遣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决。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一日通家于沈园,坐间目成而已。翁得年最高,晚有二绝云(按《沈园》二首,略)。旧读此诗,不解其意。后见曾温伯言其详。温伯名黯,茶山孙,受学于放翁。
这一记载为清人顾栋高采信:“放翁初婚某氏,颇倦于学,严君督过之,急至仳离,某氏别适某官,一日通家于沈园,目成而已,晚年游园,感而赋之。”[6]今学者周本淳《陆游〈钗头凤〉主题辨疑》[7]认为刘克庄说法可信,而周密说法有难通之处。
清人是从《钗头凤》词语俚俗角度怀疑其为前妻唐氏而作,如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云:“吾乡许嵩庐先生(昂霄)尝疑放翁室唐氏改适赵某事为出于傅会……唐氏答词,语极俚浅。”[8]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言:“有‘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等句,似非念故妻之语,且安见为改适耶?宋人小说往往诬人闺闼,可信绝少。”[9]沿此而来,当今学界明确说明陆游《钗头凤》为在蜀地而作,代表性的有吴熊和《陆游〈钗头凤〉词本事质疑》一文中的观点:“夏承焘先生指导我为陆游词编年,曾断《钗头凤》为蜀中词,盖作于乾道九年(1173—1178年)陆游寓居成都期间,与这时间的《真珠帘》《风流子》等词性质相近,似亦为客中偶兴的冶游之作,实与唐氏无涉。”[10]陈祖美《陆游〈钗头凤〉新解》[11]、周本淳《陆游〈钗头凤〉主题辨疑》[12]等文与夏承焘、吴熊和等观点相同。
除此之外,赵惠俊《〈渭南文集〉所附乐府词编次与陆游词的系年——兼论〈钗头凤〉的写作时地及其他》根据《渭南文集》以写作时间先后进行编次的特征,认为附在《渭南文集》的乐府词也是类似的编次标准,因此确定《钗头凤》写于乾道八年的南郑,眼前情景促使陆游怀念唐氏而作。[13]
通过梳理以上材料可见,今学界关于陆游《钗头凤》本事之辨基本上是沿袭宋代笔记而来。陈鹄是在沈园亲眼见到陆游题壁词《钗头凤》“笔势飘逸”,刘克庄是亲耳听到陆游弟子“曾黯”(曾黯是陆游老师曾几的曾孙)所言,可信度都很高,都有无可辩驳之处。历代受众选择性忽略刘克庄的观点而主要接受陈鹄、周密的记载,原因大概是一旦接受刘克庄的观点,《钗头凤》与陆游唐氏婚姻悲剧之间的关系链就会断开。若细细推究,以下问题都颇有意味:这一关系链及其细节存在是否合理?历代大多数接受者为何不愿意接受这一关系链的断开?如何看待陈鹄、周密的观点更易被广泛接受这一特征?笔者首先以“假定”为切入点来剖析《钗头凤》词相关本事。
二、以“假定”为切入点剖析《钗头凤》的本事
(一)假定陆游“题壁《钗头凤》”与唐氏“和词”是真实事件
学界关于陆游与出妻唐氏相见于沈园的时间,分歧在陈鹄的“辛未(1151)三月”与周密的“绍兴乙亥岁(1155)”,即陆游是27岁还是31岁时与唐氏沈园相会。不管是陆游27岁还是31岁,都是陆游已经重新娶妻王氏、至少生育二子的时间段,[14]而唐氏也已改适他人。宋人承唐风俗,不讳改嫁,但唐氏是依“七出”被休弃的,即说明此女不受封建礼法约束,在当时会受世人指点。鉴于此,唐氏的亲朋熟人,不触动唐氏内心的伤疤是最好的方式。而作为被迫休妻的前夫遇到了唐氏,怎样的表达方式才是最合情理的?
按照陈鹄的记载,27岁的陆游到唐氏再婚丈夫(只是说“南班士某”,说明身份是皇族子弟)家的园馆中游春。陈鹄未说陆游与赵家有亲戚朋友关系或如何邀请,陆游此去就是贸然前往。陆游明知自己的前妻唐氏家、已经再成家并有二子、守父亲孝刚满、反对他们婚姻的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公然地去唐氏家园馆游春题壁,应是不太能为当时的社会舆论接受。相对而言,周密《齐东野语》中的记载有合乎情理之处:陆游偶然与唐氏及后夫赵士程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氏明白地告诉丈夫后“遣致酒肴”。但下面又出现一个情节:陆游选择了“题壁”的方式,把他与唐氏相会并难以忘情的事件最大可能地公之于众。
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题壁是古时的“互联网”,传播简便快捷,题壁和观壁,是宋代文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5]如周邦彦“下马先寻题壁字”(《浣溪沙·黄钟》),姜夔“与君闲看壁间题”(《阮郎归》),甚至看到前人题壁就要“手痒”立刻和词,如李曾伯《沁园春·庚子登凤凰台和壁间韵》,王质《水调歌头·和壁间张安国作》,韩淲《浣溪沙·和辛卿壁间韵》。在这样浓厚的题壁文化生活中,陆游也是积极营造题壁文化者之一。[16]陆游游园题壁需要随从携带笔墨,唐氏和后夫一起也要携带丫鬟随从,一切都是公开的环境下进行的,当事人至少五六个,且沈园之胜景还会吸引更多的游客。陆游多次写诗歌怀念自己的前妻,这些诗是带有私密性的,而题壁词却是公开的。陆游将本来难以言说的感情公开表达,应该没有考虑过他的行为会给唐氏带来多少难堪。唐氏自己如何面对再婚丈夫,如何面对传之于大街小巷的闲言碎语?陈鹄记载的“闻者为之怆然”,似乎是强调时人与陆游和前妻的感情产生了共鸣,其实最主要的是唐氏“未几怏怏而卒”的生命逝去的悲剧引发的同情,甚至有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住陆游的题壁词。就像《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和刘兰芝,是在死亡之后才“两家求合葬”。对于因情而死者,再遵循礼法的人内心都会有些许触动,会用相对宽容的态度来对待逝者。
若坐实《钗头凤》为唐氏“弗获于姑”被休弃而写,当时的受众看到《钗头凤》中公然指责“东风恶”,自然而然想到这个“东风”——摧毁他们婚姻爱情的力量就是陆游的母亲。陆游激愤地谴责“错错错”,读这首词的并且知道陆游休妻的人,谁不肯定他这是说自己的母亲错了呢?此时陆游母亲尚在世,陆游不怕担负不孝的罪名吗?对于陆游词中的“东风恶”,明人孙能传认为“沈园一词,固亦人情,至云‘东风恶,欢情薄’”,不够“抑情”[17],即代表了身处封建社会中遵守封建礼法者的普遍观点。现代京剧大师荀慧生改编的《钗头凤》把两人分离的原因归于陆母受到恶尼不空的蛊惑而迁怒于唐氏,因此《钗头凤》中的“东风恶”就指不空,这样的改写也说明荀慧生不赞成陆游在《钗头凤》中以“东风”指责陆母。
再看这首词给人的审美感觉:香艳。如果没有陆游与唐氏仳离的本事,说这首词是写相爱却被无情拆散的文人与歌姬、小妾之间的感情绝不会有任何人怀疑。词本顽艳,对于男性词人而言,香艳的词可以写给情人、小妾,或者可以写给自己的妻子也未尝不可,宋以后的很多《钗头凤》词写得很香艳,不能明确断定是写给自己的妻子、妾侍还是青楼女子。但若把香艳的词公然地写给别人的妻子则不合情理。词中的“红酥手”不管是指女子白嫩的手,还是指女子做糕点时点红酥的一双巧手,都不能指的是已为他人妇的唐氏的手,陆游若这样公开地、毫不避讳地表达这种情感和欣赏态度,是绝对不合礼法和情理的。
假如陆游题壁之后,唐氏再和词,将两人难以忘怀的感情公布到陈鹄所说的那样被很多好事者围观,如此,唐氏的生活一定会被社会舆论打扰。唐氏改适之后,已经是在过自己安静的生活。如果陆游真的题壁《钗头凤》,那么唐氏被题壁词打扰之后的生活,真的就会像她的和作《钗头凤》中所描述的那样难以平静了。唐氏和词中写到“世情薄,人情恶”,因为她感受到了周围的人对待她这样一位被休弃的女子的态度,唐氏每日的生活是一个个难眠之夜,拖着抑郁导致的病体,流泪到天明,却又怕人看出自己的心事而“咽泪妆欢”。她不会把自己心底对陆游的思念、对被休弃带来的羞辱感表露出来,她的日常生活一直是在“瞒!瞒!瞒!”的状态下。如果没有人揭开这层面纱,虽然生活很艰难,唐氏还是会瞒着众人活下去。而陆游真的有题壁的举动,全城皆知她对前夫一直念念不忘,是山盟海誓一直存在两人的心底,以致“人空瘦,泪痕红裛鲛鮹透”,那她还能瞒得住什么呢?她再也无法“咽泪妆欢”来面对新的家人,平静生活一旦被打破,唐氏只能更快地走向生命的终结。假设陆游的创作真的是一时冲动,是醉后忘情、感情冲动之下诉说衷肠,挥洒题壁,[18]事后他会醒悟,伯仁由我而死,陆游晚年更加理性的时候,按照其“日课数诗”[19]的写作习惯,应该有诗歌创作来表达对题壁举动的负疚。但其对前妻思念的若干首诗中却没有此类表达,而是真切郑重的思念。
既然假定“陆游题壁与唐氏和词真实”之后会有如此多让人怀疑的不合情理之处,我们就尽量去寻找真正合乎情理的空间,去寻找历史真实。
(二)回归历史的常情常理来剖析《钗头凤》的相关本事
历史事件的发展一般都会合乎当时的情理,尽管随着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些情理今天看来很可能不合情理。因此回到常情、常理和常识,才是真正了解历史真实的途径。而被学界忽视的刘克庄的记载更合乎当时的常情常理。
首先,是陆游与唐氏的相见之时的反应。唐氏改嫁的“某官”,刘克庄没有说是皇族之后人,只是说他与陆游有表亲关系,“一日通家于沈园”。陆游与唐氏的仳离之事,两家及在座客人都心知肚明,于是坐间没有任何人再旧事重提,以免尴尬。因此两人唯一符合礼法的、最恰当的方式就是“坐间目成而已”,看一眼,感叹,伤情,遗憾,无奈,仅此而已,然后就各自回家过自己的日子。此后,陆游创作了许多与唐氏、沈园有关的诗歌,都是深情款款不点名地悼念早逝的前妻,让刘克庄读来“不解其意”,说明这件事并没有像陈鹄说的,有好事者将这首题壁词用竹木护好,人尽皆知,而是将一切思念都沉默在他的诗里。
其次,是刘克庄所提到的唐氏被谁休弃及休弃原因:“放翁少时,二亲教督甚严。初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于学也,数遣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决。”《仪礼·丧服》记载“七出”为: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陆家不会以二、四、五、六、七等五项罪名来休弃唐氏,毕竟陆家是诗礼传家,应不会无中生有。因此公开的理由应是“无子”,而内在的原因是“不事舅姑”。古代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礼记·昏义》)。《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唐氏因何让陆游父母不喜?刘克庄与陈鹄、周密的记载不同的是:前者是唐氏不得于陆游双亲,后者却是因为婆媳不睦,无形中把这个故事变成了《孔雀东南飞》的翻版,且这种观点被广泛接受,如明代张元忭《(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不得于其姑”;清代周铭《林下词选》卷二“不当母夫人意”;清代厉鹗《宋诗纪事》卷五十三“弗获于其姑”;清代沈辰垣《历代诗余》卷一百十八“弗获于姑”等。陆父是爱国文人,陆游笔下的“先夫人”也是出身大家庭的知识女性,她会在陆游幼年的时候给小儿子诵读自己祖父唐介的诗《九日赠僧》,回忆自己少年时期在外祖父晁家读诗的情景,还依稀记得“也”字读去声。那个时代“知书达理”的双亲,为何却见不得儿子媳妇伉俪相得,而且还是数次“遣妇”,不达目的不罢休呢?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提出这种观点:陆游父母出于对儿子的期待,不允许他在功业未成之际沉溺于温馨的爱情眷恋之中,这一动机是为陆游仕途着想,也是为国家兴亡考虑。[20]笔者以为,不管陆游父母是为家族兴盛还是为国家兴亡考虑,都不允许陆游成为一个专业诗人,嘲风弄月,诗酒风流。而诗人的人生目标和诗酒风流的生活方式却在陆游16岁的时候就彰显出来。“我年十六游名场”(《灯笼》),绍兴十年(1140)、十一年(1141),陆游在学诗的道路上已经很出名了,十九岁临安进士落榜,在陆游父母心里,诗酒生活应是耽误举业的主要因素。[21]而这种生活方式在婚后生活中似乎更变本加厉。陆游63岁严州任上时,写《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颇传于人,今秋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采得菊花做枕囊,曲屏深愰闷幽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少日曾题菊枕诗,囊编残稿锁蛛丝。”[22]43年前,正是20岁的陆游新婚不久,采菊花作枕赋诗,且“颇传于人”,字里行间显示出的是对诗名得以传扬的得意,而这是陆游与唐氏伉俪情深生活中的一个细节,表现出他们的志同道合,否则陆游不会四十三年后慨叹“灯暗无人说断肠”。陆游81岁高龄时写《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梦中的沈园,梅花盛开,早年和前妻甜蜜赏梅赋诗的生活非常清晰:“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沉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墨痕犹在的,应是陆游和唐氏当年游沈园所题壁的赏梅之诗。陆母陆父都通诗,对于诗歌不会排斥的,他们排斥的是以诗歌为主业。陆游所处的时代,因为夫妻情深而荒废举业,是不被允许的。在陆游父母的眼里,媳妇毁掉的是自己儿子的前程,唐氏的出现使陆游的人生充满不可预期性,就是不能按照陆游父母期待的目标发展,她被陆游父母休弃就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情了。
再次,是关于唐氏的早逝。刘克庄的观点中没有涉及,而陈鹄说是“未几怏怏而卒”,周密说是“未久,唐氏死”,都是在说唐氏沈园遇见陆游之后不久就因此而死。唐氏大约去世于陆游三十五岁左右,[23]欧小牧《陆游年谱》取陈鹄记载,陆游与唐氏于绍兴辛未(1151)见面,唐氏卒年,当在沈园邂逅7年之后,即绍兴三十年(1160)之间。[24]但是距离沈园相会已9年(距周密所言沈园相会时间1155年为 5年),这些时间段,都不是陈鹄和周密的“未几”“未久”心理预定的时间。他们也更倾向于沈园题壁之后,唐氏在受到更大的触动郁郁而亡。认同陈鹄和周密观点的接受者们,“对文献记载的、过去的人与事怀有同情之理解”[25],自然都是怀着同情的心去看待唐氏的早逝,但在咏叹陆游多情和传播陆游题壁与唐氏和词的同时,却是在潜意识中提前了唐氏的死亡时间。陆游醉后题壁,唐氏忍痛题词,在文学作品里,戏剧性的情节和痛入心扉的情绪,确实能加速当事者死亡;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生活苦难对人生的慢慢折磨,会有像陆游这样一生念念不忘同时也会理性地过好自己生活的人,也会像唐氏这样执着感情不能自拔者慢慢的油尽灯枯。因此,刘克庄观点中没有提及唐氏的很快死亡,是更符合历史真实的。
三、《钗头凤》词本事接受特征产生的原因
(一)传统文学史研究的惯性
学界对于《钗头凤》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研究风雅的作家生平和文本评注上。陈鹄和周密的观点被广泛接受,说明接受者对名人轶事的热衷心态。这是文学史研究的惯性,“文学史还是过多地局限在研究人和作品(风趣的作家生平及文本评注)上,而把集体背景看作是一种装饰和点缀,留给政治编年史作为趣闻轶事的材料。真正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明显地被忽略了……历史的深度仿佛在一块两维屏幕上被压扁了,文学事实因此受到扭曲,就同一张世界地图在平面投影上失真情况一模一样”[26]。陆游是一个大诗人,有一些重情的表现总会成为诗人的雅事,丰富诗人的人格精神。在文学史上,为什么会倾向于接受陆游的题壁与唐氏的和词?周密、陈鹄的观点几乎成为定论,而刘克庄的观点几乎被下意识地选择性忽视。难道宋以来的受众真的没有感受到周密尤其是陈鹄的记载中的小说家言、附会痕迹、传奇色彩?当然不是。本事作为诗性的历史存在,是与现实的批评者存在着一定的时空距离的,这个空隙是用文学性的欣赏和创造来填满。陆游的那些钟情前室的诗词需要唐氏“文学史”的回应,不能让这些诗词成为自言自语。于是接受者给唐氏安排沈园一见之后“和词”的情节,不久便去世的结局,是相对于大诗人陆游来说最浪漫最悲情的安排,一个原本应该沉浸在历史中的休妻案,就这样被文学性的欣赏和创造写入了诗性的文学史。
(二)接受者追求“传奇”的心态,更重情节冲突,彰显陆游与唐氏婚姻悲剧的浓烈
诸多接受者对陆游和唐氏在酒席上“目成而已”的情节几乎舍弃而选择接受陈鹄、周密的观点,是一种特意的误读和演绎,不是因为时间间隔久远而使人产生了认识上的隔膜,而是后人根据自己追求“传奇”的心态进行的主动改造。这种改造超越了传统日常生活,成就了陆游和唐婉的传奇。本来陆游和唐氏的悲剧发展脉络是陆游念念不忘,写诗词纪念,甚至连前妻这个身份都不直接提及,唐氏在大家淡漠他们的故事后沉默死亡。现实是默不做声的,而传奇是大张旗鼓的。有时候现实未必不比传奇更“奇”,但一般来说,在节奏、矛盾冲突的安排上,传奇会比现实更集中。这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的一般表现。文学性的接受,讲究的是故事情节的高潮迭起,有完成的故事情节发展。现实生活中,陆游和唐氏的故事在唐氏被休弃之后就应该戛然而止了,被休虽然不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也很难有传奇色彩。而陆游是著名的诗人,发生在著名诗人身上的这个故事就有了被“传奇”的可能性,也必然成为笔记热衷记载的内容。后代的接受者不断演绎,甚至使之具备了才子佳人的路子,如清代保培基将唐氏形象演绎为“才色冠一时”,与陆游偶遇沈园时“凝睇觑陆,殊不胜情”[27]。而刘克庄的记载过于平淡无奇,“散文是现实的真实面孔,是神话的对立面,但是人们却总是不断地把生活改变为神话和诗”[28],反之,过分纠缠于现实却不合读者的胃口。所以人们在接受时需要阅读带来的审美快感,情节完整、冲突剧烈的小说美学已经被传统所接受,这也是我们的本事批评最为传统的固定的样式。一旦过度关注情节,就会容易忽略现实。戏剧性的接受,接受者就循着戏剧性的叙述逻辑找到该本事的意义,仿佛陆游和唐氏不再相见或者没有任何戏剧性的相会就没有意义。而刘克庄的记载却拒绝了“戏剧性”,是对戏剧性叙事的消解,也决然断开了陆游唐氏婚姻悲剧与词作《钗头凤》的直接联系。唐氏的确会因为被休弃而死,但这是一个缓慢的默默的过程,文学性的接受却不愿意接受这样沉默的关系链,因为没有激烈的冲突,就没有鲜明的审美效果,强烈的悲剧性。就像《红楼梦》中一定要这边有黛玉去世之悲、那边有宝钗新婚之喜,追求情节的“整一性”,形成对立的冲突,高鹗写不出黛玉抑郁而亡之后宝钗再嫁宝玉。《钗头凤》词本事的很多接受者,也不愿意接受陆游和唐氏“坐间目成而已”,一定要陆游高调地题壁将自己的私事公之于众,唐氏也要与之唱和,最后快速走向死亡,这样的情节安排与高鹗的审美是一致的。但是,当我们在“热热闹闹”戏剧般去接受《钗头凤》本事的时候,热衷去赞颂陆游的多情与长情,却在不自觉中忽视了唐氏这个弱者不幸的命运。
(三)对陆游人格范型的塑造的心理期待
“一部经典作家的接受史,既是一部经典作家艺术生命的存在史,也是一部经典作家人格精神的传播史。人格精神的传播史,侧重于展示经典作家的文化生命和人格泛型在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塑造史的精神史意义。”[29]因此对于陆游《钗头凤》本事的接受,更多的是对陆游人格范型的重塑,人格精神的接受。
陆游给文学史留下的主流人格范型是爱国诗人,这个不忍与前妻分离的故事恰恰丰富了陆游这个人物形象,多情长情的诗人陆游更有血有肉,更丰富,也是符合接受者心里期待的安排,所以接受者根本就不加怀疑地接受了这个陈鹄、周密以来的“文学性事实”,而不愿意去了解历史真实。
四、《钗头凤》词本事接受特征展示的积极意义
历代读者在演绎陆游和唐氏的故事的时候,主要是两种态度:一个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轰轰烈烈地表现陆游的刻意传播与唐氏悲情接受;一个是从社会现实的角度,默默地认定他们“目成而已”。前者更虚幻、隆重,是充满着文学的想象力来赏析文学作品,因为年代久远以及作品本身具有的概括性,会使艺术作品被欣赏的空间增大,想象也就更多地进入受众的视野中去;后者更现实,唐氏的悲剧是隐藏着的,它不带有更多的被生发的空间。不管是前者的轰轰烈烈,还是后者死寂般的沉默,都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不应执其一端而否定另一端。
(一)尊重历史真实使接受者对经典作家人格范型的塑造更合乎时代特征
陆游的多首沈园诗,表达的是他一生对前妻郑重的思念。但陆游首要的社会角色是生活在封建礼法之下的人,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只拥有半壁江山的国家的“匹夫”。在对待爱情婚姻方面,他不具备超前的婚姻爱情观,不能表现出民主性。陆游父母之所以 “数遣妇”,是因为陆游的多次反对,但是他不能反抗彻底,最终“不敢逆尊者意”,妥协了。他不会成为焦仲卿那样的特例,也不会不顾父母携唐氏出走,陆游和唐氏都在仳离之后各自婚嫁,这是那个时代的常态。这样的陆游形象在那个时代更具有代表性,典型性。
唐氏与陆游坐间相见没有说一句话,并不表明他们的心是不痛苦的。唐氏的早逝,与受到的这样沉重的近乎沉默的打击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陆游的人格范式,和一般人是一样的。他对于他们婚姻的悲剧,对前妻的思念,对唐氏早逝[30]的不幸命运,是悲伤的,感情是真实的,长久的,但是悲伤之后还是认真地对待理性的生活,这都是不违背人性的表达,都是真实的人性表达。
(二)尊重历史事实彰显陆游和唐氏婚姻悲剧性之深远
唐氏作为会诗词、懂得生活情调的女性,感受到的痛苦也比常人多十分。虽然唐氏在被休之后改适他人,并且还改嫁到“某官”,按照世俗的标准应该是扬眉吐气的再嫁,但从唐氏的早逝可以看出,被休弃对唐氏的打击是致命的。夫妻被无情拆散,而且原因还在于自己,情感的伤害,高傲者的被羞辱,会使唐氏郁郁寡欢,从此再也不能真正地高兴起来。沈园一见,囿于礼法只能“目成而已”,婚姻外深爱的人就在眼前,婚姻里的必须爱的丈夫就在旁边,一切都不能靠语言来表达,这是难以言说的痛苦。况且就是能自由相见诉说旧情又如何?过去的已经再也回不来,这种无奈和痛苦,只会在这无言的会见中一点点浸透到内心深处。她不会像陈鹄记载的相见“遣致酒馔”,不会因题壁和词这样一系列难以自持的情节冲突导致“未几怏怏而卒”,而是在被休弃的十几年的抑郁中一点点走向死亡,这种必然死亡的悲剧,与陈鹄所记载的很快死亡相比,能比较出悲剧强度的孰大孰小吗?
那个时代,“知书达理”的陆母,后人尊敬的爱国文人陆父,却不停地以礼法和大义活生生地拆散了一对恩爱夫妻,这样的悲剧不够沉重吗?唐氏被休,陆游父母都不会后悔和负疚,也不会为时人诟病,因为陆游父母所为是合乎当时的情理和礼法的。当然陆游父母休弃媳妇,也不是要致唐氏于死地,但唐氏若因被休而郁郁寡欢,那是因为她没有明白自己错在何处,更不要说改正错误,当然是不值得时人同情的。多么冰冷的“合情合理”的时代!这个不是悲剧吗?“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今天我们会认为有价值的“夫妻情深”被毁灭了引起了对这个悲剧同情,而在遵循封建礼法的时代,这被毁灭的东西连“有价值”都算不上,更不要说是“悲剧”了。
(三)《钗头凤》文学性本事被接受的积极意义
本事批评是在一定的时空文化视域下的批评和阐释,追求一种效果历史。当本事批评遵循的“真”是艺术真实的时候,它的积极意义在哪里?即“陆游题壁《钗头凤》,唐氏遣致酒馔再和词”这一艺术真实对文学欣赏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接受者近千年来不是不怀疑《钗头凤》词本事的真实性和不合理性,但是基本上采取了“不穷究”的态度,不仅是因为“穷究”会使得《钗头凤》与陆游、唐氏的凄美爱情脱离,而且更因为文学性接受更符合读者的审美心理,就像罗敷和她并不存在的夫君,《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游园惊梦,《红楼梦》中贾母批评的那些“谎”,作为艺术作品,接受者都知道这些“艺术真实”存在的不可能性或不合理性,但是除却贾母这样的接受者,没有更多的读者去“穷究”,而是采取明知却视而不见的态度,说明接受者更关注的不是历史真实,而是艺术真实。就像更多的接受者赏析《钗头凤》,哪怕明知道是虚构的,也要按照这虚构的情节去赏析词作,感受男女主人公的悲剧情节所产生的撼动人心的美学意义。宋代以来的接受者基本上都愿意接受《钗头凤》与陆游和唐氏“仳离”这件事情相关,对《钗头凤》的传播一直都起到更多的正面意义。对于《钗头凤》本事的文学性接受,即热衷接受情节紧凑、感人至深的故事,激发了更多的艺术创作,因为情节的冲突性与戏曲小说相合,使它被小说和戏曲等文体不断演绎,被千古传诵,成就了《钗头凤》的文学经典地位,让更多的读者透彻了解封建礼法和婚姻制度对正常人性的禁锢与伤害,感受陆游和唐氏多情的人格魅力。
五、余论
既然陈鹄、周密记载的《钗头凤》本事不一定是真实的,那么《钗头凤》到底是为谁而写的呢?词,本身具备的特征,可以不为一件本事而写。明代茅元仪云:“放翁韵妻诗妾,又弹文中,在蜀中收尼妾一事,皆非常人,独以后妻妒极,竟不能蓄。一人早向枯寂,竟得上寿,然其惘然之怀,至老不忘。”[31]陆游一生中,遭遇过爱妻见逐于父母、爱妾复见逐于正妻,因为第三者强大的力量导致这样的婚姻和爱情悲剧,是作为一种情绪埋藏在陆游的心底的。所以一旦被某种情境触发,有作词的机会,内心的这种感情就被激发出来。另外,词的泛化特征,更容易寄托一种虚泛化的情绪。词比诗歌更不需要本事,只要理解成为一种情绪即可。况周颐《蕙风词话》认为:“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32]因此,若从文学性的角度去欣赏《钗头凤》,对于词本事的理解,可以“不穷究”历史真实,可以言之凿凿确定其为唐氏而作,诗词之本事是“诗性的历史实存”[33],本事批评是对源发的诗性实存所作的理性观照,从感性还是从理性的视角,只要达到我们赏析的目的就够了。作为历史真实角度的接受者,可以寄希望于发现更多的历史真实证据,或者根据现有的文献各圆其说,论证推理,若有新见,何乐不为?
注释:
[1] 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页。
[2] 洪治纲主编:《顾颉刚经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47页。
[3] 福 柯:《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5页。
[4] 陈 鹄:《耆旧续闻》西塘集耆旧续闻卷第十,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5][21] 朱东润:《陆游传》,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33,29页。
[6] 顾栋高:《毛诗订诂》卷三国风,清光绪江苏书局刻本。
[7][12] 周本淳:《陆游〈钗头凤〉主题辨疑》,《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
[8] 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3册.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4年,第2037-2038页。
[9] 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刘承干参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66-467页。
[10] 浙江省文学学会:《文学欣赏与评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页。
[11] 陈祖美:《陆游〈钗头凤〉新解》,《名作欣赏》2011年第4期。
[13] 赵惠俊:《〈渭南文集〉所附乐府词编次与陆游词的系年——兼论〈钗头凤〉的写作时地及其他》,《文学遗产》2016年第5期。
[14][24] 欧小牧:《陆游年谱(补正本)》,成都:天地出版社,1998年,第41,31页。
[15] 王兆鹏:《宋代的“互联网”——从题壁诗词看宋代传播的特点》,《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16] 陆游也作过多首题壁诗,但《渭南文集》中130阙词却没有明确标明为题壁的词,参见赵惠俊:《〈渭南文集〉所附乐府词编次与陆游词的系年——兼论〈钗头凤〉的写作时地及其他》,《文学遗产》2016年第5期。
[17] [明]孙能传:《剡溪漫笔》卷四,明万历四十一年孙能正刻本。
[18] 高利华:《陆游〈钗头凤〉是“伪作”吗?——兼谈文本中“宫墙”诸意象的诗词互证》,《学术月刊》2011年第4期。
[19] 陈 著:《跋丁氏子诗后》,详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5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37页。
[20] 李汉超:《陆游〈钗头凤〉词若干问题质疑》,《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22]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第3册卷三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73页。
[23] 根据陆游诗句“梦断香销四十年”可以大致推断唐氏去世时间。详见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第5册卷三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478页。
[25] 程 怡:《“文学事实”及其解释的历史——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26] [法]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 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1页。
[27][清]保培基:《西垣集》卷十八羁魂梦语,清乾隆井谷园刻本。
[28] 吴志翔:《女性叙事:走出戏剧性》,《博览群书》2004年第3期。
[29] 陈文忠:《走出接受史的困境——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30] 从陆游“梦断香销四十年”可以推断出,唐氏在过三十岁后不久去世。
[31] [明]茅元仪:《三戍丛谭》卷六,明崇祯刻本。
[32] [清]况周颐:《蕙风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第245页。
[33] 殷学明:《本事批评:中国古文论历史哲学批评范式探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2017-08-19
袁 茹, 女, 安徽灵璧人, 苏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I206.2
A
1002-3321(2017)06-0011-08
陈未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