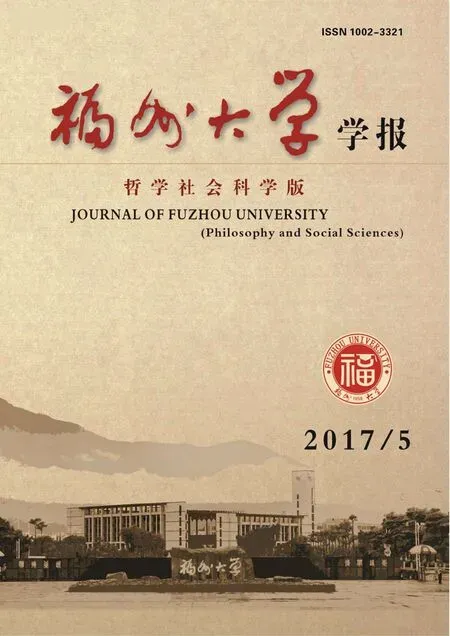非遗语境下当代民间信仰的生存策略与变迁
袁 瑾
(杭州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浙江杭州 311121)
非遗语境下当代民间信仰的生存策略与变迁
袁 瑾
(杭州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浙江杭州 311121)
非物质文化遗产化是当下民间信仰合法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非遗名录以权威的姿态将民间信仰事象纳入文化遗产的范畴,拓宽了民间信仰的社会生存空间。在申报过程中,民间信仰通过对自身文化要素的解释、取舍、重组等方式有意识地向主流话语靠拢,其本身所具有的民俗性、传承性等特征得以彰显。然而诸多人为规则的介入也为民间信仰带来了“碎片化”的危险,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信仰变迁。
民间信仰; 非物质文化遗产; 合法化; 信仰变迁
民间信仰是民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包括神灵观念、仪式制度和象征符号。它包括制度性宗教以外,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秉持的信仰观念和实践的仪式行为。
对于民间信仰,历代统治者往往采取“安抚”加“打压”的两手政策。一方面对那些符合儒家政治伦理道德要求,有利于宣扬道德教化的神灵加以赐封,纳入正祀;另一方面,对一些乡野道观庵庙中的神灵则贴上“淫祠”的标签,捣毁、封杀。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主义与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迷信”很快成为民间信仰的代名词。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民间信仰经历了被取缔,零星恢复,再到大面积复兴的历程。这当中,它不断通过民俗化、宗教化、非遗化等途径寻求合法性的表述。21世纪初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制度建立以来,已有不少民间信仰习俗被纳入其中。非遗化已然成为当代民间信仰合法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关于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三点。首先,民间信仰是否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不遗余力地为民间信仰“正名”“脱敏”,民间信仰作为本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观念逐渐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有学者认为它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在生活实践中的仪式及其表现”[1],是普通民众的信念和仪式。而“中国要使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作为整体立得住脚,就必须先学会从正面看待所谓的民间信仰”[2]。民间信仰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内容已成共识。其次是民间信仰进入非遗名录的标准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民间信仰都能够被纳入非遗名录体系,关于筛选的标准有学者提出“传统性”“伦理性”和“濒危性”三点,并希望藉此推动民间信仰的重构,“共建美好的精神家园”。[3]再次,非遗化的过程对民间信仰产生了什么影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民间信仰在获得合法化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例如信仰内涵的再诠释、传统规则的衰落、各方力量诉求的平衡、新文化语境的适应性与再生能力等。这些问题在有关个案调查研究的论文中都有所提及,研究者无不表达了深切的忧虑。民间信仰的碎片化现象显然背离了它作为民众生活方式的整体性特征与原初面貌。[4]
事实上,进入各级非遗名录的民间信仰事象主要是那些具有一定区域影响力,以群体性、周期性、开放性为特征的信仰与仪式活动,比如祭典、各类庙会、较大规模的祖先祭祀等等。这一类信仰活动往往发生在由特定人群包括各类信仰组织所共享的空间内,以供奉神灵为核心,同时又充满了节庆色彩。
现实中,它们往往扮演了区域社会生活中心的角色,围绕着它们存在着一个整体性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的核心是神灵信仰,然而这不是“基于教祖的教导,也没有教理、教典和教义的规定”,乃是“沿着生活脉络来编成的”,是民众的生活信条和行为惯制。[5]它衍生开去,将祭祀仪式、传说歌谣、社火百戏、庙宇建筑,乃至社会组织、道德舆论等要素统统包括进来。这种历时短暂却周期性发生的文化事象概括展示了特定地域内民众生活的面貌,并能够在多重因素互动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表现出相当的适应性。
一、民间信仰的“非遗化”:途径与方式
自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至今已经公布四批名录,共有1836项(含扩展名录)入选,分为民间文学、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美术、民俗等10个门类。从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来看,民俗门类是直接吸纳民间信仰项目最多的一个类别,并且每一批都有所扩展。第一批名录共列入包括安国药市、厂甸庙会、泰山石敢当习俗以及诸多“节”“祭典”在内的十余项。第二批名录在“信俗”“庙会”的条目下收入各地具有相当影响的民间信仰活动共17项,并加入了抬阁、祭祖习俗等。2014年公布的第四批名录进一步扩充此类项目,其中“庙会”名下共16小项,“信俗”7小项,“祭祖习俗”4小项,并加入民间社火、中元节等。这一过程并不只在国家层面上展开,在各省市名录中也颇为普遍。除此之外,民间信仰还以民间文学、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戏剧等为载体,被纳入各级非遗名录。
如何为民间信仰事象确定合适的名称,是进行非遗申报的重要工作。从现有的名录来看,条目名称组成既有一定规律,又各显神通、别有意味。一般来说,条目名称会采用“地名+神灵称谓+后缀”的方式排列。“地名”“神灵称谓”约定俗成,很难更改,后缀的选择则暗示了申报者对民间信仰事象某些特征的取舍与侧重,也是体现了申报的策略,常见的有“祭典”“祭”“会”“信俗”“节”等不同的叫法。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仪式类、节庆类和信俗类三种。
第一类是仪式类。所谓仪式类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具有重要历史认识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以特定信仰为基础的且充满象征的程序化与规范化的传统行为活动”[6]。仪式类文化遗产一般都保留着一套较为完整的仪礼、仪轨,并以“祭”“祭典”“会”“庙会”“案”等命名。比如黄帝陵祭典、炎帝祭典、太昊伏羲祭典、女娲祭典、妈祖祭典、文成太公祭、网船会、胡公庙会、它山堰庙会等等。这些神灵有的是亘古流传的民族文化英雄,有的是造福一方的良将贤臣,也有望族的祖先。他们或为当地带来福祉,或成为道德的典范,深受民众爱戴,享受香火供奉。
这一类信仰事象的共同特征是仪式规模较大、组织完备、程序严整,有的至今还保留相关的文字记录。比如浙江温州文成县有太公祭,当地是明代开国元勋刘基的出生地,这里的刘氏家族每年正月初一、六月十五举行春秋二祭。历来有官祭、家祭和民间祭祀三种仪式,有礼生、主祭、宾客、观礼、杂役等多个群体,祭品、礼器、乐舞一应俱全。[7]同时,围绕着仪式还包括各种传说故事、歌谣、表演艺术等,这些文化要素通过信仰彼此勾连、形成整体。
第二类是以节庆为名。节日庆典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文化现象,节日类遗产就是民众创造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节庆活动。
传统民间信仰发展为新的节庆活动,以“某某节”命名是当下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一类项目中,民间信仰形态久已存在。历史上当地民众在信仰活动中不断加入各种表演、手工艺制作、仪式活动、歌谣故事等文化要素,艺术性、娱乐性、竞技性特征日趋显著,充满了更加鲜明而热烈的节庆活动的气氛,与节庆命名可谓水到渠成。比如浙江开化平坑村的保苗节,除了驱赶野兽、禳灾祛祸外,最重要的就是祭典明太祖。还有景宁大漈抢猪节则是祭祀地方神灵马娘娘,庙会持续七天七夜。其他“旅游节”“文化节”的名称则更为普遍。
以节庆命名,意在渲染这一类民间信仰固有的世俗狂欢性与公共参与性;其中带有表演性、艺术性、娱乐性的要素得以强化。这种方式拓宽了信仰的社会生存空间,也为当下民间信仰活动与地域公共文化服务的结合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三类是以信俗命名。信俗,将民间信仰定位于民俗形态,强调它的自发性、生活性。作为“民间存在的对某种精神体、某种宗教等信奉和尊重”[8],民间信仰在民众生活世界中具有深厚的心理积淀和文化辐射力,并依其定势散发开去,不经意间包孕在日常的衣食住行、社会交往、用品器物和观念行为中,成为连接各部分文化要素的核心力量。这样形成的与信仰有关的整体性生活模式便是信俗。福建省的厦门闽台送船王信俗、安溪清水祖师爷信俗、柘荣马仙信俗、平和三平祖师爷信俗等都属于这一类。
以“信俗”定名,表明申报者对围绕信仰而形成的生活文化的整体性关照,着意突出其在民众生活世界中的样态。以温州龙湾区宁村汤和信俗为例,这一项祭祀即明初抗倭大将汤和的民间信仰事象在申遗的过程中经历了5次改名。汤和被奉为宁村的祖先神,旧时有春秋二祭,被称为“抬佛”。1994年,当宁村人试图恢复“抬佛”活动时,遭到了阻碍。2004年,“抬佛”被改为“汤和文化节”,祭祀仪式顺利举行。2007年再次改名为“七月十五‘汤和节’”,后成功地进入了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2008年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最终定名“汤和信俗”。从内容上看,汤和信俗除了神灵出巡的祭祀仪式外,还涵盖了宁村“百姓文化”、祭祖、拦街福、中元节等民俗活动,与宁村民众生活水乳交融。
无论是对仪式完整性的强调,公共节庆色彩的渲染,还是民俗生活文化的定位,都是申报者有意识规避意识形态上的模糊,对规则和主流话语体系的主动适应。定名会对民间信仰事象后期演变产生何种影响,现下还不得而知,但非物质名录以权威性话语的姿态将民间信仰纳入文化遗产范畴中,在客观上拓宽了民间信仰的生存空间,将之上升到了共同参与民族国家的建设层面。
二、“非遗化”:民间信仰的新变迁
“非遗化”的过程一方面为民间信仰赢得合法的身份,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为建构的介入,从而引起民间信仰在当下的新变迁。“非遗化”是一个依照标准有意识的筛选过程,进入申报则代表对规范有意识的归属。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民间信仰的定义与分类表明了这一过程的指导思想。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民间信仰的界定
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10]定义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内容,强调了“传统”与“传承”的文化特征。即不论各个文化社团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环境如何变化,这种文化事象必然持续地保持其在社团内的认同感和历史感。这样的表述与2003年联合国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一致的。
在分类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没有就民间信仰作出专门表述,而是将其纳入“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中,定位于民俗文化,即承认其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与传承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表达了我国特有社会文化背景下对民间信仰的认识。
从学理上来看,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信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内在观念、运行逻辑和操作模式也不尽相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颇具现代性的文化概念,它指的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11]。它的运作依托于国家、省、市甚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相关文化部门或者公共组织,进入它的体系标准势必要经过筛选、认定等程序,等级亦有高下之分。民间信仰则脱胎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依附于当地社会生活的肌理,它与民众的衣食住行、社会交往、经济、艺术等领域的活动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申报过程中,申报主体为了某些现实的考虑,根据某些申报条款标准的要求对其中的文化要素进行权衡、选择、排列,重新建构起“遗产化”的文化类型。这样做在客观上为民间信仰的变迁带来了新的力量。
2. 民间信仰内涵的道德化诠释
民间信仰本身是一个多重意识形态庞杂的体系,其中既有原始的万物有灵观念,也有制度化宗教在民间的渗透,还有民间信俗等,这当中也离不开特定社会形态、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与制约。在非遗语境下,长期以来在民众中形成的关于民间信仰的认知与实践很多都经历了“知识化”的再表述。具体来讲就是用普世化的道德价值观对相对复杂、零乱的民间信仰观念进行统合,不再刻意强调其所具有的宗教性一面,而突出其和谐社会的人文教化意义,较多地都归纳为孝德、采吉纳福、民族主义等。
各地“孝子”“孝女”信仰都很普遍,有二十四孝之首的舜、孝女曹娥、孝子周雄、孝妇马仙等。在申报中,孝德成为诠释信仰文化内涵的重点,被打造成文化名片。福建柘荣十三境每年举行一次“迎马仙”祭祀活动,并将之发展为以“孝”为主体的大型文化活动。在绍兴,经过当地文化人士的搜集、整理和演绎,发展出有关舜的二十四孝故事,最终完成了作为孝德代表的舜的形象塑造。
另一些因为“表现了大德、大智、大勇,其文治武功大利于民,为世人景仰、敬慕”,被“推举至神位,赋予一定的神性”[12]的神灵,则通过道德化的诠释走下神坛,转化为当地的文化英雄。流传于台湾、福建、浙江的女神陈十四娘娘,原名陈靖姑,她能够为民除妖,又有助产、祈雨、保境安民的功迹,在闽浙台三地拥有众多信众。相传她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临水村的一个官宦之家,如今古田每年农历3月,都要举办“临水夫人陈靖姑民俗文化节”,有回娘家、祭祀、文艺表演、巡安、发平安饼等活动。文化节期间,海峡两岸宫观代表汇集一堂,祈祝安康,共同纪念这位女英雄。
以民间信仰作为道德教化的方式,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当下对道德伦理的凸显,神而人的嬗变,一方面是和谐社会精神道德建设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视为民间信仰寻求主流价值观容纳的自适应方式。它在传承与演变的过程中不断地建构,也显示出其包容并蓄的特性和再塑的可能性。
3. 民间信仰活动的艺术化、娱乐化倾向
群体性的民间信仰形式,“除了祭祀的香火之外,更为典型地表现在民间艺术上,借以娱神、媚神、酬神,从而娱人、聚人”[13]。庙会、祭典、巡会等历来是各类民间艺术表演的重要平台,艺术门类通常涵盖民间戏曲、传统音乐、民间舞蹈、杂技、民间手工艺等。有的民间信仰则以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曲等为载体进入名录,足见当下民间信仰活动艺术化、娱乐化的倾向。
浙江金华永康方岩庙会中,上山朝拜神灵胡则的每一支队伍除了胡公神龛外,都拥有人数颇多的文艺表演队。表演内容有“讨饭莲花”“敕字莲花”“长脚鹿”“罗汉阵”“龙舞”“三十六行”“十八狐狸”“九狮图”“彩车”“十八蝴蝶”“哑口背疯”“荷花芯”等三十余种。各类表演风格各异,或粗狂豪放、或激昂阳刚、或精巧灵动、或细腻柔美,精彩纷呈,深受民众喜爱。
民间信仰中的民间艺术表演具有很强的生活气息和广泛的参与性。这些表演的内容来源于日常生活,反映了民众的审美需求与心理需要。在艺术造型上往往色彩鲜明浓郁,具有求吉纳祥、驱邪避害的功能,很能够渲染情绪、调动气氛。
然而繁华热闹的表象之下,我们也应注意到,尽管活动的核心仍是信仰,但艺术娱乐的成分明显超过了信仰或者说对意义的理解。传统生活场景渐行渐远,也影响着当下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其中各种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的解读,仪式的意义日渐淡薄。如何保持文化意义的传递,避免过度娱乐化、低俗化将是后非遗时代民间信仰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
4. 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发与利用
进入非遗名录必然会涉及保护、传承、活态等问题。非遗项目的保护利用有明确的法律条款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14]在文化产业的思路下,进入各级非遗名录的民间信仰项目很快被作为地方文化资源参与到旅游开发、节庆活动、文艺汇演等社会经济文化实践中。
这当中旅游景区的开发与民间信仰活动相结合至今仍然较为普遍,并被宣传为“深度旅游体验”。民间信仰的庙宇多建在名山大川、风景秀丽之处,旅游资源丰富,加之充满民俗风情、热闹气氛的庙会活动能够带来新鲜的文化体验,提升旅游的品质,很快地能够带来更多附加值的旅游景区整体的开发营建就出现了。嘉兴莲泗荡刘王庙景区便是其中一例,这里周边水域宽阔、风景宜人。2000年,莲泗荡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确定了 “以香客带动游客,开发旅游资源”的发展方针。在经过一番基础设施的改建完善后, 2008年,举办首届“江南网船会”。2010年4月,又举办了第二届中国江南网船会。此次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包括民俗文艺演出、水乡龙舟邀请赛、王江泾镇运河旅游线路策划研讨会、 摄影报道活动、“船民祭祀活动”、民俗风情摄影大赛6个项目,为期两天,参与人数超过万人。
此外,在传统节庆活动中加入民间信仰活动内容,以此丰富节庆内容、活跃气氛也是当下不少地区的惯见做法。比如春节各地都有庙会,正月初五财神游街,清明节杭嘉湖一带蚕花庙会,端午祭祀伍子胥、屈原,七夕乞巧等等。
通过上述各种形式的活动,庙会、祭典等民间信仰活动不再是敏感、隐蔽地局限于私人空间,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成为一个在具体场景时空中被国家容纳、承认的文化现象。但是旅游开发、过度资源化也对民间信仰本身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打破了其惯有的运行逻辑。以旅游景区为例,由于门票的限制,加之开发主体通常是旅游发展公司,民间信仰惯有的开放性与公共性被打破,生活流被阻断,破坏了民间信仰之于民众日常生活意义建构的作用。
三、结语
在当代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化无疑是民间信仰争取合法化、拓宽生存社会空间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进入各级非遗名录,民间信仰暂时规避了因为其宗教属性而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困扰,它的“传统性”“民俗性”“文化性”“地方性”特征得以彰显出来,从而成为民族国家发展模式下文化自主性、延续性的代表。然而遗产化对民间信仰同样也存在着干扰,诸如模式化运营、过度商业化、千庙一律、庸俗化等问题不容回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民间信仰争取合法身份提供了重要的一条途径,但它并不是民间信仰本身,民间信仰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变迁、重构也不应以进入非遗名录为终极目标。
民间信仰传承至今,绵延不断,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现实的需要。研究、分析、处理好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就是要促进民间信仰的积极健康发展。当下,如何解析民间信仰对民众日常生活意义的建构,如何使其在当代中国本土信仰延续方面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仍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注释:
[1][2] 高丙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民间信仰》,《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3] 萧 放:《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民间信仰重建》,《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5期。
[4] 关于这方面的个案可以参阅如下论文:王海东:《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互动关系——以上海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6期;周 星:《民间信仰与文化遗产》,《文化遗产》2013年第2期;冯智明:《人类学整体论视野下民间信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化——以广西虹瑶为个案》,《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王霄冰、林海聪:《妈祖:从民间信仰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2013年第6期。
[5] [日]渡边欣雄:《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页。
[6] 苑 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7] 林亦修、林小雯:《文成太公祭》,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5年,第62-110页。
[8] 王景琳:《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词典》,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11页。
[9] 邱国珍、陈洁琼:《汤和信仰的历史传承与申遗策略——以温州宁村汤和信仰为例》,《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0][1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12]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2页。
[13] 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2017-06-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状况研究”(16AZJ007)
袁 瑾, 女, 浙江杭州人, 杭州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K892.24
A
1002-3321(2017)05-0013-05
[责任编辑:石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