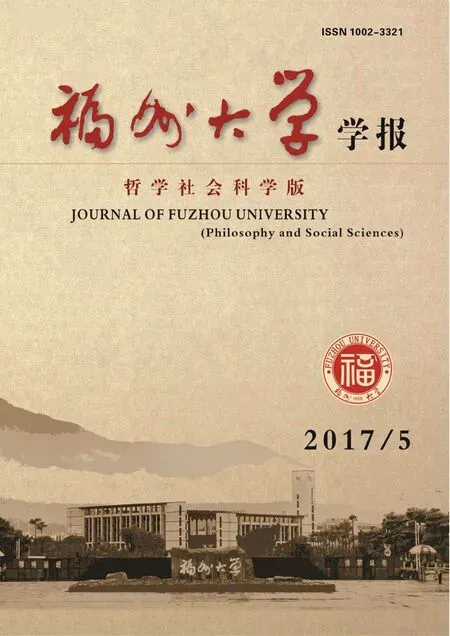文化转型与“非遗”困境:基督教对中缅跨境民族民间信仰乐舞发展的影响
徐祖祥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文化转型与“非遗”困境:基督教对中缅跨境民族民间信仰乐舞发展的影响
徐祖祥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在民族民间信仰日益弱化的背景下,随着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各项“非遗”保护项目的实施, 出现了市场化、艺术化和世俗化的趋向,其中去宗教化和民俗化的特点尤为明显。在以“非遗”主导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基督教发展和现代化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民族乐舞的发展表现为一种混融状态,但由于文化生态的核心已由过去的民间信仰转化为基督教信仰,其发展主要表现为基督教化和民俗化的趋势,“非遗”的历史主义取向陷入了尴尬的处境。
中缅跨境民族; 基督教; 民间信仰乐舞;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转型
在中缅跨境民族地区长达2000多公里的地段上,我国境内分布着10多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在历史上以不同内容和各具特征的原始宗教为核心,构成其传统的文化体系。在社会文化变迁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冲击下,其原始宗教经历近现代的衰变和转型,逐渐蜕变为民族民间信仰。我国当代各种“非遗”项目在这一地区所涉及的对象,多数与其民族民间信仰有关。刘锡诚先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与民间信仰粘连在一起,或可是民间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或可是民间信仰形式的组成部分”[1]。他的这个论断,主要针对我国汉族地区的民间社会而言,即使放到少数民族地区来考察,仍然十分贴切。然而,基督教在清末民初传入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后,在傈僳、怒、景颇、拉祜和佤等民族中不断发展,改革开放后发展尤快,至今已在怒江州多数地区以及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保山市的部分地区形成相对稳定的基督教文化区。与此同时,基督教文化区内信教群体中的民间信仰体系几近瓦解。近年来,在各种“非遗”保护项目的推动下,整个中缅跨境民族地区从官方到民间都掀起一股“非遗”热潮,刺激并带动了基督教文化区内传统文化的“复兴”。但被去除了民族民间信仰土壤的各种“非遗”项目,从保护对象的寻找到已实施项目的功能发挥,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困难。各民族的民间乐舞本是民间信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初传时被列入教规中明令禁止,当前又成为“非遗”保护的重点对象。在各种力量交互作用下,尤其是在基督教的排斥、改造和整合下,民间乐舞的发展状态和趋向无疑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对象。
一、中缅跨境民族地区“非遗”保护的现状及趋向
中缅跨境民族的文化转型几乎是与近代以来发生的多次社会转型相对应的,但在改革开放以前,无论是民族主体还是当时的学界和政府,都没有认识到文化转型对民族发展带来的影响。改革开放后,随着传统文化转型的现象完全表面化,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才得到应有的重视。进入21世纪后,云南省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推动下,实施了一系列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工程,对各民族从内部积极传承民族优秀文化起了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然而,在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基督教成为新的文化生态核心的背景下,各种“非遗”措施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带有世俗功利趋向的“非遗”工程在去除各种传统文化因素的传统宗教内核中,对传统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市场化和艺术化趋向
“非遗”保护的市场化和艺术化是最为突出和显性化发展的两种主要趋向。杨志明教授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趋向归纳为市场化和艺术化,这也是多年来各级政府和一些民间社会组织在“非遗”保护方面采取的措施和引导的方向。[2]在市场经济的商品价值观的指导下,将各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提炼出来,通过艺术化、商品化、产业化的发展路径,将文化推向市场,激发民族群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引导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因素的整合和融合,为民族文化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促进民族优秀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市场化与艺术化是民族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物两面现象,两者通常在具体的文化传承和保护中并列存在。
在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氛围中,中缅跨境民族地区逐渐兴起一些传统文化复兴的现象,但其中内含的市场化和艺术化趋向十分明显。怒江州泸水县上江镇新建村作为一个傈僳族村落,位于进怒江州府六库的道路旁边,村里仅有几个基督教徒,绝大多数保持传统的民间信仰。村民HGZ在本地组织成立了宣扬傈僳族传统乐舞的艺术团体,即泸水县上江镇新建村民族民间艺术团,并得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被纳入了非物质文化传承保护的范围。新建村民族民间艺术团主要内容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傈僳族舞蹈、民歌合唱、上刀杆、民族乐器展演,二是制售民族服饰与民族乐器,通过商业发展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HGZ的艺术团团员全部来自本村,均为中老年人,以老年人居多,每周特定时间齐聚HGZ家中培训傈僳族传统乐器与乐舞,经常受邀前往各地表演,宣传傈僳族的传统文化。[3]当地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已经完全不会傈僳族传统的乐舞和乐器,这对于傈僳族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提出新的挑战。新建村的例子从另一个侧面思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途径和方法,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在这种趋向的引导下,各跨境民族地区的“非遗”保护工程的实施中,被列入“非遗”保护名录的传统文化事项和文化传承人涉及的范围大多为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等领域,范围十分狭窄。在怒江州许多地区,近年政府投入“非遗”保护资金时,竟然陷入难以寻找保护项目的窘境,国家、省、州、县各级非遗保护名录中,大部分是经过“深度挖掘”后找出的项目,所涉及的领域多为属于表层文化的民间乐舞、传统工艺、民族服饰、传统习俗等,其中尤以民间乐舞为重点,很少接触到信仰层面真正属于文化内核的内容。比如至2014年9月,怒江州福贡县共建立了省、州、县级共4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多集中于文学艺术、传统工艺、民俗文化、民族语言、民族体育等领域。具体包括怒族语言1项,民族民间口传文学4项,民间音乐6项,民间舞蹈7项,民间美术2项,民间传统工艺7项,民族岁时节令2项,游艺与体育2项,民族民间传统习俗9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区2项(马吉乡古当村、匹河乡老姆登村),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乡2项(石月亮乡米俄罗村歌舞之乡、鹿马登乡赤恒底村传统服饰之乡)。其中2006年5月列入云南省第一批省级保护名录的有4个项目,即马吉乡古当村傈僳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怒族民间音乐“哦得得”、怒族民间舞蹈“达比亚舞”和傈僳族民间舞蹈“刮克”。2013年11月列入云南省第三批省级保护名录的有傈僳族怒族器乐“口弦”。2014年8月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有怒族传统舞蹈“达比亚舞”。2013年,福贡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组织申报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抢救保护项目”有:“傈僳族怒族传统乐器口弦”“傈僳族传统乐器起奔”“傈僳族怒族传统乐器笛哩图”“傈僳族传统舞刮克”“怒族节日习俗如密期”“傈僳族传统舞迁俄”“改编傈僳族长篇历史小说电视剧本《怒江往事》”等7个项目,涉及领域全属民间乐舞和文学。从1999年6月至2014年9月,福贡县共有58个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列入省、州、县三级保护名录,涉及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服饰、竹编工艺、传统乐器、民间文学、宗教祭祀等领域。其中省级传承人12人,州级传承人24人,县级传承人22人,但自1999年启动传承人项目至今,已有8人去世,健在的传承人中,老年化趋向十分突出。在经费投入方面,福贡县5个省级非遗保护项目由云南省文化厅投入了60万元,除前期研究用了10万元外,每个项目各有保护资金10万元。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补助由云南省文化厅每人每年发放3000元传承补助,2013年以后增加至5000元。政府有关部门还开展了其他非遗保护措施,比如建立省级非遗项目和省级传承人的“非遗项目数据库”,建立了详细的数据库档案。州县级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也建立了内容丰富的文本档案资料、图片和音像资料。除了建立非遗项目名录和非遗传承人名录外,政府有关部门还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实质性的工作。如近年福贡县政府投资建立了“怒族传统文化保护传习馆”,为民间艺人学习、交流、传承民族民间技艺提供了平台。同时,还在县城建立了民族文化“宣传文化中心”和文化广场,为每个行政村建立了“农家书屋”和“文化活动室”,在每个行政村建立了农村业余文艺队。这些行政性的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引导民族群众自发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意识和行为的作用,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创造了外部氛围,增加了民族文化自信感。
然而,文化的市场化涉及的通常是民族文化中“可视”且具有审美文化意义的文化事项。各文化事项在走向市场之前,往往经过了文化的改造,掺入了现代意义的内容和形式,填补了一些新的社会文化内容,这实际上是一个艺术化的再造过程。于是文化的产业化成为引领民族文化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路径,民族旅游业的兴盛成为必然的结果。然而这种文化发展趋势对民族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十分明显,即不具可视效果的、难以商品化的大量文化因素往往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被贴上“无用”的标签而在文化变迁大潮中逐渐隐去和消失。
2.“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世俗化趋向
除了上述两种显性存在的文化保护趋向外,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还表现出隐性的世俗化趋向。当今世界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变,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和现代教育的影响,以及促进其改变的世俗社会中不断涌现出的新文化因素及其体现的现代性趋向,是导致文化传承和保护脱离传统社会依赖宗教文化的传统轨道,转向世俗化路径的主要原因。民族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反应到文化领域,必然导致传统宗教神圣性的淡化,强调仪式和活动的娱乐性和商业性目标。
这种世俗化趋向包括以下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是传统文化的“去宗教化”趋向。具体表现为,神圣的宗教文化被迫走向文化市场,在宗教文化领域带来一系列民俗化的连锁反应。传统宗教的仪式和活动被局限于节日、艺术活动的范畴,过去作为宗教仪式组成部分的传统歌舞、音乐和仪式的功能由娱神向娱人转化,宗教活动的仪式和活动程序被人为改变和简化,以强调其艺术效果,传统宗教构筑的彼岸世界变得模糊不清,神灵世界失去了过去曾有的神圣光环和威严。传统宗教不再成其为宗教,而逐渐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基督教传入有些民族地区后,基督教会对这些原本属于宗教领域的文化事项重新进行解释和改造,将其视为世俗层面的民俗文化,而不再视其为“宗教”的根本原因。
二是传统文化的民俗化趋向。在传统宗教文化被漠视的同时,重视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尤其是节日、服饰、艺术等可视的民俗事项成为传承和保护项目的重点对象,是当今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一个趋势。然而,民俗文化虽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在剧烈变动的社会环境中,自身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迁。民俗主要通过语言与行动来进行传承,从而“决定了民俗在历时的和共时的传承过程中,不断适应周围环境而做出的相应变化”[4],因此形成了变异性这一显著特征。所谓民俗的变异性指的是“民俗传承和扩布过程中引起的自发和渐进的变化”[5],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变化的持续性。
景颇族民俗的嬗变与其本身的变异性密切相关,由于其传统社会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宗教仪式、民俗事项只能依靠口传及具体行动进行转述与表达,因此转述或表演者的自主发挥空间较大,特别是民间信仰的祭献活动中,祭词可由巫师董萨据仪式的需要随意发挥,这与董萨的语言习惯、知识储备、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因此,与有文字的民族相比,景颇族信仰民俗的稳定性相对较差,极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此外,民俗还具有一种变革式的变异,同样也是民俗自发而产生的。如景颇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随着景颇族思维方式的不断成熟,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演变,甚至消失。这种自发渐变的形式使原本就不稳定的景颇族信仰民俗在遭遇基督教文化入侵之时很快就失去抵御能力,给基督教主导下的新的民俗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基督教影响下民间信仰乐舞发展的趋势与困境
在基督教及现代社会转型中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当前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陷入尴尬的境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基督教信仰区域内,所谓的传统文化已经是基督教化的零散的诸种文化因素,并非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丛。二是当前政府部门主导下的传统文化保护的主要对象,大多属于传统文化中的艺术、服饰、体育、语言等表层文化事项。未涉及世界观、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宗教领域。
当前中缅跨境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现状不容乐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倡导和推进者未从根本上弄清他们所要传承和保护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这些受保护的文化因素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结果是花费了大量的经费和人力、物力,却总是达不到预期的保护效果。由于当前各种“非遗”保护项目所涉及的对象,要么是受到了基督教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后涵化的某种民族文化现象,要么是与作为文化传统核心的宗教信仰没有直接关系的表层文化事项。因此随着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新文化模式的形成,“非遗”对象的内容、形式和功能发生了改变,其传承的“民族文化”已非原生形态的传统文化,而是宗教文化内核已被置换的新的文化传统。
第一,基督教的排他性对传统民间乐舞的排斥和改造,使大量传统乐舞消失,同时通过对乐舞中民间信仰属性的摒弃,改变了其文化功能。
宗教与乐舞从来就有难以割离的紧密关系,乐舞在多数宗教中都具有娱神的功能,同时也是主持仪式的神职人员与神沟通的媒介。当两种性质不同的宗教相遇时,新传入的宗教必然对原有宗教的乐舞采取取缔或禁止的做法,以保证其宗教得以顺利传播,并确保宗教的纯洁性。基督教是一个音乐、诗歌特点鲜明的宗教。[6]《圣经》中记载有大量的诗篇,《圣经旧约》中就收录了150余篇诗歌,内容主要是对神的赞美,咏唱时需有弦乐器伴奏,一般有应答式、直接式和交替式三种唱法。[7]从性质看,各民族的传统乐舞均与民间信仰有关,直接构成祭祀仪式的一个重要甚至核心组成部分。比如傈僳族的祭祀歌就统称为“尼祜哦”(祭祀“鬼”唱的歌),有“招魂歌”“占卜歌”“山鬼祭歌”“路鬼祭歌”“家鬼祭歌”等三四十种之多,巫师尼叭带领众人唱跳,娱神以求达到世俗目的。有的民族乐舞除了富含宗教观念和祭祀行为外,还包含了丰富的民族历史与族群记忆,是该民族宇宙观与伦理价值观树立的根源。又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本是一种群体性的大型祭祀仪式,其中由董萨带领族人围绕目瑙迂回曲行的舞蹈路线,以及目瑙上刻画的菱形、回纹、云纹等连体图案,就是其艺术抽象化的祖先南迁之路。因此,在基督教传入的早期,几乎所有地区的传教士都有关于禁止民族乐舞的规定和做法。传教士订立摒弃传统乐舞的教规,说明他们对各民族传统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对可能或正在抵制其传教行为的民族文化系统发挥作用的那些因素有深刻的切身感触。早期教规中禁止传统乐舞的规定,实际上不仅试图彻底从视觉和意识层面消除民间信仰的痕迹,还从民族历史记忆和世界观层面改变其宇宙万物来源的本体论认识,从而得以从《圣经》中关于上帝创造万物的角度进行全新的世界观解释,建立起以基督教为中心、以民族意识为体液的新型亚文化。然而,在全球化和现代化面前,传统乐舞和基督教均面临着挑战。从调查的情况看,他们均采取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策略,不断地寻找合适的方式以应对受到国际大环境影响的区域内社会发展和文化生态的变化。
中缅边境基督教会对傈僳族中上刀山下火海、民族乐舞等传统文化因素的态度,在不同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别。以傈僳族传统舞蹈“打跳”为例,过去怒江地区教会禁止信徒参与传统的打跳活动,虽然近年出现松动迹象,但整体还处于基督教教规的束缚中。与怒江州相邻不远的德宏州陇川县章凤傈僳族教会只允许信徒在非教堂区域唱跳,在教堂是绝对禁止的。但再往南的耿马、镇康、永德等地的傈僳族教会已经积极推动傈僳族传统打跳舞蹈的复兴,并将之搬到教会聚会活动中。例如,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满福堂教会,在个别牧师的支持下,傈僳族年轻教徒的传统打跳舞蹈表演已登上教会礼拜的舞台,并深受信徒的喜爱,但此举遭到临沧市两会以及耿马县两会中部分高层教牧人员的反对,认为将民族传统的打跳舞蹈植入教会礼拜过程是与基督教信仰相违背的。这与基督教传教过程中,传教士最初所作的规定密切相关,也与其基督教信仰自改革开放之初恢复后,受基督教在不同地区的信教规模、各地不同民族杂居的社会环境、当地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和基督教协会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影响有关,由此形成了地区性差别。德宏南部、临沧地区的傈僳族人口不多,多数为后来搬迁而来,在各地与傣族、景颇族、佤族等民族交错而居。恢复基督教信仰后,虽然本民族村寨中多数傈僳族群众皈信了基督教,但在区域内整体宗教生态和文化生态环境中,基督教群体明显属于少数。景颇、佤等民族多元宗教共存的社会环境带给各族信教群体的心理暗示,在多民族共处的基督教两会管理层中产生相互影响的效应,并对基层教会的管理和信教群体的文化选择产生影响。
怒族传统文化发展遭遇基督教后也受到诸多限制与阻碍,传统的怒族乐器“达比亚”、民族舞蹈“哦勒勒”等被禁止弹、跳,基督教会试图将怒族传统的不利于基督教传播发展的文化要素都从其日常生活中剔除出去,实现基督教信仰及其文化的全面替代。因此,因保护不利、传承失继以及外来力量的冲击与破坏,怒族传统文化已变得面目全非。民族乐器达比亚,类似傈僳族的琵琶、三弦琴,其弹法及组合变化多样,当前除一些老人外,年轻人基本不会。在笔者调查期间,刚进入福贡县老姆登村时,村里多家旅馆均以“怒族达比亚”命名,可以看出达比亚除去其乐器的基本功能外,已经上升为怒族的民族象征。基督教在进入怒族社会时将达比亚踢出其日常生活,并且在当前的教会活动中乐器已经被吉他、电吉他、电子琴等现代西方乐器所取代。或许基督教传入之初因其西方背景,加之西方赞美诗等曲调全部由西方乐器谱曲而来,从而导致当前傈僳族、怒族等信仰群体尝试用民族乐器,去迎合赞美诗、舞的曲调以及创造新的由民族乐器创造的赞美诗、舞等实践面临失败的结局。信教之初怒族信徒为了在信仰上更为纯粹、正统,因此积极采用与基督教同属西方文化属性的乐器,而抛弃与传统宗教信仰同属性的民族乐器。
近年我国景颇族地区早期传教士禁止唱跳民族乐舞的规定已名存实亡。传统民间乐舞、祭祀乐舞与基督教因素的融合与共存,是景颇族社会中的一大特点。如盈江县龙盆村的MRM长老介绍说:“刚开始传入的时候,景颇族信徒是不准跳民族舞蹈、不唱山歌的,因为景颇族的舞蹈、歌曲基本上都与信鬼有关的。现在很松了,可以跳舞、唱歌了。毕竟信仰是信仰,民族习俗是民族习俗。”[8]在景颇族的传统节日上,各种传统乐舞的表演仍然十分风行,基督教徒可以参加几乎所有的歌舞活动。在目瑙纵歌节上,基督教徒可以参加除祭祀仪式以外的所有环节,各地教会对此的解释是普通信徒可以参加一般乐舞的唱跳,但不准参加祭祀环节的所有活动。
景颇族传统丧葬舞中的宗教性质被剔除,信教群众只从民俗的角度予以接受和传承。即便如此,也与怒江地区教会严格禁止各种民族乐舞有极大的不同。现在一般性的景颇族文化或民俗介绍材料中,经常只介绍其民族乐舞的艺术性,或说其乐舞表现了经济生活的若干内容,而忽略其民间信仰的性质和内容,对其乐舞的原生出处也一笔带过。景颇族传统葬礼的祭祀仪式中,常配以宗教内容的丧葬舞蹈,最常跳的有“布滚戈”“龙洞戈”“恩刚斋”和“金再再”。“布滚戈”因其节奏强烈的“咚叮”乐声又被称为“跳咚叮”,分为种板豆和种棉花两种套路,要请董萨带领大家唱歌颂死者功德的送魂歌“本阳阳”,其意大致是死者生前带领家人很好地生活,死后就放心的带着你的东西,沿着祖先迁徙之路,回到北方老家去做个好鬼,并保佑在这边的子孙人畜兴旺。景颇族人认为人死后是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去重新生活,在那里仍然需要像在生前一样从事农业生产,因此要带各种种子和农具上路。“龙洞戈”“恩刚斋”和“金再再”是驱邪赶鬼的舞蹈,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死者的灵魂不受沿路的恶鬼怨魂拦路索命,顺利抵达北方老家,与祖先团聚。因此男性舞者要手持长刀或火枪,女性舞者则手持芭蕉叶或扇子,做出各种撵鬼杀鬼的动作。[9]皈信基督教后,信徒葬礼上已经不再跳这些丧葬舞蹈,而是用祷告代替。但近年来,丧葬舞蹈中的宗教祭祀成分消失或被剔除后,已演变为纯粹艺术表演形式的舞蹈,成为一些活动的表演节目留存下来,其传承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了本质性的改变,于是基督教徒也积极参加到舞蹈表演活动中来,当地教会对此不作任何限制。虽然景颇族传统乐舞与民间信仰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摒弃其中的信仰成分,或其中的信仰因素已自然淡化或消失,景颇族教会将之视为一般性的文化因素,从而改变了早期传教士的做法,灵活处理了教规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足见基督教在发展中对文化环境的适应性。
与此同时,各地基督教会通过将一些传统乐舞予以改造,与基督教的一些宗教艺术形式和内容结合起来,同时接纳一些现代元素,达到其融入当地社会、为普通信徒所接受的目的。但如此一来,基督教艺术及其宗教性对传统乐舞发展方向的引导和改造就成为潜在的客观存在,对“非遗”对象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本是完全宗教性质的赞美诗,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增添了不少现代风格的形式和内容。结合各民族乐舞的传统,以赞美上帝为主要内容的赞美舞融合了民族传统乐舞的形式而广泛流传。怒江地区基督教会经常举行各种神学培训以及教务指导等活动,其中赞美诗与赞美舞的现场传授深受中青年基督教徒的欢迎与喜爱。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基督教赞美诗不拘于传统的曲调形式,更具灵活性,针对不同的信徒群体积极创制适合的赞美诗。以年轻人喜爱的流行风格的赞美诗为例,往往以国内外流行音乐的乐谱,配以基督教赞美诗的新内容重新创作而成,如此一来既满足了年轻人对流行音乐的追捧,又起到信仰教化的作用,从其可看出基督教所拥有的极强适应性。基督教的赞美舞其内容全是赞美上帝,因傈僳族人对舞蹈的热爱,因此傈僳族传统舞蹈在教堂被禁止以后,基督教便对当地傈僳族的文化要素积极予以改变,既保留舞蹈在傈僳族人心中的位置,也通过舞蹈强势传播基督教信仰,这也算是基督教在傈僳族社会本土化实践的表现。因此每当各地方教会出资请外面教会的舞蹈老师前来教授赞美舞时,会吸引绝大部分年轻人前往学习,包括领近村寨的青年人。在培训过程中,教会还会组织当地信徒使用DV等器材将过程录制下来,后期制作成光碟分发给教会信徒。二是在政府主导的民族文化“非遗”保护措施的带动下,各民族民间开始出现一些“非遗”保护行为,然而“非遗”保护对象经基督教改造后已民俗化和基督教化。
在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对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引导下,一些地方开始自发或半自发地组织传统歌舞团等民族艺术团体,从事民族传统乐舞的表演和传承活动。但由于传统乐舞中的民间信仰因素已式微或被剔除,同时受现代潮流的影响,年轻一代对传统艺术的传承和保护缺乏应有的热情和关注,使传统乐舞的传承陷入尴尬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基督教徒的潜在身份参与和传承其民族传统乐舞,其内心深处对这些传统文化要素的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心理、文化行为已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比如当前福贡县鹿马登乡傈僳族文化的传承与恢复开始出现苗头,就鹿马登九个行政村的民族文化恢复与传承的具体行动及反映的情况而言,基本由村委会干部牵头,这一批干部深受民族文化复兴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影响,深刻认识到传承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受其影响,许多教牧人员和普通信徒都积极投入到传统文化的保护中来。当然,其中民族自觉意识复苏的背后离不开将民族文化资源化、经济化的市场经济逻辑在背后的推动,而且民族文化复兴主要集中于民族乐舞、民族乐器、民族服饰、民族风俗等可视文化上。巴甲朵村在年轻村委干部的带动下,自发组织民族传统乐舞的编排,组建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傈僳族传统歌舞团,得到了福贡县有关部门及乡政府相关负责人的支持与好评。目前巴甲朵村的中青年基督教徒在村干部的倡导下正在积极排练傈僳族的传统歌舞,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予以创新。巴甲朵排练的所谓傈僳族传统的乐舞形式已不再那么传统、纯正,其中杂糅了很多现代流行元素,例如借用现代录音技术弥补其传统乐器弹唱技能的缺失。虽然普通民众对于复兴本民族传统文化保持极高的热情,其中不乏民族的自觉意识,但娱乐心态的促发可能才是人们积极参与的主要推力。据巴甲朵村人武干部介绍,巴甲朵掀起的排练傈僳族传统歌舞的风潮已经影响了邻近赤恒底、布拉底、赤洒底等几个村寨,这些村寨也在积极组织村民排练歌舞表演等。就巴甲朵村的情况来看,傈僳族人当下的精神需求满足主要有参与教会活动与现代娱乐方式两种,其中现代娱乐方式主要是电视、手机、电脑等所能提供的精神满足,对于当地非基督教徒而言,现代娱乐方式带给他们的精神满足是浅表化的,无法深入其内心深处。因此传统民族乐舞的恢复对他们来说既是娱乐休闲的新刺激,也是带有浓烈民族意识的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因此其意义是深远的。
景颇族社会中也面临相似的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困境,要么保护的对象已经基督教化,要么就是只涉及表层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过去景颇族文化与民间信仰几乎融为一体,并通过各种宗教祭献仪式显现于景颇族文化之中,而基督教一神信仰与原始多神信仰的冲突与对立,致使基督教在景颇族地区站稳脚跟之后大力着手于文化中的宗教祭献变革。景颇族祭献仪式在传统社会中起着文化熏陶与传承的重要作用,是景颇族传统教育的重要形式。每次祭献,董萨都要将这一习俗的来源在祭献中表述或展现出来,特别是目瑙纵歌祭献活动中大斋瓦吟诵的《目瑙斋瓦》,其内容包含了族源、民俗来源、南迁历史等,这些皆为景颇族的集体记忆,每每吟诵之时,都是对景颇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回顾,潜移默化之中景颇族文化体系得到进一步稳固。但是,这种传统文化的状貌如今已发生极大的改变,景颇族社会文化体系中承载文化传统的传统宗教的衰落和被基督教所置换的宗教信仰,彻底改变了景颇族的文化生态,直接影响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以基督教的文化排他性的特性来看,基督教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所进行的所有文化行为,本质上都是从其教义教理为出发点,经过文化选择后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展开的文化融合。我们在田野调查访谈过程中发现,众多信教群众对景颇族传统民俗的来源、禁忌等都知之甚少。当笔者问报告人是否知道为什么要过新米感恩节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信教群众都告诉笔者,“因为耶稣保佑了我们,让我们收成好,所以我们要感谢他”。这与景颇族传统新米节的内涵大相径庭。此外,诸多民俗节日在信教的景颇族地区已经不存在,如盈江县那邦镇的那邦村已经不再祭献“能尚”[10],甚至因为村干部向政府申请经费在村里建起了“能尚”,而遭到了信教群众的抵制与反对。即使连景颇族盛大的民族节日目瑙纵歌,在信教群众中的影响也逐渐衰弱,信教群众不再全程参与,仅参与跳舞这一环节。而盈江县龙盆村的景颇族基督教教会也正积极改革,以期将目瑙纵歌变成由牧师祷告代替大斋瓦(大巫师)祭献的节日。事实上,基督教会正努力在景颇族传统文化的“创新”方面作出努力,但其努力的方向,是将传统文化进一步改造为基督教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相反。
第三,受来自缅甸北部同源民族信仰群体和现代化的影响,跨境民族地区基督教信教区域内民间的艺术环境已基督教化,并不断适应现代社会各种现代性因素的变迁。
以音乐为例。在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傈僳族、景颇族、拉祜族和佤族的基督教信教群体中,信徒日常生活中所听的歌曲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由内地传播至此的现代流行音乐;二是缅甸各族所录制的反映其日常生活的民族歌曲;三是宣扬皈信基督教的歌曲和境内教会派发的基督教灵修歌碟,而各民族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歌基本被抛弃。其中由缅甸录制的民族歌曲最多,远远超过另两种歌曲在中缅边境地区的流传面。依据年龄区分,二者在各年龄层所占比例不一。在青年人中,现代流行歌曲通行其中(部分虔诚基督教徒除外)。中年人中其比例各占一半,但随着大众传播媒体的大规模进入以及代际更替,流行音乐所占比例将会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如怒江地区傈僳族村寨中老人基本已皈信基督教,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主要听基督教性质的音乐,助其灵修。福贡县城及鹿马登乡市场上售卖的光碟绝大部分为缅甸傈僳族制作的本民族内部通行的民族歌曲、MV,其中反映基督教性质的乐舞内容占近一半的比例。而在城镇中现代流行音乐绝对占支配性地位,其获取的途径依赖大众媒体以及网络渠道,教会派发给基督教徒家庭的灵修光碟就总体数量而言相对较少,但就其影响力而言,还属于强劲的势力。在德宏地区景颇族社会中,同样流行上述三类音乐。这一带流行的民族歌曲和基督教音乐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缅甸。缅甸克钦族录制的歌曲不拘于传统的曲调形式,针对不同的信徒群体积极创制适合其风格的民族歌曲,其中就包括Hip-Hop、R&B、重金属等现代流行元素,颇具灵活性,并且在录制过程全部采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因此对滇西同源民族具有极强的民族亲缘性。歌曲内容主要以宣扬基督教信仰、赞美民族优秀文化为主,其中宣扬皈信基督教的歌曲内容占有很大比例。
在南部的拉祜族地区,教会音乐以及非教会的拉祜族音乐主要由缅甸拉祜族创制并传入境内,占据着境内拉祜族音乐享受中的绝对地位,不管是手机播放还是随口吟唱,随处都可听见这样的曲调。近几年境内拉祜族歌手也不断崛起,例如凭借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出名的拉祜族民族歌手扎约以及流行于拉祜族内部的“猎虎组合”,扎约如今被拉祜族民众视为民族的代表人物而受到热捧,其创制的拉祜族音乐流传于拉祜族家家户户。就歌曲的内容比较而言,境外拉祜族歌手及其音乐创造团队主要集中于爱情这一永恒主题以及赞美上帝,而境内拉祜族歌手创作歌曲内容的主题则集中于爱情以及对拉祜族民族传统文化及自然环境的宣扬与赞美。例如“猎虎组合”所创作的拉祜语与汉语的双语歌曲《神鼓之乡》,即是赞美拉祜族传统祭祀器具神鼓的。随着境内拉祜族歌手的崛起及其所创歌曲的流行,与境外拉祜族在歌曲主题内容上的差异以及境内拉祜族歌曲的双语创造,折射出拉祜族境内外文化发展的差别。面对缅北同源民族录制的民族歌曲,当前滇西跨境民族基督教会也正在积极地筹划录制属于自己的民族歌曲,其歌曲也以宣扬基督教信仰以及赞美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例如糯福教会就将2014年风靡全中国的《小苹果》用拉祜语改变成宣扬基督信仰的全新形式,并为此特意编排了一段节奏欢快的赞美舞。
三、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现代化和基督教交错发展的冲击和影响下,民间信仰生存的文化生态早已转型,基督教已成为文化发展方向的主导力量之一,“非遗”保护的历史主义取向已难以寻找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归属。在政府有关部门和民族意识觉醒的民族精英的共同操作下,不仅使各民族民间乐舞得以恢复一些形式和内容,部分地区的一些基层教会也从另一个角度改变其发展策略,开始挖掘和引导传统乐舞走向现代化的复兴之路,努力适应来自社会、文化领域的变动,以确保自身的发展。
随着民间乐舞的民间信仰精神内核的弱化和消失,其内容、形式和性质均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传统宗教的功能被摒弃或消失,本应发挥的文化传承功能早已不存,甚至其代表的文化发展方向也发生了改变。中缅边境基督教文化区出现的各种乐舞在内容和形式上出现了以基督教为核心、各种因素并存的混融状态。不同民族中传统文化、基督教和现代性等各种因素所占的比重有明显的差异,比如傈僳族、景颇族信教群体中传统乐舞的内容就有一定差别。怒江地区的傈僳族对传统乐舞仍有一定的禁忌,景颇族则将传统乐舞纯粹以民族艺术的形式与基督教信仰融合在一起,表现出较为灵活的策略和态度,而佤族和拉祜族社会中则出现多种情况并存的复杂局面。各民族信教群体中乐舞艺术的变迁轨迹,基本上是与其文化体系其他要素的发展状况相对应的。此外,从基督教的赞美诗、赞美舞吸收现代元素的形式改变,到对传统民间乐舞的态度和行动,缅甸北部地区教会的努力表现出更大的现代适应性。缅北教会制作的各种教会音乐、民族音乐、MV到处流传,对我国境内各族乐舞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注释:
[1] 刘锡诚:《对几个“非遗”理论问题的思考》,《凯里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 杨志明:《论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化》,《思想战线》1999年第3期。
[3] 访谈对象:HGZ,男,66岁,傈僳族,泸水县上江镇新建村村民,非基督教徒,“茂源民族民间艺术团”团长。访谈时间:2015年1月19日。访谈地点:新建村茂源民族民间艺术团办公室。
[4][5]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6] 杨怀周:《基督教音乐》,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7] 陈小鲁:《基督宗教音乐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3页。
[8] 访谈对象:MRM,景颇族,盈江县太平镇龙盆基督教堂长老。访谈时间:2015年1月24日。
[9] 访谈对象:ZZB,景颇族,陇川县景颇族发展进步研究协会前常务副会长,非基督教徒。访谈时间:2014年11月4日。访谈地点:被访者家中。
[10] “能尚”,景颇族传统社会中建于村寨旁用于祭祀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各种鬼神的场所。
2017-06-03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中缅跨境民族文化与基督教关系研究”(14BZJ044)
徐祖祥, 男, 四川泸州人,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K892.24
A
1002-3321(2017)05-0005-08
[责任编辑:石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