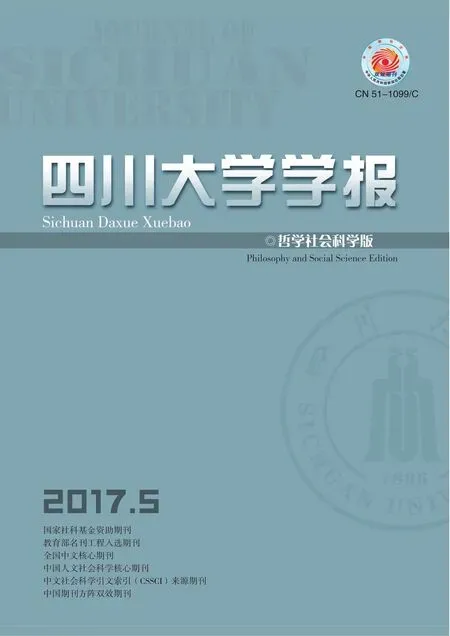如何正确看待儒学的现代价值
——与邓曦泽商榷
§儒学争鸣§
如何正确看待儒学的现代价值
——与邓曦泽商榷
崔发展
针对儒学的现代价值问题,邓曦泽作了可称之为“竞争主义”的新批判。邓氏认为,这种批判的特色不在于具体结论,而在于其整个批判性论证所依赖的与众不同的方法论。但经过考察,可知邓氏所谓的方法论批判,恰恰迷失在方法论上,具体表现为他在立场与方法、好坏与进退、普适性与有效性、事实与逻辑、中西古今的对接等诸关系上的混淆。由此,其批判的合法性与结论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了。
儒学;现代价值;方法论;竞争主义
鸦战以降,儒学日衰。后经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儒学可谓花果飘零。至文革期间,儒学跌至谷底。上世纪80年代以来,儒学命运稍转,但反传统、反儒学的思潮却不绝如缕,且不断翻新,譬如邓晓芒的“新批判主义”、刘清平的“新谩骂主义”*刘清平曾在网上公开谩骂儒家圣贤,这种爆粗口的方式可调侃而名之曰“新谩骂主义”。等。
近日,儒学又面对一种由邓曦泽发起的“新”批判,或可概括为竞争主义、新功利主义或新效用主义,集中表现在其论文《儒学现代价值新反思——基于竞争与相对进步观念的研究》之中。邓氏的批判何以值得应对?主要因为:其一,邓氏所采用的批判方法颇为独特,且从其整个论证来看,也容易给人造成这种强烈印象。因而,如何辨识其似是而非尤为必要。其二,邓氏从早先大力支持儒学转向大肆反对儒学,走向彻底的自我否定,个中缘由值得深究。邓氏本来是拥护传统的,曾深入论证儒学的价值,不但发表不少论文,更有已产生一定影响的大著《文化复兴论》。*邓曦泽:《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而《儒学现代价值的新反思》却是对《文化复兴论》的彻底否定,何以至此呢?其三,近年来,儒学迎来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最佳境遇,由此,显然不能用机会主义来解读邓氏的自我否定,故需另探究竟。
儒学应当批判,也只有在批判中才能发展。但需注意:第一,诚如陈寅恪所说,评析古代思想首先应抱着“了解之同情”,*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0页。儒学作为古代中国的思想共源,颇具复杂性,尤其需要以了解之同情而去作同情之了解。第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在运用某种方法论批判儒学之前,首先就要认真考察这一“武器”本身是否适用。既然邓氏明确说“本文认为论证高于一切,是严格的论证得出特定的可靠的结论,而不是先设定结论或立场”,*邓曦泽:《儒学现代价值新反思——基于竞争与相对进步观念的研究》,见《四川大学学报》本期。以下凡引此文,不另加注。那么,我们将集中对邓氏所依赖的方法论武器做一批判性考察。如果邓氏的论证本身就有问题,那么,其具体结论就更值得商榷了。
一、立场与方法之间的纠缠
近代以来,批儒者所使用的“武器”大致分为两类:有侧重于事实铺陈者(如鲁迅、柏杨),有侧重于学理分析者(如邓晓芒、邓曦泽)。仅就邓文的结论来讲,似乎不过是重弹胡适当年“百事不如人”的老调。但邓氏认为,研究方法的新颖是其文最重要的创新,并自认其批判与胡适等大为不同。一般来讲,在现代学术研究中,论证方法或许比结论更为重要,因为整个研究的严格性、可靠性及意义都会由此而有较大不同。为此,就需审视邓氏的方法论是否的确如其所说的那样可靠。
为表明其论证的严格性,邓氏一再声称其研究并未预设立场,而是“理智优先,遵循学术和真理本身的逻辑”。然而,读罢邓文,却得到了相反印象。
从具体行文看,邓氏的这种信心显然源于他选择了“普适”的竞争视角及效用最大化原则,此即他所说的竞争是常态、“效用最大化是普适原则”。但问题是,这种“选择”又由何而来呢?
这首先就要回溯邓氏最初的问题意识缘何而生,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问题才促使邓氏来重审儒学的现代命运?伽达默尔认为,新问题使“历史任务的真正实现仍总是重新规定被研究东西的意义。”*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Ⅰ),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84页。据此,邓氏的问题意识、研究兴趣,应该也是他有意识选择的结果,旨在重新审定儒学的现代价值。换句话说,邓氏之论必然是观念先行的,亦即是本着某种立场而言的,这是人的历史性、有限性的必然体现。而这种先行的问题视域,必然会规定或限定整个研究的方向及其意义。
为了追求论证的严格性、有效性,邓氏认为必然不能划定论域或选择立场,并寄希望于通过诉诸某种所谓的“普适”视角或论证方法来表明这一点,但结果却只能是“作雾自迷”(熊十力语)。无论如何,在被通篇的竞争意识、效用观念所笼罩的逻辑论证中,读者们或许更能体会到邓文中那份浓浓的立场或价值取向吧。其实,“无立场”作为“价值中立”的另一种表达,作为一种韦伯意义下的“理想型”标准,在人文科学研究中自有其重要意义。但是,迄今科学的发展早已证实了价值中立本身的有限性,如汉森就曾批评逻辑实证主义的中性观察,并提出了“观察渗透理论”的著名命题。此外,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更是从本体论层面明确地为“前见”恢复了名誉。*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76页;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Ⅰ),第377页。可见,“前见”作为理解的先行条件,本就有其不可否认的合法性。或可说,立场与方法或论证非但不矛盾,且恰恰相反,在选择立场与划定论域之间虽然不能简单划等号,但预设或选择某种立场,常常也能标明对某种论域的划定,而这也正是合法性论证的必要前提。只是在预设或选择时,必须谨慎甄别。
二、好坏与进退之间的两可
可叹的是,邓氏恰恰是在“选择立场”(虽然他不愿承认其先行立场)时,因缺乏审慎和明确的意识而显得过于乐观了。邓氏明确指出,他对儒学现代价值的反思乃是“基于竞争与相对进步观念”(如其篇名的副标题所示)。他认为,从竞争的角度看问题,当然要考虑效用最大化,并进而衍生出程度区分法和相对价值法。而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新方法不断产生,由此,邓氏明确提到“一种方法的优劣总是相对的”。这个方法论来自邓氏对常见的竞争的分析和提炼。*邓曦泽:《劣向选择成本——论竞争原理及其解释力》,《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可以说,没有这个方法,就没有邓氏对儒学的批判。但是,依此审视邓氏的方法,就要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不同文化之比较,竞争视角或进步观念是否是最适宜的切入点?比如,对于权衡儒学的现代价值而言,竞争视角或进步观念能否实现“效用最大化”(即发掘儒学的最大效用)?邓氏是以西式的“科学+法治+民主”来权衡儒学。且不说以这种标杆来衡量儒学是否适宜,单就在中西学人对西方现代性已有普遍反思的今天,这种标杆是否仍有其权威性,首先就要认真考量一番。
在尼采看来,西方现代性实则源发于“低贱”反对“高贵”、“奴隶”反对“主人”的运动,具体就是要取消“高贵”与“低贱”之间的区别,将是否取得进步视为评价某一事物之好坏的标准,所谓“科学是奴隶道德的禁欲观所假定的最终形式。科学为了真理转而敌视生活”。*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下),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64页。施特劳斯特别赞同尼采的这一观点,他认为西方现代性带来了“历史观念”,促使人们用“进步还是倒退”的区别取代了“好与坏”的区别,却忘记了后者本应逻辑地先于前者,以致于现代性的逻辑就是:新的就是好的,最新的就是最好的。*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导言”(甘阳),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9-10页。
由此,若是以进退的标准来替代好坏的标准,就会陷入进化论或功利主义的历史观念之中,从而也才会有邓氏从竞争与进步观念上妄议儒学,才会促成“对竞争力影响的大小,是判断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及是否应该维护它的重要标准”的认知,进而得出儒学整体落后的结论。严复当年曾将进化论简化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不想今日却又在邓氏这里重演。在邓氏看来,在现代条件下,知识生产方式乃是影响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而中西方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知识生产方式不同。但是,在竞争与进步观念的框框里,邓氏所认可的“知识”主要是“现代科学知识”,儒学在这种知识上的生产能力的确落后。然而,对于这种知识之外的其他知识类型(如道德知识),邓氏却并不太在意,尤其是,由于执着于尊西趋新的认知立场和价值取向,邓氏并不能正视其中的抵牾之处,而这恰恰表明:对于发掘儒学的“效用最大化”而言,竞争与进步观念的标准并不适宜。
三、普适性与有效性之间的误判
邓文一再表明是基于严格的逻辑论证,其结论必然有效。但这种严格、有效的解释或论证,却主要依赖于邓氏对竞争是常态、效用最大化是普适的判定。然而,这种逻辑推导中的破绽却需反思。
首先,一个常态的现象或普适的观念,并不足以保证论证的合法性或有效性。若此,当邓氏选取“竞争”作为“本文的基本视角”时,既应保持谦逊,因为还有其他视角可供选取,亦应保持警惕,因为有可能自己选取的视角并不是最适用的。然而,在邓文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同情了解”的表现,而处处凸显出强人就我的话语霸权。
其次,如果非要从逻辑角度来考量(在事实上考量又另当别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或一种看似“普适”的原则,未必就一定是有效的判别标准。套用邓氏“在语义上,‘重要’不等于‘好’”的话,即便竞争、效用最大化很重要、普适,也得不出它们在某一论域的使用就一定是好的。比如,生物进化是普遍现象,并不等于用进化论来评析社会发展就是适宜的。由此,邓氏自认的所谓“遵循学术和真理本身的逻辑”,实在是有点想当然了。
再次,当邓氏说效用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时,有可能因仅仅考虑这一命题之外延的普适性而忽略限定其内涵的重要性。比如可以问,这里的“效用”是何种意义上的“效用”?效用有很多层面,若从功利角度考虑,儒学固然没有优势,但从道德价值层面,儒学就更有效用。同样,邓氏强调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认为鸦战以来,中华文明遭遇的挑战,本质上是西方先进知识生产方式对中华文明落后知识生产方式的挑战。然而,邓氏所谓的“知识生产”,又是何种“知识”的生产?如果是他所拥护的以现代科学为代表的西方“先进”知识,儒学当然是较短板的;但若指道德层面的知识,那么,他所说的“儒家在知识生产上的问题不是它没有和不能生产许多具体知识,而是它对知识的态度即价值导向不当”,就是前半句所言甚是,后半句则大谬不然了。
可见,邓氏所依赖的“普适”观念,并不足以保证解释的合法性或有效性,不惟如此,由于论域的宽泛,反而容易造成诸多逻辑问题,最终造成解释力的下降。这也从另一层面表明,在讨论问题时,有意识地限定论域或选取立场是多么必要了。
四、事实与逻辑之间的淆乱
在其早先的大著《文化复兴论》中,邓氏曾基于历史文化是重要的交往平台的论证,而对复兴儒学持有相当乐观的态度。然而,时过境迁,邓氏意识到其中的逻辑难以自洽,这是因为,即便他成功地证明了儒学的重要性,在逻辑上也推导不出儒学一定还有价值的结论来,因为“在语义上,‘重要’不等于‘好’。”由此,邓氏进一步指出:“虽然《文化复兴论》下篇论证了:在历史上,儒家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共源和公共交往平台,但由此命题推不出儒学必然是或永远是。”
由此,邓氏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觉今是而昨非”的自省能力,而这种自省仍完全依赖于他对其中逻辑推导是否自洽的认知。然而,如前所述,邓氏所自认的“今是”在逻辑上颇有问题,而其所谓“昨非”,实则也有强求逻辑与事实相统一的形而上学倾向,而科学的发展也已表明事实与逻辑并不一定统一。邓氏的推导在逻辑上是成立的,“重要”当然不等于“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确也不等于今天仍有此效。然而,若仅考虑逻辑而罔顾具体情境,就容易把复杂的现实问题转化为单纯的观念问题,从而沦为观念上的逻辑游戏。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为了强调其论证的普适性,邓氏喜欢宏大叙事,多用“人类”“一切”“一个事物”“行为者”等宏大字眼,习惯于抽象讨论效用或价值。然而,对于某一具体文化来说,其主体却都是具体的、现实的,并浸润着这种文化的具体内涵,由此,并不能完全站在抽象的角度来判断其好坏优劣。
比如,邓氏认为“效用最大化是普适原则,也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甚至是动物行为的基本原则”,如此一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何在?人的尊严何在?马克思曾批判费尔巴哈“类本质”的观念,指责其抽象性,不知邓氏对此作何感想?再如,当分析其“相对价值法”时,邓氏指出,如果行为者本来可以在A与B之间自由选择,但他选择了A而放弃B,则他不是获得了A,而是损失了P(P为A与B之间的价值差)。这种逻辑分析看似冷静、有力,然而在生活中,做出某一选择往往要受制于很多现实条件,因而“自由选择”本身如何可能,仍需考量。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不需要考量逻辑与事实的统一。关键在于,当选用逻辑分析这一工具时,一定要审慎地考察它与所分析对象的契合度。比如,对于儒学的逻辑分析,就一定要小心。王国维、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老一辈,都认识到西方的长处在于证明方法,中国需要补上“形式系统”(冯友兰语)这一环。但在补这一环时,冯友兰也明确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学的优长就在于“负的方法”,亦即“非逻辑”(而不是反逻辑)的方法。可见,对于儒学,逻辑上的静态分析虽有必要,但并不是最适宜的判别标准。邓氏之所以自认其方法独特、论证强于前人,也主要是基于他认为自己逻辑地补上了这一形式系统,但“过犹不及”的后果(泛逻辑化的强势论证),他却不愿正视。
尤其是,当冷冰冰的逻辑遭遇活生生的事实,就容易造成逻辑对事实的戕害。比如,从语义上,“重要”固然不等于“好”,但在现实上,它们有时也能相互置换而大意不违,这要看究竟是在哪种论域中,如“这个对手很重要”,也可意味着“这个对手很好”,一个好的对手对提升自己当然是重要的。而若仅从逻辑上考量,这种事实并不容易解释。
其实,邓氏所推崇的“逻辑”,不过是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或实证主义者的逻辑,从中影射出他对西方科学所持有的单向度的狭隘认知。比如,哲学解释学的“问答逻辑”(问答辩证法或对话辩证法),就已给出了“理解”作为生活事件或事实本身的真理。伽达默尔有言:“如果人们把诠释文本的任务置于现代科学理论的偏见、依据科学性的标准之下,真正是目光短浅的。诠释者的任务,事实上从来都不仅仅是从逻辑-技术上查清任何一种言谈的意义,这样做就会完全忽略所说的话语的真理问题。”*Gadamer,Rhetorik und Hermeneutik,in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 Bd.2, S.285.试看近代以来复兴传统的诸多努力,*详见郭齐勇主编:《当代中国哲学研究(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郭齐勇:《近年来中国大陆儒学的新进展》,《广西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就显然超出了逻辑的控制。罔顾活生生的现实,就无法解释现实。套用马克思的话,就目前而言,或可说儒学复兴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更多的还是个实践问题。早先在自己拥护传统而强烈批判“以西释中”的做法时,邓氏就已明确地意识到“为什么要以西为法?这本身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近代中国的命运问题”。*邓曦泽:《现代古典学批判——以“中国哲学”为中心》,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8页。诚哉斯言!不想今日,邓氏却在“逻辑”力量的推动下转身去拥抱“西法”,而其后的国家命运这类巨大的现实问题,却被无情地消解在了暴力逻辑之下。究其原因,“原来他仍旧不曾跳出赛先生和罗辑(按:逻辑)先生的手心”。*胡适:《孙行者与张君劢》,载《科学与人生观》,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86页。由此可见,若一味迷信逻辑的力量、陷入方法论陷阱,于己、于学乃至于国家命运,都是极其危险的。可不慎欤?
五、中西古今的时空错位
邓氏力图表明“儒家的五大缺陷”,其论点大致可归结如下:在知识生产上,儒家不追求知识和真理;在社会治理上,儒家崇尚人治,反对法治;在礼仪方面,儒家主张繁文缛节;在社会等级方面,儒家主张等级区分;在教育与人格塑造方面,儒家强调服从与因循,鼓励奴性。很明显,邓氏批判的主要是传统儒学,所高扬的“法治”“民主”“自由”“创新”等则明显是西方的现代价值观。若在中西古今之间进行不对称比较,很容易得到这类结论,学界对此早有相关论述。*对这一话题的最近分析,详见原祖杰:《东方与西方,还是传统与现代?——论“东西方”两分法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误区》,《文史哲》2015年第6期。但是,邓氏也明确提到,他并不担心这种不对称比较的合理性,因为“这种比较无所谓时间对称,因为两种文化进行比较/竞争,是拿各自最优秀的文化相比较,而不是一定要拿同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相比较”。
问题是,且不说儒学是否真的如邓文所说的愚民、鼓励奴性、主张等级、反对法治等,至少必须反省的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究竟是何所指?带着西方价值观的有色眼镜来看问题,儒学必然不得好。而西方现代性所遭遇的种种不堪,以及儒学在其间可能发挥的优长,邓氏却完全无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选择性的失盲,其结论自然是重提西化论者的那种论调:抛弃传统,热情地拥抱西方吧。邓氏早先曾强烈批判西化论者,并断言“我绝不相信以西解中是我们的宿命”,*邓曦泽:《现代古典学批判》,第327页。然而,赤裸裸的事实却是他不仅未能逃脱这一宿命,而且干脆返身去热情地拥抱这种宿命了。
比如,邓文在批判儒家鼓励因循守旧时,给出的理由是“儒学的圣人观念与经典观念,是知识进步的巨大障碍”,并说“凡是认为某种具体思想、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的观念,都是反科学、反知识进步和反知识创新的”。古代儒学的圣人或经典观念,即便有保守的一面,但在今天是否仍必然会带来这种问题,就需要重新考虑。
今人言下的孔子、孔圣人以及儒学的一些核心观念,多已超出古代语境,而给予了现代性转换。近代以来,中外皆有学人致力于这类转换,早如梁启超在为谭嗣同的《仁学》作序时,就曾对“仁”作了重新释读,“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无拣择法也,故无大小之可言也”;*梁启超:《〈仁学〉序》,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3页。近如美国学者突维斯亦撰有专文《儒学与人权:一个建设性的架构》,指出“儒家传统中那些已经对人权观念产生影响,并且具有蓬勃潜力的思想资源,都应该被着重凸显并带入到充满前景的跨文化对话中来”。*萨姆纳·突维斯:《儒学与人权:一个建设性的架构》,顾家宁、梁涛译,《江汉论坛》2014年第12期。
然而,邓氏固守于古代儒学的等级观念,并不能正视近代以来儒学的现实转化。不能从历史的流动中看到变化之机,这乃是邓文的一大软肋。尤其是,从邓氏对“经典”本身的理解来看,因着意迷恋逻辑上的静态分析,却处处流露出历史感的极度缺乏。如邓氏说:“圣人和经典代表着不可超越、永恒不变的真理(绝对真理)。”很显然,这不过是一种陈旧的经典观、真理观。
其实,经典之为经典,并不在于它超脱时间的永恒性、形而上学性,而恰恰在于它必须在时间中以不同的具体表现来展示自身并借以回归自身。不应期望经典对每个人讲的是同样的话,经典也绝不会以陈词滥调来感动一代代人,而是始终敞开自身。埃布林曾指出:“实际上,同一性和可变性这两个因素不可分割地相互依赖并共存于解释的过程之中,解释的本性就是用不同的方式说出相同的东西,而且,正由于是用不同方式说,它们才说出了相同的东西。”*转引自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编者导言”(戴维·E·林格),第18页。比如一首经典曲子,只有在不同的演奏中才能展示自身、实现自身,诚如所谓“月映万川”。从一般或古典科学的标准来看,这种新的经典观念或许是“反科学”的,但却恰恰揭示出了创新意识的真正源头,它要求每个时代、每一面对经典者,都必须在现实流变中重新开启与经典对话的场域,而不是将经典对象化为列文森所说的“博物馆之物”、僵化之物,并借以放弃自己本应承担之责,更不能把历史玩偶化,随意给历史贴标签。根本上讲,邓氏所谓的经典观、真理观,乃是其陈旧的历史观的必然表现。
邓氏曾说:“西化派与本位派这两种可谓针锋相对的立场背后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即认为历史应该对现实负责”,“甲午之后历史解释的离谱之处在于:按照现实目标回溯历史,要历史为现实负责”。*邓曦泽:《现代古典学批判》,第221-222页。然而,从邓氏对所谓的儒学“五大缺陷”的研判中,却处处透露出这种将历史玩偶化的倾向及其陈旧的历史观。以儒学与政治的现代性关联为例:在现代背景下,现代政治哲学所应设计的路线,到底是使“政治从属于道德,更重要的是,从属于理性美德”,还是“使美德从属于政治”?*施特劳斯、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下),第1053页。这依旧是个重要问题。邓氏认为是后者,并断言“儒家必须完全退出政治领域,并且大幅退出社会领域”;而前者恰恰是施特劳斯在对现代性做出充分反思的基础上所开出的路子,若试着遵循这一路子(不惟此途),我们或许更能看到儒学与政治联姻的优长所在。可见,对于某一问题的解答,关键还在于选取的视角或立场是怎样的。
当然,邓氏也意识到儒学有一定的现代转换,只是他担心“任何理论都有一些核心内容区别于其他理论,如果去掉这些内容,该理论就丧失独立性而不再是它自身。”在他看来,礼仪、圣人观念、等级观念等,就是儒家的核心内容,而且不幸的是,这些核心内容恰恰与现代社会难以兼容。如此一来,邓氏认为,要么儒学摈弃与现代社会不兼容的核心内容,若此,儒学将不再是儒学;要么儒学竭力维护其核心内容,若此,儒学仍是儒学,但势必阻碍社会发展。问题是:第一,礼仪、圣人观念、等级观念之类,只是古代儒家的制度设计或观念设计,而非其精神主旨,邓氏于此明显有误解;第二,邓氏无意中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儒家必然是“以自我否定精神推动社会发展”。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自否定”的过程。*邓晓芒对“自否定”有明确论述,参见氏著:《我与儒家》,《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对此,前有黑格尔辩证法的佐证,后则有熊十力、成中英等的论证。如成中英就认为,与西方的静态本体论不同,中国本体的一大特质就是其本身就是变易不居的。*成中英、杨庆中:《从中西会通到本体诠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6页。第三,即便就儒学的精神主旨来讲,其本身也在变动不居,而不是铁板一块的僵化之物。
邓氏钟情于历史主义似的静态分析,实则渊源有自。邓氏曾言:“在比较中,比较者必须把对象看成静态的而非动态的、确定的而非模糊的、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即使比较者考察对象的运动,也必须把运动纳入静态的结构中进行考察,否则,对运动的比较就是不可能的。”*邓曦泽:《现代古典学批判》,第111页。不过,这种认识仍有问题。将研究对象专题化、命题化,虽是一个方便法门,但“语言本质地具有的无数未说出的东西不能被简化成命题,亦即简化成仅仅现成的东西,因为每一种新的解释都带来了一种新的‘未被表达的圆圈’”。*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编者导言”,第25页。不了解这种辩证法而偏执于静态逻辑分析,就容易割裂片段与整体、间断与连续、静态与动态之间的辩证关联,抹杀对象的丰富性、生动性而造成认识上的僵化、呆板与干瘪。
亚里士多德提出“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没有整体,我们就不能理解部分”,贝塔朗菲将亚氏的这一思想归结为“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之和”,并认为全部系统论就是要有效地解释该命题,且该命题早已成为现代系统科学的一个经典命题。*参见邬焜:《“整体大于部分之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哲学动态》1992年第6期。可见,对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因而只有在动态分析中,才能看清对象的系统性、完整性,并明确人类认知的有限性。由此,有必要铭记黑格尔关于界限辩证法的论证,认识到系统(总有其边界)本身也在不断自我调整,而不能执着于静态分析。
结 语
对自己提出的程度区分法、相对价值法,邓氏断言“基于这两个方法,才能且就能更客观、科学地理解和评价儒家”。然而,读罢此文却恰如邓氏所言:“如果方法错了,理解和评价就一定不客观和科学”。因为,在西方价值观主导下,在选择性失盲的无意识或潜意识中,邓氏所倚重的竞争观念、进步观念,最终成了为西学张目的手段,给人一种“名为争是非,实则争门户”的观感。罗志田说:“文化体系不同,随意用西方哲学概念或名词套中国思想恐怕多易造成‘始乱终弃’的结局。”*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9页。始则乱之、终则弃之,就邓氏思想的前后变化、邓氏写作此文的前因后果来看,可谓一语道破。
邓氏此文实则映射出新旧经典观、新旧真理观与新旧历史观之间的激烈冲突,由此,邓文虽名之曰“新反思”,而根子上却是乏“新”可陈。邓氏坚信自己走的是“科学”“逻辑”的道路,但他对这些观念的理解却相当狭隘,过度偏重于形式逻辑、因果推导,不惟如此,他又把这种被狭隘性的理解无限放大,而不能有意识地限定论域,致使其文通篇弥漫着泛科学化或泛逻辑化的倾向,整个论证亦由此而显得进退失据。
早在科玄论战期间,林宰平就曾告诫说:“科学一语,恐怕不久也要变成滥套了。这是糟蹋科学,不是提倡科学!”至今日,时人对科学已有足够反思,不想邓氏对此却置若罔闻,仍执于科学之一偏,实则无益于科学的良性发展,因为“把科学极力的普遍化,烧酒对水卖,分量越多,价值越少了”、“现在提倡科学,正要为他显出真正的价值……别像吹胰子泡似的,吹的太大,反而吹破了”。*林宰平:《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122、140页。邓氏满口都是科学如何、逻辑如何,试问:何谓逻辑?何谓科学?如果此类基本概念或观念尚未理清,那么,名既不正,言岂能顺?
邓氏说:“人类的最高目标是幸福,而一切具体的文化形式,都是增进幸福的手段。如果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能增进幸福,那么,用前者替代后者,就是正常的和应该的。”自西方现代性输入以来,我们的幸福感无疑增加了,但其中暴露出的问题也值得警醒。在亟需对现代性加以反思的今天,我们还是要仔细掂量,何为真正的“幸福”:是处在丛林法则中那些惶惶的竞争者们呢?还是诸如儒学所能涵养出的从容的生活样态呢?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坚信:不同的文化对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千万不能扣上一顶文化相对主义的帽子就以为解决了问题。偏执于静态分析、抽象论证,只能得出虚妄不实的结论,自迷而误人。此外,即便在不同文化之间有了比较或竞争,也并不一定要分出个高低上下、你死我活,因为这些比较或竞争,有可能凸显出不同文化之间取长补短、各取所需的共生关系。在面临许多全球性问题的今天,这一点尤需注意。
时值今日,我们仍需反思当年从东西文化论战延续至科玄论战的历史进程,借以清醒地意识到当下的责任所在,比如,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入江昭认为“全球一体化”应是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主义”和“大同思想”恰恰可以成为中国推动“全球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参见原祖杰:《东方与西方,还是传统与现代?——论“东西方”两分法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误区》,《文史哲》2015年第6期。由此,“不妨学学近代中国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先放弃中西新旧甚至所谓‘普世’等分类前提,直观各文化中可以帮助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基本关系的思想资源,或真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罗志田:《道出于二·自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页。如此,或许才能理解当今儒学仍有存在之可能性、必要性及其现实性究竟何在。
RedefiningtheModernValueofConfucianism—ADiscussionwithDengXize
Cui Fazhan
In redefining the modern value of Confucianism, Deng Xize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of what can be called Competition Doctrine. A unique feature of this criticism, in his view, is the different methodology on which his whole argument is depended. But by analyzing his argument, we see that he has lost himself in the methodology, confusing the following relations of position and method, universality and effectiveness, logic and fact,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and what is Chinese and what is Western, etc.. From this we know his whole criticism is doubtful.
Confucianism, modern value, methodology, competition doctrine
B222
:A
:1006-0766(2017)05-0071-07
(责任编辑:曹玉华)
崔发展,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成都610500)
中国博士后第56批面上项目资助“清代汉宋关系的解释学研究”(2014M56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