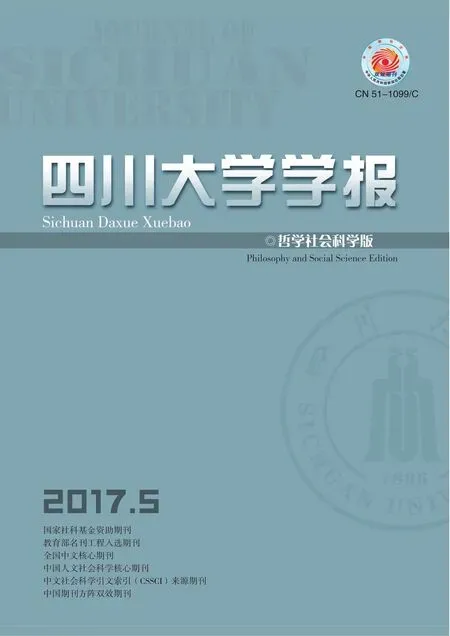西方“中华帝国”概念的起源(1516—1688)
§中国史研究§
西方“中华帝国”概念的起源(1516—1688)
陈波
欧洲建构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话语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元朝以后,因海员在16世纪初的航海活动中接触到China,欧洲知识界对中国政体的概念始有更新;巴博萨和传西栾那因触及的维度不同,先后以“王国”和“帝国”概念来理解明朝。1585年门多萨基于朝贡制度的多级体系,指出China属帝国级别;此后经利玛窦、曾德昭、卫匡国而至柏应理,以帝国-王国等级比对、欧中概念对译和谱系建构等方法渐次建构出“中华帝国”,并以清朝接续之。但欧洲的帝国观基于军事暴力,政体等级亦限于两级,与中国的政治经验相左,故无法解释中华体系;相反,中国政体模式则包容之。
中华帝国;王国;欧洲;中国体系;China
“中华帝国”话语对孟德斯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有深刻的影响,*本文是对欧洲-西方人类学王权理论和帝国概念的反思;从开题、资料收集和撰写,历时三年有余。其间得到韩笑、谭杰、怡宝、Jose Luis Flores、张颖、庄舒婷、冯佳等友人在资料搜集和材料解读方面的襄助,亦曾得到王晴佳、徐波、刘耀春、刘君、James Renton、Peter Burke、Alan Macfarlane等在欧洲史方面的指教;2013年秋季学期后,川大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们陪我一起读过相关的部分著作,感谢他们的参与。在漫长的投稿过程中,得到不少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对拙文最终成型至关重要,特致谢意;文中尚存的问题,责在笔者,惟望抛砖引玉,得到方家赐教。参见Baron de Montesquieu Charles de Secondat, De l'esprit des loix, Geneve: Barrillot & Fils, 1748, pp.160-163; 高哲等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362、365-367页;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p.4.至今仍然是西方汉学研究最重要、最根本的分析概念之一;如此重要的概念,学界却不清楚中华为何会是帝国,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甚至不加批判地袭用和发展它。*1980年代以后,中译者在翻译欧洲著作中的kingdom时普遍弃“王国”而采用“帝国”,更扩大帝国话语在华语圈的影响。如何高济和孙家堃所译的《中华大帝国史》。汪晖差不多是重新定义他在古文献中发现的“帝国”概念,并在主要是19世纪以后西方的帝国-国家二元论框架中叙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进程,没有顾及清代儒学界是否了解欧洲的帝国话语、是否以中国为帝国的议题,直接以中国即是帝国和当时思想界明确这一点为前提展开论述,尽管他承认二元论是西方建构现代合法性的手段,用于分析中国并不合适。*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理与物》,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3-46页。刘禾对东西帝国碰撞的话语政治研究,亦不加置疑地以中国即帝国作为前提。*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杨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类似取径不一而足。
在欧立德看来,19世纪初中文出现的“帝国”一词是对英文“英拜尔”(empire)的翻译;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始正式将清朝列为“大清帝国”,中国知识阶层通过媒体获知后得到普及;他批评说,民国以降,中国历史学家“以此‘帝国’的称号投射到无限历史长廊镜头中,直至远古”,把中国当作从始至终绵延从无间断的帝国,误导后人。然而中国学界不过是借用绝大多数早在17世纪的欧洲知识界就已经成型的观点而已。欧立德认为其时欧洲学者把清认定为帝国,是看到满洲的军事暴力和清廷作为“统治不同民族的政体”。他在解读欧洲文献时把这两点系统地嵌入其中。*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年第1期。为揭示欧立德以后世观点歪曲史料造成的史实错误,曹新宇和黄兴涛对欧洲史料进行细致梳理,认为当时的“帝国”概念比较宽泛,且早在1563年就有欧洲作者认定中华为帝国,并一直延续下来,其重点一直“在于中国是何种形态的‘帝国’,压根就不在于中国应不应该、或配不配被称为‘帝国’”。*曹新宇、黄兴涛:《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该文是目前国内学者所著唯一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文献,文中的细致分析值得参考,下文不一一列出。
欧立德旨在把当代帝国定义嵌入现代早期欧洲学者的著述中,“借”他们的文本来“证明”他的观点,即明朝作为China不是帝国,清朝才是帝国,所以清跟China不同;曹新宇和黄兴涛力证欧洲作者早已将明朝中国视作帝国并在进入清朝后延续,默认清朝即中国;尽管针锋相对,但他们共同的地方则是承认欧洲的帝国观当然可以用来套解中国事实。本文的议题恰好是将这一想当然的史学观念置于疑问之中,从欧洲学界把帝国话语逐渐加诸中国的漫长过程,来反思这一近五个世纪的加诸是否妥当。为此我们必须重建相关历史,找出欧洲作者塑造中华帝国话语的结构性真相,并加以解释。*Chen Bo, “Conceptions of ‘China’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48, No.4, 2015, pp.401-422.
欧洲在认知中国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马可·波罗行记时代。本文以此为起点,以“王国”(kingdom)概念之运用于理解中国作为参照,梳理欧洲学界建构“中华帝国”话语的早期过程,以期发现他们在认定中华帝国过程中所运用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否有内在的冲突,并在跨文明比较的视野中分析欧洲概念用于理解中国体系是否存在困难。
一、欧洲帝国观与元朝:选择性理解*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14.的原则
从区域性宰制上升为跨区域宰制,从宰制一王国到宰制若干王国,追求的是普世在上性。这一观念起源于古希腊斯多噶派。公元前5世纪的波希战争将古希腊引向追求普世超越性的进程;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并取得成功,使狭隘的城邦国家从此开始产生世界普世性观念(oikoumene);他们强调希腊文明是最好的人类文明,具有普世使命,对外围的蛮族统治区实施普世宰制。公元前2世纪后,希腊人把罗马帝国视为普世性存在,相信罗马的征服会走向所有文明民族的统一:帝国即全世界(Orbis Terrarum);*Lorenzo Valla, A Treatyse of the Donation, London, 1534, p.24.波利比奥斯甚至证明帝国是历史的目标;*Richard Koebner,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2.他们想象的普遍性世界随后也演绎为基督教世界(Orbis Christianus)、基督教帝国(Imperium Christianum)、罗马世界(Orbis Romanus)或不列颠世界(Orbis Britannicus)等。但帝国最初是指臣服于罗马人民后来才是臣服于帝王的“省”,且不允许政体有多样性,只在德意志诸部落侵入罗马帝国等因素的影响下才开始将省转变为政体,承认帝王的至上地位,从而生发出帝国高于王国的观念;最终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由东罗马帝国确立帝王即全世界的卓越者和诸王之王这一等级性观念。正是这一可与罗马帝国经验相分离的形式概念使得其他国王可以声称帝王,*Robert Folz, The Concept of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9, pp.4-7, 42.如英格兰在1588年击败海上霸主西班牙,国势蒸蒸日上,帝号之说复兴,才出现1611年司笔(John Speed)的《大不列颠帝国志》。*John Speed, The 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e, London, 1611.
如霍伟(Stephen Howe)所说,帝国的定义性特征是军事暴力;*Stephen Howe,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3.而当代史学家冒顿(James Muldoon)总结出欧洲历史上的八种帝国观,都视帝王为世俗有时甚至包括非世俗的最高权威:须统治王国或省才可以称为帝国。*James Muldoon, Empire and Order,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9, p.95.欧洲现代早期的文献主要用君主政体的帝国和王国形式来理解中国,*Muldoon, Empire and Order, p.125.其基础是由马可·波罗游记和曼德维尔游记奠定的。它们首先运用欧洲概念中帝国-王国二元等级的原则,如“契丹”帝国之下有“蛮子”王国,后者的国王臣服于前者的大汗即帝王(emperor);其次,混用省、王国和帝国概念,如称“契丹”帝国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王国;第三,强调军事暴力在建构帝国或王国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后,认为元朝有与欧洲相匹配的概念和事实,概念对译成为关键。*Marc Polo, Travels of Marco Polo, London: H. Bynneman, 1579, pp.11, 40-41, 47-48, 57, 74-75, 97, 143; John Mandeville, Itinerarium, Westmynster: Wynken de Worde, 1499, pp.lxviii, lxxvi- lxxviii, lxxx, lxxxiiii.但冒顿、傅兹(Robert Folz)和柯博纳(Richard Koebner)等人的帝国研究,都没涉及跨文化的概念比对是识别非西方帝国的关键这一议题。
后世欧洲学者一直沿袭等级和中欧概念比对原则,概念混用如影随形,但极大地忽视军事暴力原则。
二、大明作为China——帝国话语的出现:*Pietro Martire Anghiera, The History of Travayle in the West and East Indies, London: Richard Jugge, 1577, p.246.实际上,欧洲人一直没有“中国”观念,他们只知道China等,这基本上不涉及“中”,整个话语也不是从“中国”出发的,跟中文的“中国”及其内蕴的一整套宇宙观是两回事。张国刚、吴莉苇指出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基本立场其实从未脱离欧洲本位(《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22、426页)。1516—1577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契丹-蛮子”分类是蒙元大陆视角的产物,而“China”则是15世纪末欧洲诸邦开启的海外扩张的结果。葡萄牙文作者巴博萨(Duarte Barbosa,1480-1521)于1516年完成讲述其海旅经历的手稿,首次提到“中华王国”及其国王。*Duarte Barbosa, Livro em que dá relação de que viu e ouviu no Oriente, Lisboa: Divisão de Publicações e Bibliotec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46, p.217.他在参加麦哲伦的首次环球航行中曾与皮嘎菲特(Antoni Pigafetta)等同行近两年,或已将China的知识传给他们。
1536年皮嘎菲特著述问世,并没有以China为帝国;但同年传西栾那(Maximilianus Transiluanus)在《西班牙环球航行记》中说:中国的国王在其帝国(imperio)之下有70名国王臣服;其中缅(Moin)国王手下有22个王国。该书首次提出China为帝国之说。*Maximilianus Transiluanus, Il viaggio fatto da gli spagniuoli atorno al mondo, Roma, 1536, pp.105-106.但其主要内容与皮嘎菲特所著大同小异,尤其后者还谈到70个国王中每一个下面都有10-15个国王依附。*Anghiera, The History of Travayle in the West and East Indies, pp.445-446.这显然是朝贡体系的痕迹。卜正明(Timothy Brook)曾提出,以中国为帝国,起因于欧洲人觉得罗马帝国是唯一能与中国相若的历史单位。*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265.其时中国朝贡体系之庞大,古罗马帝国庶几近之,但并非同一。
但中国究竟适用哪个概念则是一个历史进程:直到利玛窦著作出版时(1615),都以“王国”概念占主导,“帝国”为辅。王国论者有巴雷托(Melchior N. Barreto,1558)、伯来拉(Galeotto Perera,1565)和克路士(Gaspar da Cruz,1569)。*Francisco Guerra, G. Gandolfi, J. C. Mac Coy, Michele Tramezzino, Nuoui auisi dell'Indie di Portogallo, riceuuti dalli reuerendi padri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Venetia: per Michele Tramezzino, 1559, pp.44-45; Anghiera, The History of Travayle in the West and East Indies, pp.237-238; Gaspar da Cruz, Tractado em que se contam muito por extenso as cousas da China, com suas particularidades, e assi do reyno de Ormuz, Euora: em casa de Andre de Burgos, 1569, Capitulo segundo.1563年薄如斯(João de Barros)把China与暹罗等并列为帝国,但却说其首脑是国王。*João de Barros, Terceira decada da Asia de Ioam de Barros, Lisboa, 1563, pp.36-37.
传西栾那等人是因庞大而多样、复层涵盖的朝贡体系而把China当作帝国,开启了一个缓慢而不可逆的、将其识别为帝国的漫长进程,也是欧洲学者逐渐全面比较中国和欧洲的过程。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看法,若契丹为帝国,一经拉达(Martin de Rada)在1575年提出契丹即为China并经利玛窦的考证,*张铠:《16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门多萨及其〈中华大帝国史〉》,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第1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China为帝国当属名正言顺。
三、门多萨、利玛窦和曾德昭建构中华帝国话语:1585—1642
最先奠定“中华帝国”话语学术理路的是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他首先尝试在“中华王国”的基础上确定“中华帝国”之初始;其次,在华语概念中寻找“中华王国”话语的依据;第三,建构国王谱系。
他在《中华大王国最著风物礼俗史记》中广泛使用“王国”来理解大明。他说中华王国有15个省,每个省都比全欧洲最大的国家要大,按照其幅员,确实可以叫做王国。他甚至说中国“堪与全世界已知的最佳和最大的国家相匹敌”。*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0、23-24页。言下之意,连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也跟中国不相上下。他发现交趾支那分成三个省,各有国王,前两个国王臣服于第三个国王,称他为帝王,但他却臣服于中国的国王,缴纳贡税(tribute)并派遣质子(párias)。在这多重关系顶层的中国,其政体到底该怎么定性?当谈到古代中国时,他在三个地方很明确地说第一个国王黄帝将中华王国造就为帝国。*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ie Kingdome of China, London: I. Wolfe, 1588, pp.10-11, 41, 50, 322, 345, 382, 480.既然第一个国王黄帝时中国已经是帝国,由此往下,历朝历代都应是帝国。他的困境在于:中国最早的王国时代,也是最早的帝国时代;就黄帝来说,可能他成了帝王,但仍然可以叫国王,跟欧洲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处境相似。此外,帝国是国王造就的,无需他人加冕,类似英格兰和西班牙国王之称帝号。*Folz, The Concept of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p.41, 55.

门多萨根据拉达1575年左右所写的材料,简要地叙述黄帝之后历朝的国王,直至鞑靼入主,九传其位,为大明的创始者所驱逐,复经十二王而至门多萨时代。*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98-199页;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第71-74页。这个历代国王名单是对“中华王国”话语的建构,也是这一话语的最高峰。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将中国概念与欧洲概念对应,厘定概念的等级关系,更多地使用帝国话语,也使得概念混用的情形多起来。他把“中国”解释为“中间的王国”。他也承认15个省,每个都可以称为王国。*Matteo Ricci, Le lettere dalla Cina, 1580-1610, Macerata: F. Giorgetti, 1913, pp.38, 5.这再次引出对居于诸省之上的朝廷的定性。利玛窦在札记中有一个耀眼的贡献是把华文的“皇帝”跟意大利文的imperatore(帝王)等同起来;他还把中国称为帝国,并与欧洲的帝国比对。他说中国人称他们的王(Re)为天子,而日常生活中对天子的称呼是皇帝,差不多就是指imperatore和最高的君主。*Matteo Ricci, I commentari della Cina, Macerata: F. Giorgetti, 1911, pp.5, 33-34, 37.通过“天子”利玛窦把“皇帝”跟“国王”(Re)等同。
利玛窦将天子/皇帝称呼推到政体成立之初,*Ricci, I commentari della Cina, p.33; Matteo Ricci,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Lugdun: H. Cardon, 1616, p.43.明确中国的普世君主(signore universale)在公元前2636年就已存在。门多萨的数据是公元前2611年,*Ricci, I commentari della Cina, pp.32, 4; 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第70-71页。大致相同。但他们都把中国纳入到欧洲计时系统之中,而这造成重大的知识后果:在欧洲计时系统中,欧洲史相当清晰,但中国史则是需要填充的虚空。*D. E. Mungello,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 2013, pp.103-104.填补这虚空便成为塑造“帝国”话语的重任。
利玛窦更多地使用帝国概念理解中国。除他的意大利文札记外,在17世纪初由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译成拉丁文并润色出版的札记中,也非常多地使用了帝国话语。*比如拉丁文译本Ricci,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pp.6, 48, 685.法译本Matthieu Riccius, Nicolas Trigault, Histoire de l'expedition chrestienne au royaume de la Chine, Lyon: H. Cardon, 1616, pp.5, 160.但金译本中王国-帝国话语并立的情况增多。比如利玛窦意大利文本第二章标题是“中国的名字、幅员和位置”,开章第一句是“这个最远东王国以不同的名字为我们欧罗巴人所知”;而译本在标题中加入“王国”字样,开章则用“这个最远东帝国”。*Ricci, I commentari della Cina, p.3; Ricci,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pp.3-4.
门多萨和利玛窦都因中国居于诸王国之上,而认定其具有帝国属性,跟是不是统治多民族没有关系。但两人都立意将中国塑造为同质政体:有确定的边界;内部同质,只讲汉语;有相同的风俗、律法、政府;越来越不允许政体内部出现族性多元的情况,如果出现,就把他们跟Chinese划清界限。这就不难理解他们相对一致地忽视朝贡体系。
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写《中华帝国志》*有关该著的原文和译本情况,参见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76-82页。(1642)时大明尚存。他推进帝国话语的工作有两个方面:首先,书中广泛使用“帝国”一词,如“中华帝国”“在这个帝国里”“他的帝国”等,“帝国”出现34次之多,其中只有一次是用来指欧洲的帝国,这表明他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但他依旧把“王国”和“帝国”话语并列,如说阁老是“帝国内国王之下最大的官员”。该书第一章以“中华王国”为题,他说:“这个君主国分为十五个省,每个都是辽阔的王国,古老且有自己的国王。”正文中“王国”出现189次,其中有25次是用来指吐蕃、日本、鞑靼和朝鲜等。这种并列或混用现象随着使用“帝国”概念的次数增多而增多。如他在认定China的第一个帝王为尧帝时,说尧帝把“帝国”传给舜,舜传禹,禹的德行是在“王国”内治理水患。尽管第一帝的说法跟门多萨不同,但宗旨都是从历史的开端去确定政体的属性,而且假定一旦开端确定之后,后世便不会更改。其次,他与利玛窦一样,曾把华文的“皇帝”理解为欧洲意义上的帝王;不过他在翻译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时,把“帝”和“皇帝”几乎都译为Rey(国王),只有一次例外,跟“大帝”一样,译为Emperador。他又解释说:君(Kium)是指外国的国王;王(Vam)是指国王之子,而君王指国王,但主要的还是称皇帝,也就是Emperador(帝王);*以上参见Alvaro Semedo, Imperio de la China, Madrid, 1642, pp.14, 247, 16, 21-22, 99, 135, 146, 109, 69, 5, 27, 28, 121, 127, 130, 143, 148, 202, 204, 207, 248, 264, 332-333, 352, 354, 144, 205-213.他在解释等级概念,但概念等同关系却无时不在。通过君王这个中介,皇帝也等同于国王。可见曾德昭在套用欧洲政体概念时,不但解决不了混用的情况,反而以此改造华语概念体系。
四、清朝作为“中华帝国”之始:1654—1686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写《鞑靼战纪》时(1651)已是大清。该著已经把“帝国”比较彻底而广泛地用于理解中国,开篇即说鞑靼人四千年来都跟“中华帝国”为敌。*Martino Martini,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mstelodami, 1655, pp.19, 20, 51, 56, 61, 144, 36, 50, 51, 206, 23.1658年,卫氏出版《中国初期史记》,对建构“中华帝国”话语作出实质性的贡献。首先,卫匡国一开篇就将天子理解为帝王。他说从黄帝开始,中国诸代国王才开始通称“皇帝”,好比“我们从第一个恺撒开始(历代国王)才称恺撒”。*Martino Martini,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Monachii: Typis L. Strubii, impensis J. Wagneri, 1658, pp.11, 18.这就把中国和欧洲置于同一政体层面:中国恰好比欧洲的罗马帝国,恺撒即皇帝。这暗含着国王等同于皇帝、天子和恺撒,所以他又跟传西栾那之后以国王等同于皇帝的传统藕断丝连。
其次,卫氏将“王国”话语有机地纳入到帝王历史序列之中:在帝王治下有许多王国,以与欧洲的两级政体对应。如周帝王下面有楚、齐、鲁、秦诸王国等,*Martini,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pp.117, 126, 139, 147.其君主只能称国王。春秋战国时期的王国亦皆处于帝王之下。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继承这一思路,说晋帝国时期有齐、燕诸王国等。这一路径的困难在于一旦确定唯一的帝家正统后,其他并立的诸国诸朝都必须降格为王国,不服从帝国者即为叛乱者,如说东晋安帝时期(397-419)有七个叛乱的王国。*Philppi Couplet, 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Paris,1686, pp.44, 46.除了中国史学正统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概最像欧洲中世纪的帝国-王国格局,对他不无影响。
接着,卫氏把伏羲定为第一个帝王;其出生日即帝国诞生时,为公元前2952年。这个年代比此前任何一家的说法都大大提前。但其关键仍然是追溯到历史的开端,而中国依旧是从一开始就是帝国。这是传西栾那以来识别中国为帝国这一遗产的大跃进。伏羲在位115年后,神农继位,神农在位140年之后黄帝继位,时第一甲子第一年,即公元前2697年;黄帝在位100年后经少昊、颛顼、帝喾、尧和舜,在禹帝时进入夏家帝国,时公元前2107年;10年后其子启继任,以下直到第十七帝桀,时公元前1818年;第二帝朝为商家所有,从汤帝开始,历28帝至纣帝而终,时公元前1154年;第三帝家为周,从文帝开始历30帝,至考帝算一期,自公元前425年威烈帝时进入战国年代,复经7帝至姬延帝而终,时公元前254年。秦家(Familia Cina)帝国历三帝而终,时公元前206年;汉家帝国自高祖刘邦始,历12帝至哀帝,时第45甲子第58年,即公元元年。*Martini,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这个谱系首先是中国史学正统观的成果;卫匡国之理解它,则有欧洲历史上的“帝权转移”理论和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线性史观为基础;它使帝权在罗马帝国终结后可以转移到不同的君主那里而延续帝谱,也使后世兴盛起来的王国如英格兰和西班牙等可以自行声称帝国。*Muldoon, Empire and Order, pp.50-52, 72, 103, 105-106, 120, 123-124, 143.
这就是卫匡国对确立“中华帝国”话语的贡献:对历代诸帝王逐一加以介绍,以历史材料填充那些帝王前后相续的时间空点和断点,为欧洲知识人想象“中华帝国”夯实基础。传西栾那以来,“中华帝国”的历史链条从未清晰,而现在,帝王名单在时间上无缺环,逻辑连贯,完整而全面,填补了想象的空白。
后人的工作就是继续把帝王谱系表填下去。28年后,柏应理即撰成《中华君主年表》,从第一甲子元年即公元前2697年开始,下至康熙二十二年即第73甲子第60年,亦即公元1683年,时间跨度总计4380年。表格一开头就根据太史公《史记》质疑伏羲为中华帝国的创始人,而依从门多萨以黄帝为第一帝,此前的神农氏则置而不论。年表第一部分止于孝平帝末,即公元元年。第二部分续算,经孺子婴(王莽)、淮阳王而接光武帝,以下至献帝,为汉家帝朝;复经后汉帝朝昭烈王刘备、阿斗两帝44年,进入晋帝朝,以下历朝相沿直至清。*Couplet, 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pp.iij, 20, 37-43.
尽管卫匡国将《鞑靼战纪》看作是利玛窦札记的续篇,隐含着延续中华帝国之意,但直到柏应理这里,才真正将大清纳入到中华帝国的谱系之中:他在年表中收入“二十二帝家、皇帝数及延续年代表”,从夏帝家直至第二十二的清帝家,清帝家当时仅两帝,已历40年。*Couplet, 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p.36.张国刚评述中华帝国年表之意义,侧重点与本文不同(《明清传教士的当代中国史》,《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2期)。
卫、柏二氏为欧洲学界提供的年表是当时最为齐备的,有了它,欧洲读者对“中华帝国”的想象和建构就最终坚实起来,“中华王国”话语逐渐式微,但概念混用依旧。
在卫、柏二氏的学术传统来说,鞑靼建立的大清之成为帝国,是因为它承接中华帝王谱系。换言之,不是鞑靼使China成为帝国,而是他们把大清放在中华帝国的谱系上,使之接续中华帝朝史。牛合夫(Nieuhof)认为鞑靼君主的国王称号是大明封赐的,入关前他们只使用这一称号,入关以后才用帝号。*Johannes Nieuhof,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London: Johannes Nieuhof, 1673, pp.264, 269, 293, 324.这跟欧洲的某国王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有貌似之处。
关键是为何欧洲人把经过鞑靼入主这一革命*Jesuits, Relation des missions des pè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dans les Indes Orientales, Paris: Chez Iean Henavlt, etc., 1659, p.156;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London: W. Godbid, 1671, p.1.而后建立的国度依旧称为China。根本的理由可能在于大清在汉文和满文中自称“中国”。*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3页;Gabriel de Magalhães, A New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Thomas Newborough, 1688, p.4.1676年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1610-1689)根据利玛窦的“帝权转移”观,认为帝国的名字自伏羲以后即不变,但因统治家族不同而常有其他称呼,好比德意志帝国这个称呼永远不变,而奥地利家族统治时可以称奥地利帝国。*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Madrid: la Imprenta Real, 1676, pp.2-4.因此,China概念和帝国概念在短短的一百二十余年间已本质化、静止化并逐渐单一族化:这使得它在四千多年间都是帝国,都叫China,没有任何本质变动。
五、欧洲帝国观套解中国体系的内在困难与跨文明差异
欧洲知识界确定中国为帝国仅仅是其世界性帝国识别工程的一部分。16世纪欧洲作者们在世界其他地方认定的帝国大多同时也称王国或省,如埃塞俄比亚、日本、挪威;莫斯科既是帝国也是省;鞑靼是伟大的帝国,其君主称大汗,意即“国王”。*关于埃塞俄比亚,参见Michele Tramezzino, Nuovi avisi dell'Indie di Portogallo, Venice, 1562, Vol.3, pp.118-119, 33; Escalante, A Discourse of the Nauigation,London: Thomas Dawson, 1579, pp.7-8; André de Thevet, La Cosmographie Universelle, Paris: Chez P. L'Huilier, 1575, Vol.1, pp.57-58; John Eliot, Ortho-epia Gallica Eliots Fruits for the French, London: Iohn Wolfe, 1593, p.22. 关于日本、挪威、莫斯科公国、鞑靼等其他国度,见Anghiera, The History of Travayle in the West and East Indies, pp.255, 257, 284, 265, 274, 269, 288, 303, 289, 308.1708年的《四海征旅新集》和1721年的《征旅新集》分别称摩洛哥、波斯为王国和帝国。*John Stevens, A New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London: J. Knapton, etc., 1708, pp.813, 897, 902, 914; Anonym, A New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London: printed for J. Smith in Exeter Exchange in the Strand, 1721,Vol.2, pp.2, 8.这些混用说明世界各地的政体只能符合欧洲“王国”或“帝国”之一的特征,但是不能有自己的政体概念。
欧洲的海外殖民体系使其两级政体发生变动,出现三级体系:16世纪末,受到门多萨中国著述影响的雷利(Walter Raleigh)提到西班牙王国使南美洲的秘鲁帝国臣服。*Walter Raleigh, The Discouerie of the Large, Rich and Bevvtiful Empire of Guiana, London: Robert Robinson, 1596, pp.4, 109.17世纪时又有作者确定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印加为帝国,认定它们是以暴力统治其他民族;西班牙由此就可以正义地征服两个帝国以“保护”臣服于它们的民族。*Muldoon, Empire and Order, p.126.这便是三级政治体系的开端;这或许可以与交趾支那的帝王臣服于中国的国王这一三级政治体系相比对,但二者有本质的不同。殖民体系均依赖于帝国-王国等级框架,三级格局的出现并没有使之出现结构性变化,结果仍然是概念混用的,如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居于其在印度的代表之上,后者又居于印度各部地方首领之上,1876年女王升格为印度女皇。*霍布斯鲍姆等编:《传统的发明》,顾杭、杨冠群译,北京:译林出版社,第239-240、243-244页。
这让我们看到,以欧洲政体概念套解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内在困难,首先便是欧洲缺乏中国的政治经验,以有限的欧洲政治概念来理解内容比其丰富、庞大的中国政治体系时,削足适履、概念混用便不可避免。曾德昭以后如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说该著止于1651年,因为这一年他奉上司之命,“从中华王国前往欧罗巴”。这跟他的中华帝国话语相悖。他在书中更是频繁地把“中华王国”与鞑靼、奴儿干和吐蕃王国等*Martini, De bello tartaricohistoria, p.156; Martini, Bellum Tartaricum, London: John Crook,1655, pp.7, 10, 51, 30; 20, 28, 203.置于同一层级。其《中国初期史记》中,“王国”和“帝国”并立的趋势有增无减。*Martini,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pp.11, 13, 26, 32, 40.帕莱福(J. de P. y Mendoza, 1600-1659)、鲁日满(F.de Rougemont, 1624-1676)、闵明我、柏应理、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 1609-1677)等都不例外地、不同程度地混用两个话语。*Mendoza,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pp.37, 59; Rougemont, Historia Tartaro-Sinica nova, Lovanii, 1673, pp.135-136; Navarrete, 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pp.1-2; Couplet, 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pp.69, 72; Magalhães, A New History of China, pp.73, 181, 185;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
第二个困难是以追求超越性为目标的政体等级原则与军事暴力原则相冲突,而后者复与中国经验相左。军事暴力跟政体紧密相连,是欧洲政治学的核心。“帝国”的拉丁词根指“命令”;而“王国”的拉丁词根指统治、治理。它们都处在一个历史性等级结构的两端:一边是命令者、统治者,另一边是被命令者、被统治者。它们都意味着上级依赖暴力、权力和威势使下级在一定地理范围内服从和臣服。因此,二者没有根本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两个词的所指可以互换。*Thomas Elyot, The Dictionary of Syr Thomas Eliot Knyght, Londini: Thom Bertheleti, 1538, p.I ante M, R ante E; John Veron, A Dictionary in Latine and English, London: Henry Middelton, 1575, p.IM; Edward Phillips, The New World of Words, or, Universal 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J. Phillips, 1706, p.EM, KI.统治、宰制、权力、暴力是欧洲历史上想象世界的根本特征。其原生的所有权和领属关系宇宙观在基督教之后被依附上基督教徒-异教徒的二元因素。
古希腊帝王体制从一开始便跟军事暴力密不可分,军队拥立“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方赢得重要胜利的成功将军”为帝王,由此及于拥护帝国。*Folz, The Concept of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p.5-6; Muldoon, Empire and Order, p.18.帝王“这个词的意思不过是军队的将军,只对军队有着绝对的权威和统领;尽管此后它成为臣服于帝国的诸省及罗马之主权君主的称号”。*Anonym,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Empire from Charlemagne, London: Lawton Gilliver, 1731, Vol.1, p.4; Vol.2, p.147.中世纪时,欧洲王国的军事暴力成绩跟称帝直接相关,如公元653年,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奥斯瓦尔德(Oswald)带领诸国王取得战争胜利,就获得所有不列颠的帝王这一称号。*Muldoon, Empire and Order, p.14.西班牙的一部编年史对拉米罗三世(Ramiro III, 967-984)的称呼为“伟大的帝王”(magnusbasileus),让人想起最后的西哥特诸国王和拜占庭诸帝王。尽管这仅在内部使用,但其正义性在于西班牙的基督教国王对于伊斯兰的军事胜利。*Muldoon, Empire and Order, p.14; Folz, The Concept of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p.41, 48, 55.
因此,欧洲帝国宣称的普世性实际上是有限普世性。查理曼(742-814)以后,神圣罗马帝国帝王代出,然而其东边的拜占庭帝国不承认其帝号者所在多有;其西则有西班牙王国和英格兰王国,皆独树一帜,亦曾统帅多国,或为树立内部权威,或为抗拒神圣罗马帝国之号召,自予帝号。诸处帝王皆知他方帝王之存在,因帝号与军事征服内在关联,军事暴力不及之地,即为帝国的边疆。神圣罗马帝国跟欧洲的诸多王国都无关系,正说明帝国的普世治理就是有限普世性。从其起源开始,欧洲帝国就仅是比王国高一级的政体而已。
不能否定欧洲的帝国以“普遍性的‘文明’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和合法性”,而中国历代王朝也不缺乏武力征服的历史记录,*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帝国与国家》,第26页。但这两个事实都不否定“中国”的普世性不以军事暴力为定义性特征,而欧洲反是。历史上中国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以文化而非暴力、以王道而非霸道为主导。相对于西方帝国的暴力,叶法定(Vadime Elisseeff)一言道破中国普世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文”。*Vadime Elisseeff, “The Middle Empire, a Distant Empire, an Empire without Neighbors,” Diogenes, Vol.42, Summer, 1963, p.62.传西栾那以后欧洲学者渐次识别出中华帝国,却发现它跟欧洲帝国观愈发疏远。博特罗(Giovanni Botero)在1606年说,以战争获取版图,非中国法律所许;君主只能防御,故而永享太平。除了和平,还有什么值得期待或渴望的呢?*Giovanni Botero, A Treatise, London: T. P., 1606, p.78.利玛窦也发现尽管军队每天都在操演,但全国都在深享太平,民殷国富,知足而不对邻邦咄咄相向,“这显然跟我们民族非常不同”;在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中国征服邻国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Ricci, I commentari della Cina, p.44;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7、59-60页。博克舍甚至说中国人具有天生的和平性格,跟好战的日本人相对。*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50页。近来曼可(Mark Mancall)亦指出,东亚以朝贡为特征的国际体系中,皇帝即是政治力量的源泉,而这一点跟军事力量相对不重要有关。换句话说,“文”或王道更为重要,在历史上中国总体偏于尚文,尽管有少数时期尚武精神占据主导。*Mark 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4, pp.38, 191, 313-336.这是欧洲作者在识别中华帝国过程中忽视暴力原则的原因。
汪晖梳理出中国历史上的两种帝国观,其一是指以德治为特征的五帝之治。如隋代王通《中说·问易篇》载:
文中子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张沛:《中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46页。
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概念是以德为特征,区别于强国、霸国、王国、皇国及其价值取向的政治关系,是对推行武力的政治体的否定,明显区别于欧洲的帝国观念。*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帝国与国家》,第23-26页。按照中国标准,欧洲帝国不过是最低等级的强国而已,尽管它们有霸国和王国的可能,但绝非帝国和皇国。这一思路也可破除汪晖试图在欧洲-西方框架中找到中国的出路这一取径的困境。
第三,中国皇帝和欧洲帝王存在本质上的差异。1904年,严复译《社会通诠》时说:“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严复:《社会通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3-134页。欧洲体系内有天主教教皇,而君主没有君以外的职责,帝王也主要是带兵打仗的将军;将其等同于皇帝这一做法,若放在中国文明之中,即是将一个武将跟远在其上的皇帝比附。
基于这种差异,两种政治体系在运转方面有本质不同。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在需要经费支持时,只能跟帝国内的王公贵族们商量甚至讨价还价。比如1592年鲁多夫二世(Rudolf II, 1552-1612)因对土耳其帝国的战争等花费颇巨,在拉提司本(Ratisbon)召开会议,与选侯、王公和各国商量,要求他们的援助,各国答应给他一些补助,但对兵员补充、供给和进军等提出条件。*Anonym,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Empire from Charlemagne, Vol.1, p.384; Vol.2, pp.138-139, 148-149.中国体系内天子/皇帝即是一切,朝贡者之于天子/皇帝不可能如此;在极端的情况下如安史之乱中,朝廷才会跟受册封并助唐平叛的回鹘谈条件。因此,欧洲的帝国体系跟中国的天下体系在运作方面是相反的。
因上述差异,两造在继嗣原则和方法上便有不同。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是选举官从众多候选人中选举产生的。这个传统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就存在。自1356年起,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名选侯若意见不一,就会出现多个帝王并存的现象,如14世纪末15世纪初,一度出现三帝王共存的局面。帝王候选人不一定非得是德意志血统,如1519年获选的查尔斯五世。*Anonym,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Empire from Charlemagne, Vol.1, pp.4, 376; Vol.2, p.36. Comenius认为自他以后帝国君主名曰选举,实则世袭。参见Johann Amos Comenius, A General Table of Europe, London: Benjamin Billingsley, 1670, p.47.同期,中国历史上的皇帝继位采取父系继嗣而非选举,不会出现其他血统出生的人称皇的情况。皇帝的血统若更改,即意味着天翻地覆,改朝换代。
第四,两造对世界的想象差异悬殊。欧洲以帝国和王国想象世界,而中国则是以天下五服之制。秦以前,天下由朝廷直辖部分、各诸侯国及远人组成;秦以后,除分裂时期,朝廷直辖部分基本上为没有独立法律、司法和行政权的州或省构成,此外便是朝贡诸国和远人,无所不包。因此,帝国-王国/省二元等级无法理解包容性的朝贡体系。*这个体系当然不是静止的。相关的表述参见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杜尔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曾惊讶地意识到这种包容性。*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Paris: P. G. Lemercier, 1735, Vol.1, p.80.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则认识到“中国人把所有曾经派使节的国度都看做贡税国”,分为定期和不定期朝贡两类。*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New York: Harper & Bros, 1836, pp.150-158.滨下武志区分朝贡体系为六圈。*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6-37页。但其时欧洲学者一直不理解这天下五服或九服、多层向心、诸层各异、由近及远逐层拓展、亲疏有致的非霸道体系。
由此,他们把中国的省等同于欧洲的province或王国,认定居于省之上的总体为帝国,割裂其对天下的想象,便是根本的认识论误解。此外,现代早期的欧洲,各省近乎独立于帝王或国王,如法兰西,各省归附王国时,极大地保留了原来的行政机构;17世纪君主专制时,国王设立的总督亦称为“省里的国王”;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的行政和司法还远未实现统一。*让·马蒂耶:《法国史》,郑德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84页。这跟中国体系中朝廷的直辖部分截然不同,欧洲传教士们据此用欧洲的帝国概念来理解中国就不成立。换句话说,欧洲的王国或省并非中国诸省,欧洲的帝国亦非天下。
六、结 语
欧洲作者从时-空两个角度建构中华帝国话语,逐渐以丰富的历史材料填充缺失的逻辑链条。经过杜尔德*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1, pp.270, 555; 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Paris, 1777, Vol.1, pp.2-4; 1780, Vol.11, p.610.和德庇时等,中华帝国话语最终成型。1836年,德庇时第一次确定出一个跟其他民族都相同的神话学时代,从盘古开始历经数千年。他认为,只有当秦王成功迫使六国承认他的至高无上时,其政府才开始具有帝国的性质,第一个帝王即“始皇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登基即为帝国的开端,*Davis, The Chinese, pp.161-164, 166, 190.意涵“中华王国”绝对先于“中华帝国”,从而解决了门多萨等人的困境。1912年清帝逊位后,“中华帝国”最终成为时间上不再流动的对象。“中华晚期帝国”这样的次生性概念也才会在后世西方学界大行其道。
在空间上,他们在诸省之外,逐渐纳入福尔摩沙(即台湾)、满洲鞑靼(三省)、西鞑靼或蒙古鞑靼、哈密、西番(包括今西藏)和罗罗等作为中华帝国的组成部分。*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1, pp.79-80; Maill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1780, Vol.11, pp.189-196; 1785, Vol.13, pp.177-259.此外,欧洲的中华帝国话语依赖于对族性即支那人(Chinese)的认定:支那(China)是支那人所居之地,有明确的疆界,是固定不变的;中华帝国话语所指的地域即支那人生活的地域,也由此凝固起来。这是话语的逆反:中华名为帝国,但实质上却趋向同质化的王国。这使得帝国和王国话语长期模棱两可;他们甚至改造中文概念,说明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根本的原因在于欧洲缺乏可以理解中华体系的政治经验。
我们没有发现欧立德所说的欧洲学者在17世纪时以是否统治多民族来认定中华是否为帝国的证据。这不是当时帝国的定义性特征,而是最近的发明,如布班克(Jane Burbank)等人提出帝国是“适当合并新的民族时保持区隔和等级的政体”,“帝国观假定政体内的不同民族将会被有差异地治理”,跟治理单一民族、以同质化为诉求的民族-国家相对。*Jane Burbank, etc,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8.汪晖认为这是对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不满或反思而重新挖掘欧洲所谓帝国的遗产那一脉,期望超越当前在历史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叙事。*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帝国与国家》,第12页。尽管这一诉求在当下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对还原各地被认定为帝国的学术史来说并无益处,且把现代重新设定的帝国概念加诸于历史上的帝国认定过程,本身即具有现代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色彩。人们不但没有从中国视角出发进行历史研究,反而继续忽视中国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等,包括近来所谓的“中国中心观”路径都不能有所例外。
以中国视角来看他处,或可有别样的新意。正如曼可所说,中国史是由天子/皇帝统一之下的单一中心阶段和多中心的多邦体系阶段交杂构成。*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 pp.6-7.如果按照这个划分,欧洲的帝国-王国概念体系及欧洲史仅比较接近于后者,绝大多数时期缺乏一统于某个帝王的单一中心。换句话说,在一统性上,中国史包容欧洲史模式,反之不成立。
遗憾的是,欧洲的涉华学术史反其道而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被欧洲化不言而喻。由上可知,以西方的帝国话语来理解中华体系存在难以克服的认识论困难,我们应回到中国自身的文明多元性传统,挖掘其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成就,以为世界文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做出贡献。近来王铭铭、罗志田、赵汀阳等学者试图从人类学、历史学和哲学的维度阐发中国体系在现时代的意义,值得关注。*王铭铭:《中间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Mingming Wang, The West as the Other: A Genealogy of Chinese Occidentalis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4; 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中国文化》1996年第14期;罗志田:《夷夏之辨与治道之分》,《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赵汀阳:《天下体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Tingyang Zhao, “R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 ‘All-under-Heaven’(Tian-xia, 天下),” Social Identities, Vol.12, No.1, January, 2006, pp.29-41; 赵汀阳:《世界观是美学观点》,《文明》2007年第5期;Tingyang Zhao, “A Political World Philosophy in Terms of All-under-heaven (Tian-xia),” Diogenes, Vol.221, 2009, pp.5-18.
TheOriginoftheDiscourseoftheChineseEmpireofinEurope1516-1688
Chen Bo
The discourse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Europe is a result of long-term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After Yuan dynasty, with the maritime navigation in the early16th century, European knowledge about Zhongguo came to the“China” age, upon which the concepts of kingdom and empire were employed by Duarte Barbosa and Maximilianus Transiluanus in1516and1536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spects they grasped of the tribute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In1585,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first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e Empire of China” discourse, to be followed by Matteo Ricci, Alvaro Semedo, Martino Martini and Philppi Couplet; the discourse was eventually established first through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between European concepts and facts about China and then through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of the imperial pedigree. Qing dynasty was included as part of this pedigree of Chinese Empire. However, the contradictions that emerg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discourse were created between the European frame of empire, characterized by its violence and empire-kingdom tier, and the Zhongguo political system. It is analyzed that the latter, especially with its Tian-hsia cosmology and the tribute system, is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European notion of empire could conceptualize.
Chinese Empire, the Kingdom of China, Europe, The Zhongguo system, China
K207.8
:A
:1006-0766(2017)05-0078-11
(责任编辑:史云鹏)
陈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成都61006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至19世纪欧洲塑造的‘中国’形象研究”(17BSS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