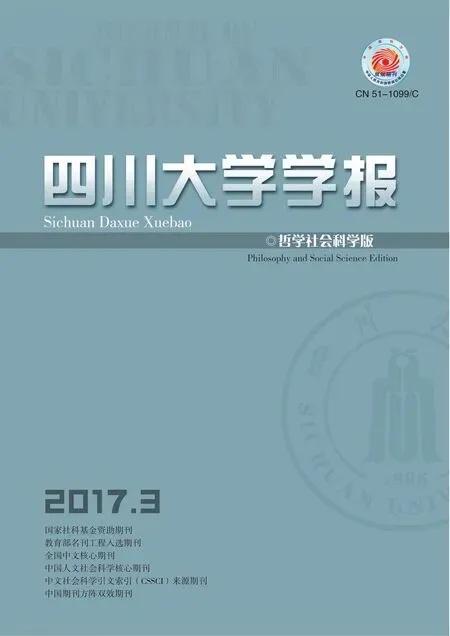“将理论继续下去”
——近二十年来国内“后理论”研究综述
陈后亮
“将理论继续下去”
——近二十年来国内“后理论”研究综述
陈后亮
近二十年来,随着“理论终结”的声音被传递到中国,后理论研究渐成学界热点话题。人们似乎普遍认为理论在西方大势已去,中国的理论研究者也必须重新检视我们在过去追随西方理论话语的得失,一方面为国内理论研究谋求新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中国文论的国际化寻找契机。国内后理论研究主要可被划分为五个话题,包括什么是理论、理论是否已经终结、如何克服文学研究或理论的危机、后理论时代的理论走向以及中国文论国际化等。对现有成果的综合考察可以为国内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未来走向提供思路。其实,无论是倡导推进文化研究还是回归文本分析,是继续理论的政治化还是回归学术本位,都是把理论进行下去的不同方式,都是在深化理论的反思行为、补偏救弊,让它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文学与社会现实。
后理论;理论的终结;文化研究;中国文论国际化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理论界陆续传出“理论的终结”或“后现代主义的死亡”等讯息,各种打着“后理论”或“反理论”旗号的评论之声此起彼伏,后理论时代似乎已成为对当前西方理论研究图景的最恰当描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不再有重要的理论家或流派横空出世,但人们对理论的兴趣似乎并未减退,只不过现在关心的热点话题是理论的死亡。大量论文和专著批量涌现,各种为理论送终的学术会议接连召开,其热闹程度并不亚于1960至1980年代的理论巅峰期盛况。
这股后理论热也快速波及到中国大陆。1995年,王宁率先发表《“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与思潮》一文,成为最早关注后理论话题的大陆学者之一。新世纪以来,后理论研究迅速成为国内学界新的学术增长点。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查到的数据,以“理论的终结”“后理论”“理论之后”“反理论”等为主题检索,可以得到超过300个结果。《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哲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学术月刊》等国内权威期刊都陆续刊发相关文章,其中《文学评论》和《文艺研究》还在近十年内连续发表十多篇文章,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国内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者,如王宁、周宪、陈晓明、王岳川、姚文放、王一川、阎嘉、周启超、金惠敏等都加入讨论,有的还把后理论当成最近几年的研究重点。与此同时,国外一些参与后理论话题讨论的重量级人物——比如乔纳桑·卡勒和文森特·利奇等——也被频繁邀请到国内讲学,他们的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相关主题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也在国内召开。*比如2004年2月11日《中华读书报》举办“文学理论死了?”专题讨论,清华大学在2004年6月主办“批评探索:理论的终结?”国际研讨会,2009年11月浙江大学举办“后理论时代与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10月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又召开了“后理论语境中的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
但另一方面,国内后理论研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国外后理论研究之间的历史错位,因为西方的后理论是真正的“理论之后”,即1960—1980年代的理论热消退之后,此时的理论早已在西方学界被体制化和经典化;而中国的后理论实际上仍发生于“理论之中”,当少数研究者紧跟西方步伐并引领国内后理论研究的风气之先的时候,其实有相当多数的人还未真正读懂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对什么是理论也没有搞清楚。这恐怕正是有学者发出如下感慨的原因所在:“(理论之后)在中国则仍然是一个西方理论的本土接受与本土应用问题,中国不会出现‘理论之后’,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很难有,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处在理论缺失的状态中。”*段吉方:《文学研究走向“后理论时代”了吗?——“理论之后”问题的反思与批判》,《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9期。很多人由于早已习惯了学术跟风,便迫不及待地抛开手头上的理论入门读本,加入后理论的争论之中。这就造成当前国内后理论研究成果繁多却良莠不齐的局面。因此,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近20年来国内有关后理论话题的研究成果,从中总结出值得重视的观点和创见,并为国内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未来走向提供思路。*“后理论”“理论的终结”和“反理论”这三个问题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谈及后理论,就必然涉及对理论的抵制或继承问题。故本文对后理论研究的梳理也兼及另外两个话题。另外受条件所限,本文也主要以考察期刊文章为主。
一、如何诊断“理论的终结”?
无论对国际还是国内学界来说,2003年都是一个标志性年份。在这一年,特里·伊格尔顿出版了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即《理论之后》。该书犹如一颗炸弹,在理论界引发巨大震动。此前国内关注“理论的终结”话题的人还只是少数,“后理论”更是鲜有所闻。但自此之后,国内以“后理论”为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大量涌现,把《理论之后》列为参考文献的论文达到上千篇之多,以它为标题的文章也不下200篇。可以说,它对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所起到的里程碑意义不亚于他的那部《文学理论导论》。如何理解、回应或者评价伊格尔顿的这部新著便成为国内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的开篇即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页。接着他又用略带讽刺和调侃的语气列举出十多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理论大师以辅证他的论断。乍看上去,伊格尔顿似乎是在发布理论死亡的讣告。实则不然。在此有两个关键词需要留意,一个是“文化理论”,另一个是“黄金时期”。也就是说,作者的意思是:已然消失的只是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而不是理论已经彻底消失;它肯定仍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可能还会活得很好,只不过会失去曾经备受尊崇的优势地位。
国内有少数读者误读了伊格尔顿。比如张箭飞认为:“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一书敲响了理论的丧钟。”*张箭飞:《文化理论在西方的死亡》,《学术研究》2005年第9期。但大部分研究者都看出,伊格尔顿只是在批评后现代文化理论放弃政治批判、逃避现实的错误倾向,“他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反思来找到问题所在,找出问题是他接下来思考未来的前提”。*尹庆红:《“理论之后”的理论——谈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正如他自己所思考的:“新的时代要求有什么样的新思维呢?”*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第4页。金惠敏和张伟等人也都试图改变《理论之后》给人造成的“理论已经终结”的错觉。前者指出:“伊格尔顿决非一般地反对理论,而是通过‘理论之死’这种振聋发聩的形式唤醒人们对于后现代理论之局限的反思。”*金惠敏:《理论没有“之后”———从伊格尔顿〈理论之后〉说起》,《外国文学》2009年第2期。另可参阅张伟:《“理论之后”的理论建构》,《文艺评论》2011年第1期。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伊格尔顿始终坚持把政治批评作为理论研究的优先方向。在他看来,理论的兴起与衰败都与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沿着伊格尔顿的思路,国内很多学者也把理论的终结归因于政治因素,比如王晓群、阎嘉、刘进、尹庆红、张箭飞、方钰等人。*参见王晓群:《理论的现状与未来》,《外国文学》2004年第6期;阎嘉:《“理论之后”的理论与文学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刘进:《文学理论的基本品格和功能——对“文学理论危机”话题的一种理论回应》,《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方钰:《论西方文化理论的困境及出路》,《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张箭飞:《文化理论在西方的死亡》,《学术研究》2005年第9期;尹庆红:《“理论之后”的理论——谈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等。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详细引述他们的论点。他们普遍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及9·11事件爆发,理论没有、或者说已经不能有效应对新的问题。它对新的阶级、文化和民族矛盾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束手无策,只是继续着以往的文化符号分析和批判工作,让理论演变成学院知识分子的智力游戏。理论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异见者,反倒成了它的合谋者,自然免不了被抛弃的命运。
与上述这种政治先行的研究方法不同,有的学者从其他方面分析了理论“退烧”的根源。在此,盛宁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说:“以‘解构哲学’和文化研究为主力的理论热之所以会消退,这里面固然有所谓‘政治斗争’的因素,但我看其中更多的则是由于自身的局限,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由于提出那些理论学说的理论大师们的离场而造成的。”除了后两点之外,盛宁尤其强调的是第一点,即所谓的理论“自身的缺陷”,也就是理论不具有指导具体批评实践的能力,“理论其实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假设,……它只不过是帮助你对自己的阐释活动、对批评行为的机理有了一种更自觉的认识, 而它与你对一个作品本身的理解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盛宁:《“理论热”的消退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出路》,《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在盛宁看来,理论终结的原因非但不是因为它逃避政治,反倒是因为它太政治化了,“什么事情一旦政治化,那就成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把文学文本认定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喉舌, 把文学批评作为为‘地位低下者’行使代言的使命,”于是,“‘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学研究,把文学研究变成了又一个‘沉闷的社会学科’,使文学系变成了一潭学术死水。”*盛宁:《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与盛宁看法相近,陈晓明也认为理论就是“一种元理论话语体系,……一种用来规范文学学科、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并且解释全部文学基本原理的元理论体系”。结合中国的具体语境,陈晓明认为这样的理论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我们的创作和批评实践均不太成熟的时候,起到了规定和立法的作用。但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均走向成熟,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姿态,突破了理论设置的那些规范,理论再想去规约实践已然力不从心,“这种理论的使命已经结束”。*陈晓明:《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二、回到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是“理论”?
在当前国内后理论话语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清楚回答,那就是到底何谓“理论”?或者说,理论与文学理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以及文化理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那么有关理论是否已经终结、为何终结、或者是否需要被终结等问题的回答就会出现偏差,进而对后理论时代的理论生产做出不同判断和预期。或许当前学界在理论终结话题上出现争端的根源就在于此。表面上大家都在谈论理论,但实际上他们真正所指的很可能并非一回事。
例如,上文提到的陈晓明所理解的理论实际上更接近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原理,或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所说的“一套问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观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32页。类似的看法也在其他人那里可以被发现。他们都把理论等同于某种超越于创作或批评实践之上的话语,对各种实践活动起到指导和规约作用。理论与实践之间似乎就是上下级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里,文学批评臣服于文学理论”。*陈晓明:《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因此,作为当代著名批评家的陈晓明呼吁终结理论的使命也就不奇怪了。然而他所要终结的这种“理论”显然并非所谓的“大写的理论”。
很多国外学者对“理论”一词的使用也比较随意,其具体内涵在不同语境下往往有所变化。即便如此,批评家们在以下两点上还是基本可以达成共识。首先,理论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范畴,它的内涵有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早在1960年代之前,理论基本上等同于文学理论或文学原理,即对文学活动的一般原理的归纳和概括,包括概念、策略和方法等。虽然它也偶尔涉及对社会历史语境的讨论,但总体来讲,这种文学理论还是以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为关注重心。到了1960年代以后,随着结构主义兴起和语言学转向,文学研究不再拘泥于探究文学文本中的意义,而是更关心意义在整个文化场域内被生产出来的过程和机制。用卡勒的话来说就是:“理论意味着一套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它可以解释不同种类的素材,它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或者没有文字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就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和文学批评的背后发挥作用的一套具体的跨学科理论。”*Jo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3.换句话说,1960年代的理论主要就是结构主义。而到了1970年代之后,后结构主义又逐渐兴起,批评家不再仅仅关注于发掘文本中的意义,而是更关心意义生产的过程和机制。他们不再仅停留于结构主义模式的“对语言、修辞、符号及其它表意系统的分析”,而是“指向对社会文化和历史状况的批判”。*Gregory Castle, 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2.于是,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左派思想的后结构主义又成为1970年代理论的代名词。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虽然时常把目光投向更大范围的文化政治文本,但总的来讲,文学仍然是它们关注的中心。不过在1980年代以后,理论的边界开始大规模扩张。受到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双重启发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开始把批判的矛头重点指向文学以外的事物,包括性别、阶级、种族和身份等。理论家们冲破学科边界,自由地穿梭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等学科之间。由此理论也就成了卡勒所说的“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著作”。*乔纳桑·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4页。此时的理论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分别是大写的、单数的理论“Theory”和小写的、复数的理论“theories”。后者指的是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不同流派的集合,包括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而前者则更强调它们的共性,即对传统文化实践的批判和质疑。也正是他们创造了理论的黄金时期。进入1990年代以来,理论又发生了所谓的文化转向。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理论成为最晚近阶段的理论的内涵。这一时期的文化理论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对非文学文本报以前所未有的关注;二是重分析而轻批判。
其次,理论的内涵虽然在不断变化,但有一点却始终未变,那就是理论的自我反思性。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理论与实践之间并不存在对立的等级关系,而是相伴相生的、同一性的关系。人们在实践中总会遇到各种问题,于是我们便需要反思,也就有了理论。在这种意义上,“一切社会生活都是理论的”,“同样,所有的理论也都是真正的社会实践”,“理论不过是人类对自我行为的回望,被迫形成一种全新的自我反射”。*Terry Eaglet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90, pp.24, 27.通过反思行为,我们对实践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可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甚至有时候可以动摇此前长期被坚持的原则和基础,并为未来的实践开创新的可能。从传统的文学理论到结构、后结构主义,再到后来的文化研究,理论走过的历程其实就是把这种对文学实践的反思不断深化的过程。它让我们对所有的文学实践有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意识,一切未经反思检验的前提、假设、原则和方法都难以被若无其事地维系下去。这也正是美国学者考夫曼所说的下面这段话的含义:“美国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要逃避和破坏实践,而是要通过各种松弛有别、但持之以恒的自我批判去修正文学研究的‘错误’。通过从其他领域借鉴方法,理论试图把文学研究变成一门更具有自我意识的学科。”*David Kaufmann, “The Profession of Theory,” PMLA, No.3, 1990, p.520.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关于文学实践的反思性话语实践。只要有文学实践——不管是创作还是批评——这种反思就不会停止,因为不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和调整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前进的源泉。反思会打破成见、惯例、常识,带来新知识,但用不了多久,随着新知识不断泛化,它又积淀成常识,又需要进一步反思。但旧的知识也不会像一件破衣服那样被扔掉,而是像河床一样不断累积,充实着人类智慧,并且不时被重新翻倒出来激励新知识。认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当前有关理论终结的讨论中,我们切不可着急扔掉理论这件破衣服,而应该把它的反思精神继续下去。只不过现在不仅需要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反思,更需要对理论自身进行反思。
值得高兴的是,国内大部分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把理论反思继续下去的重要性。王炎、周宪、王宁、张良丛、王晓群等人都认识到,理论在1990年代以来的日益学术化、体制化和经典化是终结说出现的根源。*参见王炎:《理论话语与美国学界》,《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王宁:《再论“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态势及走向》,《学术月刊》2013年第5期;张良丛:《终结还是自反:理论之后的理论言说》,《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王晓群:《理论的现状与未来》,《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理论不再构成对既有知识的反思和挑战,反倒失去了新鲜感和革命性。赖大仁和周启超等人则结合中国文论研究的实际情况,重点强调在后理论时代继续深化理论反思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必要性。前者认为:“‘后理论’转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反理论’,这里的‘反理论’不是反对理论或反掉理论,不是要消解和抛弃理论,而是注重批判性地反思理论。”*赖大仁:《“后理论”转向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后者则指出,“后理论”的前缀“后”的意义并不在于“批判、否定、区隔”,而在于“反思、承续、超越”,因此他呼吁:“不是告别理论,而是反思理论才是文论园地耕耘者的一份志业。”*周启超:《在反思中深化文学理论研究——“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三、走向文化研究还是回归文本批评?
自1990年代以来,有关文化研究或者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引发了很多争议。卡勒在他那本影响巨大的小书《文学理论入门》中曾专门开辟一章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理论’就是理论,文化研究就是实践。文化研究就是被我们简称为‘理论’的理论所对应的实践”,并且“在广义上来说,文化研究就是去理解文化——尤其是现代世界的文化——的功能,包括文化生产是如何运行的,……从原则上来说,文化研究涵括、覆盖着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实践来对待”。*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43, 44.换句话说,文化研究就是把文学研究的方法应用于其他文化产品或现象。在卡勒看来,文化研究有两个最重要的理论源头,它们皆盛行于1960年代。一是法国结构主义,二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尤其是威廉斯和霍加特为文化研究所做出的奠基性工作。结构主义方法教会人们把文化实践视为另一种文本,去发掘文化实践背后的符码系统或意义生成机制。英国马克思主义则让人们注意到这些系统如何控制、引导或规训着我们的文化实践,并且去思考是否可以从中寻找变革的可能。
在《文化批评、文学理论、后结构主义》一书中,利奇则重点讨论了后结构主义对文化研究的积极影响。在他看来,“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目的就是文化批判”。*参见Vincent B. Leitch, Cultural Criticism, Literary Theory, Poststructu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8.这包括调查和评判占据主导地位的对立的信念、范畴、实践和再现,去探究语言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伦理的、宗教的、法学的、科学的、哲学的、教育的、家庭的以及美学的话语和制度得以流行并被消费的原因、构成、结果以及方式等等。
很多人对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持反对意见。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文学批评家鲁莽地跨越了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去涉及那些自己并不擅长的文化或社会科学领域,所研究出来的结果大多属于外行话,既没有太多的实际效果,还大大削弱了文学研究的价值,直接导致了理论的终结。卡勒对此很不赞同,他认为:“文学表面上的衰退不过是一种假象,无论理论话语发端于哪里,它们通常都提醒我们去留意在各种话语中发挥作用的不同样式的文学性,从而也就以它们的方式重新肯定了文学的中心地位。”*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p.5.考夫曼同样肯定了文化转向对于文学理论的意义。他认为,理论的出现符合文学研究的专业化分工趋势,并且有助于巩固文学系在大学中的地位。通过生产出更多的流派、学术明星和专业知识,它极大地拓展了学科范围。那些认为理论弱化了文学系地位的人们没有看到,对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的坚持实际上也是文学研究者由于无法为社会提供有用产品而找到的借口。若不是理论让文学研究变得更有用,文学理论或许早就面临危机了。*参见Kaufmann, “The Profession of Theory,” pp.521-523.对于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有不少主流批评家都持积极态度,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也比较肯定。他们反对把理论终结的原因归咎于文学研究的泛化,而是把它与理论本身的日益体制化、学术化以及更大的社会政治环境联系起来。而伊格尔顿等左派理论家认为,让理论研究重新驶回正确的政治轨道是拯救理论的恰当途径。毕竟,“理论的用处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知识问题”,“理论的必要性就在于保存革命的火种”。*Eaglet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ory, pp.32, 38.
与国外情况比较接近,国内学界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上,也主要聚集在以下问题,即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到底是否应该?或者说文化转向是导致理论终结的罪魁祸首吗?围绕这个问题,国内学者可以粗略分为四个群体。首先是反对文化研究的群体,以苏宏斌、汤拥华、张伟、盛宁等人为代表。比如苏宏斌认为:“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有着一种难以相容的异质性, 它的出现并不是对文学研究的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对文学研究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苏宏斌:《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学理论的未来》,《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另可参阅张伟:《“理论之后”的理论建构》,《文艺评论》2011年第1期;汤拥华:《理论如何反思?——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引出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等。第二个群体是文化研究的支持者。比如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刊发了一组笔谈,作者均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他们都对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表示肯定,其中陈晓明认为:“当代文学理论转向不可避免要向文化批评发展。……文化批评并没有消解理论,而是使文学理论找到了新的更有活力的资源。”*陈晓明、孟繁华等:《“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陈晓明近年来显然已不再对文化研究持赞同态度。参见陈晓明:《理论批评:回归汉语文学本体》,《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6期等。
第三个群体虽没有明确反对或支持文化研究,却认为文学理论还是应该回归文学文本研究,这让他们更容易与第一群体结成联盟。姚文放、周启超和杨彬彬等人都把20世纪的文学理论发展史归结为“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的演变历程。如果说第一次转折让文学理论偏离了文学经验的话,那么正在发生的第二次转折则意味着文学的回归。姚文放认为,理论兴起的过程也就是文学理论衰退的过程,理论过多涉足文化政治实践,却严重忽视文学实践,最终“变成了不着边际、抽象沉闷的教条。它刻意与文学批评和作品阅读隔绝开来,偏好那种玄虚晦涩、令人望而生畏的论说文体,最终导致对于文学研究正业的偏离”。*姚文放:《从理论回归文学理论——以乔纳森·卡勒的“后理论”转向为例》,《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当然,绝大多数倡导文学回归的研究者都认识到,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理论教谕之后,要想完全回到那个未经理论启蒙的纯真年代已不可能。寻求理论或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有机融合才更可行。就像杨彬彬所说:“以‘理论热’为语境、在‘后结构时代’讨论回归文本,必然是另一层次和意义上的回归。……而不是回到由‘作者意图’决定其意义的文本,回到以作者视线为转移的研究,或者回到作者生平和时代背景研究。”*杨彬彬:《“回归文本”——略论美国文学研究转向中的“理论”与“文本”》,《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另外王宁在《“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走向和理论建构》(《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反对回归文本研究的人属于第四个群体。它的规模相对较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进,他异常坚定地倡导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进军,他指出:“文学理论来自于文学实践并指向文学实践,但又超越文学领域,……或者说,文学理论是理论家由对文学或指向文学的思考而介入文学以外世界的途径。”*刘进:《文学理论的基本品格和功能——对“文学理论危机”话题的一种理论回应》,《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支持文化研究的人虽然往往也反对回归文本研究,反对文化研究的人则希望理论回归文学,但在文学研究是否应该保留政治和社会批判的问题上,这四个群体经常会出现比较复杂的交叉重组现象。大部分反对文化研究、倡导回归文学的人都反对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其中尤以盛宁为代表。在他看来,“文化研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理论深度”。他非常反对“动辄就把文化问题政治化”,认为“文化研究应该和其他思想研究一样,它最基本的任务本应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成因和影响等,做从里到外全方位的研究”,而研究的目的,他觉得“充其量只是起到一种‘智库’的作用,它和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并不是一回事”。*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李西建虽然把“回归文学”视为后理论的表征之一,却也认为“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则更多地转向文化政治,强调理论生产应承担公共领域内更多更大的社会责任”。*李西建、贺卫东:《理论之后: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与知识生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而支持文化研究的人则希望保留理论的政治锋芒。比如贺绍俊认为理论转向文化研究的一个积极后果便是“越来越鲜明的社会批判性和现实针对性”,但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只是把理论作为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接纳进来,而“这些理论所蕴含的社会批判性和现实针对性却在我们的移植过程中丧失殆尽”。*陈晓明、孟繁华、贺绍俊等:《“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另外周敏在《从文化研究到文化理论——对文化研究的一个反思和期待》(《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中也提出了类似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的理论话语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更有社会干预精神和责任伦理意识。
四、后理论时代的知识图景
如前所述,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不断反思、质疑、改变和更新当前实践的话语实践。既然我们需要在不断的反思和重建中获得进步,那么理论也就永远不可能彻底终结,只会随实践情况的变化而调整自己存在的样态。虽然现在表面看上去,理论已不再如从前那样受人追捧,但实际上这何尝不是理论太过成功的表现?如今纯粹抽象的理论文章已经不太受欢迎,但忽视理论方法的所谓文本批评恐怕也不易受到青睐。即便再怎么反感理论的人,也不敢对理论完全漠视。也就是说,理论已经从几十年前的时髦、前卫知识变成今天的专业基础知识,成了文学研究入门必备的技能条件。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凯勒斯和赫布里史特才做出如下比喻:“理论就像一种病毒。它已然、并将继续在全球范围传播。”*Ivan Callus and Stefan Herbrechter, “Coda: Theory Reloaded,” in Ivan Callus and Stefan Herbrechter, eds, Post-Theory, Culture, Criticism, New York: Amsterdam, 2004, pp.283-284.而拉巴尔特则把理论比作幽灵:“如果说理论变成了自己的幽灵,那它也是一个很惹眼的幽灵,总是不停地在我们古老的学术城堡里走动,并晃动着身上的锁链。”*Jean-Michel Rabate, The Future of Theor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p.10.
不论是把理论比作病毒还是幽灵,都说明理论绝不是某种可被轻易抛弃的东西。它必定会长久、甚至永远与我们的文学活动相伴随。在这种情况下,预言或展望理论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便成为后理论研究的又一热点话题。在理论处于鼎盛时期,各种理论流派此起彼伏。那么在未来几年,是否还会延续这种趋势?是否会有新的流派成为主导范式?对此,国内主流看法比较统一,普遍认为未来不大可能再出现某种理论流派一枝独秀的局面,而是将进入一个群龙无首的多声部时代。
早在1995年,王宁就率先指出:“西方文论界和文论界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多元共生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时代,一个多种话语相互竞争、并显示出某种‘杂揉共生’之特征和彼此沟通对话的时代。”*王宁:《“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与思潮》,《国外文学》1995年第3期。类似观点也见于王宁:《“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 走向后人文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于是,“多元共生”成为此后人们描述后理论时代的知识图景时频繁出现的关键词。而阎嘉则用了另外一个更形象的表述,即“一种‘马赛克主义’或‘非中心的游牧’状态”。*阎嘉:《21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与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哪种理论范式会成为新的主导虽然很难判断,但人们还是对哪几种“主义”或“流派”有可能成为相对的主流进行了预测。比如李点预言伦理批评“也许还能从‘理论之后’的废墟中凤凰再生”,成为“我们所能使用的最佳批评工具之一”。*李点:《理论之后: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伦理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6期。李长生青睐阿兰·巴丢,认为巴丢的思想特点是“对真理的普遍性的恪守、对同一性的倡导、对科学和理性主义的肯定、对语言转向和相对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英美文化研究中差异政治的谴责”,这有可能让他成为“文化理论未来一种可能的向度”。*李长生:《文化理论的限度与“理论之后”的超克》,《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6期。陈太胜则更看好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新形式主义,认为它将成为“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的一种可能”。*陈太胜:《新形式主义: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可能》,《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程朝翔认为理论之后将是“哲学以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形式登场”,即文学理论将“更多地走向哲学、包括文学哲学”。*程朝翔:《理论之后,哲学登场——西方文学理论发展新态势》,《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王宁则预测了理论在未来的多种可能走向。1995年,他预计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文化研究会成为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文化界和理论界的最新走向”,到了2005年,他又在这个名单上加上了“流散写作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全球化与文化的理论重构”“生态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的建构”,以及“语像时代的来临和文学批评的图像转折”,认为它们代表着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2013年,王宁再次把后人文主义补充为“理论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参见王宁:《“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与思潮》,《国外文学》1995年第3期;《“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 走向后人文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
塞尔登在《当代文学理论导读》 一书中曾注意到西方理论在晚近的一个发展趋势,即“单数的、大写的‘理论’迅速地发展成了小写的、众多的‘理论’”。*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受其启发,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理论的整体发展态势作出评判。比如周宪认为理论在过去虽然对宏大叙事表示了极大的反叛和质疑,但悖谬的是,它在试图构筑包罗万象的理论帝国的过程中,也表现出明显的宏大叙事的特征或弊端,因此,“后理论的特征之一就是告别‘大理论’,不再雄心勃勃地创造某种解释一切的大叙事, 转而进入了各种可能的‘小理论’探索”,这样“那些被大理论和文化研究所遮蔽的大问题,反倒可以在理论之后的小理论的视野中凸现出来”。*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王一川则指出:“‘理论之后’的理论已经从‘大理论’转变为‘小理论’,即从‘宏大叙事’转变为‘小叙事’。”*王一川:《“理论之后”的中国文艺理论》,《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相比之下,赖大仁提出了比较折衷的看法。他认为,正如我们这个时代存在多种多样的文学观一样,我们也应该“可以有不同的文学理论建构”,既应该欢迎那种“偏重于对某些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进行说明和阐释,有助于此类文学现象的认识和引导”的小理论,“也应该有某种与之相适应的大写的文学理论建构起来”,*赖大仁:《“后理论”转向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以便更好地回应国家、民族和人类发展的时代大局。
五、西方文论的困境与中国文论的国际化机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中国学者在参与后理论话题讨论的时候,并没有一味把眼光放在西方世界,而是结合了中国具体理论语境。毋庸置疑,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大批量引进西方话语资源,就如同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引进外资一样,这极大地丰富和促进了国内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随着理论在西方遭遇终结的危机,中国的文论工作者也趁机放缓了追逐西方的脚步,开始反思中国理论研究的前景。前述苏宏斌、姚文放、周启超、王一川、张伟等人文中都批评了国内学界割裂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的状况,认为国外理论建构在细致的批评实践上抽丝剥茧、环环相扣,让人信服。相比之下,国内研究者却更喜欢空泛的评介、梳理或解析西方理论,就像描绘空中楼阁一样,严重忽视文学实践,使得中国的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几乎成为两个互不相关的学科。因此,当国外的理论生产速度放缓以后,我们有必要也放缓跟踪步伐,好好消化我们引进的理论资源,让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文学实践。
民族性问题是中国文论工作者无法回避的一个焦点。王炎的看法是:“中国学者的眼睛不过在盯着国外潮流,并未深入到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学术之间的内在关系之中,或者说尚未建立明晰的研究主体性。”*王炎:《理论话语与美国学界》,《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与之相似,王岳川也提出我们在审理西方文论的同时,必须“从中国身份立场”出发,“应力求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追问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仅仅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国家民族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的问题?是现代性文论问题还是后现代性文论问题?……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创新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新体系”。*王岳川:《“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症候》,《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
实际上,近年来已有很多研究者越来越自觉地站在这种所谓的中国身份立场上参与后理论时代的话语争鸣。如果说在1990年代之前的理论热潮中,我们因为臣服于西方理论的强势话语而患上所谓“失语症”的话,那么在很多中国文论工作者看来,当前西方理论所面临的危机或许正为中国文论走向世界创造了契机。王晓群在2004年展望理论的现状与未来时就曾预言:“新理论很可能出现在世界各地,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因为边缘也是理论最活跃的地方。”*王晓群:《理论的现状与未来》,《外国文学》2004年第6期。而卡勒在2011年应邀来清华大学演讲时也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去思考西方理论和其他地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之间的关系。”*乔那桑·卡勒:《当今的文学理论》,《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在国际文学理论版图上,中国显然处于这种“第三世界”或“其他地方”。很多研究者相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在全球经济政治版图上,中国已经跃居到世界第二的位置,那么它现在可以、也应该在国际文化版图上获得相匹配的地位。在这方面,王宁的声音最为响亮,他从齐泽克、斯皮瓦克以及霍米巴巴等著名理论家的成功经验中获得启发,认为“‘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使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一些理论话语步入前台,也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得来自小民族或非西方学者得以与西方乃至国际同行在同一层次进行平等对话”,*王宁:《世界诗学的构想》,《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而“任何一种出自非西方的理论一旦被西方理论界‘发现’,就有可能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最后由一种带有本土特征的‘地方性’(local) 理论逐渐发展演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global)理论”。*王宁:《“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在群龙无首的后理论时代,加速推进中国文论的国际化,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关键是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返回中国传统,从老祖宗那里讨回些传家宝,自然是很多人想到的首善之选。比如徐亮认为,“自柏拉图开始,西方思想一直把寻找真理作为始源性问题”,它是所有后世西方人文学科的起点,但也构成西方文论一个无法克服的原罪,因为从人出发去寻找真理根本不可能,会让西方思想家陷入无穷的形而上陷阱。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思想从不设置人与世界的二元结构,也从未把在此基础上的通达真理作为思想的主要任务。中国诗学因而也不需要背负这种形而上学重担”,这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包括文论在内)的先天优势,因此“能够为西方诗学困境的解除提供思路”。*徐亮:《理论之后与中国诗学的前景》,《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恐怕这也正是王岳川认为“我们应更加关注并回望东方去发掘自己曾经虚无化的传统和经典”*王岳川:《“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症候》,《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的原因。
与徐亮和王岳川回望过去的姿态不同,王宁更强调从当下中国的话语资源寻找中国文论国际化的动力。他先是看好以牟宗三、杜维明、成中英等海外华裔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认为他们已经克服了传统儒学专断、排他的思想模式,同时广泛吸收借鉴当代西方理论资源,因此“完全可以作为挑战‘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化的另一股话语力量”。*王宁:《“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走向和理论建构》,《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近来他又非常重视张江提出的“本体阐释”论,认为其实现了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辩证统一,可以克服西方理论固有的“强制阐释”和“场外征用”的弊端。“本体阐释”倡导“让文学理论回归文学的阐释”,“从文本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符合当前国际学界的主流认识,特别是与卡勒最近对“理论的文学性”的倡导不谋而合,这说明“在讨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时,已经接近并达到了可以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的认识高度”。*王宁:《“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结 束 语
本文围绕什么是理论、理论是否已经终结、如何克服文学研究或理论的危机、后理论时代的理论走向以及中国文论的国际化等几个方面,综合考察了当前国内的后理论话语。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理论终结”的话题给常年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们带来了几分惋惜,但自解构主义以来,似乎很少有哪个话题能引起这么多学界大腕的共同兴趣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理论现象。其实不管理论指的是一般批评方法还是对批评的反思,它都不会一去不返或彻底终结,而只会随着历史社会语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姿态、变换样式。
伯恩斯说得好,“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将理论继续下去都是重要的,即便在此过程中创造出的新理论已大不同于1980至1990年代的那些不同种类的高雅理论”。*Nicholas Birns, Theory after Theor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iterary Theory from 1950 to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2010, p.316.倡导推进文化研究或是回归文本分析,继续理论的政治化或是回归学术本位,这其实都是把理论进行下去的不同方式,都是在深化理论的反思行为、补偏救弊,让它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文学与社会现实。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否都不会再出现像解构主义那样的理论强音?多元共生的马赛克景观会维持多久?西方理论的危机是否意味着中国文论走上国际理论舞台的契机?中国文论在此舞台上能取得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位置吗?中国文论的国际化到底是顺应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的必然选择,还是如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建设中国特色话语的“民族焦虑”?*刘进:《文学理论的基本品格和功能——对“文学理论危机”话题的一种理论回应》,《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所有这些问题,恐怕都只有时间才能够检验回答。无论如何,至少在目前,还是让我们把理论继续下去,不是为了恢复高雅理论的往日风光,而是为了对文学实践进行永不停歇的批评性反思。
(责任编辑:庞 礴)
“To Keep Theorizing”: A General Review of Chinese Scholarship on Post-Theory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Chen Houliang
With the voice about the “end of Theory” arriving in China, Post-Theory studie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for Chinese scholarship in the past 20 years.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regime of Theory in the West has toppled and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reexamine gains and losses in the past when we submitted ourselves to the rule of the Western Theory. This may help us to find a new way for Chinese literary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and to seek for chances to internationaliz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Focusing on five topics, namely, what “Theory” is, if Theory has really met its end, what is the way out of the crisis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ies, what will be the new trends for Post-theory, and how we can internationaliz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this paper will cast a general perspective on Chinese Post-Theory studies, hoping to summarize important viewpoints and find inspirations for the future scholarship. Actually, most argumen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including whether to turn to cultural studies or return to literature, whether to go for or against the political edge of Theory, represent different ways to continue doing Theory, to deepen its self-reflection, and hence to adapt Theory to the new social and literary realities.
Post-Theory, the end of Theory, cultural studie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陈后亮,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武汉 430074)
I0
A
1006-0766(2017)03-0089-10
§文艺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