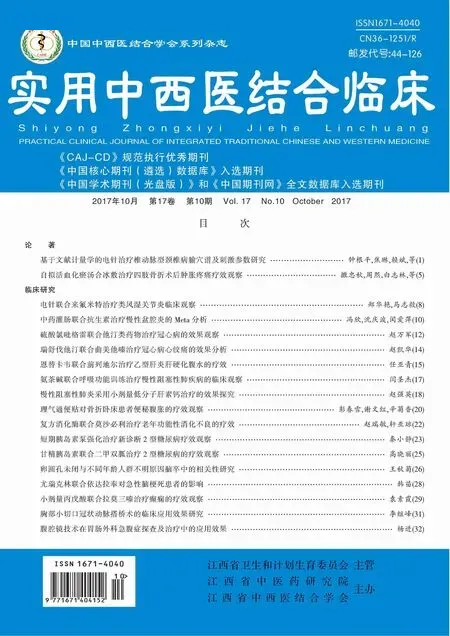胡翊健副教授治杂病验案撷英
晏章现 胡翊健
(1江西中医药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 南昌330004;2江西省中医院 南昌330006)
胡翊健副教授治杂病验案撷英
晏章现1胡翊健2
(1江西中医药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 南昌330004;2江西省中医院 南昌330006)
杂病;胡翊健;病案
胡翊健副教授,硕导,从事临床工作30余年,从事《金匮要略》教学工作20余年,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白塞氏病、皮肌炎及内科疑难杂病。笔者有幸跟诊于胡翊健副教授,在临床学习过程中,目睹其治疗多种内科疑难杂病,疗效好。在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难治性口疮以及不明原因的肾功能损害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现择其几则案例,整理如下。
1 以益气养血、活血止痛为法,用圣愈汤加减治疗尪痹病
尪痹为中医“痹证”的范畴。《内经讲义·痹论》[1]:“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素问·百病始生》中曰:“风寒湿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正如《诸病源候论·风痹》:“痹者……由人体虚,腠理开,故受风邪也,病在阳曰风,在阴曰痹。”《医宗必读·痹证》:“诸痹……良有营卫先虚,腠理不密,风寒湿乘虚内袭。正气为邪所阻,不能宣行,因而留滞,气血凝涩,久而成痹。”胡翊健副教授认为尪痹病,正虚是内因,邪气是致痹的条件,不通是病理关键,不荣是痹病的必然,该病虚实夹杂,以气虚血瘀证多见,《难经》曰:“气主煦之,血主濡之。”《内经》:“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有云:“不通则痛,通则不痛”,对于久痹患者,可从扶正祛邪角度入手,以益气养血、活血止痛为法治之,多有验效。圣愈汤为四物汤加黄芪、人参。四物汤具有补血和血的作用,其对血液系统具有补血、抗血栓形成、抗凝血的作用,改善微循环,改善血液流变学,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增强免疫力,黄芪、人参皆能兴奋中枢神经系统,抗疲劳、强心、增强免疫力,黄芪还能促进蛋白质的代谢。人参亦能增加红细胞和血红蛋白促进造血机能。此外,还有免疫与抗氧化作用研究[2]。
1.1 病案举例 胡某,2017年3月7日初诊。诉四肢关节疼痛,双腕、掌指及指间关节尤甚,关节局部有硬结、瘀斑,神疲乏力,动则汗出不止,畏风,纳呆食少,口渴不多饮,曾在多家医院就诊,效果均不显,后就诊于胡翊健副教授,诊时症如上诉,小便频,大便偏干,舌红苔少,脉沉涩。胡翊健副教授诊断为尪痹病,辨证为气虚血瘀证,予圣愈汤加减:黄芪15 g、党参 10 g、甘松 10 g、当归 10 g、桂枝 10 g、白芍 15 g、生地黄 10 g、桃仁 10 g、鸡血藤 15 g、牛膝 15 g、海桐皮15 g、威灵仙15 g、酸枣仁10 g。2017年3月14日患者复诊,诉服用上方症状大为好转,效不更方,续用上方15剂,嘱患者勿劳累、避风寒。2017年4月5日患者复诊,诉诸症状消失,唯有下肢有硬结和少许瘀斑,嘱患者须用上方间断服用,并予桂枝茯苓丸、香砂仁六君子丸隔日服用。
1.2 讨论 该患者先后曾至多家医院就诊,其关节局部有硬结、瘀斑,神疲乏力,动则汗出不止,可知其痹病日久。“神疲乏力,动则汗出,畏风”为明显的气虚之象。该患者“纳呆食少,舌红苔少”可知其中气受损,脾胃健运失司。在一派气虚血瘀之象中见“大便偏干”可见其体内阴液受损。脉沉主病在里,脉涩多见于瘀血。四诊合参,胡翊健副教授认为该患者为气虚血瘀症,以圣愈汤加减治疗。该患者疼痛,原因责之“不通则痛”或“不荣则痛”。导致疼痛的原因,有虚有实,需“急则治其标”或“标本同治”以迅速缓解消除疼痛。圣愈汤为元·朱丹溪《脉因证治》之名方,是在四物汤的基础上加补气药人参、黄芪[3]。方中黄芪、党参补气固表;当归活血,当归与黄芪配伍而为当归黄芪汤,可气血双补,桂枝通阳,与芍药配伍而调和营卫;易熟地为生地,与桃仁、鸡血藤合用,加强活血作用,取《医宗必读卷十·痹》:“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意;海桐皮、威灵仙祛风湿通经络;牛膝补肝肾、强筋骨、活血祛瘀,引药下行;酸枣仁养血安神、益阴敛汗;甘松醒脾健胃。全方共奏益气养血、活血祛风、通络止痛之效,且补而不滞,补而不滋,补血活血而不耗血,以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功效。中医强点治病求本,正如《黄帝内经》所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该患者病情缓解后,胡翊健副教授考虑到其正气虚弱之本,且有瘀血的表现,故嘱患者以桂枝茯苓丸祛瘀生新,以香砂六君子丸益气健脾。
2 以平调寒热,變理阴阳为法,用甘草泻心汤加味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
复发性口腔溃疡现代医学又称复发性阿弗他溃疡,患病率口腔黏膜疾病之首,疼痛剧烈,具有复发性、周期性、自限性特点,目前治疗方法多种,但没有非常肯定的疗效[4]。复发性口疮溃疡属中医“口疮、口糜”的范畴。关于此病的病机古代文献有多处记载,《素问·气厥论》中有:“膀胱移热于小肠,膈肠不便,上为口糜”的说法,认为本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肝热、心火、脾湿中阻和肾阴不足,使热毒内攻,脏腑受损,湿热久停,薰蒸气血,从而致肉腐失养,形成口腔溃疡。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病变部位在口腔,中医上讲“脾开窍于口”,脾脏喜燥恶湿,脾虚则易受湿困。因其具有反复发作,故临床多表现为虚实夹杂的证候,《丹溪心法·口齿》篇也曾指出:“口疮服凉药不愈者,因中焦土虚,且不能食,相火冲上无制。”故治疗应攻补兼施,寒热并用。对于口疮的治疗,最早可见于《金匮要略》:“蚀于上部则声喝,甘草泻心汤主之。”甘草泻心汤见于《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158条:“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甘草泻心汤主之。亦见于《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第10条:“狐惑之为病……甘草泻心汤主之[5]。”此方是治疗伤寒误治而致脾胃不和、寒热错杂之痞证的代表方之一。甘草泻心汤由甘草、半夏、黄芩、黄连、干姜、人参、大枣组成,方中黄芩、黄连苦降以除热;干姜、半夏辛温开结以散其寒,甘草、大枣益气兼以补虚。清代医家吴谦的《医宗金鉴》中有云:“方以甘草命名者,取和缓之意。用甘草、大枣之甘温,补中缓急,治痞之益甚;半夏之辛,破客逆之上从;芩、连泻阳陷之痞热,干姜散阴凝之痞寒。缓急破逆,泻痞寒热,备乎其治矣。”诸药合用,辛开苦降,寒热并用,甘温升补,对复发性口腔溃疡能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黄煌教授在《经方的魅力》中也指出甘草泻心汤可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是黏膜修复剂。王金凤等运用甘草泻心汤化裁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比较治疗组与对照组平均溃疡期、疼痛指数及半年复发情况等,表明甘草泻心汤化裁方可促进患者局部溃疡愈合,减轻疼痛,并可明显减少口腔溃疡的复发[6]。胡翊健副教授对于反复发作的顽固性口腔溃疡,多以甘草泻心汤加味治疗,疗效确切。
2.1 病案举例 张某,男,26岁,2017年4月20日初诊。诉6年前,出现口角生疮,先后至多家医院就诊,经予金霉素眼膏、锡类散、冰硼散及中药,效果均不显著,诊时见:形体偏胖,神情忧郁,口周多出溃疡,流水,瘙痒疼痛,咽喉肿痛,纳呆,心烦喜呕,睡眠不安,舌体偏胖,苔黄润,小便短涩,大便黏腻不畅,脉沉缓,综合四诊胡翊健副教授辨证为寒热错杂证,予甘草泻心汤加蛇床子、白廯皮。方药如下:半夏10 g、黄芩 10 g、党参 10 g、黄连 10 g、半夏 12 g、生甘草15 g、干姜6 g、大枣5枚,共5剂。嘱其少食油腻之品。2017年4月25日复诊,患者诉服用上药口疮大为好转,溃疡处开始结痂,不痒痛,饮食量增,小便色变淡,大便顺畅,唯有睡眠仍欠佳,效不更方,在上方基础上加知母8 g、生地黄10 g,共5剂。嘱其清淡饮食。2017年5月1日,患者复诊,诉诸症消失,予香砂六君子丸间断服用,少食油腻之品。
2.2 讨论 该患者形体偏胖,体内湿邪偏重,情志不畅,湿邪郁久化热,“口周溃疡痒痛流水,咽喉肿痛,大便黏腻”结合“脉沉缓”综合分析后胡老师辨证为寒热错杂证。其与《金匮要略》中狐惑病病机一致,故其甘草泻心汤治疗,李彣在《金匮要略·广注》中有注解:“狐惑是伤寒遗热所致,故乃状如伤寒也……喉、肛与前阴皆关窍所通,津液滋润之处……不欲饮食,恶闻食臭,是内热而胃气不和,故有目不得闭,卧起不安之证”表明甘草泻心汤适合应用于胃虚夹邪之证”,遂方用姜、半之辛热以排阴气;用芩、连之苦寒以降阴火;用大枣之甘温以滋屡下所伤之津液;并君甘草者,亦以其病在胃也。清代医家吴谦的《医宗金鉴》中有云:“方以甘草命名者,取和缓之意。用甘草、大枣之甘温,补中缓急,治痞之益甚;半夏之辛,破客逆之上从;芩、连泻阳陷之痞热,干姜散阴凝之痞寒。缓急破逆,泻痞寒热,备乎其治矣[5]。”方以生甘草为君,配苦寒之黄连、黄芩清热解毒,干姜、半夏辛温燥湿,党参、大枣和胃,加用蛇床子、白廯皮燥湿止痒。胡老师经常教育我们“治病求本”,该患者之症本于湿为患,恐其复发,故续用香砂六君子丸益气健脾和胃,祛除内湿。
3 以育阴清热利水为法,方用猪苓汤治疗肾盂肾炎发热
肾盂肾炎多为逆行性感染引起的肾盂及肾实质炎症,临床表现为伴有发热的全身症状,甚至有可能引起肾实质损害,是泌尿系统感染中最重要的感染病之一[7]。猪苓汤该方首见于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分别见于“辨阳明病脉证并治——阳明病经证”第223、224条和“辨少阴病脉证并治——阴虚热化证”第319条。《伤寒论》第223条言:“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8]。”以其主治阳明病用下法误治之后出现的变证,即阴津耗伤,邪热入于下焦,水热互结之证,以猪苓汤养阴清热利水。《伤寒论》第319条云:“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主治少阴热化、阴虚水热互结之证,亦以猪苓汤养阴清热利水[9]。临证中,无论何种肾脏疾病,只要抓住水热互结兼有阴伤的病机关键,皆可用此方加减治疗。胡翊健副教授活用经方以猪苓汤为基础,以育阴清热利水为法,巧治肾盂肾炎发热。
3.1 病案举例 李某,女,56岁,2017年3月17日,初诊。诉3年前由于左下肢长一疱疹,疼痛难忍,至当地诊所就诊,拟诊为“病毒性疱疹”,予大剂量阿昔洛韦抗病毒,次日,患者出现发热,腰部胀痛难忍,尿液浑浊,双下肢浮肿,后经当地中医院肾病科治疗,症状可缓解,但发热症状仍时有复发。后就诊于胡翊健副主任,诊时症见:腰膝酸软,发热,心烦,偶有咳嗽,口干多饮,饮不解渴,小便量少,双下肢稍肿,尿液浑浊,舌暗红,苔薄黄,脉浮。胡翊健副主任予猪苓汤加五味子、丹参,方药如下:猪苓20 g、茯苓12 g、泽泻 15 g、滑石 15 g、阿胶 12 g、五味子 10 g、丹参10 g。服用上方5剂后诸症大为好转,复诊3次,而诊患者诉仍有下肢肿胀,守上方加玉米须30 g,共7剂。三诊,患者诉尿液稍混浊,肿胀消退,上方改泽泻为8 g,玉米须为15 g,加萆薢15 g,7剂。该患者前后用药19剂,症状彻底痊愈,后随访3个月未见复发。
3.2 讨论 该患者热盛伤津,故口渴多饮。体内素有阴亏,故饮不解渴。膀胱气化不利水液停聚,故小便不利,下肢稍肿。综合分析可知该患者素有阴亏,体内有热,下焦由水,水与热结。其病机特征是阴虚水热互结,且以少阴阴虚为关键[10]。由此病机逆象反思,可得出,该患者脉浮发热,并非病邪在表,而是里热郁蒸于皮毛所致,故不用解表之法。因水与热结,膀胱气化不利,则渴欲饮水,阴不解渴,小便不利,尿液浑浊,阴虚有热,热扰心神故心烦。水性变动不居,水气上逆射肺,肺气不利则咳。究其病机皆为下焦水热互结兼有阴伤,故予猪苓汤加五味子、丹参。诸药相伍,有攻有补,利水而不伤阴,滋阴而不碍气化,寓清热于利水之中,使水湿去,邪热清,阴津复而发热消,从而达到淡渗利湿,兼顾清热育阴的目的[6]。方用猪苓汤加五味子、丹参,以猪苓、茯苓、泽泻、滑石渗利清热,阿胶、五味子、丹参益阴润燥,诸药合用,使水气去,邪热清,阴液复。二诊该患者下肢仍肿,故加玉米须30 g,利水消肿。三诊,患者水肿消退,尿液稍混浊,故减轻利水药剂量,加萆薢分利清浊。
4 体会
中医治病讲求审因论治,正如《金匮要略》所云:“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余皆仿此[11]。”经云:“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徐灵胎有云:“盖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此从流溯源之法,病无遁形矣。”如果能做到辨病论治,辨证论治,辨方论治,便能扩大方剂的应用范围,且可以以不变应万变,融会贯通,这应是中医临床追求的目标[5]。
[1]王洪图.内经讲义·素问·痹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194
[2]李团网.浅谈圣愈汤治疗气血虚弱型痛经[J].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杂志(电子版),2016,4(1):176-177
[3]赵菊花,祝彼得.圣愈汤的临床应用和实验研究新进展[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12(12):208-210
[4]李思敏,包洁,汪琴静,等.甘草泻心汤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研究综述[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39(8):639-642
[5]王程燕,陈赐慧,邢凤玲,等.甘草泻心汤方证浅析[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39(11):801-804
[6]王金凤,刘英.甘草泻心汤化裁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30例临床研究[J].江苏中药,2013,45(4):29-30
[7]王沙燕,戴勇.肾盂肾炎发病学的研究新进展[J].国外医学·泌尿系统分册,2000,20(3):123-124
[8]王庆国.伤寒论选读[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118-119,186
[9]游俊梅,廖成荣,路金华.猪苓汤临证运用发微[J].河南中医,2016,36(10):1694-1696
[10]陈明.刘渡舟运用猪苓汤的经验[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24(1):41-42
[11]范永升,姜德友.金匮要略[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183
R242
B
10.13638/j.issn.1671-4040.2017.10.075
2017-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