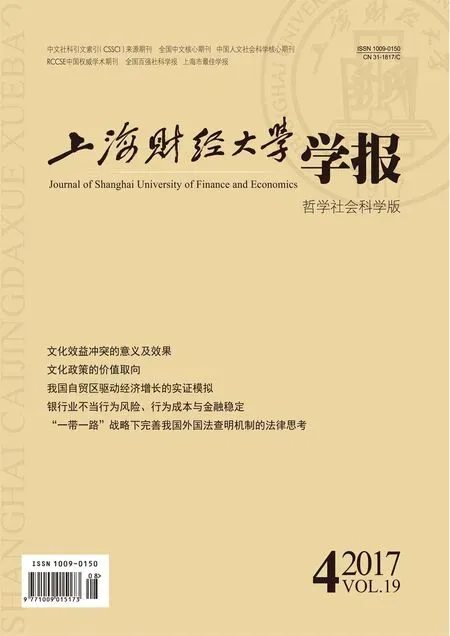文化政策的价值取向
——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到文化经济
闻 媛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 200240)
文化政策的价值取向
——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到文化经济
闻 媛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 200240)
英国工党政府在20世纪末提出的“创意产业”概念迅速取代了传统的“文化产业”概念,并成为许多国家的政策术语,随之而来的政策取向也由传统的美学价值、社会价值转为经济价值和市场价值。这种从国家话语向市场思维的政策演变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掩盖甚至隐瞒了经济中的文化意义,阻碍了对文化本身的考察与关注。文化问题不是经济和市场所能全部解释的,文化价值也是难以被化解为经济价值的。在中国,文化产业的实践远远超前于学术理论的建构。文章提出系统整体观的“文化经济”概念,开辟了一种渗透、融合、开放、共识的交往契机,以价值取向取代权力导向和利益导向,呈现出文化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昭示了文化价值的回归。
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经济;文化政策;价值取向
一、前 言
在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政策系统中,“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和“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y)”等概念被广泛而频繁地使用,它们有大体相同的外延,但意义内涵并不一致。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两股力量,即文化与经济的不同特性、效果及相互之间的张力。作为政策话语,不同的概念对应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行动方案,并以不同的政策意向和规则而发挥指导和引领的作用。本文以英、澳等国家为主的文化政策脉络来梳理这些意义相关的概念之间的交替演进历程,希望藉此厘清不同话语结构下的政策意图以及文化政策的价值取向。
英国学者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曾经将文化政策话语分为三种: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和市民交流话语。①[英]吉姆•麦圭根:《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7页。在国家话语里,国家被视为文化政策里的关键动因,政府对文化艺术进行补贴;市场话语里,市场力量被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而市民交流话语则源于市民社会,它关注交流和文化的民主化。这三种政策话语立场和目的各不相同,但相互渗透,并相互竞逐,努力令自身成为文化政策里的主导因素。20世纪7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90年代末英国工党政府对“创意产业”的界定,使文化与经济、艺术与工业这些在18世纪末出现分歧的东西,终于走向和解②[英]贾斯汀•奥康诺:《艺术与创意产业》,王斌、张良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页。,呈现出从“国家话语”向“市场话语”的政策演变方向。
随着市场话语成为文化政策最主要的考量因素,经济逐渐“脱嵌”于文化,市场开始逐步凌驾于文化之上,文化不得不屈从于市场的逻辑。诸多学者对此持悲观的态度,认为过度强调经济价值将会给文化艺术带来悲惨的影响①Pick,J., The Economic Unimportance of the Arts. Journal of Arts Policy and Management, 1989, 3(3): 25-52.;且忽略了其他价值的可贵与重要性。Lesley Sharpe就非常强调艺术的美学价值,他认为,“只有艺术在不被认为应该为任何目的而服务的情况下,它才能以其独特的方式重建失落的和谐②Sharpe,L., Friedrich Schiller: Drama, Thought an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Tom O’Regan(2002)则担忧文化或是社会性的政策目标与价值(如文化多样性或是公平的文化接近权)将会因为产业发展、市场开放、科技进步或是贸易自由的经济正当性而遭遇质疑或是被忽略。③O’Regan, T., Too Much Culture, Too Little Culture: Trend and Issues for Cultural Policy-making.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and Policy, 2002, 102(Feb.):9-24.于是,大卫•索罗斯比(David Throsby)提出评估文化政策的意义应该同时参照经济价值结果和文化价值结果,将文化政策的目标函数解释为寻求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联合最大化,“如果政策的目标函数仅仅包括经济价值,……目标函数是不充分或不全面的④大卫•索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王志标、张峥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在中国,文化产业的实践远远超前于学术理论的建构。实务界与学术界的大多数人士对“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经济”等相关概念的起源与政策含义并不十分关注,相关的研究与讨论更多在于追逐政策热点,积极给予政治上的支持,概念意义对政策制定的指导作用以及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则往往被忽视。这自然是因为中国的政策研究长期缺乏批判性维度所带来的后遗症。《学术探索》在2009年发表过一组文章,部分优秀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些相关概念曾进行过一番探索和讨论,或是梳理概念选择背后的政策意图⑤章建刚:《文化产业,抑或创意产业?——概念与政策趋向的差异》,《学术探索》2009年第5期。;或是对相关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含义进行分析⑥单世联、刘述良:《政府资助艺术:支持与反对》,《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除此,对文化政策价值取向的更为深入的讨论和研究相对比较匮乏。在经济话语甚嚣尘上的今日之中国,着眼于产业发展实践固然有其务实的一面,但因为对概念内涵及用语过程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在实践过程中难免造成一些混乱⑦胡惠林:《对“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作为政策性概念的一些思考》,《学术探索》2009年第5期。,并存在自说自话的可能。从很多地方政府选择使用“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概念仅仅只是为了提高产业增加值的统计数据就可见一斑⑧张胜冰:《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边界及中国的运作模式》,《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
本文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英国创意产业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明确“创意产业”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促成英国财政部通过产业支持计划所采取的务实变通之举,与英国要建立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的大战略相吻合。第二部分承接第一部分,指出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推广与普及,迎合了后现代社会工具主义文化观流行的趋势。可是,当经济价值俨然成为文化政策之所以赢得公共政策支持的依据时,文化却沦为经济的附庸,失去其自身应有的情感结构和“品性”。最后,通过对代表市场话语的创意产业政策进行反思,文章从整体系统观的视角阐释了“文化经济”的概念内涵,呈现出全球文化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即向市民或交流话语的价值回归,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预测性。而中国的“文化+”实践则在一定程度上清晰诠释了市民交流话语的深刻内涵,即表达、交融、开放、共识。
二、概念转换:从“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
自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启蒙辩证法》中批判性地提出“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概念以来,“文化工业”就成为文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争论性议题。然而,在政策领域中,相关概念的使用却有另一种逻辑。就现在看到的材料来看,英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早在政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即复数的文化工业)概念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英国以“文化产业”一词指称一些借助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商业形式,包括广播、电视、电影、广告、图书等,并制定了相关的产业政策,保护电影产业、推动出版自由、监管广播事业等,目的是推动相关部门能够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文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政策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并不包括艺术,政府除了资助艺术外,并不积极干预艺术。
作为政策概念的“创意产业”始于1994年澳大利亚政府《创新型国家》(Creative Nation)的声明。这一声明提出一项将艺术与新的通信技术相结合的文化政策。4年后,英国工党政府接过这一概念,在《创意产业路径文件》(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s)中全面提出了一项推进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政策并在实施中取得显著成效。由于英国的地位和影响,更由于全球文化—经济融合发展的内在趋势,使得这一概念迅速向全球扩散,并成为考察当代西方国家文化政策的新起点。
上述由“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与英国政策的调整和政党轮替直接相关。在1979年至1997年的19年中,英国工党连续四次在大选中失利。受此刺激,工党开始反思自己的传统定位及政治立场,并据此设计改革方案。在此背景下,托尼•布莱尔凭借“新工党、新英国”(Britain will be better with new Labor)的竞选纲领击败保守党而赢得选民,工党取得执政地位。成为新首相后,布莱尔着意修正传统英国古板、严肃、保守、死气沉沉的形象,重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社会矛盾激化而受到破坏的社会秩序,试图缔造充满活力而又有序的新英国。这一政策改革及其大刀阔斧的行动措施,被称为“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运动。其核心是倡导活力和创意思考,依靠直觉尝试创新,用无限的创意和想象展示一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英国。作为这一运动的一个方面,布莱尔改组内阁,将主管文化等相关领域的“国家遗产部”更名为“文化传媒体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Media and Sport,DCMS),以体现对代表年轻、创造、时尚以及“酷”的娱乐业的关注。①Garnham, N., From Cultural to Creative Industries:An analysis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pproach to arts and media policy mak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05, 11(1):15-29.1998年,文化传媒体育部内设“创意产业工作组”(Creative Industries Task Force,CITF)发布《创意产业路径文件》,宣布将采取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这份文件以就业人数、成长潜力和创新性为标准,将创意产业定义为: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与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并增加就业潜力的活动。根据这个定义,创意产业包括13个产业部门:广告、建筑、艺术品与古董、手工艺、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与录像、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与计算机服务、电视与广播。②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s, 1998.这份兼容并蓄的清单不仅包括传统艺术、文化遗产部门,也包括广播、电视、电影、音乐和出版等“文化产业”,还加入了一些创新依赖型部门。正如这份行业清单敏锐地捕捉到的文化、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动态融合一样,“创意产业”也是一个融合性、综合性的政策概念,它既显示了一种正在到来的、崭新的经济秩序的蓝图,体现了政府追求这一新秩序的明确意图和切实努力,也内含着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创意产业政策的历史脉络与追求目标。
首先,新政策放弃了“文化产业”概念,力图回避这一概念所提示的“产业”对“艺术”的伤害。这一点,是基于对20世纪80年代英国商业化政策的伤痛记忆和文化反思。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早就揭发过艺术工业化、商业化的灾难性后果,而在20世纪末的英国,“文化产业”一词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艺术”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艺术发展所面临的窘境。1979年,保守党人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10号后,立即抛弃凯恩斯主义,实施自由市场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氛围下,政府一改此前工党政府的左翼自由主义政策(强调艺术对社会的启蒙教化作用),反对政府对文化艺术的介入,主张艺术商品化和市场化。根据这种以货币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文化政策,政府大幅削减对艺术机构的资助经费,把艺术推向市场,归入服务型经济的范畴。当然,以市场和消费为取向确实有刺激文化生产、满足公众需要的一面,公众因此拥有更为多样、更为丰富的艺术欣赏途径。但是,正如霍克海默、阿多诺所说,以市场为导向的艺术标准化、模式化必然取消艺术对生活和世界的独特理解,钝化消费者的反思能力和批判意识。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判断。有鉴于此,在货币主义统治了近十年的1988年,伦敦戈德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 in London)召开了关于英国戏剧危机的会议。会议宣言强调,自由的市场经济和私人赞助无力为艺术发展提供所需的各种必要条件,以至于艺术天然所具有的多种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①Lavender, A., Theatre in Crisis: Conference Report, December 1988. New Theatre Quarterly, 1989, 5(19):210-216.显然,如果表演艺术的故事情节安排以迎合大众为目标,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音符、每一个神情都接受严格的设计,艺术就完全沦为追求利润的商品而丧失了独创性和精神性。为克服艺术商业化政策所带来的理念上的障碍,布莱尔政府的文化传媒体育部以“创意产业”取代“文化产业”,强调个体的“创意”。此处的“创意”既可被视作传统艺术的精髓,即创作;亦可被视作新兴现代化产业的核心,即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巧妙地缓解了新旧政策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次,新政策凸显广播、电视、电影、广告、图书等商业部门的文化属性,意在以“文化”的名义争取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这些部门的政策支持。在保守党政府时代,广播、电视等商业文化因不属于高雅艺术的范畴,一直被排除在政府对文化事务的补助之外。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工党控制的大伦敦市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GLC)基于“民主化文化产业”的理由,曾经对这类商业性产业的文化性给予大力肯定和强调,并将其纳入政策考量。这是地方文化产业战略的第一步。20世纪80年代英国其他地方政府也相继追随,增加在文化方面的公共支出,并增设专门的机构和政策制定者,通过对文化艺术的综合运用以丰富当地的经济基础,以期获得更大的社会凝聚力推动旧城改造和都市复兴。尽管其时撒切尔政府的中央集权化倾向非常明显,②Crouch, C. , Marquand, D. (Eds. ), The New Centr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9.但地方文化政策是这一趋势中的例外。英国艺术委员会对英格兰地区艺术协会的投入比例持续增加,从1983–1984年的14.3%增加到1988–1989年的23.5%。③Bianchini , F., Parkinson, M., Cultural Policy and Urban Regeneration : The West European Experie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285-286.作为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回应,文化政策已成为其时英国城市经济复苏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8年,时任英国艺术部长的理查德•卢斯(Richard Luce)发起了一项涉及面更广的改革措施,将许多直接面向艺术委员会的资金资助转移到地区艺术委员会。于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地方政府在文化上的投入从1976–1977年的2万英镑增加到十年后的100多万英镑。④Feist, A. , Hutchison, R., Cultural Trend in the Eighties. London: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1990: 292.英国第四大城市谢菲尔德市(Sheffield)就是通过文化政策提供大众娱乐、推进音乐产业的发展维持了当地的就业水平,并激发了公共空间的活力。可见,20世纪70–80年代的英国,在中央政府推动艺术“产业化”的同时,地方政府从另一个侧面也努力促进了商业性产业的“文化化”。布莱尔政府在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发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同时,也接受并扩展了此前工党主导的地方政府对商业性文化部门的支持政策,其结果就是将那些商业性文化部门纳入创意产业,使创意产业与文化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新政策回应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知识与创意”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尽可能为创意产业的发展谋取更大的政府支持。早在1983年,英国的《信息产业内阁报告》就将如何迎接信息时代到来的问题置于政府政策的中心,希望有效应对英国制造部门所面临的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国际收支危机。①Cabinet Office, Making A Business of Information, London: HMSO, 1983.“创意产业”在强调知识与文化的同时,通过完全数字化的新经济部门主动与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力的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等相连接,意图通过借助创新理论以及相伴而生的“创造力”等概念在信息时代所居于的重要地位令其自身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在这方面,诸如“文化”、“艺术”等术语则因其传统约束性和封闭性而不足以满足当代需求,这就需要把若干创新性部门纳入创意产业的范围,使之在“创意”的名义下获得政府的支持而发展。必须指出的是,仅仅依靠在“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之间的概念置换,并不是获得政府资金支持的充分条件,因为其时英国财政部要求所有得到拨款的机构或者个人必须表明他们可以达到的预期的经济目标②Garnham , N., From Cultural to Creative Industries:An analysis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e“creative industries”approach to arts and media policy mak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05,11(1):15-29.。所以,将英国社会的整个计算机软件部门纳入创意产业的讨论范围其实也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缘由。毕竟,计算机软件部门的加入为英国创意产业的相关统计数据大大增色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创意产业的增长速度与英国其他行业相比高出一倍以上,其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超出一倍,彰显出创意产业所具有的巨大发展潜力。恰如时任文化传媒体育部部长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所期望的,乐观、靓丽的数据给英国财政部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创意产业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力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③Smith, C., Creative Britai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98.,英国遂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政策性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
综上所述,创意产业取代文化产业,不但与英国工党的执政理念直接相关,也与艺术在当代条件下的命运、广播影视等商业部门的文化特性、与信息化时代创新部门的兴起有关。仅其作为文化政策而言,工党政府的努力是成功的,不但引领了英国创意产业的发展,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回应,直接激活了全球各地发展创意产业的热潮。
然而,创意产业政策也有其内在的矛盾。既然创意产业本身能够创造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什么需要政府的支持?如果创意产业不具有创造经济效益的能力,为什么值得政府支持?而更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创意产业政策的价值取向对文化艺术的发展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又将如何影响艺术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三、经济优先:创意产业政策后果
在归属于英国“创意产业”的13个产业部门中,广播、电影、电视等原来就是市场化的“文化产业”,知识、信息等新经济也依然属于经济的范畴,它们不会也没有因为“创意产业”的概念而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只有艺术这一门类,受到创意产业政策的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自古以来就有政府支持艺术发展的传统。这一政策的理念基础是现代自由人文主义观念,即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政治或经济领域,还具有丰富社会生活、教化公民的功能。因此,艺术同教育、健康和社会安全一样,是公民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根据自由平等的道德理念,所有的公民都拥有广泛地接触文明社会的文化产品的权利,于是,政策支持和鼓励的对象包括艺术创作与鉴赏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代艺术资助政策被提上西方国家的议事日程。不过,这一政策无论在实际操作还是理论依据层面都遭遇了诸多挑战。
首先,艺术资助政策必须清晰阐明政府资助的艺术范围以及政府资助的具体方式。选择什么,排斥什么,体现了文化艺术场域中的权力博弈。为了确保对卓越艺术的追求和对艺术体验的广泛参与,避免财政资金的流向受到政党意志及政府官员个人偏好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等国,政府对艺术的拨款都是通过一个半独立于政府的机构——艺术委员会来进行的。政府提供对艺术支持的资金总额,而将资助对象的选择与确定交给这个委员会来完成。各国的艺术委员会通常都依赖专业研究所拟定的评估体系制定拨款决策,力图使公共资金的使用更见成效。不过,这一制度设计并不能确保这一良好愿望能够真正落实。
原因是多方面的。艺术具有独创性和不可复制性,使用任何一个简单的标准,从单一的维度对其进行价值判断都是不可能的,以至于对艺术好坏雅俗的判定是一个延绵数世纪而仍未有结果的论题。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各国艺术委员会的抉择也不可能仅仅只是考虑艺术的卓越性。作为半独立于政府的机构,艺术委员会的主席是根据行政和政治需要任命的,用于资助艺术的资金也是来自政府,要真正避免政府干预、保证艺术创作的自由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艺术委员会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屈从于政府的政治取向和政策调整的变化,对艺术方针和实践进行直接、间接的控制,如希望资助对象能够或有助于培养民众某种价值观和信仰等。1989年美国国会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与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NEA)的对抗即反映了社会公众、国会审美与艺术界的专业审美标准之间的冲突。①1989年,由NEA资助的艺术家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在《完美时刻》(The Perfect Moment)展览中展出与同性恋有关的作品。该展览触怒了参议员赫尔姆斯,导致参议院投票表决制止NEA支持“淫秽或粗鄙”的作品。这一冲突的结果是,1990年美国国会对国家艺术基金会提出了一项要求:拨款决定必须考虑“庄重得体的一般标准,尊重美国公众的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否则,拨款资金将被切断。国会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艺术的创新与自由表达。也就是说,政府的以挽救艺术、防止艺术消亡为目标的支持政策也可能扼杀艺术。苏联艺术家亚历山大•梅拉米德(Alexander Melamid)曾经说过,“政府始终是传统的捍卫者,而艺术却是创新的守护神。政府与艺术家之间不存在任何摩擦是不正常的”②[美]詹姆斯•海尔布伦、查尔斯•M. 格雷:《艺术文化经济学》,詹正茂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7 页。。事实上,在今天这个成规不断被打破、价值观不断被翻新再造的世界里,任何一个国家的艺术委员会都面临着社会与文化关系的不断发展变迁所引发的艺术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使政府对艺术支持的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弊端频出,屡遭诟病。
其次,政府究竟应不应该资助艺术,对此一直存有争议。尤其是在一个崇尚自由市场,认为政府对经济、文化干预应该最小化的社会氛围中,政府对艺术的支持更是被严重质疑。本来,有关公共资金如何选择支持对象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所有这方面的争议都是在拥护政府支持艺术的前提下展开的。但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要求文化民主的平民主义者则从根本上反对政府支持高雅艺术所体现的文化精英主义的倾向。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文化的表达是多元的,既有高雅、贵族式的形式,也有日常生活化、大众化的形式。他们主张艺术与大众文化融合,成为社会的总体生活方式,相信“艺术被锁进宫廷和研究院”或是“艺术家与广泛而多样的公众之间失去交流”是非常危险的。①Williams, R., Politics of Modern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Inc, 1989: 148.同时,他们坚持认为,政府不应忽视市场能够提供并满足大多数人的文化需求的事实,所以,使艺术与市场关系断绝的尝试是失败的。在大伦敦市议会1983年意见书中,英国媒体理论家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明确表示,“过去传统的文化政策将市场排除在外,但是市场反映了大部分民众的文化需求。如果政府漠视这主流文化,就无法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更会错失主流文化赋予决策者的挑战和良机。”②Garnham, N.,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1990: 155.
尽管有关政府是否应该资助艺术的争论是一个基于信念与选择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问题,理性分析与论辩未必能够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然而,作为对反精英主义思潮的回应,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化确实呈现出大众化、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且日益强劲。作为对此一趋势的回应,创意产业政策把“艺术”也并入创意产业,实际上是看重艺术的经济效果,也就是把文化经济化。其结果是,工党的创意产业政策越来越接近甚至重复了它曾经反对的保守党的艺术商业化的政策倾向。差别仅仅在于,保守党政府是减少对艺术的财政支持,放任艺术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而工党政府则积极推动了艺术的经济化。
这是创意产业政策的自我反讽,其根源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兴起。随着对大众主体性的重视,文化的控制权必定从政府转向市场。这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有所体现,转型中的东欧与中欧国家的历史更是显示出国家对文化控制权的大力削减,如撤销管制规定、文化机构的民营化等。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以加纳姆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关注的重点是发展一种以受过良好教育的消费者的需求为基础的民主文化政策,而非经济发展战略,但自由市场对文化影响力的增强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文化在经济方面的考量显得愈益重要。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创意产业政策用“创意产业”这样一个带有修辞色彩的术语取代“文化产业”,把新经济下的信息产业部门纳入讨论范围,强调其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前景。
政策术语的改变不仅仅只是文字上的调整,更是反映了执政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文化政策价值取向的根本转变。在传统的“文化产业”概念中,虽然“产业”二字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运用经济思维来思考文化和艺术领域中的问题,但“文化产业”概念的使用依然偏向于强调产业的文化属性,集中于以美学价值和精神内涵来思考产业的定位,具有一定的民族情怀与国家认同感。即使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人对文化工业持批评的态度,也是出于对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忧虑,而非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量,所侧重的其实是基于“工业”表征而展示的新的“文化”内涵。“创意产业”显然与之不同。英国学者马克•班克斯(Mark Banks)认为,工党政府构建创意产业,以现成的技术和学科手段来描述、测量、评估并识别关键的主体、关系和过程,这一举措本身就是将文化生产中的非经济动机边缘化、将文化生产活动收编进市场经济核心的一种手段。③Banks, M.,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于是,在创意产业的语境下,文化与经济的边界已经模糊,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相连,艺术创作与商业机制相连,所有具有生产文化符号意义的产品都被视为文化的展示,而此种展示只是为了实现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商业价值。进入21世纪,全球范围内有大量的政府机关、文化组织、咨询机构等都将创意产业发展战略置于本国或地方文化与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心。或许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一概念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社会与政策脉络,但都暗含有一定的经济目标,即寄希望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与更广阔的“知识经济”相联。创意产业不仅是政策支持的对象,更成为经济增长的推手,生机勃勃的数字变化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所以,借助于“创意产业”概念,政府的文化政策与经济政策开始了某种程度的整合。创意产业对政府资金的要求不再是建立在对艺术品质和对文化价值共同关切的基础上,而是源自市场与产业的动机,强调经济价值的创造。诚如澳大利亚在《创新型国家》中所指出的,“文化政策就是经济政策,文化创造财富……文化增加价值,并对创新、营销与设计都具有不可或缺的贡献。除了文化本身是一个有价值的输出,对于其他商品的输出也有着不可或缺的附加价值。可以说,文化对于我们的经济成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①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Arts, Creative Nation: Commonwealth Cultural Policy, Australia: Canberra, 1994: 7.在这里,民族文化人文理想主义与对投资创意产业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精明考量结合起来。所以,加纳姆明确指出,“创意产业政策的实质就是文化政策和信息社会相关政策的混合”②Garnham , N., From Cultural to Creative Industries:An analysis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e“creative industries”approach to arts and media policy mak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05, 11(1):15-29.。于是,文化政策的主题由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传统的政府对艺术的无偿资助转化为对文化活动或文化产品的投资。文化创意作为经济资源步入政策制定的中心。身为投资者,政府所期望的投资回报既不是公众获得广泛的渠道接触艺术,也不是文化产品品质的日益提高,而是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形势下,创意产业能够带来财富增长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此,人文价值与商业利益、精神内涵与实用主义之间建立起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在文化充当经济增长的助推器的同时,文化政策中“文化”的涵义逐渐被消解和稀释。这是一个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政策转向,反映了社会发展进程中对文化功能的认识从本质主义观念向工具主义观念转变的趋势。即使是在传统的国家干预的政策话语领域内,其运作形式依然深受市场理性的影响。
作为文化政策与经济政策的结合,创意产业政策帮助政府成功摆脱了传统的以非商业化的艺术为中心的文化政策,曾经围绕艺术资助政策所引发的各种争议也因为资助政策本身变得不那么重要而不再引人关注。然而,对问题的回避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失或得到解决,反而引发了新的矛盾和冲突。创意产业因其巨大的影响力将几乎所有的文化艺术都卷入了市场体制。一方面,对于艺术创作者或机构而言,如果将自身视为纯粹的创意缔造者因难以商业化而希望得到政府支持,则将因为政府资助规模的缩减令自身的发展空间日趋狭小;另一方面,既然所有能够商业化的部门已全部交由市场,屈从于经济利益的优先权,结果将使获取政府资助的艺术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
四、价值回归:从“创意产业”到“文化经济”
“文化产业”作为政策术语日渐式微,“创意产业”在全球的蓬勃兴起深刻地反映了在社会历史变迁的不同阶段对文化与经济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态度和观念的演变,以及与之相关的政策价值取向的变化。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过程中,某些议题必定且已经引起关注。首先,创意产业是否足够强大到能够真正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全球社会现象与问题能否被简化为仅仅通过市场话语与价格机制来解决?
大量研究结果提醒人们,必须正视文化与创意产业的局限性。它们或许并不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捷径,也不是抵御经济衰退或解决就业问题的万能药。诚然,文化部门的从业人员确实有快速增长,但颇为讽刺的是,4/5的收入和工作量由少于1/5的专业人员所占有和承担;相对于其他领域的个体,文化部门中具备资质的个体更为频繁地周转于短期就业、失业和副业之间,这是因为在这一领域中,稳定的工作机会基本上都提供给了行政和技术雇员,主要是艺术和文化的教学、组织、干预、保存和传播等。①[法]皮埃尔-米歇尔•门格:《欧洲的文化政策——从国家视角到城市视角》,欣文译,《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4–9页。另外,欧洲委员会曾对29个文化城市进行评估,结果表明,通过政府资助文化以复兴没落的城市并推动其经济增长的努力已经失败。以格拉斯哥(Glasgow)为例,它在1990年被提名为“欧洲文化城市”,但是在得到这个赞誉以后的许多年里经济并没有持续增长。②Miller, T., From Creative to Cultural Industries: Not all industries are cultural, and no industries are creative. Cultural Studies, 2009, 23(1):88-99.不过,格拉斯哥的艺术组织的声誉却确实得到极大提升,该城市在国内和国际上也一改其曾经以城市衰败、“剃头帮”街头暴力而著称的形象。③Bianchini, F., Parkinson, M., Cultural Policy and Urban Regeneration : the West European Experie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285-286.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欧洲城市复兴的许多案例分析都显示,相比较在发展旅游业、吸引内向经济投资、积极创建城市形象以及增强城市的竞争力等方面,文化政策在形成就业与创造财富方面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④Bianchini, F., Parkinson, M., Cultural Policy and Urban Regeneration : the West European Experienc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285-286.经济发展中,文化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象征性影响,而并非可交付与可计量的成果,正如澳大利亚学者西蒙•鲁德豪斯(Simon Roodhouse)所言,文化和创意产业应该是“通过分配而不是通过自身的生产来获取收益”⑤Roodhouse, S., Have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 Role to Play in Regional Regeneration and A Nation’s Wealth? In: Proceedings AIMAC2001: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and Cultural Management, Brisbane: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1, June: 285-341.。
文化艺术有经济效益,但这个效益是有限的。这一事实提示了考察文化与经济关系的新思路。这就是随着新经济的蓬勃发展,文化艺术通过向物质领域渗透而影响和改造了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英国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和西莉亚•卢瑞(Celia Lury)在《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中指出,“截至2002年,文化产品已经以信息、通信方式、品牌产品、金融服务、媒体产品、交通、休闲服务等形式遍布各处。文化产品不再是稀有物,而是横行天下。”⑥[英]斯科特•拉什、西莉亚•卢瑞:《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要新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事实确实如此。曾经专属于艺术的品质和特征如创造性、差异性、符号性、美感性等,如今已经播散到所有产品的生产之中,使得这些产品的象征价值远高于其实用价值;商品的购买与消费行为的经济性也被不断弥散的文化影像(通过广告、商品陈列与市场营销)所调和、冲淡;消费者获取和使用的产品在满足其需要(营养、居住、行动、娱乐等)的同时,依据其特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了意义,消费行为逐渐成为某种文化宣言和个性化表达的方式;同时,随着通讯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各种文化体验壁垒的降低令相当数量的人群能够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潜能,生产组织形式更为灵活多样,产业的文化品格因其重组了生产与销售系统以及围绕这些系统的社会生活而得以彰显。全新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方式正在改变人们的艺术和文化观念,并同时影响了人们“认识世界、定位自身、确定权利以及与他人构建有效的生产关系的方式”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意经济报告2013(特别版)》(中文版),意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导言,第2页。。这并非仅仅局限于某些行业或产业,而是渗透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里,文化已经从审美意义上的文化定义转变为一种人类学传统的整体性概念,包括人类生活方式的全部内容,涵盖了对文化更广泛且更深刻的理解。于是,文化不再仅仅是一种先验的人格化冲动的表达,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扎根于社会行动的时空领域,成为社会内在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基于此,丹尼尔•马托(Daniel Mato)断言,“所有产业都是文化的”。①Mato, D., All Industries are Cultural: A critique of the idea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new possibilities for research. Cultural Studies, 2009, 23(1):70-87.这既是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也体现了消费观念的转变,更反映出文化向经济领域扩张与渗透的力量日益增强。相对于继续将讨论范围局限在狭小的视听、娱乐及其他被划入“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的产业门类中,扩大“文化”的内涵或许更有意义,更能反映当今时代发展的特色与主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04年,加拿大学者D. 保罗•谢弗(D.Paul Schafer)指出,我们正在从“经济时代”转向“文化时代”。②[加拿大]D.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高广卿、陈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创意产业政策强调以经济产出来考察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掩盖甚至隐瞒了经济中的文化意义,阻碍了对文化本身的考察与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创意经济报告2013(特别版)》就针对这一现象指出,“市场驱动的方法仅能片面地反映创意和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不能解决除经济分析以外的诸多道德和政治问题”。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意经济报告2013(特别版)》(中文版),意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导言,第1页。很多常见但或许还没有在实证研究中引起关注的行业案例、事件或“创意”活动,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具体的事例,证明经济并不能凌驾于文化之上。④[澳] Gibson Chris,[新] Lily Kong:《文化经济:一种批判性的述评》,聂启平译,见张晓明,迈克•金:《创意经济大视野(第1辑)》,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6页。所以说,创意产业政策在政策日程被政府通过之时便令文化沦为其成功的牺牲品。⑤Dimaggio, P., Social Structure, Institutions and Cultural Goods: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Bradford, C., Gary, M. & Wallach, C.,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Policy Perspectives for Individuals, Institutions and Communities. New York: New Press/ 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e, 2000: 38-62.为矫正文化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偏差,英国文化传媒体育部曾于2007年修正过“创意产业”的定义,将核心创意领域定义为:“商业输出具有较高的表现价值及产权保护诉求”(Commercial outputs possess a high degree of expressive value and invoke copyright protection)。⑥DCMS, Staying ahea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UK’s Creative Industries, London: The Work Foundation, 2007.在这一定义中,“表现价值”(expressive value)取代了此前对“创意”的强调。这里的“表现价值”囊括了诸多元素,包括审美价值、社会价值、精神价值、历史价值,以及象征性和真实性价值。文化传媒体育部选择这一概念意在利用创意的文化内涵来缓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实际上,经济原本就根植于文化之中,文化与经济之间本不应存在矛盾与冲突。只是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对物质财富的欲望与追逐使人们将经济置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之上,从而放弃了对社会整体全面发展的关注,即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经济体系从社会“脱嵌”。⑦[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如今,随着经济的文化化,经济越来越多地“通过符号、标志以及语篇等文化媒介得以体现”⑧Crang, P., Introduction: Cultural Turns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Lee, R. & Wills, J., Geographies of Economies, London and New York: Arnold, 1997: 3-15.,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在文化、社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或许文化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被经济和社会所形塑,但作为相对自主和自律的精神领域,文化也反过来塑造了产业和经济,并重塑了社会关系和规范。所以,拉什和卢瑞说,“文化无处不在,它仿佛从上层建筑中渗透出来,又渗入并掌控了经济基础,开始对经济和日常生活体验两者进行统治。”①[英]斯科特·拉什、西莉亚·卢瑞:《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要新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WVS)也充分证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②世界价值观调查网站,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jsp。
“创意产业”这个概念因自身的狭隘定义将关注的视角仅仅局限于财富的创造,无法展现社会发展进程的整体性,也不能反映当今社会发展阶段的核心要素和决定性特征,因此,亟须引入新的概念以反映时代发展的特征,凸显当下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力量。作为与“创意产业”相关又相异的概念,“文化经济”伴随着“创意产业”的兴起而逐渐普及。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文化经济”如今都已经成为一个日益通俗的概念。然而在不同的领域,这一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本文倾向于将文化经济视作一种整体的经济现象,强调物质进步中的文化引导因素,反映社会总体经济转型的现实趋势。基于这样的理解,“文化经济”概念肯定了文化的力量正在取代单纯的物质生产和技术进步而日益占据社会发展的主流,不仅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且赋予经济发展以价值意义,引领和规范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这一概念的解读修正了“创意产业”概念对文化的经济功能的过度强调,改变了以文化为手段的经济逻辑,凸显人文精神,强调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表达了以文化和经济的相互作用为中心的观点,揭示了文化认同世界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断增强的共生关系。
目前,全球创意产业政策因其市场化、商业化的价值取向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性审视,并遭遇各种现实问题的考验。为修正经济发展的片面性,文化发展的整体性将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由此形成的“文化经济”概念或许能够更为真切地界定今天的真实世界,反映世界发展的动因以及生产者、消费者、市民和中介机构在文化领域的话语空间里所处的位置,探讨建立不同于精英主义文化价值的公共空间的可能性。实际上,文化的本质在于符号观念或意义的生产与流通,不仅仅与“经济”,更与“表达”及“沟通”有着密切的关联。毕竟,“音乐、歌剧、运动、绘画和舞蹈一直都是推动市民社会发展的传播形式”③Keane, J., Civil Society: Old Images, New Vis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5.,文化活动在人类的自由表达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就有这样的规定:每个公民都有能力通过文化参与来自由地发挥个性与交流思想。④UNESCO, Cultural Rights as Human Rights, Dairs: UNESCO, 1970.将辩论和目标一致作为行为的先导、谋求相互理解的交往行为是世俗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就定义了与经济活动相对的文化活动。在这里,文化超越了纯粹的工具性而成为一种助推社会认同的中介。
面对社会生活形式多样性的增加以及社会经济不平等性的增多,“文化经济”通过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新的理解而赋予文化政策以新的内涵。不同于国家话语和市场话语通过加强控制能力以保证社会运行所具有的工具理性特征,这种反映了交往理性的市民或交流话语开辟了一种开放、平等、真诚的交往契机,以价值取向取代权力和利益导向,昭示了文化价值的回归。新思想和新概念的产生与应用需要政策的推动;而新的观点和议题进入政策视野则有助于拓宽政策的边界,开启政策新的可能性。文化政策必须重构,谋求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发展平衡,争取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个人自尊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社会凝聚力的增进。巴西文化部长同时也是著名音乐家的Gilberto Gil就将文化政策视作“21世纪实现社会解放、全球结合和人类自由的一种工具”。①Gil, G., Politicizing the New Economy, In: H. Anheier and Y.R. Isar (Eds. ). The Cultural Economy. The Cultures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 2,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8: 231.
文化历来是社会整合和个人认同的形式和机制,当代文化又日益与经济、社会融合、共生而改变着经济方式与社会体制,未来文化政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尊重人权、平等和可持续性等基本价值观的基础上开辟出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同时推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令文化成为主导力量引领经济的发展,体现出文化自身的价值内涵。
五、结 语
创意产业政策无疑可以被视为文化政策市场话语的典型代表,产业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被置于创意产业政策的核心。按照约翰•麦克海尔(John McHale)的观点,“如果根据这些从未来结果考虑被认为是过去的经验来做出今天的评判”②McHale, J., The Future of the Future,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69: 3.,那么,只有以文化创意产业能否带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标准对其进行评价才是有意义的。目前所能收集的所有证据都说明,开发创意产业虽然或许能给局部地区的经济带来好处,却无法促进社会包容,扩大社会平等。③陈小申:《创意产业政策中的证据和意识形态》,见张晓明、迈克·金:《创意经济大视野(第1辑)》,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7页。假如经济增长被视作核心,不仅忽略了创意产业自身的文化渴望,忽略了那些与经济需要相悖的艺术和文化领域中的个人和集体的价值,并且可能错过一些广阔的文化和社会目标,亦无法清晰识别对某些经济成功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价值根源。
世界是由许多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部分共同组成的,任何经济体系都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组织。整体系统观的“文化经济”概念意味着文化要素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创新。这一概念着力于挖掘文化的内涵,探寻延展的文化价值;将艺术向公众开放,扩大公共交流的空间;令文化介入市场现实,并引领社会经济生活。中国当前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清晰地诠释了这一概念所反映的市民或交流话语的深刻内涵,即表达、交融、开放、共识。从产品的品质到消费的品位,从创意农业到特色小镇,从故事挖掘到城市品牌,从文化节庆到美学生活空间,文化符号价值、文化经营理念正逐步向其他产业渗透、融合,在经济载体的建设过程中不断促进美学增值和品牌塑造,不仅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体现出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而正是在这种不断的交流和融合中,文化也展现出自身的魅力和价值。
恰当的政策术语对制定方针政策与实际应用有莫大的帮助。④Eisengerg, C., Gerlach R., Handke C. (Eds. ).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2006, Online. Humboldt University Berlin, Edoc-Server.“文化经济”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以对未来文化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研判。它暗示了一种对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理解、叙述和政策资源,通过对这些资源的正确运用,能够应对文化与经济、经济与社会之间一直存在的张力。以“文化经济”作为政策术语的文化政策将采用一种全局化的、平等主义的而不是片面的、偏袒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理解社会,致力于追求文化、社会和经济维度的相互认同,为解决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加有效的框架和途径,使得文化活动、经济活动与所有其他社会活动之间实现平衡、和谐与平等的关系成为可能。
主要参考文献:
[1][英]吉姆•麦圭根. 重新思考文化政策[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6–47.
[2]戴维•索罗斯比. 经济学与文化[M]. 王志标,张峥嵘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61.
[3]胡惠林. 对“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作为政策性概念的一些思考[J]. 学术探索,2009,(5).
[4][英]贾斯汀•奥康诺. 艺术与创意产业[M]. 王斌,张良丛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41.
[5]王四正. “文化认知”命题释义[J]. 齐鲁学刊,2016,(3).
[6]章建刚. 文化产业,抑或创意产业?——概念与政策趋向的差异[J]. 学术探索,2009,(5).
[7]张胜冰. 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边界及中国的运作模式——兼论中国创意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思维[J]. 思想战线,2010,(3).
[8]Pick J. The Economic Unimportance of the Arts[J]. Journal of Arts Policy and Management, 1989, 3(3): 25-52.
[9]Sharpe L. Friedrich Schiller: Drama, Thought and Politic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ultural Policy: From Cultural Industries through Creative Industries to Cultural Economy
Wen Yuan
( School of Media and Desig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
The concept of “creative industries” put forwar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of Labor Party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has quickly replaced traditional concep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has become a policy term in many countries.And ensuing policy orientation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traditional aesthetic value and social value into economic value and market value.This kind of policy evolution from state discourse to market thinking diminishes, covers up or even conceal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 economy, and hinders the investigation and attention to culture itself.All of the cultral issues cannot be explained by the economy and market, and cultural value is also difficult to be reduced to economic value.In China,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s far ahea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theorie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economy” based on the whole system view, opens up a communication opportunity with penetration, integration, opening-up and consensus, replaces power orientation and benefit orientation by value orientation, reflec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in cultural policy, and shows the return of cultural value.
cultural industry;creative industry;cultural economy;cultural policy;value orientation
F062.9
A
1009-0150(2017)04-0015-13
(责任编辑:海 林)
10.16538/j.cnki.jsufe.2017.04.002
2017-04-15
闻 媛(1972-),女,湖北宜昌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