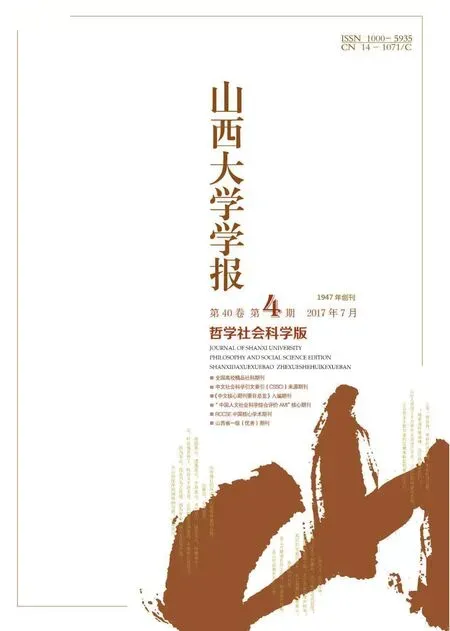论道德虚构的价值向度及其功能
赵国栋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论道德虚构的价值向度及其功能
赵国栋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道德教育是道德概念之后的非先验存在,即道德和道德教育既存在逻辑上的顺序,也存在时间上的顺序。道德和道德教育之间需要一定的“媒介”,进而让本体虚无的道德被人理解和接纳。道德虚构是中西方历史上从未舍弃的道德教育范式,通过将抽象的道德理念形象化、具体化的方式,让人们认同道德的本质,接纳道德话语的重要意义,并且使之成为个体道德实践的学习样本。道德虚构具有道德教育价值向度、功利性价值向度以及趋向生活世界的价值向度。具有帮助个体塑造道德信仰的功能、维护道德教育的合理与合法性功能、促进与构建和谐社会道德秩序的功能。
道德虚构;道德教育;道德典范
道德教育是非先验存在的,产生于道德之后,即道德和道德教育既存在逻辑上的顺序,也存在时间上的顺序。道德是非实体存在的,在我们的现有物理空间无法找到诸如“善”“恶”这样的道德实体,因此,在道德和道德教育之间需要存在一种“媒介”,进而让本体虚无的道德能以某种方式被人所理解和接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对待“媒介”的态度,决定了道德教育的性质。
翻看中国的古代史,追溯至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至圣先贤,抑或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君王们,其中存在的虚构成分比比皆是。西方的古代史,也有着相同的特点,古希腊神话、埃及神话、荷马史诗等,都在用虚构的方式讲述哲理。古代的先哲们就是通过道德虚构这样简单而直观的叙事方式,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将抽象的道德精神具体化、形象化,告诫世人道德的可贵,行善的必要。到了近代(或许更早),西方政治哲学放弃了在国家教育中使用道德虚构,其追求道德卓越和崇高的部分交给了宗教来完成。他们期望通过降低道德目标在人性的低处重新建立起一个有别于德性社会的全新社会,即现代的公民社会体系,使每个现代人在政治社会中都可以获得普遍的正义(道德),将道德事实留给了公共领域,进而完全放弃了道德虚构。即康德所言的:“用形式上的合理性,也即是普遍立法之原则,来检验行为准则之善性而不必要诉诸任何实质内容的考虑。”一切都以人的权利或普遍的公共认可为基准,至少是在公共领域放弃了道德虚构。
中国则选择了与西方不同的做法。基于传统中国道德理念和社会主义道德要求,我们相信:德性生活高于、优越于政治生活。或者说在德性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有着必要的鸿沟,这种鸿沟需要在政治社会中树立一种德性社会的样本,即通过道德虚构的方式来填补这一空白。
一 什么是道德虚构
道德虚构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经历,是人类在意识到道德教育价值之后,对于意义世界的主动建构。归纳其内涵和本质,能够让我们更清晰的理解其在现实道德教育中的特殊意义。
(一)道德虚构是道德理论的支点
虚构是道德理论难以回避的支点、不自觉的选择。审视已经存在的传统规范伦理和现代规范伦理理论,包括康德式的义务论和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伦理传统,它们都虚构了一种终极价值,如康德所说的善良意志、亚氏所说的幸福,其严密的道德理论都是通过围绕这一预设层层推导架构而成。处于道德语境中的我们,似乎天然认可存在某种终极道德价值,犹如大多数人关注什么是幸福,而不去思考是否存在幸福。因为,终极道德价值一旦确立,它是否虚构就显得不再重要。
康德和老子对于本体世界有着相似的认识。老子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德”的方式也许可以领略到“道”的玄妙。康德则认为,我们只能通过虚构的方式实现对世界表象的认知,而怎样的表象呈现,取决于“桥律”(bridge low)。老子言谈的“德”与康德的“桥律”,都是他们解释本体世界的方法。各种道德理论和道德律令,是不同的人依据不同“桥律”对人类应当具备的道德本质的道德虚构。正是历史上这些外在于既定道德理论体系之外的人,通过上述有意识的道德虚构方式,告诉了人们什么是道德、为什么要道德乃至通达于至善的方法。
(二)道德虚构是参与性的实践方法
道德虚构是参与性的实践方法,它希望客体形成“非认知且具有不可妥协性”[1]的道德信条,因而其本质是他律。从主体论的视角来看,掌握话语权力的群体为了维护和延续自己的利益,设计出基本的、代表自己意愿的,诸如善、恶等决定道德观念和道德教育根本方向的纲领性概念。又为了使这些抽象的概念更具权威,虚构出一系列符合其时代思维逻辑的典范形象和事件,进而形成道德教育的逻辑闭环。道德虚构的产物是道德权威设计的形象,再加上权威者对于现实道德虚构形象的标榜和表彰,勾勒出一幅道德从行为和后果都绝对正确的图案,灌输给个体某种道德行为的未来意义,从一定意义上遮蔽了超道德义务和道德理想之间的界限。
道德学习者建立对道德内容或观念保持“是”而非“应该”这样的信条,是保证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基本条件。表面上看来,道德虚构只是言他人之行、诉他人之事,脱离了粗暴与强硬的说教式规定,并且在虚构事实中道德实践者也具有自由的选择机会。然而,其实质是促进道德学习者对道德内容建立“是”的信念,通过刺激被教育者的情感,让个体获得道德情感上的触动,进而使之成为个体自己的道德目标。
从历史上以儒家道德为主要范本的道德虚构来看,个体遵守普遍的道德规则和道德义务,同时需要接受和理解超道德义务是其基本特点。当道德义务与个体权力、自由等基本生存条件相违背、相冲突的时候,个体依旧能够自觉自愿的履行道德虚构倡导的道德义务。个体在被要求履行道德义务的同时,道德行为者自身的价值和地位在道德意义上被否定与贬低,是一种完全的道德义务论范畴的道德。然而,“道德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与强暴”[2],他律性的道德能够牢固确立个体对于某种道德价值认同,但是也束缚了个体道德意志的主体性,让个体失去了自由选择和反思反省的权力。一旦典范形象崩塌,人们对于整个道德价值体系就会发生质疑甚至完全否定。道德虚构形象能够代表时代和社会稳定要求,有着单一的价值导向,并使人们明确道德学习的方向和目标。通过学习者的情感活动来实现道德价值的认可和道德行为的外显。
综上所述,本文的道德虚构是指:为了在公共领域推行美德,接纳道德话语的重要意义,道德权威通过将抽象的道德理念形象化、具体化的方式来塑造美德实践范本的方法。
二 道德虚构的价值向度
道德虚构的价值向度旨在通过其具体的特征和表现,进而澄清道德虚构的性质以及道德虚构的有用性限度,为当代道德教育中的道德虚构摒弃可能的价值偏移和方法失当提供借鉴。在不同的时代,道德虚构的价值向度会有所不同,但是也存在一些根本的、不会随着时代更迭而变化的维度,如道德虚构的道德教育向度、功利性价值向度和趋向生活世界的向度等,反之,则会异化为其他范畴的内容。
(一)道德教育向度
毋庸置疑,道德虚构的首要价值向度在于道德教育。每个合理的心灵都具有自身的特定原则,即存在能够支配其主动性力量活动、且能感受到精神自由的方式,成为人与他人交往的概念性统觉。传统和现代道德的话语主体发生了变化,传统社会使用了宗教图景的道德教化方式,而现代社会宗教图景的世俗化进程,将道德的权利还给了普通民众。
传统的道德虚构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性构建和情感设计,实现了道德行为产生的必然,体现出古典时代道德的“集体意识”性。从道德虚构的教育对象来看,道德虚构需要面向的是除道德观念定义者——即界定道德的含义与内容的主体之外的个体。从道德虚构的德育内容来看,道德虚构的德育内容是以道德典范为承载的道德观念的体现。其根本的价值指向在于对权力的认可和维护,对德政合体国家体制的认可和维护,是严格的服从与从属伦常关系。
随着传统秩序的破裂,现代理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新的脱离宗教式道德教化的强制力量,现代道德虚构逐渐转变。福柯认为现代性的实质仍然是控制与统治,虽然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变化,但这些以主体和知识变化为内容的产物只是一种构造物。韦伯更加直白的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循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3]现代性的“除魅”,实质是消除过去宗教式统治的绝对地位,逐渐地扩大了私人领域的范畴,将本就属于个人的权利重新归还,这个过程中,宗教式的德性推崇价值也被殃及。现代性意义上的道德虚构,集体教化功能日趋式微,那些曾经代表至善、美德和天道等形而上的道德憧憬逐渐弱化。而涉及诸如正义、公平、平等新的道德教育内容,成为道德虚构的主要价值点。
(二)功利性价值向度
在功利性价值向度层面,传统和现代的道德虚构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传统道德虚构的价值指向权力和权力所有者,现代道德虚构则更为关注公共生活和个体德性的获得。
从社群主义的视角而言,传统道德肩负政治社群至善和公共利益(其公共利益带有明显的阶级性)的工具性使命,是在权力统治和生产生活中形成的非制度化协约。因而,传统道德虚构主体利益指向权力或统治者,社会意义在于维系道统的合理性和道德习俗的文化性。如传统中国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古代典范虚构,既体现了儒家德政合一的思想,也体现了道德作为目的性存在的道德理念,无论是上古先王道德典范的本质特征,或者二十四孝中的公共性形象都因为他们具有至高德性,得到统治阶级或者“天”的嘉奖和眷顾,因而,其功利性及阶级性不言而喻。
在现代社会之中,制度和德性的双重建构、完整公民身份确立和认同是各个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政治生活和基本制度中,公民如何在公共事务中运用两种道德的能力(自主与正义感)是维系自由主义国家的关键。”[4]因而,现代社会追求身份与美德融合的基础上,期望公民具有两种能力,一种是作为社会共同体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能力;另外一种则是在精神自由、自在中获得道德的崇高感。
进入现代以后,道德虚构的消极价值正在被逐渐式微,逐步消除了道德功利性价值思维中工具性膨胀和外在承诺的压迫。现代道德虚构出现过两种模式。一种是将道德虚构作为功能的承载者。具体方法是通过降低道德要求,将一些在自己岗位上做出过杰出成绩的个体塑造成道德典范,(此方式曾经在某段历史时间内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但是,这种缺乏基本逻辑性,如果恪守工作职责可以当作道德的至高样本,那么是不是也反映了那个时候人们的道德水平之低下呢?)在此意义上的道德典范成了功能化的符号,道德典范的道德教育功能被弱化,而仅仅代表了各行各业的较高工作标准,职责和道德的意义被混作一体。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及底线道德,抑或追寻崇高道德境界,成为个体道德发展的难题。从这一角度而言,道德虚构需要还原其道德性价值指向。另外一种则是试图将价值观作为道德虚构的承载对象,这也是我党和政府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尝试,即通过道德虚构的方法,将具有社会主义道德信仰和践行统一的个体作为道德典范。不仅弥补上述道德虚构方式在崇高道德价值宣传上的不足,同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具有重大的价值。
(三)趋向生活世界的向度
从发生学角度来说,道德的基础是生活。对于社会个体而言,道德的目的是为了生活的需要,即通过道德,个体能够感受到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命意义的延伸。鲁洁先生认为,道德教育的对象应该是人和人的整体需要,而非抽象意义上的人、政治中的人等片面的人。“道德存在于生活,生活是道德存在的基本形态……把道德理解为生活、生活的方式,澄清了道德的本质。”[5]道德和道德教育无法脱离于人的生活世界,人因为具有道德而更好的生活(从道德的时代性特征而言),好的道德因为关涉人的生活而有意义。
传统道德虚构旨在引导人们“回归”现实生活,并且认可当下合理、形成某种确定性的生活坚守和幸福的自觉意识,虽然其关涉的生活,建构在政治、宗法和习俗等异化理念之下,其虚构对象所展现的思维逻辑体现非科学性、封闭性和局限性的特征,用现代的眼光来看,甚至丧失了生活的本意,但是,这仍然是人们生活的部分。传统道德虚构面向于个体的所有生活,混淆了个体的主体自觉性和义务性界限,形成了道德即无差别利他的逻辑悖论。
现代道德虚构,则趋向于引导人们“建构”可能的道德生活。现代生活建立在科学的认知基础上,科学世界成为生活的重要部分,超越当下、面向未来可能成为了“合目的的生活”。制度化进程促使私人生活世界和公共生活世界相区分,法律等规范性内容取代了部分公共领域的道德教育功能,科学化的社会生活设计逐渐驱逐了与之相左的道德谎言。因而,现代道德虚构所关涉的生活世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公共领域形成了尊重科学和制度的样本,在私人领域形成了引导人们追求崇高德性的形而上体验。
三 道德虚构的功能
通常,因为人们习惯于道德话语的实在特征。即在日常做出道德判断或者道德对话的时候,我们把这种类似于道德事实的内容当作了客观事实,好比“我们在说孰是孰非的时候,那种确定的态度和方式,如同我们说太阳东升西落一般,像是在说某些客观存在的东西,”[6]然而,“太阳东升西落”可以通过科学观察所证实,我们却无法从物理世界中通过科学实证得到诸如“助人为乐是对的”这样的属性。但是,否定这些道德属性即否定我们的道德历史和现实道德生活、否定道德话语的有效性,我们显然无法承受。因而,承认道德虚构的价值,选取和推荐某些道德虚构,作为社会语境下“值得说”的道德主张,当作是有价值的道德判断以供人们学习显得有意义。“教育模式的构建者所确立的教育目的就是对各种理论认识的选择和组合。”[7]道德虚构的构建者们,其教育目的同样是基于多重价值的叠合而成。道德虚构具有帮助个体塑造道德信仰的功能、维护道德教育的合理与合法性功能、促进与构建和谐社会道德秩序的功能。
(一)帮助个体塑造道德信仰的功能
道德虚构是现代社会帮助儿童养成道德信仰的重要助力。从道德教育的历史维度而言,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要求其具备传递某种真理性终极价值、教育目标能够指向与现实生活看似无关的未来道德社会。道德虚构能够契合儿童道德信仰养成的诉求。通过道德虚构可以填补个体道德发展所需的客观道德载体,借助道德虚构的力量发展其本体的道德性,塑造个体道德发展中的参照和动力源泉,弥补其道德信仰发展中的迷惘与空虚。
道德虚构具有引导个体形成道德和成为个体道德发展的动力的功能。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受体——青少年来说,由于他们的认知能力和抽象能力的缺陷,以及个体的道德发展具有阶段性、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等特征,导致其道德的发展总是需要更为客观的道德形象和“为什么要道德”的回答载体。因此,学校中经常出现的一种道德虚构几乎出现在教育产生的各个阶段中,如学校文化中的名人画像、励志简介等等,通常通过假如……你就会……的语言逻辑来引导学生发展与成长,而几乎所有的这些校园软文化建设都与成功和道德相关;再如课堂教学中,教师常常会潜意识地将自己作为道德榜样,通过以实体虚构的方式,为了解释某种结果的艰难和教师形象的树立(几乎没有教师认为自己是不道德的),过滤掉自身发展中的其他因素,将自己作为道德的载体进行虚构,或者将学生本人作为载体进行道德虚构,勾勒出服从和接受规训的美好愿景等等。
康德认为道德榜样能够对个体产生道德感染的功能,并且能够鼓励个体去践行道德之事。道德榜样可以让原本抽象、空洞的道德法则规定,通过具体的形象进行展示,进而使得个体或者处于学习道德规范初期的儿童更直观和深刻地感受到道德法则的可行性或实践性。即“所规定的东西变成可行的、无可怀疑的。它们把实践规则以较一般的方式表示出来的东西,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8]但是,康德又谈到,道德榜样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道德榜样是道德虚构的产物,是善的复制品,而非善的原型、善的本体,是经过他人刻意的塑造而产生的;另一方面,道德榜样是对于他人的价值塑造,而非个体的实践理性下自生的道德原则过分对道德典范的肯定,会遮蔽了实践理性在道德生活中的绝对重要性,而且,道德榜样对人从感性层面的教育功能总是有限的,而实践理性则可以让个体确立普遍而有效的道德法则。道德教育的最终对象是人,道德虚构的最主要影响在于对个体的道德影响。合理的、适度的道德虚构,对于个体能够产生积极的、有效的道德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无用的,甚至引起个体反感和反抗的影响,失去了道德教育的效果,进而导致道德虚构的使用与道德教育的目的产生悖离。道德虚构应该遵从必要的限度,这里说的限度主要是指道德典范与个体生活世界的相关度。
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乃至无视道德榜样的作用,应该借助于这种力量的引导与鼓舞,逐步确立自己的、主宰意志的实践理性。“个人凭借其两种道德能力(正义感、善观念的能力)和理性能力(判断能力、思想能力以及与哲学能力相联系的推论能力)而成为自由的。拥有这些能力,使他们在所要求的最低程度上成为充分参与社会合作的成员,这一点又使每个人成为平等的。”[9]理性能力的发展是个体具备自由观念的重要保障,因此,对于道德虚构下的道德榜样,我们更应该理智而客观的评价和使用它们,呵护个体理性发展的可能性,避免道德悖论的产生(即由一种善的合乎逻辑的道德方法却导致了恶的结果的产生)。同时,在道德教育中,我们也应该不断的探讨道德虚构的必要界限,以及如何消解其对于个体理性的可能性束缚。
(二)维护道德教育的合理与合法性功能
当道德的话语权掌握在强权政治之手时,由于没有独立于世俗权力的道德权威,道德学说被作为强化专制君主权力正当性的助手,通常以他律为特性的控制形式出现,包括以制度、规范和条例等形式表现的强控制,和以榜样情景、奖励训练等以“教化”为主要形式的软控制。然而,随着人类生活的日渐理性化和个体自由意识的觉醒,过去被过度人为设计的道德教育和道德教育方式,逐渐被人们所质疑甚至抛弃。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德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大多数由教导而生成、培养起来的;另一类是伦理的(ethics),由风俗习惯(ethos)沿袭而来,一个人从小养成的这样或那样的习惯不是件小事,相反非常重要。”[10]在过去看来正确、合理、理智的道德观念、道德价值诉求发生了异构,其道德价值所追求的政统与道统的统一、天命与民意的统一等内涵,同现代个体的道德追求和价值追求发生了冲突。
东西方历史上的道德权威具有不同特质。在西方的文化体系构建中,由于其道德虚构的完成者是思想家、哲学王,其塑造的道德形象出现代表智慧、力量等美德特征。而我国古代的道德虚构话语权却往往集中于权力者之手,其特征往往是压抑自我情感和人性的伸展。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道德虚构形象中,一类是对前代统治者的形象予以修饰,使之更加完美和光辉,如后世王们对于先王的道德虚构,其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王权的合理合法性,是典型的道德虚构的历史主义方法;第二类是权力夺取者对自己的道德虚构,同前面对于先王虚构方法相同,将自己的王权获得宣称为是天命所系,将自己的行为宣称为天赐之德,是上天至高德行在现世的代表,“比如下启讨伐有扈氏、成汤篡夺夏政、武王篡夺殷商政权,所采取的伎俩如出一辙,即一方面打出受命于天和替天行道的王牌,另一方面自我标榜有德,因为自己有德,上帝才受命于他,让他拥有替天行道的杀戮特权。”[11]号召人们遵从自己创造的道德价值的特权。通过上述两种方法的交错运用,构成了我国古代的道德体系,并且成了两千多年王权专制制度保持稳固的重要辅助。
同传统社会相较,现代公民社会形成的共同体结构,要求个体同时兼具自我和集体的双重认同,社会需要通过一定的教育措施,使个体对其身份有着充分的接纳,实现个体外在的身份内在化,并且将其内化为个体的内在品质和行为。德里克·希特将美德、法律、政治、认同感等并列作为现代公民身份的基本要素,因而,现代道德虚构应当做出主动调适,进而适应现代道德教育的要求。
(三)促进与构建和谐社会道德秩序的功能
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趋同的道德秩序认识对于社会和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现代社会,多数的国家具有异质性的特征,即多数国家是由不同宗教信仰和民族构成,由此而导致的文化差异和道德认同差异,会因历史的分离现象和可能发生的分离而产生对抗的隐忧,而消除这种隐忧的可能性值得怀疑。所以,在超越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建构被广泛认同的道德秩序,是现代政治生活对抗文明断层线的必然选择。根据道德虚构的方法论特征,站在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的高度上,超越文明断层,整体性建构具有当代文明特征的道德语境、道德文化和道德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价值。
长期以来,道德一直被作为维系社会生活的关键缆绳。人们毫无猜忌的认为道德能够使我们的生活从一种状态通往另一个辉煌(按照这样的逻辑,历史是没有辉煌的),进而让人性发展为崇高和完美,同时,道德的普遍性、普世性、一致性和总体性是道德实践一直期望的理想,人们期望通过道德的魅力和道德教育建立那种充满真理、幸福和美德的理想国(没有虚假,又何来真理,没有不幸,何谈幸福,没有邪恶,又何来美德,因此,“充满”的世界是虚无的),也期望通过道德教育塑造区别于过去的“新人”,为此,人们一直不断通过学习和理解,认识和获得道德真理,为道德理想的建立寻找终极的合理性根据,为人们的道德生活确定终极的目的,我们有了这种终极性的道德真理,就可以建构一个道德的人性,可以在善恶之间勾画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进而对所有的生活形态进行道德的评判。道德教育史就是在如此的形而上学指导下,试图塑造完美尽善的道德主体、寻求道德的本质、建构完美的道德、塑造完满的人性、建构完美的社会,作为我们理性所确认的道德追求。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道德典范表现为一种“无我”存在,我们的很多道德虚构下的道德典范是不容许怀疑和反思的对象,是命令式的道德教育,道德典范的行为似乎跟个体的道德智慧、道德自觉毫不相关,而只是在某种精神感召下的冲动,从个体道德发展的层次性来说,道德典范对于儿童道德水平的早期影响至关重要。因此,在这样的道德榜样教育之下,儿童很难产生更具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道德智慧。
道德虚构的道德教育运用能够反映人的认知发展程度和文明发展程度,当人的认知发展到能够自我反思、自我塑造的水平,道德虚构的道德教育功能则会被削弱。而文明程度越高,代表人性的高贵与光明的文明越发展,相应的道德虚构中的消极功能也会被弱化乃至摈弃。相反,在一个时代中,道德虚构的消极功能越重要或者常常被当作可以利用的工具,那么,这个时代人的认知发展和人性文明则越狭隘,同时,通过道德虚构的不断教育和强化,可以对人性的狭隘发展趋向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导演宁浩在其电影《无人区》中有一个发人深省的反思:当我们的社会秩序、道德和法律都消失的时候,人的本性会剩下什么?宁浩认为人和动物之间最根本区别在于使用火。火是人类真正的文明(不同于其他的用以谋利的带有文明幌子的工具),是人性高贵和光明的一个缩影,因为火的使用初步开始使人和动物有所区别——动物只知利己,只是存在,而人却能利他,是在生活。
[1]Mark Elikalderon.Moral Factionalism[M].Oxford: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5:25.
[2]〔英〕约翰·洛克著.政府论[M].杨思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3.
[3]〔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钱永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45.
[4]John Rawls.The Priority of right and Ideas of the Good[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88(4):251-286.
[5]鲁 洁.德育课程的生活论转向——小学德育课程在观念上的变革[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3):9-16.
[6]张亚月.道德虚构主义的理论困境与可能前景[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1):10-13.
[7]刘庆昌.教育理论向实践转换的现实路径[J].教育学术月刊,2015(6):3-8.
[8]〔德〕康 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59.
[9]〔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64.
[1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7.
[11]唐代兴,左 益.先秦思想札记[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22.
(责任编辑 徐冰鸥)
On the Value Dimension and Function of Moral Fiction
ZHAO Guo-dong
(SchoolofEducationScience,ShanxiUniversity,Taiyuan030006,China)
Moral education is a non-a priori existence after the moral concept, that is, moral and moral education have both logical order and time order.A certain medium is needed between moral and moral education so that the moral of ontological nihility is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Moral fiction is a paradigm of moral education that has never been discard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West. It can become the learning model for the individual in moral practice through visualization and embodiment of the abstract moral idea and make people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nature of morality and accept the important meaning of moral discourse. Moral fiction has the value dimension of moral education, utility and the trend towards life world.It also has the function of helping the individual to shape the moral belief, maintain the rational and legitimate function of the mor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and construct the function of the moral order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moral fictional;moral education;moral model
2017-03-10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社会主义语境下的道德虚构设计与实践研究”(CEA140169)
赵国栋(1983-),男,山西平遥人,博士,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发展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德育原理和高等教育学研究。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7.04.018
G410
A
1000-5935(2017)04-013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