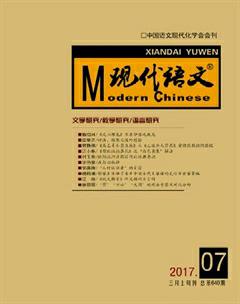《穆斯林的葬礼》之“白色意象”解读
摘 要:在《穆斯林的葬礼》中,白色是作品的主要基调。小说中的白色意象不仅体现了霍达对文学事业的虔诚、对美的执着、对主人公的原型饱含深切怀念之情,同时也象征作品中人物圣洁无染、纯真善良的精神品格,以及伊斯兰返朴归真的丧葬文化。白色意象使全书笼罩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带给读者难得的艺术享受。
关键词:《穆斯林的葬礼》 白色意象 象征
《穆斯林的葬礼》是回族作家霍达的代表作,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冰心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它是现代中国百花齐放的文坛上的一朵异卉奇花,……它以独特的情节和风格,引起了‘轰动的效应”。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与作者娴熟地驾驭色彩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代派绘画大师毕加索认为,色彩是一幅画作中,最能有力表达画面情绪的元素。其实不仅仅是在绘画领域,色彩已经超越了自身,渗透到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领域,承载了更多文化内涵。色彩与人类审美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色彩丰富的内蕴在文学中有着神奇的表现力,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它能增强话语的情感效果,给读者以艺术般的视觉美感,色彩语言是特定情绪的象征,具有审美的性质和想象的空间。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中充分利用色彩语言,营造特定的意境和独特的审美情趣。
作为穆斯林的霍达对白色情有独钟。在《穆斯林的葬礼》中,白色是作品的主要基调。无论是穆斯林的日常服饰还是节日服装,无论是作者笔下的景物色彩,还是葬礼上的色调,都以白色为主。
一、质朴淡雅的白色
霍达通过素朴的白色,营造了淡雅的意境。“月”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重要意象,作品中作者不惜笔墨描写月亮,尤其是对月光的描写情有独钟—— “屋里很暗,朦胧的月光从窗外反射过来,窗纸是一片淡淡的灰白色……”“西天的月牙儿已经转到了东南,天色不知不觉从浓黑变成了灰白”“仿佛走进了一座浓密的森林,黛色参天,苍茫无际,没有鸟鸣,没有人迹,只有月光照耀下的一条羊肠小道,明晃晃地显现在脚下,……”。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北京,这座北方的城市每到冬天就会变得银装素裹。作为穆斯林的霍达对这洁白的雪不可能视而不见,不可能不产生情感的共鸣,于是她写道: “洁白的燕园,洁白的未名湖,洁白的小岛,漫天飛雪中,伫立着一个少女的身影……”“未名湖畔,一个洁白的世界,白雪下面,露出备斋的画栋雕梁,一条雪路通往白色的湖心小岛,……”。对雪景的描写使作品呈现一种质朴的美感,淡雅的意境。
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引用前人的观点,从主体方面谈到了意境中三个不同层面的结构,“始境,情胜也;又境,气胜也;终境,格胜也。”[1]宗白华进一步解释说:“‘情是心灵对印象的直接反映,‘气是‘生气远出的生命,‘格是映射着人格的高尚格调。”[2]这部小说不仅以情胜,更以格胜。正如霍达所言:“文学,来不得虚伪、欺诈和装腔作势,也容不得污秽、肮脏和居心不良。‘文如其人,作家的赤诚与否是瞒不过任何人的眼睛的,我历来不相信怀着一颗卑劣的心的人能写出真善美的好文字。”“人是需要理想、需要幻想的,需要美,以美的意境、美的情操来陶冶自己。”[3]霍达在小说中通过对月光、雪等白色景物的描写,营造出质朴淡雅的意境,正是她对文学事业的虔诚、对美的执着、对主人公的原型饱含深切怀念之情的体现。
二、圣洁无染的白色
白色是穆斯林节日服装的主要基调。每年伊斯兰历的第12个月,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要聚集在麦加,参加一年一度的朝觐。朝觐者在踏上圣地前,都要脱去常服,脱去人间的各种虚伪、炫耀、高低、贵贱,换上统一的两片不加缝制的白色戒衣,以示彼此一样、本无区别。
小说中,作者笔下的人物着装也以白色系为主,玉儿穿着“白色的短袖衬衫,白色的西服裙和白色的皮鞋”,韩新月有时穿着“白色丝袜”和“飘然下垂的白裙子”,有时穿着“米色长裤和白色的毛衣”。吐罗耶定“头上缠着白色的‘泰斯台”,韩子奇身穿“一件月白色竹布长衫”。霍达笔下的穆斯林女性几乎都是皮肤白皙,“不必特别地打扮自己,便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朴素的美”,男性穆斯林也呈现出玉树临风般的儒雅气质。白色作为一种色彩语言,象征了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精神世界,他们都各有其痴迷的一面,存在各不相同的个性弱点,但都有着一颗纯真而圣洁的心灵。
老一辈玉器匠人梁亦清,“艰难地、顽强地、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信奉着自己的主”。他虽然手艺高强,却缺少书本知识,又秉性木讷,不擅言辞,没有本事应付生意场中的交际和争斗倾轧,足不出户,只会埋头做活儿。即使人家靠他的手艺赚大钱也不抱怨,“安贫守摊”,维持一家人生计。梁亦清并不以供家养口为满足,他自有建基于虔诚信仰之上的执着追求,这信仰和追求寄托在宝船《郑和航海图》的雕琢上。梁亦清说:“我应这活儿,一不是为了保住奇珍斋的招牌,逞能;二不是贪图他给的这个价钱。让我横下这条心的,就是因为三保太监郑和是个穆斯林,是咱们回回!”又说:“人,不能忘了祖先啊,冲他们,我也得豁上这条老命,做出宝船,让外国人也瞧瞧,中国的穆斯林对得起祖宗!”玉碎人殁的悲壮的结局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显示出“梁亦清一生的追求,穆斯林心中的信仰”的力量。
梁亦清的长女、韩子奇的妻子梁君璧与其父亲一样没念过书,不识字,刚烈、激情,有坚忍卓绝的血性。她的性格在与梁冰玉、韩子奇的婚恋纠葛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冰玉宣布她和韩子奇才是真正的爱的结合,要姐姐“下岗”时,君璧果真大打出手,直至逼走冰玉。她干预韩天星的婚事,阻挠新月的恋情。这一切皆因梁君璧坚定地顺从真主、虔诚地信奉伊斯兰教。梁君璧所做一切的精神动力、她的做人理念、她的行为根据,可以归结为一条,即:遵从万能的真主的旨意,恪守伊斯兰教规教义。她不能原谅妹妹与韩子奇的所为是因为穆斯林把已婚者通奸列为不可饶恕的罪恶,《古兰经》更明文规定:“真主严禁你们……同时娶两姐妹。”梁君璧割断韩新月和楚雁潮的恋情,也不是故意和女儿过不去,找茬儿把她赶向死亡的深渊,而是在她看来,“我们穆斯林不能跟‘卡斐尔作亲!”
虽然梁君璧不乏性格负面,但她的性格中也表现出穆斯林的美德,如纯洁、善良、包容等。韩新月死后,梁君璧还是悲伤,觉得自己欠女儿的太多了,想要弥补,她“凝视着女儿,抚摸着女儿,不忍释手”。韩子奇临终前向她告罪:他是一个假回回。假回回——这本是教规所不容的,而梁君璧却宽恕了他,真诚地认为“他一辈子都遵从着回回的规矩,他做出了大事业,为回回争了光;他一辈子都遵从着真主的旨意,他和玉儿的那点过错,也应该原谅了!他是个真正的回回,真正的穆斯林,决不能让他在最后的时刻毁了一生的善功!”
“玉器梁”家第二代人中地位和作用比梁君璧更重要的韩子奇,始终是一个真正的玉人,一个一生琢玉、鉴玉、品玉、览玉、藏玉、爱玉胜过生命,能为玉牺牲一切的玉器制作家、鉴赏家和收藏家。而玉在韩子奇的心目中不单是交换货币、增殖资本的媒介,更是中国最珍贵的历史文物,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是国宝。蒲寿昌收三块商玉毁掉两块,然后高价售出剩下的一块,韩子奇不惜以更高的价格从买主亨特手里购回,让无与伦比的国宝得以还家。日本侵略者进占北平之际,韩子奇不惜抛妻别子,携带五大箱古玉器远走异国他乡,并踏遍英伦三岛办“玉展”“向西方人展示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明”,一旦战争结束,又“完璧”归国。隐忍痛苦和不幸,保存所收藏的价值连城的珍宝;发现“密室”中变卖出去的乾隆翠要被倒卖国外,不禁气绝,摔成重伤。这一切义举、壮举,一再地体现了韩子奇热爱祖国,热爱并弘扬中华文化的情操与殊勋。的确,他不仅为回回民族,也为华夏民族争了光。
“玉器梁”家第二代人中的梁冰玉,受过高等教育,还到英国留学,因而像当时许多女性“新青年”一样,有爱国心、正义感,因初恋情人杨琛出卖革命、进步的同学而心灵受创伤。她追求个性、婚姻自由,唾其不当爱,决然与叛徒卖国者决裂;爱其所当爱,敢于不顾一切让“感情冲破理智”,决然同韩子奇结合。她的婚恋不见容于真主和穆斯林,也不见容于华夏传统道德,但无论遭受什么样的冷眼、诅咒和承担什么样的罪名,她死而无憾,永不后悔,因为她“享受了作为一个人的权利”。抛出幼婴,毅然从博雅斋出走,与韩子奇分手,梁冰玉维护了人格的独立和尊严。
“玉器梁”家的第三代韩新月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从小立志上名牌大學,成为学者,改变回回只能经商的习惯看法。她倔强地说:“人的灵魂是平等的”,她不认为少数民族的同学就低人一等,满怀信心地要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平等地同任何民族的人比个高下。在爱情上,韩新月也高扬“真诚的平等的”恋爱观,宣称“爱情总不等于同情、怜悯和自我牺牲”。命运对新月不公,她没有留下功业便走完了短促的人生。但她不曾向命运低头,而是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她从鲁迅的《起死》与欧·亨利的《热爱生命》中获得同病魔较量的信念,从楚雁潮的坦诚痴爱中获得朝既定的目标,朝着事业的远景继续攀登下去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她坚韧执着地追求生命的价值,无愧为有“一颗坚强的心,在布满迷雾的人生中能牢牢地把握自己的命运,闯过一道道难关的强者”。
“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内容都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凭借一定的物质材料组成的感性形象才得以展现并诉诸我们的感官的。”[4]“我们只能按照意义与符号的区别来区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把内容视为该作品所含有的精神填充物、精神的含义、精神的信息,而把形式视为用词、声音、动作、花纹、颜色、体积表示的这一信息、这一意义、这一含义的物质体现。”[5]霍达笔下人物外貌所呈现的白色主调,正是其笔下人物圣洁无染、纯真善良精神品格的外在形式。
三、返朴归真的白色
《穆斯林的葬礼》用不小的篇幅描写了回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使之成为情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突出的例子如葬礼和婚礼。小说中,共描写了两次葬礼,分别是梁亦清、韩新月的葬礼。梁亦清的葬礼标志着小说情节的开端,亦表现了穆斯林葬礼的基本特点:土葬、薄葬、速葬,最为简朴不过,同时却隆重而庄严。“……伊斯兰教的葬礼是世界上各民族、各宗教中最简朴的葬礼,没有精美棺木,没有华贵的寿衣,没有花里胡哨的纸车、纸轿、纸人、纸马,没有旗、锣、扇、伞的仪仗,没有吹吹打打的乐队,没有满天抛撒的纸钱……一心归主的穆斯林,不需要任何身外之物来粉饰自己。”
在葬礼的描写中,白色亦成为其主要色调。 “白幔里,韩子奇跪在师傅的身旁,手持汤瓶,由清真寺专管洗‘埋体的人履行神圣的职责,为他洗浴。”“圣洁的白布覆盖着他的全身,蒙蒙的细雨冲洗着亲人们的泪眼。”“……在他的颈下枕上了用白布包着的香料。”
新月的葬礼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高潮,也是对其短暂一生的总结。“韩太太用洁净的白布把女儿身上的水擦干,三个人一起把她抬到铺好‘卧单的床上……”(第567页)“楚雁潮的手臂剧烈地颤抖,凝望着将要离别的新月,泪如雨下,洒在洁白的‘卧单上,……”
回族的葬礼文化是在穆斯林独特的生死观、人生观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发展并确立的。伊斯兰教认为,人是由真主用泥土创造的,实行彻底的土葬,可以使人与泥土化为一体,最终回归本源。当一个穆斯林“无常”后,其遗体必须在三天之内被埋葬,以表示对亡者的尊重,体现亡人入土为安的意义。
薄葬则体现了穆斯林的简朴本质。“穆斯林没有任何祭品,没有食物,也没有花圈,只有一束圣洁的香河熟记在妈妈心中的经文。”伊斯兰教认为,既然人是赤身来到今世,就应孑然一身地离开。除了“信仰和善行”可以伴他(她)进入后世外,人世的任何物品,对亡者都毫无作用。
中国穆斯林称人的死亡为“归真”,意即皈依真主。洁白的幔帐上写着:“没有真主的许可,任何人也不会死亡,人的寿命是注定的。我们都属于真主,还要归于真主。”葬礼上,“一片肃穆,一片寂静,除了‘真主至大的赞颂,没有任何声音。”“最后一次‘泰克毕尔念完之后,阿訇和穆斯林们向各自的左右两侧出‘赛俩目向天使致意。……全体穆斯林把双手举到面前,接‘堵阿以。在这一刹那,亡人的灵魂才确切地感知自己已经亡故了,该走向归宿了!”
在伊斯兰教中,生老病死都是真主的旨意和安排,死亡也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它仅仅连接着今世与后世,是真主的前定,是短暂今世的结束和永久后世的开始。人的肉体死后,人的灵魂却不会消失,人的意念或精神仍然存在。
伊斯兰教信仰后世,确信末日审判。《古兰经》中有明文训诫:“今世生活,只是游戏、娱乐……只是欺骗人的享受。”“每个灵魂都站在真主的面前,接受审判。……生前的财富和地位、权势变得毫无意义……”。就是说今世的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人的最终归宿还是在后世。“真主将根据每个人的善恶判定他的归宿。善者,永居天园;恶者,投入火狱。”所以当“夜深人静,……她(韩太太)仿佛听见了真主的许诺,女儿是无罪的,是圣洁的!她感念真主的宽恕,热泪涌流……”。而韩子奇临终前充满惭愧和恐惧,“这五功,我一样也没能完成,怎么能算个合格的穆斯林呢?又有什么脸面去见真主?我不敢啊!到了那个世界,这一切都要清算的,更何况,我还……”
伊斯兰一词的意义为“顺从”“皈依”或“信服”,即“顺从真主而获得安宁”之意。伊斯兰的生死观、人生观决定了穆斯林对死亡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众不同的伊斯兰丧葬文化。作为一种色彩语言符号,白色象征着顺从、皈依,使人获得安宁。霍达用白色作为伊斯兰返朴归真的丧葬文化的象征。
《穆斯林的葬礼》中的白色意象不仅体现了霍达对文学事业的虔诚、对美的执着、对主人公的原型饱含深切怀念之情,同时也象征作品中人物圣洁无染、纯真善良的精神品格,以及伊斯兰返朴归真的丧葬文化。“正因为是为穆斯林人心作传,全书笼罩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因此,“它是穆斯林的圣洁的诗篇”,带给读者“难得的艺术享受”[6]。
注释:
[1]蔡小石:《拜石山房词》,转引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2]宗白华:《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3]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604-605页。
[4]王宏建:《艺术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78页。
[5]凌继尧、洪天富、李实译,[苏]莫·卡冈卡冈:《美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页。
[6]刘白羽:《序二穆斯林诗魂》,转自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
(汪小艳 江苏南京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 21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