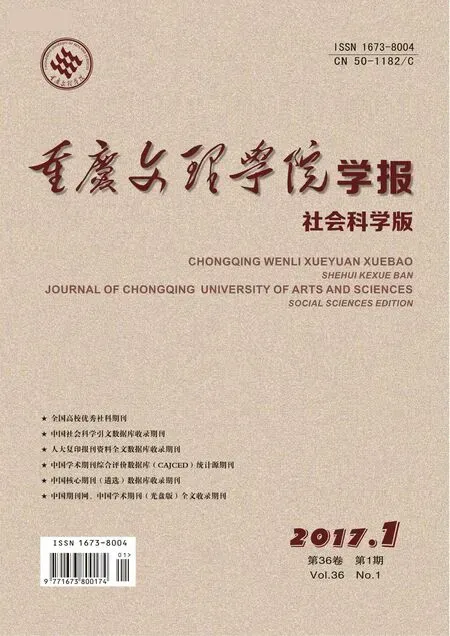论中国翻译史中的大规模“合译”传统
陈 议,鲜 玥
(西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310500)
论中国翻译史中的大规模“合译”传统
陈 议,鲜 玥
(西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31050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翻译在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融合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合译”占据了翻译史的重要一隅。以佛经翻译、《毛泽东选集》英译、马恩列斯著作中译为例,找出不同时代采取合译的共性和个性,从而增进对翻译事业的理解。
合译;佛经翻译;译场;《毛泽东选集》英译;马恩列斯著作英译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翻译活动在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融合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陈寅恪所说:“文化史就是翻译史,所以可以说,翻译活动是基础,是根本,永不过时。”翻译按方式可分为合译和独译。合译,顾名思义,就是指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作进行翻译的一种群体行为。本文将主要对我国翻译史中“合译”行为尤其是大规模的“合译”现象进行粗略的整理和详细的分析对比,以此回答各合译活动的相似与区别,合译行为在当时历史语境下的价值和意义,对当今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及这些合译行为对当今科技翻译和其他需求量较大、单人完成难度较大的翻译活动有何启示等问题。
一、合译,“合为一”
合译,顾名思义,就是指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作进行翻译的一种群体行为。根据合译者分工、合作方式的不同,合译又可进一步分为以下四种方式:(1)主译加润色的主配角式;(2)口述加笔译的互存式;(3)“化整为零”的承包式;(4)大规模合作的立体式[1]。本文主要讨论第四种合作方式——大规模合作的立体式。这类合译模式国外最典型的便是《圣经》的英译,国内典型的便是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史、《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和中央编译局对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译等。
据郑延国[2]对史料的研究,我国关于合译这种翻译方式的最早记录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记载在宋代《册府元龟·外臣部》:“周公居摄六年,制作礼乐,天下和平。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稚,曰:‘道路遥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其中的“象胥”和“重译”均指译员。接着便是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等,这其中合译的案例举不胜数。可以想见,合译在翻译活动中自古以来就是非常有效的翻译手段。但是,对于这种手段,我们只能说是“有效”,而不能称其为“适用一切”,尤其是大规模的立体式的翻译活动。虽然合译能够提高译文质量,加快翻译速度,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译作因为翻译人员涉及过多以至于不能达到“合为一”;组织这样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一般都是基于政治原因,而政治原因又多在特殊的时机和场合才会发生。所以纵观中国历史五千年,大规模的集体翻译也就只有历时上千年的佛经翻译和现代《毛泽东选集》的英译以及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译。既然案例这样少,为何还要研究一番呢?因为这样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一旦形成,其影响之深,辐射之广,对整个文化史都做了改写。尤其是对于当今世界,各民族之间交流互鉴的规模和频率空前高涨,无论是经济、文化上,还是政治、军事上,各国人民都需要彼此了解、彼此学习。所以研究这种带有政治性的集体翻译不仅对翻译学有意义,甚至对其他学科诸如社会学、政治学都有一定启示。
二、佛经翻译的历史沿革和译场职司的构成以及其他集体翻译方式的传承
马祖毅将我国佛经翻译分为四个阶段[3]。第一阶段,草创时期,从西汉末年到西晋(前2—316);第二阶段,发展时期,从东晋到隋朝(317—617);第三阶段,全盛时期,唐代(618—906);第四阶段,尾声时期,北宋(954—1368)。初期的译经者多是中亚一带来华的高僧,以后逐渐有了直接从印度来的高僧,由于他们的汉语水平不高,所以必须先通过口头诵出,叫做“传言”或“废语”,然后依仗中国僧人进行翻译,叫作“笔受”。此时,佛经翻译规模小,翻译质量也不高,尚处于“个体化的私人翻译阶段,在组织上很不完备,译场制度仍在孕育之中”[4]154-155。
从东晋到隋朝以前,译场模式逐渐形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译场是竺法护,于晋武帝太始二年(266)建立主持的白马寺译场。朝廷派遣使者从西域请来了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僧人,这两位僧人不仅从西域带来了佛像,还带来了佛经。由于这些佛经是从印度传入的梵文经书,为了便于传教,摄摩腾和竺法兰将佛经翻译成了汉文。自此以后,中印两国的僧人来往不断,更多的佛经传入中国,经过200多位译师10个世纪的辛勤努力,由梵文翻译过来的汉文三藏达到了1 690余部、6 420余卷,佛教的声闻乘、性、相、显、密各部学说都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从而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巨大宝藏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广泛传习,越来越多的僧人、居士加入了翻译佛经的事业。前一阶段的私译转入了官译,参加人数之多,而且有了比较细致的分工。例如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时,“于长安大寺集四方译学沙门二千余人”;译《维摩诘经》时,姚兴“命大将军山公左将安城候马义学沙门千二百人于长安大寺”参与活动;译《大智度论》是500人“共集”;译《思益经》是2 000余人“咨悟”。当然,这许多人并非都是直接参加译经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听译主讲解经义或参加讨论或辩论的[5]。所以,此时主要是以讲经形式的译场为主,同时也是弘法的讲堂。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形式往往会引起现场激烈的辩论,因为在座的信徒如果对译经大师的译文有不解之处,可以当面质疑。例如,马祖毅在《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鸠摩罗什在译《法华经》时,拿竺法护的旧译本来对照,其中“天见天,人见人”是照原文直译的。罗什认为该译文太“质”了,他的弟子僧睿提出可以改译为“天人两接,两得相见”。罗什大喜,采用了僧睿的译文[5]。所以,这种集体讨论合作的方式不仅提高了译文的质量,使之更加接近原文,而且扩大了宣扬佛法的人群,使佛教传习更接地气。
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便是隋唐了,此时的译场制度在之前的几百年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已臻于完善,译场“大多由专家组成,他们在译场内以译经为主,讲经为辅”[6]131。而且此时的译场职司的设置也最为完善。早期的译场分工主要有主译、传言、笔受和劝助。而根据《宋高僧传》卷第三·唐京师满月传的记载,唐朝涉及的职司数量最多,共计12种,即译主、笔受、度语、证梵文、证梵义、证禅义、润文、梵呗、校勘、监护大师和正字字学。宋代译场从职司功能上来看则更加完备,只是在译经数量和质量上不如李唐。而宋以后的各个朝代,由于印度佛教式微,而且那些足以彪炳史册的译经大师不复多见,所以整个译经事业逐步没落,可资立传者已难觅踪影,译场形态也就随之淡出人们的视线。
我国的佛经翻译事业从西汉末年开始,历经魏晋南北、唐、宋,最后在元代结束,历时之久,影响之广,名声之盛,在人类交流文明史中都茕茕孑立,显赫一时。
除了佛经翻译这种大规模的集体合译方式外,还有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即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翻译,以及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均是以集体合译方式为主要翻译方式。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因为作为翻译主体的传教士,他们的汉语能力有限,而对中华文化了解不够,所以需要精通汉语的人士协助,如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与李之藻合译了《园容较义》和《同文指标》;傅汛际和李之藻合译了《名理探》;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和徐光启、李天经等编译了《崇祯历书》;邓玉函口授,王澄笔录的《奇器图说》等等,这些翻译活动虽然都是当时传教士为传教吸引中国人的一种手段,但也或多或少促进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至于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翻译,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洋务机构设置了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作为专职翻译部门。采用的翻译方法与佛经类似,以口译加笔受为主。然后就是林纾和他的助手们,先后与林纾合作的译者近20人,译作多达163种,对当时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余的还有鲁迅、周作人合译的《日本现代小说集》,苏曼殊、陈独秀合译《悲惨世界》,罗家伦和胡适合译《娜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像《水浒》《红楼梦》等中国文学[4]166-170。
三、《毛泽东选集》英译过程梳理以及马恩列斯著作的集体翻译
《毛泽东选集》英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始于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文章的的译介。第一篇被译成英文的毛泽东文献是1927年6月12日《共产国际》刊登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翻译了大量毛泽东著作单本,并在国内外出版。1945年董必武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时,借机将一批毛泽东著作交由时任美共中国局书记的徐永煐,让中国局组织翻译审定,后来由浦寿昌负责具体翻译事务。1949年建国后,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毛泽东著作,最早的有《论人民民主专政》《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并多次修订,其中《论人民民主专政》就先后修订了39次,《矛盾论》也至少修订了5次。单篇毛泽东著作的对外译介为《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做了一定程度上的准备,也可以说,单篇著作的英译本身就是《毛泽东选集》英译的一部分,不过,真正本体意义上的《毛泽东选集》英译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
根据巫和雄关于《毛泽东选集》英译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英译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4]37-50。第一阶段从1950年开始,到1956年结束,完成了《毛泽东选集》前3卷的翻译,并在国外出版。该阶段的主要工作由徐永煐负责组织和领导。其他的人员还有金岳霖、钱钟书、王佐良、郑儒箴、赵一鹤、袁可嘉、王仲英、黄爱、王楚良等专家学者。第二阶段从1957年至1959年,在这个阶段,英共党员作家吉尔斯(Giles)因对劳伦斯出版公司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前3卷英文不尽满意,主动着手修改,并邀请钱钟书、徐永煐、浦寿昌等参与,约在1959年完成。这次的修改稿由于发起人是外国人,国内并没有相应的出版计划,加之译稿质量受到质疑,最终没有正式发行。第三个阶段始于1960年,结束于1966年,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翻译《毛泽东选集》第4卷和修订出版前3卷。参加第4卷初译的主要有徐永煐、程镇球、杨承芳、陈龙、吴景荣、方矩成、于宝榘、郑儒箴、赵一鹤等,为译稿润色的则有钱钟书及外国专家马尼娅(Manya Reiss)和柯弗兰(Frank Coe)等人,定稿组成员包括孟用潜、徐永煐、程镇球、冀朝鼎、唐明照、袁克安等,以及外国专家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和李敦白(Sidney Rittenbury)。1975年至1977年是《毛泽东选集》英译的最后一个阶段,第5卷的翻译出版工作在此阶段完成,从而为整个《毛泽东选集》英译画上了句号。此阶段除了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的工作人员之外,又从外交部、新华社、中联部、外交局、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全国总工会、对外友协等单位调集了大批优秀翻译人才,甚至从外地调来著名教授,组成了35个不同语言翻译组,每组配备2~3名外国专家。1977年9月,也就是在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正式发行仅仅5个月之后,其英文版向全世界发行,出版后半个月即在美、英等国与读者见面。
从上面梳理的资料可以看出,参与《毛泽东选集》翻译的译员人数众多,构成复杂,历时20多年,是中国翻译史上继佛经翻译之后的又一大规模合译活动,对传播毛泽东思想、展现现代中国革命历程具有深广意义。
除了《毛泽东选集》英译这一宏大的翻译活动外,中央编译局对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也是一项浩大工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全称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成立于1953年,前身是1949年创立的中央俄文编译局,中央直属机构,主要任务就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等。
新中国成立之前,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马列著作只能零星地译成中文。为了传播革命的真理,编译局便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漫长的翻译之路。“当时的编译局,除了少数像师哲、陈昌浩、张仲实、姜椿芳、谢唯真这样有很深造诣的翻译官外,绝大多数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7]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编译局先后出版发行了《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于1975年开始着手重新编译《列宁全集》。其中,《斯大林全集》收录文章近500篇,约340多万字;《列宁全集》共38卷,1 500万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更是囊括50卷,字数高达3 200万。新版的《列宁全集》共60卷,字数3 000万字,收录文献9 289篇,总字数比旧版增加一倍多,“是目前世界上各种文本收藏列宁文献最多的版本”。这样卷帙浩繁的理论宝库单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的。每一篇译文都经过了集体翻译、集体讨论、集体定稿。除了诸如翻译、初校、初定稿、定稿以及最后审定等许多工序外,还有主管同意译名,加解作释。例如,原马克思室主人周亮勋回忆,当时仅翻译《资本论》一书,他们为统一译法而做的卡片就有数万张之多[7]。
如今,全国人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手拈来,不能不承认中央编译局对此做出的巨大贡献。
四、佛经翻译、《毛泽东选集》英译和马恩列斯著作翻译过程的分析与对比
佛经翻译、《毛泽东选集》英译以及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过程既有共同点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其共同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都是分工协作的集体翻译方式而且规模宏大。佛经的翻译经历了从初期两三人简单搭配到后来大规模译场的发展过程。与之类似,《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在早期也是由少量的几个人完成的,直到1950年中宣部成立《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之后,这项翻译工作才走上了立体式合作的道路。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大规模的集体翻译组织有序、结构完整,既自上而下又平行展开,整个翻译过程像是精准的机器,所以译出的作品质量高、影响深远。展示了不管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合译都不失为一种高效而可行的翻译方法。
第二,反映了所处时代的特点,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佛经翻译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借助宗教美化甚至神化封建统治者,教化人民,从而巩固皇权统治的目的。而且统治者历来重视并资助佛经翻译,将佛经翻译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允许的范围内,从而扩大了佛教的传播,使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是一种政治行为,反映了我国当时宣传毛泽东思想,宣扬中国人民伟大革命的政治诉求。《毛泽东选集》堪称中国共产党智慧的结晶,理应得到重视和对外传播,所以《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赞助,反映了我国对外宣传中华文明的决心和勇气。马恩列斯著作的汉译也是党中央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展开的一种政治行为,作为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最大的理论武器,也是党的理论基础,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潜心钻研、认真学习。
第三,促进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千年佛经汉译,不仅是建立中国佛教的重要基础之一,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佛教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都发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在中国翻译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国外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和各种主要版本的毛泽东文集,对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加强毛泽东思想在国外的影响和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对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不仅让中国人民全面地了解其他民族优秀的思想理论,而且我们引进之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丰富了民族文化。
第四,对现代翻译机构或机器翻译的共同启示。大规模的集体翻译能译出经典,译出常人不能译出之作。现代机器翻译的运行原理跟集体翻译是一致的,各大翻译平台都拥有巨大的语料库,如同将许多翻译大家聚集在一个屋子里,以前人工做的事,现在用机器进行操作,相信如果能够模拟集体翻译的模式,并且随着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翻译将会大放光彩。
虽然都属于合译,但三次翻译过程又各具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译入与译出。佛经翻译和马恩列斯著作都是将外语译成中文,属于译入。而毛泽东著作的英译发行及对外传播,是从西方传教士传播中国文化开始,至今近400多年间,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历史中主动传播的第一次。
第二,三场合译的不同点还在于原文本。佛经翻译时,译者有选择原本的自由。无论是随意性较大的口诵译经时期,还是后来成规模的译场译经阶段,“译什么”的问题总是由译者来定夺。反观《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和马恩列斯著作的中译,译者在原文本的选择上没有任何权利,该译什么不该译什么,根本与译者无关,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遵照指示把分配的任务完成好。
第三,三场合译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译作是否有署名。在佛经翻译中,译经人员的名字一般会被列在经文正文的前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某部经书是由谁翻译的。不仅如此,就具体的某部经文来说,译者信息甚至具体到谁做的笔受、谁担任了证文以及谁又进行了正字。《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上我们看不到任何译者信息,而且马恩列斯著作译本上也只注明了“中央编译局”几个字,读者不能看到其背后默默奉献的译者,当然,这和当时的政治气候不无关系。
五、结语
在中国的翻译长河中,翻译人员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不管是采用合译的方式,还是单独行动,都为中国人民与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文中所列举的三场大规模的合译活动,证明合作翻译模式是客观存在的,有时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这种翻译模式的生存空间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愈发扩大。如基于互联网的集体分工翻译、大规模科技资料的翻译、中央编译局组织的其他集体翻译等。所以我们应该从多角度对合作翻译模式进行更为深入、更为细致的研究,唯有如此方是翻译界的幸事[8]。
[1]张德让.合译,“合一”[J].中国翻译,1999(4):25-28.
[2]郑延国.合译,佛经翻译的一大特色[J].现代外语,1995(4):22-26.
[3]马祖毅.中国翻译史话——我国的佛经翻译[J].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1):83-99.
[4]巫和雄.《毛泽东选集》英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5]马祖毅.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J].中国翻译,1982(5):24-25.
[6]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M].台北: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7]何平,刘思扬.为了传播真理之火——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采访纪事[J].瞭望,1991(21):6-8.
[8]刘杰辉,冯书彬.中国传统合作翻译模式刍议[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1):23-25.
责任编辑:吴 强
On the Tradition of Large-Scale Co-Translation Initiative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CHEN Yi,XIAN Yu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500,China)
China has a history as long as 5 000 years,and the translation has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xchanges and fusion of diverse ethnic groups.Co-translation,or collective translation,as a method of translating,has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This aims to examine the common traits and different features of co-translation initiatives in different times in China so as to achieve a better understand of translation as an indispensable undertaking for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exchanges.
co-translation;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translation workshop;the translation of The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the translation of the Marxist works
H059
A
1673-8004(2017)01-0103-06
10.19493/j.cnki.issn1673-8004.2017.01.019
2016-07-13
陈议(1978— ),女,四川泸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鲜玥(1992— ),女,四川巴中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