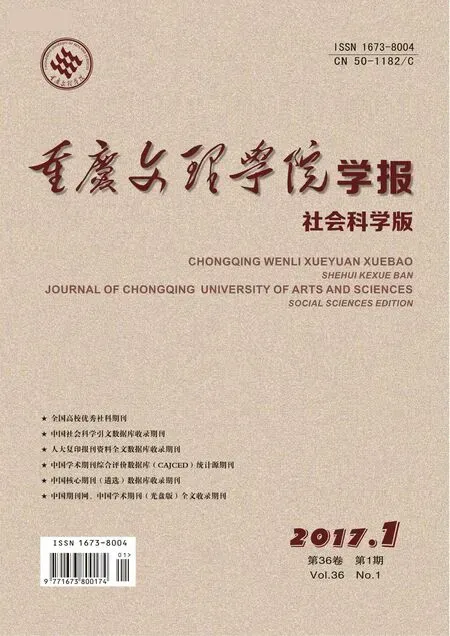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分析《苔藓》中的父权解构
康茜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骨干示范办,重庆 永川 402160)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分析《苔藓》中的父权解构
康茜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骨干示范办,重庆 永川 402160)
《苔藓》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的一部短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生态环境、人物关系和特定意象三个方面在对作品父权中心主义的解构叙事中呈现出了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文章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门罗的这部短篇小说进行批评,既符合作品的女性主义客观性,又融入了生态主义现实意义。文章对于激发读者对父权文化进行审视和批判,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建立一个平等、包容、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生态女性主义;父权中心主义;解构;《苔藓》
一、引言
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加拿大女作家,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她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并于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论家艾尔迪科·卡灵顿高度评价门罗的叙事艺术:“叙述人就像一个超然的布局者,将各种难以把握的因素捏合到一起,来描绘出真实的现实。”[1]而这些描绘出来的现实大多是关于当代普通人,尤其是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接近日常生活的题材更容易让读者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找到归属感,产生共鸣。
《苔藓》选自门罗198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爱的进程》,这部包括11个短篇的小说集,令她斩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同门罗的其他大多数作品一样,《苔藓》也是以女性为中心展开的故事。作品以普通小镇家庭女性斯泰拉浓缩的日常生活场景为背景,描述了夫妻、恋人和亲人之间难解难分的心理和现实纠葛,以敏感而精准的笔触,记录了不同阶段中女性的自我抉择以及对爱的体验如何转变,反映了女性的心理变化及成长,弘扬了女性特质和美德,肯定了女性的独立意义。作品中的描述与现实生活如此接近,有益于帮助读者从中受到启发,引起女性自我认识及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现实的思考。
本文以《苔藓》的中文译本为研究对象,抽取、归纳和分析散见于文本中的生态女性主义元素,从生态环境、人物关系和特定意象三个方面对作品中呈现的父权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解构叙事进行分析,挖掘作品中隐藏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父权中心主义主张男子在家庭、社会中的支配性特权,造成男性和女性、男性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体系,形成了人类社会最大的不平等:男性是“自我”,处于权威、统治地位,掌握着话语权,而女性和自然变成“他者”,处于劣势、服从地位,“失语”成了女性的标签。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正是为了改变女性和自然的“他者”地位而生,是西方女权运动和生态环境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既是女性的,又是生态的[2]。它强调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反对物种歧视和性别歧视,批判柏拉图式的二元论造成的男性以主人的心态对女性、自然进行压迫的父权中心主义文化价值观,提倡以整体性、和谐性、多样化和相互依存的生态原则为思想基础,消解男权等级制的意识形态,构建平等的男女关系以及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作品中父权中心主义的解构叙事
《苔藓》以独居在农场里的家庭女性斯泰拉的日常生活为场景,叙述随着已分居多年的丈夫大卫依照惯例在每年夏天前来拜访居住在附近养老院的岳父而展开,一起随行的有大卫的女友凯瑟琳,一位顺从、柔弱和敏感的女性。一天的时间,恰似斯泰拉整个生活的缩影。以斯泰拉为中心展开的叙述是日常琐事,与大卫以老朋友的姿态叙旧聊天,与凯瑟琳毫无顾忌地愉快交谈,与那只名叫大力神的猫平等相处,与父亲之间的温情交流,与朋友之间的坦诚相处,与养老院的其他人之间的友善问好。作品正是以寻常人都有体验的普通日常生活为切入点,深入探析人物心理,揭示统治人类社会的父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在多处体现出了对父权中心主义的审视和批判,并以高超的叙述技巧不着痕迹地将生态女性主义意识一点点地渗透其中,改变女性和自然被迫接受的“他者”和“边缘化”地位[3],最终完成对父权中心主义造成的二元对立关系的消融和解构。整部作品通过解构父权中心主义,以精准自然的叙述展示了女主人公在对自我及和谐生活的追求中所付出的坚持和努力,传递出了尊重人的自然性以及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思想,唤醒读者的生态整体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恢复女性长久以来被压抑、扭曲的自然天性,试图建立一个物种平等、两性和谐和具有包容性的多元社会[4]。本文拟从生态环境、人物关系和特定意象三个方面分析《苔藓》中对父权中心主义的解构叙事,揭示作品中呈现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一)从生态环境角度对父权中心主义的解构
1.自然环境。女主人公斯泰拉独自居住在位于休伦湖白垩岩上的老房子里,种植蔬菜,采摘水果,自制果酱,作品以农庄为背景,与生产联系在一起,更有利于反映女性与自然的亲密关联、和谐共处模式。故事中的两位男性,已与斯泰拉分居的丈夫大卫住在城里,她的父亲生活在养老院。独居环境的设定暗示,在女主人公的家庭生活中,男性权利和秩序被解构,女性边缘化的他者地位得到了逆转,解除了压迫和统治,取得了独立的身份和地位,有利于女性自我意识的树立。
2.社会文化环境。独居在休伦湖畔的斯泰拉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社区有多样化的正式或非正式团体,如历史学会、戏剧阅读小组、教堂合唱团和制酒人俱乐部等。这些都展示了平等、自由和多样的社会文化在这里蓬勃发展。为斯泰拉在精神上追求“自我”的身份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这些团体里,她接触到五花八门的人群,有退休到此的老年人,有背景各异的年轻人,有本地的牙医,有会织布的女人,也有同性恋,这些人都成了她的朋友。作品中斯泰拉的表述“现在我们这儿宽容得出奇啊……我们并不是非要男女搭配。这对我们这些被淘汰的老婆们来说挺不赖的”[5]。宽容和多样性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具体内涵。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性取向和不同职业的各色人物从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形成对传统父权中心主义的解构。作者在叙述中打破了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消除了高低等级之分,成功地构建了一种多元的、尊重差异的、包容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文化氛围。正如卡拉·安布鲁斯特博士用生态女性主义认同的多元化观念进行的阐释:“人类与自然其他的差异以及人类之间的差异,包括性别、种族、族群和性取向等,不会再是冲突的根源。相反,他们有可能成为人类文化内部以及文化与非人类之间全新且更为稳定的关系的潜在来源。”[6]
(二)从人物关系角度对父权中心主义的解构
1.斯泰拉与大卫 。斯泰拉的丈夫大卫,是一个典型的父权中心主义者的代表,多处细节描写都能体现这一特征。首先是对自然的态度,以他的视角对斯泰拉居住环境的描述中,“光秃秃、灰色、旧、不结实”等词语显示出大卫与自然对立的立场——批判、降格自然。他将黑莓的藤称作是带刺的灌木,认为它们该被清空,烧掉,以腾出地方来停车。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父权中心主义的延伸,将自然视为“他者”,希望统治自然、压迫自然,最终必将导致破坏自然。而他眼中的斯泰拉:“矮胖的白发女人,穿着牛仔裤和脏兮兮的T恤。”根据他的判断,“这些衣服下没有穿任何支撑或束紧她身体的东西”[5]39。对斯泰拉外形的嘲讽,是在掌握了绝对控制权的二元关系中,大卫贬抑女性的表现。他把斯泰拉的自然衰老解释为她对自然老化的逆来顺受,甚至更糟。“就有一种女人到了这个年纪,非得从女性的外形中挣脱,炫耀起满身的肥肉或者难看的皮包骨头,长起鼓突的疙瘩和脸上的毛发,拒绝遮挡住苍白的、青筋暴突的腿部,而且对此几乎是沾沾自喜,好像这就是她一直以来的理想似的。彻头彻尾就是些憎恨男人的女人嘛。”[5]40大卫在完全主观定义下对女性自然衰老的毫不留情贬抑与批判,把人的衰老这一自然现象理解为女性对男性的憎恨。在主观意识中设立起了双方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体现了父权中心主义社会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控制,男性完全以自己的意志建立的审美标准及要求,迫使女性服从,来成就其自我优越感。同时也暗示出男性无视自然与自然规律和希望彻底控制自然的欲望。而“现如今,你还不能大声说出这类观点”[5]40这句话暗藏深意:“现如今”暗示时代不同了,女性的觉醒和反抗在悄然撼动着父权中心主义统治地位。另外一个事实同样证实了这一点。在他第一次背叛婚姻,逗弄住在附近的一个有夫之妇时,他依然认为只要还能感受到这份对于她的好意和温柔,他那隐秘的个人行为应该是在她的祝福底下完成的。大卫甚至认为男性可以控制女性的意识和思想,只要是男性的决定,女性都应该无条件服从,不该违抗。这是完全处于占统治地位的男性对女性的驯养意识,没有丝毫的平等、尊重可言。再到多年后,大卫带女朋友来拜访斯泰拉,与斯泰拉倾诉他的感情纠葛,将新女友的私密照片放在斯泰拉处,都是父权中心主义产生的男性优越感的表现。表现出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完全是男性单方面的主观选择,无论爱情还是婚姻,都是男性的施舍,不以女性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完全的以男性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无视平等,无底线地压迫女性,必将视自然和女性为“他者”,形成与男性“自我”的二元对立。
在处理斯泰拉与父权中心主义者大卫的关系时,作品中体现出女性与自然相同的包容性特点。斯泰拉与丈夫分居后,自然以农场的形式接纳了她,她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中经历了蜕变与成长。面对背叛,出乎丈夫的意料,她并不认为自己与他是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必须依附于他,而是通过分居的方式、摆脱父权中心主义在家庭中对她的压迫和控制,为自己争取到了公平和尊重。祛除衣服下支撑或束缚她身体的东西意味着女性觉醒后,主动解除男权文化的审美标准对身体的束缚,采取与男性平等对话等方式打破被父权文化控制的生活秩序,回归到自然的女性本色状态,摆脱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从父权制中解放出来,与自然建立亲密和谐的关系,追求自由与独立。
多年后,“他搂住了斯泰拉,他们拥抱了,两个人都是真心诚意的”。“他们过去常说些辛辣、伤人的话,说的时候偏要假装挺开心,心平气和,甚至故作亲切状。如今,这种一度是伪装的语调渗进了他们所有尖锐的情感,被吸收了,深入心底,而那份辛辣虽然还在,却显得陈腐、平庸和流于形式了。”[5]67斯泰拉与大卫坦诚的交流、真心诚意地拥抱以及大卫对本色的斯泰拉油然而生的欢喜,暗示父权中心主义如一道枷锁,控住女性思想与身体的同时,也制约着男性对自我的认识,让男女两性处于刻意的、不自然的关系对立状态中,都无法享受真正的自由。而“陈腐、平庸和流于形式”是对父权中心主义的批判性认识,也暗示着它会走向终结。在作品中,大卫与斯泰拉之间关系的转变体现在了日常生活中平等、友善、和谐地相处,此处通过打破二者的对立关系实现对父权中心主义的解构。
2.斯泰拉与凯瑟琳。凯瑟琳是大卫的女友,与斯泰拉散发出的自然健康的气息不同,“凯瑟琳比她高出不少,高挑、瘦弱、骨感,满头金发,皮肤细嫩,以至于根本不能用化妆品,而且动辄由于感冒、事务或者情绪而发红……她水汪汪的蓝色眼睛,那颜色浅得好像都无法承受日光……”[5]41美貌、脆弱和病态的凯瑟琳代表的是父权中心主义社会中,受男性驯养、控制和压迫的女性典型。她在男权的统治下,脱离了与自然的密切联系,身体和精神都印上了男权文化的痕迹,成了男性的附属品,丧失了自我,即使是在抗议的冲动下做出的反驳,依旧显得很温顺,这是女性失语的典型表现。很明显,顺从并不能改变女性所处的境况:大卫将车停靠在黑莓灌木旁,“他停得离黑莓灌木太近了——对凯瑟琳而言太近了,她刚从副驾驶座挤出车门,立刻遇到了麻烦。“凯瑟琳穿的蛛网似的棉质长裙被黑莓灌木密密麻麻地勾住,她没完没了地摘着钩子,试图脱身”[5]40。斯泰拉为其解围,建议大卫多给凯瑟琳留点空档,解除其窘境。狭小的生存空间反映了成为男性附属品的凯瑟琳不但没有得到男性尊重与爱护,反而随着脱离了拥有自主意识的女性群体,与自然亦形成了对立的关系,失去了女性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能。使自己陷入窘迫的境地,而这种境况的改变完全取决于男性的主观意志,处于失语地位的她失去了自我选择和控制的权利。
斯泰拉与凯瑟琳相处得十分和谐。独立让她拥有了自由的意志,她选择以平等、尊重的方式对待凯瑟琳。她没有因为大卫男性意志的操控而让自己陷入与他人对立的矛盾关系中。她如朋友般接纳、照顾凯瑟琳。引领她接触自然,感受自然的启示,勇敢地追求自我。斯泰拉居住的环境给了凯瑟琳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激发了她潜藏的热爱自然的女性本质。文中多处用“可爱”一词来描述凯瑟琳对自然事物的感受,暗示并建立起她与自然潜在的友好关系。作品中,在波浪的启示下,凯瑟琳长期被压抑的自我开始觉醒。她告诉斯泰拉:“我觉得我生活中要有变化了。我爱大卫,但我淹没在这爱中太久了,太久啦……我想,波浪永远永远都不会有尽头。所以我明白了,这对我来说是个信号啊。”[5]55这些细节印证了女性与自然生来具有某种潜在的联系,在特定的条件下,自然会成为女性觉醒的催化剂,能够给予女性心灵的指引和心理的纾解,启发女性挣脱男权社会的制约和束缚,追求女性自我的独立和平等[7]。在斯泰拉与凯瑟琳的关系处理上,与自然的共通性和自然赋予女性的包容性解构了二者由于父权中心主义而引起的对立,有力地遏制了男性意志的恶性膨胀。
3.斯泰拉与父亲、护理中心的弱势群体。斯泰拉的父亲,由于年迈体衰,生活已不能自理,与其他老年人一起,居住在休伦湖附近的养老院里。在斯泰拉与大卫一起去探望他的时候,父亲与大卫有许多共同的语言,这些关于人类工业文明的对话,暗示着父亲与大卫属于同一阵营,同属父权中心主义的代表。尤其是斯泰拉提到如果父亲知道她与大卫的事情,一定会站在大卫那一边,也证明了这一点。
面对体力上已经处于弱势的父亲以及其他护理中心坐在轮椅上的人,斯泰拉并没有丝毫控制、压迫、排斥或者贬抑的欲望,即使父亲作为父权中心主义的代表与大卫站在一边,她也以平等、包容和尊重的心态对父亲表示理解,通过行动践行了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压迫的思想。她轻柔地搂住父亲的脖子,用女性温柔的方式来表达对父亲的爱,她以圆融、柔顺的姿态关注这个弱势群体,举止温顺优雅,声音娴静,在他们面前,以她自然的女性本色与他们平和相处。这部分的描写充分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和谐共处的生态思想,同时充满了对女性自然美德的赞誉。
4.斯泰拉与大力神。大力神是斯泰拉养的一只姜黄色公猫。作品中赋予了它人性化的描写。它睡眼蒙眬地出场,耳朵打架撕碎了,在斯泰拉领着大卫和凯瑟琳一个接一个沿小路进屋时,斯泰拉因它没有动弹跟进来而以亲昵的口气骂它“懒畜生”,文中的另一处描写,“晚餐期间,大力神一直在桌子另一头的第四把椅子上睡觉……”[5]56“桌子的另一头”和“第四把椅子”这些字眼强调出大力神得到的与人类一般的平等对待。表明在斯泰拉认知里,大力神是跟其他人一样的存在,她将它视为家中的一员。作品通过人类与动物之间相处的一个简单细节描写,打破了父权文化中人类与其他物种的二元对立状态,传递了一切物种没有等级之分而皆为平等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三)从特定意象角度对父权中心主义解构
1.苔藓。大卫拿给斯泰拉的照片,是他的新女友。“地平线上远远地有一堆平放的乳房。前景是叉开的双腿。双腿大大地打开——光滑、金色、盛大;一对倾倒的石柱。当中是那团她称为地衣或苔藓的黑色毛丛。不过实际上更像一只动物的深色毛皮,脑袋、尾巴和爪子都被砍掉了。某只倒霉的锯齿动物深色的、丝绒似的毛皮。”[5]51苔藓没有根和维管束,喜欢有一定阳光和潮湿的环境,从形态特征和生长习性两个方面都极其符合女性私密之处的特征,但脑袋、尾巴和爪子都被砍掉的倒霉动物隐喻着女性失去了自由和生命力,已沦为男权社会的玩物。这是斯泰拉初次看到照片时的评价。当大卫离开后的一周,斯泰拉在清理起居室时,发现这张塞在窗帘后面的照片,“因为躺在阳光中,照片有点褪色。照片上那团黑色毛发已经变成灰色。一种蓝灰色,或者绿灰色。胸部的轮廓线已经褪掉。再也看不出腿是腿了。黑色变成灰色,变成植物柔和、干燥的色泽,这植物神奇地从岩石上得到滋养”[5]68。女性身体由看似苔藓到成为苔藓这一转变,暗示着女性一定能够脱离男权社会,重新建立与自然的亲密联系,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从自然界获得滋养,与自然相互依存,交融共生,获得新的生机。
2.起居室。作品前部分和结尾处都有关于斯泰拉居住的房子的描写,房间从大卫来时充满生活痕迹的混乱景象到他离开一周后秩序井然、赏心悦目的新状态,不仅仅形成前后文本结构上的简单呼应,也是在完成对一系列父权中心主义造成的二元对立的解构后,新的生活秩序得以建立的表征。
3.灯塔。文中两次出现“灯塔”。第一次提到是斯泰拉告诉凯瑟琳她在写一篇关于老灯塔的东西。她把远处的灯塔指给凯瑟琳看。“你朝窗外看,看到最远那里,就可以看到它了。”[5]43第二次出现在大约一周之后,斯泰拉在清理起居室时发现大卫把照片藏在起居室长条形窗子的一角,在窗帘后面,也就是通常站着看灯塔的地方。灯塔,在西方的语境里一直都是有象征含义的。灯塔是汹涌大海里的指向灯,给远航的船只以方向;灯塔也是守望者,它不灭的明灯给迷茫者以希望。在文学作品中,灯塔的意向大量地存在,灯塔通常具有指引的意象。可以带给人目标和希望,指引人走向正确的方向。在斯泰拉的生活里,灯塔就是自由、平等和和谐的象征,是她追求自我的精神向导,让她能够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同时,她也把这一向导传递给了凯瑟琳,启发更多受父权文化统治和压迫的女性觉醒,从而改变女性的失语地位。
4.蒂娜。蒂娜这个形象在文中并未以真实的身份出现,只是在经由大卫的回忆、想象和推测等一系列的心理叙述中完成构建的。作品用了相当的篇幅以大卫与斯泰拉交谈以及给蒂娜打电话等情节呈现出这一意象。大卫与斯泰拉交谈时,对蒂娜的描述用到了诸如“坏丫头、变野了、小巫婆”之类的词语,但是他却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个女孩,如他自己所说的“她要索我的魂呐”。晚餐时,他看似兴致勃勃地与斯泰拉和凯瑟琳聊天,手指却一直在木餐桌底下描着蒂娜的名字。饭后急切的去电话亭打电话给蒂娜却未能如愿接通的过程中,他心中的猜测和心情的急剧变化,“他手指颤抖,掌心冒汗。腿、腹和胸部都充满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5]60。电话响起的第一声铃让他的五脏六腑都沸腾起来。哪怕他知道蒂娜这时已经或一直都在背叛他,他觉得自己会发出卑微的哀求,他把自己比作受难者,必须放弃同情,断绝尊严,自己对付灾难却心甘情愿。这些心理刻画体现了一种男性对异性的欲望、依赖、膜拜甚至对自我的悖逆。作品正是通过这部分描述彻底揭示男性在本质上与女性的相似之处,也会在异性的吸引下做出相同的反应而脱离其有意识地构建的父权中心主义权威。体现出男性与女性从生理本质上的平等,都是会受情感支配的生物。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此刻的迷恋终究会随着蒂娜被男性驯服,被社会打造成一个洗衣店里被孩子缠着的妇人这样的女性形象而消退。那时他将再换个人。作品此处暗示了男性潜意识里事实上也渴望拥有平等的两性关系,但父权中心主义社会违背了自然的人性,妨碍了两性关系的正常发展,使得男性不断地在选择与放弃的重复中寻求自我存在的意义。
三、结语
《苔藓》通过生态环境的刻意设定,人物关系的和谐处理、特定意象的巧妙蕴含,在日常生活细节刻画中体现了对父权中心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人类之间的二元对立体系的批判和解构。作品以女主人公斯泰拉为中心展开叙述,她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幸与窘况,在寻求自我的过程中,坚信水流的力量——能把坚硬的铁丝也磨光。凭借自然赋予的女性美德,以如水一般温和的方式,大地一般包容的心态,结合自我的主动选择与自然的启示,一点一滴地渗透、瓦解生活中的父权社会秩序,抵制压迫与歧视,遏制父权统治的扩张。成功地解构了传统的父权中心主义社会文化,建立和谐的新秩序。整部作品传递了反对压迫、追求人与自然、人类之间平等尊重、相互包容、和谐共处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8]。激发读者对男权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改变自然和女性的他者地位,建立一个物种平等、两性和谐、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包容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社会。
[1]姜欣,时贵仁.爱丽丝·门罗的生态女性书写[J].当代作家评论,2014(4):178-184.
[2]格蕾塔·戈德,帕特里克·D.墨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和教学法[M].蒋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68.
[3]戴桂玉.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主体身份研究——解读美国文学作品中主体身份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76.
[4]STURGEON N.Ecofeministnatures:Race,Gender,Feministtheoryandpoliticalaction[M].NewYork:Rout-ledge,1997:209.
[5]爱丽丝·门罗.爱的进程[M].殷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6]高楷娟,付小兰,聂潇潇.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看《他们眼望上苍》中珍妮的婚姻观[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5(3):105-108.
[7]吴琳.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82.
[8]刘春伟.20世纪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4:47.
责任编辑:罗清恋
Deconstruction of Androcentrism in The Mo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KANG Qian
(Key Demonstration Office,Chongqing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 College,Yongchuan Chongqing 402160,China)
The Moss is one of the short stories written by Alice Munro,the 2013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In The Moss,the author indicates strong ecological feminist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ve narration of Androcentrism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s,and specific images.It is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 its feminist objectivity,but also integrat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ism to approach Munro’s short story The Mo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feminism.This approach is positively meaningful for arousing readers’re-examination and critique of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and evoking people’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and establishing an ideal society of equality,tolerance,harmon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logical feminism;Androcentrism;deconstruction;The Moss
I106.4
A
1673-8004(2017)01-0040-06
10.19493/j.cnki.issn1673-8004.2017.01.007
2016-10-31
康茜(1982— ),女,山西忻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