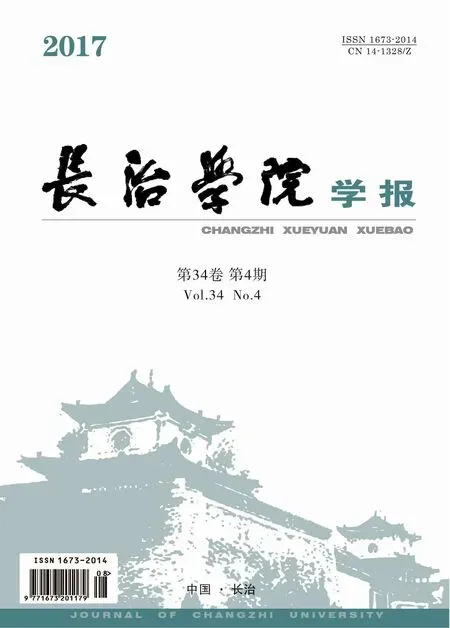“画里”“画外”话《野草》
——评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
任 慧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画里”“画外”话《野草》
——评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
任 慧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张洁宇对《野草》的“细读与研究”,师承孙玉石先生“接近诗美”的道路。但其并未在师辈“影响的焦虑”下亦步亦趋,而是从“自画像”的角度进入《野草》文本,由此将孙玉石所谓“审美”与“求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化为“画里”之象与“画外”之史,并以“中国现代解诗者”的身份解读散文诗集《野草》背后的“诗情画意”,可谓自生别趣。
《野草》;“自画像”;《独醒者与他的灯》
《独醒者与他的灯》一书,首先从文本的微观研究入手,对《野草》(包括《题辞》在内)的24篇散文诗,一一进行了解析与研读;在审慎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两篇具有“导论”性质的论文:《审视,并被审视——作为鲁迅“自画像”的〈野草〉》、《“诗”与“真”——〈野草〉与鲁迅的现代文学“写作观”》,以此提炼出全书的整体性研究思路和所讨论的核心问题:《野草》作为鲁迅的“自画像”性质。如是,张洁宇将既有研究成果“画”进个体经验的熔炉,以此为《野草》研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气息。
一、“画里”之象
脱胎于鲁迅创作中“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张洁宇从“审视,并被审视”的角度出发,认为《野草》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观察者的鲁迅和一个被观察着的‘自我’”[1]2。有藉于此,张洁宇在专著的首篇文章中就创见性地提出了“她之《野草》观”,亦即《野草》作为鲁迅的“自画像”性质。
循着这一整体性理解,反观《野草》的单位意象,不难发现这组“自画像”首先是以“夜”为底色的。这并不仅仅因为《野草》以“秋夜”开篇,就奠定了一种黑暗的基调,关键在于,这里的“秋夜”与《希望》里的“暗夜”、《好的故事》中“昏沉的夜”,甚至《死火》中的“冰谷”的象征性所指相同,不只存在于鲁迅的外部,同时也指向鲁迅内心的冰冷、严酷。在《独醒者与他的灯》一书中,作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遂淋漓尽致地剖析了鲁迅“身外”的暗夜与“身内”的暗夜,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深刻了“自画像”的精神意蕴。
其次,“枣树”、“笑声”、“影”以及“过客”等意象作为“画里”的主体,始终都离不开一个“黑夜闯入者”的形象。“野草”的精魂渗透其中,大致可视为鲁迅以沉郁笔墨描画出的自我形象的具体化。由此,它们往往可以被赋予重新阐释的可能性,进而为《野草》的审美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范式。
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张洁宇以“自画像”一说,对《秋夜》中“两株枣树”和“笑声”两个难点做出的别解。面对“两株枣树”引发过的讨论、质疑甚至批评,张洁宇倾向于将其看做“鲁迅式”的修辞方式,并以“自画像”一说阐明了“两株枣树”所奠定的对立而又统一的基调:“这是同名同种、相邻而立却彼此独立的两棵树,它们之间合一而又分立的奇特关系,正如一个画家与画布上的自画像相互面对。”[2]3在这里,张洁宇还注意到一个缝隙——枣树的意象只在篇首开头以成对(“两株”)的形式存在,而后文所有提及枣树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单数了。按照“自画像”的说法,二者从各自独立到一体共名,或可以理解为作为“画家”的鲁迅和“画上”鲁迅之“审视”与“被审视”的完成了。类似地,《秋夜》中的“笑声”也因违反日常的语言习惯和思维逻辑而成为难懂的又一细节,张洁宇也以“自画像”的特殊角度做了新解。果不其然,“把《秋夜》理解为鲁迅的自画像,理解为他以一个自我的眼光去审视和呈现另一个自我的实验,这两个细节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3]46
除此之外,还有《影的告别》中的“形”与“影”,《过客》中的“老者”、“小孩”与“过客”:几个意象(形象)合在一起时,构成一个正常的人的形象;而在某种奇异的时刻——实际上是鲁迅内心的两个“我”在进行思想搏斗的时刻——他们又成为彼此分开、对话的个体,导致“我——我关系”[4]228产生断裂。在这里,附生于“形”的“影”也许可以看做画家笔下的“自我”,而当这个“自我”完成之后,他与画家本人之间就有了一场语言的对弈和辩驳。
二、“画外”之史
正如“《野草》并不是拔地而起的孤立的高峰”[5]231,张洁宇的《野草》研究亦非无根之萍。以“自画像”这一问题意识为中心,张洁宇在进行“画里”的审美研究、尤其是意象研究的同时,还秉持学术“求真”的态度,对“画外”的史料做了大量的搜罗和博采。详实之至,近似于“竭泽而渔”[6]6。在这里,张著中“以史为证”的“开放性细读”,既避免了走上“自说自话”的研究窄道,又同英美前期新批评理论所倡导的封闭式文本细读方法区别开来。
从《野草》的“发生学”角度出发,张洁宇将这组“自画像”置于当时的文化、历史场域中,深入考察了鲁迅“身外”的暗夜与“身内”的暗夜之联系。比如,在解读《影的告别》与《求乞者》两篇散文之前,就以鲁迅的日记、与友人的通信等史料为证,考察了“兄弟失和”事件前后的鲁迅心迹;再比如,在解读《野草》的最后两篇散文诗,也就是《淡淡的血痕中》与《一觉》时,同样考虑到其时“女师大”事件对鲁迅创作心理的影响。正如张洁宇所道,“当他(鲁迅)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更多的事情,比如爱情的降临、‘华盖运’的烦扰,‘女师大’事件逐步升级的斗争,直至‘三一八’惨案的血淋淋的事实,以及直奉之间的军阀混战所带来的各种见闻,等等,都一一汇入了《野草》的写作之中。”[7]303由此可见,处于《野草》时期的鲁迅,“身外”是动荡大于平安,“身内”亦是痛苦高于幸福,将“秋夜”视为“自画像”的底色并不为过。
诚然,《野草》的诞生,是鲁迅在特定历史境遇下的个人化表达。但是,张洁宇的“《野草》观”是“发展”的而非静止的,亦即将其视为鲁迅创作链条中的“中间物”。后期新批评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指出,文本细读的研究,应该具有一种“透视主义”的功能,也就是说,“把诗和其他类型的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不同时代都在发展着,变化着,可以互相比较,而且充满着各种可能性。”[8]36在《独醒者与他的灯》一书中,张洁宇就常常以某个线性的时间点为圆心,以鲁迅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为半径,将其小说、散文、杂文甚至翻译工作统统划归到研究“圈”里,形成鲁迅的“自身互文”。譬如,在《鲁迅的1924年9月24日》一文中,张洁宇就以“1924年9月24日”为中心,做了“散点透视”:先是对“高产”的一天做了“产量”梳理,其中包括三则散文诗、一项翻译,还有一封长信;后又将时间点回溯到9月15日,再以期间9天的“沉郁”反观9月24日创作的“高产”,“画外”之事不得而知。
可以说,《野草》的“发生”和“发展”,都在不同的侧面再次印证和深化了张洁宇的“《野草》观”:与其说《野草》是鲁迅写给自己的,毋宁说《野草》是鲁迅写自己的。“‘写给自己的’往往是日记,而‘写自己’、‘写出自己’,则是自叙传,是自画像,是创造出一个可以变形但必须完整的自我形象。”[9]5值得注意的是,张洁宇在这里并非将《野草》视为对过去时态的总结,而是“以面向未来的姿态”[10]来理解《野草》,同时认识到了它对于鲁迅个人思想清理和写作转变的重要作用。从“野草”到“无花的蔷薇”,从散文诗集的“内向型写作”[11]23到后期杂文“激烈的‘呐喊’”,借助张洁宇对于《野草》中“自画像”性质的发现,无疑最能把握住鲁迅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文学思想,也有助于读者贯通地观察和理解鲁迅一生的文学写作的历程。
三、“画像”别趣
除了在研究方法上将“审美”与“求真”具体化为“画里”之象与“画外”之史以外,张著的独异之处,还表现在作者以“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经验对《野草》研究的“再创造”上。换言之,正如《野草》是鲁迅的自画像,《独醒者与他的灯》亦是研究者的自画像,其间隐含的微妙,恰是张洁宇作为“中国现代解诗者”的别样“诗趣”。
对于鲁迅的“诗才”,胡适曾有过很高的评价。[12]300后来的文学史家也认为,鲁迅的新诗作品“拒绝直白的说理,追求意境的幽深,其象征手法的娴熟,以及驾驭白话的能力,却非同期半词半曲的‘放大的小脚’可比。”[13]29而散文诗集《野草》的难解之处,无非就在于它的“语言被撕裂了”[14],以至于有很多逻辑上无法解析的“诗质”存在。由此看来,想要体悟“鲁迅式的表达”,进而切入《野草》内在的精神肌理,研究者于诗学方面经验和修养,自是深得其妙的应有之义。
张洁宇深受孙玉石先生的影响,在鲁迅研究与中国新诗研究的道路上笔耕不辍。早在2003年,就出版了《荒原上的定向——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诗歌研究》一著,加之其近年来对废名、闻一多、林庚以及姜涛等的诗学研究颇具代表性,遂逐步奠定了她作为“中国现代解诗者”的身份。
于是,有了“触着”鲁迅“诗才”的这一独特视角,便近乎获得了一把开启《野草》隐秘之门的神钥。比如,站在《秋夜》的“阅读史”上,张洁宇在论述“枣树”于鲁迅而言,是“在”而“不在”的存在时,就以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为例,指出鲁迅的“枣树”正如“南山”一样,“要在注视者准备好一种悠然的心态时才能够‘看见’”[15]40;尤其,在细读《野草》中唯一一首“拟古的打油诗”《我的失恋》时,张洁宇就在孙玉石、孙席珍等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解,认为鲁迅对四种礼物的选择,更多的是从“押韵”的角度考虑的;最值得称道的一处解读,出现在张著对于《风筝》中“悔恨”之情的体悟上。张洁宇以“只要想起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这一句诗,来表达现代人对于“悔”的普遍体验。而这首诗恰恰出自当代诗人张枣的成名作《镜中》,该诗同样建构了“镜中”与“镜外”的两个“我”,以此表达现代人对于自我的诘问。张洁宇以此诗作比,实在是切中肯綮。
结语
《野草》作为中国现代“散文诗中艺术造诣最高的一株奇花异卉”[16]222,历来是鲁研界热衷于阐释甚至“过度阐释”的对象。然而,正如著者用“自画像”一说找到了与《野草》“对话”的有效方式一样,张洁宇的“细读与研究”也与前辈研究者之间形成了内在的“对话”。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部著作里,总是不乏“我认为”、“我个人的理解是……”、“我比较赞同……的理解”等表现个人态度的句式。这固然有“课虚坐实”[17]的危险,但这种未被统一的个性和态度,恰恰是对“学界暮气”[18]的反驳。
诚如鲁迅自陈,“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19]119,而张洁宇自述“愿意把他当做一个同龄的友人,感受他,理解他”[20]329。一个是于“暗夜”中踽踽独行的写作者,一个是于文海里勇作孤舟的执笔人,《野草》的纽带就这样将两位独醒者牢牢拴在一起。坚韧如“野草”的精神,始终是属于一代又一代文学青年的“象牙之塔”,即使一灯如豆,亦能支撑着他们“越过黑暗/纵使黑暗重重”(张洁宇)。
[1][2][3][6][7][9][11][15][20]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张枣.亲爱的张枣[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5][16]孙玉石.《野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0]段从学.用“文学的”《野草》研究重绘鲁迅[J].鲁迅研究月刊,2015,(09):94.
[12]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13]胡适.尝试集·尝试后集[M].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
[14][18]孙郁.《野草》研究的经脉[J].鲁迅研究月刊,2013,(07):36-39.
[17]李有智.《野草》研究中的“课虚坐实”问题——试以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为例[J].中国图书评论,2014,(12):71-75.
[19]鲁迅.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 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史素芬)
I207
A
1673-2014(2017)04-0043-04
2017—04—08
任慧(1992— ),女,山东德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