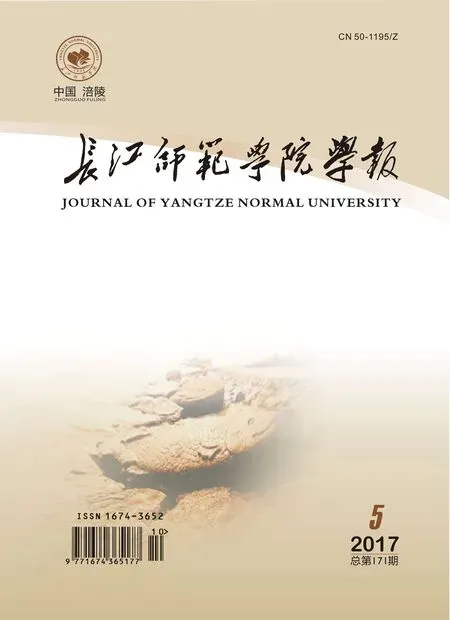“白话”的诗性本体意义
梁 平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重庆 408100)
“白话”的诗性本体意义
梁 平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重庆 408100)
人们对于胡适“白话”的作用,往往只从工具层面进行认识,未能察觉它的本体性意义,并且习惯将当时通行的“白话”加以封闭,造成与今天所称“口语”的隔离。“白话”应是一个广义的流动的称谓。白话无论是从“形式”的构筑还是“诗意”的承载来看,都具有本体性。面对新诗,我们应充分认识它自身的特质,深刻理解它所依据的社会语境,在坚守“诗意”这个最高原则的前提下,以宽广的胸怀善待新诗的多种可能性,并保持对“劣诗”“非诗”的高度警惕。
白话;口语;本体性;诗意
“白话”是五四“文学革命”的语言工具,这个工具首先从语言形态上造就了中国现代小说、现代散文和现代戏剧,并最终创立了具有现代性质的“白话诗”及“新诗”。当时的“白话”,是与“文言”相对应的一种语言称谓,是“现代汉语”的起始形态。从对称角度讲,“白话”该对应“文言”,“现代汉语”对应“古代汉语”,并且“白话”就是“现代汉语”(至少在现代语言之初是这样),“文言”就是“古代汉语”,这是没问题的。但是,由于在一定语境中人们的用语习惯不同,却造成了以上对应关系的错位。比如,我们说到今天写作的语言方式,通常用“现代汉语”这个称谓而不用“白话”,而说到古典文学的语言方式时喜用“文言”称谓而不用“古代汉语”。仔细考究,显而易见其间的不严密和别扭感。为了还原严密性和对称感,我们用“白话”来指称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语言方式。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白话”,事实上就是“现代汉语”,但又不仅仅如此,还特指现代汉语中的“口语”。现代汉语在不断书写的过程中,有些语言已成为书面语,有些语言则依旧沉落在口语层面,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新的口语还在不断增生。我们之所以如此看重“白话”(口语),是想对诗歌的全部语言基础给予足够的审视和尊重,并由此分析“白话”的诗性本体意义。我们看到,有些学者在强调诗歌格律化形式的本体意义时忽视了语言现实的全面性,他们着意于格律化对口语的提炼作用而推崇雅化的语言,这不但忽视了“白话”(口语)在新诗创立之初以及后来的本体意义,也忽视了“诗意”(不仅仅是格律化)对口语更为根本的诗化之功,并且遮蔽了新诗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白话工具的本体性
“白话诗”的创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国古典诗歌至唐代而鼎盛,尽管鼎盛之后是衰颓,是裂变,但由于古典诗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其内容渐趋沉稳,形式慢慢定格,最终陷入物质化、符号化的境地而难以动弹。内容上,“吾国之诗,虽包罗宏富,然自少数人外,颇病雷同。贪生怕死,叹老嗟卑,一也;吟风弄月,使酒狎娼,二也;疏懒兀傲,遁世逃禅,三也;赠人咏物,考据应酬,四也”[1]卷49白屋吴生诗稿自序;形式上,“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2]71。封闭的内容与形式,一方面限制了诗人内在气象的生发与吞吐,另一方面消弭了诗人艺术自觉的冲动和奔突。诗人们仰望着“格律化”这个神话,却麻木了“格律化”这个紧箍咒带来的疼痛。尽管后来有宋诗直到晚清诗歌的变革,但也只是在表达方式和局部的内容上进行调整、实验,始终未能意识到格律化形式的根本制约。宋人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物质化追求,梁启超的“新意境、新语句、旧风格”,都不离既成的格律化框架,以致被讥讽为“学唐诗而不像唐诗”“旧瓶装新酒”等。当然,自宋以来的诗歌变革呼声和种种盲目的诗性涌动,尽管未能冲破格律形式的桎梏,却也让人们渐渐逼近了突破的临界点。可以说,是宋以来无数诗人的相继努力,把期望中的“新诗”上升到了瓶颈部位,即将呼之欲出。而真正突破这个瓶颈让新诗落地生根的,还是胡适。
如果说晚清以来的“新诗”倡导者和探寻者是借“诗界革命”之名实则致力于解决社会政治体制而漂浮于诗歌机制表面的话,胡适则始终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与态度而专注于文化教育这个“底层”的培育。因此,相较于他的前辈,胡适有着明确而坚定的文化本位观。而文化要通行,或者说要显出文化的精义,就须得占领和发掘诗歌这个阵地[3]18。这正是胡适决意“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作先锋去攻打“诗的壁垒”[4]29的内在逻辑。胡适痛感唐以后的诗歌不“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也深明黄遵宪、梁启超等前辈诗人失败的教训,并受王国维文学进化观的启发,他最终意识到创造新诗的根本在于“诗体的大解放”。他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 ‘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3]295应该说,胡适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是,如何实现诗体的解放呢?“文的形式”主要包括体例与语言文字,而体例由具体的语言文字构筑而成,语言文字不变,体例也就难以松动。因此,胡适敏锐而又历史性地将目光聚焦在白话这种鲜活的语言上。作为一个实验主义者,在前人语言实验无法前行的地方,他别无选择同时也是高度自觉地认定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白话。他认为,文学革命必须分工具革新、方法引进和创造3个步骤,而当时的文学“还没做到实行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尽可不必空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步预备的功夫罢!”[5]287他进而说:“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新文学。若要造一种活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的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活的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3]19-20显然,胡适是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看待白话的,在这一观念指导下,他的 《尝试集》根本上还是古诗的体例,并且因为主张“说话要清楚”“意境要平实”,强调“意旨不嫌深远,而言语必须明白清楚”[6]。“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3]308,以致他忘掉了“诗之所以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7]。但是,将白话收入诗里,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文言中单音词居多,适合古格律的体例,音节容易与节奏相妥帖。而白话中双音词增多,它们的运用,容易打破稳固的格律,胀裂定型的体例。因此,正是因白话在古典诗歌内部的爆破,才有了格律的消散和体例的垮塌,一种以白话为支撑的新诗体才得以最终创立。这个新诗体,不是胡乱臆想出来的,它是自由精神的沉淀物和符号化,具有本体性质,而这个本体的确立最终是由白话来完成的,所以,白话本身就是这个具有本体性质的新诗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体意义不言而喻。尽管胡适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他更知道“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 ‘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能跑到诗里去”[3]295。因此,尽管胡适还只是将白话视为工具,但这个工具却具有本体意义。倒不是说胡适本身持有语言本体观,而是本着唯物主义观念,从客观效果上来说,白话具有本体意义。“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属于意识范畴,它们得有所附会才得以表达,被人感知。黄遵宪、梁启超之所以未能在诗中真正表达出自己的内心世界,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找到与内心相应的“白话”。“文的形式”包括主要文体、语言,如果不从它们寄寓的意味而是从视觉效果看,它们显然是一种物理性存在,具有物质性。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本体,这是起码的唯物思想。具体到胡适,“白话”这个物质化的工具具有本体性,当是无疑。但是,人们今天似乎已习惯将“白话”看成一种凝滞的语言形态,特指新文学运动时期通行的口语,但事实上,“白话”的口语属性本身一直在持续,其具体意指该与今天的“口语”相一致,只是具体的词汇及词汇数量有一些变化。我们现在依然说某某的文章中满是“白话”,不是指文章中充满了“五四”时期的生活语言,而是指当下的口语。所以,“白话”应是一个流动的称谓,现今的口语也该叫做“白话”。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讨论的“口语”就等于广义的流动着的“白话”。
二、现行口语的本体性
对于胡适从白话入手最终创立新诗的历史功绩,人们往往只从诗歌形式表面给以肯定,忽略了白话是新诗形式中最重要、最关键的组成要素之一。即是说,人们只是在抽象的层面上谈论“胡适之体”,未能将他所用的白话还原到具体的诗歌之中,并且将白话与诗体割裂开来,只看到新诗的外形,忘掉了这种外形得以产生的话语形态的根本作用。也就是说,对于“白话诗”,人们只关注这种外形参差的“诗”,却淡化了带来这种参差外形的“白话”。因此,人们眼中的胡适,不是一个生动而完整的形象,而是显得抽象,显得散碎。似乎只是在谈白话诗,不是在谈胡适,也似乎只是在谈白话的历史功劳,不是在谈胡适对于白话的合乎历史语境的发现和运用。也因此,人们对于胡适“白话”的认识,就停留在一般工具论的层面。王光明说:“胡适与陈独秀都未曾以本体的立场看待语言,他们都还是语言的工具论者。”[8]72“胡适在谈及语言问题时,就常常混淆了语言本体与语言运用的区别,认为语言是人们任意役使的 ‘工具’,没有看到它是一种超主体的、具有自己历史的现象,而只是从历史进化论的简单信念出发,把一切东西都一刀切成 ‘新’与 ‘旧’、‘活’与 ‘死’两种水火不容的世界。”[8]650没错,胡适自己也明言是把白话作为革新的工具,他也确实没认识到语言的超主体性质以及语言自身的历史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到白话作为工具的运用事实,却看不到这个工具对于新诗形式的物质化建设,进而认识到这个物质对于“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的激发与容纳,显然也是对另一层面的语言本体性的漠视。尽管胡适并未在自己的诗里真的表达出这种理想和感情,但后来实现了这种表达的诗人却显然是受惠于胡适在形式方面的开创之功。
除此以外,王光明在其书中还反复强调建立新诗的象征体系和文类概念。这固然是有识之举,是对新诗在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所进行的总结,是对目前诗歌混乱局面的一种忧心表达,也是对新诗发展方向的理想化设计,并且为实现这个理想而一直主张新诗格律化,可谓用心良苦,其情殷殷。但是,他的主张却存在明显的问题,其一,他认为格律化形式有利于强化诗性思维,增强诗歌意蕴,但是,他依然是在抽象层面上谈论形式,忽视了形式中语言这个重要的组成要素,既然形式具有本体意义,那么语言也应有本体的气息;其二,尽管他也注重“现代汉语”全部的语言实际,但因其形式的抽象化而切断了诗中语言与现实语言特别是口语的联系,持一种理想却又抽象的语言观。我们从中国诗歌史可以看到,由诗经而骚体、五七言诗,由赋体而无韵骈文,由古诗而律诗,由诗而词、曲,无一不体现出诗歌形式的变化,形式确实是各个阶段诗之为诗的自律性制约,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抽象地看待各个阶段的诗歌形式,依然不能忽视当时语言对相应形式的构建作用。人们习惯静态地对待已有的语言形态,似乎“文言”是一个一成未变的静物。事实上,语言确实有他自身的发展演变史,每个历史阶段的语言都有其不同的形态特征,其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生动的生命情怀,是语言带上这些信息和情怀一并创建了与之相应的诗歌形式。当然,形式一旦确立,就会反过来要求诗歌的内容及其表达,就是说形式对于内容及表达具有形而上的制约作用。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我用形式指代那种规定艺术之为艺术的东西,也就是说,作为根本上 (本体论上)既不同于 (日常)观念,又不同于诸如科学和哲学这样一些智性文化。”[9]17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形式就可以独自悬浮,可以摆脱语言这个基础。人们未能认识到胡适白话的本体意义,就在于将形式视为抽掉了语言的空架子,让白话在形式之外独自流散。王光明正是在这样的形式观念中,将诗歌视作一种封闭的存在,尽管十分看重语言的诗性转换,但实际看重的却是已经诗化的语言本身,将诗外的语言特别是口语悬置不顾。
事实上,口语是诗语的重要源头。诗歌在发展,诗中的语言也在发展,而根本的动力就是口语的生生不息。如果我们切断了两者的联系,诗语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会失去给养,日渐枯竭。没有口语滋养,诗语就会陷入独自空转的境地,最终沦为板结而空洞的符号。口语是诗语的母体。口语的本体性,由此可以再次见出。我们还注意到,将口语转化为诗语,不单是形式的作用,形式的作用只是这种转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并且不是最根本的部分。最根本的作用在于“诗意”、在于“诗意”主导下形成的诗歌语境,而诗歌形式不过是这个语境中的一个方面。“诗意”本身比形式更高,是诗歌中最高的本体。我们看到,古今中外,有丰富的各不相同的诗歌形式,具有相应形式的诗歌之所以都被称作诗歌,不是因为它们有自己的诗歌形式而是它们都表达了诗意。进而我们可以说,诗歌形式本身无所谓优劣高低,只要能适合表达诗意就行。形式本身会随着社会及语言的发展而变化,但诗意的要求却是永恒不变的。因此,无论什么语言,只要能融入诗歌的语境并妥帖地表达出诗意,就是成功的语言。比如目前比较流行却遭受多方非议的口语诗,其实并不错在口语入诗,而是某些口语诗营造的诗歌语境不浓郁,在口语之先没能将诗意酝酿成熟。事实上,口语若是进入了完美的诗歌语境,会自然转化成诗歌语言。这样的口语,既受到诗意的统摄,同时也是诗意的载体。口语与诗意同体并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语同样具有本体性。同时,口语会给诗歌带来更真切的生活信息,容易让人产生现场感,显得平易、亲切,让诗里充满丰富而会心的语感。相反,我们也看到,在人们自认为优越的诗歌形式中,无论语言多么精美、华丽、书面化,最终却可能成为劣诗、非诗。因此,王光明特别看重格律化的新诗,忽视了“诗意”这个最高的本体,实质上是把诗歌降格了。推而广之,新诗以来的“自由诗”“散文美”“口语化”中的某些拙劣表现,根本原因不在于形式不格律、语言不诗化,而在于对“诗意”的不严肃、不敬畏。实际上,“自由诗”“散文美”“口语化”中都不乏典范之作。
现代汉语是一种相对于古代汉语的语言形态,它既有自己的生成性,也有向外的开放性,所有的语言元素都可能成为它吸纳转化的对象,包括古代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等。它流动不居、生生不息,同时又有相对的稳固性。这种丰富而鲜活的语言现实应该成为新诗的语言资源,而不是将它们悬置起来,去臆想另外一套“天然”的诗歌语言。王光明在书的附录中说:“长期以来,文言完全在文人和官方系统里自我循环,造成了书写语言与口头语言的严重脱节,未能在民间流通语言中不断获得活力。”[8]649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将这种认识用于已成历史的古典诗歌,忘记了新诗同样需要口语的推动,这种认识就只拥有对历史事实的穿透力而缺乏对社会发展的远视力了。历史的教训应该成为我们回避的陷阱。“白话已经提供了新诗写作基本的一种需求,一个诗人不应该去怀疑一种语言是否已经可以达到表达的需要,而应该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用写作来创造出满足这种表达需要的语言”。[10]新诗历时尚短,谁也不能成为它的终极裁判。我们当然应有对新诗的努力探索和理想设计,但切忌归于一端。我们该做的,就是充分认识新诗的自身特质,深刻理解新诗发展的社会语境,在坚守“诗意”这个最高原则的前提下,以宽广的胸怀善待新诗的多种可能性,并保持对“劣诗”“非诗”的高度警惕。
[1]吴芳吉.吴白屋先生遗书[M].[中国台湾]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2]徐中玉.通变编[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71.
[3]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4]潘颂德.中国现代诗论40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29.
[5]胡适.胡适文存(二集)[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287.
[6]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J].自由评论,1936(12).
[7]梁实秋.读《诗的进化的还原论》[N].晨报副刊,1922-05-27.
[8]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650.
[9]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78.
[10]陈太胜.口语与文学语言:新诗的一个关键问题——兼与郑敏教授商榷[J].江汉学术,2004(6):10-14.
Poetic Significance of“Vernacular” in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LIANG P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8100,China)
People often perceive the role of Hu Shi’s“vernacular” only on the level of tool,but fail to be conscious of its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Besides,they are used to blocking the“vernacular” prevailing at that time,thus leading to its isolation from today’s“colloquialism” .“Vernacular” should be a generalized flowing term.Vernacular,whether from the“form” construction or“poetic” bearing capacity,are ontological.Facing the new poetry,w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and deeply understand the social context on which it is based.Under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the highest principle of“poetry”,we should treat various possibilities of new poetry with a broad mind,and maintain a high vigilance against“bad poetry” and“non poetry” .
vernacular;colloquial language;ontology;poetic
1207.2
A
1674-3652(2017)05-0098-04
2017-04-06
梁平,男,重庆石柱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志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