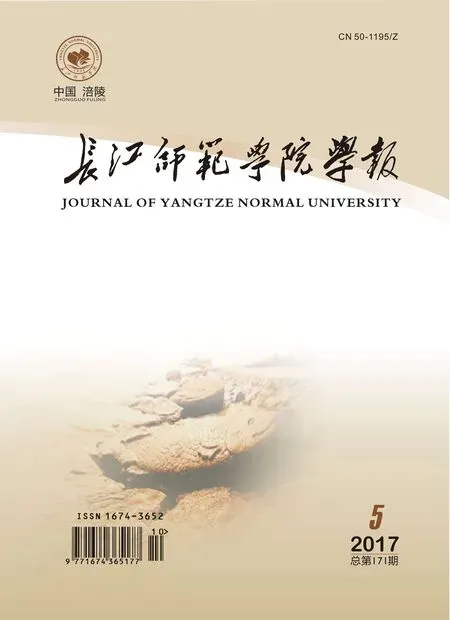重庆诗人梅依然诗歌创作论
——以梅依然诗集 《蜜蜂的秘密生活》为切入点
周 航
(1.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 2.重庆当代作家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
重庆诗人梅依然诗歌创作论
——以梅依然诗集 《蜜蜂的秘密生活》为切入点
周 航
(1.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 2.重庆当代作家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
重庆女诗人梅依然近些年创作力旺盛,写出不少好诗,在诗坛获得好评并产生了较大影响。通过对她新近出版的诗集 《蜜蜂的秘密生活》的解读,大致可探明梅依然诗歌创作的特征:首先,诗人以一个女人的姿态用诗意的文字来抵达内心世界,以触摸生命的存在感;其次,诗人力避宏大的虚空,在时间和生命的流逝中捕捉个体存在的意义;最后,从诗中隐现的哲思来衡量 (比如对死亡和爱情多层面的思考),诗人并非在浅表式地痛苦呻吟,而是以诗的针线缝补爱情、死亡与虚无的缝隙,并期待与读者灵魂的相遇。
梅依然;《蜜蜂的秘密生活》;死亡;爱情;存在感
一、引言
不需要了解“为什么”和“何必”
这些事物,仍然以时间的形式
消失在了黑暗的中心
——这是万物平衡的方式
——(梅依然: 《喻言》)
重庆女诗人梅依然近些年创作力旺盛,写出不少好诗,在诗坛获得好评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初看书名着实令人吃惊——《蜜蜂的秘密生活》,这与美国南方著名女作家苏·蒙克·基德(Sue Monk Kidd)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The Secret Life of Bees完全同名!如果是巧合,那么这事本身就让我十分惊讶;如果是诗人有意为之,那么我个人认为有一定的风险。为此,我特意问了梅依然,她也表示惊讶,说我是第一个问她这方面问题的人,她说确实受到那部小说的影响,不过她想用诗的形式作出来自生命体验的回应。
基德少女时代即受梭罗 《瓦尔登湖》和凯特·肖邦 《觉醒》的影响。前者的诗情和田园风情,后者的女性主义精神,以及美国南部文学梦幻与现实相结合的灵性探索的传统,都一道融入基德的成名长篇小说 《蜜蜂的秘密生活》中。小说以美国20世纪6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女主人公莉莉因孤独无助而离家出走以寻求心灵的休憩、安慰与解脱的故事。小说内涵丰富,融合了性别、民族、种族和历史等多种元素,关涉爱的疗伤和救赎,拷问了人性中的痛苦、快乐、梦想、死亡、尊严以及蜕变。整体上来看这部小说,女性主义立场是十分明显的,但从文学意义上讲,其中独特的个体叙事和生命感觉则更为人所重视。
我不知道梅依然的人生经历过一些什么,但她的内心肯定是无限丰富和充满诗意的。她刻意以国外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诗集,在此我不妨斗胆猜测其不畏撞车风险的某些原因。首先,诗人以一个女人的姿态用诗意的文字来抵达内心世界,以触摸生命的存在感;其次,诗人力避宏大的虚空,在时间和生命的流逝中捕捉个体存在的意义;第三,从诗中隐现的哲思来衡量 (比如对死亡和爱情多层面的思考),诗人并非在浅表式地痛苦呻吟,而是以诗的针线缝补爱情、死亡与虚无的缝隙,并期待与读者灵魂的相遇。以上几点,与基德的小说形成既明显又深刻的、不同文体之间的互文性关系,这无异于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而并非莫名的撞车之举。
二、作为“个人表达”的肉体存在
肉体:用想象与理解构建
这是美学——
我们进入它的内部
——(梅依然: 《想象与理解》)
梅依然的很多诗来得直接,来得坦然,“肉体”经常出现,而不是羞羞答答的“身体”或“人体”。或许,在她看来“肉体”更为及物,更有触摸的实在感,也更能直抵人性。她在200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女人的声音》,2013年出版第二部诗集 《女人书》,包括现在的第三部 《蜜蜂的秘密生活》,或许诗人都是在尽力“想象”和“构建”一间女人肉体美学的诗屋。其中的美学根基是来自灵魂深处的、个体的。不过,这种“个人表达”以及女人对身体的意识和觉醒并非从梅依然这里开始。现代以来的西方和中国对此早就划下了一道深重的哲学和诗学的轨迹,只是在现实和人性面前,这道轨迹仍需不断地重划和延伸。只是梅依然的女性“意识和觉醒”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以往基础上的剥离和新生。
我很想举出一首有代表性的诗来分析诗人对肉体的“进入”,然而发现这将是一场徒劳。诗中对肉体的迷恋超出我的想象,其与隐寓其中的存在感竟然浑然一体,如果将其强行剥离,就只能看到其中的某一侧面,正如盲人摸象那般。就此而言,这本身就成为一种不断增强式的“重复”,是不断燃起的火焰,浴火之后的新生或许要等火光全然熄灭之时。其诗中肉体之存在总与生命、死亡、爱情、性、愉悦、痛苦、精神、哲学等元素融为一体,在女诗人看来:“所谓女性美,是由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故作为身体含义的更为直接的肉体,就成为诗人进入诗歌和进入自由精神的有效通道,也成为切入现实的一道裂缝。“整日,我的肉体/徘徊在黑褐色的土地上/两条腿不知道怎么摆放/像一把剪刀/似乎能撕裂任何东西”(《五月的田野》),这让我们似乎突然明白了一点什么。肉体以及对肉体的思考 (包括爱欲)或许正是诗人用来对抗生活现实、真相的利器,而不仅仅是女性主义的卫道者。
黑格尔曾经在他的巨著 《美学》里阐述过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尽管他谈的是雕刻,却不乏当下的现实性意义。他认为精神性可以“在肉体中自为存在”“关于精神和肉体在各种情感、情欲以及其它(他)精神状态方面的较确切的联系,我们还很难把它归纳成为牢实可靠的原则”,故其提出“精神的肉体”之说,并以此作为一种艺术之美来进行探讨。大概诗人梅依然的写作姿态与此有很多相合之处吧。后来,写出女人“圣经”之作 《第二性》的波伏娃,从性别的角度对女人肉体和精神的存在作过全面的论述,使女人在现实和精神领域第一次能够真正地面对自身。从而,女性肉体不再是性别歧视的载体,而成为女性觉醒的诸多能够“彼此传递的暗语”(爱丽丝·史瓦兹语)。波伏娃的著述,使“女性世界”不再仅仅作为男性世界的参照物,而是大大增强了女性存在的主体性,女人的世界已然超越肉体而能够获得精神上的自立、自足。精神资源的获得,无异于给诗人梅依然展开了一方可供无限开垦和劳作的“荒原”——“我返回荒原/在那里/我将成为一座葡萄园的庄主/收割我的苦难和喜悦”(《博物馆》)。
1994年林白发表 《一个女人的战争》,1995年陈染发表 《私人生活》,这开启了中国“私人写作”“个人写作”的先河。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又给中国女作家们提供了一个“个人表达”的较为宽松的社会大语境。这股创作潮流强调女性叙事回归自我生命的内部,发掘自身主体的生命体验。这可能是中国精神领域女人正式敞开“肉体”的开始。不过,我们别忘了,林白和陈染最初都是写诗的,是诗歌提供给她们最早的写作经验和情感体验。我们更不能忘记,早在1983年成都女诗人翟永明就写出 《女人》组诗 (1986年 《诗刊》“青春诗会”发表)。翟永明在组诗开头的 《独白》中写道:“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我们不得不说,梅依然的诗歌创作或许正是这一渊源的延伸。同样地,我在她的诗中读到了奇诡,读到了惊世骇俗,读到了来自女人身体内部的呼唤、挣扎和立场。那些来自女人内心深处的秘密、凄怆和激烈,同样能让我再次感受到性别之下某种无奈的决绝。
正如翟永明所言:“我永远无法像男人那样去获得后天的深刻,我的优势只能源于生命本身。”于是,梅依然也是再次将肉体诗意化并满含期待:“我的肉体静静卷曲/像一只盛放 ‘过去’的器皿/等待打开/我嘴唇的洞穴,涌出细微的光的声音/无人可听”(《微光》)。“过去”意味着时间,承载时间的只有肉体这只“器皿”,其中的存在感由诗人明确了下来;而诗人的“嘴唇”则充满着性暗示的隐喻,幽深的“洞穴”里将会传出“光”和“声音”,那既是对男人说的,更是对女人说的。我们从中隐隐可感受到女人“细微”的绵柔和强大话语的并存,诗人对身体的烛照和感知愈是“细微”,就愈加能够真实地进入自我意识的精神世界。这个感知的过程,恰恰是借助肉体的“想象与理解”来实现的一种美学建构,而并非纯粹肉欲的解构。这是梅依然诗歌的一个陷阱,一个让读者容易误入的雷区。
肉体于每个人而言都只有一次。集母性与美于一身的女人,其肉体天生神秘而被赋予更多的想象,这还暂且没有考虑“性政治”的因素。自古红颜易老,平添无限哀愁。当女人在精神上对自己的肉体一再敏感之时,其肉体则在时间的打磨中无异于一次孤独的旅行,而这个旅程定当“短暂且充满艰险”。从对肉体的感知和体验中,诗人竭力探寻生活的本质;在排斥现实和拥抱生命的悖论之余,诗人在寻找着快乐与现实的融合,以及本能与道德的某种和解;在存在与虚无、爱欲和与时间的对抗之中,诗人一直都在采撷生活缝隙间的诗意和生命的存在感。而这一切,既是充满“局限”的女人所做的“一个并不完满的梦”,又是肉体承载着的灵魂的一次孤独之旅。
在梅依然的这本集子中,直接出现“肉体”字眼的诗有25首,与性意识和性体验直接相关的达17首。如果加上其他暗示性的同类诗歌,数字还会大幅增加。不过,已有的统计数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肉体”就是梅依然这本集子中的核心意象。一般而言,在小说叙事性文本中大谈肉体和性体验是为人所忌讳的,遑论以精致、美、情感升华见长的诗了。对梅依然诗中所出现的性和肉体,我们看不到类似于“下半身”“垃圾派”“废话诗”一类的粗鄙性存在,反而更多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人性深处的欢乐和痛苦的交集,以及超出性和肉体之上的诗性哲语。
且看:“我把黑色的头发、眼睛、鼻子、红色的嘴唇/甚至是乳房、河流、古老的洞穴/全部奉献给你/啊,我多么嫉妒它们/能够得到你的爱抚/——却独自抛下我的一颗心在别处”(《轨迹》)。这类诗充分表达了对灵与肉分离之际的无奈。不过,诗人透过肉体传达出来的对爱、性的体验都浸溢着独特的感受。在此不妨举再举几例领略一番:
表达对爱的渴望:“我铺展自己/像一段旅游线路/有亢奋的起点和戛然而止的结尾/又像一把放弃演奏的旧日的大提琴/不再发出一个噪音/我辗转于晦暗不明的光中/只等待一列呼啸的火车驶过/碾碎我这微小的肉体”(《夜宿洪安小镇》)。
表达对爱憧憬式的满足:“当时间坚硬的胸膛变得温柔/紧贴在我的身上/我的眼睛微微眯起/我们共同完成了最后一次冲浪/啊,什么是爱?/当我们安静而疲惫地睡去/——世界圆满而仁慈”(《奏鸣曲》)。
表达对爱决绝式的赞美:“当我们分开/我们为什么感到失落/一具空空的肉体/男人和女人是否应该/死在做爱的途中/或是爱上的瞬间/爱——才会具有震颤的效果?”(《爱》)
以上描述基本上能涵盖梅依然假借肉体名义来表达女性自我存在的体验。其思想大胆而热烈,言辞俏皮却忧伤,态度犹疑又决绝,这些都能够充分体现梅依然诗歌的独特性。不过,诗人在性体验之下所表达出来的“自我”存在感,应该有其更为深刻的内涵和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这种“个人表达”做出尝试性的分析。
第一,“精神的肉体化”。梅依然的诗,善于将肉体置于精神与外部现实对立面诸要素之间并将其动态化,从而最终实现对立中的统一。诗人或许面临太多现实中的失望,才以另类逃避方式以寻求内心的某种平衡,而自我肉体终成为一种最令人清醒而真切的“表述方式”。从而,精神的物质化或肉体化就成为诗人调和精神与现实矛盾的策略性选择。
第二,将肉体的隐秘性进行语言的物质化,以表达生活的本质。压抑成为现代人的常态,现实在很多时候是扭曲和变异的,正如尼采说的:“世界早已成了疯人院”。基于此,诗人才会踅入肉体的隐秘性之中以求表达另类的生活本质。人的存在本质上是对快乐的追求,而不是痛苦的替身。当诗人从所面对的现实中不能获得快乐或幸福感时,就会另寻出路,以求摆脱精神困境和获取另一个多变、复杂的快乐来源。于是相对隐秘的肉体和爱欲,就成为一种形而下意义上的诗意表达,而诗本身又是形而上的,如此一来,诗歌的内涵也就形成了一种较为强烈的悖论式的张力。从以上所举的例子来看,由时间所贯穿起来的肉体体验,恰恰能使诗人的精神世界渐次丰盈起来,其存在感也就愈加强烈而得到伸张。
第三,“超我的反动性”。诗人一味以肉体来表达生活是相当冒险的,这与受社会和文化影响的“超我”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关系,毕竟强加于生命个体的“外在约束”充斥着现实和精神的双重世界。听命于一切的“超我”在梅依然的诗中不断冒现,爱欲层面上常有的负罪感和道德甲胄也常使诗人陷于沉重的负累之中。然而,诗人的勇气却又在不断上升,隐藏于诗行中的反动性力量也在不断增强,为了让时间和美好一道驻留,诗人外在柔弱的表达却不时迸射出耀眼的火星。
其实以上所述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表达我存在”。诗人终究是在文字中追寻一种生命诗意的存在感,并以此与生活中如影随形的虚无感相抗争。黑格尔和海德格尔都对虚无进行过阐述,萨特却理解得最为彻底。其中,萨特专章论述过“身体”(这可以具象化为梅依然诗中的“肉体”),指明了“人为性”存在的“身体”和“为他的身体”。诗人在诗中,是否也在构建着一系列“人为性”的肉体和“为他”的肉体呢?只是这趟心灵之旅未免过于孤独了。诗人似乎在为众多年届中年的女人代言,为肉体正在走向终点的路途中加速磨损而惋惜,在女人所经历的独特的时间感受中抒发诗情。所以,这部诗集,无异于诗人在一个单独房间里做着“不完满的梦”,在反对时间之流的行程中做着不懈的抗争,如此才能把握住此诗篇的存在感觉。
三、时间之下肉体的消解和灵魂的救赎
时间与肉体
一种完美的结合
(梅依然:《时间与肉体》)
梅依然在一首诗中写道:啊,作为女人/我们的局限在于:/在一间自我的房子中/做着一个并不完满的梦/——我们的旅程短暂且充满艰险(《永生》)。谁敢说,人生不就是一次孤独的旅行呢?尤其对于诗人笔下存在“局限”的女人而言,做着“不完满的梦”的旅行将会更加凄清、短暂和“充满艰险”。我们不妨设想,身体和灵魂必有一个在路上的话,那么身体和灵魂合为一体的时候呢?或者说,肉体作为灵魂的真实载体且如此可感可触的时候呢?谈论这些的时候,面临诗歌在阐释生命本真的时候,真的能够让人产生惊心动魄之感。因为,当人真切意识到孤独、局限和不完满的时候,恰恰会让人同时意识到活着的意义,尤其是承载着一个女人命运的意义。
当女诗人意识到灵魂的孤独之时,贯注在诗行中的意味将会更加悲怆而决绝。这或许正是诗人将肉体和灵魂紧紧绑系到一起的又一深层原因,惟其如此,肉体与灵魂才能同在。在这种情形之下,肉体才如灵魂射出的唯一一颗真实的子弹,在短短的人生射程之内,瞬间的旅程眨眼即可结束,而同时击中的却是诗人和读者两颗共颤的心。在这个意义上讲,梅依然的确是一个能将肉体和灵魂合二为一的诗人,她将肉体和灵魂以诗的形式或名义结合在一起的心理历程,又的确无异于一次深沉而孤独的旅行。这让人想到美国惠特曼的诗句:“我是肉体的诗人/也是灵魂的诗人/我占有天堂的愉快/也占有地狱的痛苦”(《肉体的诗人和灵魂的诗人》)。我在想,惠特曼的诗句是否正可作为梅依然诗歌的注脚呢?
不过,千万别以为梅依然的诗只是出于一个女人的呓语,我们只能说在她看似指向不算太复杂的诗中隐含了太多的东西。一个女人借助文字的火山口,所喷发和透露的内心世界,或许比我们游身其中的现实更为博大,这就犹如没有谁能够理解一只从未停止过歌唱的蜜蜂过着怎样的秘密生活。我们不得不感慨,作为女人的命运,承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女人所面临的可能比男人要面对的复杂得多,其命运的复杂性无异于又一道斯芬克思之谜。理解梅依然的诗尤如猜谜,极容易走入意识的误区,又极容易跌入其文字的迷宫而难以自拔。不过,其谜底仍然是“人”,只是梅依然的这个谜底具体到了“女人”,并且是一个在时间中穿行、忧伤并确立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的女人。想想这一切,就让人心惊肉跳,举步维艰。难怪有人说,读者和作者一样,当面对文本建构和理解文本之时,都一样地经历着一次次灵魂的历险。
“如果,你不能给我和睦与爱情,那么就给我苦涩的名声”,安娜·阿赫玛托娃在诗中如此写道。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作为一个女性在社会、家庭、婚姻、爱情中所负载之多、之重,是何其令人扼腕感叹!在人心不古,麻木和冷漠的现实人际关系中,梅依然采取了一种迂回向上的姿态,始终信奉茨维塔耶娃所说“用心灵的深邃来保证自己的与众不同和自给自足”。
如果对梅依然的诗歌只作浅表化的猜测和理解,我们就只能游离于其文字之外,挠诗歌之痒。诗人所信奉的,也是她在诗中所着力追求的。那么,“心灵的深邃”“与众不同”“自给自足”都将成为解读梅依然诗歌的一把把钥匙,尽管对这些钥匙的使用有时只是做出一些努力的尝试。比如说,诗人在这本集子中 (其实也包括以前的两部集子),肉体和爱欲成为经常晃动在眼前的一种“现实”,如果我们只是停留于此,就不可能理解诗人的灵魂轨迹和“逆向性”的渴求及其抗争。或许她要求的十分简单,没有宏大诗歌建构的野心,也不做故作高深的宇宙思考,而是将一颗诗心彻底地钉入社会、家庭、婚姻、爱情诸多关系交织的纽结上,然后在诗行中做着无尽的稀释和洇染。鉴于此,我们在读梅依然的时候,就不能够忽视其诗中无处不在的肉体与时间的关系,也不能忽略她诗歌中另一个核心意象:死亡。
我们就是那必死之物 (《界限》)
她们诞生,她们死亡/——无人干预(《生活》)
你成为一个“突然的”/或“可怕的”事件/死亡的宗教/我们终于光顾了它 (《来临》)
“默默无闻”/这是我们奔赴死亡的形式/无关事件本身/我所表述的/和政治几乎不相关/而是关于情感的统一 (《一月的田野》)
像父亲和母亲的爱/始终照看着我/并带着我消失——/死亡每一天都会降临(《比喻》)
……
我们甚至可以说,梅依然在诗中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死亡;或者说,有多少肉体,就有多少死亡。诗人是如此沉迷于对死亡的诗意透析,犹如CT核磁共振在检测身体重要器官的任何病变一样,她执著于人性混乱之中对爱情、婚姻、家庭的深度思考。这一点无疑也构成了梅依然诗美追求的重要内核,以至于她直接写出 《死亡的感觉》《死亡的艺术性》一类的诗。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的“超我”(superego)是受社会和文化制约的道德良心和自我理想,其本身是孤独而完善的。诗人在诗中所表达的,我们不能误解为性幻想或者色情,而是寄托了诗人的孤独、忧伤、痛苦、愤怒……的情感,以及对和谐家庭、婚姻和爱的无限憧憬。与“超我”相矛盾的是爱欲本质上是放荡不羁的,这可以作为人的一种本能来理解,而且一般而言性本能也易受时空的限制。从诗中让爱共生死的表述来看,实际情形却往往令人感到不如意甚至是绝望。如果从整体来看梅依然的诗,隐隐传达出某种人类共性的“性反常”意味,这恰恰是对现实男女精神世界的高度概括。
由此一来,人的消失也就不仅仅是肉体的消失那么简单,而是让人爱欲本能和死亡本能实现了最终的融汇。甚至,从诗中的决绝态度来看,爱欲最终是屈从于死亡本能的。这种表达的结果又形成了新的“超我”,也即死亡可以捍卫某种道德感,于是死亡本能又降服于爱欲了。这或许正是诗人纠结与彷徨于爱欲 (以男女之爱为核心的婚姻和家庭)与死亡两者之间的本因。在这种分析之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诗人是如此那般沉醉于时间的感受,爱欲是时间的永恒,而死亡则是对时间的终止。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人性的焦虑、生命的存在感和诗性的张力得以生发。从诗本身的角度来看,死亡美学成为梅依然诗歌美学整体追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成为洞窥梅依然诗歌蕴含的一个有效切入口。
不过,在梅依然对爱欲和死亡的对立而又统一的诗性书写中,我们可看出诗人对生命深沉的热爱以及对生命的无限敬畏。惟其热爱,才渴望;惟其渴望,才焦灼。在这些情绪波动中,诗人的诗绪得以升华并产生了深不可测的孤独感,以至于她在不同诗中一再发出那些古老的天问:我是谁、你将到何处去。诗人在排斥现实和拥抱生命的悖论之中,透过时间和肉体的缝隙,她终于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救赎,并使时间和肉体得以完美地结合。
读完梅依然的 《蜜蜂的秘密生活》,我无意以一个评判者的身份轻率地做出任何判断。实际上,梅依然诗歌的哲理性相当深刻,她的绝大多数诗歌几乎都寄寓着有意识的哲学思考。读她的诗,委实是一个与诗人、也与自己的心灵秘密交流的过程。这或许是又一次灵魂的历险,然而却是一个充满意味、意义和收获的情感体验过程。读梅依然的诗,还是一次独特的语言体验和不断迎来惊喜的过程。梅依然的语言是充满诗意的。新诗虽为自由体,但并不是简单的分行。诗的句子如果太有逻辑性和连贯性,过于平衡而缺少跳跃性,那么分行和不分行的意义都将不明显,如此诗的形式感就不强烈。梅依然的诗,尽管日常化的口语随处可见,然而我们从中却能够感受到诗人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种超乎寻常的语言驾驭能力,从而其诗读来诗意浓郁而又充满另类意味。梅依然的诗除了哲思和语言为其特色之外,画面感也很强。“她举起一只手/一个不明含义的语句/并不期待我们的理解/另一只手悄无声息地垂下/害怕引起过多关注”(《古城》),她的此类诗歌,无意中融入中国传统诗歌的诗画技巧,并超出了传统意象的建构模式,更为贴近现实生活而能够为人所感受。且在诗歌中还注入了日常叙事成分,这又使得她的诗歌的生活气息更为扑鼻而充满生气。梅依然的诗充满奇思妙想:“床头钟表滴嗒/像没有拧紧盖子的大海/不停渗出的水滴漫进房子里”(《等待》),这样的诗句在集子里比比皆是,读来饶有诗意而又充满雅趣。
或许,梅依然的诗还有我们未曾发现的更多秘密。我们又有多少人能透彻理解“蜜蜂的秘密生活”呢?我们除了注目,还充满期待①本文主要参考文献:梅依然的《蜜蜂的秘密生活》,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黑格尔的《美学》,商务印书馆,2016年;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
On Chongqing Poetess Mei Yiran’s Poetry Creation--Taking Mei Yiran’s Poetry Anthology Secret Life of Bees as Starting Point
ZHOU Hang
Research Center of Chongqing Contemporary Writers,College of Literature,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8100,China)
Chongqing poetess Mei Yiran has been productive in these years.She has composed a lot of excellent poems and has been well recognized in the field of poem.By interpreting her recently published poetry anthology Secret Life of Bees,we can roughly summarize the features of her poem creation.Firstly,the poetess,in the gesture of a woman,reaches the inner world with poetic words to touch the existence of life.Secondly,the poetess tries to avoid emptiness to catch the significance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in the flow of time and life.Thirdly,the poetess considers,for example,death and love with philosophical thinking concealed in her poems;she does not moan miserably on superficial level,but aims to mend the gap of love,death and nihility and to anticipate meeting the soul of the readers.
Mei Yiran;Secret Life of Bees;death;love;sense of existence
I207.2
A
1674-3652(2017)05-0092-06
2017-03-25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期以来重庆乌江流域诗人群研究”(2016YBWX076)。
周航,男,湖北咸宁人,博士,博士后,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诗学研究。
[责任编辑:志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