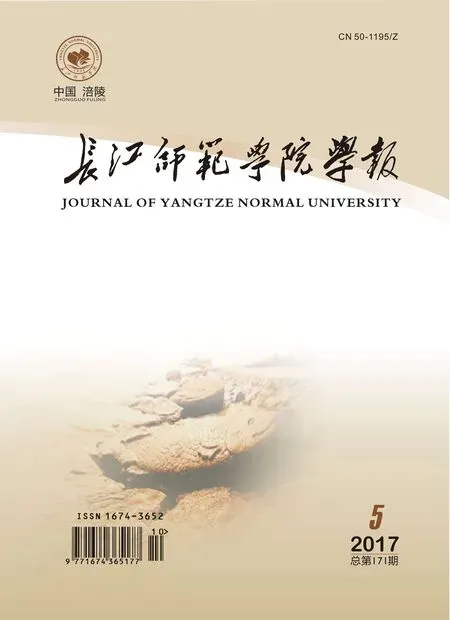巴·彭·板楯蛮·賨
薛宗保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四川 达州 635099)
巴·彭·板楯蛮·賨
薛宗保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四川 达州 635099)
巴地、巴人、巴国有不同的含义,巴地族群因战乱而迁徙。晋文公灭巴子国,汉水流域的“彭人”等族群南迁与当地族群融合后,世人泛称“板楯蛮”。秦人将巴地人群称呼“赋”的语音记为“賨”,汉代,将呼“赋”为“賨”的巴地人泛称为“賨人”,川北、川东、川南 (渝东南)均有文献记载。賨,不能简单定义为民族。
巴地;巴人;彭;板楯蛮;賨
一、古代的巴地
巴,是一个泛指的地名,一般人们将四川东部称巴。甲骨文中有卜辞“巴方”“虎方”,系指汉水中游的巴人族群。《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其地,东至鱼腹,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如此,“巴”就是广袤数千里的大国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由氏族到部落,由小国到大国。以华夏历史而论,夏有万国,殷有三千,周有八百,到战国时期才出现方千里、方三千里的大国。僻处华夏西陲山区的古代四川,是不可能有如此统一的大国,何况还不包括江汉流域的姬姓之巴人、彭人,丹、淅间的孟涂之巴和清江流域的廪君之巴以及云梦泽国的夏羿屠巴蛇之巴。按常璩 《巴志》中说的巴地氏族或民族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其实,这些相近又相异的民 (氏)族,就是相对独立的邦 (方)国或部落势力集团,后世以民族发式、服式、葬俗、居住等特征异同,通称为“百濮”或西南夷。因此,有学者指出:“先秦时期的巴地,既不曾有过一个统一的巴国,也没有一个同一的巴族,甚至找不到一个被命名为 ‘巴’的民族,在这里长期存在着多个分散的部落 (氏族或方邦)国家。”[1]
二、周封姬姓之巴
《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 《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但 《尚书·牧誓》却记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参加牧野之战宣誓的没有明确列有巴人,但所列八属却多是在巴地。蔡沈注释是: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武王伐纣,不期会者八百国。今誓师独称八国者,盖八国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约束以战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则泛指诸侯而誓者也。
近代考古发现,汉水中上游出土的殷周时期青铜器物,有明显的蜀、巴文化特征。如:以城固青铜器群为代表的蜀文化,宝鸡市茹家庄、竹园沟等地出土的 ()国器物与都蜀文化渊缘深厚,可以佐证汉水上游一部分当时是蜀的势力范围。《巴志》云:“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周武王封姬姓宗族于汉水中游,管控剽悍的彭人族群。其一是因彭人的战功;其二是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因为这里夏商时曾被称作虎方或巴方:《殷契粹编·1230》记:“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沚巴方”;沚,山西西南,汾水以东;,伐;有又,有佑。《殷墟文字丙编·313》记:“□□卜□贞王佳妇好,令沚巴方,受有又。贞王勿佳妇好,从沚伐巴方,弗其有又。”《殷墟文字乙编·5280》记:“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沚巴方,王自东受蚩,阱于妇好立。”还有多枚甲骨卜辞记载伐虎方、伐缶、伐蜀。周初封姬姓宗族于“巴”,其王称“巴子”,与其他“汉阳诸姬”一样是护卫周王朝的南部屏障。《左传·昭公九年》载周大夫詹桓伯说,自武王克商以来,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即是例证。周封巴子国于前632年,在晋文公联合秦、齐、宋诸国攻楚的“城濮之战”中被捎带灭掉。亡国的标志是解除王权,杀戮不是目的。之后,数百年间仍有“巴人、巴师、巴国”的记事。如 《左传·文公十六年》载:“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左传·哀公十八年》载:“巴人伐楚围鄾……巴师败于鄾”;《巴志》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战国策·燕策》载:“楚得枳而国亡。”“楚得枳”是巴地的势力集团全部覆灭的拐点。所以,此巴非彼巴!多个“巴”恰好表明了巴地是多氏族、多民族的聚居地,也因此巴地才有多个不同的“军事集团”。姬姓巴国灭亡之后文献记述的“巴”多居川东长江流域左近,其消亡的时间也不同。
三、彭
巴地是多民族构成且有别的势力族团,由 《尚书·牧誓》所列八族可知“彭”所在位置。陕东南,鄂西北一带,西有魏兴 (陕西紫阳)之彭溪,东有新城 (湖北谷城)彭水。卢族活动于湖北南漳县一带,其北邻南河,古称彭水。周初封姬姓巴子国即是此地,其土著民 (氏)族以“彭”为主,而姬姓宗族及随行,则是统治者。彭人之名有二说。其一,源于族人善用的木楯。刘熙 《释名·兵器》卷7云:“盾,遯也。跪其后辟 (避)以隐,遯也。”大而平曰“吴魁”,本出于吴;隆者曰“须盾”,本出于蜀……以缝编板谓之木络,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其所用之名也。巴人用虎皮蒙在盾上称“虎皮衣楯”,亦即虎楯。因讳称虎曰“斑”,斑、板音近而称板楯。殷、周时称楯为“干”;吴越之人称“渠”,如“文犀之渠”;巴地呼为彭排或彭旁,故多用“彭”名之物事。其二,源于地名。彭人聚居地多称彭溪、彭水。如张澍在 《蜀典》中指出,彭,即彭水夷。晋文公灭巴子国后,新崛起的秦楚在汉水流域拉锯争夺,迫使汉水流域的巴人族群迁徙。彭人一部分南越巴山,一部由汉水南下武陵山区。分别融入到当地的土著民族中。更有“荆人鳖灵”及苴、蜑等族系溯岷江而上至郫,入广都,进而夺取了杜宇王朝的统治权,建立了延续十二世的开明王朝[2]。
四、板楯蛮与賨
大巴山南,带有彭字的地名亦不少。《汉书·地理志》载:阆中有彭道将池,彭道鱼池。《水经注·沔水》载:有彭溪自今城口北至紫阳注入汉水 (今任河)。《水经注·江水》载:有彭水经今开县、云阳双江镇彭溪口注入长江。巴黔中亦有彭水 (县),小地名亦有彭水、彭溪。这些带彭字的地名,是彭人南移后出现的还是之前就有,难以考定。按古人迁徙有“名随人走”的习俗,已能佐证彭人南移的史实。姬姓巴子国灭后,越过巴山的彭人,融入大巴山南麓的其他氏族中,仍是一支剽悍的族群,因善用板楯而被中原人称作板楯蛮。所以,板揗蛮应是姬姓巴子国覆灭后,对巴山南麓彭人与原有土著氏族融合后的泛称;之后,为向秦人交纳贡赋,而称“賨”。以“賨”名人,则起于汉。賨,可以是对一个区域族群的泛称,但不是一个民族学意义上的名称。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之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出义赋一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
秦灭巴蜀之初,除主要城邑之外,邑民居住地难以实际控制,于是政府在行政制度上采取分封、移民与郡县并行的策略,即“封侯置郡”“县吏驭民”。《水经注》载:“七国称王,巴亦王焉。秦惠王遣张仪等救苴于巴,仪贪苴、巴之富,因其执王以归,而置巴郡焉。”这个“巴王”就是巴地原有势力集团的代表,但不知其姓氏,是居阆中或是江州县亦难断定。《舆地纪胜》卷185引 《九域志》曰:“阆中古城本张仪筑也。《图经》云,秦司马错执巴王以归;阆中遂筑,有张仪庙存焉。”若其居阆中,与苴近,苴求救及时。且文献述及“板楯蛮”的军事力量亦在这一带。如 《水经注》载:“江州县,故巴子之都也。周慎靓王五秦灭巴,旋置郡,张仪筑江州城。”则应是江州县,但往救于苴不能及时。文献记述相悖,是因所据和见解不同。参考谢元鲁的《罗家坝巴人遗址与川东北旅游形象再造》所述:2003年第二次发掘罗家坝墓葬,32座墓葬中28座墓有随葬兵器,死者皆战伤,年龄30-40岁,男性居多,老小则少,其中M15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有矛、剑、钺、箭镞。墓主人盆骨、股骨处有6枚箭镞插入骨中,为箭伤致死。M5墓主头、股、体右分插有箭镞,足见战斗惨烈[3]。故有学者推测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晚期,与秦张仪等灭巴有关。因此,从秦设郡和控制地方势力角度考虑,被执以归的“巴王”居阆中显系合情。
进入四季度以来,小麦市场行情与上年同期相仿。虽然理论上市场流通粮源好于上年,但高质量小麦滞留不多,加之持粮主体看好后市,惜售心理较强,阶段性供需状况依然偏紧,主产区小麦价格持续高位偏强。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板楯蛮》载:“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 (所记事有以虎寓人之义)。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倾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夷人安之。至高祖为汉王,(惠栋 《补注》:阆中人范目)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表明汉初郡县制度下,氏族或姓氏集团势力仍具有强悍的战斗能力。《魏书·董绍传》载:“董绍字兴远……萧宝夤反于长安也。绍上书求出之,曰:臣当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肃宗谓黄门徐乾曰:此巴真瞎也?乾曰:此是绍之壮辞,云巴人劲勇,见敌无所畏惧,非实瞎也。帝大笑。”巴人之悍勇,此处生动可见。而这些军事力量分布在阆中、宕渠一带。这一点,从具有地域、民族特点的“巴渝舞”的传承可知大概。
《汉书·礼乐志》载:“巴俞鼓员三十六人。”巴渝舞在表演时演者披盔甲,持弩箭,用民族语言唱古老的巴人战歌。杜佑 《通典》卷145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安台、弩渝、行辞四章,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
《后汉书》载:“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盐铁论·刺权》中记:“贵人之家,中山索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汉代的巴渝舞已演译成为豪门贵族居家观赏的舞曲。《通典》卷147记:魏文帝黄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舞。之后,这一民族艺术即鲜见于文献,而舞无所观。
渝水,早期称阆中以上的水系,后称巴水,再称嘉陵江。其源头之一在陕西宝鸡,出于秦岭南麓,还有数支发源于米仓山麓,一支经旺苍汇入阆中。
唐代颜师古注 《汉书》载:巴,巴人也。俞,俞人也。当高祖初为汉王,得巴俞人,并趫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因存其武乐也,巴俞之乐因此始也。巴即今之巴州,俞即今之渝州,各其本地。
《舆地纪胜》卷162载:“巴西宕渠,其人勇健好歌舞,邻山重叠,险比相次。古之賨国都也。”(此句有误。实为宕渠城,其遗址又名土溪城坝,在渠县土溪乡渠江东岸。前314年,秦在此置宕渠县,东汉中期是宕渠城兴旺发达的盛期,车骑将军冯绲曾扩建此城,故俗名车骑城,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宕渠县治迁渠江镇。)
汉以后的文献,没有提及彭人南移的实情,记录的是秦灭巴蜀之后巴地的人和事。因而形成了板楯蛮即賨,助武王伐纣的巴师即賨人之师的认识。
賨。《说文》载:“賨,南蛮赋也。”《魏书·李雄传》:“巴人谓赋曰賨,因为名焉。《蜀录》载:巴人呼赋为賨。”《文献通考·户口》载:“蜀李雄薄赋,其人口出钱四十文,巴人谓赋为賨,因为名焉。”
学者对“賨”有不同的解释。如潘光旦指出賨是巴语。刘琳认为,賨字是根据巴人语言而造的。刘志成则说,巴人不懂赋为何物,见秦人索要钱、布装进口袋拿走,则把装进口袋里的赋称为dzuoη。秦人不懂其音何义,听其每每呼之,遂称之为賨人。后交往增多,知巴人以此音称赋,秦人遂造从贝宗声之字[4]。賨,惟秦人如此呼巴人之别称,故不见于 《史记》《汉书》。至杨雄把此字用在 《蜀都赋》里才渐流传。之后,成为汉人称呼缴纳“賨”的一群人的名称:賨人、賨民、巴賨。
彭秀模考证“賨人”是他称,賨人的自称叫“服孳”,即周昭王时 《宗周钟》铭文:“南国服孳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服孳乃遣间来逆昭王,南夷、东夷具见廿有六邦。”[5]服孳是汉水中游另一个较大的族团 (邦国),或是彭的别称但不确定,但有甲骨卜辞证即虎方。《甲骨文合集·6667》记:“贞,令望乘斜眔舆伐虎方。”《殷墟粹编·1175》记:“丁卯卜,◇贞,王伐缶于 (与)蜀。”意即商王武丁准备征伐缶和蜀。郭沫若早年释“缶”为陕南方国。《四川通志》注晋文公灭巴。《吕氏春秋》载:晋文公西伐巴蜀,晋所灭乃姬姓,秦 (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灭巴)虏乃风姓。折射出缶—虎—服孳南迁的信息。邓少琴在 《巴蜀史迹探索》指出:楚语虎读为於 (读“wu”)菟,於菟急读则为土。土家族崇虎,自称毕兹卡,意即当地人。毕兹为服孳之变,意即土;卡,即家。因此土家族先民可能源自汉水中游[6]。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载:射虎的阆中夷人,世号“白虎复夷”,曰“板楯蛮”。“白虎服夷”及前文“复夷人”应是服孳夷的别称。
综合上述,虎方—缶—巴方—彭—服孳南迁后与巴山南麓土著相融合的脉络大致清晰。
称赋税为“賨”的不仅仅是在大巴山之南的地区。《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载:“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两丈,是谓賨布。”賨布是賨人所生产,以布代赋。《永顺府志·物产》载:“棉花,所产可给本境织成布,皆粗厚。汉时令蛮输賨布,大人一匹,小口二丈。”宋时辰之诸蛮与保靖、南谓、永顺三州接壤,蛮酋贡溪布,即此类。賨布也称“幏”。《说文》载:“幏,南郡蛮夷賨布也。”《风俗通》载:“盘瓠之后,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布。”廪君之巴氏出幏布八尺,幏亦賨也,故统谓之賨布。巴地许多地区有别的民族称贡赋为“賨”,从另一角度佐证了“賨”不是族名。
四、关于 《巴志》中的资料
研究、宏扬巴文化,考古发现的文物资料是重要的佐证;而从 《巴志》《汉书》《后汉书》等文献中摘录资料,一部分却需从文献记录的事件、时间、地点以及比对相关资料进行佐证。
常氏编簒 《华阳国志》的背景,诚如任乃强所言:“永和三年,桓温伐蜀军至成都,璩与中书监王嘏等劝(李)势降晋,随势徙建康。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璩时已老,常怀亢愤,遂不复仕进,裒削旧作,改写成为 《华阳国志》。主要内容自周至晋,时间跨度移大约1 500年。其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颃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7]
常璩力述巴蜀自古以来皆为华夏一员,与中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频举巴蜀的先贤士女,就是要向东晋士族表明,包括自己在内的巴蜀人士,丝毫不比东晋的所谓名士差。这一点在其 《后贤志》的结语中说得更明白:“文王多士,才不同用。孔门七十,科揆百行。殊涂贵于一致。若斯诸子,或挺珪璋之质,或苞瑚琏之器,或耽儒、墨之业,或韬王佐之略,潜则泥蟠,跃则龙飞,挥翮扬芳,流光遐纪,实西土之珍彦,圣晋之多士也。徒以生处限外,服膺日浅,负荷荣显,未充其能。假使植干华宇,振条神区,德行自有长短。”为彰显益州地、人、事的影响,常氏还在全书体裁、结构上煞费苦心,采取历史、地理、人物和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相结合的方法撰写。因创作目的激愤,且记述时间跨度长,有的内容模棱两可,有些内容则难免有拔高的痕迹,引用时须认真辨析。
[1]蒙默,刘琳,唐光沛.四川古代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29.
[2]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33.
[3]谢元鲁.罗家坝巴人遗址与川东北旅游形象的再造[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31-35.
[4]刘志成.释賨[J].古汉语研究,1992(2):9.
[5]彭秀模.“服孳”考[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4):24-29.
[6]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30.
[7]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
K203
A
1674-3652(2017)05-0088-04
2017-05-06
薛宗保,男,重庆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学、区域发展研究。
[责任编辑:庆 来]